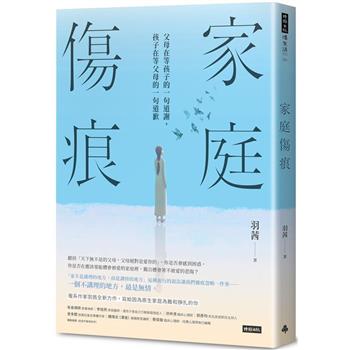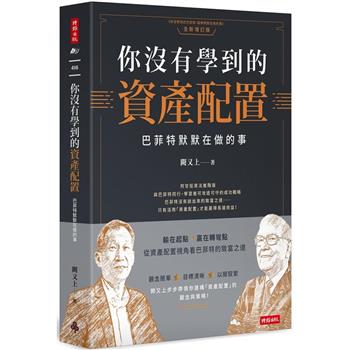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新譯尸子讀本(二版)的圖書 |
| |
新譯尸子讀本(二版) 出版日期:2021-11-26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2 |
Books |
$ 315 |
社會人文 |
$ 351 |
中文書 |
$ 352 |
中國哲學 |
$ 352 |
Other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新譯尸子讀本(二版)
內容簡介
尸子,是商鞅變法的得力顧問。商鞅作法自斃,促使尸子對法家思想進行反思,進而發現了其中的不足與弊害,遂起而破除學派壁壘,摒棄一家一派之偏見,以更高一層次的立場,宏觀而客觀公正地看待各家各派的長短曲直,以各家之長,融為一體,著成《尸子》一書。今本《尸子》殘缺,全貌已不可復睹,然所剩殘篇已足窺見其綜合各家所長之特色。本書考訂以得原文之真者為準,而不拘於一家,並力求注釋與語譯淺白易懂,以供讀者大眾參考研究之用。
目錄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導讀
勸學一
貴言一九
四儀三三
明堂三七
分四七
發蒙六一
恕八一
治天下八七
仁意九九
廣一○九
綽子一一九
處道一二七
神明一三五
止楚師一三九
君治一四七
佚文一六九
導讀
勸學一
貴言一九
四儀三三
明堂三七
分四七
發蒙六一
恕八一
治天下八七
仁意九九
廣一○九
綽子一一九
處道一二七
神明一三五
止楚師一三九
君治一四七
佚文一六九
序
導讀
一
尸子,名佼,是我國戰國時期的一位學者。其人最早見述於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楚有尸子、長廬。」但只說他是楚人,餘皆略而不言。其後劉向《別錄》則云:「司馬遷言『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劃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裴駰《集解》引)劉氏之言,使我們得以知道尸子生平的主要經歷與其著述之情況。班固《漢書‧藝文志》「雜家」類有「《尸子》二十篇」。自注云:「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指其為「魯人」,與劉氏異。尸佼究為晉人,抑或魯人,或如宋翔鳳所云:「『晉』乃『魯』之誤。」由於缺乏可資論證的根據,故只能暫付闕如。
劉向所言,另為我們了解尸子的學術思想及其演變提供了有益的線索。尸佼本為商鞅之賓客,是商鞅在秦實行變法的得力顧問,則其學術思想無疑當屬法家。商鞅被誅而佼亡命於蜀,然後撰著其二十篇之書。班固《漢書‧藝文志》將其書歸入「雜家」。所謂「雜家」,如班氏所云,乃「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道之無不貫」。據今所傳《尸子》觀之,正與之相合。有鑒於此,我們似可作這樣的推測:尸佼本為法家,及至商鞅罹難之後,使他對法家思想進行反思,發現了其中的不足與弊害,因此變而吸收各家之所長,將之融為一體,從而實現了他學術思想上的重要轉折。
商鞅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他自西元前三五六年被秦孝公任為左庶長而在秦國全面推行變法,至前三三八年孝公死而慘遭車裂為止,前後共十八年時間。在這十八年中,尸佼是否一直作為商鞅的高級參謀,已不可知。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尸子在學術思想上曾給商鞅以一定的影響。這從今所傳《尸子》與《商君書》(此書非商鞅自撰,而出於法家者流掇拾商鞅餘論而成)中是可以窺見其端倪的。如尸子對於君主之治國,十分強調正名分,這一點,在〈發蒙〉中說:「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群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又云:「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商鞅亦注重名分,《商君書》中有〈定分〉云:「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可見他們是一脈相承的。
然以《尸子》之總體思想而論,則分明是「兼儒墨,合名法」的。
如他對於孔子是推崇的,並多方面吸取了儒學之所長。在〈勸學〉中稱讚孔子是使人至善成材的賢師。他多處將孔子之言作為至理之言加以引述(見〈處道〉等篇)。儒家認為君主治天下當先行修身。此為尸子所重視,故他在〈明堂〉中說:「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處道〉又引述孔子之言:「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四儀〉中則以「仁義忠信」作為為人之「四儀」,並言「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在〈恕〉更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道奉為為人處事的典則。儒家特別注重民心,認為民心向背關乎興衰存亡。尸子於此亦有所取法。如云:「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皆見佚文)此外,他還主張以「孝親」、「忠君」、「信義」去觀人之品行(見〈分〉)。顯然,這正是儒家所倡導的品行。凡此,可見他吸取儒家思想是多方面的。若以分量而論,則它在今所傳之《尸子》中的比重也是較大的。《後漢書‧宦者列傳‧呂強傳》唐章懷太子李賢注云:尸子「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可見原本《尸子》亦復如是。然而,尸子對於孔子亦有貶辭。〈廣〉以「孔子貴公」為「弇於私」之弊。此所謂「貴公」,即貴君,是以君為貴之意。尸子以為若能秉之公心,則能以天下為貴了。
尸子也推崇墨子為賢者(見〈貴言〉),而他對於墨子「兼愛」思想的吸取與闡發更令人矚目。「兼愛」是墨子學術思想的核心。他主張人與人之間要相親相愛,反對人為「自利心」所驅使,而做出損害他人、他家、他國的行為。尸子承此意而云:人無「公心」,則必致「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之結果。因此,他主張要律以「公心」,具有「兼天下而愛之」的心胸。另外,墨子言「愛」而注重實「利」,將「愛」落實於「利」,以「利」來體現「愛」。這是墨子「兼愛」思想的一大特色。如〈天志中〉云:「愛人利人,順天之意。」〈魯問〉云:「愛利百姓」等。尸子於此,亦深會其意,而云:「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發蒙〉)又云:「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君治〉)「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治天下〉)尸子與孟子同時,在孟子斥罵墨子「兼愛」之說為「禽獸」之道的時候,尸子對之卻有如此識見,亦是難能可貴的了。能行「兼愛」,必由「公心」,此理易明。然尸子卻云:「墨子貴兼」,亦為「弇於私」。此當為失言。《尸子》中有〈止楚師〉一篇,記述墨子止楚攻宋的事跡並加以贊頌。於此,亦正可見尸子對於墨子兼愛無私精神的充分肯定。除此而外,墨子還主張「節葬」而抨擊世俗「厚葬久喪」之流弊。尸子亦云:「禹之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舜西教於西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見佚文)與「節葬」說幾無二致。
對於法家學說,尸子仍認為為治政所不可缺。故他除強調正名分,「以實覈名」而外,又極主行賞罰,並認為這是君主「獨斷」之權。他說:「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發蒙〉)以為「刑罰」,對人民可起到「鞭策」之作用(見佚文)。
二
汪繼培云:「劉向《別錄》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八,可為嘆息。」《尸子》全貌已不可復睹,但僅據此十二之文,已可窺見其綜合各家所長的基本取向。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蔚然成風,使我國學術界初次出現活躍繁榮的局面。然而,學派的形成,人囿於學派之見識而對別的學派採取不相容的態度,畢竟是有礙於學術之發展的,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在此種學術背景下,有能破除學派之壁壘,摒棄一家一派之偏見,而能站在高一層次的立場之上,宏觀而比較客觀公正地看待各家各派的長短曲直,從而取其所長而捨其所短,則不能不說是有識之士的卓異之處,而大有益於學術之發展。所謂「雜家」,就其主體而言,正是適應此種要求而產生的一個新的派別。尸子所論,固然不可能事事皆是,然而這種嘗試與開拓,畢竟是可貴的,在基本上也是成功的。
《尸子》本二十篇。《隋書‧經籍志》云:「《尸子》二十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此書唐時尚全,故《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雜家類」均有「《尸子》二十卷」。但書至宋而殘缺。《宋史‧藝文志》將之列於「儒家類」而僅為「一卷」。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有《尸子》,但不著卷數。此後,則散佚不存。時至清乾隆年間,有任兆麟校本《尸子》刊行。是書乃以其家傳之〈仁意〉、〈君治〉、〈廣釋〉(《爾雅》疏引作〈廣澤〉,任云:「徐廣曰:『古「釋」字作「澤」也。』」)三篇本為主,復取見於惠棟鈔本而為舊本所未見者,以及采錄見於群書之文,編為〈附錄〉一卷。嘉慶時,又有孫星衍等所編的《尸子集本》刻行。孫本所收錄者,一為見於魏徵等所編《群書治要》之〈勸學〉等十三篇;一為見於歸有光所編《諸子彙函》之〈止楚師〉、〈君治〉二篇;再為見於《爾雅》注疏與他書引文。比之於任本,可為詳備。稍後,又有汪繼培湖海樓本問世。其自序云:「繼培初讀其書,就所攬掇,表識出處,糾拾遺謬,是正文字。後得惠、孫之書,以相比校,頗復有所疑異,迺集平昔疏記,稍加釐訂。以《群書治要》所載為上卷,諸書稱引與之同者分注於下,其不載《治要》而散見諸書者為下卷。引用違錯及各本誤收者,別為〈存疑〉附於後。」今比較孫本、汪本,優劣互存。汪本雖有所釐訂,然亦有失誤。故本書所用正文,以得原文之真者為準,而不拘於一家。全書之編次,則依孫本,以十五篇據前而佚文次後。佚文之次序,亦依孫本。其中孫、汪二本皆缺而獨存於任本者,則補錄於後,以使《尸子》之遺篇佚文而尚存者,略備於此。
水渭松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寫於杭州寶善橋寓舍
一
尸子,名佼,是我國戰國時期的一位學者。其人最早見述於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楚有尸子、長廬。」但只說他是楚人,餘皆略而不言。其後劉向《別錄》則云:「司馬遷言『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劃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裴駰《集解》引)劉氏之言,使我們得以知道尸子生平的主要經歷與其著述之情況。班固《漢書‧藝文志》「雜家」類有「《尸子》二十篇」。自注云:「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指其為「魯人」,與劉氏異。尸佼究為晉人,抑或魯人,或如宋翔鳳所云:「『晉』乃『魯』之誤。」由於缺乏可資論證的根據,故只能暫付闕如。
劉向所言,另為我們了解尸子的學術思想及其演變提供了有益的線索。尸佼本為商鞅之賓客,是商鞅在秦實行變法的得力顧問,則其學術思想無疑當屬法家。商鞅被誅而佼亡命於蜀,然後撰著其二十篇之書。班固《漢書‧藝文志》將其書歸入「雜家」。所謂「雜家」,如班氏所云,乃「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道之無不貫」。據今所傳《尸子》觀之,正與之相合。有鑒於此,我們似可作這樣的推測:尸佼本為法家,及至商鞅罹難之後,使他對法家思想進行反思,發現了其中的不足與弊害,因此變而吸收各家之所長,將之融為一體,從而實現了他學術思想上的重要轉折。
商鞅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他自西元前三五六年被秦孝公任為左庶長而在秦國全面推行變法,至前三三八年孝公死而慘遭車裂為止,前後共十八年時間。在這十八年中,尸佼是否一直作為商鞅的高級參謀,已不可知。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尸子在學術思想上曾給商鞅以一定的影響。這從今所傳《尸子》與《商君書》(此書非商鞅自撰,而出於法家者流掇拾商鞅餘論而成)中是可以窺見其端倪的。如尸子對於君主之治國,十分強調正名分,這一點,在〈發蒙〉中說:「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群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又云:「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商鞅亦注重名分,《商君書》中有〈定分〉云:「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可見他們是一脈相承的。
然以《尸子》之總體思想而論,則分明是「兼儒墨,合名法」的。
如他對於孔子是推崇的,並多方面吸取了儒學之所長。在〈勸學〉中稱讚孔子是使人至善成材的賢師。他多處將孔子之言作為至理之言加以引述(見〈處道〉等篇)。儒家認為君主治天下當先行修身。此為尸子所重視,故他在〈明堂〉中說:「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處道〉又引述孔子之言:「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四儀〉中則以「仁義忠信」作為為人之「四儀」,並言「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在〈恕〉更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道奉為為人處事的典則。儒家特別注重民心,認為民心向背關乎興衰存亡。尸子於此亦有所取法。如云:「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皆見佚文)此外,他還主張以「孝親」、「忠君」、「信義」去觀人之品行(見〈分〉)。顯然,這正是儒家所倡導的品行。凡此,可見他吸取儒家思想是多方面的。若以分量而論,則它在今所傳之《尸子》中的比重也是較大的。《後漢書‧宦者列傳‧呂強傳》唐章懷太子李賢注云:尸子「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可見原本《尸子》亦復如是。然而,尸子對於孔子亦有貶辭。〈廣〉以「孔子貴公」為「弇於私」之弊。此所謂「貴公」,即貴君,是以君為貴之意。尸子以為若能秉之公心,則能以天下為貴了。
尸子也推崇墨子為賢者(見〈貴言〉),而他對於墨子「兼愛」思想的吸取與闡發更令人矚目。「兼愛」是墨子學術思想的核心。他主張人與人之間要相親相愛,反對人為「自利心」所驅使,而做出損害他人、他家、他國的行為。尸子承此意而云:人無「公心」,則必致「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之結果。因此,他主張要律以「公心」,具有「兼天下而愛之」的心胸。另外,墨子言「愛」而注重實「利」,將「愛」落實於「利」,以「利」來體現「愛」。這是墨子「兼愛」思想的一大特色。如〈天志中〉云:「愛人利人,順天之意。」〈魯問〉云:「愛利百姓」等。尸子於此,亦深會其意,而云:「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發蒙〉)又云:「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君治〉)「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治天下〉)尸子與孟子同時,在孟子斥罵墨子「兼愛」之說為「禽獸」之道的時候,尸子對之卻有如此識見,亦是難能可貴的了。能行「兼愛」,必由「公心」,此理易明。然尸子卻云:「墨子貴兼」,亦為「弇於私」。此當為失言。《尸子》中有〈止楚師〉一篇,記述墨子止楚攻宋的事跡並加以贊頌。於此,亦正可見尸子對於墨子兼愛無私精神的充分肯定。除此而外,墨子還主張「節葬」而抨擊世俗「厚葬久喪」之流弊。尸子亦云:「禹之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舜西教於西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見佚文)與「節葬」說幾無二致。
對於法家學說,尸子仍認為為治政所不可缺。故他除強調正名分,「以實覈名」而外,又極主行賞罰,並認為這是君主「獨斷」之權。他說:「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發蒙〉)以為「刑罰」,對人民可起到「鞭策」之作用(見佚文)。
二
汪繼培云:「劉向《別錄》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八,可為嘆息。」《尸子》全貌已不可復睹,但僅據此十二之文,已可窺見其綜合各家所長的基本取向。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蔚然成風,使我國學術界初次出現活躍繁榮的局面。然而,學派的形成,人囿於學派之見識而對別的學派採取不相容的態度,畢竟是有礙於學術之發展的,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在此種學術背景下,有能破除學派之壁壘,摒棄一家一派之偏見,而能站在高一層次的立場之上,宏觀而比較客觀公正地看待各家各派的長短曲直,從而取其所長而捨其所短,則不能不說是有識之士的卓異之處,而大有益於學術之發展。所謂「雜家」,就其主體而言,正是適應此種要求而產生的一個新的派別。尸子所論,固然不可能事事皆是,然而這種嘗試與開拓,畢竟是可貴的,在基本上也是成功的。
《尸子》本二十篇。《隋書‧經籍志》云:「《尸子》二十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此書唐時尚全,故《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雜家類」均有「《尸子》二十卷」。但書至宋而殘缺。《宋史‧藝文志》將之列於「儒家類」而僅為「一卷」。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有《尸子》,但不著卷數。此後,則散佚不存。時至清乾隆年間,有任兆麟校本《尸子》刊行。是書乃以其家傳之〈仁意〉、〈君治〉、〈廣釋〉(《爾雅》疏引作〈廣澤〉,任云:「徐廣曰:『古「釋」字作「澤」也。』」)三篇本為主,復取見於惠棟鈔本而為舊本所未見者,以及采錄見於群書之文,編為〈附錄〉一卷。嘉慶時,又有孫星衍等所編的《尸子集本》刻行。孫本所收錄者,一為見於魏徵等所編《群書治要》之〈勸學〉等十三篇;一為見於歸有光所編《諸子彙函》之〈止楚師〉、〈君治〉二篇;再為見於《爾雅》注疏與他書引文。比之於任本,可為詳備。稍後,又有汪繼培湖海樓本問世。其自序云:「繼培初讀其書,就所攬掇,表識出處,糾拾遺謬,是正文字。後得惠、孫之書,以相比校,頗復有所疑異,迺集平昔疏記,稍加釐訂。以《群書治要》所載為上卷,諸書稱引與之同者分注於下,其不載《治要》而散見諸書者為下卷。引用違錯及各本誤收者,別為〈存疑〉附於後。」今比較孫本、汪本,優劣互存。汪本雖有所釐訂,然亦有失誤。故本書所用正文,以得原文之真者為準,而不拘於一家。全書之編次,則依孫本,以十五篇據前而佚文次後。佚文之次序,亦依孫本。其中孫、汪二本皆缺而獨存於任本者,則補錄於後,以使《尸子》之遺篇佚文而尚存者,略備於此。
水渭松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寫於杭州寶善橋寓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