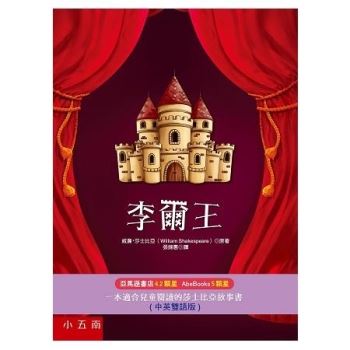在中國小說史中,風行一時的文言言情小說,《遊仙窟》可能是最早的一部,而《玉梨魂》則是最後的一部。上世紀初,一些文學青年寓居上海租界(那時叫做「洋場」),從事創作。由於他們熱衷於言情小說,好寫才子佳人「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蔭花下,像一對胡蝶,一雙鴛鴦一樣」(魯迅〈上海文藝一瞥〉),
有人以「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戲稱當時的哀情小說(平襟亞〈鴛鴦蝴蝶派命名的故事〉),因此稱為「鴛鴦蝴蝶派」。後來這派作者所寫小說的內容不斷擴展,於是又以其早期最有影響的雜誌禮拜六為名,通稱為「禮拜六派」。鴛鴦蝴蝶派不談政事,寄情風月,遊戲筆墨,供人消遣,在五四以後,曾遭到不少非議。不過作為一個歷時甚久、作者眾多、影響頗大的文學流派,不能一概而論,應作具體分析。連魯迅也說:與那些狹邪小說相比,像《玉梨魂》這樣的作品,「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進步」(同上)。
鴛鴦蝴蝶派「作品應當以《玉梨魂》為代表,作者則以徐枕亞為代表」(范煙橋《民國舊派小說史略》)。《玉梨魂》作者徐枕亞(西元一八八九—一九三七年),名覺,別署東海三郎。為紀念亡妻蕊珠,又號泣珠生。江蘇常熟人。虞南師範畢業,曾任小學教師。與兄徐嘯亞(天嘯)俱以詩文知名。加入南社後,與徐天嘯同主《民權報》筆政。民國後自辦《小說叢報》等刊物。《小說叢報》於一九一四年創刊,是創辦僅晚於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的小說刊物。後又在上海創辦清華書局。徐枕亞仗義疏財,好濟人急難,故無積蓄。晚年潦倒,在滬賣文為生,與徐天嘯放浪形骸,以酒澆愁。日軍侵華,為避戰亂,歸居常熟南鄉楊樹園,不久病死。所著小說,除《玉梨魂》外,另有《雪鴻淚史》、《余之妻》、《刻骨相思記》、《燕雁離魂記》、《雙鬟記》、《讓婿記》、《血淚黃浦》、《鴛鴦花》、《秋之魂》、《蝶花夢》等十種,及短篇小說集《情海指南》、《枕亞浪墨》等。
《玉梨魂》寫青年才子何夢霞在一崔姓鄉紳家任教,與崔家年輕貌美的寡媳白梨影相愛,兩人詩信往來,情好日篤。白梨影始終不敢越過「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禮教大防,為擺脫情網,竟想出移花接木之計,撮合小姑崔筠倩與何夢霞的婚事。但何夢霞對白梨影一往情深,矢志不移;崔筠倩也因婚姻不能自主而陷入痛苦之中。白梨影見事與願違,含痛徇情。崔筠倩也悒鬱而亡。遭受這兩重打擊的何夢霞,為謝二人之情,立志報國,在武昌起義中獻身。
《玉梨魂》問世不久,有人說這是徐枕亞的「傷心著作」、「寫真影片」(《雪鴻淚史‧自序》)。據說這部小說隱藏著作者年輕時的一段經歷。徐枕亞曾在無錫西倉鎮蔡氏家任家庭教師,白梨影的原型即蔡氏年輕孀婦,何夢霞乃作者自況(范煙橋《民國舊派小說史略》)。情動於中,流於筆端,故寫得悱惻幽怨,哀感動人,以致當時人都稱徐枕亞為「多情種子」(同上)。徐天嘯論此書,也說是「作言情小說為情種寫真」(《雪鴻淚史‧序》)。
孔子早已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何夢霞、白梨影,以及崔筠倩,都或多或少受新思想的感染,也都有追求愛情和自由的願望。夢霞曾憤然表示自己的決心:「天乎天乎!搔首問之而無語,虔心禱之而無靈,憤念至此,殊欲拔劍而起,與酷虐之天公一戰。明知戰必不勝,則惟有以死繼之。」(第十九章〈秋心〉)筠倩更是「憤家庭之專制,慨社會之不良,侈然以提倡自由為己任」(二十九章〈日記〉)。就是梨娘在其遺書中也承認,她無法抗拒情愛的力量:「余情如已死之灰,而彼(指上天,天意)竭力為之挑撥,使得復燃;余心如已枯之井,而彼竭力為之鼓盪,使得再波......余身已不能自主,一任情魔顛倒而已。」(第二十七章〈隱痛〉)
但經歷數千年的禮教,卻表現出比任何王朝都頑固的力量,即使在清王朝日薄西山、搖搖欲墜之時,依然強有力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書中人物,最終都未能擺脫禮教有形無形的束縛。這種束縛,有的在禮制,有的在習俗,有的在輿論,有的就刻在人的心中。而後者是最致命的。梨娘曾獨自去夢霞住處,留下一張相片。相片上的梨娘,身穿西洋服裝,花冠長裙,手持西籍一冊,風致嫣然(第九章〈題影〉)。可見她也有著成為一個新女性的憧憬。但在她的心中,又始終存在著情與禮的衝突,一旦「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觀念占了上風,就只能抑制情感,拒絕情感,進而埋葬情感,導致心死。《莊子》說「哀莫大於心死」(〈田子方〉)。正是禮教使梨娘心死,自絕於愛情,同時也不自覺地葬送了最愛的人的幸福。
由於身分不同,處境不同,禮教對夢霞、筠倩的束縛不像對梨娘那麼大。但在追求愛情的坎坷過程中,他們怨天不公,怨自己無能,卻也從不曾詛咒過禮教,出現過與禮教徹底決裂的念頭,當然更談不上激烈的行動。徐枕亞之友韋秋夢為《雪鴻淚史》作序,謂夢霞、梨娘的戀情,是「對於不能用情之人而又不能不用之情」。兩人都為「情種」,惺惺相惜,生死不渝,可謂「不能不用之情」,但礙於禮教,彼此又成「不能用情之人」,結果只能在「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的自怨自艾中了結。這是夢霞、梨娘的無奈,也是作者及其同時代眾多青年共同的困惑。千百年來的教育和薰陶,使人們相信禮就是理,就是合理,從而抑制自己的感情,成了禮教祭臺上的犧牲。這部小說通過夢霞、梨娘、筠倩的啼痕和血痕,已發出「禮教殺人」的先聲。
何夢霞、白梨影、崔筠倩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他們的處境,是當時青年男女共同面對的處境;他們的命運,是當時追求愛情的青年男女也會感受遭遇的命運。雖然「痴心猶冀活梨花」,但事實上「難將赤手挽情波」(張荇青〈題詩〉)。由此,他們的不幸就具有普遍意義,能引起人們的共鳴。《玉梨魂》不同於普通的言情小說,能在當時引起巨大的轟動,就在它揭示了一個時代悲劇,從而具有明顯的社會意義。
和以往描寫才子佳人的作品都喜以大團圓結局相反,這部小說以完全、徹底、令人壓抑、窒息的悲劇收場。而這正是這部作品的價值和意義所在。夢霞、梨娘、筠倩至死都沒有認識到導致自身悲劇的真正原因,從而給同時代的人和後人留下深刻的啟示,使他們由傷感而震撼,由震撼而思考,由思考而覺醒,由覺醒而行動,終於在五四時期,爆發出「禮教殺人」的呼聲。作為一個新舊交替時期的女性,梨娘對新生活的嚮往,決不會不如《西廂記》中的崔鶯鶯、《牡丹亭》中的杜麗娘、《桃花扇》中的李香君。誠如人所言:造成梨娘悲劇的死結,在禮教對寡婦再嫁的干預。只有提出問題,才有可能解決問題。這部作品「雖沒有直接說出『寡婦再嫁之可能』,但在寡婦不得再醮慘狀的描寫內,及舊禮教吃人力量的暗示內,已把『寡婦不得再醮』的惡制度攻擊,間接的提倡和鼓吹『寡婦再嫁』的可能了。」(冰心〈玉梨魂之評論觀〉)後來電影《玉梨魂》為迎合一部分市民的心理,背離原著,改成一個喜劇性的結尾,讓夢霞和筠倩遵照梨娘的意願,締結良緣,撫養她的兒子鵬郎成人。這個改動,并不可取。
雖然傳統的「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說已遭人非議,但賢惠、聰明、美麗、能幹,始終是一個理想的女子的美德。這些美德,梨娘都具備。但這樣一個完美的女性,卻背負著時代強加在她身上的不幸命運。深深瞭解她的小姑筠倩曾直訴不平之意:「吾他無所惜,所惜者梨嫂耳。以嫂之天資穎敏,心巧玲瓏,使得研究新學,與幾輩青年女子,角逐於科學世界,必能橫掃千人,獨樹一幟。惜乎生不逢辰,才尤憎命。青春負負,問誰還乾淨之身;墨獄沉沉,早失盡自由之福。」(第十二章〈情敵〉)這種同情和不平,對促進女子覺醒,爭取自身權利,客觀上起了推動的作用。
作者處於舊時代向新時代過渡、舊思想向新思想轉變、舊小說向新小說轉型的歷史時期,因此無論其思想,還是創作手法,新、舊兩方面的影響都同時存在。和《遊仙窟》一樣,這部小說也多用駢詞儷句,這被前人批評為四六濫調,甚者認為毫不足取。無論從內容、結構、語言上說,《玉梨魂》確實都有因襲陳腐的地方。有些描寫,不離傳統言情小說的俗套。與不少言情小說相似,書中也有刻意模仿《紅樓夢》之處,如開篇夢霞「葬花」,收局梨娘「焚稿」,前者純屬效顰,後者可謂畫虎不成。過於堆砌的麗詞縟句,猶如「七寶樓臺」。第二十一章〈證婚〉中寫秋兒見石痴上門,急告梨娘的幾句話,本意是秋兒受梨娘薰陶,略知文理,有如鄭玄之婢,但其聲口,全不似近代侍女,從而顯得矯揉造作。特別是受新思想薰陶、充滿陽光和朝氣的筠倩,竟會如此馴服地接受父、嫂的安排,放棄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犧牲自己來了斷情緣,這和她性格的邏輯發展,顯然不合。
但從另一面看,儘管是帶著鐐銬跳舞,這部小說在藝術上仍有其可取之處。作者用文言寫作,雖不如白話淺顯明白,但遣詞造句,時見功力。如「關山色死」、「煙消山瘦」,字練句琢,不落凡近。形容病中呻吟之聲如「病猿啼月,老馬嘶風」,設譬形象,詞句工整。書中寫筠倩午睡未起,枕臂斜眠,「手書一卷,夢倦未拋,書葉已為風翻遍,片片作掌上舞。窺其睡容,秋波不動,笑口微開,情思昏昏,若不勝其困懶者。」(第二十二章〈琴心〉)表現少女嫵媚可愛的睡態,伸手可掬。而「庭樹因風,蕭疏作響;牆花偎露,憔悴泥人......溪邊殘柳數株,風情銷歇,剩有黃瘦之枯條,搖曳於斜陽影裏......仰視山容,暗淡若死,愁雲疊疊,籠罩其顛。」(第十九章〈秋心〉)寫蕭瑟淒涼的景象,有觸目不堪之感。第二十六章〈鵑化〉寫夢霞在家中得梨娘訣別書,閱後方寸大亂,驚疑不定,自言自語,難解難明,低徊往復,一往情深,辭氣頗似韓愈〈祭十二郎文〉、李商隱〈李賀小傳〉中文字。
作者好作詩詞,文中融化前人詩句,信手拈來,筆下生色。在這部小說中也穿插了不少詩詞,以抒情思,雖有不少炫耀才情的無謂之作,但其中也確有佳篇。如夢霞於途中面對秋江夜景,但見前途混茫,碧波無際,雨後新霽,月色澄鮮,漁舟泛泛,流螢點點,笛聲參差,寒氣襲人,不覺觸動情思,口占一律:「日暮扁舟何處依,雲山回首已全非。流螢黏草秋先到,宿鳥驚人夜尚飛。寒覺露垂篷背重,靜看月上樹梢微。茫茫前路真如夢,萬里滄波願盡違。」(第十六章〈燈市〉)此詩情境淒清,辭意凝重,讀之令人悄然生悲,惻然傷懷。
這部小說的長處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節的鋪敘,而在繼承了唐人小說的流風餘韻,重視情景渲染,充滿抒情色彩。書中常借助自然景物,於慘綠愁紅之中,寓憤悒不平之情。並通過季節的更替,敘寫心情的波動,以示榮悴不常,「若為浮世人情,作絕妙之寫照者」(第十九章秋心)。書中敘述的故事,在春天開局,於秋季收場,象徵主人公的愛情,如新葉吐芽,曾充滿希望,但經不起風霜的摧殘,最後惟餘凋零的敗葉,為情殤悲咽。書中最後寫作者與石痴去崔宅夢霞葬花處憑弔,但見重門深鎖,景物荒蕪,人去樓空,淒涼不堪。多情種子,而今安在?他生未卜,此恨綿綿。斜陽下的一抔黃土,即使鞠為茂草,在落花鵑語中傳送的,依然是並非幻渺的往事前塵。
這部小說尤長於在情景的渲染中,刻畫人物的心理。第十六章〈燈市〉寫鄉村風俗,秋收報神,「十里彩棚,懸燈錯落,紅男綠女,點綴其間,笙歌隱隱,響遏雲表」。夢霞和梨娘也走出家門,隨著人群,到處探望。但其意並不在燈。夢霞偶一注目,於「鴻影翩翩,鶯聲嚦嚦」中,彷彿看到梨娘的衣香鬢影;而倩妝梨娘,也正翹首企盼夢霞出現,「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時「燈影與人影齊明,燈光與目光互射」,彼此心馳神往於意中之人,卻又不能片言交接,互訴衷曲。兩人再也無心觀燈賞景,轉身返回,對著一盞熒熒的孤燈,獨自品嘗「剪不斷,理還亂」的相思滋味。這段文字,沒有一句對白,寫兩顆落寞的心,難以融入周圍歡天喜地、競巧爭妍的氣氛之中,曲折細緻,真切動人。
不同於傳統的言情作品,這部小說心理描寫甚多。第四章〈詩媒〉寫梨娘趁人不在,獨自去夢霞住處,取走《石頭記影事詩》稿本,而留荼蘼一朵。夢霞見了,半是驚喜,半是疑惑,於是寫了第一封信,表達了對梨娘的仰慕之情,希望能有機會和梨娘面談。「梨娘讀畢,且驚且喜。情語融心,略含微惱;紅潮暈頰,半帶嬌羞。始則執書而痴想,繼則擲書而長嘆,終則對書而下淚。九轉柔腸,四飛熱血;心灰寸寸,死盡復燃。」梨娘芳心撩亂,輾轉思量,對鏡而泣,顧影自憐。想到自身已如墮落的柳絮,又怎能在空中盡情飄揚?情海茫茫,自己安身之處只是一隻破碎的小舟,只有躲在僻靜的港灣,方能保全,又怎能再起非分之想?不幸遇上狂風暴雨,後果不堪設想。人一惹情絲,便難解脫,豈能因為一時感情的波動,引起日後無窮盡的痛苦和煩惱,既誤己,又誤人?想到這裏,不禁心灰意冷。但情愛的力量又豈是理智所能控制?特別是深埋心底的青春情火,只要有心心相印的摩擦,便會重新燃起。剛想斷此情根的梨娘,「未幾而微波倏起於心田,驚浪旋翻於腦海,漸漸掀騰顛播,不能自持......旋死旋生,忽收忽放,瞬息之間,變幻萬千,在梨娘亦不自知也。」這段描寫,表現梨娘想愛又不敢愛、想拒絕又難於拒絕的心理,絲絲入扣,細膩入微。
夢霞和梨娘,雖相知相悅,相慕相愛,生死不渝,情投意合,但前後僅二次會晤。前一次因李某蓄意陷害夢霞、梨娘,梨娘情急之下,約見夢霞,商量應對之法。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用這樣的方式見面,不僅梨娘、就是夢霞也不願意,但事出無奈,又不得不如此。半載相思,一朝相見,本該是激情迸湧、欣喜若狂之時,但兩人此時心懷冤憤,哪裏還有歡情可言?燈前握手,簾下談心,原是在心頭時時躍起的願望,但當夢霞真的到了梨娘面前,卻惟有兩行清淚,相對無言。在這深邃幽寂的境地之中,重重心事,「盤旋迴繞於腸角,無一息停,與此時鐘之搖擺聲,作心理上無形之應答。」為了保護名譽,只能犧牲幸福。「滾滾愛河波浪惡」,「東風有意虐殘紅」。「我更何心愛良夜,從今怕見月團圓」。都說相思味苦,誰知相逢更苦。「受盡萬種淒涼,只博一場痛哭」。殘宵將盡,不可再留,在梨娘低唱西方名劇《羅米亞》(《羅密歐與茱麗葉》)中「天呀天呀,放亮光進來,放情人出去」的悲切聲中,兩人慘然道別。(第十八章〈對泣〉)這段文字,寫一對可憐人因無端受到傷害而悲憤不安的心理,十分傳神。
只因難捨難合,終成多愁多病。梨娘因情而病,心潮起伏,舊恨新愁,觸緒紛至,心懸一線,腸回九折,百感交集,無以自解。病重因情重,病深情愈深。因為沒有心藥,又如何治癒心病?自筠倩歸後,忽然想出「一接木移花之計,僵桃代李之謀」,以筠倩許配夢霞,成就這對天然佳偶,自己也得以擺脫情網,頓時「心地大開,病容若失」。但又想到筠倩醉心自由,夢霞矢志終身,未必肯聽從,頃刻之間,又「眉峰壓恨,眼角牽愁」了。繼而又想:不管成與不成,只要盡力而為,此心也可釋然。因心中湧起了新的希望,病也就霍然痊癒了。(第十三章〈心藥〉)這段描述,曲曲寫出梨娘的感情波瀾,情深意密,娓娓動人。
何、白兩情相戀,礙於禮教,難以晤面,只能通過書信來往,詩詞唱和,抒寫心中深沉執著的思慕和愛戀。這些書信,都是刻畫其心理狀態的佳作。如梨娘病後致夢霞書,勸其向筠倩求婚,宛曲陳情,反覆勸諭,入情入理,情至義盡,令夢霞閱後如痴如醉。(第十四章〈孽媒〉)又如梨娘給筠倩的絕筆書,披露心曲,訴說不能言又不得不言的「致死之由」、深埋心中的隱痛,字字皆血淚鑄成,充滿了真愛和真情。(第二十七章〈隱痛〉)這些書信,和詩詞一樣,是夢霞和梨娘攀登情山、跋涉恨海的真情記錄。其中有心有靈犀,息息相通的愛憐,有「有情難遂,有恨難平」的怨憤,有一死徇情,以待來生的無奈,有「春蠶到死絲猶縛,蠟炬成灰淚不乾」的遺恨。聲聲掩抑,唏噓欲絕。依戀之誠,溢於言表。《玉梨魂》於一九一二年六月起,在上海《民權報》副刊連載。次年一月,民權出版部出版鉛印單行本,一冊。嗣後翻印本甚多,僅上海清華書局,至一九二八年已出至第三十二版。卷首有吳雙熱序及作者等十人題詞。此書不僅為當時國內最暢銷的小說,而且還遠銷南洋,銷量高達數十萬冊。上海民興社曾將小說改編成話劇。而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又將小說改編成電影。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影片《玉梨魂》在上海夏令配克大戲院首映,觀眾如水,好評如潮,隨後從東三省到南洋、菲律賓同時播放,贏利創當時國產片之冠。
在《玉梨魂》熱潮的推動下,徐枕亞用同樣的題材,另作《雪鴻淚史》。自一九一四年五月起,在《小說叢報》創刊號開始連載。這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日記體小說。書中主要人物,悉依《玉梨魂》原本,情節較《玉梨魂》增加十之三四,詩詞信札則增加十之五六。
上世紀二十年代,柔石的中篇小說二月問世。這部作品寫一個外來的鄉村中學教師蕭澗秋對寡婦文嫂的同情、和女學生陶嵐的戀情,最後以文嫂含恨自殺、蕭澗秋被迫離開結束。無論其主題思想,還是情節結構,都明顯受《玉梨魂》的影響。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遊仙窟玉梨魂合刊(二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4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06 |
文學作品 |
$ 306 |
小說/文學 |
$ 335 |
中文書 |
$ 335 |
中國古典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遊仙窟玉梨魂合刊(二版)
太平盛世間,一段旖旎多情的奇幻豔遇
大爭亂世中,一則無法相守的愛情悲劇
────兩則時代經典言情故事,跨越時空相遇────
本書合刊〈遊仙窟〉與〈玉梨魂〉二篇文言言情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它們一前一後,相互輝映,有著特殊的意義。〈遊仙窟〉首創以自敘的方式,寫作者在旅途的一段豔遇,辭采絢麗,刻畫傳神,在唐人小說中別具異彩,風行一時,並且傳入日本,自唐以來即流傳不衰。《玉梨魂》則是民初上海鴛鴦蝴蝶派小說最有價值的代表作,描寫青年才子何夢霞與年輕貌美的寡婦白梨影相愛卻不能相守的悲劇故事,因為有作者的身影在其中,寫來悱惻幽怨,哀感動人,曾改編成話劇和電影,轟動一時,並且遠銷至南洋。二篇雖是文言小說,但都情采並茂,耐人尋味,並有詳細注解,誠摯邀您一同鑑賞。
作者簡介:
張鷟(658~730)
字文成,號浮休子。唐代深州陸澤(今河北深縣)人,曾官御史、都尉、鴻臚丞、司門員外郎。著有傳奇《遊仙窟》、《朝野僉載》。
徐枕亞(1889~1937)
名覺,字枕亞,別署徐徐、東海三郎、泣珠生等,江蘇常熟人。近代小說家,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南社社員。著有《玉梨魂》、《餘之妻》、《雙鬟記》、《讓婿記》、《蘭閨恨》、《刻骨相思記》、《秋之魂》等。另有雜著《枕亞浪墨》四集、《無聊齋説薈》、《情海指南》、《輓聯指南》、《近代小説家小史》以及《悼亡詞》一百首、《雜憶》三十首、《鼓盆遺恨集》等。此外還編有《無名女子詩》、《諧文大觀》、《廣諧鐸》、《錦囊》等。
黃珅(1949~)
生於上海,1982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後留校從事文史研究。現為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序
在中國小說史中,風行一時的文言言情小說,《遊仙窟》可能是最早的一部,而《玉梨魂》則是最後的一部。上世紀初,一些文學青年寓居上海租界(那時叫做「洋場」),從事創作。由於他們熱衷於言情小說,好寫才子佳人「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蔭花下,像一對胡蝶,一雙鴛鴦一樣」(魯迅〈上海文藝一瞥〉),
有人以「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戲稱當時的哀情小說(平襟亞〈鴛鴦蝴蝶派命名的故事〉),因此稱為「鴛鴦蝴蝶派」。後來這派作者所寫小說的內容不斷擴展,於是又以其早期最有影響的雜誌禮拜六為名,通稱為「禮拜六派」。鴛鴦...
有人以「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戲稱當時的哀情小說(平襟亞〈鴛鴦蝴蝶派命名的故事〉),因此稱為「鴛鴦蝴蝶派」。後來這派作者所寫小說的內容不斷擴展,於是又以其早期最有影響的雜誌禮拜六為名,通稱為「禮拜六派」。鴛鴦...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遊仙窟
【總目】
引言
正文
玉梨魂
【總目】
引言
章目
正文
【章目】
第一章葬花
第二章夜哭
第三章課兒
第四章詩媒
第五章芳訊
第六章別秦
第七章獨醉
第八章贈蘭
第九章題影
第十章情耗
第十一章心潮
第十二章情敵
第十三章心藥
第十二章情敵
第十三章心藥
第十四章孽媒
第十五章渴暑
第十六章燈市
第十七章魔劫
第十八章對泣
第十九章秋心
第二十章噩夢
第二十一章證婚
第二十二章琴心
第二十三章翦情
第二十四章揮血
第二十五章驚鴻
第二十六章鵑化
第二十七章隱痛
第二十八章斷腸
第二十九章日記
第三十章憑弔
【總目】
引言
正文
玉梨魂
【總目】
引言
章目
正文
【章目】
第一章葬花
第二章夜哭
第三章課兒
第四章詩媒
第五章芳訊
第六章別秦
第七章獨醉
第八章贈蘭
第九章題影
第十章情耗
第十一章心潮
第十二章情敵
第十三章心藥
第十二章情敵
第十三章心藥
第十四章孽媒
第十五章渴暑
第十六章燈市
第十七章魔劫
第十八章對泣
第十九章秋心
第二十章噩夢
第二十一章證婚
第二十二章琴心
第二十三章翦情
第二十四章揮血
第二十五章驚鴻
第二十六章鵑化
第二十七章隱痛
第二十八章斷腸
第二十九章日記
第三十章憑弔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