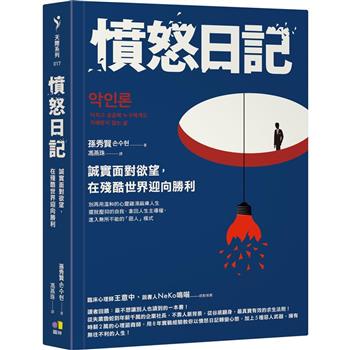出版緣起
林富士教授為臺灣史學界的著名學者,畢生研究以身體為軸心,致力於宗教史、醫療史與文化史,以做一個現代薩蠻為自我定位,透過文獻進入異域,瞭解另一個世界的現象,不僅探究歷史發展的脈絡轉折,也關注於「邊緣」的小歷史。教授自2000年起,擔任三民書局「文明叢書」編輯委員,並出版《小歷史──歷史的邊陲》(2000年)及《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2001年)等作品,透過教授的研究,我們得以看見庶民歷史的精彩與活躍。
教授2021年辭世後,各界無比悵然,但其所遺留的豐碩研究成果,仍持續影響著相關學術主題的發展。《巫者的世界》是教授多年來針對巫者歷史的研究總結,對於臺灣常見的宗教人物「童乩」亦多所關注,曾以簡體中文出版,但始終未曾以繁體中文版呈現給臺灣讀者,甚為可惜。源此若能出版以饗讀者,將有助開拓讀者對於臺灣宗教文化的理解,為學界之福,想必也是富士教授所願。
出版本書,對與教授有多年淵源的三民書局而言,責無旁貸,幸得其家人林雅蘭女士促成,及陳藝勻博士協助審閱、校訂,特此致謝。亦希盼本書的出版,能將教授嚴謹的研究精神與學者風範永傳後世。
三民書局編輯部謹識
推薦序
李貞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1978 年秋進入大學,歷史系班上人才濟濟,其中一位同學特別出色,不僅善詩能文,還很會說故事。他來自雲林濱海的村莊,講述兒時見聞,童乩降神附體,活靈活現,常令生長於城市的我感覺匪夷所思。他是林富士。
之後十多年,富士以自幼熟悉的巫者為題,陸續完成碩、博士論文,先談漢代、後論六朝,為當時幾乎無人涉獵的領域拓邊開新。普大畢業後,重返史語所,他持續關注巫者的世界,對帝制中國的巫覡研究,下探至宋代和清末。更重要的是,他跨出文字史料的框限,進行田野考察,跑遍臺灣大鄉小鎮,普查記錄童乩與信眾,又遠赴韓國,拍攝巫女在喪禮中牽亡的儀式影片。他的研究室和我比鄰,不論在講論會、工作坊,或走廊上、茶水間,聽他分享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經驗,總是他說得興高采烈,我聞言莫名感佩。
《巫者的世界》一書,正是富士多年來爬梳史料、尋訪考掘、反覆思辨之後,對傳統中國和近代臺灣巫覡信仰的精道剖析。2016年曾以簡體字出版,今依原稿補正更新,以正體字刊印。其中收錄八篇專論,涵蓋巫者的社會形象與地位、他們和統治政權弛張交錯的關係、巫覡作為醫療者與病人信徒的互動, 以及這些角色功能對歷代巫俗巫風的影響。篇篇皆反映史語所鋪天蓋地蒐羅史料的傳統, 也展現富士不畏艱難勤跑田野的毅力。即以 〈臺灣童乩的儀式裝扮〉一章為例,雖短小卻精悍,透過細究巫者的外貌、服飾、法器,以及在儀式中的作用與意義,綜論古今、反思學史,並且圖文並茂,充分顯示他調度各種資訊、推進論題的志氣與功力。
早期宗教史研究,多從經典教義入手,也有分析教團組織的。上世紀末,宗教經驗的考察風生水起,學者對信仰所涉及的儀式、物品、活動,乃至其中個人的身體、情感及其意涵,皆興趣大增。富士自學涯之始,便立志追尋巫者在歷史上的足跡, 藉由掌握宗教人物來認識更廣大的社會文化, 可謂慧眼獨具。巫覡信仰非組織型宗教,巫者在帝制時期屬底層人物,史料分散,載論隱曲,研究者除了廣事蒐羅的耐性,還需有觸類旁通的機敏,而富士以溝通者自期,這些正是他作為歷史學者最在乎的能力。
是的,富士研究歷史,正是以上古絕地天通,巫者溝通人神自況。他致力於穿越古今、進出知識異域、梳理紛紜眾說,再以流暢的文筆傳達轉譯。瀏覽本書,不論是宗教史、中國史或臺灣文化的專家學者,相信都能因其中豐富的資料、寬宏的論述而受益。初入門者,即使僅僅閱讀他的長篇自序,也能受到啟發。〈序:吾將上下而求索〉彷彿一篇學術自傳,始於「摸索」,終於「未央」,循循善誘,引領年輕學子一窺士林堂奧。
確實未央!雖然,富士已在2021年遠颺,但他留給學界的遺產豐厚,我們將透過他的著作,和他,以及他所探討的巫者世界繼續
序
吾將上下而求索
一、摸索 (1982-1984)
1982 年夏天,我從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 立刻面臨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抉擇:繼續升學或當兵。後來,我選擇入伍擔任預備軍官,但仍保留了歷史研究所的入學資格。
當兵是無可逃避的「義務」,也是體魄與心智的鍛鍊。在文學院浸泡了四年,心靈自由而奔放,生活隨意而自在,因此,在入伍之後,格外難以忍受講求權威、服從、標準、齊一的軍人文化。而且,當時還在「戒嚴」時期,言論、思想與行動幾乎都戴上了手銬與腳鐐。役期一年十個月,苦悶慢慢煎熬。所幸我是少尉經理官,擔任補給和管理的工作,較為輕鬆,而且還有獨立的臥室,在半是禁閉的狀態下,讀書成為最好的解脫。
那時,我帶了王守仁 (1472-1529) 的《陽明全書》和葛洪(約284-363)的《抱朴子》到部隊。我特別挑沒有標點的版本,一個字一個字點讀,在斷句的過程中,彷彿吐納一般,呼吸著儒、道二家的思想。我先是讀王陽明,因為我大學時代的志業是彬彬的儒者。但是,越讀越無聊,紙面上充斥著天、人、性、命、道、理、心、良知、格物這一類的字眼,以及一篇又一篇的問答、書信、序文,反覆纏繞著仁義道德與學問事功。我非常佩服,但如墜五里霧中。後來讀《抱朴子》,一看,眼界大開,驚愕連連。葛洪所描述的道教世界實在太有趣了,有煉金、房中、辟兵、禁咒、長生、神仙、隱形、分身、變形等法術,提供了各種慾望的滿足方法。對於神仙之說,我雖然不敢置信,但仍被勾引起一絲富貴不死、法力無邊的貪念。更重要的是,童年時期在鄉村的一些經驗突然醒覺,我恍惚又聽見了道士在喪禮中的搖鈴聲、吹角聲、唱誦聲,看見了三清道祖、十殿閻王、地獄鬼怪的圖像。在閱讀、冥想的過程中,我逐漸找到當下與往昔的聯繫,也找到自己歷史研究的方向。
我選擇宗教作為主戰場。原本打算從中國道教史入手,但是,當時我所能讀到的只有許地山 (1894-1941)、傅勤家、孫克寬 (1905-1993)、李豐楙(1947-) 四人的著作,而他們在討論道教起源的時候,都提到道士與巫覡有緊密的關係,這讓我想起小時候所碰到的童乩。
1960年代,我所生長的濱海村莊(雲林縣臺西鄉五港村瓦厝)還相當「落後」,沒有象徵「現代文明」的自來水、汽車和醫生,多的是蒼蠅、流氓和砂眼。病痛的時候,通常會求助於童乩,降神、問卜、畫符、唸咒、收驚、叫魂、祭解、驅邪,無所不致。而我的表姨丈就是村裡最神氣的童乩。事實上, 我還有一位姨丈、兩位表哥、一位堂哥,也都是童乩。我對於這樣的人並不陌生,他們應該就是傳統文獻所說的巫者。
可是,根據《國語‧楚語》的記載,巫者在古代是聖、智、聰、明的才藝之士,是統治集團的一分子,而童乩在當代社會卻受人輕賤,被人打壓。官方與主流媒體不斷宣稱他們是低級、野蠻、邪惡的神棍,應該予以禁斷。在知識的殿堂中,他們更是毫無立足之地,很少人願意碰觸或討論這樣的人。因此,我很快就決定要探索巫者的古今之變。我的終極關懷,不是陌生巫者的往日光輝,而是我所熟識的童乩的當代困境。
(完整請見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