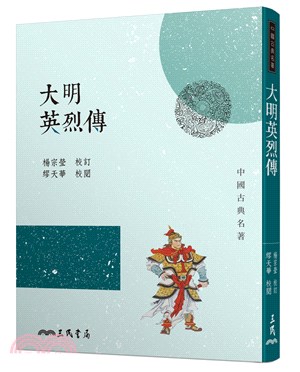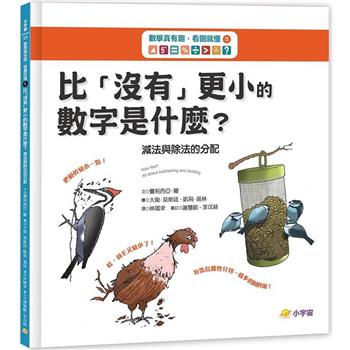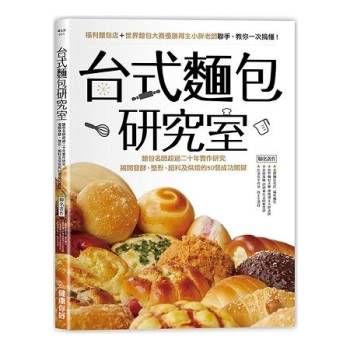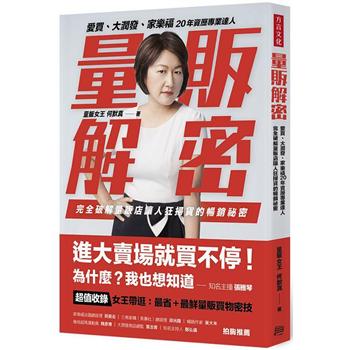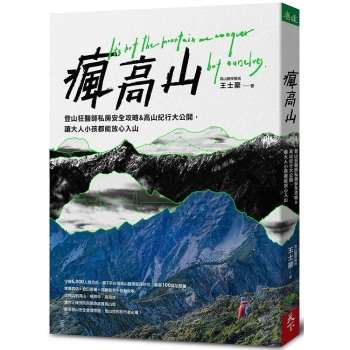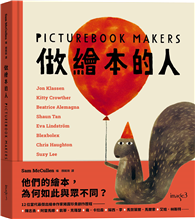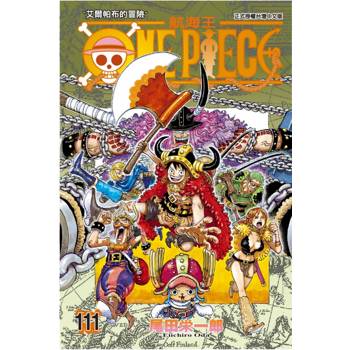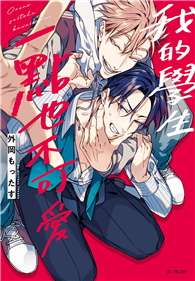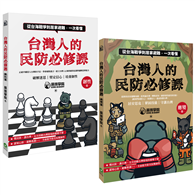《大明英烈傳》,又名《英烈傳》、《皇明英烈傳》、《雲合奇蹤》。講述明太祖朱元璋逐元而一統天下的故事,許多人物事蹟皆與正史相對,斑斑可考。元朝末年,順帝荒淫失德,天下群雄四起反抗,明太祖朱元璋亦乘運而起,他先入皇覺寺做和尚,二十四歲投郭子興麾下當親兵;其後靠著劉基、徐達、常遇春等多位友人的協助,連年征戰而終於平定天下。小說作者將朱元璋及其身邊功臣皆比為神仙及星宿轉世,故事增添了許多神話色彩。本書除考證剖析歷來版本、作者之說外,隨文並附有簡明扼要的注釋,便於讀者深入領會《大明英烈傳》的精彩動人之處。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大明英烈傳(三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8 |
文學作品 |
$ 315 |
華文歷史小說 |
$ 315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25 |
中文書 |
$ 326 |
中國古典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大明英烈傳(三版)
內容簡介
目錄
【總目】
引言
大明英烈傳考證
插圖
回目
正文
【回目】
第一回元順帝荒淫失政
第二回開濬河毀拆民房
第三回專朝政群奸致亂
第四回真明主應瑞濠梁
第五回眾牧童成群聚會
第六回伽藍殿暗卜行藏
第七回販烏梅風留龍駕
第八回郭光卿起義滁陽
第九回訪徐達禮賢下士
第十回定滁州神武威揚
第十一回興隆會吳禎保駕
第十二回孫德崖計敗身亡
第十三回牛渚渡元兵大敗
第十四回常遇春采石擒王
第十五回陳也先投降行刺
第十六回定金陵黎庶安康
第十七回古佛寺周顛指示
第十八回劉伯溫法伏猿降
第十九回應徵聘任人虛己
第二十回棟樑材同佐賢良
第二十一回王參軍生擒士德
第二十二回徐元帥被困牛塘
第二十三回胡大海活捉吳將
第二十四回趙打虎險受災殃
第二十五回張德勝寧國大戰
第二十六回釋亮祖望風歸降
第二十七回取樊嶺招賢納士
第二十八回誅壽輝友諒稱王
第二十九回太平城花雲死節
第三十回康茂才夜換橋梁
第三十一回不惹庵太祖留句
第三十二回張金箔法顯街坊
第三十三回胡大海被刺殞命
第三十四回花雲妾義保兒郎
第三十五回朱文正南昌固守
第三十六回韓成將義死鄱陽
第三十七回丁普郎假投友諒
第三十八回遣四將埋伏禁江
第三十九回陳友諒鄱陽大戰
第四十回歸德侯草表投降
第四十一回熊天瑞受降復叛
第四十二回朱亮祖魂返天堂
第四十三回損大將日現黑子
第四十四回常遇春收伏荊襄
第四十五回擊登聞斷明冤枉
第四十六回幸濠州共沐恩光
第四十七回薛將軍生擒周將
第四十八回殺巡哨假擊鑼梆
第四十九回張士誠被圍西脫
第五十回弄妖法虎豹豺狼
第五十一回朱亮祖連剿六叛
第五十二回潘原明獻策來降
第五十三回連環敵徐達用計
第五十四回俞通海削平太倉
第五十五回張豹排八門陣法
第五十六回二城隍夢告行藏
第五十七回耿炳文殺賊祭父
第五十八回熊參政捷奏封章
第五十九回破姑蘇士誠殞命
第六十回啞鐘鳴瘋僧顛狂
第六十一回順天心位登大寶
第六十二回方國珍遁入西洋
第六十三回征福建友定受戮
第六十四回破元兵順取汴梁
第六十五回攻河北大梁納款
第六十六回克廣西劍戟輝煌
第六十七回元宮中狐狸自獻
第六十八回燕京破順帝出亡
第六十九回豁鼻馬裏應外合
第七十回追元兵直出咸陽
第七十一回常遇春柳河棄世
第七十二回高麗國進表頌揚
第七十三回獲細作將計就計
第七十四回現銅橋天賜奇祥
第七十五回賜鐵券功臣受爵
第七十六回取西川劍閣兵降
第七十七回練猢猻成都大戰
第七十八回皇帝廟祭祀先皇
第七十九回唐之淳便殿見駕
第八十回定山河慶賀封王
引言
大明英烈傳考證
插圖
回目
正文
【回目】
第一回元順帝荒淫失政
第二回開濬河毀拆民房
第三回專朝政群奸致亂
第四回真明主應瑞濠梁
第五回眾牧童成群聚會
第六回伽藍殿暗卜行藏
第七回販烏梅風留龍駕
第八回郭光卿起義滁陽
第九回訪徐達禮賢下士
第十回定滁州神武威揚
第十一回興隆會吳禎保駕
第十二回孫德崖計敗身亡
第十三回牛渚渡元兵大敗
第十四回常遇春采石擒王
第十五回陳也先投降行刺
第十六回定金陵黎庶安康
第十七回古佛寺周顛指示
第十八回劉伯溫法伏猿降
第十九回應徵聘任人虛己
第二十回棟樑材同佐賢良
第二十一回王參軍生擒士德
第二十二回徐元帥被困牛塘
第二十三回胡大海活捉吳將
第二十四回趙打虎險受災殃
第二十五回張德勝寧國大戰
第二十六回釋亮祖望風歸降
第二十七回取樊嶺招賢納士
第二十八回誅壽輝友諒稱王
第二十九回太平城花雲死節
第三十回康茂才夜換橋梁
第三十一回不惹庵太祖留句
第三十二回張金箔法顯街坊
第三十三回胡大海被刺殞命
第三十四回花雲妾義保兒郎
第三十五回朱文正南昌固守
第三十六回韓成將義死鄱陽
第三十七回丁普郎假投友諒
第三十八回遣四將埋伏禁江
第三十九回陳友諒鄱陽大戰
第四十回歸德侯草表投降
第四十一回熊天瑞受降復叛
第四十二回朱亮祖魂返天堂
第四十三回損大將日現黑子
第四十四回常遇春收伏荊襄
第四十五回擊登聞斷明冤枉
第四十六回幸濠州共沐恩光
第四十七回薛將軍生擒周將
第四十八回殺巡哨假擊鑼梆
第四十九回張士誠被圍西脫
第五十回弄妖法虎豹豺狼
第五十一回朱亮祖連剿六叛
第五十二回潘原明獻策來降
第五十三回連環敵徐達用計
第五十四回俞通海削平太倉
第五十五回張豹排八門陣法
第五十六回二城隍夢告行藏
第五十七回耿炳文殺賊祭父
第五十八回熊參政捷奏封章
第五十九回破姑蘇士誠殞命
第六十回啞鐘鳴瘋僧顛狂
第六十一回順天心位登大寶
第六十二回方國珍遁入西洋
第六十三回征福建友定受戮
第六十四回破元兵順取汴梁
第六十五回攻河北大梁納款
第六十六回克廣西劍戟輝煌
第六十七回元宮中狐狸自獻
第六十八回燕京破順帝出亡
第六十九回豁鼻馬裏應外合
第七十回追元兵直出咸陽
第七十一回常遇春柳河棄世
第七十二回高麗國進表頌揚
第七十三回獲細作將計就計
第七十四回現銅橋天賜奇祥
第七十五回賜鐵券功臣受爵
第七十六回取西川劍閣兵降
第七十七回練猢猻成都大戰
第七十八回皇帝廟祭祀先皇
第七十九回唐之淳便殿見駕
第八十回定山河慶賀封王
序
引言
楊宗瑩
元朝末年,順帝荒淫失德,民不聊生,以致各地群雄紛紛而起,反抗暴政。經過數十年的征戰,最後由明太祖朱元璋削平群雄,逐元而統一天下。這部大明英烈傳,就是敘述明太祖得天下的經過,以及諸開國英雄征戰的英勇事蹟。
本書的故事,大體上是依據歷史寫成。其中的許多人物事蹟,正史上皆斑斑可考,並非虛構,但故事的情節發展,與歷史則不盡相同。
朱元璋是本書的主角。作者為了強調他是真命天子,因而把他加上了神話色彩,說他和馬皇后本是玉皇大帝身邊的金童玉女,是玉帝派他下凡來到塵世間肅清世界,統一天下,拯救烝黎的。連他身邊的輔弼大臣,也都是天上的星宿降生凡間的。這類神話傳說,自古有之。大凡登上了九五尊位的人,為了鞏固自己的權益,禁止別人窺伺帝位,他左右的人,往往替他編造出不平凡的來歷。例如漢高祖的母親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史記高祖本紀)後高祖因斬大蛇而知自己是赤帝子,他所居之地,上空常有五彩雲氣。又如東漢光武帝出生時,「有赤光照室中」,那年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
朱元璋沒有顯赫的家世,幼年父母雙亡,因貧窮而出家做和尚。這一段平凡的史實,在本書裏卻賦予了不平凡的意義:他的父母是玉帝命令天下的城隍、土地,從民間千挑萬選,選出來的仁德之家,是惟一修了三十三世的。皇覺寺的住持,是神和他家之間的橋梁,代替天神照顧他們的。他早已是住持的記名弟子,因貧而出家成了順理成章之事。
本書中說,朱元璋在廟裏受到別的和尚欺侮,卜了幾個大吉的卦後,有了做皇帝的雄心大志。離開皇覺寺去投靠姐夫,轉而跟隨舅父郭光卿在滁州起義,邁開了打天下的第一步。
事實上,朱元璋在皇覺寺接到朋友的信,勸他參加革命組織,他怕別的和尚知道檢舉他通匪,在卜了一個大吉的卦之後,投效了郭子興。郭子興是劉福通的屬下。
在本書裡,朱元璋一直擁戴滁陽王郭光卿,對他忠心耿耿;滁陽王死後,又扶他的兒子繼位為和陽王。任左右的人怎樣勸,也不肯自己稱王。甚至和陽王因忌恨曾設宴想毒殺他,他也寬宏大量不與計較。一直到和陽王死,他仍不肯正大位。
在歷史上,劉福通找到宋徽宗的後代韓林兒,奉他為大宋的皇帝『小明王』。朱元璋一直受劉的節制,打了勝仗向劉告捷,接受劉任命的官職,一直打著反元復宋的旗幟。在宋皇帝居住的安豐被圍,劉福通戰死後,朱元璋帶兵救援,把韓林兒接到滁州,自己回應天府。照理他應當把韓林兒接到應天府,對他北面稱臣的,大概這時已受了劉基的影響,有意為自己開創一個新的局面。三年後,派廖永忠去滁州接韓林兒來應天府,途中所乘的船翻身,韓林兒落水而死。韓林兒一死,『宋朝』也就結束了。
在本書裡,說郭光卿最初是投在劉福通的旗下,朱元璋勸他除去紅巾,自稱滁陽王後,劉福通派人來問,何以去了紅巾,稱了王號?朱元璋對來人說:「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名據一方,不必相問。若日後你們有厄,我當與你解圍,以報起兵之義。」劉福通之事就如此輕巧地略過。後來安豐被張士誠圍攻,劉福通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親自率兵前往,才到泗州界上,傳令安營,就有人來報告說:張士誠已攻下安豐,殺害了韓林兒及劉福通。
歷史上,劉福通是失敗的英雄,在元朝末年,是個大有作為,響噹噹的革命領袖,曾經風馳電掣地橫掃北方,直逼大都,打到汴梁,摧毀元朝的內蒙中心都邑,幾乎把元朝真正推倒,並且始終對韓林兒盡忠竭智,了無私心。而本書寫他的事,只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可能是因為在明史上把他稱為寇,即使作者對他有相當的尊敬,又怎敢犯忌諱加以頌揚呢?不貶抑,已經等於褒揚了。
至於攻打陳友諒,消滅張士誠,本書則不厭其詳地敘述。陳友諒是個不擇手段,爭功爭利,害友弒君,妄自尊大的小人。張士誠一生惟利是圖,反元之後又投降元,投降之後又再度反元,這些劣跡,書中敘述唯恐不詳。其他如征討方國珍、陳友定,北伐中原,趕走順帝,攻取西川,平定雲南,都有趣味化的敘述,大事和史實相彷彿。
因為有神話色彩,全書從頭至尾,都穿插了許多神異的故事。除了開頭朱元璋降生的神話之外,還有如第七回販烏梅風留龍駕;第十三回朱元璋乘的船,有烏雲繞轉如飛,從澗中穿過,進入大江;第十七回劉基在山中得到兵書的奇遇;第二十五回朱元璋將五條花蛇盛在頭巾內,戴在頭上的奇異事;第四十回朱元璋誤入廬山;第四十二回朱亮祖魂返天堂;第五十六回二城隍夢告行藏;第六十回啞鐘鳴瘋僧顛狂;第七十八回歷代功臣廟內的神異之事等等,都是極富趣味的神話。另外還有幾位異人,如鐵冠道人、周顛、赤腳僧等穿梭其間,因此朱元璋的軍隊遇到任何情況,都能逢凶化吉,而所向無敵。這些神話故事,都在烘托朱元璋真命天子的身分。無論他身在何處,隨時有天神保護他,幫助他。書裡也一再有:「此真天子出世」、「王氣應在金陵」、「致意大明皇帝」等語。
作者處處頌揚朱元璋的美德,說他具有仁德,戰爭不多殺傷,不擾民,一切皆為天下蒼生著想。對上盡忠,始終事奉滁陽王、和陽王,不肯自己取而代之。能知人善任,禮下賢德之士,每克服一地,必先拜訪當地的賢能之士,或得降將死力,因而有劉基、宋濂、常遇春、李善長等文臣武將。他又驍勇善戰,指揮若定,好謀而成。他的美德真是不勝枚舉,總之是集知、仁、勇於一身。
在頌揚之外,有時候也透露了一點朱元璋的兇殘。如第三十一回「不惹庵太祖留句」中,說朱元璋私行打探民情,走到不惹庵中。有一個老和尚問他居處姓名,他不應。老僧說:「尊官何以不說居處姓名,莫不是做些什麼歹事?」朱元璋看見桌上有筆硯,便題詩一首道:
「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顧嘵嘵問姓名。」
詩裡充滿血腥的殺氣。第四十回太祖誤入廬山,老僧拿出緣簿向他化緣,朱元璋不得已寫了五千兩,而心中即發嗔念道:「和尚是不好惹的,見面就要化緣。我本無心到此,被他將茶果誆住,寫上許多銀子;若我日後登了大位,當殺此貪僧,滅盡佛教。」並在門上題詩一首道:
「手握乾坤殺伐機,威名遠鎮楚江西。青鋒起處妖氛淨,鐵馬鳴時夜月移。有志掃除平亂世,無心參悟學菩提。陰陰古木空留意,三嘯長歌過處溪。」
老僧看見詩句,責備他殺氣太重,叫沙彌洗去字跡。他自覺慚愧,即便辭回。這兩個故事表現出他本性中的兇狠。有時候也透露出朱元璋的自大狂妄。如第六十回,孝陵城西門之內,掘出吳大帝孫權之墓,朱元璋微笑說:「孫權亦是個漢子,便留著他守門也好,其餘墓坟,都要毀移。」第七十八回朱元璋在歷代功臣廟內,看見張良的塑像,烈火生心,手指張良罵道:「朕想當時漢稱三傑,你何不直諫漢王,不使韓信封王?那躡足封信之時,你即有陰謀不軌,不能致君為堯舜,又不能保救功臣,使彼死不瞑目,千載遺恨;你又棄職歸山,來何意去何意也?」這番狂妄的話,使劉基聽了內心躊躇不安,因而萌生退隱之志。同一回裏又稱贊太祖登基後的仁政,說他「仁政多端,說不盡洪恩大惠。」接著敘述數年來功臣之凋零,提到劉基、宋濂、鄧愈、廖永忠之死,雖與歷史稍有出入,但這裡似乎有兔死狗烹之哀嘆。「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這兩句詩裡,有深意在焉。
本書文字淺顯,內容精彩,文筆生動,讀來趣味無窮。在每一回後,都有詳細的注解,把這一回中比較難懂的詞語加以解釋,或徵引各書之記載,與本書內容相印證,以備讀者查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