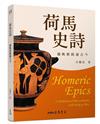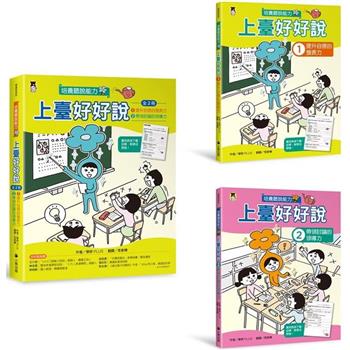傳說為荷馬創作的《伊里亞德》和《奧德賽》,歐洲最古老的書寫文本,是希臘的史記。本書上溯印歐語族群遷徙殖民的歷史,下探歐洲史詩的源起與流變,透過獨樹一幟的史觀,展現別開生面的史識,全面探究荷馬史詩蔚然成學的來龍去脈。作者所見史詩景觀的嬗遞反映文化史的進程,從口傳史詩以實體城牆界定土地認同,經由文人史詩以文化城牆界定族群認同,到基督教史詩以信仰城牆界定宗教認同。由於英雄的偉業根基隨認同的本質而改變,地理空間不斷廣化,從強調具體的身體經驗,經由強調歷史的閱讀經驗,最後演變為強調自傳色彩的想像經驗。同步發展的是心靈空間的深化,其主旋律為兼具心理與情感雙重意義的生死辯證,從直面死亡,經追尋不朽,到信仰永生。朝特定目標前進的線性敘述終於取代永恆回歸的環狀結構,呼應方興未艾的小說不可或缺的人生觀。
作者簡介:
呂健忠
以翻譯西洋文學經典為志業。已出版譯注本包括荷馬史詩《伊里亞德》與《奧德賽》;希臘悲劇《奧瑞斯泰亞:逐行注釋全譯本》(埃斯庫羅斯)、《索福克里斯全集》(二冊)與《尤瑞匹底斯全集I》;希臘喜劇《利西翠妲》(亞里斯多芬尼斯);《易卜生戲劇集》(五冊);《蘇格拉底之死:柏拉圖作品選譯》;奧維德《變形記》;馬基維利《君主論》與《論李維羅馬史》;《馬克白:逐行注釋新譯本》(莎士比亞);《情慾幽林:西洋上古情慾文學選集》、《情慾花園:西洋中古時代與文藝復興情慾文選》、《情慾舞台:西洋戲劇情慾主題精選集》;《丘比德與賽姬:陰性心靈的發展》。著作包括《陰性追尋:西洋古典神話專題之一》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強力推薦 (以下依姓名筆劃排列)
吳宜蓉 Special教師獎得主、《這樣的歷史課我可以》作者
李有成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李奭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張上冠 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戴逸群 亡牌教師
謝易霖 慈心華德福高中資深教師、金鼎獎推薦作家
本書內容豐富、敘議兼具,是一部介於學術與通俗之間的作品,加以作者文字甚佳、行文流暢,頗富可讀性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李有成
無論是對一般讀者、莘莘學子、或是西方文學的專家學者而言,這是一本豐富詳實、文字雋永、可供便捷查檢的文學歷史著作。
──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張上冠
本書凝聚呂健忠先生翻譯與研究荷馬史詩的多年心得,為中文世界提供了解希臘文學與西方經典的便捷之道。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單德興
名人推薦:▏強力推薦 (以下依姓名筆劃排列)
吳宜蓉 Special教師獎得主、《這樣的歷史課我可以》作者
李有成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李奭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張上冠 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戴逸群 亡牌教師
謝易霖 慈心華德福高中資深教師、金鼎獎推薦作家
本書內容豐富、敘議兼具,是一部介於學術與通俗之間的作品,加以作者文字甚佳、行文流暢,頗富可讀性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李有成
無論是對一般讀者、莘莘...
章節試閱
英雄的始祖出世
阿柯美妮的丈夫安菲崔翁(Amphitruon) 前往底比斯參戰時,宙斯假冒丈夫的身分和她睡了一覺,生下神種海克力斯。細節值得一提的是三種不同的版本:《伊里亞德》19.91-136 強調宙斯和希拉的齟齬,這是希臘神話的一個母題;阿波羅多若斯《神話大全》2.5.8 特別提到宙斯為了延長春宵時光而把夜晚時間加倍;奧維德的《變形記》9.281-323 由阿柯美妮對孫媳婦回憶長達七天七夜的生產痛經驗,陰性書寫的筆觸獨步上古文學。
海克力斯八個月大時,希拉指派兩條蛇爬進他的搖籃,想要害死他,卻被他徒手捏死。希拉貴為希臘的天后,當然不會善罷干休,畢竟她身為婚姻女神的天職就是維繫父系單偶婚制。不同的是,這一次被盯上的不是情敵,而是無辜的孩子。希拉醋海掀波是海克力斯終生苦難如影隨形的根源。
他拜師學武術,駕馬車、摔角、射箭、擊劍都有名師指導。他也跟黎諾斯(Linos) 學彈琴,由於音樂天賦駑鈍而受體罰,他還手打死老師。被控謀殺,他以自衛辯解而獲無罪開釋。十八歲時,他的養父安菲崔翁深懷戒心,派他去牧牛。放牧期間,他殺死一頭獅子,剝下刀槍不入的獅皮為衣。身披獅皮是他出
現在圖像藝術常見的裝束,吻合他出身狩獵時代的背景。
海克力斯為底比斯立下戰功, 底比斯王把女兒梅格樂(Megara) 賞賜給他,生下三個孩子。希拉的醋勁再度發威,她設法使海克力斯在神智失常的情況下殺死自己的孩子。待神智清醒,他又是震驚、又是懊惱,於是前往德爾菲向阿波羅神諭求助。女祭司皮緹雅(Puthia) 指示他贖罪之道:伺候邁錫尼王尤瑞斯透斯(Eurustheus),任憑使喚十二年。
「希拉的榮耀」
從此海克力斯作牛作馬,先後完成十二件苦勞:搏獅剝皮、殺九頭蛇怪、活捉神鹿、生擒野豬、限日清掃陳年大牛棚、驅趕湖中鳥怪、馴服克里特公牛、捕獲神駒、劫奪女人族阿馬宗(Amazon) 女王的束腰帶(搶奪女性的束腰帶是性侵的委婉語)、搶奪巨人放牧的牛群、摘取百頭龍守護的金蘋果、活捉冥府入口一身三頭的看門狗。他終於完成賴以建立英雄名望的十二件苦勞,也為自己奠定堅忍不拔的形象。
海克力斯原本以Alkeides 行世, 意思是「阿爾開俄斯(Alkaios) 之孫」,皮緹雅卻以Herakles 稱呼,從此定名。這個名字是Hera(希拉)後接kleos(榮耀),暗喻「希拉的榮耀」。希拉的迫害成就海克力斯永垂不朽的聲名,甚至被雅典人視為’’pathos’’(希臘文「一個人遭遇的具體經驗,苦難」)的化身,接著被羅馬人尊為天下第一英雄,甚至產生’’Herculean task’’ 這個英文慣用語,意思是「艱鉅的任務」。他在完成這些任務的過程中到過陸地的西極,在大海和洋川的出入口樹立一對「海克力斯柱」(Pillars of Herakles),為的是警告世人「往西一步就死無葬身之地」。
海克力斯完成十二件苦勞之後,再度因為偷牛事件而犯下殺人罪。為了賺取贖金, 他成為呂底亞(Lydia) 女王翁法烈(Omphale) 的奴隸。期滿之後,他率領六艘船,號召一批英雄志願軍攻擊特洛伊。他的目的是復仇。復什麼仇?
洗劫特洛伊
話說從頭。《伊里亞德》1.399 提到宙斯曾面臨天界革命的威脅,波塞冬(Poseidon) 和阿波羅是參加造反的兩位男神。宙斯秋後算帳,指派他們協助勞梅東(Laomedon) 建城牆。完工之後,兩位神索求事先約定的酬勞,被拒(《伊里亞德》21.442-57)。因此,阿波羅降下瘟疫,波塞冬則派遣海妖,聯手肆虐特洛伊。神諭告知勞梅東犧牲女兒賀溪娥妮(Hesione) 是唯一的解方。勞梅東迫於無奈,把公主綁在礁岩上獻給海妖。海克力斯路過該地,得知其事,與國王達成協議:他殺死海妖並釋放公主之後,國王將宙斯賞賜的神駒轉贈給他。勞梅東又一次食言,海克力斯因此大怒,發兵攻打特洛伊。
戰爭開打,帖拉蒙(Telamon) 率先破城。海克力斯容不下有人立下比自己更大的功,舉劍逼近。帖拉蒙急中生智,蹲下堆石。海克力斯問幹什麼,帖拉蒙答「造祭臺獻給無敵勇士海克力斯」,意思是「海克力斯你是辟災致勝的英雄,理當接受崇拜」。於是,戰後敘功,剛獲得自由的賀溪娥妮成為俘虜,海克力斯把她賞給帖拉蒙。眾王子中唯一戰火餘生的波達凱斯(Podarkes) 也被俘。賀溪娥妮摘下頭巾(即付出貞操) 為哥哥贖身。波達凱斯從此改稱普瑞阿摩斯(Priamos = Priam,希臘文priamai 是「購買」)。
海克力斯之死
海克力斯戰後賦歸途中,希拉掀暴風為難,惹怒宙斯。宙斯以金線綑希拉的雙手,又在她的腳下綁兩個鐵鉆,吊在奧林帕斯山(《伊里亞德》14.250-9, 15.18-30)。海克力斯得宙斯之助脫險後,在伯羅奔尼撒一連串的戰役所向無敵,先後征服西北部的埃利斯(Elis),西部的皮洛斯,南部的拉凱代蒙,以及中部的阿卡底亞。這段經歷濃縮了青銅時代赫林子裔入主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歷史。
海克力斯征服伯羅奔尼撒之後,來到科林斯灣北岸埃托利亞(Aitolia) 境內的卡律東(Kaludon) , 和河神阿科洛俄斯(Akheloios) 比武,贏得新娘蝶雅妮瑞(Deianeira)。新婚的他,依舊為功業奔波。這次是征伐希臘東岸最大的離島埃維亞(Euboea,今稱Evia),帶回島上俄卡利亞(Oikhalia) 王國的公主易娥烈(Iole)。蝶雅妮瑞聽到丈夫移情別戀的風聲,使用法術要挽回情勢,卻誤把毒衣當作情趣衣送給丈夫。海克力斯穿上身, 瞬間烈焰灼身而亡。索福克里斯(Sophokles , 公元前497/6-前406/5)的悲劇《翠基斯少女》(Trakhiniai) 鋪陳這段插曲,在濃烈的情慾色調增補畫龍點睛的一筆。悲劇主角海克力斯臨終的遺言是交代兒子許洛斯(Hullos) 務必實現父親的心願,娶易娥烈為妻。我說這個結局是「畫龍點睛」,因為海克力斯的一生體現天父宙斯的父權意識。
羅馬詩人奧維德在他的變形神話史,揮灑近乎巴洛克風格的筆觸,渲染肉胎成神的首例。按《變形記》9.230-72,海克力斯強忍劇痛,登上俄塔(Oeta) 山頂,伐木搭出高聳的火葬柴堆,硬是把毒衣情火變成鳳凰自焚。母親遺傳的肉體火化無遺,父親遺傳的靈魂升天變形,成為星光熠熠的武仙座。雖然性別意識形態昭然若揭,《變形記》9.400-1 暗示宙斯的兒子海克力斯和希拉的女兒赫蓓(Hebe) 婚配成佳偶,這意味著宙斯和希拉和解。希臘神話源遠流長的兩性戰爭終於奏出休止符。
海克力斯生性暴烈又愛慕虛榮,或許稱得上草莽英雄,卻沾不上文明教化的邊。他生平富有人文趣味的經驗大體上是後荷馬時代踵事增華,如《神話大全》2.7.2 說他「創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為伯羅奔尼撒半島(「佩羅普斯之島」)的名祖佩羅普斯(Pelops) 建祭臺,為十二位奧林帕斯神建六座祭臺」。他的死亡備極哀榮,最主要的理由離不開他的兩個身分:他既是第一位希臘英雄,又是最後一位「神子」(=宙斯/天父之子)。這兩個身分共同表明海克力斯是赫林子裔原鄉記憶的化身。意義尤其重大的是,從兩性關係的角度來看,他的死亡為希臘神話建構父權論述畫上句點,男權大革命在天界大功告成。
英雄的始祖出世
阿柯美妮的丈夫安菲崔翁(Amphitruon) 前往底比斯參戰時,宙斯假冒丈夫的身分和她睡了一覺,生下神種海克力斯。細節值得一提的是三種不同的版本:《伊里亞德》19.91-136 強調宙斯和希拉的齟齬,這是希臘神話的一個母題;阿波羅多若斯《神話大全》2.5.8 特別提到宙斯為了延長春宵時光而把夜晚時間加倍;奧維德的《變形記》9.281-323 由阿柯美妮對孫媳婦回憶長達七天七夜的生產痛經驗,陰性書寫的筆觸獨步上古文學。
海克力斯八個月大時,希拉指派兩條蛇爬進他的搖籃,想要害死他,卻被他徒手捏死。希拉貴為希臘的天后,當然...
作者序
這是有相當共識的說法:歐洲文化源自希臘,希臘歷史源自荷馬史詩。荷馬史詩是歐洲文化的紀念碑,紀念愛琴海青銅文明輝煌盛世的結束,揭開歐洲歷史的新紀元。荷馬史詩也是希臘口傳詩歌的墓誌銘,記載印歐人殖民最南端的希臘語族群口語創作英雄詩歌傳統的結束,孕育萬紫千紅的歐洲文學史。歸在荷馬名下的兩部史詩《伊里亞德》和《奧德賽》取材於亞洲城市特洛伊的滅亡。因此,閱讀荷馬無異於喚醒一段遺忘的歷史,也是體驗一場記憶的重生。
要了解「紀念碑」緬懷的對象,有必要了解特定的歷史背景,所以本書從印歐語族群的擴張運動切入。要了解「墓誌銘」記載的功德,有必要闡明功德的餘蔭,所以本書以基督教史詩收尾。要想透過荷馬史詩體驗記憶的重生,有兩個管道。一個是從荷馬史詩蔚然成學的縱切面著手,另一個是從《伊里亞德》和《奧德賽》這兩部史詩的橫剖面著手。使用隱喻措詞,荷馬史詩在公元前約800 年發芽,經歷一千三百年茁長成神木。本書雙管齊下,先順著這棵枝繁葉茂的知識樹的樹幹軸心切開,呈現荷馬學的緣起、流變與趨勢。在另一方面,本書截斷樹幹,分析史詩文本質地,觀察在特定的時空採取特定的觀點所見到的景象。特定的時空是此時此地的臺灣,特定的觀點是我個人的文學見地。見地由史觀和史識交織而成,兼顧史觀和史識的見地必然使人大開眼界,我希望本書有示例舉隅之效。
特洛伊戰爭標記愛琴海青銅文明的結束。《伊里亞德》回顧希臘人對於那一場戰爭的集體記憶,透過記憶中理想的圖像呈現戰爭對人性的考驗。《奧德賽》轉而追尋因戰爭而失落的記憶,透過追尋的過程呈現記憶對人的意義。兩部荷馬史詩是歐洲文學的源頭,分別承載族群記憶和個體記憶重生的結果。
一如歷史有族群與個人之分,記憶有集體與個體之分。《伊里亞德》以批判的眼光回顧族群的記憶,從中透露喚醒記憶有重生之德。《奧德賽》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個體的記憶,彰顯有涯之生追憶前塵的重生經歷。記憶在時光陰影中顯像,由於記憶的深度而立體成形,而引人回味。可資回味的記憶必定有故事的材料。可是,荷馬不甘於只講故事,也不甘於一味強調意義所在。這兩個不甘使得《伊里亞德》和《奧德賽》在神木如林的文學世界挺拔參天一枝獨秀。本書無非是要說明挺拔與獨秀之所在,邀請讀者共同欣賞神木林區最偏僻卻也最醒目的一座大觀園。配得上「大觀園」這個隱喻的文學作品必定是形式與意義互相輝映,也必定有助於培養讀者的史觀與史識。此所以第二和第三這兩章的介紹有其必要。
《伊里亞德》和《奧德賽》的旨趣可以從本書分析的主題看出。《伊里亞德》的主題是「儀軌有道」,《奧德賽》的主題是「歌路有節」。「儀軌」和「歌路」分別是這兩部史詩聚焦最清晰的隱喻。《伊里亞德》描寫英雄的世界依照眾所公認而心照不宣的一套民俗禮法在運作,即使戰火方酣也可以有戰爭之道。儀式是民俗禮法的體現,儀式通行意味著有常軌可以行大道。《奧德賽》以英雄世代襯托戰後歌舞昇平的世界,詩歌演唱的內容足以透過記憶的承傳形成歷史的長河。以長河隱喻歷史意味著「有規律可循的流動」,正是希臘文「節奏」的本意。歌唱有如槳帆船運載記憶穩穩航向未來, 槳葉拍打水路必有「節奏」。我希望能夠在書中辯明,荷馬史詩一如神話,不是只有故事,而是深入故事別有洞天。
關於荷馬史詩,以訛傳訛的繆見罄竹難書。信手舉最常見的三個訛傳。把《伊里亞德》詩中阿基里斯和帕楚克洛斯的關係說成同性戀,誤以為親密的戰友同志就是同性戀。把《奧德賽》的標題和詩中主角奧德修斯混為一談,誤以為「奧德賽」是人名。把神話故事和神話原典混為一談,誤以為荷馬史詩只是述說神話故事。錯,錯,錯,速食文化不求甚解連三錯!如果不知道為什麼錯誤,那麼本書值得推薦;如果想知道正確的答案,那麼這本書值得一讀。
寫出如前文摘要介紹的一本書,既已畫龍,理當點睛。藉這個機會把這整本書的「見地」小結如下。
由於荷馬無與倫比的詩歌造詣,承載集體記憶的口傳史詩成為絕響。因個人意識勃興而產生的文人史詩在人生觀與時間觀出現新的意趣。反映在史詩創作的敘事模式,朝特定目標前進的線性敘述取代永恆回歸的環狀結構。在兩性關係則是性別糾葛取代同性情誼。經歷中古時代宗教信仰大一統的局面,但丁和米爾頓承襲史詩的傳統,卻高舉基督教的大纛,但旨趣大相逕庭。但丁獨尊基督教觀點,寫出一部宇宙書,米爾頓採取宗教改革的觀點,描繪一座基督城。信徒愛上帝的信念讓位給上帝愛人類,上帝則從人生經驗的終極仲裁一變而為寬容與悲憫的道德典範。
前述史詩的走向反映歐洲的文化史進程。英雄的偉業根基因史詩的演變而改變。口傳史詩以實體城牆界定土地的認同,文人史詩以文化城牆界定族群的認同,基督教史詩以信仰城牆界定宗教的認同。隨認同本質的改變,地理空間不斷廣化。口傳史詩強調體驗,是具體的身體經驗;文人史詩強調閱歷,是眼界展現的歷史敘述;基督教史詩強調自傳色彩,是個體的想像經驗。和地理空間的廣化同步發展的是心靈空間的深化,其主旋律為生死的辯證:口傳史詩直面死亡的必然,文人史詩探索不朽的可能,基督教史詩追尋永生的意義。這一場生死的辯證兼具心理與情感雙重意義。就心理意義而言,史詩始於面對死亡,經由認識死亡,最後超越死亡。就情感意義而言,口傳史詩寄意「友愛」(philos = friendly, loving),文人史詩寄意「虔誠」(pietas = piety) , 基督教史詩寄意「熾情」(passio =passion)。
就這樣,本書透過史詩的流變,管窺歐洲文化景觀的嬗遞。主題景點當然是獨占四章的荷馬史詩。行文當中以括號附加專有名詞和關鍵詞的原文。專有名詞和關鍵詞以一般讀者熟悉的英文拼法為主,只有極少數情非得已的情況附希臘文。以羅馬字母拼寫希臘文有不同的書寫習慣,下列對照表標示兩種通用的拼寫方式:
ai = ae
-e = -a
-ei = -i
k = c
oi = oe
-os = -us
-u- -y-
拉丁文和羅馬化的希臘文之後的數學等號(=) 附記英文的同義詞。括號也用於標示引用史詩原文的行碼:阿拉伯數字以整數代表卷碼,小數點之後是行碼。引用史詩原文都是我自己的中譯。其中荷馬的兩部史詩《伊里亞德》和《奧德賽》,由書林出版社分別於2018 和2021 年出版譯注本。此外,書中數度提及歷史之初的一場大變革,父神崇拜取代母神信仰所反映社會制度與兩性關係的改變,其神話表述名為「男權大革命」,是依據我在《陰性追尋:西洋古典神話專題之一》書中所論,該書由暖暖書屋在2013 年出版。
這是有相當共識的說法:歐洲文化源自希臘,希臘歷史源自荷馬史詩。荷馬史詩是歐洲文化的紀念碑,紀念愛琴海青銅文明輝煌盛世的結束,揭開歐洲歷史的新紀元。荷馬史詩也是希臘口傳詩歌的墓誌銘,記載印歐人殖民最南端的希臘語族群口語創作英雄詩歌傳統的結束,孕育萬紫千紅的歐洲文學史。歸在荷馬名下的兩部史詩《伊里亞德》和《奧德賽》取材於亞洲城市特洛伊的滅亡。因此,閱讀荷馬無異於喚醒一段遺忘的歷史,也是體驗一場記憶的重生。
要了解「紀念碑」緬懷的對象,有必要了解特定的歷史背景,所以本書從印歐語族群的擴張運動切入。要了...
目錄
自序
一、荷馬史詩的歷史背景
1.1 印歐語族群擴張運動
1.1.1 「舊歐洲」
1.1.2 原始印歐語的誕生
1.1.3 印歐語的分化
1.2 歷史與神話
1.2.1 神話故事與神話原典
1.2.2 神話原典與歷史事實
1.2.3 希臘人進入歷史的視野
1.2.4 希臘神話的原鄉
1.2.5 歐洲歷史新紀元
二、《伊里亞德》與《奧德賽》的作者
2.1 荷馬之疑
2.1.1 荷馬史詩
2.1.2 荷馬其人
2.2 橫空問世荷馬學
2.2.1 上古時期
2.2.2 中古時期
2.2.3 近代時期
2.2.4 考古學
2.2.5 口傳詩學
2.2.6 表演文本
2.3 貫串古今雲霄羽
2.3.1 認知口傳詩學
2.3.2 歷史邊疆的拓展
2.3.3 文學傳統的溯源
2.4 荷馬的世界
2.4.1 唱詩人荷馬
2.4.2 「我們希臘人」
2.4.3 尋找自己的名稱
三、史詩傳統的形成
3.1 讀荷馬唱詩
3.1.1 敘事觀點
3.1.2 格律
3.1.3 聲韻修辭
3.2 看見宇宙
3.2.1 三重結構二元觀
3.2.2 人神同形同性論
3.2.3 天神干預
3.2.4 原型結構
3.3 史詩成規
3.3.1 英雄的形象
3.3.2 套語
3.3.3 描述詞
3.3.4 類型場景
3.3.5 展延明諭
四、《伊里亞德》儀軌有道
4.1 特洛伊戰爭神話
4.1.1 第一次特洛伊戰爭
4.1.2 第二次特洛伊戰爭
4.2 情節概述
4.2.1 第一部分:心結壁壘(卷1-7)
4.2.2 第二部分:沙場烽火(卷8-12)
4.2.3 第三部分:淬鏡練形(卷13-17)
4.2.4 第四部分:明心見性(卷18-24)
4.3 主題探討
4.3.1 情節結構
4.3.2 聚焦阿基里斯
4.3.3 儀軌有道
4.4.4 阿基里斯的盾牌
五、《奧德賽》歌路有節
5.1 特洛伊戰爭餘波
5.1.1 戰爭尾聲
5.1.2 木馬劫城
5.1.3 城破山河在
5.1.4 歸鄉路漫漫
5.2 情節概述
5.2.1 第一部分:王子成年(卷1-4)
5.2.2 第二部分:英雄返鄉(卷5-8)
5.2.3 第三部分:大海浮蹤(卷9-12)
5.2.4 第四部分:父子會合(卷13-16)
5.2.5 第五部分:變裝返家(卷17-20)
5.2.6 第六部分:重整家園(卷21-24)
5.3主題探討
5.3.1 情節結構
5.3.2 奧德修斯的記憶
5.3.3 奧德修斯的弓
5.3.4 歌路有節
六、史詩的變革
6.1 史詩的新傳統
6.1.1 個體心聲的崛起
6.1.2 史詩成規的演化
6.2 文人史詩的問世
6.2.1 阿波婁尼俄斯《阿果號之旅》
6.2.2 維吉爾《埃涅伊德》
6.2.3 奧維德《變形記》
6.3 史詩傳統的蛻變
6.3.1 禁慾文學的先聲
6.3.2 宮廷愛情的理念
6.4 基督教史詩
6.4.1 但丁《神曲》
6.4.2 米爾頓《失樂園》
6.4.3 神話進入歷史
參考書目
圖片出處
自序
一、荷馬史詩的歷史背景
1.1 印歐語族群擴張運動
1.1.1 「舊歐洲」
1.1.2 原始印歐語的誕生
1.1.3 印歐語的分化
1.2 歷史與神話
1.2.1 神話故事與神話原典
1.2.2 神話原典與歷史事實
1.2.3 希臘人進入歷史的視野
1.2.4 希臘神話的原鄉
1.2.5 歐洲歷史新紀元
二、《伊里亞德》與《奧德賽》的作者
2.1 荷馬之疑
2.1.1 荷馬史詩
2.1.2 荷馬其人
2.2 橫空問世荷馬學
2.2.1 上古時期
2.2.2 中古時期
2.2.3 近代時期
2.2.4 考古學
2.2.5 口傳詩學
2.2.6 表演文本
2.3 貫串古今雲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