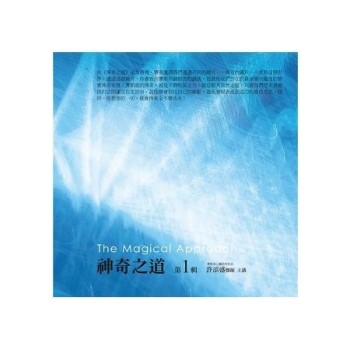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世變中的畫意詩心:晚清民初題畫詩詞研究的圖書 |
 |
世變中的畫意詩心: 晚清民初題畫詩詞研究 作者:柯秉芳 出版社: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8-01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世變中的畫意詩心:晚清民初題畫詩詞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以清代盛行之題畫詩詞為研究,分別藉由黃爵滋〈如此江山圖〉、章壽麟〈銅官感舊圖〉、余治《江南鐵淚圖》、侯名貴〈疏勒望雲圖〉、王鵬運〈春明感舊圖〉、戴三錫〈春帆入蜀圖〉、高旭〈花前說劍圖〉七個極具時代特色與政治隱喻的圖畫主題作為探究,勾勒自白蓮教之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陝甘回亂、新疆回亂、庚子事變,乃至滿清滅亡、民國建立的一整段歷史,探討士人如何在晚清民初波詭雲譎的時代巨變中,轉借題畫為隱喻,透過「詩言志」、「詞緣情」的婉轉喻託,隱微道出自我的處境與憂世之感;並更進一步從中尋繹同代人的共相特性,甚而延伸至跨時代題詠者的創作心緒,探析士人如何透過題詠畫作達到抒發身世之感與相互慰藉的目的,從而展現當代時人的世相,以及他們共有的「集體記憶」,凸顯晚清民初題畫詩詞的「存史」價值。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柯秉芳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曾任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兼任助理教授。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專修詞學,兼及詩學、文圖學、文學批評領域。著有碩士論文《徐釚詞學及其詞研究》、博士論文《畫意心曲──晚清民初題畫詩詞傷時憂國之研究》;另有多篇學術論文發表,範圍包括:詞學、題畫文學、版本學、考據學、現代小說等。
柯秉芳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曾任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兼任助理教授。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專修詞學,兼及詩學、文圖學、文學批評領域。著有碩士論文《徐釚詞學及其詞研究》、博士論文《畫意心曲──晚清民初題畫詩詞傷時憂國之研究》;另有多篇學術論文發表,範圍包括:詞學、題畫文學、版本學、考據學、現代小說等。
目錄
序 張宏生
總 論
第一章 晚清民初題畫詩詞興盛的背景
第二章 鴉片戰爭下的制敵良方──
〈如此江山圖〉題詠與黃爵滋之禁煙倡議
第三章 湘軍抗擊太平軍的護國之戰──
〈銅官感舊圖〉題詠與章壽麟的宦途得失
第四章 太平軍戕害江南百姓亂離生活史
──《江南鐵淚圖》題詠與余治的勸捐宣教
第五章 左軍征討捻亂回變的思親念鄉之情
──〈疏勒望雲圖〉題詠與侯名貴從軍效國之志
第六章 戊戌變法後沉鬱悲壯的詞境
──〈春明感舊圖〉題詠與王鵬運之感時憶友
第七章 清亡之後思賢念遠的集體追憶
──〈春帆入蜀圖〉題詠與清遺民的故國之思
第八章 南社社友革命未竟的失意與期許
──〈花前說劍圖〉題詠與高旭的革命之志
結 論
參考文獻
後 記
總 論
第一章 晚清民初題畫詩詞興盛的背景
第二章 鴉片戰爭下的制敵良方──
〈如此江山圖〉題詠與黃爵滋之禁煙倡議
第三章 湘軍抗擊太平軍的護國之戰──
〈銅官感舊圖〉題詠與章壽麟的宦途得失
第四章 太平軍戕害江南百姓亂離生活史
──《江南鐵淚圖》題詠與余治的勸捐宣教
第五章 左軍征討捻亂回變的思親念鄉之情
──〈疏勒望雲圖〉題詠與侯名貴從軍效國之志
第六章 戊戌變法後沉鬱悲壯的詞境
──〈春明感舊圖〉題詠與王鵬運之感時憶友
第七章 清亡之後思賢念遠的集體追憶
──〈春帆入蜀圖〉題詠與清遺民的故國之思
第八章 南社社友革命未竟的失意與期許
──〈花前說劍圖〉題詠與高旭的革命之志
結 論
參考文獻
後 記
序
序
題畫之作在中國至少可以追溯到戰國的屈原,據王逸〈天問序〉:「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恠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瀉愁思。」屈原的創作衝動是由於看到楚王廟和楚國公卿的祠堂中的各種圖畫,乃撫今追昔,呵壁問之,寫下〈天問〉這首千古名篇。題為東漢劉向所撰的《列女傳》是中國婦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據劉向記載,他「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五〈屏風〉)。顯示劉向為了增強其生動性、直觀性,乃將相關內容畫在屏風上,也就是有意識地採取文圖結合的形式。作為一個傳統,這一形式影響中國文化甚深,後來紙本(或絹本)繪畫興盛起來,以詩(詞)題畫者蔚為大觀,就成為中國文學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特色,吸引了不少作者投入其中。
一般來說,詩是時間的藝術,畫是空間的藝術。前者的優勢在於能夠寫出過程,體現發展;後者的優勢在於能夠凝固瞬間,富有暗示。傳統的文藝理論有詩畫一體之說,但人們也認識到,並不是所有的詩畫都能一體。從本質上看,無論是詩還是畫,想像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於畫來說,由於受到空間的限制,無法將所有元素都表現出來,尤其需要調動想像去加以填補。以詩詞題在畫上,內容的關合度很深,本身就是一個整體,即使從形式上,配上題詠的畫面,也是一個藝術的整體。不過畫作的空間有限,題詠作為一種公眾行為,有時範圍甚廣,規模甚大,形成了一個超越具體空間的共同體。即使如此,所有的題詠,無論怎樣外溢,都還是通向特定的畫,在這個意義上,題詠和畫作仍然構成一個整體。至於其效果,也有可說者。北宋范仲淹的名作〈岳陽樓記〉,據說是看了他的好友、當時的岳州知州滕宗諒寄來的一幅〈洞庭晚秋圖〉而寫出來的,原圖至今不存,但即使仍然存在,大約也掩蓋不住范記在寫景抒情上的光輝,而且,寫這篇〈岳陽樓記〉時,范仲淹身處千里之外的河南鄧州,此前他並未到過洞庭湖,更沒有登過岳陽樓。這個例子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讓我們轉換不同角度去思考畫作及其題詠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可以認為,當詩(詞)和畫構成了一種互動關係時,顯示出來的是一種新的書寫樣態,能夠體現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近些年來,在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中,文圖學方興未艾,帶有前沿性,不少學者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也出現了不少優秀的研究成果。在柯秉芳博士的這部著作中,也能看到這種學術風氣的影響,不過作者又有自己的選擇角度和考察方向。
這本書在時間上,以中國近代社會為大背景;在空間上,涵蓋當時中國的主要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內容上,以家國世變為主要對象,涉及的歷史事件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捻軍之事、戊戌變法、清朝滅亡、南社活動等;在文體上,以畫為中心,題詠之作則是詩或詞;在創作主體上,涉及文人士大夫的各個不同階層。從而不僅展示了一幅幅激烈變動時期的時代歷史畫卷,也能從一個側面揭示出當時文人士大夫的心靈歷史,以及通過文體的交叉互動所帶來的一些新鮮感受。
和詩歌一樣,中國的繪畫在娛情的同時,往往也有言志的功能,自進入近代以來,創作者對此似乎有了更為自覺的意識,尤其是面對重大的社會變化,往往成為主動性的行為。事實上,畫的作者本身經常也就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參與者。湯貽汾的〈如此江山圖〉以金焦二山作為對象,或許和鴉片戰爭有著直接的淵源,因為鴉片戰爭中的鎮江之戰,正是南京安危存亡的關鍵,但是,湯貽汾更沒有缺席的是幾年之後開始的太平天國戰爭。湯貽汾詩(詞)書畫俱佳,同時又有武官的身分,太平軍進攻南京,他組織抵抗,城破後,投池以殉。在那前後的幾十年間,他是文壇的一個標杆性人物,在許多作家筆下不斷被提及,被歌詠,滿足了人們對一個文人加官員加戰士的身分的完美想像。另一個活躍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的余治,不僅在戰爭中展開了豐富的文藝活動,而且有感於江南的滿目瘡痍,作《江南鐵淚圖》,發起募捐,顯示了巨大的影響力。湯、余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他們既是文藝作品的創作者,又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或參與者,這無疑增強了現場感,也增強了感染力,他們的作品帶有生命書寫的意義。
文學藝術發生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是對創傷的言說,這種言說,往往不僅喚起了記憶,而且還促進了其傳播和接受,在不同的文體中,或者在各種交叉的文體中,將時代發展、歷史進程、社會變化、倫理表現、文化狀況、主體認同等各種因素聯繫起來,塑造出多元的價值。這種價值與「詩可以怨」的觀念密切相關,又廣泛涉及記憶重塑、心理認同、符號記事等,呈現出具有現場感的震撼書寫。秉芳的這部著作,選擇近現代社會中與世變密切相關的繪畫作品及其題詠,縱向看,貫穿了不同的歷史事件,橫向看,涵蓋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和作品,堪稱是一種集體記憶,呈現出畫史、詩(詞)史相結合的獨特樣貌。
秉芳從本科開始,一直到博士畢業,一直在臺灣東吳大學求學。東吳大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學風樸實,尤其注重文獻。我有兩位在1990年代初就認識的朋友,一位是王國良教授,一位是林慶彰教授,都和東吳大學深有淵源。人所共知,研究時段較近的文學,文獻往往太雜,而且大多沒有經過系統整理,需要細緻爬梳,認真考訂。這部著作雖然只是研究7幅圖,但是涉及的層面很多,不僅相關的本事需要一一還原,而且涉及的人員,以及彼此的關係,也需要抽絲剝繭般地一點一點弄清楚,纔能拼接出一幅真正完整的畫面,這些地方都能看出秉芳的用力之處。
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歷史中蘊含著非常多的資源,相當一部分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即以文圖的研究來說,也有不少內容可以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我所主持的《全清詞》編纂,現在已經進行到「咸同卷」以後。在編纂中,我們發現,清詞中的題畫作品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層面之豐,非常突出,值得關注,其中的價值意義也有待於進一步發掘。特別是,清朝距離現在還不是太遙遠,不少畫作仍然存世,結合物質文化去研究類似的課題,一定會開啟新的學術空間。清詞如此,想來清詩更是如此。因此,我也對清代文學中的這一領域出現更多的優秀研究成果充滿期待。
張宏生
2022年6月10日序於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
題畫之作在中國至少可以追溯到戰國的屈原,據王逸〈天問序〉:「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恠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瀉愁思。」屈原的創作衝動是由於看到楚王廟和楚國公卿的祠堂中的各種圖畫,乃撫今追昔,呵壁問之,寫下〈天問〉這首千古名篇。題為東漢劉向所撰的《列女傳》是中國婦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據劉向記載,他「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五〈屏風〉)。顯示劉向為了增強其生動性、直觀性,乃將相關內容畫在屏風上,也就是有意識地採取文圖結合的形式。作為一個傳統,這一形式影響中國文化甚深,後來紙本(或絹本)繪畫興盛起來,以詩(詞)題畫者蔚為大觀,就成為中國文學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特色,吸引了不少作者投入其中。
一般來說,詩是時間的藝術,畫是空間的藝術。前者的優勢在於能夠寫出過程,體現發展;後者的優勢在於能夠凝固瞬間,富有暗示。傳統的文藝理論有詩畫一體之說,但人們也認識到,並不是所有的詩畫都能一體。從本質上看,無論是詩還是畫,想像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於畫來說,由於受到空間的限制,無法將所有元素都表現出來,尤其需要調動想像去加以填補。以詩詞題在畫上,內容的關合度很深,本身就是一個整體,即使從形式上,配上題詠的畫面,也是一個藝術的整體。不過畫作的空間有限,題詠作為一種公眾行為,有時範圍甚廣,規模甚大,形成了一個超越具體空間的共同體。即使如此,所有的題詠,無論怎樣外溢,都還是通向特定的畫,在這個意義上,題詠和畫作仍然構成一個整體。至於其效果,也有可說者。北宋范仲淹的名作〈岳陽樓記〉,據說是看了他的好友、當時的岳州知州滕宗諒寄來的一幅〈洞庭晚秋圖〉而寫出來的,原圖至今不存,但即使仍然存在,大約也掩蓋不住范記在寫景抒情上的光輝,而且,寫這篇〈岳陽樓記〉時,范仲淹身處千里之外的河南鄧州,此前他並未到過洞庭湖,更沒有登過岳陽樓。這個例子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讓我們轉換不同角度去思考畫作及其題詠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可以認為,當詩(詞)和畫構成了一種互動關係時,顯示出來的是一種新的書寫樣態,能夠體現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近些年來,在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中,文圖學方興未艾,帶有前沿性,不少學者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也出現了不少優秀的研究成果。在柯秉芳博士的這部著作中,也能看到這種學術風氣的影響,不過作者又有自己的選擇角度和考察方向。
這本書在時間上,以中國近代社會為大背景;在空間上,涵蓋當時中國的主要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內容上,以家國世變為主要對象,涉及的歷史事件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捻軍之事、戊戌變法、清朝滅亡、南社活動等;在文體上,以畫為中心,題詠之作則是詩或詞;在創作主體上,涉及文人士大夫的各個不同階層。從而不僅展示了一幅幅激烈變動時期的時代歷史畫卷,也能從一個側面揭示出當時文人士大夫的心靈歷史,以及通過文體的交叉互動所帶來的一些新鮮感受。
和詩歌一樣,中國的繪畫在娛情的同時,往往也有言志的功能,自進入近代以來,創作者對此似乎有了更為自覺的意識,尤其是面對重大的社會變化,往往成為主動性的行為。事實上,畫的作者本身經常也就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參與者。湯貽汾的〈如此江山圖〉以金焦二山作為對象,或許和鴉片戰爭有著直接的淵源,因為鴉片戰爭中的鎮江之戰,正是南京安危存亡的關鍵,但是,湯貽汾更沒有缺席的是幾年之後開始的太平天國戰爭。湯貽汾詩(詞)書畫俱佳,同時又有武官的身分,太平軍進攻南京,他組織抵抗,城破後,投池以殉。在那前後的幾十年間,他是文壇的一個標杆性人物,在許多作家筆下不斷被提及,被歌詠,滿足了人們對一個文人加官員加戰士的身分的完美想像。另一個活躍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的余治,不僅在戰爭中展開了豐富的文藝活動,而且有感於江南的滿目瘡痍,作《江南鐵淚圖》,發起募捐,顯示了巨大的影響力。湯、余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他們既是文藝作品的創作者,又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或參與者,這無疑增強了現場感,也增強了感染力,他們的作品帶有生命書寫的意義。
文學藝術發生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是對創傷的言說,這種言說,往往不僅喚起了記憶,而且還促進了其傳播和接受,在不同的文體中,或者在各種交叉的文體中,將時代發展、歷史進程、社會變化、倫理表現、文化狀況、主體認同等各種因素聯繫起來,塑造出多元的價值。這種價值與「詩可以怨」的觀念密切相關,又廣泛涉及記憶重塑、心理認同、符號記事等,呈現出具有現場感的震撼書寫。秉芳的這部著作,選擇近現代社會中與世變密切相關的繪畫作品及其題詠,縱向看,貫穿了不同的歷史事件,橫向看,涵蓋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和作品,堪稱是一種集體記憶,呈現出畫史、詩(詞)史相結合的獨特樣貌。
秉芳從本科開始,一直到博士畢業,一直在臺灣東吳大學求學。東吳大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學風樸實,尤其注重文獻。我有兩位在1990年代初就認識的朋友,一位是王國良教授,一位是林慶彰教授,都和東吳大學深有淵源。人所共知,研究時段較近的文學,文獻往往太雜,而且大多沒有經過系統整理,需要細緻爬梳,認真考訂。這部著作雖然只是研究7幅圖,但是涉及的層面很多,不僅相關的本事需要一一還原,而且涉及的人員,以及彼此的關係,也需要抽絲剝繭般地一點一點弄清楚,纔能拼接出一幅真正完整的畫面,這些地方都能看出秉芳的用力之處。
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歷史中蘊含著非常多的資源,相當一部分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即以文圖的研究來說,也有不少內容可以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我所主持的《全清詞》編纂,現在已經進行到「咸同卷」以後。在編纂中,我們發現,清詞中的題畫作品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層面之豐,非常突出,值得關注,其中的價值意義也有待於進一步發掘。特別是,清朝距離現在還不是太遙遠,不少畫作仍然存世,結合物質文化去研究類似的課題,一定會開啟新的學術空間。清詞如此,想來清詩更是如此。因此,我也對清代文學中的這一領域出現更多的優秀研究成果充滿期待。
張宏生
2022年6月10日序於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