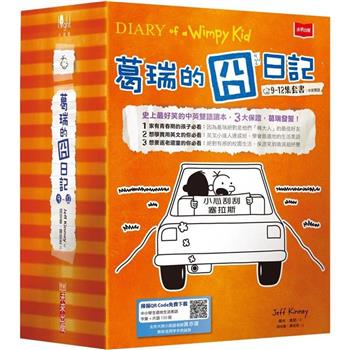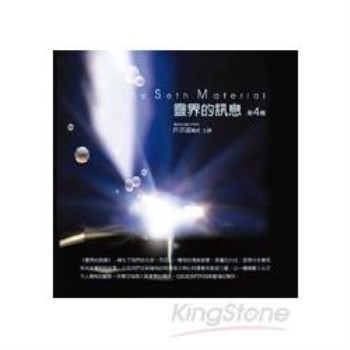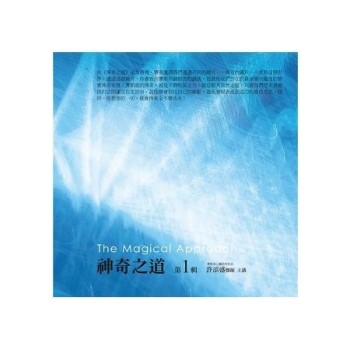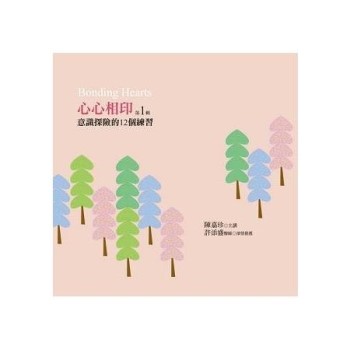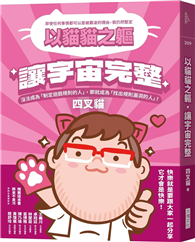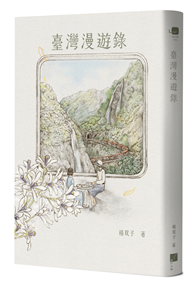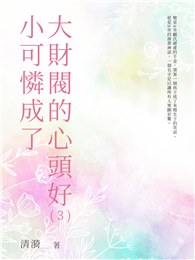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現代詩學(精)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三民網路書店 評分:
圖書名稱:現代詩學(精)
- 圖書簡介
「現代詩學」是民國建國以來,新文學運動之後,第一本對現代詩做完整檢視,全面探討的最具系統的文學理論書籍。全書近三十萬字,皇皇巨構,分為「現象論」、「方法論」、「人物論」三大部份。
「現象論」,研析現代詩中呈現之各種不同風貌,諸如鄉愁、時代意識、感覺新貌、奇情諧趣、城鄉衝突等等。
「方法論」則提示現代詩的創作途徑,由意象之開展、想像之追索、雙關與歧義之設定,及於生命感與使命感之確立,內容與形式兼容並包,思精體大,尤具意義。
「人物論」不做全面性的歷史探索,側重於藝術特殊點的闡述,可以做為前面二論之驗證,足堪詩人學者參佐。 - 作者簡介
蕭 蕭
本名蕭水順,台灣彰化人,一九四七年生,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著有詩集「舉目」,散文集「蕭蕭的心跳」,評論集「鏡中鏡」,並與張漢良合編「現代詩導讀」五冊。 - 序
自 序
現代詩的發展已有七十年的歷史了,從胡適的嘗試開始、到今日臺灣都市文學、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以至於大陸年輕一代的朦朧詩陸續出發,中間歷經各種不同的流派、運動,相互之間激盪、推衍,頗有可觀之處。但是,遺憾的是沒有一本全面、深入而具系統的理論書籍予以研析,現代詩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面貌,發展成一種什麼樣的效應,終無具體而可信的驗證,最後,現代詩又會有什麼可能的走向呢?也無專人、專論、專書去探究。一種文體新興,發展到某種階段必有理論、批評相隨而生,但在中國,一直缺乏適當的論評專業人才,偶而興之所至的書評、詩話,吉光片羽,也無法五臟俱全、具體而微地呈現一種有機的生命體,一脈不息的文學源流,或者竟然只是一株殊異而獨立的樹都不可能。所謂詩的民族,是詩的創作旺盛的民族吧!全唐詩的龐大,人所共見,而宋詩的數量又超過全唐詩甚多。今天發表在臺灣報紙、詩刊、雜誌上的詩的數量,一年也在五千首左右,漪哉盛歟!真的是詩的民族。然而,所謂詩的民族,或許不應該只停留在詩人不停創作,而詩法、詩論、詩評、詩學卻未能適時跟進,或解析、或闡述、或者站在迥異的立場予以銓衡、鑑戒吧!一個詩的民族,應該是全民共同關心詩的命脈,有想像傑異的詩人努力創作,有喜好詩情畫意的讀者閱讀,更要有思辨能力高強的評論人才為詩做分析、做解剖,時而演繹,時而歸納,伴著詩的創作形成另一股清流。基於這樣的認識,不揣淺陋,我開始寫作「現代詩學」裏的篇章,在「現象論」中指陳現代詩所共同涵具的面貌,進而溯探現代詩的特質何在。至於現代詩創作途徑的踏勘,則在「方法論」中一一訪求,從最基本的意象的塑造到超現實表現的可能,從層疊修辭的外在形式要求,以至於詩人的生命感與使命感的培養,期能周全兼顧詩的內容與外緣。「人物論」裏則著眼於特殊藝術風貌的闡述,不以全面性的歷史探索為重,全面性重要詩人風格的搜尋則有待於「現代詩史」的寫作了,那或許是下一步我該走的路吧!完整的「現代詩學」的建立,需要詩人、專家共同戮力以赴,當然也非十年、二十年所可達及,而我只是踏出第一步罷了。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寫於臺北 - 目次
自 序
●現象論
現代詩裏「鄉」的面貌
現代詩裏「人」的位置
現代詩裏的時代投影
現代詩裏的社會意識
現代詩裏的中國精神
現代詩裏的傳統詩情
現代詩裏的感覺新貌
現代詩裏的女性意象
現代詩裏的奇情與諧趣
現代詩裏的玄思與哲理
現代詩裏的城鄉衝突
現代詩裏的時空設計
●方法論
意象是詩的第一個面貌
從譬喻中開展詩的世界
轉而化之,所以成詩
對比的力量
層疊便是美──字句的層疊
層疊便是美──形式的層疊
層疊便是美──物類的層疊
想像刺激創作
夸飾刺激想像
詞類的變化
讓感情激盪,再激盪!
兩點之間最美的距離是曲線
詩以含蓄為貴
異中求同與同中求異
雙關與歧義
或岔斷,或跳脫
象徵象徵,象而有徵
超現實的表現手法
結構與節奏
生命感與使命感
●人物論
細論洛夫的一首詩「無岸之河」
論羅門的意象世界
論葉維廉的秩序
青春無怨,新詩無怨──論席慕蓉
政治與詩的邊緣──論苦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