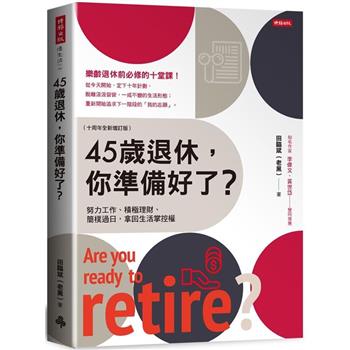中國管理之道的現代詮釋──自序
1699年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在《中國最新事物》一書序言中特別提到,中國的治國之道強於西方,而西方對於自然的知識強於中國。所以他希望西方傳教士們在向中國傳授自然知識的時候,不要忘記把中國的治國之道傳回西方。—這代表了17世紀一代啟蒙思想家對於中國政治、道德、文化的景慕和嚮往。
中國的17、18世紀正是所謂「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鼎盛時期。一方面是專制政體,另一方面又包含著治理國家之道。這就說明了管理之道—它體現著一整套的哲學、思想、制度和技術—的普遍性。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能夠維持如此之久,不能不說有這一管理哲學治國之道的一份「功勞」。
當然,專制制度是必然要失敗的,再「開明」的專制制度也不能取代健全的民主制度,因為所謂的「開明君主」並不等於社會公共意志的結合。所以好的管理之道仍然需要開放的、和諧的、民主的社會制度相配合,才能充分發揮它的作用。
國家是一個集體組織,企業也是一個集體組織,二者的不同在於國家是全面性的生活,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而企業組織只是以經濟發展為終極目標。但是,有關治國之道的政治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價值文化,完全可以為企業的發展帶來更大的活力和更高的境界。簡言之,現代的企業組織,已經處在民主和諧開放的環境中,如果又能夠運用宏觀的管理理念和價值觀念來完成其價值目標,才能更加符合開放社會的需要,真正走向高度和諧、高度繁榮的真善美的人類社會境界。
為什麼幾個世紀以前西方啟蒙思想家讚嘆不已的中國治國之道,近代以來卻走向衰落,既為西方人所否定,也使中國人失去信心了呢?為什麼它非但不能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反而使中國一步一步地落後了呢?這同與之緊密結合的封建專制政治制度有關。如果把專制制度與管理制度分開,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及其所孕育的管理之道,仍然可以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們知道,管理之道具有工具性,可以和不同的社會制度相結合;而專制制度只不過是家族式的政治權威,必須經過現代民主制度的洗禮。但是,專制制度的衰亡並不意味著管理之道的失敗,後者可以經過「淨化」,成為新社會制度的管理工具。因此,中國哲學文化傳統及其管理之道並不因為中國在近代史中政治上的失敗而喪失其內在的價值。
另一方面,西方從17世紀開始,民主國家興起,提倡科學理性、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而尋找新的社會政治權威。盧梭的《民約論》說明真正的權威來自於社會的群體意志,從而奠定了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就奠定了現代民主社會的思想基礎。但是,它並沒有真正解決社會的管理問題。如何使社會真正走向有秩序而又充滿發展的活力,這就需要考慮管理的問題。
韋伯因此提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問題。他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沒有宗教改革所賦予的個人的終極權威,其發展是有限的。西方社會肯定個人創造力和自由發展的權威,這就是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最根本的祕密。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的發展就是憑藉個人的理性、科學的知識、宗教的信念,從而設計出一套管理的方法,去推動和控制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管理科學在西方的誕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工業革命、經濟發展、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
與此相反,中國的管理理念是憑藉對人性的反省與思考,提倡集體主義,突出人的社會價值,結合人的感情需要,運用共同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責任感去實現管理並推動社會的發展。比較東西方的管理理念,前者是人性的社會的發展,後者則是理性的個人的發展;前者曾經同封建專制制度結合在一起,後者則在資本主義的伴同之下發展出來。東西方管理理念上的差異本質上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東西方社會組織的差異,東西方哲學思維方式、價值體驗和歷史經驗的差異。
到了20世紀後半葉,東西方兩種管理思想體系風雲際會,其標誌就是由於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這些具有中國哲學文化背景的國家和地區,在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西方管理學界對於源遠流長的東方管理之道不得不刮目相看。特別是日本,在其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比較自覺和完整地保存了源自中國古代的東方管理之道,把其從政治層面成功地轉移到經濟層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日本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現代化並不意味著一定要走西方發展的道路。在現代管理的理論與實踐中,古老的東方管理之道依然有著不可埋沒的價值。
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我就一直思考著如何以中國哲學文化為基礎,結合東西方兩大管理思想體系的長處,而發展出一套能夠為現代人(包括東方人和西方人)所接受的新的管理哲學。它既能夠包含西方科學管理的精神,又能夠汲取中國哲學管理的智慧,更能夠洞察當代西方管理科學的局限性而加以改進。我所思考的問題並不是當時人們所熱中討論的美日管理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把管理的問題放到更大的歷史空間與現實空間去加以哲學的反省,從而提出一條新的管理學之道。
這一條新的管理學之道,這一套新的管理哲學,我命名為「C理論」。所謂「C」指中國(China)的《易經》(Change)的創造性(Creativity)。它表明,這套新的管理哲學是以中國的文化歷史經驗為背景,以中國哲學思想為基礎,對於現代管理問題所作的思考和回答。中國哲學特別是《易經》哲學是「C理論」的哲學基礎。根據個人的長期研究和體會,《易經》哲學具有宏大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創造性,足可以容納古今中外一切有價值的管理思想和哲學思想。例如,西方的管理具有理性的權威、科學的基礎,但卻缺乏人性的靈活,從個人主義的角度切入,社會的諧和力明顯不足;日本的管理注意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卻過分壓抑了個人的活力和獨創性,同樣缺少靈活性和包容性。而《易經》哲學講「一陰一陽之謂道」,據此我們可以把西方的理性管理作為「陽」,而把日本的人性管理作為「陰」,使二者相互結合,在整體性的基礎即「道」的基礎上把握全面的管理。
本書就是我對管理問題進行長期哲學思考的結果,從1979年我在臺灣正式提出「中國管理科學化,管理科學中國化」的主張迄今已經十五年。在這期間,我來往於美國、日本、新加坡、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等地,為建立中國化的管理哲學,為推進中國式的管理教育,而奔走呼籲。1983年,我應(高雄)中山大學李煥校長的邀請,到該校作「中國現代化管理模式的發展問題」的學術演講。1985年,我在美國創辦了「遠東高級研究學院」,在臺灣建立了「國際中國管理文教基金會」及研究所(後發展成為「國際中國管理研究學院」)。1989年,我作為臺灣大學哲學系的客座教授,應臺大商學院的邀請,為他們的研究生和大學部的學生開設「中國管理哲學」課程,進行「C理論」的系統教育和實用研究;講課內容並在臺灣《經濟日報》和《實業家》雜誌連續發表。1989年,我應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的邀請,在該公司的「名人週」作有關東西方管理哲學比較的演講。1992年,我分別應新加坡華文報業集團和《易經》學會的邀請,先後兩次赴新加坡作「《易經》與中國管理哲學」的講座。從1990年開始,遠東高級研究學院同在北京的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合作,舉辦每屆兩年的高級管理人才研究班,此後,廣州的中山大學、瀋陽的遼寧大學以及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華東理工大學等院校也陸續加入這一管理人才培育計劃。在這些教學和研究的過程中,作為中國式管理哲學的「C理論」得到了不斷的充實和發展。
1993年初,我的學生(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黎紅雷博士,為教學需要,將我有關中國管理哲學的部分論文整理成《C理論:易經管理系統》一書,打印作為內部教材,在上述廣州、深圳、瀋陽、上海等地的高級管理人才研究班中使用,受到了歡迎。1994年6月,黎君應邀來美國夏威夷大學作訪問學者,期間更進一步抽出時間幫助我充實整理本書。
這次整理,我們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面的工作。第一,由我口述,黎君根據錄音編寫成文,最後再由我審定,形成本書的〈本論 C理論的基本內涵〉部分,作為全書的主幹與靈魂。第二,把我歷年來發表的有關論文和講演稿,目前能夠收集到的,進行加工整理,分別編入書中的〈分論 C理論要素分析〉、〈比論 C理論與東西方管理〉、〈綜論 C理論的管理境界〉和〈附論 C理論講演與答問〉部分;有兩篇用英文發表的論文,也由黎君翻譯成中文並編為〈比論〉最後兩章。
黎紅雷君學術思路開闊,思維敏捷,尤其熱心於中國管理哲學的研究事業,近兩年來,他已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等地出版了四部有關專著。在本書的整理和編輯過程中,黎君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勞動,特別是在全書的內容架構、篇章標題、論點闡發、論據充實、文字表述等方面,融進了他本人的許多獨到見解和智慧,對於本書得以完整的形式問世,貢獻良多。
最後,希望讀者不僅把本書作為一部管理學著作,而且作為一部哲學著作。實際上,哲學研究是我的本行。在三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我覺得我做了兩個重要的理論建樹工作:一個是我提出的「本體詮釋學」;另一個就是本書所闡發的「C理論」。前者重於哲學思辯,後者重於管理理論,實際上二者是互相聯繫互為體用的。哲學為管理之體,它是管理的理論基礎和最高表現形式;而管理又為哲學之用,它可以作為哲學思想靈魂的運作之所。我歷來主張,用哲學來闡發管理而又用管理來闡發哲學,用理論來啟發實用而又用實用來啟發理論,最後達到二者並進共榮的化境。是為序。
成中英
1995年5月15日於美國夏威夷大學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C理論─易經管理哲學(二版)的圖書 |
| |
C理論-易經管理哲學 出版日期:2016-12-23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32 |
Social Sciences |
$ 378 |
社會人文 |
$ 378 |
社會人文 |
$ 378 |
企業管理 |
$ 399 |
中國/東方哲學 |
$ 399 |
中文書 |
$ 399 |
管理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C理論─易經管理哲學(二版)
本書是中國哲學與現代管理相互闡發的典範之作。作者以《易經》哲學為基礎,對現代管理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與探索,從而提出了一套命名為「C理論」的新型管理哲學。相對於「A理論」(美式管理)、「Z理論」(日式管理),作為中國管理結晶的「C理論」,既包含了道家的決策哲學、法家的領導哲學、兵家的權變哲學、墨家的創造哲學、儒家的協調哲學,又強調了易在管理中的融合與轉化功能、禪在管理中的超越與切入功能,更結合了現代西方管理理論所指出的管理職能與管理要素。
本書分別就「C理論」的基本內涵、要素分析、東西方管理比較、管理新境界等問題,進行詳盡的論證;並附有作者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部分演講報告及問題解答。閱讀本書,無疑是一種智慧的享受,並可以得到實踐的指南。
作者簡介:
成中英
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現為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曾為臺灣大學哲學系研究所所長、臺灣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教授、國際中國哲學會創會會長、國際易經學會會長、《中國哲學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主編。
主要研究領域為儒家哲學、中西哲學比較。並以《易經》為基礎,創立了「本體詮釋學」的哲學理論。
著作有《中國現代化的哲學省思--傳統與現代理性的結合》、《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科學真理與人類價值》、《儒家與新儒家哲學的新維度》(英文版)、《當代中國哲學》(英文版),發表中外文論文百餘篇。
TOP
作者序
中國管理之道的現代詮釋──自序
1699年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在《中國最新事物》一書序言中特別提到,中國的治國之道強於西方,而西方對於自然的知識強於中國。所以他希望西方傳教士們在向中國傳授自然知識的時候,不要忘記把中國的治國之道傳回西方。—這代表了17世紀一代啟蒙思想家對於中國政治、道德、文化的景慕和嚮往。
中國的17、18世紀正是所謂「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鼎盛時期。一方面是專制政體,另一方面又包含著治理國家之道。這就說明了管理之道—它體現著一整套的哲學、思想、制度和技術—的普遍性。從另一個角度...
1699年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在《中國最新事物》一書序言中特別提到,中國的治國之道強於西方,而西方對於自然的知識強於中國。所以他希望西方傳教士們在向中國傳授自然知識的時候,不要忘記把中國的治國之道傳回西方。—這代表了17世紀一代啟蒙思想家對於中國政治、道德、文化的景慕和嚮往。
中國的17、18世紀正是所謂「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鼎盛時期。一方面是專制政體,另一方面又包含著治理國家之道。這就說明了管理之道—它體現著一整套的哲學、思想、制度和技術—的普遍性。從另一個角度...
»看全部
TOP
目錄
中國管理之道的現代詮釋──自序
本論 C理論的基本內涵 1
一、管理的哲學省察 3
二、易經哲學的管理學詮釋 19
三、C理論的理論架構 37
分論 C理論要素分析 53
一、認識易經管理 55
二、由易經詮釋管理 57
三、易經管理的八大要素 62
四、易經管理的運用 72
五、C理論的管理模型 81
六、道家的決策哲學 85
七、法家的領導哲學 88
八、兵家的權變哲學 91
九、墨家的創造哲學 95
十、儒家的協調哲學 98
十一、易經在管理中的融合與轉化功能 101
十二、禪在管理中的超越與切入功能 ...
本論 C理論的基本內涵 1
一、管理的哲學省察 3
二、易經哲學的管理學詮釋 19
三、C理論的理論架構 37
分論 C理論要素分析 53
一、認識易經管理 55
二、由易經詮釋管理 57
三、易經管理的八大要素 62
四、易經管理的運用 72
五、C理論的管理模型 81
六、道家的決策哲學 85
七、法家的領導哲學 88
八、兵家的權變哲學 91
九、墨家的創造哲學 95
十、儒家的協調哲學 98
十一、易經在管理中的融合與轉化功能 101
十二、禪在管理中的超越與切入功能 ...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成中英 著
- 出版社: 東大圖書(股)公司 出版日期:2016-11-25 ISBN/ISSN:978957193137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92頁
- 類別: 中文書> 商業> 管理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