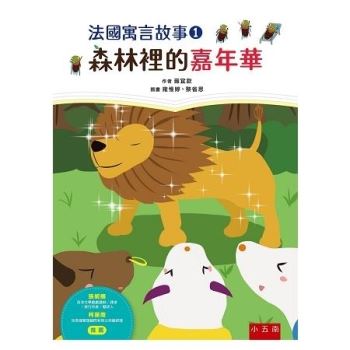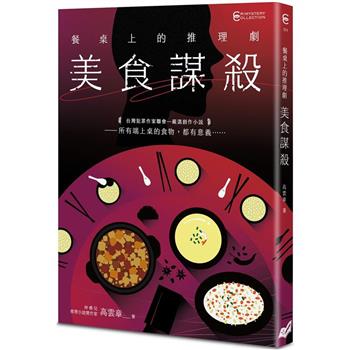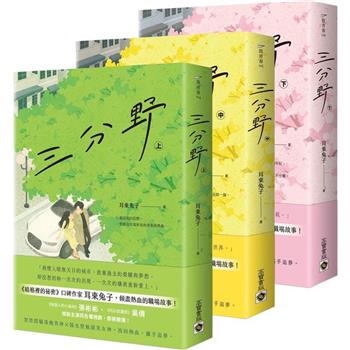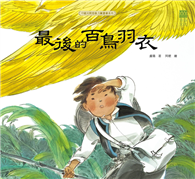序 論 談儒道兩家的「道」
—從儒道兩家的「心」,談生命價值的開發—
本文是筆者在耕莘寫作班、東海、輔仁與師大的演講詞,由師大國文系的同學錄音整理,再經由筆者潤飾補正。筆者研究中國哲學有年,寫下的論文不免背負了學術論文的包袱,不大能放得開,故可讀性不高。這篇演講詞的整理,自然較為平易,故以此文發表,並作為筆者《老子的哲學》一書的序文。或許通過本文的疏導,使讀者較能走進拙著《老子的哲學》的思想領域裡,對中國哲學的精神也較能有親切的體會,與恰當的知解。
人會向自己發問:人為什麼活著?我要往何處去?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顯現了生命莊嚴的意義。人之成為萬物之靈,就從這裡開始。我們要問生命的價值何在?人生的方向又如何貞定?實則,意義得自己去尋求,自己去賦予。你參與人間,承擔使命,生命的存在就會湧現莊嚴而真實的意義。生命的意義,是我們賦予它,而不是它給我們。所以人生在世,不能等待意義自己到來。今天我試圖從儒道兩家的思想,來談談生命價值如何開發的問題。
一、形而上與形而下
首先,我們從《易經‧繫辭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這句話,開始反省生命進路的問題。孔穎達解為:自形外而上者謂之道,自形內而下者謂之器;宋代大儒張橫渠亦以形而上是無形體,形而下是有形體解這句話。朱夫子便不大贊同,他雖認為理氣是二元,卻仍主理與氣不可離,故反對以有形、無形區分道與器;而戴東原則解「形而上」是形以前,「形而下」是形以後,是以成形與否來區分。因此,《易傳》此言在歷代思想家的注疏中,皆各就己學加以二分。大略說來,形而上是在有形世界之上,叫道;形而下是有形世界,叫器,是兩層劃分的,一是感官所對的萬有世界,這就是形器,另外有一個超乎官覺的無形存在,是讓這一切有形世界所以存在的原理,我想即是指「天道」。一、兩千年來中國學者一直採信這個觀點。當代日本學者即以「形而上者謂之道」來翻譯西方的metaphysics,就是所謂的形上學。在西方,physics是物理學,meta是「後」的意思,也就是在物理學後面的。「後」本是時間的先後,亞里士多德遺著編排出版時,他的學生將探討宇宙形成之原理的那一部分,放在物理學後面。這種探討宇宙之根本原理的學問,就是所謂的實現原理或第一哲學。因為排在物理學之後,就以「後物理學」得名。「後」本是時間先後的意義,就那麼巧,它所探討的正是問物理現象與自然宇宙的上面或背後,它的原理是什麼。形就是自然宇宙,也就是physics,形之上的原理,是metaphysics。因此日本學者以「形而上」來翻譯metaphysics,可說是天衣無縫,神來之筆了。問題是以西方形上學的標準,來看中國哲學,便不很恰當。我想,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在特質上應該不一樣,我說「應該」是有根據的。因為《易傳》是儒家後起的經典,所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句話的解釋,不能違背《論語》的義理系統。我以為,儒家最主要的義理,都集中在《論語》、《孟子》,《學》、《庸》、《易傳》是後起的。所以道和器的解釋,不能遠離《論語》本來的意義。由是引起我進一步的反省。另外,我也是師大國文系出身的,有我們訓詁文法方面的訓練,所以不能輕易跟著前賢說是形以上、形以下,或者說形以前、形以後。我們必得先問,什麼是「而」?「而」在這句話裡面是什麼樣的用法?假如按照歷代注解來說的話,形而上是當形之上來講,有形世界之上的那個原理就叫「道」,有了天道的終極存在才有萬有世界,也才有山河大地、鳥獸蟲魚。問題出在第二句話,什麼叫「形之下」?形就是有形世界,哪裡還有形之下?在有形世界之外,怎麼可能另有在有形世界之下的存在?難道「天上」「人間」之外,還有個「地下」?此不可解。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把「而」當作「以及其」來解,形以及其上者就稱之為道,形以及其下者就稱之為器,這樣原來的問題還是存在,「形以及其下」仍然不可解,另外更增加一個難題,「形」到底應安放何處?若說「形以及其上」、「形以及其下」,則「形」已足跨兩界,既是道又是器了。所以我認為「道」「器」不該作如是解。道應該是「人能弘道」的「道」,是人走的路,人所開出的路,通過人的心所開出的人文世界就叫道,本來就沒有西方哲學在自然現象之上,作為萬有世界之實現原理的意義。因此,依我的反省,「而」應該可當「往」解,是代表一種動向,生命的動向。我們說生命價值的開發,它的可能就在此,中國哲學的特質也在此。
「形」不是指外在的自然世界,而是指我們的形軀。每一個生命來到人間都有形軀,就是形的存在。我們要問:人要往何處去,生命的歸屬何在?人生的方向,先不問東西南北,而當問個上下。人生的方向,是東西是南北,係起於外在偶然的因素,人的生長歷程,一生的種種遭遇,在在都受著來自社會各種條件的決定,這方面是沒有必然性,也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但有一點,我們總是追求一條往上的路,這才有意義呵!所以我們先不要說生命的方向在東西南北的哪一方,而應該先問個上下。《易傳》說「形而上」、「形而下」,就是說人的生命都有一個「形」,這是很公平的,問題在這個「形」,我們是應該自覺的往上提昇呢?還是順任的往下去凝聚?因此,我認為所謂的形而上或形而下,是代表生命的動向。
第二個問題,我們要問「形」的內涵是什麼?依我的理解,「形」包括三方面:首先,是指人的形軀最原始的生理、官能、欲求,生之理、官之能、欲之求是形軀生命最基本的存在。其次,是指人的性向才情,有的人在某方面反應特別靈活敏銳,有獨特的才華,所以有王貞治、林海峰,也有紀政、楊傳廣。第三,是指人生命熱血的表現,慷慨悲歌、從容就義,勇於面對與承擔人間使命的生命熱血。上述三者是與生俱來的,這就是所謂的「形」。那麼我們該將它們往上昇越呢?還是僅僅往下凝聚?往上昇越的路就是「道」的路,往下凝聚的路是「器」的路,故一成道,一成器。
二、人生上下兩路—成道與成器
有關「道」與「器」的解釋,我們當然要落到《論語》與《老子》的義理系統去尋求。依照上述,以我們的生理官能、性向才情,與生命熱血,去承擔人間的使命叫「道」。因此道是人走的路,是人間的大道,這就是成道的路。另外我們僅僅把我們的生理官能、性向才情,與生命熱血去凝聚下來,成就自己,我們可能是一個學者專家,也可能破紀錄,在人間表現生命的精彩,但它可能只是「器」而已。因為成器僅成就自己,不一定能承擔人間,為人類而活,所以生命有兩條路—上與下。
當然,器並非不好,如俗語所說「恨鐵不成鋼,恨兒不成器」,成器很好,成器是成就一個人的專技特長,我們在社會上扮演各種角色,當然希望成器,做個有用的人。但孔子說「君子不器」,老子說「大器晚成」。我們先說「大器晚成」,「大器晚成」現在成為許多青年朋友自我解嘲的哲理教言,往好的方面說是自我期許—且看「他」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但老子本義,大器係指道的作用,是說道最後才完成它自己,即天下萬物都能成就,我才成就,這叫「大器晚成」,而不是說真正的大器到了晚年才能造就有成。故道是萬物都成就了才成就它自己,道就在萬物中成就它自己,這是老子所謂的「善貸且成」。老子又說:「道常無名樸。」樸就是好的,是生命的本真,是真也是美,當「樸」散落而去追求某一專門成就,這已是雕琢斲喪,即老子所說的「樸散則為器」了。孔夫子說「君子不器」,故樊須請學農,孔夫子慨歎的說:「小人哉,樊須也!」因為孔子正是教學生去承擔天下的使命,你是我孔夫子的學生,怎麼只想去做個農學專家?所以他乾脆說:「我不如老農。」一個知識分子的路,在道而不在器,不是君子不想成器,而是君子不僅僅是器而已,他的生命熱血,他的性向才情,不只是發展成就自己,而且要承擔這個世界,這叫「君子不器」。所以「器」並非不好,但知識分子的胸懷抱負應該是不同的。
我們說「形而上」、「形而下」,人的「形」可以往上提昇飛越,也可以往下落實凝聚。後者並非不好,但往上提是大家往上提,而不只是我往上提。問題是生命往上提如何成為可能?人都難免有情緒陷於低潮,而失落自我的時候,我怎能保證自己一定形而上而不形而下。形而下的心,是墨子、荀子、韓非的心,是如何在人間成就一專家學問,去開出禮制、法制的客觀體制,此涉及知識性、技術性的東西,並不決定生命方向應該向上的問題,即今所謂的專門知識。當前所有的大學科系均志在成器,都是屬外王的學問。我們希望在人間承擔什麼,從事某一行業,在某一工作崗位,有某一方面的成就,即所謂「器」的工夫。今天大學教育顯然忽略了所謂的「道」,大概文史哲科系由於講文化傳統,還可以維繫「道」的理想於不墜。那麼成道的可能根據,到底何在呢?就在中國人的「心」。故「形而上」的背後,實隱藏了一顆中國人的心,它是儒家孔孟、道家老莊的心,而不是墨子、荀子、韓非的心,後者成就的正是所謂的「器」,真正能開出「道」的,是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莊,我們就從儒道兩家的「心」,來談生命價值的開發。
三、儒家的人文之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儒家的生命精神可透過《論語》「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四句話來說明,而道家的哲學旨趣,正是回應這四句話痛加反省與批判。
(一)志於道
孔子嘗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並說「志於道」。何謂道?道是人生的大路;何謂志?志即心之所往,在先秦士本貴族之一—武士,有其人文涵養,受教育正是貴族的專利。自孔子始,才有民間教育,貴族沒落,士因而流落民間。儒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禮樂書數是屬於人文的涵養,射御則屬於武事的訓練。戰國四公子養士,士為貴族的家宰,附屬於貴族豪門之家。士到了孔夫子時代已脫離貴族的約束,而走入人間社會,成為「天下士」,非單為某一國君、卿大夫尋求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了,而是要為整個時代承擔生命存在的問題,此即「志」—士之心,也就是知識分子的心。而知識分子的心,就當去承擔所謂的「道」,即人間的大道,而非小徑—小徑是奇技異能之士與專家學者所走的路,須靠特殊的性向才情、生命熱血,去表現生命的精彩,並非人人可為。人人都可以走的才叫大道,所以孔子說:「行不由徑。」故志於道是為人類打開出路,找出每個人都能走的平等之路,不必待特殊的財富、身分、地位與權勢就能走的路,市井小民、鄉野村夫都能走的路,這才是人生的大道,這叫「志於道」。
(二)據於德
再說「據於德」。怎樣的路才是人人都可走,而非僅少數專家學者、有天才有地位的人才可走的?儒家說道德實踐人格修養的「路」,做一個好人是人人都能成就的,而做一個好人,做一個有道德人格的人,是生命境域最莊嚴最有價值的,古往今來多少人—當真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能流傳下來的有多少人,且真正能今古輝映,讓人永難忘懷感動的是什麼?是偉人的生命人格。故儒家為人類所開出的道路,是依據德行去開的,「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每個人都可以做個好人,此即人生真正的大道。與身分、財富、地位無關,與階級、種族、膚色無關,這叫「據於德」。孔子就以「據於德」,來規定「志於道」。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老子的哲學(三版)的圖書 |
 |
老子的哲學(三版) 出版社:東大 出版日期:2017-01-2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24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三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8 |
哲學 |
$ 266 |
中文書 |
$ 266 |
中國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老子的哲學(三版)
老子的思想,不是被解得太虛玄高妙,就是被講得過於實用淺陋。道德經雖言簡意賅,不易把握;然它最玄妙,也最平實,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生命反省,對老子作一哲理的詮釋,與存在的印證。作者試圖把老子安放在先秦 諸子的思想源流中,去探究道德經的義理真實,並建構其思想體系。八十一章的每一句話,都可以得到義理的安頓,並有一整體的通貫。本書由生命修證,開出形上體悟;再由形上結構,探討其政治人生的價值歸趨;並由生命與心 知兩路的歷史迴響,對老子哲學作一價值的評估,以顯現其精義與不足。
TOP
章節試閱
序 論 談儒道兩家的「道」
—從儒道兩家的「心」,談生命價值的開發—
本文是筆者在耕莘寫作班、東海、輔仁與師大的演講詞,由師大國文系的同學錄音整理,再經由筆者潤飾補正。筆者研究中國哲學有年,寫下的論文不免背負了學術論文的包袱,不大能放得開,故可讀性不高。這篇演講詞的整理,自然較為平易,故以此文發表,並作為筆者《老子的哲學》一書的序文。或許通過本文的疏導,使讀者較能走進拙著《老子的哲學》的思想領域裡,對中國哲學的精神也較能有親切的體會,與恰當的知解。
人會向自己發問:人為什麼活著?我要往何處去?這...
—從儒道兩家的「心」,談生命價值的開發—
本文是筆者在耕莘寫作班、東海、輔仁與師大的演講詞,由師大國文系的同學錄音整理,再經由筆者潤飾補正。筆者研究中國哲學有年,寫下的論文不免背負了學術論文的包袱,不大能放得開,故可讀性不高。這篇演講詞的整理,自然較為平易,故以此文發表,並作為筆者《老子的哲學》一書的序文。或許通過本文的疏導,使讀者較能走進拙著《老子的哲學》的思想領域裡,對中國哲學的精神也較能有親切的體會,與恰當的知解。
人會向自己發問:人為什麼活著?我要往何處去?這...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修訂二版序──老學講論三十年
《老子的哲學》寫於民國六十七、八年間,是升教授的論文,距今已近三十年。新版改為橫排,並略作校正修補,而以新的面貌發行。
當初,原以「老子哲學的形上架構與其政治人生的價值歸趨」作為學術研究的專題,在《鵝湖月刊》連載發表,每個月寫兩萬字,連登五期成冊,通過教育部審查,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升等教授。
我當時任《鵝湖月刊》社社長,看諸多專欄,都難以為繼,無疾而終,故率先作一示範,證明只要專注凝聚,經由連載的責任感,不到半年間,就可以完成升等論文。民國六十九年九月,正式成書,由東...
《老子的哲學》寫於民國六十七、八年間,是升教授的論文,距今已近三十年。新版改為橫排,並略作校正修補,而以新的面貌發行。
當初,原以「老子哲學的形上架構與其政治人生的價值歸趨」作為學術研究的專題,在《鵝湖月刊》連載發表,每個月寫兩萬字,連登五期成冊,通過教育部審查,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升等教授。
我當時任《鵝湖月刊》社社長,看諸多專欄,都難以為繼,無疾而終,故率先作一示範,證明只要專注凝聚,經由連載的責任感,不到半年間,就可以完成升等論文。民國六十九年九月,正式成書,由東...
»看全部
TOP
目錄
修訂二版序──老學講論三十年
序 論 談儒道兩家的「道」
—從儒道兩家的「心」,談生命價值的開發— 1
第一章 身世之謎及其成書年代的推斷 35
第二章 哲學問題 47
第三章 人的生命何以成為有限 73
第四章 即有限而可無限的實踐進路 117
第五章 生命精神與政治智慧 157
第六章 價值重估與歷史迴響 191
結 語 現代意義 217
序 論 談儒道兩家的「道」
—從儒道兩家的「心」,談生命價值的開發— 1
第一章 身世之謎及其成書年代的推斷 35
第二章 哲學問題 47
第三章 人的生命何以成為有限 73
第四章 即有限而可無限的實踐進路 117
第五章 生命精神與政治智慧 157
第六章 價值重估與歷史迴響 191
結 語 現代意義 217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邦雄
- 出版社: 東大圖書(股)公司 出版日期:2017-01-16 ISBN/ISSN:978957193139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