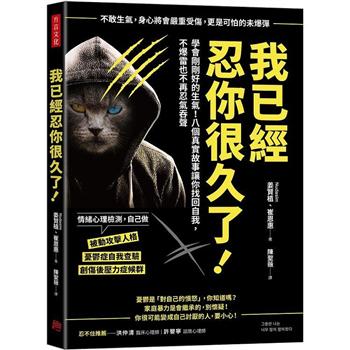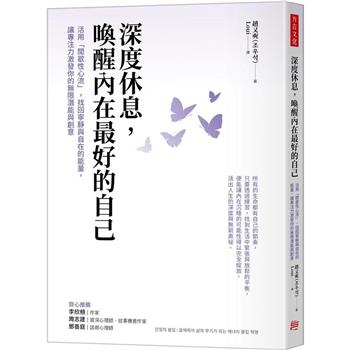序: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日英文《中國日報》登載了一篇題為〈考試是學校生活的禍根〉的文章,描述了當代中國的教育問題。文章首先指出,控制高校(大學)入學的重點中學和普通中學之間的差距製造了普通中學師生的冷漠感。其次,高校入學考試的巨大分量導致學生專注於考試準備,而忽略了包括正常功課在內的其它活動。第三,學校教學質量因此降低,使年輕人「智力、體質和精神均得不到充分發展」。文章引用一位教育權威人士的話作結論:「考試取向的學校制度應找出灌輸這些價值的途徑」。
我們生活在一個考試無處不在的世界上──不僅用於教育,而且用作挑選工作人員和鑑定人們的工作技能的手段,這些問題本不足為奇,因為公平和價值觀的問題與競爭選擇的制度是形影相隨的。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同宋代的教育問題如出一轍。
眾所周知,中國首創用文學考試選拔官吏和政治精英,其起源可上溯至孔子的教義及漢代的政治。鮮為人知的是科舉考試的制度化及其(至少在上層的)廣泛運用主要出現在宋代(960-1279年)。因此中國宋代可謂歷史上第一個考試取向的社會,並已遇到《中國日報》文章論述的問題。
在一九八五年英文初版的《宋代科舉》一書中,我試圖闡明這個考試取向的社會的歷史和社會結構。以前的宋代考試和學校的研究幾乎都採用制度史的形式,極少論及這些制度的社會影響。一個特出的例外是先師柯睿格(E. A. Kracke, Jr.),他指出考試推動了社會向上流動。隨著深入研究宋代考試,我進一步認識到考試具有連接社會和政治的重要意義。其作用涉及皇室的目標、官僚人事安排、社會地位、地方士紳社會的形成、地區的發展以及家庭結構和作用的變化。本書因而企圖在不失為制度史的同時,勾勒此等多重作用之互動。
是書開端論述宋代初期皇帝,對始於大約四個世紀前隋朝的科舉制度所作的一糸列卓有成效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大量增加錄取名額;創設州試和殿試──因此連禮部舉行的考試,共有三級;採取具體步驟保證書面考試的匿名和閱卷之最大限度的公正性;以及設置一套州試的定額制度以穩定各州貢生到首都的數量。此等改革成功地將考試變成政治文化的一個中心特點。考生數目急劇增加,考試競爭性隨之益趨激烈。政府學校的體系在十一世紀出現,改進學校和考試成了此後主張改革的大臣的主要目標。再加上十一世紀的另兩項改革——建立考試的三年周期及決定「進士」為考試及第者唯一的學位(以前有不同科目的多種學位)──為未來近千年的考試定型的一種制度遂告形成。
即使考試繁盛、制度發展,宋代初期皇帝的「菁英政治」的目標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實現。人們學會了鑽制度的漏洞來增加考試及第並取得官位的機會。除了全然的作弊和行賄,有些遷移到定額較寬的州府。官員的親戚湧入為減少主考官偏愛的可能性而設置的特別考試,但事實上這卻給了他們競爭的優勢。隨著皇朝的延續,他們更多地運用世襲的保護特權,所謂「蔭」──高級官員可有一個或幾個親屬僅通過簡易的考試即取得官階。事實上,十一和十二世紀的蔭補如此廣泛,以致經由考試招募的官員的比例降低,雖然考生數目和考試競爭程度急劇增加。
然而,此等不公平並未阻礙一些因考試而引發的社會文化發展。這些包括:一、文人作為一種固有利益的地位集團的出現(至南宋時,即使部分通過考試過程者可在地方社會取得地位);二、雖涉足考試和國家事務但積極參與地方事務,發達於十二和十三世紀發達的書院的地方士紳階層的出現;三、有其獨特的規範、象徵和經驗的考試文化的形成。本書的最後一部分討論這些現象及其在地方上的表現。
宋代結束於七百多年前,讀者很可能會問為何其考試制度值得在今天討論。我想其理由至少有三。首先,宋朝的考試代表延續至1905年才廢止的中華帝國考試制度的一個重要階段。殿試、在京城外舉行初試、唯有殿試後才授予唯一的學位──進士、授予州試及第者以舉人學位、三年考試周期以及貢院的發展──這些明清考試的特徵無不濫觴於宋代。以學院而言,州學、縣學和書院唐代都有,但是要論組織、課程、財政、校園布局以及政府學校的正式納入考試制度,明清學校和書院大致可看作宋代的創造。可能最重要的是,帝國後期特出的士大夫階層的致力追求教育和考試競爭主要是宋代的發展。因此宋代考試和學校史對於整個中國歷史意義重大。
其次,宋代考試的重要性超出中國之外,因為中國考試本身具有相當的世界史的意義。西方傳統諸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中心在歐洲和美國現時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確認。很少有人認識到現代社會的另一個普遍特徵──學校和考試不但用於教育青年人,並且在選擇員工和區分地位中起關鍵作用──發源於中國,並非西方。拜耶穌會員和其它晩明和清朝的觀察家之賜,「精英政治」的中國模式為啓蒙哲學家們提供了有力的模式,並幫助鑄造了現代西方社會。
第三,考慮到宋代和《中國日報》文章中描寫的教育問題的共同點,宋代經驗的分析具有現實意義。比如,宋代初期皇帝用考試創造一種「精英政治」的卓著嘗試,甚為十二世紀的革命家和改革者所效尤,所以顛覆這些嘗試的方式對我們都有啓示。這並非説過去的教訓可以簡單地移植到現在,但認識到有些問題並非今日獨有,當有助於觀察和理解。
最後,謹向使本書得以出版的很多人表示謝意,特別是慨允出版一本「洋鬼子」研究中國科舉的著作的東大圖書公司以及為這篇序言費心的賓漢頓大學的陳祖言教授。我尤其要感謝杭州大學的楊渭生教授,他不辭勞苦地為此書付出心力,實在十分感激。最後也感謝紐約市立大學亞洲研究系的李弘祺教授,他在過去數年中耐心地、仔細地幫忙使這本書得以問世。李教授與我是問學的知交,砌磋多年,一定很高興看到這本書的出版。
賈志揚(John Chaffee)
於賓漢頓大學
199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