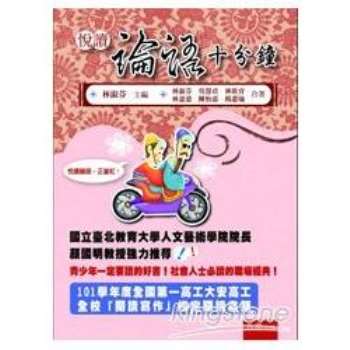戲劇發展的四個主要型式
第一型:描寫個人與運命鬥爭
一切戲劇的題材都是描寫人類意志的一種鬥爭。從希臘時代起直至現代為止,一共創造了四種型式。這幾種型式,就其與人物意志對抗的勢力之性質,而生出區別。
戲劇發展的第一型,描寫個人與運命抗爭,希臘戲劇可為代表。
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 他的代表作是《伊底帕斯王》。故事是這樣的:
古希臘「甲」國國王,生了一個兒子。他便興高采烈地跑到神壇去祈問這個孩子的將來的命運。神在空中回答,說這個孩子將來會殺死自己的父親,娶自己的母親,和篡奪父親的王位。這個預言如像一盤冷水似的潑在國王的頭上,他忙跑回宮中,把神的意旨告訴王后,覺得這小孩既然交了這種惡運,與其留下來會犯大逆不道的罪惡,倒不如趁早把他結果了,杜絕禍根。於是便令廷臣抱了這個小孩子到荒郊把他殺掉。
廷臣奉命抱著那小孩子跑到荒郊,眼見得這小孩子生得英俊伶俐,不忍下手殺死他,便把小孩放在一塊木板上,用釘釘住他的雙腳,丟在一棵大樹底下,以為到晚上一定會給豺狼野獸喫掉。於是回宮覆命,說是已經完成了任務。
到了傍晚時分,有一個「乙」國的牧羊人正趕著羊群從郊外回來,聽到樹林裡有小孩的啼哭聲,走前一看,發現了這個用黃綾裹著的肥白可愛的嬰兒,心想一定是貴族人家的私生子,便把他救起來,抱返家中。剛巧乙國國王年老無子,牧羊人便把他送給國王。國王見了這個孩子生得相貌堂堂,喜出望外,便立他為太子,留在宮中,悉心調養,取命為伊底帕斯,原意是腫腳的意思。因為他腳的釘子雖然拔了出來,但是傷處卻腫了。
伊底帕斯在宮中長大成人,因為教養得好,文才武藝都非常出眾,滿朝上下都非常喜歡他。到了二十歲的時候,依照慣例,也跑到神壇去預卜將來的命運。不料神的答覆竟然和二十年前對他的生父的預言一樣,嚇得他膽跳心驚,垂頭喪氣地跑回宮裡。到底他是一個善良的人,怎樣忍心做這些大逆不道的事,便決定漏夜出奔,遠離國土,想逃出命運之神替他安排下的陷阱。因為他一向不知道自己的底蘊,以為乙國國王就是他的親父哩。
話分兩頭。當時出現了一隻人首獅身鷹翼的怪物,叫做「斯芬克斯」,出沒於荒郊甲乙兩國交通的孔道,喫人纍纍,弄到行旅裹足。原來這隻怪物每逢見到有人過路的時候,總出來攔住,出一個啞謎叫過客們猜,猜得中的便可以通過,猜不中的便給牠喫掉。可憐那些商旅一個一個地都成了牠的犧牲品,整個國家鬧得雞犬不寧。甲國國王只得高懸王榜,招募勇士去為民除害。如果有誰能把這隻怪物除掉,便把王位讓給他,王后嫁給他。王榜揭示多時,還是沒有人敢輕於嘗試。
再說,伊底帕斯逃出了王宮,獨自個遠走天涯。一路上道聽塗說,都是關於怪物為患的消息。他心裡想,橫豎自己交了惡運,已是了無生趣,不如拼了這條命去猜猜斯芬克斯的謎語。猜不中也就一死算了;假如猜得中,為民除了一個大害,也許蒼天憐憫他而減輕他的罪過。
於是他走到怪物的面前,怪物果然照例對這來人說出一個謎語。牠說:「有一種動物,早上是四條腿,中午時候是兩條腿,到了晚上便成了三條腿,這到底是甚麼東西呢?」伊底帕斯想了一會。回答說:「這是『人』。因為人在初生的時候,好比一天的早晨,兩手兩足都在地上匍匐爬行。到了長成,好比一天的中午,他已經能直立步行了。到了晚年,好比一天的晚上,他要拿一根手杖走路,不是成了三條腿麼?」斯芬克斯的「人生之謎」,果然給伊底帕斯猜中了。牠還想逃走,怎知劫數難逃,給伊底帕斯拔劍殺掉,推落山崖,跌成粉碎。
殺了怪物之後,伊底帕斯滿懷歡喜,得意揚揚地朝著「甲」國走去。走到一條狹路的時候,剛巧迎面而來有一乘轎子,侍衛們前呼後擁,高喝伊底帕斯讓路。伊底帕斯自小長大宮闈,正是嬌生慣養,怎受得人家頤指氣使?於是一言不合,便打起上來。前邊的侍衛都給伊底帕斯砍倒,他殺得性起,順便一劍向轎子裡刺去。可憐轎裡那個老頭子,無辜地便歸了西天,後邊的人急忙跑回去報訊。
伊底帕斯就在這不知不覺中,應了神的第一句預言。原來轎子裡坐的正是「甲」國的國王,這天因為了國家的憂患未已,便輕車減從,到神壇去祈福,不料給他的兒子攔途刺殺了。
這個時候,甲國朝廷給這一件高興的事和一件悲哀的事鬧昏了。高興的是大憝已除,國家從此安樂;悲的是國王給人謀殺了,兇手無從弋獲。只得一邊開喪,一邊由王叔暫時攝政。好容易才發現伊底帕斯是殺死怪物的功臣,又忙著實踐前王的諾言,奉伊底帕斯為新王,把王后嫁給他。可憐伊底帕斯一一應了神的預言,他自己還懵然不知。
這個故事匆匆經過了廿多年,伊底帕斯和他的母親結婚以後,已經生下了兩個女兒。這一年各地鬧大瘟疫,死人無數。國王和百姓都不明白為何上天如此降罪,詢之神靈,神答曰,除非緝獲刺殺前王真兇,大難不止。於是舉國上下至誠祈禱,一面出重賞緝拿真兇。時適乙國國王病危,臨終時亟欲一晤伊底帕斯,因為他早已偵悉這個腫足的孩子做了「甲」國的國王,便派了一個使臣來宣達王旨。伊底帕斯想起了神的預言,堅決地回絕。使臣便把原委告訴他,說他並不是「乙」國國王的親生兒子。這個洩露激起了伊底帕斯的懷疑,便窮加追問。這時那個抱伊底帕斯丟在荒郊而且釘了他的雙足的老臣還不曾死,真相終於大白。
王后知道了真情,羞愧無已,躲在後宮上吊死了。伊底帕斯更是悲憤莫名,把自己的雙眼挖出來,獨自離開王宮。那兩個女兒,同時又是他的妹妹跟隨著他。到後來,一個狂風暴雨的晚上,兩個女孩疲憊不堪地睡在樹下。趁著這個時機,伊底帕斯丟下她們,獨自個兒向樹林深處走去,不知所終。
這個劇本故事,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希臘社會的一般情形,那時正是神權時代,人類的知識未開,遇到大自然裡許多不能解釋的事情,都諉於神明。而運命之神更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他不單只支配人類的行為,同樣也支配其他諸神的命運,例如伊底帕斯,他明知命運之神給他擺下了一個陷阱,他不斷地鬥爭想圖自拔,想逃出命運之神的掌握,但他的努力是徒然的,不論他是如何倔強,如何奮力去打破一切的成法,可是因此命運更判定他的難免於苦悶。這種宿命論的人生觀,正是當時以農業為基礎的封建社會思想與生活的反映。
我們現在稱希臘時代的戲劇為「古典主義」的藝術,所謂古典主義,是純然以描寫貴族的生活為其內容的。舞臺上現身的男女主人翁,都是統治階級的代表,他們為人類而抗爭和受苦,藉此而激起被統治者的同情與憐憫,和鞏固對統治者的擁護信心。更加上濃厚的宗教色彩,使人民屈服於宗教的不可抗衡的勢力之下,使他們因恐怖畏懼而生出尊敬和嚴肅的心情。從希臘戲劇之「貴族的概念」和「宗教性」這兩點看來,我們便可知道古典藝術是貴族封建政治的文化產物。
這一個型式的寫作,是希臘第一個悲劇家埃斯庫羅斯創造的,而完成於索福克勒斯。
***
第一章 戲劇是甚麼
戲劇是安排由演員在舞臺上當著觀眾表演的一個故事。這段簡明的敘述給戲劇下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定義這樣簡單的定義,就是一望也能明白,因此無須加以解釋。但如其我們逐字逐句把這段敘述細為推敲,我們便會明白此定義已概括了一切的戲劇原理;而從這個基本原理出發,我們可以演繹出戲劇批評之實踐的哲學底全部。
「故事」一詞,其意義極為顯明。故事是一串為因果律所聯結而向著預定的頂點進行的事件之演述每一事件顯示一班想像中的人物,在適宜的想像的裝置之下,扮演想像的動作。自然,這個定義對於敘事詩,短曲,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描敘藝術一切其他的方式,以及對於戲劇,均為適用。
但是「安排表演」這句話,嚴格的使戲劇異於描敘藝術一切其他的方式。尤應特別注意戲劇並不是寫來讀的故事。戲劇本不應視為文學之一部比方如敘事詩或小說一樣。從劇場之立足點說來,文學反映視為只是戲劇家藉以把他的故事更有效地傳達給觀眾之方法。偉大的希臘戲劇家需要有對於雕刻與詩歌之理解;而在近代劇場,劇作家須表現畫家與文人之想像。戲劇本應訴之於視覺而非聽覺。在近代舞臺,裝飾洽宜的人物應現身於設計與描繪得極其周詳,光與影照耀得極其適當的裝置之內,並常需音樂的藝術以輔助其感效。因此戲劇家不只應賦有文學的天才,並須對於繪畫效果底雕刻的與造型的要素有明晰之見地,節奏與音樂之理解,與乎演劇藝術之洞澈的知識。因為戲劇家應同時在同一的作品裡將許多種藝術的方法配合調和,故不應集中注意去單獨批評他的對話,和只就文學的領域去褒貶他。
自然,真正偉大的劇本常是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戲劇。純粹的文學原素對話中文體之技巧不過是使作品能流傳永久的防腐劑而已。埃斯庫羅斯(Aschylus)的作品在現代早已不能演,我們只把它當作詩歌來讀。但是在別方面,我們應知不排演他的作品底重要理由是因為他的戲劇不適於近代劇場表演他的劇本,劇裡的建築物之外形體積以及設備都完全不同。在他的時代,他的作品卻並不是也當作詩歌來讀,而是常在劇場裡博得采聲的,因此欲適當地欣賞他底戲劇的而非文學的呈訴,我們必須在想像中重構他當日的劇場情境。不過他的劇本,雖則始初計劃成戲劇,後來一代一代的經批評家及文學研究者的流傳,遂轉變而接近於詩歌;在批評觀念之轉變中,只有藉它的對話之文學的價值,才能保證埃斯庫羅斯之不朽。一個劇本,因為物質環境改變,常為劇場所擯棄,假如那是偉大的劇本的話,只能在紙上保留。從這個事實,我們可以推出一句實際上的格言,便是雖則有技巧的劇作家無須把他的劇本寫成如何偉大去博取他當時的稱譽,但假如他想為後世所不忘,他必須從事於文學的修養。
關於文學元素在戲劇上之基本重要,那是必得承認的。但別方面也必須承認在戲劇上佔有崇高地位的劇本,在文學的領域裡亦必有相當的位置。鄧那尼(Adolphe d'Ennery)的最有名的傳奇劇《二孤女》(The Two Orphans)便是一個好例。此劇傲然地支配劇場差不多一世紀,至今仍受人之稱道。那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劇本,於排列得極其縝密的戲劇情節中,演述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全劇有十來個腳色,雖然很少真正算得上是有個性的人物,而仍然寫得非常忠實迫真,在舞臺上兩小時的演劇裡,能使演員呈現可驚的現實的幻象。真的此劇寫得非常可怖尤其是在標準的英譯本。二孤女之一在開始時張大眼睛地獨語:「我是瘋了麼?……我是做夢麼?」下邊那幾句話也突然的刺進耳裡「如果你還是拿這種殘忍的態度來逼害我,我便到捕房去控告你。」實在說,這在文學上是沒有甚麼了不得的地方。可是憑藉視覺的媒介,賴乎境遇之巧妙的排列,卻使觀眾大受感動;在最激昂的關頭,觀眾是沒有能力去注意說白之美麗或平凡的。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戲劇藝術之發展及其原理(六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Books |
$ 252 |
藝術設計 |
$ 252 |
藝術設計 |
$ 266 |
中文書 |
$ 266 |
戲劇總論 |
$ 266 |
戲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戲劇藝術之發展及其原理(六版)
本書為趙如琳先生研究戲劇多年的心得結晶。書中共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特別闡明戲劇發展的四個主要型式;對羅曼主義之興起與沒落、寫實主義戲劇應運而興替進行透澈的說明;對史丹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藝術體系之形成、發展、衍變及影響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舞臺藝術之轉變與發展亦有全面性的探討。下篇翻譯漢米爾頓的名著《戲劇原理》,極具研讀和參考價值。對於戲劇藝術工作者與戲劇文學研究者,本書是不可或缺的最佳參考資料。
作者簡介:
趙如琳(1909~1983)廣東省廣州市人,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士。曾任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兼戲劇系土任。
譯著有《蘇俄的新劇場》、《舞台藝術論》、《戲劇原理》及劇本《衝出重圍》、《油漆未乾》、《當代獨幕劇選》等。
章節試閱
戲劇發展的四個主要型式
第一型:描寫個人與運命鬥爭
一切戲劇的題材都是描寫人類意志的一種鬥爭。從希臘時代起直至現代為止,一共創造了四種型式。這幾種型式,就其與人物意志對抗的勢力之性質,而生出區別。
戲劇發展的第一型,描寫個人與運命抗爭,希臘戲劇可為代表。
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 他的代表作是《伊底帕斯王》。故事是這樣的:
古希臘「甲」國國王,生了一個兒子。他便興高采烈地跑到神壇去祈問這個孩子的將來的命運。神在空中回答,說這個孩子將來會殺死自己的父親,娶自己的母親,和篡奪父親的王位。這個...
第一型:描寫個人與運命鬥爭
一切戲劇的題材都是描寫人類意志的一種鬥爭。從希臘時代起直至現代為止,一共創造了四種型式。這幾種型式,就其與人物意志對抗的勢力之性質,而生出區別。
戲劇發展的第一型,描寫個人與運命抗爭,希臘戲劇可為代表。
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 他的代表作是《伊底帕斯王》。故事是這樣的:
古希臘「甲」國國王,生了一個兒子。他便興高采烈地跑到神壇去祈問這個孩子的將來的命運。神在空中回答,說這個孩子將來會殺死自己的父親,娶自己的母親,和篡奪父親的王位。這個...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弁言 黎覺奔
趙如琳先生是我國傑出的戲劇理論家和戲劇教育家,是名演員也是名導演。在與我們經過抗戰洗禮的同輩朋友們中,在抗戰期前後的中國劇壇上,趙先生的名字並不陌生。
趙先生原籍廣東,早年出身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在學生時代,即嗜好演劇;特別對於戲劇文學,有濃厚的研究興趣;孜孜不倦,披覽世界戲劇名著。他的外文基礎很好,時而喜愛迻譯一些西洋名劇及一些重要的戲劇論文;因感於我國早期話劇理論之貧乏,甚至一本像樣子的「戲劇概論」也闕如,便決心把漢米爾頓的《戲劇原理》翻譯出來,藉供話劇工作者參考,期有助於理論...
趙如琳先生是我國傑出的戲劇理論家和戲劇教育家,是名演員也是名導演。在與我們經過抗戰洗禮的同輩朋友們中,在抗戰期前後的中國劇壇上,趙先生的名字並不陌生。
趙先生原籍廣東,早年出身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在學生時代,即嗜好演劇;特別對於戲劇文學,有濃厚的研究興趣;孜孜不倦,披覽世界戲劇名著。他的外文基礎很好,時而喜愛迻譯一些西洋名劇及一些重要的戲劇論文;因感於我國早期話劇理論之貧乏,甚至一本像樣子的「戲劇概論」也闕如,便決心把漢米爾頓的《戲劇原理》翻譯出來,藉供話劇工作者參考,期有助於理論...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次
【上篇戲劇藝術之發展/趙如琳】
戲劇發展的四個主要型式
第一型:描寫個人與運命鬥爭
第二型:描寫個人與自己的性格的鬥爭
第三型:描寫個人與環境抗爭
第四型:描寫集團與集團的鬥爭
羅曼主義的戲劇:十九世紀初的戲劇主潮
(一)導論
(二)羅曼主義的定義.諸家的見解
(三)羅曼主義產生的背景
(四)羅曼主義之發展
(五)羅曼主義在戲劇上的革命
(六)羅曼派在劇場的輝煌的勝利
(七)古典與羅曼的對照
(八)對羅曼派的批判
史丹尼表演藝術體系的精義
史丹尼表演藝術體系的形成
史丹尼表演藝術體系的...
【上篇戲劇藝術之發展/趙如琳】
戲劇發展的四個主要型式
第一型:描寫個人與運命鬥爭
第二型:描寫個人與自己的性格的鬥爭
第三型:描寫個人與環境抗爭
第四型:描寫集團與集團的鬥爭
羅曼主義的戲劇:十九世紀初的戲劇主潮
(一)導論
(二)羅曼主義的定義.諸家的見解
(三)羅曼主義產生的背景
(四)羅曼主義之發展
(五)羅曼主義在戲劇上的革命
(六)羅曼派在劇場的輝煌的勝利
(七)古典與羅曼的對照
(八)對羅曼派的批判
史丹尼表演藝術體系的精義
史丹尼表演藝術體系的形成
史丹尼表演藝術體系的...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