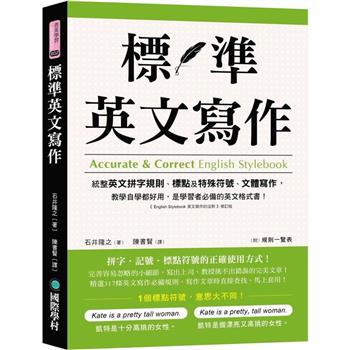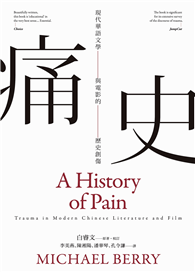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新百喻經:開啟人生智慧的80則續四益的圖書 |
 |
新百喻經:開啟人生智慧的80則續四益 作者:陳四益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2-1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新百喻經:開啟人生智慧的80則續四益
不貪不等於好官、寬容不一定是美德、真理也有限度、主意不宜過多、愛並不都是好的、盡信書不如無書、書中沒有黃金屋……關於本書 《百喻經》是一部流傳極廣的佛經寓言,為西元五世紀時,天竺法師僧伽斯那從《修多羅藏》十二部佛經中,摘取素材,編纂而成;在西元四九二年,南朝齊武帝永明十年時,由僧伽斯那的徒弟求那毗地翻譯成中文。全經包括了九十八則的「喻」,加上卷首引言及卷末偈語共計百則。原無單行本,現在所能見到的《百喻經》,是魯迅在一九一五年捐資鏤版所印行的。 陳四益自一九八三年起,使用自創的「聊齋體」文言創作《新百喻經》。試圖以淺近的文言,寫全新的寓言故事。全書本無解說,後在每篇文末多加註解文字,遂成今日《新百喻經》一文言,一圖,一解說的面貌。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四益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2-11-01 ISBN/ISSN:9789572072493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神話/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