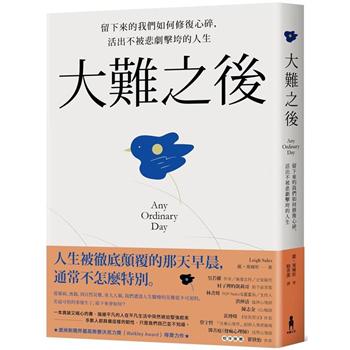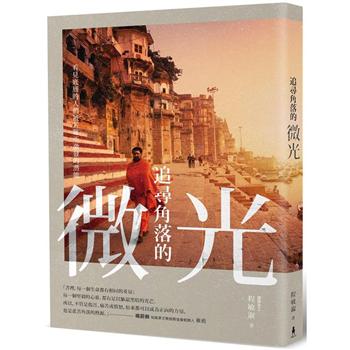導讀
舌頭的旅行
《完全壯陽食譜》出版後,我被誤會成美食家,常應一些餐館邀請去「試吃」。我生性貪吃,又死要面子,如今有機會到處暴飲暴食,只好努力裝點這方面的常識,三年多以來,幸而讀了不少好文章。
福爾摩斯的老朋友華生醫師說:「福爾摩斯的好胃口就是破案在望的兆頭」,其實任何事情柳暗花明時,任何人都會有好胃口,也都需要一點好胃口。
蕭伯納雖然二十五歲起茹素,又是絕對的戒酒主義者,卻從未缺乏胃口。他不喝茶,下午茶時間就喝一大杯牛奶,並吞下許多巧克力餅乾和水果蛋糕,有時候竟坐著舔一碗糖或一瓶蜂蜜,一匙匙塞入口中。直到老年他都這樣嗜吃甜食,而且一生極其健康。我們輕易可以想見這個才華洋溢、睿智的老人,學童般,手裡總不離一片巨大的蛋糕,上面還覆著厚重的糖霜。
我最同情吃飯乏味的人,應付般三兩口交差了事。既然時間倉促,吃飯又那麼沒趣,何苦自虐呢?現代人普遍營養過剩,稍微餓幾餐也不要緊的,我建議乏味於吃飯者兩天吃一餐,將其它五餐的時間儉省下來,集中在一餐仔細品味,才不會愧對食物。
天下的桌子以餐桌最迷人,坐在餐桌前,往往充滿了幸福感。對我來講,走進餐廳像走進教堂,總是帶著虔敬、期待的心情。
貪吃鬼不免肥胖,這是我的宿命。貪吃而痴肥者的形象,容易與愚蠢聯想在一起,兩眼常呆滯,行動遲緩,可能連思考能力也喪失了,從前讀土庫曼斯坦詩人馬赫圖姆庫里的詩,就覺得像在警告我:「不要像傲慢的石雞把山林嫌棄∕受食欲的誘惑而喪失雙翼」。我固然明白貪吃的形象欠佳,卻知易行難,要節制飲食是多麼艱苦,多麼難以下定決心。
臺灣俗諺「一吃二穿」,人生在世以腸胃為根本,這道理淺顯,路人皆知,不吃則不能生,然而吃飯豈是簡單?所謂「富不過三代,不會吃飯穿衣」,可見吃飯關聯的是文化,比較不是富裕;一個富足的社會像台灣,可能猶原是貧困文化(poor culture)。
「品」字三張口。對法國人來講,知味、辨味,並不是品味的一部分,而是品味的全部。相對於中國和法國,英國人顯得不太理會肚皮,林語堂就比較過,「法國人的吃是熱烈地吃,而英國人的吃,是歉疚地吃」。
一個人的耳朵聽不懂巴哈、舒伯特、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可能顯得這個人的音樂修養不足,不夠高尚。一個人不懂得欣賞梵谷、夏卡爾、達利、畢卡索、張大千的畫作,我們也許可以說他藝術修養不足,還需要多用功。但是,如果一個人不懂得吃,不懂得分辨食物的好壞,或完全不知道飲食文化,那麼,這肯定是個非常值得同情、憐憫的人。
飲食是文化,也是品味,任何主張和創意,都指向一種生命的胃口,而這種生命的胃口,來自對食物的好胃口。
有時候出國旅行,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多相當短暫,許多美好的風光早已忘得乾乾淨淨,唯獨記得某種菜肴的滋味。我竟用味覺在記憶城市。張愛玲說,叫賣「草爐餅」的聲音,「是那時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鄰家無線電的嘈音,背景音樂,不是主題歌」。
面對食物,不僅口舌或消化器官的問題,也是一種審美品味,而品味並非與生俱來,需要點點滴滴地養成。有些文人將飲食簡化為人的本能和生理需求,對他們而言,飲食僅能滿足生理需求──止飢解渴;無法滿足精神需求──審美活動。這不是食物本身的錯,是他們的精神智障。
我大膽以為,中國文化稱得上「博大精深」的大約只有飲食一道。先秦時期,雖然還沒有飲食專著,《詩經》、《禮記》、《周禮》、《儀禮》等儒家經典即有大量關於飲食的記載。
《論語.鄉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這一段文字頗為詳細地談論飲食,可見孔老夫子不但喜歡烹調精緻的食物,也講究衛生,他不吃的東西還真不少──飯走了味,不吃;東西不新鮮,不吃;烹飪得差,不吃;非季節性產物,肉沒切得方正,調醬不對,統統不吃;連市面上買的肉,唯恐不夠新鮮,也不吃。
其實中國文學自古即不乏飲食書寫,許多前人精采地品味過飲食,光是明清就包括劉伯溫、陸容、陸樹聲、徐渭、屠隆、張大復、謝肇淛、袁宏道、王思任、文震亨、張岱、許次□、徐樹丕、傅山、周亮工、蒲松齡、鈕琇、紀曉嵐、俞蛟、諸聯、梁章鉅、陳徽言、林紓……可見不注意飲食,缺乏食物知識和可能的判斷,委實感染了文化健忘症。讓標榜清心寡欲的人繼續鄙視口腹之欲,我呢,還是愛戀著美味的食物。
我歡喜讀菜單,全世界只有中華料理的菜單最像詩句,一般西方菜單上呈現的菜名都旨在顯示食材,中華料理的食材去常常故意隱晦,形而上地表現菜式的意境,如廈門南普陀的素菜名:「彩花迎賓」、「南海金蓮」、「半月沉江」、「白璧清雲」等等;又如客家菜的菜名有「孔明借箭」、「八脆醉仙」、「雙燕迎春」、「四季芙蓉」、「玉兔歸巢」、「麒麟脫胎」等等,乍看之下,豈知「麒麟」是狗,「胎」是豬肚呢。
我更歡喜讀食譜。其實許多一流的文學心靈都寫過食譜,如蘇東坡、袁枚、李漁、朱彝尊、張愛玲……我還收集了一些外國文人、藝術家的食譜,包括西洋作家如未來主義的創始人馬里內堤(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狄更斯、蕭伯納、海明威、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費雪(M. F. K. Fisher),畫家如莫內、達利、畢卡索……這委實是一種才華,創作的才華,和生活的才華。
飲食活躍了作家的精神和生涯,殆無疑義。英國廚藝家伊麗莎白.大衛(Elizabeth David)的食譜裡有一篇短文〈義大利魚市場〉,描寫黎明前的威尼斯市場,場景恍如「欣賞一齣前所未有的精采芭蕾舞劇」,各種活蹦亂跳的海產,魚身的條紋、色澤,閃著新鮮的光芒,我們彷彿聽聞嘈雜的吆喝、交易,與海洋的氣味,不僅令人食慾蠢動,也令人精神感動。
食譜裡不乏優美的文字,遑論文學裡的飲食。提姆(Uwe Timm)用一道菜鋪排出《咖哩香腸誕生》這部長篇小說,藉食物的滋味,表現戰爭的滋味,和亂世兒女的際遇。艾斯奇弗(Laura Esquivel)以十二道墨西哥菜肴,編織出充滿情欲糾葛的《巧克力情人》。電影《芭比的盛宴》和《濃情巧克力》分別通過一頓法國大餐、巧克力,改變了一個村鎮的面貌,也等於是對這個小鎮的所有的人,進行了一次成功的人格改造工程。吉本芭娜娜的小說《我愛廚房》則通過一客美味的豬排飯,幫助櫻井美影和雄一,發現了相互信靠的情愛,那客豬排飯,扮演了從驚喜到發現到分享人生滋味的要角。
當文學逐漸淡出了生活,有人在飲食裡重新發現了文學。
文學裡的美食總是帶著懷舊況味,令人沈思,令人咀嚼再三。大概美食屬於記憶,曾經嚐過的美好食物,保存在記憶裡徘徊,回味。
然則飲食跟人生一樣,是無常的,口福值得吾人珍惜和追求。從前我常去「涎香小館」品嚐朱家樂先生的手藝,忽然有一天店門口就掛出暫停營業的牌子,原來朱先生罹患肺癌住院;後來竟連招牌也拆了,聽說竟不敵病魔謝世了。啊,從此去何處吃順德菜……從前,多次在假日帶家人、朋友遊陽明山,並到馬槽溫泉附近的「日月農莊」泡湯,吃燒酒雞,二○○二年六月十九日,日月農莊遭祝融肆虐,忽然就化成了灰燼……
提倡、研究飲食文學,是一種文學主題學的生產,同時也意在喚起沈睡的審美感受。
臺灣早期的飲食散文,大抵帶著濃厚的懷念況味,如梁實秋、梁容若、唐魯孫、琦君、林太乙,或懷人情或懷鄉味,形成書寫的主調;後來則呈現描寫對象的差異,漸漸較重視文化景深,和較純粹的審美感受。
《臺灣飲食文選》還是優先考慮文學性,因此而沒有選入一些美食家朋友的文章。這是我初步爬梳臺灣飲食散文的成果,我希望通過這些散文,呈現臺灣飲食散文的發展風貌,和世代差異,從梁實秋以降,飲食散文在質量上都已經開發出可觀的成績。
三年多以來的閱讀,我發現頗有作家歡喜藉食物描寫親情,將飲食作為一種話語策略,由於篇幅不少,另輯為第二冊,堪稱「親情的滋味」。
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