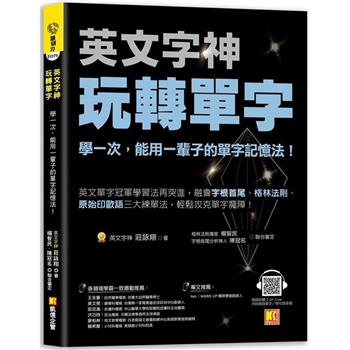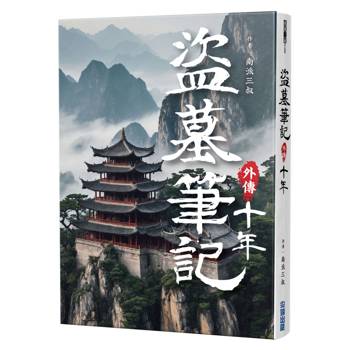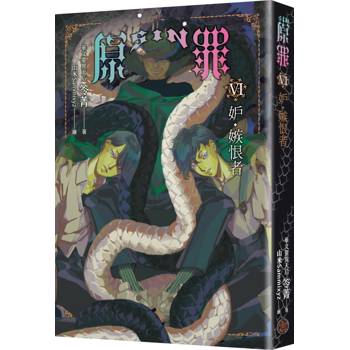摘要
小說家駱以軍自二○○二年起每週固定於《壹週刊》上發表一篇約二千字的專欄文字,另外亦由印刻出版公司整理集結為「我們」系列諸書。這些作品一方面具有漫談、隨筆的鬆散性格,而另一方面卻因其強大的「虛構唬爛」質地,使得讀者在文類認知上備受混淆。本文嘗試檢視駱氏如何以其獨特的思維與書寫性格瓦解「副刊專欄」(散文文類)與「私小說」(小說文類)的枷鎖,同時向文類未生成時的「說故事傳統」回溯的冀為學界及出版界對駱氏作品的分類歧見,提供另一視角。在當前後現代語境下,文類的權威已有逐漸崩毀之趨勢,駱氏於《壹週刊》之「去文類」實驗,亦或可視為「時文」之新標竿。
關鍵詞:駱以軍、壹週刊、文類
一、前言:被置換的圖書分類號
二○○二年五月,駱以軍於《壹週刊》第50期開闢〈我們〉專欄,自此之後,每週一篇,至今不輟,累計已達四百餘篇。其後又編次其中篇章,由印刻出版公司集成「我們」系列三書,分別為二○○四年之《我們》、二○○六年之《我愛羅》、以及二○○九年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而在這體例、內容皆如水銀瀉地的漫汗專欄中,亦間雜有作者代擬成人後之次子,追述其幼年時期關於父親(及整個時代)之種種,自成系列之連貫品,這部份則另集結為二○○五年之《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一書。
按理專欄文體本無固定範式,駱以軍之文字表現,或許可用「隨筆」二字便盡皆概括,在文類區分上,幾乎不構成值得研究的問題。然而當這些篇章脫離週刊載體,變換為實書出版後,在閱讀認知上便產生了不同的意義。讀者不論在進行閱讀行為之前或當中,勢必將不斷探尋這些零散文字「糾合於同一本書的邏輯」何在?這個提問有助於理解整部著作的敘述風格與脈絡,而文類的定位,往往就成了解決此問題的重要參考。
細察駱氏上述四部著作,《未》書與「我們」系列三書於文類劃分上,幾乎可以用最基本的辨別法則「一刀切」。因為不但該書的「敘述者」為「虛構」,甚至包含次子之未來職業(學者?作家?),以及臺海大戰後都市荒蕪破敗之設定等「背景」亦然。在這樣粗略的比較歸納下,我們或許能快速認可《未》書的「小說」地位;而相對的「我們」系列,看來則可歸入另一「同類邏輯」。三書當中的敘述者「我」,無疑即駱以軍本人,總一貫絮著其陰暗的成長史、傳媒中浮誇渲染的社會新聞事件、以及種種莫名其妙、或親歷或竊取而來的妖異人生際遇;有時更不免夾敘夾議,大放厥詞、亟發牢騷與感慨。此類書寫體裁、風格,無論要稱為「散文」,或「隨筆」、「札記」,其實皆不脫以作者生活為核心的「誠實」 描述,與虛構小說之區囿應當十分明顯。
以上文類劃分,雖是筆者「一廂情願」之見,但竊亦認為這理應是所有受過基礎文學閱讀訓練者之共識,然而在綰合相關資料準備進行驗證之時,竟不禁開始為自己過於輕率的判斷感到擔憂。茲稍舉一例,比如從與出版品關連極深的圖書館圖書分類法來看,這幾本書的文類就會顯得相當錯綜複雜。一般來說,出版社在版權頁上的「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裡,大致會先提供「建議性」的圖書分類號,然書籍送到國圖實品館方仍會再行斟酌。
《未》書的分類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按「中文圖書分類法」 編號,即屬於857小說類下。然而《我》書,卻頗出乎意外的未被歸納於855散文、隨筆、日記類下,無論是出版社及國家圖書館皆以小說目之,將其歸諸857,此中落差,便甚可推敲。再看《羅》書,出版預行資料還是在857項下,但國圖對此或已產生疑慮,因此在最後編目時,便改置此書於855散文類中。及至《經》書出版,出版社早已自動把其圖書分類修改成855,惜國圖檢索系統上尚未見此書編目,無法做最終比對,不過光從這些資料來觀察便不難看出「我們」三書在文類判定上的掙扎。
當然,我們或許可以猜測,會不會是因駱以軍之前從未有所謂「散文」之集結,故出版社權且依生產者之「小說家」身分,逕將作品以「小說」報上戶口;而在第二次如法炮製時,國圖卻開始對作品的家世提出質疑,經過此番「提醒」,出版者才將其「正名」回散文之下。但若以這種歸咎於「行政程序」的方式來判讀,便未免太小了看駱以軍在文類上作亂的才能。雖然這幾組置換跳躍的分類號僅是簡單的數字,卻不啻是文類如何受到變亂的一種,因為除卻分類號碼,在各式各樣與此系列有關的文學評論當中,類似的疑問更所在多有,足見其文類特性,本來就非簡單的法則所能盡解。由於「我們」三書體例相當一致,實在找不出理由來區分何以此書是小說而彼書卻是散文,故無論如何,都應將它們視為一個整體來加以分析。而從週刊專欄的性質出發,探索這駱氏這三部著作如何漂浮於文類的「裂縫」,最終又將落向何方,則是本文最欲著力之處。
另外必須強調的是,《未》書雖以虛構視角進行敘述,但實質上卻與「我們」三書無甚差別,只是觀察者與說故事者有所轉換,其次子追憶之「往日」情節正是駱以軍之「今日」,只是借次子之口遂行其最擅長的「扯淡」之實。欲研究駱氏之週刊書寫,本不應將此書排除在外,然本文既以「文類」為切入核心,小說特質明顯之《未》書便只好作為另三書之參照,難以合併討論。或許這也是駱以軍的創作潛意識,在不願被分析歸納的前提下所入的暗樁路障。此即標題僅列舉「三書」而非「四書」之原因,特此加以說明。
二、刊屁股的文類輻散
駱以軍的〈我們〉在《壹週刊》上可說是個相當長壽的專欄,其資歷大約僅低於從第15期專欄草創時便開始撰寫的黎智英與詹宏志。《壹週刊》後的專欄集合,應可直接視為該刊物之「副刊」,或許亦可仿「報屁股」之例,戲稱其為「刊屁股」。有趣的是,像《壹週刊》這樣的八卦娛樂刊物,倒是頗願意大力資助文學創作者,讓他們領取高額稿費,以助妝點充實副刊之門面。當然,在某些較強調文學嚴肅性的論者眼中,這裡頭不免也隱含當代作者難逃被資本體系「納編」的悲哀。駱以軍亦自承接下這個鬻賣文字的「工作」,可確保其經濟來源無虞。但毫無疑問地,對駱以軍這樣一個以小說為職志,並早已習慣小說思維的創作者而言,週刊專欄的限制,多少都會對其寫作策略乃至於作品性質造成影響。這些影響簡而言之可由兩個面相來理解。
其一是對篇幅框架之屈就。唐諾對此便曾甚表憂慮,「裏面很多內容就沒法回頭,每個禮拜一篇,書寫就以1800字為單位進行思考,字數到了就收尾,很難有完整的空間處理東西。」 對駱以軍小說書寫具有期待的純文學讀者,恐怕一時難以接受這種欲言又止、不痛不快的方寸小格局。在《我》書當中,駱以軍的戛然斷尾幾乎是慣例,不顧讀者觀感之程度有時已達無理之境。不過到了後期,特別是《經》書中的篇章,便有不少已被乖乖馴服至「理想專欄」的樣貌,不但偶有些「時事評論」、「藝文引介」,甚至還溫溫吞吞地起承轉合起來。駱氏的「職業道德」讓他很清楚知道,在《壹週刊》上賣不了真正的「小說」,只能算賣出的文字表演,因此駱以軍寫散文 這件事固然引人側目,但卻不免帶來「關西大漢執紅牙板」的突兀感。在如椽大筆寫蠅頭小楷的前提下,或許這類「小說家散文」,本質上就容易隱藏著變異的基因。
其二則是書寫內容的選擇。正如唐諾前引文所強調,為應付「每週一篇」的高壓寫作,其機械式生產思維一旦開始運行之後,確實便難以煞車。駱以軍大概很擔心聽到「你年輕時還挺性感的,後來怎麼生了孩子後,就儘寫些包尿布洗奶瓶的瑣事,我就不看你的東西了。」(未121)之類的抱怨,所以「避免日常生活細瑣之陷溺」與兼顧「好看」,同樣是他念茲在茲之事。當然事實擺在眼前,駱以軍的表現是極為成功的,《我》書上市後即十分罕見地以純文學出版品型態殺進了金石堂書店暢銷書排行榜。 姑不論書中那「五年級男性外省藉都市邊緣人生活史」的情調是否觸發了某些導致讀者瘋狂的機栝,但可以確定的是,駱以軍太善於拾掇、組合、操作那些暗合於《壹週刊》調性的光怪陸離奇譚軼事,甚至挺懂得適時「爆料」拋出一些代號或索引,供讀者追尋、破解一點藝文界之「八卦」。例如在三書之中反反覆覆現身的D君,總難免讓讀者幽幽歎道:「啊!原來戴立忍平常是這副德性哪!」,看到D在當兵時女友不幸遇害的悲慘戀情,讀者必然大受震動。這可看出駱以軍專欄書寫的另一類機械化制約──「故事不驚人死不休」,此或是駱氏得以榮冠「暢銷作家」頭銜之主因(諷刺的是靠的並非小說作品)。
另外,在內容「上道」、「敬業」之餘,駱以軍的散文,更就此拋去了傳統的「抒情」氛圍,不再對讀者掏心掏肺,只專注在「表演」,而成為「因自閉害羞而只能用胡說搞笑化解尷尬者」的獨白。這是駱以軍這個小說家在「市場」上被磨練出來的最佳寫作策略。在按時交貨的壓力下,作者只好像一千零一夜中的王妃一樣,著魔般地把故事之網編織下去。當單一碎拆的故事漸漸在網上交錯縱橫,顯現出另一種大規模的拼貼風景時,便勢難以用專欄以規範,文類之脫出,亦成為必然。
董啟章在一次與駱以軍的對談中,曾經提起因為之前認識駱以軍,都是透過小說,後來「當我讀到你在《我們》一書裡面那些『非小說』的散文,感覺竟是跟讀你的小說差不多。」 這一方面是在當中看見了駱以軍的難以隱藏的小說語調,另一方面的意思則是,「小說和你分不開來」,駱以軍散文所書寫的「生活」未免也太「小說化」得讓人難辨虛實。
黃錦樹在評論《我們》時,同樣曾提起「這是小說?還是隨筆?」之質疑,然後為本書下了一個概括式的斷語,「這本書充斥著小說的屍骸。」 換句話說,「我們」三書的原質幾乎是駱以軍小說的「廢料零件場」,作者將平時拾荒而來的材料略加整理,需要時便巧手拼飾成小說,餘者不足以成事的,居然也可變成專欄小篇章「廢物利用」。若反向追索,在「我們」系列中,同樣可以找到太多駱氏小說中的「原材」,像大學同學「純種人渣倒楣鬼盧子玉」在高中時誤將一名北一女學生推下火車的故事(我43),駱以軍顯然甚為寶愛。「盧子玉」不但是一切人渣之「原型」(第三個舞者),那北一女學生,也成了故事主角所「曾經軋過的一個女人」(月球姓氏161)。南迴搞軌案的李氏父子(經148),則擴展為《西夏旅館》中二十餘頁名為〈鐵道〉的章節。是以「我們」系列庶幾可視為駱氏小說之延伸閱讀,或者當成「補注」,有了這層聯繫,其「散文」地位自然沒那麼單純。
駱以軍對於撰寫專欄,除了抱持養家活口的職業自覺外,其實還有種更積極的態度,就是把它當成「如同運動員般在現代管理技巧下日常重複的拉筋劈腿作細部的訓練」 ,用以蓄積能量,以等待上場時機。屢受憂鬱症襲擊的駱以軍,便是靠這樣規律的暖身,而終於再造四十五萬字《西夏旅館》之高峰。準此,駱氏即使在為此「雕蟲小技」之時,也決不馬虎。畢竟,《壹週刊》專欄的讀者,絕對比到書店買小說的人口多得多。而不論是否熟悉其小說作品,或了解其文學史成就,對普通讀者而言,「我們」系列都是好看的散文。平心而論,在去除「小說優先」的「成見」後,光看其受歡迎的程度,唐諾、黃錦樹等人對「專欄形式如何限制了台灣這一世代最受期待的小說家駱以軍?」之疑慮,或者也顯得不那麼必要了。
三、私小說的紓緩空間
駱以軍的小說常被評論者冠以「私小說」之名目,有時也因而備受批判。駱氏雖不否認日本文學中私小說的筆法與形式對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卻不認為自己真的有意於此。其小說作品向來慣於使用第一人稱敘述,然正因在取材上勇敢(或大膽)地暴露「真實自我」以及以「我」為中心而輻射出去的人際社群中的種種,遂難免動輒受到道德眼光的檢視。除了內容提及混亂的生活及思想被評為「惡德」,隨時獵題材的習慣也幾乎使其被視為「狗仔」或「故事豬籠草」。有時這種使「他人的生活被虛構入侵」 之作風,甚至讓他身邊的親友都不由自主緊張起來。駱以軍雖不想為自己辯白,可是當看到「這種人我不分的寫法,令人迷亂,卻中傷許多人,作者的道德爭議,留給讀者去判斷吧」之類的評論,卻還是「屢屢被這樣平庸又粗暴的想像力手指伸進小說的黯影界面弄得厭煩又沮喪」(羅113)。
小說與真實之模糊交涉,雖早就有比駱以軍更「灑狗血」之案例(如李昂北港香爐事件),但堅持以「我」為小說敘事觀點,更無異授人以柄,讓讀者產生諸多聯想。對小說魔法具備充分抵抗力之讀者,自然可認同以下這種專業評析:
小說中說話的『我』,其實不是任何一個人,既不是駱以軍本人也不是小說虛構的敘述者,而是『它』……透過各式雜交交雜的訊息與集體記憶述說著一種非人稱(或第四人稱)的話語;而『我』不再是我,是由事件(八卦)空間與時間(記憶)疊層所共構的『他者』。
而閱讀經驗更廣泛的讀者,或更早已有對日本私小說乃是將「我」放入所處環境,進一步反省「群我關聯」之認知。可惜的是,駱氏仍然只能慨嘆:「台灣不知從何時起,將『我』這一詞劃出了邊界,使得它變成一個簡單層面的『道德神話』,或是與文學無涉的道德判斷。」
駱以軍面對荒謬的大環境,對自己的書寫視角確實產生了極大焦慮,他不但開始自覺到「小心哦,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你不會用『我』以外的人稱去說故事了」(我224),更賭氣似地採用「他」(圖尼克)這一敘述人稱進行《西夏旅館》之撰寫,即使寫得「很悶」也在所不惜。當然,除此之外,他還開發出了另外的新方法,而且說來好笑,這還得歸功於他那不自覺將事情弄得更糟的爛個性。比如說他在小說《遣悲懷》後面所附加的那篇〈後記) ,裡頭不但如真似幻地寫了一段到大學演講而遇上惡漢作家W(舞鶴)的往事,更穿插了幾幕因寫作《月球姓氏》而激怒妻族三舅,使得其他家族成員也因此緊張、迷惑起來的「不大不小的麻煩」。最後當妻的大姊以維護自己妹夫的態度說出「小說就是虛構的嘛」一語時,我們也很難判斷是否這些可憐的族人(或讀者)又被駱以軍呼弄了。故而他在小說後面安排的這記「回馬槍」,遂更加讓人看不出究竟是「反省」抑或「挑釁」?到底要讓論者更加「知之」是「罪之」?
我們不妨把這個例子看成是個供作者「紓緩壓力」的裂口,雖然在小說後面加上這麼一大篇「自道」實在不是常態,但以「自我治療」的角度看,效果應當相當不錯。駱以軍有時也需要脫掉「小說我」的面具,以較接近真實的自我向世界「幹譙」幾句,因此這篇文字甚具啟發意義。按《遣悲懷》出版於二○○一年底,當時駱以軍尚未在《壹週刊》開闢專欄,因此這篇格調極似「我們」系列的〈後記〉,只能像鬼魅一樣附身在小說作品之中。數月《壹週刊》這爿讓他恣意胡說漫道的園地正式啟用,駱以軍在小說寫作時所受之「鳥氣」,便可盡數發洩於斯。
在《第三個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懷》連續三本重量級長篇之後,駱以軍創作正陷入頗長的一段低潮期,身心上的疾病亦接踵而至,而專欄的寫作,正好是一種小說技藝緊繃枯竭後的紓緩放鬆。甚至在下一部小說遲遲未能成形的「鬼打牆」時期,也能在此整理、搬弄、預演一些零零碎碎,免得陷入一事無成的自我譴責之中。前幾部小說,既然因「我」之敘述而招致「私小說」的誤解,那麼藉由散文寫作,應該就可以暫時卸下「務須嚴守虛構與現實之界線」的枷鎖,「我我我」得理所當然,除了偶爾八卦一下的「私德」問題(反正本來就是腥羶色雜誌),最少在小說的「職能」上,當可不用再受質疑。
然而,承接上述的討論理路,當我們再次把焦點移回週刊專欄的這幾本集結時,一定不禁想檢視在這些每篇不過兩千字左右的「散文」之中,駱以軍是否又手癢偷渡了某些「私小說」的毛病,或者說在這裡面如何積蓄小說之能量。在「我們」系列作品中,駱以軍顯然把「私」這個概念做了更「私人化」的發揮,這部分可舉兩類例子為證,即「唬爛敘述」與「夢境書寫」,此二者都已脫離了原本私小說概念之現實主義層面,而進入他人無法置評的幽微處。
所謂「唬爛敘述」,完全就是作者書寫性格之擴大,駱氏小說本來就具有此類基調,其「非比尋常的打屁才能」 一向為人稱道。但到了專欄時期,駱以軍終於毫不避諱地大談自己的唬爛哲學,揚言「唬爛就要龐大華麗」(經156),不但認真搜羅身旁貨真價實的「唬爛」之事,更自承「『關於唬爛的故事』恰是我的死穴。如果有一部電影叫《我這樣唬爛了一生》或《唬爛國再見唬爛國》,我可能光聽片名就淚腺失禁了」(羅242)必須強調的是,駱氏所謂之「唬爛」絕非「虛構」,而是立足於真實之「不可思議」,比如其九十餘歲高齡的外祖母因多重器衰竭而昏迷,醫生亦發出病危通知,在親族於「靈床」前助念六七小時之後,又勁搞搞活過來的「謬事」,駱以軍就深受震撼,還因此「興沖沖」地寫了兩次。(經125,179)另外朋友大象斬釘截鐵發誓,在三十年前,曾於台鐵餐車上遇見當代《電視冠軍》中年輕女性大胃王赤阪尊子的「怪事」,駱以軍也因難以質疑,又轉而向讀者大唬特唬。(我222)故而閱讀「我們」系列,無異於窺探一個唬爛故事組成的萬花筒。
而「夢境書寫」,亦是駱以軍開發出的另外一絕,乃是將故事之編撰交給潛意識代行,他只要在床頭備妥紙筆,在醒來的間隙奮力記述便行。作者扮演的角色,只不過類似村上春樹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裡所塑造的「夢讀」。駱以軍融合夢的情節在小說中已有前例。不過在專欄裡,其比例之高、頻率之繁則更引人注目。如《羅》、《經》二書,皆以數篇目不暇給的夢境漫遊開場,讓讀者如入霧中。夢境所生產出的情節更為細瑣繁複,情景轉換則更為劇烈,對讀者而言,要跟上作夢的駱以軍也愈加困難。一開始或許這是駱以軍在「唬爛」故事青黃不接時,用以避免開天窗的好方法,但在運用熟練之後,那些閃跳無邏輯的夢境竟也開始發出異質的光芒,甚至已經超出專欄的器性,轉而變化成情節巨大龐雜之小說的縮影或暗示了。
當駱以軍從焦慮的小說書寫情境中暫退,在閒散的專欄文體中尋求療養時,卻還是不慎導出了「唬爛」、「說夢」的寫作習慣,這二者所構築的「去真實性情節」,必然造成其筆下散文文類主導要素(dominant)之位移 ,讀者在閱讀的過程當中,自然極容易因此產生疑似觀覽小說的錯覺。這些作品在當今的文類成規下,當然不宜稱為小說,但我們或許可將它們視為比「私小說」更貼近作者之個人性格、潛意識,而以一種更紓緩的方式呈現的「準小說」文字,它們是包含對消逝時間之慨嘆、真實詭麗世界之描述、以及跳樓大拍賣式的荒誕故事大拼貼,是駱以軍為二十一世紀台灣社會所撰寫的「時文」。
四、講故事的人和書
雖然前兩節已經提過關於「爆料八卦」與「唬爛故事」之觀念,但前者屬於週刊專欄(散文)之美德,後者是私小說的轉化,兩者都還是以既有文類規範為中心來開展。此處筆者想更進一步討論的是,既然駱以軍在此三書當中,總像起乩般不斷碎念著一個又一個的離奇故事,那麼我們是否可以乾脆去除文類的迷思,將目光轉回故事本身,看看這本「故事集」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敘述性質。
村上春樹有部作品名為《東京奇譚集》,內有五篇短篇,事實上就是一本現代版的「唬爛鬼故事」。對許多讀者而言,此書引起之感受絕不同於村上其他「小說」著作,那是因為「說鬼」的氣氛,勢將調動起過去成長歷程中種種關於「聽故事」的經驗及想像,比純粹閱讀具有更豐富的層次。駱以軍之「我們」系列,也有相似的效果,只是氣氛並不像是「試膽大會」,而比較接近豬朋狗友在酒館或咖啡館中的胡天胡地。
關於小說與故事的差別,班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曾論到,小說基本上是印刷術發達後的工業產物,對「書本」嚴重依賴,因此不論是作者或讀者都是孤獨的人,他們無法面對面互相分享經驗。故事則全然屬於一種「手工藝」氛圍,美好的聽說故事經驗,大約都須建立在「時間不足惜」的基礎上。在上個世紀三○年代,班雅明已經慨嘆道:
講故事這門藝術已是日薄西山,要想碰到一個能很精采地講一則故事的人是難而又難了……當有人提出誰給大家講個故事的時候,滿座面面相覷,一片尷尬。就彷彿是與我們不可分割的某種東西,我們的某種最可放心的財產被奪走了:這東西、財產就是交流經驗的能力。
故駱以軍以「我們」為專欄題名,恰恰散發出一股潛藏於作者心中,亟欲將讀者拉入一暱暱低語的「自己人」氣氛,並在此物以類聚(或駱氏的常用詞「物傷其類」)的情境下,葷腥不忌地交換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教訓。駱氏時時遺憾自己是個「經驗匱乏者」,不像白先勇、張愛玲甚至章詒和,打從誕生在那樣的家庭開始,便坐擁令人驚嘆的素材。班雅明也提及有兩類人特別擅長說故事,一是常常遠行的水手,二則是善於探聽鄉里動靜、習於發揚傳統智慧的農夫。駱氏的「宅」風格,當然趨近於農夫,不過從眾多曾揚帆於偉大航道的朋友身上,他則獲得了更多超乎其想像的精采故事,這已足以讓他在專欄裡扮演一個「很有故事」的智者,吸引眾人乖乖圍坐在他身邊烤火聆聽。筆者讀駱以軍,常感到作者那股「再不說就要忘了」的急迫。起因一方面或許是作者有保留「五年級成長經驗」之使命感,另一方面,則或許是在憂鬱造成的孤寂中,所極需的「與人交流而獲得的存在感。無論如何,這些正好都是說故事的重要緣由。
況且表面上看來,駱以軍的故事雖既八卦又唬爛,但其實此中仍蘊藏了所謂故事應有的「教養」。班雅明認為,故事既植根於經驗交流,那麼裡頭就應該要含有真正的智慧,亦即對聆聽者的「忠告」。 駱以軍雖然不見得有洞照世間的目光,也沒資格對誰說教,然而他卻很清楚,即使他無法完全敘說出來,但故事裡一定潛藏了某種發光的秘密。在《羅》書中〈故人〉這一篇,駱以軍提到在長輩友人家中,遇見一位極面熟的人物,但無論如何卻又想不起是何方神聖,最後謎底揭曉,原來此人即侯孝賢電影《戀戀風塵》的男主角。雖然那是一輩人的共同記憶,但因他僅只演了這一部電影,後來當然也成了無面目之普通人,目前則是正常上下班之記者。於是在對方「像是第一萬次面對這種『被認出』的場合」,耐性地解釋起當時參演電影的一切時,駱以軍又掉進了「那個年頭我在幹什麼?」的回憶渦流之中……這個故事不但重新改寫了「故人」之意涵,更像是個有關「時間」或「人際關係」的寓言。 駱以軍的「忠告」,即是以這種隱喻的方式展現。相較於寫作小說之「保持距離」,駱以軍在說完故事後便可開始亂聊其「啟發」,甚至開啟另一個故事,大多時候讀者雖仍不明所以,但卻絕對比閱讀小說來得「舒愜而親切」。
朱天心在為駱以軍《降生十二星座》所做序文裡,即曾指出書中種種「小道元素」,簡直與小說人物的生命與命運緊密生成一體。 而「我們」中的駱以軍,可說復從「小說」轉向了真正的「小道」書寫。我們甚至可以在當中觀察,駱以軍如何在「家族史」(月球姓氏)、「國族史」(西夏旅館)等「大敘述」的夾縫中,練習將自己完全放鬆沈溺於後現代的「小敘述」語境裡。駱以軍的故事,除了零碎細微、不具明顯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們還不斷散發一種駱氏所謂的Kee-Vee(台語「氣味」,羅76)。朱天心所提及電玩、動漫等「元素」,其實只是駱以軍所捕捉當代氣味的一部分;〈投籃機女孩〉、〈火影忍者〉諸篇,正是當代生活的「微物誌」。再推而向外,如〈楊宗緯〉、〈黎礎寧〉等寫歌唱選秀節目中浮沈的年輕生命,則勾帶起讀者在每週固定時段,對著螢光幕被引出淚水的廉價感情。寫咖啡館則描述「就巷弄裡兩排四層舊公寓的一樓改裝,進門前通常有個極小的園圃甚至小魚池,店前用寫生架放了塊黑板,上面黃綠紅粉筆寫幾道女主人私房菜的簡餐……店夫婦沉默敦厚,壁櫃上陳列著各式各樣他們去各處旅行帶回來奇怪玩意兒」(羅50),某間這樣面目模糊之咖啡館在歇業的最後一晚,竟刻意邀請作者夫婦共渡,並隱約暗示徵詢想將店面交由「氣質相近」之人繼續經營的可能。此即駱以軍筆下充滿台北Kee-Vee之故事。微細無甚意義,但卻極其精準。
正如同我們面對薄伽丘《十日談》那樣映現十四世紀義大利各階層生活縮影,甚至帶有淫猥氣息的作品(這部份駱以軍也不差)時,因其獨特性,遂很難用現今的文類法則加以界定。那麼駱以軍這套「故事集」,是否也可以還原其「後現代成人故事書」的面貌,而無需讓其在僵化的文類原則裡「妾身未明」?我們確實必須讚嘆,駱以軍在任何純文學都難以生存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竟能在資本媒體上重現班雅明所眷戀的純樸說故事氣氛。說故事,憑藉的當然還是文字的經營能力,因此文學顯然不會被趕絕,然在「故事」的身影又龐大起來時,此文類返祖現象必定使「散文」、「小說」之界域趨於模糊。準此,「我們」系列的文類意義,也可從「散文」、「小說」之辯外,找到更高的視點。
五、結語:故事之海、文類之妖
陳芳明在編選《九十三年散文選》時,曾選入駱以軍《壹週刊》專欄中〈觀落陰〉 一篇,在序文當中,陳芳明也對駱氏的文類頗為注目,認為「每篇都是獨立單元的敘事。但是,全部集結在一起時,又變成結構完整的小說。」 不可否認,駱以軍「我們」諸書作品間具有極強的互文參照性,在獨立以專欄呈現時,這一點並不明顯,但若並而列之,本來常常就沒頭沒尾的篇章,則更渙漫不知終始地擴散開來,讀者往往很容易從某篇之中找到另一篇的結局或前傳;若熟知其所有作品(包括小說),更勢必將產生各種似曾相識之「既視現象」(比如時常蹦跳鑽躺於駱氏文字中那些狗子「小花」、「妞妞」、「馬達」、「阿默」等的形影)。因此駱以軍一週週涓滴累積的結果,也逐漸匯聚成茫茫一片充滿幻覺的大海。
其實論述至此,恐怕仍不免要導向一個必然之結論,這也點出了《我們》一書在剛開始便逕被以小說指稱的緣由。回顧駱以軍過去的幾本小說,基本上正是由相似的邏輯堆疊而成,只是在長篇小說的「成規」之下,駱以軍仍必須盡力在唬爛的故事群裡撐起一個主軸,讀者亦一早就相信小說必然存在此「有機架構」,而將培養抽絲剝繭之整理能力視為自己的重要鍛鍊。但到了「我們」諸書,這個支持所有零件的「脊骨」被倏地抽離,其碎了便像被破壞的3D拼圖一樣散落一地。或者更嚴格地說,這些碎片在一開始就不曾成為一個整體,僅僅只具有被「拼湊」的可能。它們可能是下一部小說的「預告片花」,更可能什麼都不是。
不過,我們更不妨將其看成一種未來文類對讀者的「教育」。眾所皆知,文類只是一個權宜系統,其標準從來就非先驗存在。當駱以軍先前的脫軌創作已經可漸漸被接納為小說時,或許等到某一天,「我們」諸書亦能讓人萌生「原來小說也能這麼寫」的體悟。專欄散文之外型,也許並不必然是小說的對立面,縱使現在看似「不倫不類」,但證諸文學史先例,前景則大可期待。「文類妖孽」之說在文學史上並不少見,而此類貶余通常來自於先前文類系統內的既得利益者,筆者猜想,駱以軍或許會很樂意頂著這個「光環」,然後客氣而謙讓地說:「不不不!其實您才是對的!」
陳巍仁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專案客座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