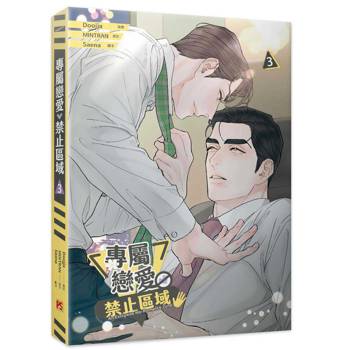暗夜中的男孩
他們在馬翁市外奧卡凡哥河地區露營,頂頭一片通天高的牟本樹(mopane,非洲特有樹種,大象喜食它的葉子)掩護著。往北,近半哩之外,湖泊綿迤而去,在棕色與綠色的樹叢間點綴一抹藍。在這裡,大草原的草又濃又密,是動物的良好屏障,連想看到一隻大象,都得聚精凝神才行;因為植物繁茂,即使大象緩移覓食的巨大灰影,也令人難以察覺。
那營區是半常設性的,五、六個大帳篷依半圓形排列而成。營區屬於一位普拉先生,也就是「雨先生」所有。據信(事實上也經過多次驗證),有他在,就會帶來大地亟須的雨水。普拉先生也樂見這樣的說法永垂不朽。雨代表好運,所以有好事發生,或在慶祝好運到來時,人們都會歡呼:「普拉!普拉!普拉(普拉亦是金錢的單位)!」他臉龐瘦窄,皮膚有如皮革,佈滿了曬斑,一如其他一輩子都生活在非洲豔陽下的白人。只是那點點雀斑跟日斑早已合而為一,一張臉全變成棕色,很像是被放進烤箱的淺色餅乾。
「他慢慢變得跟我們一樣了,」一天晚上,他們圍坐在營火旁,有個人這麼說。「有一天,他會醒過來,會變成茨瓦納人(Motswana,在南非和波札那講班圖語的民族),跟我們一樣的膚色。」
「你要變成茨瓦納人,不是光憑改變皮膚就可以,」另一位說。「一個茨瓦納人,是說裡面是茨瓦納人。祖魯人外表跟我們一樣,但他的裡面永遠都是祖魯人。你也不可能將祖魯人變成茨瓦納人,他們就是不一樣。」
營火旁一片靜寂,大家為這個問題陷入沉思。
「有許多東西會影響你成為什麼樣的人,」一位專事動物追蹤的獵人先開口說話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母親的子宮。你在那裡喝的奶水,決定你是茨瓦納人或祖魯人。茨瓦納奶,茨瓦納小孩;祖魯奶,祖魯小孩。」
「子宮裡是沒有奶水的,」一個較年輕的說:「不是那樣。」
年長那位不悅的瞪著他:
「那你在那九個月都吃什麼來的,聰明先生,科學專家?難不成你吃的是母親的血?你說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年輕人搖搖頭:
「我不確定那時吃的是什麼,但我很確定,人要到生出來才有奶吃。」
年長那位一臉輕蔑:
「你懂什麼!你沒有小孩,不是嗎?那你又知道些什麼?沒有半個小孩的人,居然跟人家高談闊論小孩的事,一副生過一堆孩子的樣子!我可是有五個小孩,五個!」
他舉起五根指頭。
「五個小孩,」他重覆一次:「五個都是喝母親的奶水生下來的。」
眾人陷入沉默。
另一座營火旁邊,有人不是坐在木頭上,而是坐在椅子上。那是普拉先生和他的兩名客戶。他們含糊的談話聲,原本一直不斷飄過來,但現在也沉寂下來。突然,普拉先生站起來。
「那邊有東西,」他說:「可能是狐狼。他們偶爾會走到離火很近的地方。而其他動物通常會保持距離。」
旁邊戴著寬邊軟帽的中年男性客戶,也站起身來,望入暗夜之中。
「如果是美洲豹,會走這麼近嗎?」他問道。
「絕對不會,」普拉先生說:「牠們是很害羞的動物。」
一個坐在帆布折椅上的女士突然轉過臉來。
「那裡確實有東西,」她說:「聽!」
普拉先生放下手裡的馬克杯,召喚他的手下:
「西蒙!莫托比!你們誰拿把手電筒過來給我,要快!」
年輕那位站起來,快步的走向放設備的帳篷。就在要將手電筒拿過去給僱主的途中,他也聽到了聲響。他轉開手電筒的強光,順著半圓形營區,朝黑暗的營外掃瞄。在光線的探照下,樹叢與矮樹的輪廓看來非常古怪,全都變得扁扁的,像是單一的平面。
「這樣不會把牠嚇跑嗎?」女人問道。
「或許吧,」普拉先生說。「不過我們也不想被嚇壞,對不對?」
光線轉動著,再迅速往上,照亮一棵刺棘樹的樹葉,然後往下照到它的根部。就在那裡,他們看到那東西。
「是個小孩!」戴軟帽的男人說:「小孩?在這種地方?」
那小孩四肢匍匐在地,圈在光線中,就像是被車燈照到的動物一樣,僵在那裡,不知所措。
「莫托比,」普拉先生叫道:「去帶那孩子,把他帶過來。」
拿著手電筒的莫托比很快越過草地,手裡的光一直不離那個小孩。當他到達時,那孩子突然飛快的退到身後的暗處,但不知被什麼妨礙到了,摔倒在地。莫托比伸手向前,手電筒卻掉了下來,砸在一塊岩石上,發出砰響,光線當下熄滅。但那時他已抓到那個小孩,他將他舉起來,小孩一直踢來踢去,扭動掙扎。
「別找我打架,小傢伙,」他用波札那語說:「我不會傷害你的,我不會傷害你的。」
那小孩用力一踢,踢中那人的胃。
「別這樣!」他搖晃那個小孩,一手抓著他,另一手用力的朝他的肩膀打下去。「敢踢你老叔,我就給你好看。你不給我小心點,我再打!」
小孩被那一拳震懾住了,不再掙扎,整個人軟趴趴的。
「還有,」莫托比喃喃的說,朝普拉先生的營火走過去:「你有夠臭。」
他將小孩放到地上,放在上面有煤油燈的那張桌子的旁邊。但他仍抓著小孩的手腕,以免他又要逃跑,甚至踢了那些白人。
「原來這就是我們的小狐狼,」普拉先生說,低頭看那孩子。
「他一絲不掛的,」女人說:「身上連一片布也沒有。」
「他幾歲?」一個人問:「最多不會超過六、七歲吧?」
普拉先生將燈拿起來,靠近那孩子,上下照看。小孩的皮膚佈滿小小的傷痕及刮痕,彷彿曾被拖過荊棘樹叢。他腹部塌陷,肋骨根根可數,瘦小的臀部縮皺無肉;一隻腳的腳背上有道傷口劃過,皮肉外翻,中間深黑,四周泛著白色。
小孩抬頭看向亮處,但面對眾人的審視,又退縮回來。
「你是誰?」普拉用波札那語問他:「你從那裡來的?」
小孩只是一味盯著燈,對問題毫無反應。
「你用卡朗加話(屬於班圖語,使用地域在波札那及辛巴威)問他,」普拉先生跟莫托比說:「先試卡朗加話,再試赫雷羅語,他可能是赫雷羅人(西南非洲班圖族的一支,主要居住在納米比亞北部和安哥拉南部,使用赫雷羅語),或者是巴沙瓦人,這些話你都通的。莫托比,看你能不能從他嘴裡問出任何東西。」
莫托比坐到地上,以便與小孩同高。他先用某種語言發問,咬字刻意清晰,不過,得不到回答,於是又換上另一種語言,但小孩還是沉默不語。
「我不覺得這個小孩會說話,」他說:「我想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女人往前走,伸手去碰小孩的肩膀。
「可憐的小東西,」她說:「你看起來像是……」
突然,她大叫一聲,飛快的將手抽回。那小孩咬了她一口。
莫托比一把抓住小孩的右臂,將他拖起來站住,然後往下用力甩他耳光。
「不可以!」他吼道:「壞小孩!」
那女人,氣極了,將莫托比一把推開:
「別打他!」她叫道,「他都嚇壞了,你沒看到嗎?他不是故意要傷害我的,是我不應該去碰他。」
「不能放任小孩子咬人哪,夫人,」莫托比安靜的說:「我們不喜歡那樣。」
女人拿出一方手帕將手包住,有一小片血滲了出來。
「我給你塗一點盤尼西林,」普拉先生說:「人咬過的傷口可能會變嚴重。」
他們低頭看那孩子,這時他已經躺下來,像是準備就寢,只是眼睛仍向上望著他們,觀察著他們。
「這個小孩身上有股怪味,」莫托比說:「普拉先生,你注意到沒有?」
普拉嗅了一下。
「沒錯,」他說:「可能是那個傷口吧,都化膿了。」
「不是,」莫托比說:「我鼻子非常好的,我有聞到傷口的味道,但除此外還有另外一種味道,那種在小孩身上不該會有的味道。」
「是什麼味道?」普拉先生問:「你聞出來了嗎?」
莫托比點點頭:
「是的。那是獅子的味道。沒有別的東西會有那種味道,只有獅子。」
有一會兒,沒人說半句話。然後普拉先生笑了起來:
「用點肥皂跟水,就可以把它洗掉了,」他說。「還有,給他腳上的傷塗點東西。硫磺粉應該會讓它消腫乾燥。」
莫托比輕快的將小孩提起。小孩瞪著他,神情畏縮,但沒有反抗。
「將他洗乾淨,然後留在你的帳篷裡,」普拉先生說:「可別讓他跑了。」
客戶們各自回到營火邊的位置。那個女人與男人交換眼神,但男人只是揚揚眉毛,聳聳肩。
「他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她問普拉先生。
普拉先生正在用一根燒黑的柴枝撥弄營火。
「應該是附近的某個村莊吧,」他說:「最近的那個,往那邊去大概要二十哩。他可能是牧童,迷了路,誤入叢林。這樣的事常有。」
「那他為什麼沒穿衣服?」
他聳聳肩。
「有時牧童身上只圍著一片圍裙。很可能他的圍裙在荊棘叢裡被扯掉了,或是掉在別的地方吧。」
他抬眼看著那女人。
「這樣的事在非洲常常發生的。好多小孩走失了,但最後又出現了,而且毫髮無傷。你該不會是在擔心他吧?」
女人皺眉。
「我當然擔心,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的。就說野獸吧,他很可能就被獅子吃掉了。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是啦,」普拉先生說:「是有這個可能,不過事實上沒有發生嘛。明天我們就帶他去馬翁,把他交給那裡的警察。他們會查出他是從哪裡來的,然後送他回家。」
女人看來若有所思。
「為什麼你的手下說他聞起來像頭獅子?那樣說不是很奇怪嗎?」
普拉笑起來。
「這裡的人呀,什麼古怪的事都說的出來。他們看事情的角度不同。像莫托比那個人,他是一個很棒的追獵者,但你聽他談起動物,那簡直是把牠們當人。他說動物會跟他說話,還說他可以聞出動物的恐懼。他說話就是這種調調,沒什麼啦。」
然後他們靜靜的坐了一會兒。最後女人說她要去睡覺了。大家道過晚安後,普拉先生跟那位男士又在營火旁坐了大約半個鐘頭,兩人沒說上幾句話,只是靜靜看著木頭燒成灰燼,火花飛向夜空。帳篷裡,莫托比直直的橫躺在帳篷門口,這樣,小孩要出去的話,就不可能不吵到他。但那小孩似乎無意逃跑,被放進帳篷後,他馬上就睡著了。莫托比也進入寤寐狀態,半睜著一隻沉重的眼守著小孩。孩子身上蓋著一件薄薄的羊皮斗篷,呼吸深沉。他把他們給他的肉全吃光,貪婪的撕著,吃著;也把他們給他的那一大杯水飲個精光,像動物在水坑喝水那樣,用舔的。他身上還是透著那股奇怪的氣味,莫托比想,一種腐酸味,令他強烈的想到獅子。
可是他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小孩子會聞起來像獅子?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不道德美女:堅強淑女偵探社(3)的圖書 |
 |
不道德美女:堅強淑女偵探社(3) 作者:亞歷山大.梅可.史密斯 / 譯者:柯翠園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4-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不道德美女:堅強淑女偵探社(3)
如何才能直透人心?「堅強淑女偵探社」的社長蘭馬翠姊說:看眼睛,秘書馬庫琪小姐說:看頭顱,而《偵探調查守則》則告訴我們:「不要忽視直覺,直覺是另一種型態的知識。」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練習題,卻也無須困擾,因為,就像這本故事告訴我們的,只要保持仁厚包容的心,即使猜錯了很多事,我們仍可以做對很多事……***本集中,蘭馬翠姊在事業與家庭生活上都遇見難題。偵探社的業務雖然令她覺得十分有成就感,卻不得不面對現實的問題:收支難以平衡,經營難以為繼。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多餘的人事費用--亦即她其實不需要秘書馬庫琪小姐。然而對珍視人才且看重情義的蘭馬翠姊來說,要辭去馬庫琪小姐實在不符合她做人的原則。不過在這問題上,我們又看到蘭馬翠姊如何在現實與原則之間折衝,發揮她的巧智,暫時解決了她的問題。何謂暫時解決了她的問題?因為任何問題也比不上這問題大--梅特康尼先生突然對生活畏縮起來,放棄他鍾愛的修車廠事業,一心只想回鄉下種田……蘭馬翠姊這下也束手無策,只能求助他人。不過在這段沒有梅特康尼先生支持的時期中,蘭馬翠姊仍然堅強的接下一個政府官員委託的下毒案件,牽涉到大家族成員中的矛盾情結;還有一個來路不明、「聞起來像獅子」的小孩需要驗明正身。而最令人驚訝的是馬庫琪小姐的表現,不僅沒讓梅特康尼先生的修車廠關門,還在蘭馬翠姊焦頭爛額之季,自己獨力調查了「美麗正直小姐」選美大賽的內幕……書中兩位女性面對挫折的處理能力令人讚賞,一點小智慧,一點小堅持,改變了視野,也改善了處境。
TOP
章節試閱
暗夜中的男孩他們在馬翁市外奧卡凡哥河地區露營,頂頭一片通天高的牟本樹(mopane,非洲特有樹種,大象喜食它的葉子)掩護著。往北,近半哩之外,湖泊綿迤而去,在棕色與綠色的樹叢間點綴一抹藍。在這裡,大草原的草又濃又密,是動物的良好屏障,連想看到一隻大象,都得聚精凝神才行;因為植物繁茂,即使大象緩移覓食的巨大灰影,也令人難以察覺。那營區是半常設性的,五、六個大帳篷依半圓形排列而成。營區屬於一位普拉先生,也就是「雨先生」所有。據信(事實上也經過多次驗證),有他在,就會帶來大地亟須的雨水。普拉先生也樂見這樣的...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亞歷山大.梅可.史密斯 譯者: 柯翠園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4-01 ISBN/ISSN:9789573260158
- 裝訂方式:平裝
- 商品尺寸:長:18mm \ 寬:148mm \ 高:205mm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