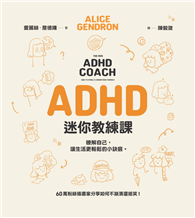下水之前
INTRODUCTION
創意跟魚是一樣的。
如果你想捉小魚,留在淺水即可。但若想捉大魚,就得躍入深淵。
深淵裡的魚更有力,也更純淨。碩大而抽象,且非常美麗。
我在找某種我在意的魚,一種能轉化為電影的魚。但水裡游的魚形形色色。有商業的魚、有運動的魚。萬事萬物都各有其魚。
只要能稱得上事物的東西,都是來自最深的層次。現代物理學把這層次稱為統一場(Unified Field )。你愈是拓展你的意識知覺,你愈是往源頭深處探究,就有可能捉到更大的魚。
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我練了三十三年,對我的電影、繪畫與生活各方面意義至鉅。在我而言,它是我入深淵捉大魚的方法。我想在本書中與你分享這些經驗。
令人窒息的橡皮小丑裝
SUFFOCATING RUBBER CLOWN SUIT
不識自我而獲致快樂真諦,難於把整片天空捲成一小塊布。
《奧義書》(Upanishads )
我開始靜坐的時候,內心充滿焦慮與恐懼。我有一種沮喪憤怒之感。
我常把怒氣發洩在第一任妻子身上。我學習靜坐約兩個星期之後,她過來問我:「怎麼回事?」我沉默了一會兒,我最後開口說:「你是指什麼?」她說:「你的怒氣,它跑哪裡去了?」我甚至沒意會到,它已經被連根拔起了。
我把那種沮喪與憤怒稱為令人窒息的負面能量橡皮小丑裝。它令人窒息,而且橡皮很臭。然而,一旦你開始靜坐,潛入內在,這套小丑裝便開始消解。等到臭味開始散去時,你這才明白它有多麼令人作嘔。等到它消解之際,你便得著自由。
故事裡的沮喪、憤怒與悲傷有其美感,但對電影工作者或藝術工作者來說,則是是毒藥,有如老虎鉗,扼制創造力。你要是受其鉗制的話,恐怕連床都下不了,更別說去體驗創造力與創意的奔流。你必須心志清明才能創作。你必須有辦法捕捉創意。
創意
IDEAS
創意即思緒。當你接收到這思緒時,它所蘊含的東西比你以為它所能夠容納的還多。不過,在最開始的片刻,還只是火光一閃而已。在連環圖畫裡,每當有人想出個點子,就有燈泡發亮。這是電光火石之間的事,就跟現實生活是一樣的。
假如一次就能把一整部電影想清楚的話,那就太棒了。但是對我來說,它是零星而片斷地浮現。第一塊斷片就如同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 )一樣。它是指向其他斷片的一塊拼圖。這塊拼圖充滿希望。
在《藍絲絨》(Blue Velvet)中,是紅唇、綠草,還有那首歌──巴比.雲頓(Bobby Vinton)翻唱的《藍絲絨》。接下來是野地上的一隻耳朵。就只有這樣。
你愛上了第一個念頭,那微不足道的一小塊。而你一旦有這一塊之後,其餘的遲早會出現。
欲望
DESIRE
欲望之於創意,就像釣餌一樣。你釣魚的時候,得要有耐心。你把餌掛到釣鉤上,然後等待。欲望就是把那些魚──那些創意──鉤進來的餌。
美妙的是,你抓到一條你喜愛的魚,就算是一條小魚──一個創意的小碎片──這條魚會招來其他的魚,它們都會上鉤。那麼你就上了軌道。很快就會有愈來愈多的片斷,然後整個全貌便會浮現。但一切皆始於欲望。
意識
CONSCIOUSNESS
透過靜坐,人體會到開闊無際。
開闊無際即是幸福。
狹隘渺小了無幸福。
《奧義書》
小魚浮游水面,但大魚在深處悠游。假如你能夠拓展垂釣的容器──也就是意識──你就能捉到大魚。
事情是這樣: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純淨又充滿生氣的意識汪洋。當你置身超覺靜坐中「超脫」時,便潛入那一片純淨意識的汪洋中。你濺著水花蹬入水中。那裡是至福。你可以隨著至福浮沉。去體驗純淨意識便能活化、拓展純淨意識。它於焉開展並增長。
假使你的意識只有高爾夫球那麼大,那麼你看書的時候,理解力也只會有高爾夫球那麼大;你望向窗外時,知覺也只有高爾夫球那麼大;你早晨醒來時,清醒的程度也只有高爾夫球那麼大;你度日的時候,內在的幸福也只有高爾夫球那麼大。
但你若能拓展意識,使之增長,那麼,你看書的時候,理解會更深刻;你看窗外的時候,知覺會更敏銳;你醒來時,會更清醒;而度日時,會享有更多的內在幸福。
你有辦法在更深的層次捕捉創意。創造力確實奔流不息。它讓人生更像一場妙趣橫生的遊戲。
轉譯創意
TRANSLATING THE IDEA
對我而言,每部影片、每個案子,都是一場實驗。你要如何轉譯創意?你要如何把創意變成電影或椅子?你有這念頭,你能看見它、聽見它、感覺它、瞭解它。好,我打個比方,你開始切一塊木頭,但就是不怎麼對勁。這讓你想得更多,所以你能從這裡下手。現在你正在行動與回應。所以這是一種實驗,讓它感覺起來是對的。
你靜坐時,這種流動會增加。作用與反作用力也會變快。你在這裡有個念頭,然後你會到那裡,然後再到那裡。就像即興舞蹈一樣。你只要跟著它動來動去;你會整個動起來。
這不是裝神弄鬼;也不是那種讓人心情愉快的課程,要你「停下來聞一聞玫瑰花,你的人生會更好。」。它來自內在。它必須發自內在深處,然後不斷增長、增長、再增長。事情就真的變得不一樣了。
因此,超脫、體驗自我──純淨意識──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音樂
MUSIC
我在拍《象人》(The Elephant Man)的時候,有一天在廣播上聽到巴伯(Samuel Barber )的〈弦樂慢板〉(Adagio for Strings)。我愛上這首曲子,想把它用到最後一場戲。我請製作人強納森.桑格(Jonathan Sanger)去找。他買了九張不同的版本。我都聽了之後說道:「不對,這跟我聽到的完全兩樣。」九張全都不對。於是他又出去再買幾張。最後,我聽到普烈文(Andre Previn)的版本,我說:「就是這個。」當然,它演奏的音符跟其他版本是一樣的,差別在於他演奏的「方式」。
音樂必須與畫面相結合,並有所增益。你不能就這麼隨便丟個東西進去,以為這樣就行得通,就算是你最喜歡的音樂也不行。那首曲子可能跟那場戲一點關聯沒有。兩者彼此結合時,你能感覺得到的。東西會跳起來;一種「整體比個體之總合來得大」的事情會發生。
直覺
INTUITION
藉由知曉全知之事而知之。
《奧義書》
生命充滿了抽象,我們唯一能加以理解的方法,就是透過直覺。直覺就是看見解決之道──看見它、認知它。情感與理智攜手前行。這對電影工作者來說至為重要。
你如何讓事情感覺起來對味?這些工具每個人都有:攝影機、影帶、這個世界,還有演員。但是如何把這幾個放在一起,方式各有不同。直覺就是在此切入。
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透過靜坐、潛入自我,直覺會更敏銳、更廣延。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在,都有一片意識的汪洋,各種解決之道盡匯於此。你潛入那片汪洋、那片意識之時,你便將生氣注入其中了。
你並不是為了找尋特定的解決方法而潛入其中,而是為了活化這片意識汪洋。你的直覺開始滋長,然後,你得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你知道什麼時候不對勁,也知道如何把事情弄對。這種能力會日漸發展,事情進行得也會更順利。
排戲
REHEARSAL
排戲的時候,從哪裡開始並不重要。你把演員湊在一起,然後只要挑一場在你心目中足以界定角色特性的戲。你開始排戲,不管進行到哪裡,就先這樣。情況可能有點凌亂。
然後你跟他們談。這些談話聽起來往往言不及義。但對我來說、以及對於我的談話對象來說,確實有其意義。你可以感覺到它有意義。所以等到下次排戲的時候,也許會更接近一點。然後下次又更接近一點。
排戲的時候會有很多交談,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你可以說很多話,有時說些奇怪而愚蠢的字眼。但是你與某些男、女演員發展出小小的密碼。比方說,對我來說,「多一點風」代表「多點神秘感」。這是件怪事。但是慢慢地,你只要動一動手或是說某個字,就會有個人說:「啊、啊,好。」而演員在剛開始排戲沒多久就會跟上,然後盡情發揮。他們的才華都能步上正軌。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跟你共事的人身上。大家說到「排戲」的時候,通常只是指演員而已。但是每個部門、每個工作人員都在排戲。這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攜手合作,朝著相同的方向──由想法指引出來的方向──一同前進。
舉個例子來說,管道具的人可能會找來一堆道具,但是全都不對,但是你說幾件事,然後他說:「噢,好。」然後他再回來,這次更接近你要的。然後你再說幾句,他再回來,這次他把東西全都找對了。這關乎交談、動作與反應。
拍電影就跟各部門做事一樣,因為整部電影要是都能統合在一起,那麼每個元素都至關重要。它的過程都是類似的。你開始著手排戲,無論事情有多麼遙不可及。開始就是了。而你可能會說:「老天爺──我們還差得遠呢。」(當然了,你只能在心裡說!)然後你開始溝通、排戲。然後事情開始愈來愈接近、愈來愈接近。這種事情有點抽象,但每個人都往那裡去。每個人的燈泡在某個時刻都會亮起來。然後他們會說:「我想我明白了。」然後你再排一次。但是你不想揠苗助長,所以你在開拍之前都先不去管它。
你永遠思考著最初的想法──氛圍、角色。透過交談、排練、交談、排練,它很快就會出現。一旦大家都抓到你的意思,他們就能跟你一起往下發揮,他們隨著初念中的東西一同流動。事情就是這麼進行。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大衛‧林區談創意的圖書 |
 |
大衛‧林區談創意 作者:大衛.林區 / 譯者:盧慈穎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2-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5 |
二手中文書 |
$ 198 |
社會人文 |
$ 225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大衛‧林區談創意
台灣最有創意的頭腦★詹宏志、李崗、馮光遠、詹偉雄、鴻鴻、蕭青陽★二話不說,一致推薦★詹宏志:用身體,用知覺,用觀想,用內在的修煉改造與冥想超越,躍入深淵捕捉創意大魚,奇才導演大衛.林區在這本書中示範了一個幽微神秘、光影獨特的創意滋長歷程。★李崗:看這本書很有感覺,「我思故我在」,覺得自已越來越像熊,年紀越大對獨處的需求越強,總想鑽到自已的洞裡,抓住那完全屬於自已的時空。★鴻鴻:真是一本讓我大出意料的書,好像「賴聲川創意學」!在本書中,享譽國際的電影導演大衛.林區敞開一扇鮮少開啟的窗扉,讓我們一窺他身為藝術家的創作方法、獨特的工作風格,並現身說法,分享修練靜坐對創造力的助益。林區將這種經驗形容為「潛入內在」,「捕捉」創意有如捉魚──然後以影像表達為電視、電影或以及他涉入的其他媒材──如繪畫、音樂、設計等。這是第一次林區寫到他致力修練超過三十年的超覺靜坐,以及超覺靜坐對其創作過程所造成的影響。在簡短的章節中,林區解釋他創意的發展過程──從何而來、如何捕捉、以及哪些對於他來說最具有吸引力。他特別仔細討論他如何將他的思考轉化為行動,以及他如何與身旁的其他人互動。最後,他思索自我與周遭的世界──以及這個深切影響他自身創作的「潛入內在」過程,如何能夠直接嘉惠其他人。對於想要更加深入瞭解林區個人觀點的廣大影迷而言,《大衛‧林區談創意》不啻一大啟示。而對於那些思索著如何才能培育自己創造力的讀者來說,本書同樣令人玩味不已。
章節試閱
下水之前INTRODUCTION創意跟魚是一樣的。如果你想捉小魚,留在淺水即可。但若想捉大魚,就得躍入深淵。深淵裡的魚更有力,也更純淨。碩大而抽象,且非常美麗。我在找某種我在意的魚,一種能轉化為電影的魚。但水裡游的魚形形色色。有商業的魚、有運動的魚。萬事萬物都各有其魚。只要能稱得上事物的東西,都是來自最深的層次。現代物理學把這層次稱為統一場(Unified Field )。你愈是拓展你的意識知覺,你愈是往源頭深處探究,就有可能捉到更大的魚。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我練了三十三年,對我的電影、繪畫與生活各方面...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大衛.林區 譯者: 盧慈穎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2-01 ISBN/ISSN:9789573262671
- 裝訂方式:精裝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心理學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