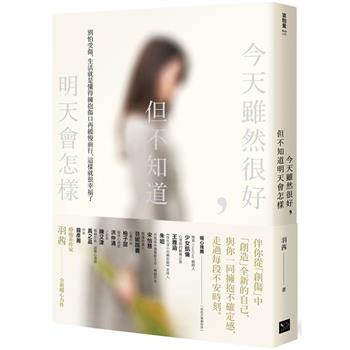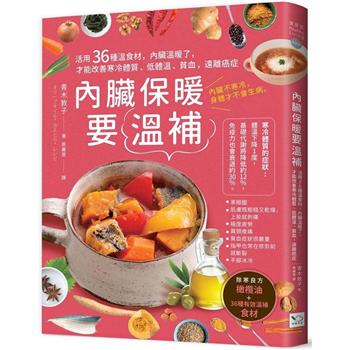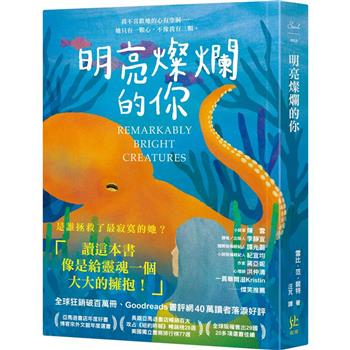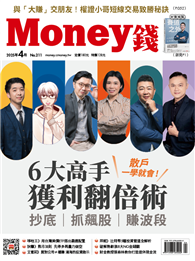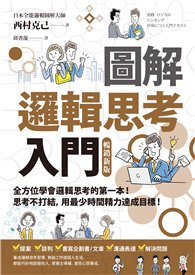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的圖書 |
 |
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 作者:大江健三郎 / 譯者:許金龍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6-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
一位作家自我驗證的反省之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超越自傳的自傳」!半世紀作家人生,最坦誠的告白──大江的創作秘話、戀愛觀,與長子光的父子親情,與同時代作家葛拉斯、薩伊德、米蘭.昆德拉的友情與奮鬥,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的交流,對村上春樹的評價,與安部公房的絕交秘辛等,都在本書中一次道盡……
商品資料
- 作者: 大江健三郎 譯者: 許金龍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6-01 ISBN/ISSN:9789573263180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文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