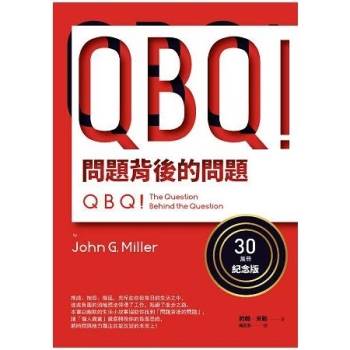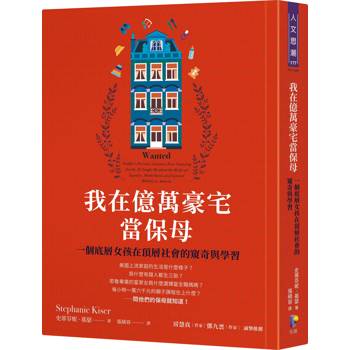導讀
藍茨的「邪惡三部曲」
◎南方朔
有關邪惡及如何面對邪惡的問題,早就已經成了近代新顯學之一。而對此,必須特別感謝兩位德國人,一是德裔美籍的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另一個則是德國作家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 1926-)。
漢娜.鄂蘭的重要,乃是二戰之後她在研究納粹罪行時,發現許多納粹高級幹部,其實並非人們所以為的那麼邪惡。許多納粹皆秉性忠誠,個性正常。他們工作時盡忠職守,而居家生活時則愛護子女,喜歡小動物和音樂藝術,是個典型的好父親與好男人。但這些人卻還是在納粹罪行裡扮演了下令或執行的工作,而他們對自己的罪行並無不安之感,原因即在於他們皆能以「自己只是奉行命令」這樣的認知來合理化所做的一切。「奉行命令」「盡忠職守」也使他們對邪惡的良心防線徹底失守。漢娜?鄂蘭的這些發現,使得她提出了邪惡的共犯概念,它對哲學、政治、心理學、法律,甚至制度及管理研究上,都具有極大的開創性。不久之後,密西根大學的實驗心理學家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 1933-1984)用一組心理的設計試驗證明了這種心理機制的存在。
而漢娜.鄂蘭的研究固有開創之功,但它畢竟只限於學術這個小範圍。與她異曲同工,但更發揮社會影響力的,則無疑要算齊格飛?藍茨的《德語課》、《燈塔船》、《失物招領處》這「邪惡三部曲」了。這三部作品所意圖碰觸的乃是邪惡的形成;面對邪惡時的怯懦只會將其助長;以及面對邪惡不但要有個人的警惕,更要有社會的整體醒覺。「邪惡三部曲」的層次清晰而完整,對人類的心靈守護,的確具有暮鼓晨鐘般的意義。
《德語課》乃是大卷帙的心靈史詩。一個偏遠地區的警察在盡忠職守,奉行命令這個自以為是的「最高價值」下,而成為壓迫兒時玩伴(後來成為著名畫家)的幫凶。這個故事被安排在心靈受創,住進精神病院的兒子身上出現。在文學呈現方式上,乃是罕見的高明設計。邪惡、共犯、自我心靈扭曲和扭曲他人的心靈。一場邪惡的歷史大劫難,其實就是千千萬萬個看似平淡,但其底蘊都是如此令人顫慄不安的小黑暗堆砌而成的。具有擬神聖性的行為,如守紀律、負責任,當它缺乏了對更高內在良心的自省,它和邪惡的距離竟然不會大過一張紙的厚度。《德語課》的經典性,可以和漢娜?鄂蘭的政治共犯經典《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並列。它會被推崇為廿世紀廿或五十重要作品之一,確實一點都沒有溢美。
《德語課》挖掘邪惡底層的那個功能性的共犯問題,它所揭示的,其實是個嚴峻並恐怖的課題。自古以來,人們即視邪惡宛若本體,是撒旦的具體化。但到了現在,人們卻突然察覺到竟然有所謂的集體邪惡,而這種邪惡的起動要素竟然是愛國、負責、盡忠職守這些在本質上並不邪惡的元素。這時候,如何辨識邪惡,察覺邪惡的寄生在不邪惡中,不就成了一個高難度的待答問題嗎?
至於《燈塔船》,雖然沒有時代場景,而只能算是個特定的場合,但敘述的卻是個如何面對邪惡的問題。有一艘海岸外的燈塔船,對船長而言,這已是最後一次出任務。燈塔船的水手們眼見一條小船漂流出海,而船上有人,遂將其營救上了燈塔船。詎料這些被救者都是劫匪。由於船長只想平平安安完成這次任務,而且也認為對劫匪採取任何行動也必將危及船員,因此對劫匪遂只是妥協讓步。由於燈塔船不執行任務,亮起燈號,過往船隻即難免觸礁或誤走航道,於是劫匪也利用船長必須盡責的這個弱點加以威脅。善意換來邪惡,因循妥協鼓勵了邪惡,船長的盡責觀念使他淪為被劫匪脅迫的原因。整部作品裡有一大半都是邪惡在主宰。最後是船員們在付出代價後採取了一致行動,終於制伏了劫匪而得以改變命運。
因此,《燈塔船》說的是另一種看似單純,其實卻同樣讓人手足無措的困境。雖然人們都知道有時必須勇敢,但事實上卻是人活在情境中,被各式各樣的情境所捆綁。船長只想平平安安完成這次燈塔船任務;船長必須把每個船員安全的帶回家;由於劫匪有槍他不能讓船員們冒著與劫匪起衝突的風險;燈塔船必須用燈號幫助過往船隻,如果出任何事而燈號不亮,就會有別的船隻受害,因此他為了別的船隻,只好以不惹事為最高原則,這也就是說,船長被包裹在一層一層的責任心裡,責任心使他因循懦弱,使他向邪惡低頭,但這並未能使他的一名船員免於遇害,也不能使他免於更大的可能傷害(如劫匪可能把他們全都殺掉),最後是全體的一致行動,才脫離被邪惡脅迫的困境。
因此,《燈塔船》說的是另一種因循的心理故事,邪惡之所以形成和出現,是因為我們善良、姑息、懦弱,以及另外許多自認正確的理由如船長必須承擔的責任等,這些品質在平常時候可能是對的,但在面對邪惡時,它卻成了邪惡得以主控情勢的原因。面對邪惡必須有另外一些品質如決斷,如團結等。《燈塔船》以非說教的方式,將如何面對邪惡的問題做了點醒。
至於《失物招領處》,則是更正面的一部覺醒作品了。這部作品指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縱使到了一九八○和九○年代,那種古老的種族歧視和敵視,仍然深深的藏匿在有些人的心靈深處。到了某個特定時刻,就會公開地以羞辱他人或者暴力欺凌他人的方式出現,這是邪惡的遺傳和建制化,這也意謂集體的邪惡無法被消除,但可以在它剛萌芽之際被挫壓。小說裡,社區居民對邪惡施暴的機車光頭幫發出怒吼,這是集體的覺悟,它才是面對集體邪惡的唯一途徑。由《失物招領處》,就讓人想到一九八○年代德國新納粹初興,以排外和攻擊外勞來建立他們的威勢,但法蘭克福的居民無視於這種暴力威脅,而是有個夜晚,舉城居民手持白蠟燭做月光遊行,宣稱要侍衛外來同胞。法蘭克福居民的表現,就文明的角度而言,的確是前無古人的境界。他們不向邪惡與暴力低頭,而是以集體醒覺,集體行動去面對邪惡!齊格飛?藍茨以面對納粹始,以面對新納粹終,把政治邪惡的相關面向做了三個層次的討論。他的「邪惡三部曲」,無疑的已成了廿世紀的文學瑰寶。
邪惡與聖經上所說的七宗死罪有關。邪惡會讓人嫉恨、貪婪、野蠻、殺戮。而在邪惡問題上,威廉?高汀(William G. Golding, 1911-1993)的《蒼蠅王》,所碰觸的則是與齊格飛?藍茨相關但不同的課題。邪惡原本就是人的內在成分,當某些臨界條件因緣湊巧,它就會被喚起。不久前,美國史丹福大學做了一項實驗心理研究,徵求學生自願參加,讓他們分別扮演獄吏和囚犯角色。但很快的,可怕的邪惡如刑求、酷虐、仇恨等即萌發。它嚇壞了計畫主持人,立即喊卡。史丹福大學的監獄實驗雖然緊急停止,但它的重要意義,其實和米爾格蘭的心理實驗互在伯仲間。他們都證明了邪惡的無從逃避!
在今天這個時刻重讀齊格飛?藍茨的「邪惡三部曲」,對台灣其實有著另一重意義,它也提供了我們另外一些思考的空間。今天的台灣正走在漫長的民主化路程中,但台灣的民主化卻很不順利。由於仇恨因素的積累,由於制度有太多縫隙,因此整個台灣政治舞台其實是為奸詐狡猾者而搭建的,再大的貪污腐化都可藉著「只問立場,不管是非」的思考惰性而被移轉;再怎麼惡劣不堪,也可以在必須團結的壓力下而受到支持。嚴重的貪污腐化是邪惡的一種,當這種邪惡在扭曲中被支持、被轉移、被包容,台灣的無是無非也就確定。將來若出現某種臨界情境,更大更嚴重的邪惡並非不可能發生。邪惡的阻擋,必須以國民是是非非的堅持為基礎,而在台灣,這種覺悟還早得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