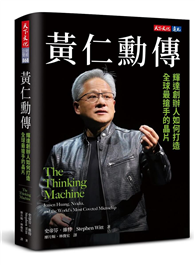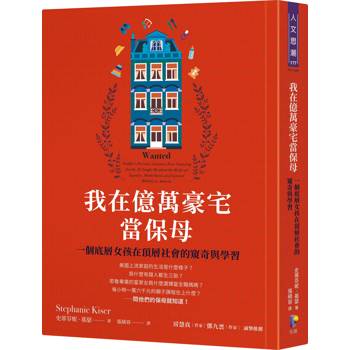後記
去年杪,收到臺灣遠流出版公司鄭祥琳小姐的信,云及要為我編輯一本《梁羽生散文》於臺北出版。於我而言,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可惜我遠適澳洲,老病纏身,隱居於一清靜療養院中,疏食曲肱,遊心於古詩詞中,一應出版事務皆委託香港天地圖書的陳松齡、孫立川二兄隨機處置。但對於這本散文集能在臺灣出版,我是滿懷欣喜之情的。
我與臺灣讀者的結緣,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說來話長,自一九五四年「不慎」寫作武俠小說之後,聽說我的一些作品曾與金庸的作品一起被偷運入臺灣,卻因意識形態的緣故,早被列入「禁書」之列。這種狀況直到一九八七年年底方有改觀,是年十二月,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與我正式簽約。一九八八年元月,臺灣當局正式宣布對大陸出版物「開禁」,《中央日報》副刊於元月二日即開始連載我的武俠小說《還劍奇情錄》,而且特請臺靜農先生題字。臺先生不僅是著名的書法家與古典文學家,還曾是出色的小說家,他是我心儀已久的文壇前輩。七個月之後,我首次訪問臺灣,參加《中央日報》副刊主辦的「武俠小說算不算文學」座談會,記得與會者有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孫同勛、臺大外文系教授林耀福、武俠小說研究家葉洪生、陳曉林、小說家黃凡等。訪臺時,我曾專程去「龍坡丈室」拜候臺靜農先生,向他請益,今次文集中收有一張我在他的家中作客的照片,而今臺先生已作古,睹此照片,不免令人唏噓。而此前聽說臺北的文學界、戲劇界於一月十八日已開過一個名為「解禁之後的文學與戲劇」研討會,曾「以梁羽生作品集為例」說明問題,詩人?弦先生就在會上語出驚人:「由梁羽生作品集的問世,可見已到了『武俠小說研究學術化的時候』。」是耶非耶,已成舊話。
此後,《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分別刊載《塞外奇俠傳》和《武林天驕》,《民生報》則刊載《飛鳳潛龍》,《自由日報》又開始連載《白?魔女》。臺灣的電視也將《雲海玉弓緣》改編成「天山英雄傳」的電視片集。同年年底,風雲時代版的《梁羽生武俠小說全集》亦已全部出齊,交由臺灣遠景出版社發行。
一九八八年,可謂是我的人生中的「臺灣年」。
半生中寫了三十五部武俠小說,耗我三十年心血。回想初涉小說界,我在第一部小說《龍虎鬥京華》的開篇填了一首詞,調寄〈踏莎行〉,首句:「弱水萍飄,蓮台葉聚,卅年心事憑誰訴?」不料,此語竟成意外之預言,一寫就寫了三十年。文名所累,「梁羽生」以「武俠小說家」而鳴於世。其實,我還有許多自視為正職的副業,譬如對於「聯話」、撰聯的興趣;對於「棋話」、對弈的喜好;對於「史話」、掌故的偏愛,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所謂,暗念平生,無非一書生也。有武俠小說研究家曾批評我創作時有「慵懶」之表現,我對於他的批評全盤接受,慚愧慚愧,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確實不好看,他是看出了我的毛病,心猿意馬,不能專注於此也。所以,一千多萬字的武俠小說之外,我也不知還寫了多少「散得可以」的散文文字了。這本集子中所收的散文,主要選自《三劍樓隨筆》(金庸、陳凡兩兄與我的合集)、《筆不花》及《筆花六照》三書之中,按照錢鍾書先生的說法,都是「舊時貨色」,明日黃花,不值一哂。蒙遠流出版公司不棄,將這些散文第一次結集,奉獻給臺灣的讀者,權充我與臺灣的第二次文字結緣,可以與我所親愛的臺灣讀者分享我的一點「雜學」之見,何幸之有耶?!
龔自珍有一首〈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其一云:「少小無端愛令名,也無學術誤蒼生。白雲一笑懶如此,忽遇天風吹便行。」這首詩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引用過,彼時是八○年代初,我正想「封筆」,不再寫武俠小說了。而今重睹這些舊文,使我又想起龔自珍在這組〈雜詩〉中的「其三」那首詩:「情多處處有悲歡,何必滄桑始浩嘆。昨過城西曬書地,蠹魚無數訊平安。」每一位作者,在年暮之際,對著曩昔寫下的文字,多少也有同樣的感觸吧!
臺灣留給我許多美好的憶念,太魯閣的旖旎風光,士林夜市的美味小食,而更令人難忘的是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情懷。我記起首赴臺灣時,在《聯合報》為我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我與臺灣的「聯聖」張佛千先生邂逅,一談起「對聯」,我們之間馬上有了許多共同語言。他賜我一副親筆書寫的嵌名聯,聯曰:
羽客傳奇,萬紙入勝;
生公說法,千石通靈。
並有題序云:「羽生先生為武俠說部千百萬言,天下傳誦。奇肆詭變,引人入勝,竊慕久矣。頃喜其自港來臺,得接杯酒之歡,又讀其近作談聯之文中,引余為孫立人將軍作鄭成功祠長聯,喜製小聯為贈。借博方家一粲耳。」過獎之譽,實不敢當。而今張佛老已往生多年,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歷歷在目。他曾有自題聯:「直以友朋為性命,多從翰墨結因緣。」引為美談。而星雲大師與我也結文字緣,臺灣佛光山創辦的報紙《人間》上曾連載我的武俠小說,這一切都因我的這本集子而勾起思緒的漪漣。
末了,我在此要多謝為本書而做了大量工作的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副主編鄭祥琳小姐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副總編孫立川兄。並藉此向臺灣的文友們與讀者們致意。
梁羽生
2008年7月
(本文出自2008年8月遠流出版之《梁羽生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