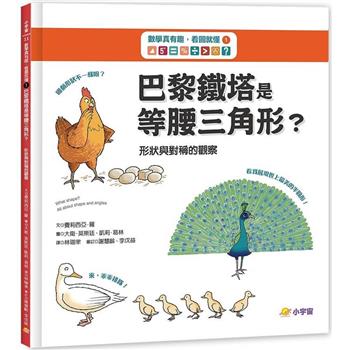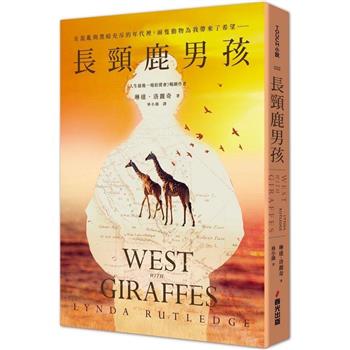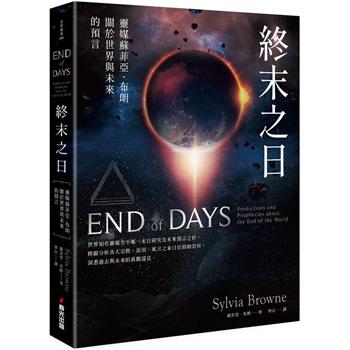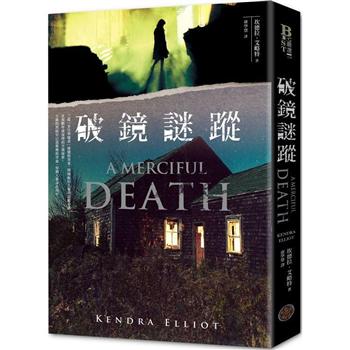我發現自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非要和別人談談,透露一點線索,一些暗示。這種遊戲和朋友玩就太危險了,我想我需要的是,利用一個可以控制得住的宣洩管道來說我要說的話,而你,中選了……兩個生命找不到出口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發出了救援訊息,在冥冥之中默默地交會。一位身分不明的陌生人,不斷地寄出匿名信,向中約克的刑事主任狄埃爾透露生存的悲哀。但狄埃爾無暇他顧,因為他見到一位金髮裸女,活生生在他眼前遭到射殺!他亟欲逮捕兇手,但各種證據卻顯示那只是一樁意外事件;他堅持追查,卻發覺相關人等陸續失蹤,自己的手下甚至受到襲擊--條件對他越加不利,終於他被勒令停止調查。就在不得不放手的那一刻,精於人性的他,在洋洋得意的某人身上看到了某樣訊息,恍然大悟後終於水到渠成,案情直轉急下……被冷落的匿名信此時也終於露出線索,在對自大專橫的狄埃爾做出抗議及協助後,深深告別。名家推薦:不管是案情的設計或辛辣幽默的對白,都顯現出作者意在言外的機智;尤其是令人驚訝的收尾,更讓你闔上最後一頁後,才突然意會到它不著痕跡、處處鋪陳的高明手法。--李家同(前暨南大學校長)這系列有趣的不只是曲折懸疑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書裡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其中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位胖胖的、言詞有些粗魯、但行事卻潛藏著無限柔情的狄埃爾刑事主任,他思維的形成,令人激賞,我真想多聽一`些他的故事。--曾志朗(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把一個脾氣暴燥的刑事主任、一個細膩的探長、一個很古意的同性戀探員組合在一起,配上不斷出現的金髮長腿艷屍、不知誰寄來的匿名信跑出來瞎攪和,小說勢必得有非常精密的布局,和極端不尋常的發展。希爾用他幽默的幹譙對白,慢慢引領讀者去蒐尋凶手,閱讀的過程中當然充滿愉悅。--張國立(作家,時報周刊社長)讀雷金納.希爾的小說,最叫人拍案讚嘆的,是那一個個深具個性的人物、機鋒處處的對話,巧思滿溢。希爾的布局功力更是一絕,千絲萬縷中自在地引導讀者穿梭勾連,聚攏後浮現的真相成功營造出意外性,餘韻無窮,無愧大師之作!--冬陽(推理評論者)每次閱讀雷金納.希爾的作品,總有一種欲罷不能、暢快淋漓的爽冽感。尤其是代表作《骸骨與沉默》僅以一樁極為單純的女子槍殺案為始,卻在希爾神乎其技的精采描述下,各種機鋒、驚奇、喟嘆、絕倒層出不窮,情節開展有鋪天蓋地之勢,解謎擒兇有石破天驚之局,不愧是當代英國解謎推理的超級經典!--既晴(恐怖推理小說作家)最道地的英式幽默,不可錯過的當代解謎推理極品。您尋覓已久的古典解謎推理大師,就是雷金納‧希爾。--紗卡(推理評論者)狄埃爾這個死胖子真是合我的口味。他這次被女人設計還栽了觔斗,只能獨排眾議以還自己清白。他與部下的互動既寫實又生活,讓我們讀小說好像在聽朋友話長短,然後視四五百頁的厚書如無物,一口氣就把書讀到最後。--張東君(推理評論者)仿古希臘劇的詠唱式開場,以戲中戲形式貫穿謀殺宿命,再點綴骸骨黮闇的沉默控訴,希爾最具形式主義與風格化的傑作!--黃羅(推理評論者)
章節試閱
狄埃爾先生大鑒:
你不認識我。你怎麼會認識我呢?有時候連我都覺得不認識自己。耶誕節前,我正經過市場的時候,突然停了下來。別人撞在我身上,可是那不算什麼。你知道,我突然又變回十二歲,正走過麥爾洛斯大教堂附近的一塊空地,小心翼翼地捧著一罐剛從農家拿來的牛奶。我們家的帳篷和車子就在前面,我看見我父親正面對著後照鏡刮鬍子,我母親則彎著身體在爐灶上烹煮食物。我聞到煎鹹肉的味道,它聞起來好香,我想著它美妙的滋味,腳步加快了起來。可是接下來,我的腳趾頭卡到草叢,跌了跤,把牛奶潑得到處都是。我覺得世界末日來了,可是他們只是大笑,開了個玩笑,然後就遞給我滿滿一盤的煎鹹肉、蛋、馬鈴薯和磨菇,彷彿是我打翻了牛奶,他們還更加愛我了哩!
那天我就像個傻瓜似地站著,擋在人行道上。在內心裡,我又只有十二歲,感到有人愛著我,保護著我。為什麼呢?
因為我正經過卡夫市場,抽風機把煎鹹肉的香味吹送進早晨清涼的空氣中。只要一個味道,就能把我轉換到那樣遙遠的時空裡,我又怎麼能說我認識我自己呢?
可是我認識你。不對,在我寫下剛才那件事之後,這話說來太狂傲了。我的意思是說,我請人把你指給我看過,我也聽過別人怎麼說你。其中有很多話——事實上是大部份的話,都不怎麼好聽。不過這不是一封罵你的信,所以我不想重覆那些話來冒犯你。然而即使是把你罵得最凶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你的工作能力很棒,從不畏懼找出事情的真相。喔,還有你不會容忍愚蠢的人。
嗯,我這個愚蠢的人,你倒不必多加容忍。因為,我之所以寫信給你的原因是:我打算自我了結。
我並不是要馬上動手,不過,就快了,一定會在接下來的十二個月以內進行。這也是一種新年新決定。可是在這段時間裡,我想要找個人談談。然而任何和我有私交的朋友都不適合,醫生、心理醫師、所有專業的諮商人士也不適合。你知道,這不是在求救,我已經下定了決心,問題只剩要選定一個日子而已。但是我發現自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非要和別人談談,透露一點線索,一些暗示。這種遊戲和朋友玩就太危險了,我想我需要的是,利用一個可以控制得住的宣洩管道來說我要說的話,而你中選了。
很抱歉,對任何人來說,這都是個很重的負擔,可是由別人談到你時所提到的特質來看,我給你的信會像其他任何一個案子一樣,也許會讓你覺得煩心,卻絕不會為此而睡不著覺。
我希望我選擇你是對的。我最不願意做的事就是給陌生人帶來痛苦——特別是,我也知道我最不願意做的,就是給我的朋友帶來痛苦。祝
新年快樂!
(一月一日)
1
「我還是不懂她為什麼要開槍自殺。」彼德•巴仕可頑固地說。
「因為她煩悶無聊,因為她被困住了。」艾莉•巴仕可說。
「可是一般人不會幹這種事。」巴仕可露出約克郡人的誇張表情。
艾莉看起來好像要爭辯,於是他露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樣說道:
「只要有鬼,我就看得出來,小子。」
她這才看出他是在模仿、取笑他刑事部的上司安迪•狄埃爾。她露出了微笑,巴仕可也報以一笑。
「你們兩個看來很快樂嘛,」宗愛琳拿著一瓶新開的酒走了過來。「這就奇怪了,因為你們可是花了大錢來受罪呀。」
「哦,是滿受罪的。不過彼德最不準的直覺告訴他說,女主角是被謀殺的。」
「你的看法真正確,親愛的彼德。」愛琳說著把她七十五吋的美體移到躺椅上他的身邊。「這正是我想要表現的。我把你的酒杯加滿吧。」
彼德環顧了一下台上,金寶戲院的工作人員似乎都準備回去了,他站起身,說道:
「我想我們該準備回……」
可是宗愛琳又把他拉坐下來。
「忙什麼?」
「不忙,」他說:「我還沒回去忙呢。」
「你跛得很漂亮,」她說:「我好喜歡這根枴杖。」
「這根枴杖讓他覺得很尷尬。」艾莉說著在他另外一邊坐了下來,他挺高興被夾在中間。「我猜他認為這玩意有損他的大男人形象。」
「彼德,寶貝!」宗愛琳把手放在他膝蓋上,抬眼正視著他說:「枴杖不過就是男人性器官的象徵吧?也許你想要換根大點的?我會到我們的道具間找一找。想想那些瘋狂的跛子,戀母弒父的奧迪帕斯王,他根是個操他媽的傢伙;還有詩人拜倫,老天,就連他的親姐妹也不安全……」
「可憐的彼德不但是孤兒,還是獨子。」艾莉插嘴道。
「啊,媽的。彼德,抱歉,我都不曉得。還是有很多不跟自己家人糾纏的人,比方說,魔鬼;他就是個跛子。」
在此之前,彼德•巴仕可始終很適然地承受這種拙劣的戲弄,能置身在他所愛的艾莉和他想要的宗愛琳之間,他心甘情願付出這種代價;然而,現在他才知道他被出賣了。
他正打算起身,可是宗愛琳已經站了起來,臉上閃著「這下好戲上場囉」的光輝。
「魔鬼!」她興奮地說:「這個主意真好。彼德,親愛的,讓我看看你的側面。好……極了,加上跛腳,太、太完美了!艾莉,你最了解他了,他可以演嗎?他可以演吧?」
「他的確具有不少魔鬼的特性。」艾莉承認說。
這實在有點過分了。有根枴杖在手上也有好處,他拿枴杖用力敲了敲面前的茶几。這樣做他一點也不會良心不安,因為那張茶几原來是他的。宗愛琳蒐集道具就像瑪麗女王蒐藏骨董一樣,拚命誇讚到你只好送她當禮物——可是她休想把他當禮物!
這都怪艾莉,不過更該怪他自己。他忘記了那條黃金定律——愛琳的任何一個朋友都是有罪的,除非能證明其清白;說不定證明之後還不行。當初這位新任命的市民劇場總監宣稱她要製作一齣具有社會意義的戲劇時,他的疑心就和艾莉的熱心一樣強烈。可是她的美豔和魅力卻很快地就將他征服了。
但她最新的企畫案瞄準了上帝和財神爺,這才真讓他心生不祥之兆。
「不行!」他叫道:「我不幹!」
兩個女人忍不住感到有趣地對望了一眼。
「不幹什麼呀,親愛的?」宗愛琳一派天真無邪地問道。
現在是連最愛搞曖昧的人也要弄清楚狀況的時候了。
他慢慢地說道:
「我不會在你的神蹟劇裡演魔鬼,現在不答應,將來也不答應,休想!」
他仔細思量了一下自己的話,聽起來好像不怎麼有力。
兩個女人吃驚地對望著。
「噢,彼德,當然不會要你演啦!你是怎麼想的?」宗愛琳瞪大了眼睛,就像以為堪薩斯州消失了似的吃驚。
「彼德,我的天,你是怎麼了?」艾莉用為人妻者在好友面前才會顯露的怒氣逼問道。
這時候該繼續堅持立場。他聽到自己說:
「你們在講我的跛腳,又說魔鬼的腳是跛的,又說我適合那個角色……」
「開玩笑的啦,彼德。你把我當什麼呀?媽的,運氣好的話,等上戲的時候,你早就不跛了。我是說,你明天就要回去上班了,不是嗎?你以為我真會去欺負一個手腳不方便的人嗎?再說,你這人太好、太親切了,我心目中的魔鬼人選要看起來就像魔鬼那樣驕傲而討厭,完全不是你這一型的!」
他雖然還不確定問題到底在哪裡,卻覺得自己好像越陷越深了。不過這都沒有關係,他需要完全弄清楚的是,這絕對不是一個陷阱。
「那你現在是絕對不會、將來也一定不能要我在這齣或是你任何一齣戲裡演出囉?」
「彼德,我發誓,誠心誠意地發誓。」
她很嚴肅地把手放在心口發了誓,然後看到他的視線所及,便挑逗地捏了下自己的左乳,笑了起來。
「呃,彼德,事情是這樣的,我寄了張請柬給你的上司,就是鼎鼎大名的刑事主任狄埃爾。也是該讓本城的兩大巨頭會面的時候了。只不過他還沒回覆。」
「他不太喜歡正式的社交場合。」巴仕可說。
他知道負責收發狄埃爾信件的警員曾接獲嚴格的指令,要他們把那種看起來是無聊的公共聚會或自以為是藝術活動的請帖或邀請函,全丟進一個大型塑膠垃圾袋裡。
「呃,好吧。可是我真的希望他能到場。彼德,你能不能運用你的影響力讓他來呢?」
這事一定有鬼。不可能有人會急於找狄埃爾參加一個有酒可喝的酒會;這簡直就跟農夫要把狐狸請進他的雞舍裡一樣。
「為什麼呢?」巴仕可說,一面想著也許他該聰明點假裝昏倒讓人抬出去,而不要再繼續追問這件事。「你為什麼要找狄埃爾來?不單單是因為社交禮貌吧?」
「你實在是太機伶了,我搞不過你,彼德。」宗愛琳很佩服地說:「你說得一點也沒錯。事情是這樣的,我想要看看他能不能演一角。你知道,親愛的,我聽到過不少關於他的事,不管是你說的,艾莉說的,還是其他人說的,都讓我覺得安迪•狄埃爾很可能是扮演上帝的不二人選!」
巴仕可突然覺得他一定得坐下來,否則的話,他真的要昏過去了。
大約就在那邊宣告他即將被神化的同時,刑事主任安德魯•狄埃爾正在家中朝一個桶子裡嘔吐。
在一陣陣的作嘔之間,他腦子裡開始追查嘔吐的原因。他逐一追究,:在「黑公牛」酒館裡灌下的六品脫啤酒加六杯雙份威士忌不該予以追究;在「特區專業紳士俱樂部」吞進去的「洞中蟾蜍」、「麻子警探」還有一整瓶薄酒萊也不獲起訴;最後判決下來,是他被搭配乳酪的酸漬洋蔥給嗝到時一時失察所灌下的那杯礦泉水受到指控並宣判有罪。
極可能是法國來的礦泉水。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他就是一時失去判斷力了。法國人老吹牛說他們瓶裝的是天然礦泉水,未經人工處理,可是這個國家「處理」過的水連健康的馬喝了都會吃不消。
噁心的感覺似乎止住了,他這才發現桶子原來不是空的,除非他在俱樂部裡還吃了兩雙襪子和一件網眼背心。他抬起眼來環顧一下廚房。他剛才沒有開燈,但即使是在黑暗裡,也看得出這裡急需重新裝潢。這棟房子是他結婚時搬進來的,後來就再也沒時間和精力搬出去。所以當他的眼光轉到沒有掛上窗簾的窗口時,他所看到的仍是他極其熟悉的景物——一個小後院。即使月光也不能讓那裡美化,院外是一堵需要粉刷的圍牆,還有一扇需要油漆的木門通往一條後巷。巷子的一邊是狄埃爾所住的這條街,另一邊則是另外一條小街,上面都有著相似的房舍後門,而那些房子的煙逗都矗進鐵灰色的夜空。
只不過今晚還有些不一樣的東西可看。在他房子正後方的那棟屋子裡的一間臥室,亮起了燈。過了一下,窗簾被拉到一邊,一個裸體的女子站在一方金黃色的燈光裡。狄埃爾饒有興趣地看著,如果這是幻覺的話,那麼那些法國佬可能真在耍什麼陰謀。然後,就好像為了要證實她這個人的真實性,那女子推開了窗子,將身子俯靠進夜色裡,深深呼吸著冬日的空氣,讓她那對雖小卻絕不容忽視的乳房極具娛樂性地起伏不定。
在狄埃爾看來,她既然已經這麼客氣地移開了一層玻璃的屏障,他至少也可以把另一層給消除掉。
他很快地走到後門口,輕輕地將門拉開,走進屋外的黑夜裡。可是他這樣的快速卻是白費心機。他的動作使魔法為之消失,那美麗的景象不見了。
「我真他媽的活該,」狄埃爾埋怨自己道:「居然像個從來沒見過奶子的小孩一樣。」
他正轉身準備回他的屋子裡,卻有什麼使得他又立刻轉回身來。在那金黃色的一方銀幕上,軟調的情色電影突然變成了純動作片,有個男人在動著,手裡拿著什麼東西;另外還有一個男人……然後是一聲爆裂的聲音,就像音樂會裡演奏到最弱音的樂句時觀眾壓抑太久的咳嗽聲。狄埃爾想也沒多想,提腳就衝過去,一路上因為碰撞到一堆又一堆的雜物而越來越光火,話也越罵越粗。
他後院的門沒有鎖,但那棟房子後院的門卻是鎖上的,可是他還是像門沒鎖一樣就撞了進去。他現在因為靠得太近而沒法往上看到二樓的房間;而就在他朝廚房的門衝過去的時候,他才想到,說不定會正好碰上一個同樣急於要衝出來的槍手。可是由另一方面想來,屋子裡說不定還有尚未遭到槍擊的人,會因為他的趕到而能安然脫身。其實這種反覆考量也是很抽象的,就好像把一顆燒夷彈扔在德勒斯登城上空時,才開始考慮這樣的轟炸是不是人道一樣。
廚房的門被他一推就開了。他假設房子的格局和他自己的房子相似,事實上果然如此,因此他不必撞倒牆壁就能直接跑過前廳,上了樓梯。那裡仍然像空無一人似地沒有聲音、沒有動靜。他準備衝過去的那張門微微開著,燈光透出來照在走廊上。現在他終於慢了下來。如果裡面有暴力行為的響動,他就會猛衝進去,可是看來沒必要故意刺激對方。
他輕輕地敲了敲門,將門整個推開。
房間裡有三個人。其中之一是個三十多歲的高個子男人,穿了一件前胸口袋上繡了徽章的深藍色上裝,正站在窗口,右手握著一把還在冒煙的左輪手槍,槍口則指著一個比較年輕的男子;後者穿著一件黑色毛衣,蹲在牆邊,兩手緊摀著他那張蒼白而嚇壞了的臉;同樣在場的還有一個裸女,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狄埃爾對後面兩個人都沒怎麼注意。那個年輕男子看來似乎兩條腿不管用了,而那女人更顯然是所有的東西都不管用了……
狄埃爾先生大鑒:你不認識我。你怎麼會認識我呢?有時候連我都覺得不認識自己。耶誕節前,我正經過市場的時候,突然停了下來。別人撞在我身上,可是那不算什麼。你知道,我突然又變回十二歲,正走過麥爾洛斯大教堂附近的一塊空地,小心翼翼地捧著一罐剛從農家拿來的牛奶。我們家的帳篷和車子就在前面,我看見我父親正面對著後照鏡刮鬍子,我母親則彎著身體在爐灶上烹煮食物。我聞到煎鹹肉的味道,它聞起來好香,我想著它美妙的滋味,腳步加快了起來。可是接下來,我的腳趾頭卡到草叢,跌了跤,把牛奶潑得到處都是。我覺得世界末日來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