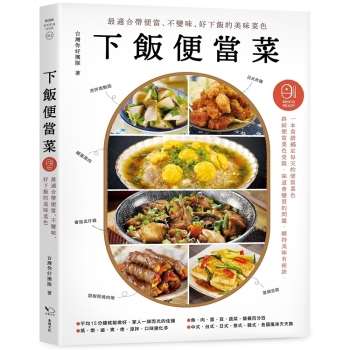推薦導讀
流氓社會學家的告解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當凡卡德希還是社會學研究生時,他誤打誤撞走進芝加哥大學附近的黑人國宅區。他的第一印象是:「高樓緊緊挨在一起,卻和城市徹底隔離,彷彿身上帶著劇毒。」身為一個印度裔、美國加州長大的中產階級子弟,他懷抱著天真的熱情,想要研究黑人的貧窮問題,沒想到竟遇上一個賣毒品的黑幫組織。黑幫老大皆踢嘲笑他手上的問卷:「你別拿著這麼蠢的狗屁問題四處問人,想了解我們,你最好和他們往來,搞清楚他們在做什麼。」就這樣,凡卡德希開始了與黑幫成員及社區居民近十年的相處。
凡卡德希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知名教授,根據黑人國宅的系列研究,他發表了《美國國宅計畫:現代貧民窟的興衰》(American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 Modern Ghetto)以及《兩本帳:都市窮人的地下經濟》(Off the Books: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of the Urban Poor)兩本學術專書。二○○八年,他再出版《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書中沒有艱澀的術語、抽象的論證,他用生動的文字、誠實的語言,映現貧民社區裡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以及他這個外來者的角色與互動。這本書比小說更好看,比紀錄片更真切,翻開首頁便讓人欲罷不能。
底層階級(underclass)的貧窮為何發生、如何延續,是美國社會學家長期辯論的議題。「貧窮文化」的說法曾經主導了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的思維,這樣的看法把貧窮視為一種「有毒」的次文化,促使下一代遺傳與複製了類似的價值與生活方式。美國的黑人家庭,由於非婚生子女的普遍現象,形成青少女母親與家中年長女性共同撫養小孩的家庭型態,這樣的母權獨大、父親缺席的家庭,被認為容易造成下一代黑人男性的認同失衡與適應失調。這些看法是一種把社會問題病理化的論述方式,把底層階級的生活邏輯視為不變的劣根性,而不是社會結構的歷史產物。
凡卡德希的研究不然,他走進了貧民社區,與居民共同生活,體察生活在都市貧窮與社會邊緣的人們面臨怎樣的結構限制,以及他們發展出來的生存策略。
書中的泰勒國宅接近台灣的「平宅」,低收入戶才有資格承租。國宅興建的原意是解決窮人的居住問題,也有將窮人集中管理的社會控制功能,然而這樣的社區往往無法幫助他們「脫貧」,反而將之孤立於主流社會之外,有如都市裡的貧窮孤島,也容易成為貪污與犯罪的溫床。
國宅裡有兩種幫派,一種是皆踢的黑幫,他們不只販賣毒品,也提供獻金與政客和教堂合作,甚至鼓吹社區選民投票,藉此維護有利於販毒生意的社會秩序。另一種幫派是握有合法權力的警察,其中的濫權者向黑幫索取保護費,以各種名義進行騷擾與施暴;理應扮演社區守護者的公部門,卻往往成為控制弱勢居民的白道。又如擔任大樓代表的貝禮小姐,利用住宅管理局提供的福利資源,或與幫派合作、或賄賂公務員,以鞏固其分配的權力與個人的權威。
一般人常批評平宅居民懶惰不工作、學壞搞幫派。其實,加入幫派常常是黑人男性在主流勞動市場中遭受歧視與挫折後的退路。此外,社區居民其實有許多帳面上看不見的工作,他們想盡辦法隱瞞收入,以免喪失國宅租約或其他社會福利補助。
混亂的社區表象下,其實有著相對穩定的道德經濟。泰勒國宅裡的許多家庭組成了一個互助網,婦女彼此分享資源以維持生存。她們也發展出諸多求生法則,如透過性與身體交換資源,她們和官員上床交換房租寬免,和社福人員上床交換協助,和警察上床讓牢裡親人好過一點。
凡卡德希的研究,採取的是所謂民族誌(ethnography)的方法,此詞顧名思義是關於人的書寫,民族誌的研究者透過進駐「田野」,與研究對象長期相處、深入互動,深刻體察而能豐富描寫日常生活的紋理。
然而,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在近三十年來歷經許多反省與批判,尤其是研究過程中涉及的權力關係與倫理議題。貌似客觀中立的研究者,其實必然是從特定的社會位置與主觀經驗出發,更不免對田野對象有情感甚至慾望的涉入;全知全能的詮釋權威,其實粉飾了研究者與當事人之間的權力不平等。人類學家於是開創了一種「告解民族誌」(confessional ethnography)的寫作風格,其中,研究者不再隱而未現,反而成為反思敘事的主軸。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便是凡卡德希的民族誌告解。
民族誌研究中往往有所謂的「關鍵報導人」(key informant),在這個研究中,無疑就是黑幫老大皆踢。他讀過大學,對於學術略知一二,也許正因為如此,他願意把凡卡德希帶進黑幫田野。皆踢不時嘲諷蛋頭學者的無用,還把這個毛頭研究生戲稱為「教授」,然而面對黑幫人生的起落甚至生死的無常,皆踢也喜歡對人誇耀說,凡卡德希將會為他作傳,留名後世。
民族誌研究者常會不自覺地陷入田野中的權力蛛網。凡卡德希對於國宅的居民做了許多工作情況的深入訪談,他喜孜孜地與皆踢和貝禮小姐分享這些研究資料,結果兩位有力人士卻運用這些資料向居民抽稅。社區居民後來嚴厲地指責他:「你幫你的教授挖到東西,整個人爽歪了,你心裡只顧著自己的事!」
為了紓解「剝削」國宅民眾、「強取豪奪」弱勢經驗的內心責難,凡卡德希想盡辦法回饋研究對象。他開課替社區裡的青少年(多為幫派成員)補習,課堂卻陷入販毒、賭博、玩槍的混亂場面。他熱心替單親媽媽開授寫作班,讓她們以文字抒發心情,卻被民眾懷疑是找她們上床。
凡卡德希在研究過程中也經歷其他的道德困局:當黑幫弟兄對社區民眾施以暴力時,他應該袖手旁觀還是挺身而出?若他得知黑幫的某項槍擊計畫會傷害他人時,他是否有道德或法律的責任舉報?當他被法庭傳喚作證時,是否可以用保護報導人的理由,拒絕出示他的田野筆記?
進入田野並不容易,離開田野往往更加困難,因為研究者的腳踝上纏繞著田野對象的情感連帶與期待壓力。凡卡德希在結束研究工作後,皆踢強烈建議他搬去東岸後繼續黑幫的比較研究,甚至熱心地提供紐約和波士頓黑幫的聯絡資訊。凡卡德希拒絕了,皆踢的失望反應讓他無法轉身輕鬆離去,假裝沒看到腳下的權力鴻溝。
他在書裡這樣說:「我忽然明白自己這些年來到底做了什麼:我來、我看、我拿走......我可以選擇何時離開國宅,他們不能。等我結束研究貧窮,他們還要繼續貧窮活著,很久很久。」
回到台灣,我們面對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平等與貧窮問題:金融海嘯讓更多人陷入失業與彈性就業的險灘,燒炭自殺的個案暴露出社會安全網的殘破,河岸的原住民部落被逼著流離失所,新移民仍身陷歧視與排除的角落。這些議題都在召喚著社會學家走出圖書館,把手弄髒。當然,一旦走進田野,研究者也無從逃避倫理的困局,必須時時刻刻反思研究者的現身對於當事人生活的介入與影響。民族誌的告解,雖不能直接改變現狀,但能誠實地面對滲透於自身以及周遭的權力關係,而這正是改變的一個起點。
推薦序
深入虎穴,發掘真相
杜伯納(Stephen J. Dubner,《蘋果橘子經濟學》共同作者)
我認為凡卡德希生來就有兩點不正常:好奇心比誰都強,膽子比誰都大。
不然你要怎麼解釋他的行為?那年秋天,他和無數學生一樣走進研究所,被指導教授派去做研究,讓他一腳踏入芝加哥的泰勒國宅(Robert Taylor Homes),美國最恐怖的貧民窟,置身於一群武裝販毒幫眾之間。換成我們肯定魂飛膽喪,但他憑著無敵的好奇心與超人的勇氣,竟然不斷重返虎穴。
幾年前,我和經濟學家李維特(Steve Levitt)合寫《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nomics),因訪問之便和凡卡德希初次見面。他和李維特已經針對「快克 經濟學」聯名發表過幾篇論文,內容有趣自然不在話下,但他本人更是精彩萬分。凡卡德希語氣溫和,言辭簡潔,並不多話,但你只要開口提問,就像扯動古老織錦的絲線,只見千絲萬縷霎時鬆脫,繽紛落在你的面前。他會給你無數的故事,鉅細靡遺,充滿勉力求得的睿智洞見。你會聽到流氓警察如何恐嚇居民,貧困家庭如何透過零零落落的社會網絡苟延殘喘,還有凡卡德希又是如何成為「一日黑幫老大」。
雖然我們在《蘋果橘子經濟學》提到凡卡德希,那一章也是許多讀者的最愛,但因為篇幅有限,我們並未盡述他的故事。幸好凡卡德希寫了這一本出色的作品,詳細描繪自己的探險與危險經歷。他的故事比小說還要離奇,也比小說還要有力、精彩、令人心碎。他帶我們走進外人幾乎一無所知、所知也常是誤解偏見的世界,描繪其獨特的面貌。我們做記者的也會進出貧民窟,但只待上一星期、一個月,頂多一年,而社會科學家和慈善機構多半只管自己份內的事。凡卡德希不但住了進去,還與他們朝夕相處了將近十年。他以外人之姿走入當地,帶著內幕出來公諸世人。不少著作喜歡將窮人描繪成深受外力左右的傀儡,而非有血有肉的生命,會呼吸、會開玩笑、努力餬口、有感覺、講道德。《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不是這樣的作品,凡卡德希告訴我們,毒販、住戶代表、娼妓、家長、騙徒、警察和他自己都在貧困環境中奮鬥掙扎,只為了過好日子。
儘管我非常欣賞凡卡德希,對他敬佩有加,但可不想成為他的家人或研究對象,因為他的大膽肯定讓我害怕,好奇心讓我窮於應付。然而,我非常、非常樂意成為《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的首批讀者,因為這本書就和凡卡德希本人一樣:精彩絕倫。
前言
清晨七點半,我從睡夢中醒來,地點是泰勒國宅二三○一大樓一六○三號公寓,快克毒販的巢穴。大家都叫這間公寓為「屋頂」,因為這裡可以讓你「飛上天」,飛得比大樓真正的屋頂還高。
我睜開眼睛,見到二十多人四散在各個角落,幾乎全是男人,睡在沙發或地板上。這間公寓已經好一陣子沒有人住,牆壁剝落,塑料地板上蟑螂四竄。昨夜的活動(嗑藥、喝酒、性交和嘔吐)於深夜兩點達到高潮,意識不清的人開始超過意識清醒的人數,清醒又有錢再買一劑快克的人更是寥寥可數。當地販毒幫派「黑大王」知道生意差不多了,便決定打烊、收工。
我也睡著了,睡在地板上。我不是衝著快克來的,而是另有目的。我是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為了撰寫論文,開始和「黑大王」往來。
陽光從「屋頂」門口(門板很久以前便不知去向)灑了進來,將我喚醒。我從其他熟睡同伴身上爬過,往下走到十樓的派頓家。做研究讓我認識派頓(必須強調一下,他們一家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他們對我很好,幾乎視我為己出。我向派頓媽媽道早安,她正在替派頓爹地煮早餐。爹地是退休工人,當時七十歲。我洗好臉,抓了一塊玉米麵包,走出大樓迎向涼風徐徐、輕快宜人的三月早晨。
又是貧民窟的一天。
又是外人活在內幕裡的一天。這本書就是這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