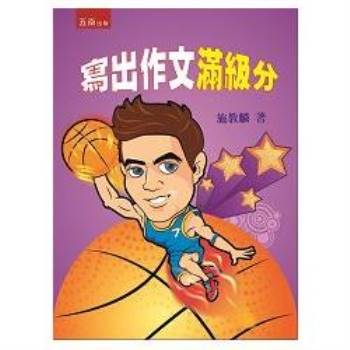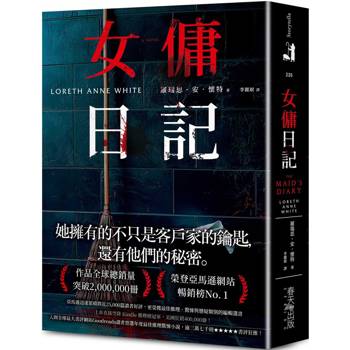該死的蛋
我八點四十五分抵達大都會美術館,提早了十五分鐘。我身穿深灰色亞曼尼西裝,腳踩深紅色古奇平底鞋。我的頭脹痛不已,但已經很習慣這樣了,通常到下午就不再頭疼,等晚上第一杯黃湯下肚後,疼痛便會不藥而癒。
我昨晚不算有睡,只是小憩而已。雖然喝得爛醉,我還是知道今早得穿出點人樣,所以在我把自己打扮好,倒頭上床之前,勉強打了電話給鈴聲服務公司,請他們叫我起床(再賴床,就走路!)。
他們六點就把我叫醒了,但我還是覺得很醉。我在浴室裡拚命將自己弄醒,將臉又拉又扯。我如果知道自己醉了,就會這麼做。六點耶,精神和體力都還沒恢復,就像醉掉的半邊腦子,對著正在工作的另外半邊腦袋玩著聲東擊西的把戲,讓它不知道自己其實已成為醉鬼的囚徒了。
我洗淋浴、刮鬍子,用紐約人氣美髮沙龍潘氏(Bumble and Bumble)的髮霜將頭髮往後梳整,再用吹風機吹頭,然後把頭髮弄成自然休閒狀,讓一小綹頭髮垂在額前,並用水網(AquaNet)的髮膠固定住。經過無數次的辛苦實驗後,本人發現老式的水網效果最好,會讓頭髮呈現出風吹的休閒感——除非你不小心碰到。萬一碰到的話,也許會發出木頭的敲擊聲。
我在脖子四周噴了唐娜.凱倫(Donna Karan)的男用香水,順便噴噴舌頭,免得散發出酒味。接著我走到十七街和第三大道街角的二十四小時營業餐廳,吃炒蛋、培根和咖啡。我想,我吃進去的油脂,應該會把酒都吸掉吧。
為了安全起見,我又吞了一把口齒芳香片,佩戴一條花色豔麗的領帶,引開別人注意。
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不久之後就全員到齊了。我在心裡提醒自己:要注意觀察,配合大家,也許哪天我可以把這概念用到廣告裡。
我用異於平日早上九點的超人精力與熱情,跟大夥握手寒暄。當我面對別人時就屏住呼吸,等轉身後才吐氣,而且走路時一定領先別人十步以上。我們這群人不多:法貝熱香水客戶——一名穿手織背心的嬌小女子,我們公司的AE兼藝術指導葛莉兒。
葛莉兒和我當「創意搭檔」五年了,最近對我喝酒的事很有意見。「你上班遲到了……你看起來亂七八糟的……你看起來很浮腫……你老是心浮氣躁的……」加上我錯過幾次重要展示,她就更加囉嗦了。於是最近我告訴她,我已經把酒量減到很低,幾乎快滴酒不沾了。葛莉兒一直沒原諒我半夜兩點鐘打電話到客戶家,要跟對方在電話裡嘿咻的事。當時我已醉到不省人事了,所以毫無記憶。
眾人踏入第一個展覽間時,我晃到中央的展示櫃旁,假裝對那顆集四盞聚光燈於一身的俄羅蛋深感興趣。太恐怖了:一顆深藍色的蛋上,布滿了一道道俗豔的黃金,還鑲了一堆鑽石。我繞著櫃子,從各個角度去看,一副著迷不已的樣子,腦子裡想的卻是:我怎麼會忘記《脫線家族》的歌詞?
葛莉兒帶著古怪的表情挨到我身邊。那表情不是古怪,而是不可置信。「歐各思坦,我覺得有件事應該讓你知道,」她開口說,「整個展覽間都是酒臭味。」她等了一會兒,然後狠狠地瞪著我,「而且全是從你身上發出來的。」她雙手疊在胸口,怒道:「你聞起來就像他媽的釀酒廠。」
我偷偷瞄了另外兩人一眼,他們正擠在房間遠處角落裡觀賞同一顆蛋,而且好像在竊竊私語。「我連舌頭都刷了,還用掉半瓶口氣芳香劑。」我不爽地說。
「發臭的不是你的口氣,而是你的毛細孔。」她說。
「噢。」我覺得被身體的化學作用出賣了,還被我的體香劑、古龍水和牙膏一併
賣掉了。
「別擔心,」葛莉兒翻著白眼說,「我會跟平常一樣罩你。」接著她走開,鞋根像冰錐似地在大理石地板上踩得叩叩響。
大夥繼續在美術館裡前進時,我感覺到兩件事。一則感到沮喪,覺得自己像個被活逮的現行犯;另一方面,又覺得鬆了一大口氣,既然葛莉兒知道了,我就不必再大費周章地掩飾了。我的心情很輕鬆,但有時還覺得頭暈目眩。一整個早上,葛莉兒都設法讓其他人跟我保持距離,因此我不太需要理會那些蛋,而是專心去看美術館漂亮的硬木地板,和巧妙的嵌燈設計。我看得靈感大發,很想裝修自己的公寓。接著,我們到西南街上的時髦餐廳吃午餐,平凡無奇的食物在那裡變成了美食。
葛莉兒破天荒點了一杯義大利葡萄酒,她低聲在我耳邊說:「你最好也點杯酒,萬一他們在美術館裡沒發現你有酒臭,現在聞到了,會以為是午餐的緣故。」
每天踩四十五分鐘腳踏車、不碰飽和脂肪、拒絕酒精的葛莉兒,實在是太理智了。我則恰恰相反,是個生活靡爛的活例。我聽她的話,也點了一杯雙份馬丁尼。
有人說話了:「嗯,既然你們二位要喝……」接著我們的客戶和AE也都各點了一杯啤酒。
接下來的時間就過得很順了,不久我便回家了。
走進家門時,我輕鬆無比,很高興能回到家裡,不必再屏住呼吸,或拚命為自己解釋了,我立刻灌了一杯威士忌。一杯就好,我告訴自己,只要讓精神放鬆就好。
等我喝完一整瓶酒後,我決定該上床了。時間已過午夜,我明天早上十點還得參加全球品牌會議。我將兩只鬧鐘設在八點半,然後爬上床。
第二天我在驚駭中醒來,我跳下床,衝到廚房,看著微波爐上的時鐘:中午十二點零四分。電話答錄機不祥地閃著燈,我極不情願地按下播放鍵。
「歐各思坦,我是葛莉兒,現在九點四十五,你離開家了沒。好吧,你應該已經出發了。」
嗶——
「歐各思坦,十點了,你還沒到,希望你已經上路了。」
嗶——
「十點十五啦,我現在要進會議室了。」葛莉兒最後的留言,有一種嚴厲與啥都瞭了的味道,一種「我跟你這個下三濫算玩完了」的味道。
我把昨天穿的西裝扔開,盡快沖了澡。我沒刮鬍子,反正沒差,本人嘴毛頗細,而且有點邋遢看起來比較有明星味。我走到外面攔了計程車。想當然耳,這一路到上城全是紅燈。五月的氣溫雖然溫和,當我踏進公司大樓的大廳時,前額已都汗溼了。我用袖子擦汗,然後進電梯,按下辦公室樓層:三十五樓。按鈕沒亮,我又按了一次,還是沒反應。一名婦人走進電梯按三十八樓,她的按鈕便亮了。門關上,婦人轉頭對我說:「天啊,你午飯是不是喝了五杯馬丁尼啊?」
「沒有,我睡過頭了。」我立刻明白事態嚴重。
婦人笑容一斂,死盯著地板。
電梯停在我的樓層,我走出電梯沿著走廊衝到辦公室,將手提箱丟到桌上,從前面口袋拿出一盒薄荷糖,嚼一大把,一邊努力地編藉口。我從窗口望向東河,我真想不計一切,跟那個用拖船將垃圾箱朝上游方向推的傢伙易地而處。他一定不必面對這種壓力,他只須坐在舵上,任輕風拂他的髮際,讓陽光照在他臉上就行了。也許他會憶起在北大西洋航行的日子、用膠布貼在遮陽罩上,與孫子們的發黃快照。要不就是把酷爾斯(Coors)啤酒夾在兩腿間,聽著廣播節目。反正不管哪樣,他的日子過得都比我好。他當然不會在國際香水會議上遲到了。
我決定不找藉口,盡可能地表現友善,並努力地參與會議就好了。我打算偷溜進去,坐到位置上,說些五四三的,讓大家相信我一直都在那裡。
我打開會議室的門,但門鎖著。「媽的,」我咬牙說。這表示我得敲門了,而且有人得過來開門放我進去才行,因此我的隱形計畫告吹了。於是我極輕地敲著門,這樣只有最靠近門邊的人才能聽得到。
門被打開了。開門的是我老闆伊蓮娜,公司的創意總監。「歐各思坦?」她驚訝地看著我說:「你會不會有點太遲了。」
我看到會議室裡滿是穿西裝的人,有二、三十個,而且每個都站著,正在將文件塞進手提箱裡,把空的健怡可樂罐往垃圾桶裡扔。
會議剛剛結束。
我瞥見葛莉兒在角落跟我們的香水客戶講話。不只是客戶,還有客戶的老闆、產品經理、品牌經理及國際行銷主任。葛莉兒瞄見我,眼睛恨恨地瞇成一小條縫。
我對伊蓮娜說:「我知道,很抱歉遲到了,家裡突然有事。」
她像聞到臭屁似地皺起眉,然後湊近一步嗅了嗅。「歐各思坦,你是不是……醉了?」
「什麼?」我驚駭地說。
「我聞到酒味了,你是不是喝酒了?」
我臉都紅了。「沒有,當然沒有,我沒喝酒。我昨晚是喝了幾杯,可是……」
「這事我們待會兒再談,現在你應該先去跟客戶道歉。」她繞過我離開會議室,而且絲襪還磨出刷刷刷的聲音。
我擠到葛莉兒和客戶旁邊,他們一看到我,便不再說話。我擠出笑容說:「嗨,你們好,我沒參加會議,真的很抱歉。我有點私事必須處理,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一時間沒人開口,他們只是看著我。
葛莉兒說:「西裝不錯。」
我忙著道謝,然後才想到她是在挖苦我,因為我昨天就是穿這套西裝,而且看起來好像幾個禮拜前就該送洗了。
其中一名客戶清了清喉嚨,看著錶。「嗯,我們得走了,我們得去機場。」一群人從我身邊走過,全都穿著細紋布料,提著手提箱,拿著公文。葛莉兒一個個拍著他們的肩膀說再見,然後又朝著他們背後說:「一路順風哪,華特,幫我跟寶寶和蘇打個招呼唷。」她笑顏如花。「下次見面,麻煩把那位針灸醫師的名字告訴我。」
稍後,葛莉兒和我已經在我的辦公室裡「談話」了。
「不是只有你的問題,這也是我的麻煩,我們是搭檔,會影響我耶。因為你沒把你那一半的工作做好,害我很為難,我的前途也受到影響。」
「我知道,我真的很抱歉,只是我最近壓力真的很大,我真的已經少喝很多了,可是有時候就是會出狀況。」
葛莉兒突然從我書架上抽出一本《艾迪廣告大賞》(Addy Award),朝對面的牆壁扔過去。「你他媽的是哪個字沒聽懂啊?」她尖聲大吼,「我在告訴你,你會把我們一起拖下水,不僅毀掉你自己的事業,也毀了我的。」
她的憤怒震得我完全無言以對,我看著地板。
「看著我!」她大聲喝道。
我看著她,看到她太陽穴上暴起的青筋。
「葛莉兒,我已經道過歉了嘛,妳這樣會不會太誇張,我怎麼會毀掉任何人的事業?有時候開會難免遲到,有時會錯過,總是會有鳥事嘛。」
「但不會一直不斷地有,」她罵道,一頭絲亮的完美金髮,看來格外刺眼。她連一根頭髮都沒弄亂,不知怎地,看了就讓人覺得不順眼。
這下換我想扔書了,而且是對準她扔。「妳冷靜一點行嗎?天啊,妳這瘋婆子,這太誇張了。如果我這麼不堪,那妳說,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成功?」我邊說邊用手比著自己的辦公室,彷彿在說:妳瞧這一切!
葛莉兒瞄著書架,然後又看著地板,深深吸氣,再把氣吐出來。「我又沒說你不優秀,」她比較平靜了,「我是說你有問題,而且影響到我們,我是在擔心你。」
我的雙手在胸口交疊,注視著她身後的牆壁,我需要靜一靜。奇怪的是,我的腦袋竟然一片空白,雖然我是在爭吵中長大的,但我痛恨爭執。我父母的心理醫師非常擅長爭執,他鼓勵怒吼和尖叫,你大概會以為我很能吵,但我偏偏就是不行。我只是乾瞪著牆壁,腦子裡亂成一團,我想是因為覺得罪惡吧,好像被逮到了。問題是,我知道自己喝太多了,或是別人認為我喝太多了。可是酗酒已成為我的一部分了,就像我的手臂長得太長,有辦法改嗎?瞪著牆,又想到另一件令我不爽的事。這裡是曼哈頓耶,大家都在喝酒,大部分的人都跟葛莉兒不同,大部分人都比她懂得享樂。
「我有時的確喝太多了,我是幹廣告的,廣告人本來有時就會多喝一點。拜託,妳看看人家奧美廣告公司,他們的自助餐廳還設了吧檯呢。」接著,我指著她鼻子說:「妳把我說得像個街上的遊民。」我想提醒她,遊民沒有六位數的薪水,也不會得艾迪廣告大賞。她毫不猶豫地凝視我,對我的話全然無動於衷。「歐各思坦,」她說,「你在往下沉淪,但我不想陪你。」她轉身走出辦公室,將門重重地摔上。
我獨自待在辦公室裡。結束了,她走了。也許她說得對。我的狀況比自己想像的糟嗎?我突然怒不可抑,就像一名被迫停止遊戲,上床睡覺的孩子。小時候,我爸媽常開派對,我最恨派對才要開始,他們就逼我上床睡覺。我痛恨那種錯失一切的感覺,所以我才會跑到紐約市住,因為我什麼都不會錯失。今天算是給那個爛女人毀了,我一整天都沒辦法專心工作了。葛莉兒和我之所以成為好搭檔,原因之一是我們手腳都很俐落,事情沒解決就很不痛快——所以我們會沒命地專心工作,快速地解決問題,激盪出合適的廣告詞。有些人會閒晃幾天或幾個星期,可是我們一做完簡報,就會立刻投入工作,而且總是盡量在一天內想出四個點子,然後才會放鬆。
可是經她這麼一鬧,我也甭玩了,沒戲唱了。我真是對她深惡痛絕,我受夠了,我要喝酒!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吼搭啦!的圖書 |
 |
吼搭啦! 作者:歐各思坦.柏洛斯 / 譯者:柯清心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9-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0 |
二手中文書 |
$ 288 |
中文書 |
$ 288 |
歷史人物 |
$ 456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吼搭啦!
《一刀未剪的童年》暢銷作家柏洛斯二十四歲時,意氣風發,為NIKE球鞋寫出「JUSTDOIT」這句傳誦全球的廣告文案,但他也是個酒杯不離手,經常上班遲到的酒鬼。終於,他的上司與同事都受夠了不斷從他毛細孔飄出來的酒氣,要求他去戒酒。一個月後,柏洛斯回到曼哈頓,規律地工作,定期參加匿名戒酒會,並接受心理治療。但摯友「豬頭」的愛滋病逐漸惡化,成為壓垮他所有努力的最後一根稻草。柏洛斯因為無法承受即將失去豬頭的壓力,又開始喝酒。豬頭過世後,柏洛斯頹廢地生活,跟阻街女郎到陌生的地方嗑藥,還曾經醉到昏迷不醒,幾度尿床。某天,柏洛斯接到一通陌生人的電話,說豬頭一個月前在珠寶店訂製了東西給柏洛斯,請他去取件……一部令人絕倒的回憶錄,溫暖、坦誠和率直。點出作者的深度與完整的人性,讓讀者在大笑之餘,亦深深同情。──《歐普拉雜誌》
章節試閱
該死的蛋我八點四十五分抵達大都會美術館,提早了十五分鐘。我身穿深灰色亞曼尼西裝,腳踩深紅色古奇平底鞋。我的頭脹痛不已,但已經很習慣這樣了,通常到下午就不再頭疼,等晚上第一杯黃湯下肚後,疼痛便會不藥而癒。我昨晚不算有睡,只是小憩而已。雖然喝得爛醉,我還是知道今早得穿出點人樣,所以在我把自己打扮好,倒頭上床之前,勉強打了電話給鈴聲服務公司,請他們叫我起床(再賴床,就走路!)。他們六點就把我叫醒了,但我還是覺得很醉。我在浴室裡拚命將自己弄醒,將臉又拉又扯。我如果知道自己醉了,就會這麼做。六點耶,精神和...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歐各思坦.柏洛斯 譯者: 柯清心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9-01 ISBN/ISSN:9789573265108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