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中國二百年》記述了自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至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這二百年間在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是從我那一大堆雜亂的讀史筆記裡整理出來的,談不上系統和全面,只是把我認為有興趣的一些題材按時序編排起來而已,儘管如此,從我一開始動筆之時就意識到這可不是件輕鬆的事情,沒有決心是不可能完成的。
促使我下決心動筆的原因固然有多起,不過對我最大的激勵還是起於一樁偶然的事。
幾年前,我正在一處書攤上翻看一本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書,恰好被一位朋友看到了,他很不以為然的搖著頭說:「這些事情是弄不清楚的!你一個說法,他一個說法,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是一個說法……」。我不得不承認,朋友的議論確實很有道理,他所談到的「說法」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事件的真相,二是指對事件的理解。
不過我仔細一想,比較一下這些不同說法,而後記錄下自己的判斷和見解,不是也很有趣麼?
早就有人評論說:讀中國的報導有如看日本電影《羅生門》,那部電影中的四個人,強盜、武士、武士之妻和一位樵夫,他們對一樁命案有五種不同說法,電影似乎沒有強迫觀眾去採信某一個說法,觀眾可以自由選擇答案。自由選擇就是樂趣。
讀書人不正是可以從讀書中享受這樣的樂趣麼?
不過我這裡所說的讀書人不包括下列兩類人。
第一類是在校的莘莘學子,他們首先要應付考試,所以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致去比較那些不同說法,他們只能勉強記住教科書或者教師講授的說法,而後在試卷上複述這些說法,考完之後也就儘快把它們送進回收站,以便讓出容量來應付新一輪輸入。
記得五十年前筆者就讀於重慶大學礦冶系之時,有一門必修的政治課稱為《聯共(布)黨史》,各系同年級的學生在一起聽大課,課後分組討論,然後各班課代表向教研室會報討論結果,其實這些討論也不過就是複述聽講內容而已,但是有一次我們班上的一位同學卻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問題的內容我早已忘記了,只是記住了後面發生的事,幾天後,課代表傳達了教研室的答覆:《聯共(布)黨史》是經典性著作,必須嚴肅對待,不允許懷疑,也不允許不同的理解。
試問,如此讀書還有什麼樂趣可言?好在,從來也沒人指望在這類讀書中尋找樂趣,最近我倒是想查一下那本書中的一些說法,可惜在任一處圖書館裡都不見該經典的蹤影了。
第二類讀書人也不在我所說的範圍之內,他們是專業治史者,專家讀史應該不同於一般讀書人。
一般讀書人以「書」為限,他們能接觸到的不外是書店和公共圖書館內書刊,最多再佐以自己的見聞。他們只能從這些資料中選擇自己的判斷和得出自己的見解。在這一點上他們與電影《羅生門》的普通觀眾沒有多少區別。
專家則不應如此,他們必須去挖掘一切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正如一位刑事偵察專家研究一樁謀殺案那樣。他們研究《羅生門》的方式絕不會與普通觀眾相同。
讓我來舉一個例子,上世紀六○年代,戚本禹與羅爾綱就李秀成投降案辯論,戚本禹遍查清廷軍機處檔案,終於找到了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樣的專業性研究確實必不可少,不過這不是一般讀書人能夠從事的工作。
中國近代史料浩繁,一般公共圖書館內的史料已經令人無暇遍讀,更何況還有許多重要史料尚深藏於臺北、北京、東京、莫斯科、倫敦和華盛頓等地檔案館內,就算這些檔案允許公眾去自由查閱,恐怕一般讀書人也難以問津。
所以我們一般的讀書人也只能就自己身邊可用的資料來分析對比,來尋找讀書的樂趣。就筆者而言,他的閱讀範圍就以昆明市各圖書館藏書和市面售書為限。
筆者發現,僅自己所接觸的這些史料,也有如朋友所說:「你一個說法,他一個說法,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是一個說法」。其實這正是一個正常而合理的現象,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法律專家不也是各執一詞以供陪審團及審判長兼聽及選擇麼?
筆者還發現,在圖書館的許多書籍上都留下了讀者的批語,他們用這種方式向作者發出疑問或者批駁,也向其他讀者交流見解。從道理上說,讀者有權評論這些書刊,不過,在公共圖書上去塗寫畢竟不是很妥善的作法。
感謝臺北的遠流出版公司為我出版此書,使我不必在公共圖書上去亂畫了。
李守中 二○○三年五月於昆明
後記
筆者在〈自序〉中已經提及,本書記述了自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至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這二百年間在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筆者對這些事件的理解。
然而從一開始,這個預定的時間範圍就被打破了,第一章是從康熙的一席談話講起,因為用它做引言更容易使人了解一七九三年之前的一個重要情況。今天我們談論中國的事情已經不能脫離世界大環境,而在康熙至乾隆年間,也就是清代鼎盛期,中國的知識界還不具備這個眼光,他們還要經歷不知多少磨難才學得這一點並且傳授給我們。康熙大約是第一個意識到這個危機的人。
本書從整理筆記開始,斷斷續續差不多用了十年才完成書稿,這距離一九九二已有十多年了,而這十多年又發生了不少大事須得一提,於是筆者不得不又一次越過了原定的時間範圍。
如今人們都欣慰的見到臺海兩岸和緩,見到理解與合作的進展,大陸經濟改革的巨大成效,然而更加重大的事件應該是臺灣的政治改革,一個多年施行威權的政黨逐步把自己置於與人平等的地位,這是一項艱難而痛苦的轉變。
二十世紀出現了幾處威權政體,他們的權力,他們對社會的控制都是空前的。有段時期這種體制似乎成為大勢。它總是率先出現在一個大混亂與大危機的社會,民眾渴望秩序,渴望拯救。一個強有力的威權也就應運而生。它於實施之初往往成效顯著,但其後則弊端叢生,社會停滯,民眾困苦。體制也不免瓦解。
一個多年施行威權的政黨能及時改革實不多見,能以民選退居在野更難得,而由民選再度執政者就尤為可貴了。這說明民主進程的成功,這個政黨在變革社會的同時也革新了自己。
胡適在上世紀二、三○年代多次引用一句話:「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要換個樣子了!」據說這源於荷馬的史詩,在文藝復興和其後的歐洲改革運動中常被人引用,筆者寫到此處不禁想到了這一句,也就用這一句話作為結束。
李守中
二○○九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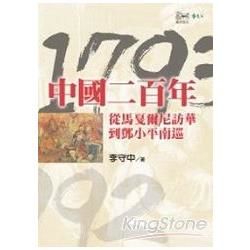






![失智症照護指南[經典暢銷增訂版] 失智症照護指南[經典暢銷增訂版]](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41/2014150562736/2014150562736m.jpg?Q=e3fc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