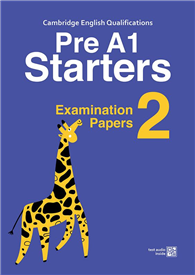天文十八年(一五四九)。日後以勇猛殘虐行狀令世間驚顫的武州公,此時乃身為人質的十三歲少年。困於即將陷落的牡鹿山城,某夜,在闇黑倉庫搖曳燈燭底下,目睹異樣的死亡之美——少年初萌的青春慾望,自此埋植了被虐性變態的恐懼與妄想……
耽美名家谷崎潤一郎設定戰國時代為背景,以虛實交雜的考據史料、畸絕奔放的驚人異想,古文白話操縱自如,織出艷絕流暢的短篇傳奇,直探人性慾望之幽微邊角。
本作於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初刊《新青年》雜誌,連載搭配的木村莊八插畫亦一併收錄。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柯裕棻:「谷崎潤一郎筆下的感官世界真是美得難以逼視。」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紀大偉:「《武州公秘話》以古雅的文體說出前衛的故事--古雅和前衛並置,固然是一大矛盾,一大諷刺,但谷崎就愛矛盾諷刺。」
作者簡介:
谷崎潤一郎
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生於東京日本橋,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謝世。東京帝國大學國文科中輟。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初試啼聲,發表短篇小說〈刺青〉〈麒麟〉,永井荷風盛讚,從此確立文壇地位。
除小說、隨筆,亦創作戲曲。初期文風屬耽美派一支,隨生涯轉折迭有變遷;兼納古今文體、俚俗方言,以端麗文風鋪陳出充溢著豐潤官能美與陰翳古典美之綺想世界。《癡人之愛》《春琴抄》《細雪》《瘋癲老人日記》等名作具藝術高度而雅俗共賞,出手盡皆不凡。
除獲頒每日出版文化賞、朝日文化賞、文化勳章、每日藝術賞,亦得世界文壇敬重,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任美國藝術暨文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名譽會員。
譯者簡介:
張蓉蓓
輔仁大學日文系夜間部學士,日本熊本大學文學碩士,二松學舍大學文學博士,專攻日本平安朝和歌。現任輔仁大學日文系專任助理教授。
撰有日本文學導讀十餘篇,譯有《夢十夜》《古今和歌集》等,並為《百人一首》作全譯注;作品尚有小說《相思與君絕》《催嫁》等,並曾獲教育部創作文學獎短篇小說獎佳作。
多情傻氣的牡羊女,古典中毒活人之一。最大的心願是趕快提早退休,好專心寫官能小說。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異端者的視界如此幽暗絕美 / 柯裕棻
谷崎潤一郎筆下的感官世界真是美得難以逼視。
谷崎寫作的視野是內向的,他探詢的主題不是社會的外在維度,他的目光深深地向內掘進肉身裡,彷彿在這私密軟膩的身軀裡的某處,靈魂也像血肉那樣汨汨流顫著。也許這也正是谷崎畢生著迷於「陰暗」這一概念的原因:與其以俗眼在日常生活中搜尋窺伺,不如閉上眼睛,在自我的闇黑中想像摸索,如此也許更能貼近生命的核心慾念和追求。他的多部作品都以可見與不可見、模糊難辨的朦朧之美為主題。在那看不見的暗處,剖露的慾念往往令人背脊發涼,涼到了底,又彷彿發燙燃燒。
雖說谷崎文學是耽美派、是官能主義,但他追求的不僅僅是身體書寫的表現。在形式上,他積極實驗語言的可能,極力追求文字結構在視覺以及音韻上的完美;在人物設定、背景細節、情節安排上都展現對美的極致膜拜,如此極致的身體美學表現反而使這些作品超越了肉體的物質性、超越寫作時代的道德限制,使得它們不論在哪個時代看來都非常奇特、犀利,展現他對於性靈自由的渴望。
在偷窺盛行的今日,所有的慾望都已無足為奇,再隱晦的隱私也都成為日常談資,再也沒有甚麼驚世駭俗的告白或真相可讓我們震驚了,儘管如此,谷崎的作品仍舊不減其令人驚歎的特質。這驚歎倒不是因為書中有多少暴露刺激或香豔的內容,恰恰相反,當今的讀者會覺得,谷崎直接描寫肉慾的文字非常少,既不暴烈也不暴露,相當迂迴含蓄。他令人震撼之處乃在於揭露的慾望如此怪誕離奇,那是在肉慾之外的,無以名之不可訴說的「非常」。他描繪的異端者的視界如此幽暗絕美,超乎常理想像,游移漂浮在常與非常之間,無可名狀。那是另一種曖曖含光的世界,有另一種重力和準則。《武州公秘話》就是這樣一部驚人的作品,能寫出這種故事的人究竟有怎樣的眼睛呢?如此的天才看見怎樣的世界呢?
說來奇怪,我最早讀到的谷崎潤一郎作品,並不是廣為人知的那些,而是早年不知在哪個報紙或雜誌上節譯的關於中華料理的小說。這個故事對食物與人體的滋味、形狀、色澤及觸感的描繪極盡感官語詞之能事,幾乎能聞見那肉汁迸濺、令人暈眩的香氣。那文字十分神妙,又萬分墮落,然而又有某種隱隱的恐怖在暗中閃爍。我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將他想像成一個肥胖而猥褻的老頭,而且我以為他的年代更為晚近,是當代的作者。
後來才發現他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個大起大落的風雲時代,目睹了文化的巨變,經歷了日本史上最大的社會變革。他確實胖,好吃好色,是個有濃烈生命力,目光炯炯,略微害羞,治學嚴謹、生活風雅的江戶子。他非常喜愛女性的手腳,作品中曾多次以女性的腳作為慾望標的。據說他到了晚年仍然會大剌剌的盯著女性的手腳瞧,這一點其妻松子曾在回憶錄中提過。谷崎也喜愛貓,曾創作貓主題的小說。他在知名的散文集《陰翳禮讚》中剖析自己越來越孤僻的個性,並且希望自己能像貓一樣長一條尾巴,可以隨時搖一搖,用來應付他懶得理的那些人--「希望有條貓尾巴」這種話由他說出來,感覺也有異色趣味。儘管是這麼奇特的人,對於讀書和寫作他有相當嚴謹的堅持,在論寫作的《文章讀本》一書中谷崎曾一再地闡述「熟讀」與練習的重要,此書更可看出他對古典文學的熱愛和精研。
谷崎作品的複雜也如同他的性格一般矛盾,因為谷崎不僅有非常現代主義式的實驗作品,也有結構完美的古典的作品,如《盲目物語》(一九三一)、《武州公祕話》(一九三一)、《春琴抄》(一九三三)、《聞書抄》(一九三五)等。《春琴抄》的年代設定在幕末至明治時期,《盲目物語》和《聞書抄》則是以眾人熟知的織田、豐臣、德川戰國爭霸時期的女性命運為主題──此三本小說的主角或敘事者都是盲人。
《武州公祕話》則完全不同,這是一個徹底的異端。此書以戰國時期為背景,敘事方式與《春琴抄》相似,亦即,《武州公祕話》也是採取虛實難辨、真假交錯的史料剪裁方式,虛構出詭譎的情愛故事。將真實歷史和捏造的史料天衣無縫的接連在一起,此書堪稱一絕。
這個故事中有許多血腥場面,有主角武州公深深為慾望苦惱而顫抖的殘暴、駭人的性虐、美豔而強勢的女性、又寂寥又糾葛的深宮後院生活、女性復仇的陰狠渴望。重要的故事空間除了臥室和庭院之外,竟是屍體清洗以及廁所這般污穢之處。然而全書的意象卻非常幽寂凜冽,恍若可怖又空靈的夢境,無絲毫不潔之感。若非出自奇才之手,這些複雜殘酷的異端故事無法如此昇華。
谷崎巧妙地運用漢字的意象於角色命名,如「松雪院」、「牡鹿城」、「法師丸」、「桔梗夫人」、「池鯉鮒女兒」、「瑞雲院」等曼妙的名稱,營造出似真似假的朦朧詩意,也是古典文學基底深厚的谷崎擅長的手法。
吾輩俗人俗眼,讀此書驚歎讚賞,毫不覺得彼為異端,反而為他強烈綻放的妖異才華所震懾,深感自慚形穢了。
***************************************
分身禮讚 / 紀大偉
「分身」,「本尊」,一對寶。這對活寶,早就可以在東西方的古今文化找到。但是,一九九六年宋七力事件掀起軒然大波之後,這一對概念才開始在台灣日常語言大肆流行。「本尊/分身」這一組詞是互相搭配的,但兩者引起的注意力截然不同:本尊家中坐,不值得大驚小怪;分身雲遊四海,才讓人嘖嘖稱奇。變態大師谷崎潤一郎早在奇書《武州公祕話》,就禮讚了分身的美妙。稍後我會解釋分身與變態的瓜葛,但我要先勾勒分身與本尊的關係。這兩者的關係,正是《武州公祕話》的主要課題之一。
本尊,好比梵谷親手完成的油畫;分身,恰似原畫的複製品。本尊是真貨,分身是膺品;本尊貴,分身賤;本尊供奉美術館內,分身化為梵谷油畫圖案的T恤,馬克杯,郵票,月曆,在紀念品中心或是網路販售。分身輕賤,卻反而享受優勢:本尊不能行遍天下,分身卻可以;本尊必然老朽,淪為時間的塵埃,可是分身卻生生不息(反正可以在工廠大量複製),永垂不朽。
如果梵谷的原畫被人燒毀,就救不回來了;但原畫的分身還在,可以一再scan, print, 出售。且讓我轉向美術館的另一個角落--也是更貼近谷崎潤一郎神髓的美術館一隅--木乃伊。
古埃及王公的肉身是本尊,而本尊改造之後的木乃伊是分身。既然是分身,木乃伊得以穿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今天的巴黎或台北展出:分身享有行動性--指「行動電話」的那種「行動」。值得注意的是,本尊和分身的角色不是固定的:木乃伊雖然是肉身的分身,但木乃伊也被當作本尊,跟梵谷的原畫一樣供在藝術殿堂裡。木乃伊衍生了它的分身,在店裡或網站流通。本尊,動不得;分身,以及分身的分身,卻具有一再延展一再蔓長的潛力。
谷崎潤一郎小說以變態出名,而我認為他作品中的變態和分身脫不了關係。《武州公祕話》中的分身至少有兩個意思:一,分身不長在本人身上,而是代理人,例如代替本人去辦事的跑腿小弟小妹。二,分身長在本人身上,尤其是指性器官。這兩者分身常常「被認為」不聽話,害主人(本尊)「做壞事」。第一種分身可能盜用主人的私章提款卡,但主人自己漏財的時候,也常愛栽贓給這一種分身。第二種分身(通常是指性器官)讓主人沈溺肉欲,但主人也愛把這一種分身當作代罪羔羊,充作自己淪喪理智的藉口。在《武州公祕話》中,有些人是第一種分身,代替父兄報仇;有些器官是第二種分身,激發小說人物的賀爾蒙。值得留意的是,谷崎藝高人膽大,書中描繪的肉欲器官偏偏並不是一般定義的性器官,卻寫得比生殖器還讓人臉紅心跳。
這兩種分身,雖然一種長在人體外,另一種長在人身上,但這兩者的分界線是很模糊的。送披薩的小弟可能也就是自己的性器官,而自己的性器官也可能身兼坐捷運賺外快的小妹--例子在各種電視劇常見,我就不列舉了。四處趴趴走的小弟小妹是整個商業體制中的小零件,而在人體零件化的這個時代(想想看:多少人裝了義肢,人造器官,助聽器,或量身訂造了一身肌肉?),肉欲器官也是整具身體機器中的小零件。早在台灣風行的日本動畫《攻殼機動隊》系列以及伊藤潤二的恐怖漫畫《富江》系列,就展現了人體解體,器官變零件,器官從人體外溢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荒唐景致;但,且慢,此等地獄變相,早在一九三一年的《武州公祕話》幽然浮現。在時間軸(古vs. 今),《武州公祕話》生猛勁爆;在空間軸(東vs. 西),《武州公祕話》也毫不遜色。
在吾輩3C時代,「分身化」以及「分身的行動電話化」是商機滾滾的趨勢。家用電話是本尊,手機是分身,分身還可以帶出國進行國際漫游,結果本尊(家用電話)的地位反而嚴重下滑。人腦是本尊,USB隨身碟是分身,有時候躺在牛仔褲袋裡,有時候插入自家筆電,有時候又拔出來插入公司桌電。3C零件的隨機抽插固然好方便,但人體零件的隨機抽插卻好變態。
誠然,人體的分身化,以及人體分身的行動化,是商機滾滾的--獸體器官移殖人體,實驗室工廠壓製人造器官,第三世界女性在第一世界被雇用為子宮(而非一個完完整整的人),器官市場一片看好;但,將人體零碎化且商品化的種種趨勢,往往讓大眾覺得「不自然」甚至「變態」,這些器官市場也都成為法律和宗教的戰場。
在這裡我無意多談器官商機的倫理是非,而只想回歸谷崎,點出「變態」與「分身」的糾纏。所謂的變態,尤其性變態,總是跟人體的「零件化」/「分身化」有關。人與人互動,不管是交普通朋友還是談情說愛,一般認定雙方應該把彼此都當作完完整整的人來對待;如果只關注對方的某個身體部位,就有變態之嫌。當然,有些婆婆挑媳婦就專看候選人的屁股(藉此猜測對方的生育能力),有些人挑男伴就專看候選人的鼻子(藉此猜測對方的性器尺寸),但大家大致上都把持在不逾距的範圍之內,不至於把對方徹底化約成一個分身,一具器官,一張排隊取貨的號碼牌。而有些人把持不住,把花花世界送進碎紙機剪成北海鱈魚香絲長條狀來享用,結果被人冠以性變態或戀物癖之名,有時候被自己的性伴侶罵,有時候根本被扭送警局;這些性變態或戀物癖者,幹了下列「傻事」:對著另一半的性器官說話--彷佛對方的性器官「擬人化」了,變成一個人類;或,把另一半的其他器官(如腳趾頭)當作性器官來撫愛;或,把陌生人的腳趾當作另一半的腳趾來親熱;或,不碰陌生人的肉體分身(如腳趾)而收集陌生人的貼身之物(如舊內褲,穿過的高跟鞋)。
上述行為被認為很變態,是因為大家對於「完整」這個概念很執著。我們要「完整的家」,要「完整的國土」,要「完整的戀人」,要「完完整整不打折扣的愛」。我們理應去愛一個完完整整的人,而不該只是愛上他的股票,她的腳踝,他的鼻樑,或她的內衣。一個完完整整的人才是本尊,而身外之物(如錢財內衣和折斷落地的指甲)和身上之物(如器官,還留在身上未折斷的指甲)都只是一件又一件的分身。如果只愛他的錢,會被訕笑;只愛她的未洗內衣,怕要送警。然而,我們對於「完整」的執著,和對於「殘缺」的畏懼,其實是一體之二面;我們畏懼殘缺物,正是因為我們太依賴殘缺物了,我們根本就愛貪小便宜撿拾七折八扣之後的人事物,可是我們又沒辦法承認這個事實,結果充滿內心戲的我們就否決殘缺物,厭棄殘缺物。我們聲稱只收紙鈔,其實更愛零錢。這些道理,張愛玲都說過。
其實,我們與人突然來電時,往往都只是被對方的某種碎片/分身所吸引,如她的眼神,他的體臭,她的耳垂,他的胸毛,而不是被對方的完整無缺本尊給煞到。就算我們持有她/他留下的紀念品,如蜜月合照,flickr相片集,或「骨肉」(這個詞可真傳神),這些珍品也都是殘片,一點也不完整。就算我們用3D立體攝影機留下對方的紀錄片,這支3D紀錄片終究還是分身,不是本尊。
《武州公祕話》以古雅的文體說出前衛的故事--古雅和前衛並置,固然是一大矛盾,一大諷刺,但谷崎就愛矛盾諷刺。《武州公秘話》連文體都充滿了矛盾諷刺:誠如許多研究者指出,《武州公秘話》是歷史與虛構(「小說」即「虛構」)交錯的,是實與虛交錯的;換句話說,此書呈現出完整與碎片的辯証:完整的大歷史vs. 瑣碎的野史;小說開頭充滿壓迫感的漢字文言文 vs. 如落櫻撒遍全書的性學新鮮字。此書歪歪扭扭說出這個道理:人,終究迷戀分身。這種迷戀是不是變態呢,未必重要;重要的是,這種迷戀是我們生命中的既有組成成分,我們難以否認。完整的本尊偏偏要碎裂成鏡子碎片般的分身,一片一片,零零落落,血水淋漓插在我們皮肉之上。我們像白泡泡幼咪咪的?薯,在滿地玻璃碎屑中打滾。這種身心俱裂之苦,才讓我們刻骨,銘心。
紀大偉,台大外文系學士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比較文學博士。在美東教書五年後,現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曾獲聯合報文學獎等。小說集《膜》日文譯本已出版。
名人推薦:【專文推薦】
異端者的視界如此幽暗絕美 / 柯裕棻
谷崎潤一郎筆下的感官世界真是美得難以逼視。
谷崎寫作的視野是內向的,他探詢的主題不是社會的外在維度,他的目光深深地向內掘進肉身裡,彷彿在這私密軟膩的身軀裡的某處,靈魂也像血肉那樣汨汨流顫著。也許這也正是谷崎畢生著迷於「陰暗」這一概念的原因:與其以俗眼在日常生活中搜尋窺伺,不如閉上眼睛,在自我的闇黑中想像摸索,如此也許更能貼近生命的核心慾念和追求。他的多部作品都以可見與不可見、模糊難辨的朦朧之美為主題。在那看不見的暗處,剖露的慾念往往令人背...
章節試閱
少年的眼光首先便盯上了屋內最恐怖的物事。他從靠自己最近的婦女膝上的首級看起,然後視線繼之掃過並排的首級。法師丸很滿意自己能夠盯著看了那麼久。不過說實在,那些首級看起來就像假人頭一樣乾淨,絲毫不見他所預期的戰場實感或勇者面貌。看得愈久,愈覺得那些首級不屬於人類。
大概老嫗事前便已告知,法師丸一進來,婦女們投以恭敬的注目禮,接著又繼續安靜工作。在場人數正好五人。其中三人將首級一個個擺在自己面前,另外兩名當助手。一名婦女以水壺在臉盆內注入熱水,由助手從旁協助清洗腦袋。洗完後放在首級板上,轉給下一位。另一名婦女接過後重綁頭髮。第三名婦女則別上名牌。作業流程大致如此。最後則是所有的首級井然有序地在三名婦女身後的長形大木板上排成一列。為了怕首級滑落,板面釘上釘子,首級不偏不倚掛在上面。
為了作業方便,三名婦女中間擺著兩盞燈火,照得滿室通明。而且是一起身就幾乎要撞到屋頂的低矮閣樓,法師丸得以將室內光景盡收眼底。首級本身並未給他太強烈的印象,反倒是首級與三名婦女的對比,讓他興味盎然。處理著許多首級的女性手與指,與失去生氣的死人膚色相較,顯得異樣靈動、白晢,誘人。她們為了移動首級,常常要抓著髮髻舉上舉下,對女性而言有點吃力,所以必須將頭髮纏繞在手腕上好幾圈,以利搬動。此時那素手竟更添魅力。不只如此,臉龐亦然。已經習慣這樣工作的女子,面無表情,有種近乎事務性、石頭般冷峻的感覺,幾乎看不出有任何情緒,但是又和無感於死人首級的層次不同。一種是醜陋,一種是崇高。這些女性對死者仍持有敬意,無論任何時候都不會草率處理,而是儘可能鄭重、謹慎、輕柔對待。
法師丸受這毫無預期的光景吸引,一時間進入了忘我狀態。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在發酵,他後來才理解,但當時的少年是毫無所知。他只知道是某種未曾有過的體驗——或說一種無以名狀的興奮。如此說來,兩、三天前的黃昏,老嫗最初與他攀談時,這三名女性也在場,的確對她們的面容有印象,但那時尚無任何感覺。同樣的面孔,為什麼在這閣樓裡、對著首級工作,就令他深深著迷?他往返盯著三名婦女的作業程序。坐在最右邊的為木牌結上繩子,然後綁在首級的髮髻上,然而有時是童山濯濯的首級——「和尚頭」——出現,這時便用錐子在耳朵上打個洞,穿過繩子。她打洞時的樣子很惹他歡喜。但最令他陶醉的是中間負責洗髮的女性。她是三人之中最年輕的,大概十六、七歲。也是圓圓的臉蛋,面無表情中流露幾分自然嬌美的神態。她之所以惹少年注目,是她注視著腦袋時,雙頰偶爾會無意識地牽動出一抹微笑。在那瞬間,似乎有種無邪的殘酷在她臉上浮現。還有綁頭髮的纖纖素手,動作比誰都靈活優雅。偶爾她會拿起旁邊桌上的香爐來薰頭髮,然後把頭髮攏起、綁上帶子,接下來的動作好像是某種儀式:以梳背輕敲頭頂。這時的她在法師丸看來真是美極了。
「如何?可以了嗎?」
老嫗開口了,少年突然一陣面紅耳赤。老嫗又恢復了慈祥高雅婦人面貌,但法師丸覺得她那含笑的眼神彷彿看透了自己的祕密。
「這樣您就了卻一樁心事了吧。今天晚上是我一手安排的,千萬不可告訴別人。」
回到寢間門口,老嫗湊上臉在他耳邊輕輕叮嚀:
「知道嗎?——那就請安歇吧。」
老嫗說完便回身走了。法師丸鑽進自己的臥褥後,依舊無法壓抑亢奮的情緒:通明燈火下有無數首級滾動,那表情、膚色、血淋淋的切面——然後,在那群靜寂的物體當中,生氣勃勃工作著的女性,優雅的手指,以及十六七歲美女的圓臉蛋,整個晚上如同詭異的幻影朦朧浮沉不定。他目擊了如是異常的光景,充滿刺鼻的異臭,以及和死人頭同樣默默不發一語的女性。十三歲少年夜半探黑,踏著庭中皎潔的月光,被帶到這樣不可思議的場所——而且是稍縱即逝——這完全脫離現實的世界突然乍現,又忽倏地消失無蹤。
*************************
少年與昨天同樣時間,再度踩入庭院的月光。打開倉庫的門,來到梯子下面,至此彷彿都被一種無法捉摸的力量吸引而心無旁騖,然而一抵達後,他突然停步豎耳細聽閣樓動靜。說來昨夜種種對他仍像一場幻夢——就算是懷疑那老嫗變了魔術無中生有,但現在來到此地,見屋內鍋水沸騰,暖烘烘的空氣中彌漫著那難忘的異臭。閣樓靜寂無聲,但可見梯子上端燈影搖曳,確定是有人在。少年昨夜沒去注意鍋裡為何燒著沸水,現在一想,才明瞭那是為了洗首級用。
慢慢分辨出幻境與現實的差異,羞恥感使得他備覺壓力。他一步步攀上梯子,卻覺得彷彿有什麼東西把他往底下拖,他心裡一面抗拒,一面奮力往上爬。如預期一般,與昨夜相同的作業情形,也是相同的五名女子進行工作。但是她們沒料到今晚他會再來造訪,一看到少年現身,很明顯面露狐疑。主要的三名女性停下手邊工作,直視著少年。最年長的一位低頭行禮,另外兩位女性見狀心領神會,手中還捧著頭顱,也隨之端淑地頷首致意。她們只有那一剎那才見到真實的表情,立刻又默默投入工作。
女子們向這位身為人質的貴公子行禮時,少年傲然昂首——他連頸脖都羞紅了——展現身為大名少主應有的威儀。他還不懂得以一笑置之來掩飾羞赧與尷尬。他生來是武將之子,無論何種場合——尤其在女性面前——更不能失了氣度。內在的羞赧與外在的矜持——抱懷著如此矛盾的少年故意裝出威風凜凜的樣子,確有幾分滑稽。幸而女性們馬上就投入工作,並未多注意他。她們對少年隻身前來一定感到不解,可是責問又嫌失禮,況且也與她們的任務無關。事務性地、面無表情地、勤奮不懈工作的女子們,以及目光所及之處無不排列整齊的頭顱,映著低矮天花板的燈影,薰香與血腥交織的氣味——凡此種種皆與昨晚如出一轍。
法師丸甚至覺得昨與今是連續的夜晚,不曾中斷。雖然也有白晝,可是自己孤身溜出來闖進另個世界,彷彿是場夢境。差別只在於身邊沒有老嫗作陪。那種渾然忘我、怦然悸動的興奮,不知何時擄獲了他。
最右邊的女子,今晚同樣擔任在光頭耳上用錐子穿洞的工作。中間負責洗髮的女子也依舊用梳子敲著死人腦袋——昨晚最吸引他的是這一位,思量起來,或許是因為她正值青春玉體發育的年齡。為何這麼說呢?這屋內盡是人頭,是「死」的積累。置身其中,女孩擁有的青春及水潤更顯奪目。例如那紅嫩豐頰與慘白人頭兩相對照時,彷彿更添一分生氣。還有,她的工作是把毛髮解開再打結,那滲入髮油的指尖,與髮色的漆黑一相對照,更顯得白皙透明。法師丸今晚仍盯著她眼角和嘴邊浮現的不可思議微笑。左邊的女子遞來洗淨血痕的人頭,她接過手,先剪掉髮髻的結,然後愛撫般地輕柔、專心梳理髮絲,有時塗油,有時剃掉腦袋瓜中間的餘髮,有時自桌上取來香爐,把頭髮放在煙上薰;然後右手持新的纏線,口咬一端,左手都攏髮絲,像打女性髮結一樣結個髮髻。她似乎無意識地動作著,但每當她檢查綁好髮髻的首級,視線落在死人臉上的時候,都會浮現謎樣的笑容。
或許這是她與生俱來的魅力也不一定。在人前總會微笑以對,即便面對死人也有同樣的習慣。長久以來一直處理死人首級,已經對頭顱無所畏懼,而替死人化妝久了生出某種情感,就像對待活人一樣,似乎也無可厚非。只是看在突然闖進的不速之客眼裡,一邊是面無血色、死於非命且仍然心存不甘的死人頭,另一邊是脣紅齒白、面帶微笑的少女,儘管那笑容多麼不經意,仍令人印象深刻,那是一種帶有殘虐性質的妖美。因此,已滿十三歲的法師丸,被這美震懾住也是理所當然。他體驗到一般男子不會有的極端感情。《道阿彌話》詳述了他當時的心理狀態,裡頭提到法師丸非常羨慕置於美少女前的人頭,甚至到了嫉妒的程度。這裡所說的嫉妒、羨慕,不單單是希望讓這名少女親手結髮髻、剃餘髮,用她那帶有殘酷的眼眸盯著瞧而已;而是希望自己被斬首,呈現出一種醜惡、痛苦的表情,然後由她親手整理。一定要變成一顆人頭,這是必要條件。活在她身旁並無樂趣,一定要變成像那人頭一樣,臣服在她的魅力之前,那是至高無上的幸福——他如是想著。
少年的眼光首先便盯上了屋內最恐怖的物事。他從靠自己最近的婦女膝上的首級看起,然後視線繼之掃過並排的首級。法師丸很滿意自己能夠盯著看了那麼久。不過說實在,那些首級看起來就像假人頭一樣乾淨,絲毫不見他所預期的戰場實感或勇者面貌。看得愈久,愈覺得那些首級不屬於人類。
大概老嫗事前便已告知,法師丸一進來,婦女們投以恭敬的注目禮,接著又繼續安靜工作。在場人數正好五人。其中三人將首級一個個擺在自己面前,另外兩名當助手。一名婦女以水壺在臉盆內注入熱水,由助手從旁協助清洗腦袋。洗完後放在首級板上,轉給下一位。另...
推薦序
【導讀】
官能導演 谷崎潤一郎 / 張蓉蓓
「妳擁有如此誘人的肉體,為何一直沒有展露出來?」
「我怕看到這美絕的極品,有人要感動得哭出來。」
──節譯自《卍》
「妳是我的寶貝,
「是我發掘到的,親自研磨的
「鑽石。
「只要能讓妳更美麗,
「買什麼我都願意。
「我全部的薪水都給妳。」
──節譯自《痴人之愛》
如果你的情人要你一起與他(她)共赴黃泉,你(妳)會如何?
在一起總是相處難,明明心知肚明卻難捨難分,如此的愛是幸或不幸?
《卍》的小說中丟出了前者極端的選擇題,《痴人之愛》作品中,問到人世間男女常面臨到矛盾習題。
要如何介紹谷崎潤一郎(一八八六~一九六五)這位私人感情生活與小說同等精采的大正時期作家呢?
與妻子千代子,好友作家佐藤春夫,三人之間發生的糾葛,在社會上轟動一時。千代子常向佐藤春夫訴說遭到丈夫虐待的事實,佐藤春夫由同情轉為愛憐,要求谷崎潤一郎把妻子讓給自己,兩人因而絕交,但最後谷崎依然放棄,立下名噪一時的〈吾妻讓渡書〉。千代子夫人成了佐藤夫人,之後為他產下一子。
谷崎並未因失去妻子而消沉,相反的,他娶了小自己很多的小姨子,是的,就是千代子的妹丁未子,盡情為她打扮、奉獻,想把她塑造成最美的青春女神。(《痴人之愛》多麼近乎谷崎自身的吶喊呀!)
好景不常,在婚姻內的谷崎,已經與後來的第三任妻子──松子夫人──一位大阪富商的老婆同居 ,松子離婚後與谷崎度過人生最後一段還算快樂的時光,是谷崎最後一位永恆的女神,在許多作品中為她謳歌,為她頌揚,谷崎在與松子夫人的生活裡,找到生命中感情的慰藉與小說靈感的泉源。
感情生活波瀾萬丈的谷崎,把對「性」、「愛」、「不倫」、「變態」、「虐待」……的等等題材,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在作品中,甚至大膽縱情地表現官能場景,一度在國會中,尚且有議員質疑《鍵》的作品,究竟「是藝術還是猥褻?」近半世紀前他多采多姿的私生活,就已遭人批評「文學家的道德觀如此薄弱嗎?」谷崎自身對愛情的態度,其實也都忠實地反映在每一個時期的創作中。
谷崎潤一郎的創作活動,自明治末年至昭和四十年為止漫長的歲月中,可以粗分為五大時期:
第一:耽美主義的時代:以處女作〈刺青〉登場後,就以詞藻華麗、古典懸疑的手法營造小說氣氛,直到明治最後的三年當中,皆屬此一時期。
第二:現代主義時期:約從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的關東大地震至大正年間左右。自稱幼時未吃過洋食、未看過洋片的谷崎,在這一時期,刻意地擺脫西洋文化的入侵,寫出許多自傳性作品,如《異端者的悲哀》、《痴人之愛》,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
第三:回歸古典的時代:由於東京大地震的影響,谷崎離開故鄉,移居關西,浸染於日本傳統文化的發源地,傾心於古典文學的世界,從昭和初年起至十年前半,可謂他開花結果的豐盛期,寫出了《吉野葛》等一連串膾炙人口的小說。本譯作《武州公祕話》也誕生在此時期。
第四:戰時期,昭和十四年,谷崎開始著手《源化物語》的現代日語翻譯工作,並完成創作生涯中的代表作品《細雪》,只是無法在戰爭時期發表,直到戰爭結束的昭和二十三年才問世。
第五:戰後成熟期,谷崎的晚年,離不開「母親」的主題,如《少將滋幹之母》、《瘋癲老人日記』,都是晚年的產物。
本書《武州公秘話》成立於第三期時,即回歸古典的時代。
土生土長的谷崎潤一郎,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遇到前所未有的東京大地震,毅然決然撤離了熟悉的江戶環境,來到日本傳統文化的孕育地:關西。從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這七年中,創造出許多以日本近代或中世紀的古典物語為題材的作品。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十月,完成了《武州公祕話》。
「武州公」是何許人?指的是日本武將武輝勝,幼時稱「法師丸」少時稱「河內介」,大膽敘述武州公有被虐待性的變態性向,故事從一位名為「妙覺尼」的比丘尼開始,從她留下的一本作品《夜夢所見》,窺得武州公許多不為人知的祕密……
首先,讀者不要被谷崎巧妙的技巧矇騙了,這一時期的寫作風格,谷崎有了新的「伎倆」:
先捏造一些煞有其事的史料與人物,讓人誤以為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然後娓娓道出這段看似無人所知的祕辛,實則是谷崎高超的想像力所構築的小說。
當然,為了增加故事的逼真性,及寫作材料的豐富性,中間穿插了「真正」的史實,詳細的考證與稗官野史的穿鑿附會點綴其中,偶又來一段耳熟能詳的軍記物語,谷崎可說把讀者耍得頭暈轉向,但這也是他寫作的高明之處吧!使人信以為真,便是最大的賣點了。
故事從武州公幼時當人質的經驗為引線(日本戰國時代為取信盟友,有把自己的小孩,甚或母親等親友送到對方家中生活,謂之為「人質」的習俗。說穿了,好似一種抵押品,有至親骨肉抵押著,比較不容易背叛與造反。)在當人質的幼小歲月中,不意目睹了影響終生的畫面。
──亭亭玉姿的少女(也是人質之一吧!)正專心處理著戰場中遺留的戰利品──敵人的項上人頭,徐徐清洗著人頭,仔仔細細細地梳著髮絲,綁上牌子以示分辨……
女孩紅潤猶似微酡的雙頰,深深吸引著幼小的武州公,雪白的柔指,細膩的動作,令他感到無比性感,尤其當女孩看著一般人盡可能避視、覺得駭怕醜陋的死人人頭時,卻有意無意地浮出不解其意的淺笑──這淺笑是勾懾往武州公的枷鎖,他甚至希望自己是女孩手上的首級,任她把弄,任她處置,那才是真正喜悅的快感。
若說異常的「性經驗」,便是從這開始的。之後要和尚獻藝,不把他人的腦袋當回事,或是執意取敵人的鼻子復仇,而不是砍下腦袋等等的情節,都是源起於幼時在那詭異神秘的小房間內,見到如此異於常景,引人入勝的一幕。這種有別於尋常百姓家的經驗埋下他日後偏頗性的價值觀,亦或自身潛在的嗜虐因子被誘發而日益成形,終成牢不可破地所謂變態性虐,恐怕只有作者本身知道,或是本來它就同時存在,藉由作者的生花妙筆,使劇情更合理化。
《武州公祕話》被作家者里見「弓享」譽為「天下第一大奇書」,它不若《春琴抄》或《細雪》這些評論谷崎文學時不可或缺的代表作,只是一部與滿漢全席相較下的單品料理,但是也堪稱色香味俱全,有其完整的文脈及流暢的文風。常被封為「官能與肉體的思想家」的谷崎,其實是用一種非常「乾淨」的筆法,表達黏濁、鹹膩的感官議題。在「武」一書中,讀者會忘卻背後主人公的殘虐性,只會被故事亦詼亦諧的高潮吸引,或是急於窺得武州公與桔梗夫人有何令人臉紅心跳魚水交歡場景,這些緊湊的情節都淡化了武州公背後真正的異常性人格,但在看過連環劇情之後,猛然閤書,才油然升起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發現也樂在其中的自己,是否與武州公一般,喜歡這種略帶凌虐性的折磨,原來是一種強烈的快感刺激,自己也躍躍欲試,探求更深邃、更令人興奮的高潮場面;發現背後露出滿意詭笑的是谷崎潤一郎本身。
他是導演,是掌握讀者官能起伏的導演──你我都是劇中人。
***********************************
譯後記
《武州公祕話》的成立背景,如〈導讀〉中所述,是谷崎潤一郎移居關西一地時的產物,這是他轉身寫古典作品的時期,有幾分古意盎然,也有幾分殘虐美學,《細雪》的東瀛氣質酷似川端康成的《古都》(不過後者比前者年輕,應該說川端有谷崎的影子。)這一時期的作品群,有許多是翻案自日本古典傳說,或引用歷史傳記而寫成的小品。
也許在該時期的《春琴抄》等鉅作或知名度較高的作品光環遮掩下,《武州公祕話》及《聞書抄》的出版不能造成吹皺一潭春水的效果,僅更增加谷崎這一時期的作品完整性,不由令筆者自身有些遺憾,因為譯文的難度無法得到相得益彰的功績,彷彿使勁老牛拖車,拖上了山頂,大伙兒看不出車子的重量,還嫌妳手慢腳拙,瞎忙了一場。
然而文學作品是不應以「結果」論成敗,也就是說不應該以其知名度高低來決定作品是否優劣,身為一個翻譯者,更不能虛榮地冀望每部譯作都是經典傳世的不朽之作。翻到好作品,自己如沐春風,翻到捉襟見肘、手足無措的難作時,只能反省自身功力不足,慧根不夠,無法把作品表現得更精妙來吸引讀者,如果真的碰到冷門難解的作品,也只能當作是一個試鍊與考驗了。
谷崎不愧是耽美派大家,文筆非常秀麗流暢,但《武》書的漢文體使筆者頻頻蹩眉,怕讀者被這一大串文言文澆熄了閱讀的熱情。日本的漢文,由中國人讀來或有文法及「和習」(日本語法式的中文)的問題,並不易懂,筆者本想改寫成較近於中文文法的語調,考慮再三,又保留其原文,希望讀者能領略谷崎大作家的漢文文筆。而接下來的文白交雜,起初的確也令筆者感到力有未逮,對故事尚未有所掌握之前,的確不知谷崎在葫蘆中賣什麼藥,而有些焦躁不安。但在故事結構窺見端倪的同時,便覺如臨桃花源勝境,越走越深而流連忘返了。
希望讀者也能嗅得這桃花的芬芳。
初稿於二00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基隆
定稿於二0一0年八月十日輔大
【導讀】
官能導演 谷崎潤一郎 / 張蓉蓓
「妳擁有如此誘人的肉體,為何一直沒有展露出來?」
「我怕看到這美絕的極品,有人要感動得哭出來。」
──節譯自《卍》
「妳是我的寶貝,
「是我發掘到的,親自研磨的
「鑽石。
「只要能讓妳更美麗,
「買什麼我都願意。
「我全部的薪水都給妳。」
──節譯自《痴人之愛》
如果你的情人要你一起與他(她)共赴黃泉,你(妳)會如何?
在一起總是相處難,明明心知肚明卻難捨難分,如此的愛是幸或不幸?
《卍》的小說中丟出了前者極端的選擇題,《痴人之愛》作品中...
目錄
目次
導讀
官能導演:谷崎潤一郎 張蓉蓓
卷之一
妙覺尼寫《夜夢所見》之事,及道阿彌手記之事
武藏守輝勝甲胃之事,及松雪院畫中容姿之事
卷之二
法師丸為人質育於牡鹿城之事,及女首之事
法師丸在敵陣剮鼻之事,及展現武勇之事
敵我陣營皆狐疑不安之事,及藥師寺圍城解除之事
卷之三
法師丸元服之事,及桔梗夫人之事
筑摩則重成為兔唇之事,及貴夫人如廁之事
卷之四
桔梗夫人與河內介會面之事,及兩人陰謀之事
則重失鼻之事,及源氏花散里和歌之事
卷之五
河內介歸父城之事,及與池鯉鮒家千金喜慶之事
道阿彌感淚之事,及松雪院悲嘆之事
卷之六
牡鹿城陷落之事,及則重遭活捉之事
解說
異端者的視界如此幽暗絕美 柯裕棻
分身禮讚 紀大偉
譯後記
目次
導讀
官能導演:谷崎潤一郎 張蓉蓓
卷之一
妙覺尼寫《夜夢所見》之事,及道阿彌手記之事
武藏守輝勝甲胃之事,及松雪院畫中容姿之事
卷之二
法師丸為人質育於牡鹿城之事,及女首之事
法師丸在敵陣剮鼻之事,及展現武勇之事
敵我陣營皆狐疑不安之事,及藥師寺圍城解除之事
卷之三
法師丸元服之事,及桔梗夫人之事
筑摩則重成為兔唇之事,及貴夫人如廁之事
卷之四
桔梗夫人與河內介會面之事,及兩人陰謀之事
則重失鼻之事,及源氏花散里和歌之事
卷之五
河內介歸父城之事,及與池鯉鮒家千金喜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