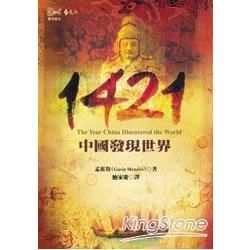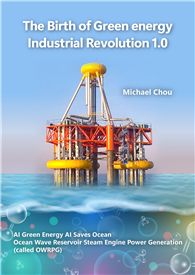1421──明成祖永樂十九年
中國人發現美洲大陸,早於哥倫布七十年;
中國人發現澳洲,先於庫克船長三百五十年;
中國人到達麥哲倫海峽,比麥哲倫的出生還早一個甲子;
中國人解決計算經度的問題,遠遠領先歐洲三個世紀。
過去的歷史課本都可以扔了,過去學的也可以遺忘,因為這本書改寫了一切。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明成祖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在宦官鄭和的帶領下,史上最大的艦隊從中國出發,其中不乏一百五十公尺長的巨艦。中國艦隊如同海上仙山,陣容最浩大時可以容納三萬人,船上美女如雲,然而指揮官卻都是太監。其出航的目的為「宣德化而柔遠人」,這次旅行將經歷兩年,並環遊世界一周。
當他們回航時,明成祖朱棣早已體衰勢微,中國也走上鎖國的道路。巨船朽壞,遠航的記載也遭到毀棄。從此再也沒人知道早於哥倫布七十年,中國人就發現了美洲大陸,並且在麥哲倫的一百年前便已環繞地球。除此之外,中國人更是在庫克船長的三百五十年前就發現了澳洲與南極洲,並且領先歐洲人三百年解決測量經度的問題。
作者孟席斯(Gavin Menzies)花了十五年時間研究這段中國艦隊的驚人旅程。憑藉他的生花妙筆與如山鐵證,歷史的真相如同抽絲剝繭慢慢呈現。他廣泛蒐集古地圖、領航知識、天文學以及東西方斷簡殘篇的證據,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成功地解釋了近年所發現的艦隊沿路留下的遺物與碑文,以及中途的沉船,還有水手在各地祭拜媽祖的遺址。
作者簡介:
孟席斯(Gavin Menzies),英國皇家海軍退伍軍官。一九三七年生於中國,兩年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始離華。一九五三年加入皇家海軍,於一九五九~七○年間於潛艦服役。當他還是低階軍官時,曾經跟隨哥倫布、狄亞斯、卡布拉爾和達迦馬的航跡行遍世界。一九六八~七○年間,當他於皇家海軍「?鯨」號任職時,曾經航行過麥哲倫和庫克船長的旅程。退伍之後,他曾多次重訪中國與亞洲各國。在撰寫《1421》和《1434》的過程中,他造訪了一百二十個國家,並到九百多個博物館與圖書館與中世紀末期的各大海港蒐集資料。孟氏已婚,有二女,寓居倫敦北部。
譯者簡介:
鮑家慶,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科技史組碩士、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譯有《馬背上六千公里:追尋達爾文的南美演化之旅》(新新聞,二○○○年)、《1421:中國發現世界》(遠流,二○○三年)。目前從事軟體開發。
章節試閱
摘自1421-5新天地
我用皮里司令地圖的敘述以及冰塊的位置將南美洲的南端修正為大約南緯五十五度,也就是浮冰的最北極限。確定火地島的緯度之後,我便可進一步查核皮里司令地圖的南部,並與現代的海圖對照。我馬上就發現最初的製圖師把巴塔哥尼亞高原的東海岸畫得極為精確。海岸主要的地形特徵,好比懸崖、海灣、河流、河口與港口,從北方的白灣到南方的麥哲倫海峽入口都非常相符。皮里司令地圖的製圖師甚至還在陸地上畫了一些動物。
照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說法,這裡是個狂風四起的荒涼之地。「沒有人煙,沒有水,沒有樹,也沒有山,這裡只長了少數矮小的植物……巴塔哥尼亞是個無邊無際的平原。因為這裡簡直無法穿越,因此也不為人知。」最初的圖不可能是哥倫布畫的。他從來沒到過赤道以南。他對這個區域的知識,包括他描述南大西洋一天二十二個小時不見天日的「黑暗」島嶼,只能從他複製的那份一四二八年海圖中獲得。
像是麥哲倫這樣最早的歐洲探險家,只有在皮里司令地圖問世多年後才開始前往巴塔哥尼亞。到底是誰提供資料,讓巴塔哥尼亞出現在皮里司令地圖上?他又是怎麼得到資料的?知道我在談的巴塔哥尼亞雖然極度荒涼,卻還有些動物能在此存活,我開始研究地圖上畫出的五種動物。
第一種動物是長著大角的鹿,位置剛好在今天的一個國家公園上頭:小墨瑞諾國家公園(Parque Nacional Perito Moreno)。這種動物顯然是隻駱鹿(guemal,譯按:駱鹿屬﹝Hippocamelus sp.﹞,現已瀕臨絕種),一種安地斯山(Andes)的鹿,頭部和犄角畫得頗為正確。皮里司令地圖描繪的地方現在仍有大群這種鹿存在。下一隻動物位於今天的橄欖灣(Caleta Olivia)以南一百五十公里的化石木自然紀念地(Monumento Natural Bosques Petrificados)。以前我在安地斯山脈拍過野生動物,一眼就認出那種動物是隻駱馬(guanaco)。駱馬與駱駝同科。他們軟趴趴的耳朵頗為有趣,在興奮或緊張時就會往前翹。安地斯山的居民用紅色流蘇裝飾駱馬的耳朵,就跟我們替馬的鬃毛綁辮子差不多。從旁邊看,前翹的耳朵與尖兒朝前的犄角頗為相似。顯然抄襲原海圖的製圖師把前翹的耳朵當成犄角了。在化石木自然紀念地可以找到大群的駱馬,正好符合皮里司令地圖所畫的。這種動物也跟駱鹿一樣,是南美洲特有的動物。第三種動物是隻山獅,繪於今天獅山國家公園(Parque Nacional Monte León)的位置。如同名字所示,山獅在這裡極為常見。這三種動物在地圖上的位置,正好對應於今天在巴塔哥尼亞還能發現牠們的地方,而且地圖是歐洲人到來之前所畫的。
圖上還畫了個蓄鬍的裸體男人。第一印象是那個人的頭在身體中間。但是仔細一看,這個姿勢仍然是可能的。因為圖上的姿勢是曲著膝,好讓長鬍子遮住其下體。我猜想從擄獲的葡萄牙地圖描繪出皮里司令地圖的土耳其製圖師應該是個穆斯林。因為穆斯林對赤身露體非常保守,如果製圖師信仰伊斯蘭教,很可能就不會想在圖上畫裸體。當麥哲倫在該圖問世多年後造訪巴塔哥尼亞時,他驚訝的發現即使天氣寒冷,當地的人仍然裸體,藉著生火取暖,就連在船上還是要生火。因此他就把這個地方稱為──“Tierra del Fuego”「火地」。
最後剩下的動物似乎來自神話中:那是個狗頭人。地圖上有兩段話形容這隻動物:「這裡有……長得像這樣的野獸」,「這種獸類的長度可以達到七開掌(span)……兩眼之間僅有一開掌的寬度(單手拇指指尖與小指指尖張開的寬度)。然而據說這種動物對人無害。」皮里司令地圖相當正確的畫出其他巴塔哥尼亞的動物,並且生存的地點也跟今天一樣。因此如果那種怪物真的存在,我想應該就住在今天阿根廷的聖克魯茲省(Santa Cruz)南部,或是智利的麥哲倫省(Magallanes)北部。地球上真的有過這種怪物嗎?倫敦的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不能鑑定這種動物,所以我就以皮里司令地圖上描繪這種怪物的位置為中心,跟三百公里半徑內的每一家自然科學博物館聯絡。
我第一通電話打到位於麥哲倫省綠川鎮(Rio Verde)的動物相博物館(Museo de Fauna)。答案是否定的,他們還忍不住偷笑。第四通電話打到附近納塔列斯港(Puerto Natales)的遺址博物館(Museo de Sitio),他們的回答就有用多了。
「我要找一種大概是人類身高兩倍的怪物。你們這個區域曾經有過類似的東西嗎?」
「沒錯。」
「你們的博物館有展覽這種動物嗎?」
「有啊。」
「這種動物怎麼稱呼?」
「大樹懶(mylodon)」
大樹懶是一種當時我完全沒想到的動物。後來倫敦的自然史博物館給我許多有關牠的資料。這種怪物其實是兩百多公斤重、南美洲特有的樹懶。一八三四年達爾文在巴塔哥尼亞的白灣(Bahía Blanca)的海灘上發現一具這種動物的骸骨,位置離皮里司令地圖所標的地點不遠。他把骨頭寄給倫敦皇家外科學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的歐文醫師(Dr. Richard Owen),由其重組骨骼。這種動物看起來就像長了個狗頭的巨人,牠抬起屁股,以雙腿與尾部當三角架穩固下半身,揮舞前腿打倒小樹。然後把葉子和果實都吃掉,接著繼續摧殘下一棵樹。據說這種動物可以長到三公尺高,甚至更高,而且一天到晚總是在睡覺。巴塔哥尼亞的原住民冬天把牠們關在洞裡,夏天送出來覓食,牠們的肉嘗起來就像清淡的羊肉。據說三個世紀以前,最後一隻這種「二楞子」(harmless soul)就絕種了。然而,近年來有人在洞穴裡找到應該是當地原住民存放的肉製品,讓人不禁猜想是否還有些這種動物仍然活在巴塔哥尼亞的曠野裡(譯按:大樹懶一般認為已經絕種了幾千年)。
後來我翻到一本宣德五年(西元一四三○年)出版的中國書《異域圖志》。如同書名所暗示的,這本書記載中國人在旅途中看到的珍禽異獸。裡面有張圖就很像皮里司令地圖所畫的狗頭怪物,上面還有註解──整本書就這裡沒翻譯出來──內容是說這種動物是在從中國出發、西行兩年後發現的。
當年中國人發現這種陌生動物時一定很驚訝,而且馬上就想動手抓幾隻當樣本。他們見到珍禽異獸時,都會帶幾隻回中國獻給皇帝以充實其宮苑。鄭和曾經帶回幾隻麒麟(長頸鹿),明成祖驚訝之際龍心大悅。我相信他們在船上就帶了幾隻大樹懶,有兩隻最後活著到了中國。我可以想像中國水手把這些笨拙的狗頭動物引誘出洞,帶到船上,又收集數以噸計的樹葉以供其食用的景象。
皮里司令地圖不僅地形描述正確,對南美洲特有動物的描述也一樣。顯然是真的測繪過巴塔哥尼亞。因此我也幾乎可以肯定畫在西邊的山脈就是安地斯山。從大西洋岸看不到幾百公里外沿太平洋岸北上的這條山脈。最初的製圖師一定在歐洲人到達太平洋或是南美洲以前,就航行過太平洋岸。他們要不然就是通過麥哲倫海峽,要不然就是得跟合恩角永無休止的驚濤駭浪搏鬥。
摘自1421-5新天地
我用皮里司令地圖的敘述以及冰塊的位置將南美洲的南端修正為大約南緯五十五度,也就是浮冰的最北極限。確定火地島的緯度之後,我便可進一步查核皮里司令地圖的南部,並與現代的海圖對照。我馬上就發現最初的製圖師把巴塔哥尼亞高原的東海岸畫得極為精確。海岸主要的地形特徵,好比懸崖、海灣、河流、河口與港口,從北方的白灣到南方的麥哲倫海峽入口都非常相符。皮里司令地圖的製圖師甚至還在陸地上畫了一些動物。
照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說法,這裡是個狂風四起的荒涼之地。「沒有人煙,沒有水,沒有樹...
作者序
導論
十多年前我意外得到一個難以置信的大發現,那是個藏在一張古地圖裡的線索。雖然這個線索不會帶領人找到埋藏的寶藏,卻暗示我們流傳幾百年來,人們想當然爾的世界歷史可能需要大幅改寫。
當時我對中世紀歷史的愛好,正走上了欲罷不能的道路。特別讓我著迷的,是早期探險家的地圖與海圖。我迷上了查閱這些古老的海圖,追蹤他們畫下的輪廓線與海岸線、形狀多變的淺海和沙洲,還有險惡的岩岸與珊瑚礁。我跟隨著潮汐起伏,順著暗潮牽引與季風的推送前進,一層一層揭露這些海圖隱藏的意義。
激發我進行研究的地方,是在美國明尼蘇達州冬季的大平原上。談到發現寓意如此深遠的文件之處,各位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位置,不見得會是這個地方。然而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詹姆士福特貝爾圖書館(James Ford Bell Library)確實收集了相當豐富的早期海圖和地圖。其中有項收藏品特別引起我的興趣。那張圖原來屬於十八世紀末期出生的一個有錢收藏家,湯瑪斯爵士(Sir Thomas Phillips,譯按:稱呼爵位時,一律不是用全名,就是單用他的名)。但是那張圖卻幾乎不為人所知,直到半個世紀前他的收藏品被人重新發現為止。
那張海圖的年代是一四二四年,落款人是一位署名為匹奇嘎諾(Zuane Pizzigano)的威尼斯地圖繪製員。圖的內容是歐洲以及非洲的一部分。我把這張圖拿來比對現代的地圖,發覺他繪製的歐洲海岸線頗為精確。雖然對當時的地圖繪製而言,能有這樣的成就已經難能可貴了,然而其重要性還算不上驚天動地。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圖上幾個最有意思的特別之處。製圖師在大西洋最西邊又畫了四個群聚的島嶼。他給的名字分別是:"Satanazes"、"Antilia"、"Saya"及"Ymana"這四個名字和現代的任何地名完全無關,而在他畫上四個島嶼的區域,也不應該有任何大型海島。這可能只是個很簡單的經度計算錯誤。因為當時歐洲人尚未精通計算經度的困難技術,計算技術直到十八世紀以後才得到突破(譯按:計算經度需要用到精密的時鐘)。但我最初有點困惑的想法,還是把那四個島嶼當成憑空想像,只存在於製圖者的腦海之中。
我又檢查一遍海圖。兩個較大的島嶼著上醒目的顏色:"Antilia"是深藍色,"Satanazes"是英國信箱的那種洋紅色。剩下的地方沒有著色,因此似乎可以推論匹奇嘎諾想要特別強調這兩個最近發現的重要島嶼。圖上標示的名字似乎都是中世紀的葡萄牙文:"anti"是對面,"ilha"是島嶼,"Antilia"是「對面島」的意思。也就是對葡萄牙而言,那個島嶼在大西洋的另一邊。除此之外,這個名字所提供的線索便到此為止。"Satanazes"的意思是撒旦(Satan)或魔鬼的島嶼,這個名字頗為特別。最大的毣ntilia?島上標示了好幾個城鎮,顯示這個島嶼比較為人所知。就只標了五個地名,而且上面還寫著謎一般的"con"和"ymana"兩個字。
這下子我的興致全來了。那些島嶼是什麼呢?它們真的存在嗎?這張圖的年代、來源,以及真實性無可置疑。然而如果這張圖是可以相信的,根據一般公認的歷史,上面標示的陸地的區域,歐洲人卻要到七十年後才會探勘。經過幾個月在地圖室與檔案室裡查閱輿圖與文獻,我逐漸認定"Antilia"和"Satanazes"就是今天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島(Puerto Rico)以及瓜德魯普島(Guadeloupe)。因為其中有太多相似之處,不可能是純屬巧合。但這意味早在哥倫布在加勒比海上岸的七十多年前,就有人正確的測繪過那幾個島嶼。看起來這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發現:新大陸不是哥倫布發現的,即使我們總把他的航海當成歷史的分水嶺。在他之後,以葡萄牙為首,歐洲人開始進行盛大的發現之旅,引領五百多年風騷,無止無休的對外擴張。
我要更多證據以支持這個發現,所以我就請教當時在葡萄牙駐倫敦大使館服務的中世紀葡萄牙文專家山多斯教授(Joao Camilo dos Santos)。他檢視過匹奇嘎諾的海圖,並且把我對"con/ymana"的翻譯修正為「火山在此爆發」。這兩個字放在"Antilia"的南部,剛好就是瓜德魯普島的三座火山所在之處。這裡的火山一四二四年以前是否曾經爆發?我欣喜若狂地打電話詢問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史密森學會(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他們說該島的火山在一四○○到一四四○年之間爆發過兩次。之前休眠了幾百年,之後又有兩個半世紀不曾爆發。此外,當時加勒比海地區也沒有其他的火山活動。我想答案已經出來了:早在哥倫布之前至少六十八年,就已經有人到達加勒比海,而且在當地建立祕密殖民地。這就是我要的確切證據。
山多斯教授引薦我去見葡萄牙里斯本(Lisbone)國家檔案館(Arquivo Nacional Torre do Tombo)的館長。於是在一個美麗的初秋午後,我開始在那裡的後續研究,希望能找到證據補強我有關葡萄牙人登陸加勒比海的直覺猜想。讓我訝異的是,研究的結果恰恰不同於我的期望:葡萄牙人根本沒發現那些加勒比海島嶼。在匹奇嘎諾畫那張海圖的時候,他們根本不知道那幾個島嶼是怎麼回事。然而這些島嶼也出現在年代稍晚一點,製圖者不詳,直到一四二八年才被葡萄牙人取得的另一張海圖上。除此之外,我還找到一份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西元一三九四年~一四六○年)於一四三一年頒發的命令,要他手下的船長去尋找標在一四二八年海圖上的"Antilia"島。如果那個島嶼是葡萄牙人發現的,亨利就幾乎用不著下這道命令了。但倘使發現並測繪兩個島嶼的不是葡萄牙人,又會是誰呢?諸如匹奇嘎諾的這些製圖師又是從誰手上拿到資料?
我繼續研究,追溯早已消逝的中世紀文明興衰。十五世紀初期有能力進行如此航海壯舉的國家一個接著一個,被我從名單上消去。威尼斯這個最早也最強的歐洲海權霸主當時已是一團混亂:老總督病痛纏身,早已權威不再;他的繼承人已經在旁邊等著即位,並且下定決心放棄海權,改尋陸上霸業。歐洲北方的霸主只要有船能渡過英倫海峽就不錯了,遑論遨遊四海。埃及諸王正在陷於內戰之中AB單單一四二一年,就至少有五個速檀2擁兵自重。伊斯蘭世界正在解體:葡萄牙進軍他們在北非的心臟地帶,曾經在亞洲盛極一時,由帖木兒(Tamerlane)打下江山的蒙古帝國也分崩離析。
還有誰會去探勘加勒比海?我想找找看有沒有什麼地圖跟一四二四年的這張圖一樣,標示了在歐洲人的發現之旅以前就已被勘查的大陸。我找得愈是深入,就揭露出愈多意料之外的發現。我驚訝地發現,早在被歐洲人發現的一百年前,就有地圖畫出了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亞高原(Patagonia)和安地斯山脈(Andes)。早在被歐洲人發現的四百年前,南極洲就已經很精確的出現在圖上了。另外還有張地圖畫出了東非海岸,經度完全正確。歐洲人還要經過三個世紀,才能達到如此成就。我也在一張比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早三百年的地圖上看到澳洲大陸。其他的地圖則是早在歐洲人到達的很久以前,就畫上了加勒比海、格陵蘭、北極、南北美洲的東西兩岸等地。
要畫出如此精確的世界全圖,不管是誰都要環繞地球一周。這些探險家必須懂得星座導航,也要設法決定經度,以極小的經度誤差畫出地圖。要想進行這麼遙遠的旅程,就得在海上航行好幾個月,這意味他們能夠淡化海水。我後來還發現他們四處探勘資源,挖掘金屬礦產。這些人也精通農藝,飄洋過海移殖動植物。簡單說,他們改變了整個中古世界的面貌。我彷彿看到了人類史上一連串最神奇的旅程。但是這個旅程卻早已從人類的記憶中抹去。大部分的記錄已經遭人毀棄,他們的成就也被人忽略,最後終至遺忘。
這些發現讓我既驚訝又戒慎恐懼。如果我繼續追查下去,就等於是挑戰某些世界探勘史上最根本的知識。在學校裡,每個孩子都知道那些功勳流傳千古的歐洲大航海家與探險家的名字。好比狄亞斯(Bartholomeu Dias,約西元一四五○年~一五○○年)於一四八七年離開葡萄牙,成為繞過非洲最南端好望角(Cape of Hope)的第一人。他被暴風吹到好望角以南,等他發覺已經看不到陸地時,便下令轉向北航行。結果就繞過好望角,在非洲東岸登陸。十年後達迦馬(Vasco da Gama,約西元一四六九年~一五二五年)追隨狄亞斯的航蹤。他一路航過非洲東岸,橫越印度洋來到印度,為香料貿易打開第一條航路。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西元一四五一年~一五○六年)發現了今天的巴哈馬群島(Balamas)。讓他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見到新大陸的歐洲人AB即使他始終不明白自己看到了什麼,還以為自己到了亞洲。後來他又航海過三次,發現許多加勒比海的島嶼,以及中美洲的大陸。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約西元一四八○年~一五二一年)繼續哥倫布的航程,發現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海峽,至今那個海峽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雖然他沒走完航程,但是他的船隊繼續西行,成功環繞世界一周,凱旋回到西班牙。麥哲倫於一五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菲律賓被殺。
他們都曾受惠於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當年他招賢養士,把葡萄牙西南的領地建設成探險家、製圖師、造船工匠以及儀器師傅的大本營。在這裡,歐洲的造船工藝有所創新,航海儀器與技術不斷發展與進步,盛大的探勘與殖民之旅也得到推動。
當我結束在檔案館的研究時,我的情緒陷入一片迷惑中。一個起霧的傍晚,我閒坐在里斯本海邊的酒吧裡,望著航海家亨利的雕像。我開始明白他的微笑何以如此神祕。因為我們分享相同的祕密:就是他跟隨著前人到達新大陸。我想得愈深入,就愈感到不能自拔。究竟誰是那些發現並測繪新陸地與海洋,事後除了這幾張神祕的地圖,就不留下半點痕跡的航海大師?
某些奇妙的線索洩漏出這些高人的身分。有一張圖把巴塔哥尼亞海岸、安地斯山、南極大陸以及南昔得蘭群島(South Shetland Islands)畫得極為正確。從北到南,由厄瓜多爾(Ecuador)到南極半島(Antarctic Peninsula,譯按:南極面對南美洲最南端突出的半島),距離相當遙遠。需要一整個龐大的艦隊才能勝任。當時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有那樣的物力資源、科學知識、船艦以及航海經驗足以發動如此壯闊的發現之旅。那個國家就是中國。但是想到要證明中國艦隊在歐洲人之前老早就探勘過世界,我就感到頭痛。要為近六個世紀以前的事情挖掘詳盡資料,已經夠讓人望之卻步了。這個工作還有一項重大,甚至是無法克服的阻礙擋在前面,只會難上加難。在十五世紀中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出現重大轉變,朝廷官員刻意毀掉那段期間幾乎所有的地圖與文件。得到那麼多的海外大發現之後,中國非但不擁抱世界,反而轉向閉關自守。任何紀念當年積極對外拓展的記錄,都從檔案之中消失了。
如果要拼湊中國航海發現的輝煌歷史,我就得另尋資料出處。但是光想到要開始動手,我就心生敬畏。一個退休的潛艦艦長,何以能發現這麼多偉大學者沒發現的東西?豈不幾乎到了傲慢自大的程度?然而,雖則跟這個領域的學者專家比起來,我只是個外行人,我卻擁有一項決定性的優勢:一九五三年當我十五歲剛加入皇家海軍時,英國還是個海上霸權,擁有強大艦隊與支援艦隊航行世界各地的基地。在我服役海軍的十七年內,我沿著歐洲大航海家的路線航遍世界。例如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年之間,我指揮皇家海軍「?鯨」號(HMS Rorqual)從中國航行到紐澳海域,經過太平洋到達南北美洲。
我從潛望鏡裡所看到的海岸、峭壁與山嶺,就和早期探險家在後甲板高度的所見幾乎一樣。我很快學到在海平面所見的景象,不必然就是如此。在還沒有衛星導航的時代,我們要用天上的星星指引航路。我看到的星星和那些大航海家所看到的完全相同,我用測量太陽的高度和方位計算位置的方法,正好是他們想要做到的。在南半球,航海人靠著老人星(Canopus,譯按:船底座α)和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帶路。星星在我正要揭露的這個非凡故事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沒有我在海軍學到的星座導航經驗,這本書就永遠也不可能寫出來。而我所得到的發現或許還會繼續埋沒很多年。
不會看海圖的門外漢,不管在別的領域有多少成就,拿到一張地圖或海圖就只能看到一連串很像,或是有點像熟悉陸地的形狀錯誤的輪廓線。有經驗的領航員拿到同一張圖,能推理出來的就多了:最初製圖者航行到什麼地方、航向如何、速度是快還是慢、跟陸地的距離是近還是遠、他的經緯度計算能力怎樣,甚至連日夜測繪的差別都可能看得出來。如果對圖中的陸地與海洋有足夠的認識,領航員還可以解釋為什麼製圖者會把山頭畫成島嶼,為什麼今日的淺灘、珊瑚礁與島嶼當年卻是大片的陸地,以及為什麼有些陸地會被畫成令人玩味的特別大。
我看過一些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初的海圖,上面畫有歐洲探險家當時還不知道的地區。有些地方真的有錯:某幾塊陸地根本不知道畫的是什麼,或是根本形狀不對,還是畫在完全不該有陸地的地方。由於這些圖所顯示的世界抵觸眾所公認的探險歷史,大家把那些圖當作是神話、假貨或者至少是讓人迷惑的異聞。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回過來檢視那些早期的地圖與海圖,隨著我不斷的研究評估,新的中世紀史觀從此誕生。
我的研究證實十五世紀初期,中國艦隊確實進行過多次探勘之旅。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壯大的一次,有四組艦隊(譯按:中國當時稱為分)編組為一個龐大的艦隊群,於一四二一年(明成祖永樂十九年)初出發。完成旅程的船當中,最後幾艘於兩年後的夏秋兩季回到中國。之間他們航行過什麼地方,至今沒留下過記錄。但是那些海圖顯示出他們不只是繞過了好望角,他們還橫越大西洋以測繪匹奇嘎諾一四二四年地圖上的島嶼。此外他們又探勘了南北極、南北美洲,以及橫越太平洋到達澳洲。他們解決了計算經緯度的問題。並以同樣的精確度測繪地圖與星圖。
一直到我五歲為止,我是給一位中國保母帶大的。分手當時的離情依依,如今還深植在我的心頭,這些年來我也曾多次回到中國。然而儘管我對這個偉大的國家充滿興趣,我的中國史程度卻上不了檯面。在我著手探索中國艦隊不可思議的旅程以前,我得先讓自己熟悉未知的古中國。對我自己來講,這件事的本身已經算是一趟發現之旅了。對於這個偉大的民族,我想我就跟一般的西方人一樣徹底無知。我學得愈多,就對古中國的光榮以及文化的深度愈感敬畏。那個時候的中國對科技及世界的了解,比起同時期的歐洲是如此先進,以至於歐洲要經過三、四個世紀,有時甚至要到五個世紀以後,才能趕上古中國。
對中國的偉大文明略知一二以後,我花了許多年走遍全球,追蹤中國人的探勘之旅。我研究各地的檔案館、博物館以及圖書館,參觀中世紀末期所留下來的紀念碑、城堡、宮殿與主要海港。到各地的海岬、珊瑚礁、灘頭以及孤島察看。不管走到哪裡,我都會發現更多支持我的論點的證據。我發現一些逃過劫難的中國文獻與航海針位記錄,還有幾份第一手報告:兩份是中國歷史學家寫的,另一份的作者是個歐洲商人。其餘資料的作者則是跟隨中國的航程前進,並且發現前人的蛛絲馬跡與遺留文物的第一批歐洲探險家。
他們留下的證物至今仍不難發現。好比中國瓷器、絲織品、祭品、文物,以及中國水師將領用來紀念功績的石碑。這些遺物都可當成他們輝煌成就的紀念碑。此外非洲、美洲、澳洲與紐西蘭的岸邊仍可找到中國的船隻殘骸。直到第一批歐洲探險家來臨時,仍有很多中國人從原產地帶來的動植物在異域繁衍。這些證據都在在證明那些地圖的真實性,以及我最初的猜測。那些地圖所記載的驚人知識,一直都沒有消失,大家都可以看見,但是許多傑出的中國歷史學家卻不曾察覺。並非他們不認真,而是因為他們不懂星座導航以及海洋。如果我看到的東西他們沒看到,只不過是因為我懂得怎麼看那些描述一四二一年到一四二三年之間中國艦隊航行的方向與範圍的海圖罷了。
哥倫布、達迦馬、麥哲倫、庫克船長在他們之後得到相同的「發現」。但他們都心知他們是在跟隨前人走過的路線。因為在他們出發探索「未知」以前,船上也帶了好幾份中國海圖。容我硬套一句牛頓的名言:如果他們能看得比別人遠,那是因為他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註釋
1.譯註:由十九世紀英國科學家史密森(James Smithson)捐贈的遺產建立。目前包括十六座博物館與畫廊,一座動物園,以及許多科學研究機構。
2.譯註:有些人把"Sultan"譯成「蘇丹」,這是很不適當的。蘇丹(Sudan)是非洲的一個國家,名字源於阿拉伯文的「黑色」;「速檀」則是中亞與
中東許多民族稱呼統治者的頭銜。由於古代各國腔調不一,光是《明史》就有「速魯檀」、「速檀」跟「鎖魯檀」等譯法,其他朝代也另有譯名。
這裡使用「速檀」,但其他書籍也有用「素檀」的。
結語:中國的遺產
從日本到非洲,乃至於世界各地,中國全盛時期威震海內,澤及萬民的遺產並未完全消失。從麻六甲到神戶,中國式的佛教建築裝飾亞洲的天際線。從非洲到日本,到處都還可以發現明朝的中國絲綢;從澳洲到滿洲,則是中國光輝燦爛的青花瓷。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墳墓也留著當時中國的玉器。就連最漫不經心的遊客,到了東南亞照樣不會錯過無所不在的中華文化遺產。從蘇門答臘到帝汶島到日本,社會仍然連結在中國傳來的貿易、宗教以及文字之下。在東西南北四千公里內,中華帝國的影響力猶在,而且影響的深度驚人。
中國文化的深刻就如同其博大一樣難以想像。三千年前的中國人就已經是青銅鑄造的大師,同時還擅長簡潔有力的雕刻。到了秦朝,當時的陶器莊嚴尊貴到世上無出其右,從秦始皇陵的兵馬俑,其馬俑之優雅與兵俑之流暢便可見一斑。到了唐朝,當我們歐洲人的祖先仍然還是衣衫襤褸的蠻族時,富裕的中國人便以裝飾龍鳳的金盤用餐,從雕刻駿馬的玉杯中飲酒。白玉海碗裡裝著水果,穿著絲綢的商人婦身上噴了含蓄的波斯香水。她們的耳朵、喉嚨和手腕還裝飾了金玉製成的首飾。
不管是人能想到的什麼行為,中國人都有幾千年的經驗與專業知識。在西元前三○五年(譯按:東周戰國時代,周赧王十年),帝王便下詔要求人民保育土地,並且實施輪耕。明成祖朱棣的巨大寶船跟偉大探險也是八百多年來發現之旅的最高鋒AB宋朝時代就有船到了澳洲。當鄭和出發時,中國已經和印度做了六百多年的生意。甚至就算談船的大小,鄭和的每艘船還是遠遠不及兩百多年前的忽必烈艦隊。當時中國的科技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好幾個世紀,光是從修築長城,就可看出中國軍事科技與都市計畫的能力。世界上有這麼多古文明,中國有了這條提供穩定和保護的長牆,成為唯一的倖存者。這是中國最了不起的國家象徵,也是個歷史的紀念碑,紀念中國與中國人的屢敗屢起和亙古長存。
雖然幾百年來中國的航海記錄相繼遺失或遭毀棄,有種最實在也最明顯的證據至今仍隨處可見:中國人帶去新天地,以及從新天地帶回中國或是東南亞的動植物。中國對文明最大的貢獻可能就是植物的培育與傳播。
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總以為哥倫布在一四九二年「發現」南北美洲,是植物在世界各地傳播的開端;而英國在特拉法加(Trafalgar)海戰大捷之後的海上霸業興起為其加速。但是即使維多利亞時代花了不少工夫收集植物,在哥倫布的第一次航海之前,大部分重要的糧食作物就早已經傳遍全球了。歐洲人不但有海圖帶他們去新大陸,他們到達後還發現最重要的作物已在那裡欣欣向榮。在夏威夷,至少可以找到來自於印度、亞洲、印尼、美洲,甚至是非洲的重要經濟作物。當歐洲人第一次踏上夏威夷的土地時,這裡早就長了甘薯、甘蔗、竹子、椰子樹、竹芋、山芋、香蕉、薑黃、薑、卡法樹(kava)、麵包樹、桑樹、葫蘆、木槿、石栗樹……。這些植物沒有一種是原生的。
從玻里尼西亞群島(Polynesia)直到半個地球外的復活節島都可以看到這種模式。歐洲人最初在的的喀喀湖(Lago Titicaca)發現一種叫做托托拉(totora reed)的蘆葦,在南美洲發現番茄、野生的鳳梨和甘薯,在中美洲和北美洲發現菸草,在非洲發現葫蘆,在中美洲發現木瓜,在東南亞發現山芋,以及在南太平洋發現椰子樹。最先到達加勒比海的歐洲人也見到了椰子樹;麥哲倫還在菲律賓補充了不少原產於中美洲的玉米;加利福尼亞有中國的金櫻子點綴;南美洲也有亞洲的雞。南美洲和澳洲之間至少有九十四種屬名相同的植物。1此外非洲西部和美洲二地的熱帶區域也有七十四屬,共一百零八種相同的植物。
有人主張這些植物可以靠洋流、風或是鳥類帶著種子,自然的傳播出去。椰子能漂浮在水上,理論上可以從南太平洋流過印度洋、南大西洋、北大西洋,最後到了加勒比海。有些椰子真的在島嶼間漂流,也有些種子跟孢子也確實藉風力傳播,但是要說所有的植物都經由這種管道傳播是很荒謬的。因為一提到玉米和甘薯,這種論證就完了。兩種都是不會漂浮的,甘薯更是笨重到不可能被鳥叼來叼去,周遊列國。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來,許多著名的植物學家研究糧食作物的起源。隨著植物分類學的進步,對於這些植物的野生親屬與發源地的理解也有了極大的轉變。椰子樹是一個例子,早期的歐洲探險家在中美洲的太平洋與大西洋沿岸都發現這種植物。
過去一度有人認為椰子樹(Cocos nucifera)源自於新大陸,因為這個地方還有另一種同屬的植物。如今椰子樹卻自己一個種就構成一個屬,而且最近的親屬也變成在非洲。從以上資料再加上椰子的化石記錄,還有這種植物在東南亞的分布範圍,顯示出椰子樹可能起源於西太平洋,然後越過大海由西向東傳播,而非由東向西傳播。2
分析非洲與南美洲的共通植物物種,以及分析南美洲和澳洲的共通植物物種,可以發現它們都是順著風和洋流移動的。換句話說,就是坐船被人帶著走的。過去沒有玻里尼西亞群島的船離開太平洋進入印度洋或是南大西洋的記錄,這些物種的遷徙又先於歐洲人的發現之旅。只有一個國家可以運送這麼多種動植物環遊世界。載運植物和種子的顯然是中國船,在沙加緬度的帆船裡就可以發現它們。而且這些植物和種子環遊世界的傳播路線也剛好符合從中國經由東南亞到印度,然後再到非洲,從這裡越過南太平洋到南美洲,最後到達澳洲。
稻米是中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或許也是世界上變化最多、適應力最強的作物之一。中國人培育出能長在乾燥的山坡上的旱稻,也有要浸泡在水中的水稻。有些稻子要好幾個月才能成熟,有些只需兩個月。還有些對溫度變化敏感,有些則是對日照敏感。甚至有些雜交種耐鹽的程度高到可以栽種在海埔新生地。稻米是種很好的糧食作物,吃起來口感不錯,而且用黃豆製品調味後營養更豐富。它容易儲藏,烹煮方便。也是同樣面積的農地上,所能栽培的各種穀物當中總熱量最高的。直到二十世紀,每一公頃的土地拿來種稻米,產生的熱量是其他任何農作物的七倍。3因此中國也是世界上耕作效率最高的國家。
中國的十幾億人民仰賴稻米為生。這是養活人口眾多的亞洲最好的作物。稻米在亞洲,地位比麵包在歐洲的地位還高。中國形容失業,就叫做「丟了飯碗」;結婚與訂定買賣契約則會相互敬酒,這酒也是米釀造的。西方國家婚禮時會灑五彩的碎紙,用來代替米討個吉利。日本兒童仰望夜空時,會說月亮上有玉兔搗年糕,同樣也是米製品。
明朝時代,中國向太平洋島國出口稻米,主要穿越今日印尼的望加錫海峽(Selat Makassar,譯按:在蘇拉威西島和加里曼丹島﹝Karimata﹞之間)。寶船艦隊當中也有糧船運送米糧,沙加緬度的帆船裡就發現了稻米。4然而中國人也進口植物,我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人運用外地植物時的巧思。從中國到印尼的東南亞氣候區是穀類植物的一個重要來源。我們可以推論小米、稻米,以及山芋等重要農作物的馴化是在這個區域發生的。後來從印度引進中國的作物包括甘蔗、香蕉、薑、幾種柑橘類的植物,以及棉花。但是最驚人的例證便是鄭和的艦隊從美洲帶回來的玉米。
僅次於稻米,玉米是世界上產量最高的植物。同樣的土地,比起小麥收成至少高過三倍。更不用說玉米既可以種在乾燥的沙漠裡,也可以種在潮濕的叢林中;從海平面一直到三千六百公尺高。玉米起源於中美洲,但是最早到菲律賓的麥哲倫卻在菲律賓買了一大堆玉米,而中國殘存的記錄則說鄭和的艦隊運回「穗子極大的穀物」。因為玉米的根部長得很深,下大雨時不會被水沖走,而且種在山坡上可以將霜害降到最低,特別適合中國的山地居民栽植。對中國西南的苗人而言,引進產量高的玉米是族人的一大福氣。如今玉米這種世界上第三重要的農作物已經傳遍亞洲,並成為許多非洲國家的主要食物。
中國人攜帶的第三類食物是芋頭、山芋以及甘藷(Ipomoea batatas)。甘藷起源於南美洲濕熱的氣候下,之後便成為溫暖的副熱帶國家的重要根部作物。當庫克船長到達紐西蘭時,毛利人已經以甘藷作為主食。他們管甘藷叫"umara",和祕魯沿海的利馬(Lima)附近仍使用的名稱"umar"幾乎一樣。山芋(屬名為Dioscorea)起源於非洲和東南亞。然而在歐洲人初次造訪夏威夷時,就已經長在那裡了。芋頭起源於東南亞,但也在歐洲人來臨前,早已到了夏威夷。芋頭屬於天南星科(arum, araceae,譯按:原文aracheae拼字有誤),跟馬鈴薯一樣都是富含澱粉質與澱粉的植物。從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到北太平洋的夏威夷都有人種植芋頭。大溪地機場的出境大廳門口就有歡送遊人的芋頭池塘。
稻米、玉米、甘薯、芋頭和山芋起源於不同的地方,是熱帶與亞熱帶地區人口的主食。這些植物的傳播對人類有無比的價值,讓人得以在任何土壤跟任何氣候環境下培育並收穫穀物。
中國人也對其他經濟作物的傳播貢獻卓著。扣掉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蠶絲生產與出口地,中國也是運用其他紡織品的先驅。棉花的歷史可以從幾千年前的印度河谷地講起,這種植物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經濟作物,產值佔世界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五。長年來科學家和學者對南美洲棉花的基因組成很納悶。但是經過一連串的繁複實驗,如今專家同意美洲棉花的祖先之一絕對來自於亞洲。當歐洲人到達美洲時,他們所發現的美洲野生棉花有一組基因來自印度。棉花從印度傳到廣東,八世紀時已有人工栽培,元朝時開始大量生產。明朝的艦隊出海時,就載運了大量的棉花。5柯枝國王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對永樂帝表示無比的感激:「何幸中國聖人之教,沾及於我。乃數歲以來,國內豐穰,居有室廬,食飽魚鱉,衣足布帛。」6
椰子是核果類的作物中最重要的一種。雖然椰子的發源地是印尼的島嶼,歐洲人最初到加勒比海地區以及中美洲的太平洋岸時就發現當地有椰子。如今菲律賓、印度、印尼、斯里蘭卡,以及加勒比海地區共栽種了三百五十萬公頃的椰子樹。椰子樹生長在熱帶,卻也可以忍受一點寒冷。除了提供好吃的椰肉和椰子汁外,從乾燥的白色椰肉分離的椰油幾百年來也被人用於烹飪,以及製造肥皂、化妝品,還有潤滑劑。搾油之後的乾椰仁也可以磨碎製成含有豐富蛋白質的粉末,用來餵食家畜或是家禽。椰子樹的樹幹可以當屋頂的大梁,椰子殼的纖維可以搓成繩索。明朝的艦隊就是椰子殼纖維的大買家。
香蕉來自東南亞,但是早期的歐洲探險家也在夏威夷見到香蕉。後來這種植物還傳播到印度、非洲和美洲的熱帶區域。香蕉和葡萄、柳橙、蘋果並列為世界最重要的水果農作物。在熱帶區域,人們常吃香蕉的一種近親,就是含有大量澱粉的芭蕉。鳳梨起源於氣候濕熱的南美洲大西洋岸,然而哥倫布卻在一四九三年他第二次航海到西印度群島時見到鳳梨。中國寶船艦隊四海遨遊的證據,的的確確正在我們四周遍地生長茁壯。
在長期追尋十五世紀的中國大航海家之初,有一天我站在一座紀念碑前,那是鄭和立在長江口的一塊石碑(譯按:本段引文為福建長樂縣的《天妃之神靈應記》。可能是作者遊覽世界各地,見聞過廣,有點弄混),我站在紀念碑前閱讀碑文。寶船艦隊的傳奇性的第六次航海,在整個中國大陸上幾乎就只留下這唯一的物證了:
皇上……命和等(鄭和、周滿、洪保、周聞、楊慶)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奉使西洋……大小凡三千餘國7,涉滄溟十萬餘里。
在我開始這段長達數年的發現之旅時,我曾對這塊石碑感到困惑。如今旅程結束,我又回到這裡,深信自己已經得到了證據,足以推翻西方世界長期公認的歷史。我發現了由鄭和、楊慶、周滿、洪保與周聞率領的中國艦隊,在傳奇性的第六次探險中曾勘查世界每一塊大陸的許多證據。他們航行經過六十二個群島,共有一萬七千多個島嶼,並且測繪了數萬公里的海岸線。鄭和自稱造訪過「大小凡三千餘國」似乎是對的。中國艦隊橫渡印度洋到達非洲東部,繞過好望角到綠角群島,又經過加勒比海到北美洲與北極,又南下合恩角跟南極、澳洲、紐西蘭,再橫渡太平洋。整整十萬里的航行,只有到了南極洲,寶船才需要逆風或是逆流航行。
在永樂十九年到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一年到一四二三年)的大航海之前,明成祖已經把整個東南亞,還有滿洲、朝鮮、日本都納入了朝貢中國的領域內。絲路的東側從中國開始,最遠又開通到波斯(今伊朗)。整個中亞對中國俯首稱臣,印度洋也成了中國海運的勢力範圍。永樂十九年到二十一年的寶船艦隊擴展了這個本來已經很廣大的貿易帝國。他們在從加利福尼亞到祕魯的南北美洲太平洋岸建立永久殖民地,又在澳洲、印度洋各地乃至東非開始屯墾。他們在太平洋上設立多處補給站,以連結美洲與中國,其次則連結澳洲、紐西蘭和中國。他們的基地涵蓋範圍甚廣,分布在:從復活節島經過馬克薩斯群島(Marquesas)和土木土群島一直到皮特凱恩島(Pitcairn Island),卡洛琳群島的大溪地、西薩摩亞(Western Samoa)的沙來島(Sarai)、東加群島(Tonga)、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的聖克里斯托伯島(San Christobal)、南馬杜爾島(Nan Madol)、雅蒲島(Yap)、托比島(Tobi),以及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的塞班島(Saipan)。至今在這些島嶼上還經常可以發現留下的石造營房、簡易碼頭、房舍、水池,以及天文臺。鄭和的龐大艦隊和他們的補給隊連結了這些殖民地和補給站。
對於從永樂十九年到二十一年,這兩年「失蹤」期間的中國航海旅行,我的相關主張是奠基在疆理圖、皮里司令地圖、若茲海圖、甘地諾地圖、瓦德西穆勒地圖,以及匹奇嘎諾海圖的真實性上。至今這些圖的真實性無人挑戰。過去有人懷疑文蘭地圖,但是如我所證明的(見第十四章),我相信這張圖已經通過真實性的考驗了。皮里司令地圖、若茲海圖,以及甘地諾地圖畫出了整個南半球,從南極到赤道間,涵蓋幾千萬平方公里以上的海洋,成千上萬個島嶼,以及數萬公里的海岸線。他們所畫的陸地,只可能是在歐洲人的發現之旅以前,曾經被航行過南半球的艦隊勘查,而當時唯一的可能就是中國人的艦隊。
偉大的中國航海旅行也有豐富的物證。菲律賓班丹南島的沉船讓我們清楚的看見中國跟印度洋、美洲,以及東南亞諸國貿易的盛況。東非海岸、波斯灣、澳洲等地發現過明朝的青花瓷,北面一直到開羅都發現過明朝的絲織品。寶船的殘骸分布在紐西蘭和澳洲南部的外海,而那些國家也有許多中國人到此一遊的其他證據。越過印度洋,石碑被樹立在綠角群島、紐西蘭,以及美國南部。中國雞流傳到南美洲,美洲的玉米又流傳到中國。在拉姆群島、澳洲的達爾文、紐西蘭的魯普克海灘都發現過祭品。
就是因為證據具備如此的深度、廣度,還有多樣性,永樂十九年到二十一年之間偉大的中國航海旅行才如此可信。澳洲的一艘紅木沉船可以解釋為被暴風吹離航道的印度商船,但是許多沉船加上中國人用的祭品、陶器,以及船錨的形式,述說的就是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了。況且這個故事還有原住民傳說與壁畫作為旁證。更不用講還有在歐洲人到達澳洲的幾百年前,就已經畫好的大堡礁海圖。散見印度洋各地的明朝瓷器也許是葡萄牙帆船殘骸裡的船貨,但是這些證據也從來不是個案。最早的葡萄牙探險家記錄了他們發現黃皮膚的人、中國人的祭品以及絲織品。而且在葡萄牙人可以精確的勘查印度洋以前,就已經有畫了數百萬平方公里以上海洋的詳盡海圖。對於南極洲為什麼在歐洲人到達前四百年就出現在海圖上,至今只有一些文人筆下的怪力亂神之說,例如丹尼肯(Erik von Daniken)的「外星人降臨」,還有哈普古德(Charles Hapgood)的「法老王時代以前的埃及文明」。
麥哲倫在出海之前,就已經看到描繪在一張海圖上的「麥哲倫海峽」與太平洋了。也就是說在他之前,曾有人穿越那個海峽,並且橫渡太平洋,同時在任何歐洲人見識到巴塔哥尼亞高原土生土長的動物之前,就先畫下牠們。珍禽異獸的圖片(西元一四三○年出版,譯按:指刊印於宣德五年的《異域圖志》)、路途上隨處可見的中國文物,以及倖存的中國海圖所畫的大陸,在在證明這裡所說的「有人」是指中國人。中國人當然有船也有專門技術,同時也不缺資源和時間進行這種了不起的環球航行。這就跟當時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這點一樣的毫無疑問。
我的各項主張自然很多人不敢相信,但是撇開心理因素不談,這樣的主張並沒有任何不合理之處。中國人的航海歷史比歐洲人更久遠,也更豐富。永樂十九年當明成祖的艦隊啟航時,他們已經累積了至少六百年海洋探險與天文導航的傳統。而在狄亞斯與麥哲倫出海時,葡萄牙人到了赤道以南,就不知道該怎麼辨認方向了。沒有中國的經濟力量,就不可能有宏大的造船計畫,造出鄭和艦隊的寶船以及負責補給的各式船隻。卡布拉爾、狄亞斯,以及麥哲倫的快速帆船,看起來就像是在中國船舷側的登陸用小艇。直到近四百年後拿破崙建造他的旗艦「東方」號(L'Oriente),西方才有足以和明朝稱霸海上時的寶船差不多大的木造船隻。就連特拉法加海戰時所用的歐洲戰艦,都難以和中國帆船的大小、航程,以及火力相抗衡。納爾遜(Horatio Nelson)的艦隊最強時不過三十艘船,一萬八千名水手。跟鄭和動輒上百艘船,兩萬八千名水手的艦隊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他的寶船有英國皇家海軍「勝利」號(HMS Victory)的兩倍長,三倍寬。同時還有更好的損害管制與後勤補給,可以在海上航行更久,必要時甚至可以維持好幾個月。
中國艦隊測繪了整個世界,他們懂得用月蝕決定經度,同時他們能夠以比對海圖解決其餘的經度誤差,並且完成至今已知的第一張世界地圖。但是這些知識是用極大的代價換來的。洪保的船只有四艘返回中國,周滿則僅僅剩下一艘船。光是他們的這兩支艦隊,就損失了至少五十艘船。人命的損失也一樣高:周滿的艦隊在永樂二十一年九月(西元一四二三年十月)返航,九千名水手只回來了九百人。艦隊最初的成員有四分之三應當已經死亡或是被遺棄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如今世界各地已經找到二十四處沉船遺跡,更多的沉船以及幾千噸寶物有待我們發現。總有一天,大海必然會給我們更多的證據。人命與金錢的損失無以計數,就連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也無法負擔下去,但是明成祖的水師將領卻完成了皇帝託付的任務。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成就。
明成祖打算發現並且測繪全世界,同時透過貿易與外交政策,讓萬民接受儒家思想的偉大計畫原來可能成功,因為如今整個世界都臣服在中國的腳下──或者在永樂二十一年秋天,一小群寶船艦隊倖存的船隻施施然回航時,水師將領心裡應當是這樣想的。但是當他們回來以後,卻發現中國已經變了,世界也不一樣了。明成祖成了個垂死又心碎的老人,官僚正在摧毀他差點兒就創造出來的世界性帝國的基業。從此再也沒有遠人朝貢,沒有偉大的科學實驗,更不會有貿易與發現的遠航壯舉。中國進入了閉關自守的漫漫長夜。艦隊的太監司令官遭到解編,他們的船隻要不然是拆掉,要不然就在停泊處等著自然朽壞。地圖、海圖以及成千份記錄他們的功績的寶貴文件被毀棄。明成祖的霸業,沒人當一回事,最後終於被人遺忘。
歷史上最有意思的「萬一」之一,便是萬一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西元一四二一年五月九日)閃電沒有擊中紫禁城,萬一大火沒有沿著御道延燒,將皇帝的宮殿和龍椅化為灰燼。皇帝最寵愛的妃子還在世嗎?他會保持雄心壯志嗎?他會命令鄭和的船隊持續其旅程嗎?他們會繼續在非洲、美洲,以及澳洲建立永久殖民地嗎?今天的紐約會不會叫做「新北京」?雪梨的「唐人街」會不會變成「英人街」?新大陸上會不會處處佛寺,而非成為基督教的領域?
和中國人有教養的「宣德化而柔遠人」比起來,基督教徒對被殖民者的態度簡直就是殘忍,甚至是野蠻。皮薩羅打敗印加王國,得到祕魯的手段是毫不留情的血腥屠殺五千名印地安人。換成今天,他早成了戰犯。
葡萄牙人利用中國的地圖學,帶領他們到東方。然後他們偷了印度人和中國人幾百年來發展的香料貿易。誰想阻擋他們,就是死路一條。當達迦馬到達古里時,他要手下先把印度俘虜遊街示眾,然後把他們的手、耳朵、鼻子都砍掉。所有割下來的肉都堆在一艘小船上。史學家科瑞亞(Gaspar Correa)這樣描述達迦馬的下一步行動:
當所有印度人都行刑後(原文如此),他下令把這些人的腳綁起來,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手可以鬆綁了。為了避免他們用牙齒鬆綁自己,他要手下用棍子把這些人的牙齒都打掉,還要他們吞下去……8
有個婆羅門到古里為他們請命。「勇敢的」達迦馬把他的嘴唇和耳朵割掉,縫上狗的耳朵代替。
看起來鄭和的艦隊再次出海,應該就會到這世界上他們還沒蒞臨和測繪的地方──歐洲。北京的亂象斷了任何再次出海的希望。但是誰又能說得出在一四二○年代,中國的寶船出現在歐洲的海平面上,歷史將會如何演變?唯一勉強能確定的是:如果繼明成祖之後的皇帝不落入畏懼外國而閉關自守的困境,中國將成為世界的主宰者,而輪不到歐洲。
如今紫禁城仍舊巍巍聳立,成為明成祖雄才偉略的象徵。但是改以勇敢的騎士雕像──它就安放在亞述爾群島的柯佛島火山頂端,傲視懸崖下大西洋的滾滾浪花,當作這位「戎馬一生的皇帝」的墓誌,豈不更適合?這尊雕像充滿激情的手指西方,面朝扶桑之地,也就是他手下勇敢又老練的船員所發現的美洲大陸。當中國開始自我封閉,背棄明成祖的雄心壯志時,其他人,特別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便開始填補這塊空白。幾百年內,他們沉浸在原本屬於別人的榮耀中。如今該是我們為歷史平反,將功勞歸於應得之人的時候。
主張中國人先探索新世界和澳洲,不代表就是減損狄亞斯、哥倫布、麥哲倫,還有庫克船長等人的功業。這些勇敢又老練的探險家永遠不會被人遺忘,但現在該是推崇那些沒沒無聞太久的其他人的時候。中國艦隊在狄亞斯之前六十六年就繞過了好望角,在麥哲倫之前九十八年就穿越了麥哲倫海峽,比庫克船長早三百年勘查澳洲,比歐洲人早四百年勘查南北極,比哥倫布早七十年勘查美洲。偉大的水師將領鄭和、洪保、周滿、周聞,還有楊慶也值得紀念與褒揚。因為他們不但是最先的,也是最勇敢、最不畏艱難的。跟隨他們前進的那些人,不管成就有多麼大,都是效法他們而航行。
我花了多年時間研究這些偉大的中國航海旅行,終於在二○○一年的聖誕節告一段落。我把初稿寄給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並且根據他們的指正修改內容。到了二○○二年三月十五日,我已經準備好要在皇家地理學會發表自己的發現。這場演講在人口總共二十億的三十六個國家轉播,之後我便得到世界各地更多研究者所提供的旁證。有些資料已經收錄在這本書裡頭,還有很多也將不斷湧入。諸如沙加緬度的帆船、比麥尼群島的沙丘,以及羅德島州的塔樓之類的有趣發現,正等待更全面的調查與評估。我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而它將由全人類共同分享。
註釋
1.Barbara Pickersgill, '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ivated Plants in the New World', Nature 268(18), pp. 591-4.
2.R.A. Whitehead, Evolution of Crop Plants, Longman, 1996, pp. 221-5.
3.F.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sations, trs. R. Mayne, Penguin, 1994, pp. 158-9.
4.卡尼(Judith A. Carney)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地理學教授,他寫了一本引人入勝的書Black Rice: The African Origins of Rice
Cultivation in the Americas (Harvard UP, Cambridge, Mass., 2001)。這本書講的是稻米引進南北美洲的真實故事,並且主張一般人所信
「歐洲人把稻米引進非洲西部,再帶到美洲」的通說有根本上的謬誤。
5.Roderich Ptak, 釢hina and Calicut in the Early Ming Period: Envoys and Tribute Emissaries*,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9, St 447,以及Ptak教授與筆者之私人信件。
6.冊封柯枝國的碑文,見《明太宗實錄》,卷一八三,轉引自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Oxford UP, Oxford, 1996, p. 145.
譯註:原文出於《明太宗實錄》卷一八三,永樂十四年十二月丁卯。
7.譯註:各書籍流傳的中文版本與原石碑之照片寫的都是「三十餘國」,作者根據的英譯本可能有誤。
8.Gaspar Correa, The Three Voyages of Vasco da Gama, trs. H.E.J. Stanley from Lendas da India, 1869.
譯後記
玉米何時引進舊大陸,始終是個爭議問題。傳統理論認為哥倫布發現美洲後玉米才傳到歐洲;但也有很多人主張玉米早就到了舊大陸,哥倫布絕非最早發現美洲的非美洲人。
關於玉米的發現,每個學派都可以提出證據,這本書自然也提出了一些。近年來大陸學者也提出很多理論,例如有人主張元曲曾出現過吃玉米麵的段落。筆者並非農業專家,對玉米更是所知甚淺,純粹是個罐頭玉米的消費者。以下我會提出一項權威的證據,用來證明早在西元前八百多年,玉米就已傳入中東。接下來我會拆穿自己的理論。
詹姆士國王欽定本《聖經》(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是英語世界最為人所熟知的《聖經》版本。一六○四年,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召集了五十幾位學者翻譯這個版本的《聖經》,七年後出版。這個版本歷經時代考驗。將近三百年的時間,英語國家天主教會以外的基督教會以此為最主要的《聖經》版本。
在欽定本《聖經》的舊約《列王紀下》四章四十二節可以找到這樣的記載:
And there came a man from Baal-shalisha, and brought the man of God bread of the firstfruits, twenty loaves of barley, and full ears of corn in the husk thereof. And he said, Give unto the people, that they may eat.
有一個人從巴力沙利沙來,給神人帶來初熟穀類作的餅,二十捆大麥,和一些帶葉子的整根玉米。他說:「分給眾人,好叫他們喫!」
《列王紀下》的背景這裡不多談。總之故事發生在西元前八百五十年左右,猶太人南北分裂時北方的以色列國。寫作時間約在西元前五百五十年,猶太人逃出巴比倫之際。從以上的片段可以看到,有人帶著玉米去找某位神人。此處使用的片語"Full ears of corn in the husk"可以解釋為包在葉子裡的整根玉米。可見當時猶太人已經在吃玉米了。英文版的舊約《聖經》裡處處可見"corn"這個字,好比在《創世紀》裡面"corn"一共出現十六次。後頭出現的更是不計其數,但多半只用了"corn"這個字。《列王紀下》的用法應當是最完整的,很容易可以看出就是玉米。由此可知玉米很可能在西元前八百多年,就傳到了中東。即使這個段落的玉米出自作者的捏造,玉米引進最晚也不會遲於西元前五百餘年。《聖經》更早的地方也多次談到玉米,只是因為沒這麼清楚,在此不列入證據。
眾所周知,《聖經》的翻譯相當嚴謹,錯誤極少出現。欽定本更是由十七世紀的學者專家參考當時可考證的原文,由在英國廣泛流傳的丁道爾(William Tyndale)等譯本修訂而來的。可說是經過千錘百鍊。欽定本的文字風格影響後世數百年的英國文學。很多人靠著研讀這本《聖經》學會遣詞造句,欽定本翻譯的《聖經》成語也豐富了英文的內涵。因此權威性自然毫無疑義。玉米在西元前九世紀或是六世紀便已經傳入舊大陸,自然也是證據確鑿。
很不幸的,前面所引的段落剛好是欽定本容易混淆今日讀者的地方之一。美式英文的"corn"現在最主要的意義是玉米粒,原來卻是泛指多種穀類種子,例如大麥、小麥、裸麥還有玉米之類;"ear"也可解釋為整條麥穗或是整根玉米。一七六八年初版的《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dia Britannica)開宗明義就列出九項穀類,其中玉米擺在第七項。這個單字會專指玉米,是因為美國盛產玉米,美式英語流傳廣泛的緣故。《牛津英文大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一直到第二種解釋的第五小項才舉出"corn"可以專指玉米,還特別聲明這是美國特有的用法。但即使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玉米在美國都還沒獨佔這個字。好比一九一三年版《足本韋氏大辭典》(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仍然把"corn"解釋為「某幾種穀類的種子」,1玉米還列在最後面。一九一一年版的《大英百科全書》更言明這個字在英格蘭主要指小麥、蘇格蘭和愛爾蘭主要指燕麥、在美國主要指玉米。2
所以欽定本講的「玉米」應該只是「麥子」罷了。十七世紀的讀者很清楚這個字是指麥粒。而"full ears of corn"也該解釋為幾條麥穗。舊約《聖經》的原文是希伯來文。如果古代這個語言的流行區域沒有玉米,自然也不會有玉米的辭彙。歐洲原來也沒有玉米,因此英文也沒有玉米這個單字,而是傳入後再把別的字搶過來用。電腦是二十世紀的發明。在電腦發明以前,英文就有"computer"這個字,意思卻是「計算數字的人」。因此希伯來文的"karmel"翻譯成英文的"corn",自然不帶「玉米」的意義。
有些學派認為翻譯《聖經》時,每個字、每個詞,都該有統一的翻譯方法。例如某個字先前譯成「律法」,後面就不能譯成「法律」。如此讀者才能真的了解原文意旨。欽定本編譯之用心,自然不在話下。但是這個版本的特點之一,就是為了避免文字生澀,譯文不要求緊盯《聖經》原文。因此《聖經》中雖然多次出現"corn"這個字,卻是從不同的希伯來文原文翻譯而來的。這段經節把希伯來文的"karmel"譯成"full ears of corn"(整條麥穗),其他地方還曾翻為"green ear"(新收成的麥穗),別的地方出現的"corn"還是其他單字。
因為古希伯來文有些生字已經難以考證,不同的時代,也有不一樣的解讀。欽定本把希伯來文的"tsiqlon" 翻譯為"in the husk"(在穀殼裡)。後來的學者參照其他相近語言的研究,多半認為這個整部《聖經》裡只出現一次的字,正確的意義應該是「在袋子裡」。
舊約《聖經》的原文是希伯來文。西元前三世紀,希臘文成為共通語文。猶太的十二個支族便各推派六個學者把《聖經》翻譯為希臘文,翻譯出來的版本現在稱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據說當時每個人在自己的小房間裡翻譯。七十二天後,交出七十二套完全相同的《聖經》譯本。西元五世紀,聖耶柔米(St. Jerome)又主要根據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譯出拉丁文的武加大譯本(Vulgate,這個字的意思是通俗譯本,拉丁文是當時的「普通話」)。這些版本各有些許錯誤。由於後代的《聖經》翻譯者參考他們的譯文,有些錯誤也影響到之後的版本。
希伯來文是種死掉的文字,在以色列建國前,已經少有人懂得。《聖經》的作者文化程度有高有低,撰寫更是歷經上千年歲月,在許多不同的地方分別完成的。照道理講,必定包含各地的不同方言,以及不同時代語言的細微差異。雖然兩千多年來學者不斷的研究與還原《聖經》原意,並且參考其他已知的閃族語言(Semitic Language)的文法,有些地方還是很難解讀。就像這裡舉的小例子一樣。還好外送的食物不是很重要的地方。不會因為弄錯當年的菜單,導致基督教失去價值。後來的《聖經》版本多半把這兩處地方修正為麥穗跟袋子,好比中文世界最常用的基督教會和合本《聖經》和天主教會思高本《聖經》,都避免了欽定本的錯誤。之後很多欽定本的修正版本,也更正了內容。
有一個人從巴力沙利沙來,帶著初熟大麥作的餅二十個,並新穗子,裝在口袋裡送給神人。神人說、把這些給眾人喫。(和合本)
有一個人從巴耳沙里來,在自己的行囊裡,給天主的人帶來了初熟大麥作的二十個餅和一些新麥穗。厄里叟說:「分給眾人吃罷!」(思高本)
And there came a man from Baal-shalishah, and brought the man of God bread of the first-fruits, twenty loaves of barley, and fresh ears of grain in his sack. And he said, Give unto the people, that they may eat.(以欽定本為基礎的美國標準本﹝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如果各位留意,會發現中文《聖經》將原來的三項食物翻譯為兩項。這可能是從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延續來的另一個錯誤。雖然武加大譯本也有很多錯,這裡的翻譯倒是比較正確:「初熟穀類作的餅(panes primitiarum)和二十個大麥餅(et viginti panes hordiacios)以及一些新穀子(et frumentum novum)裝在袋子裡(in pera)。」希伯來文原文的大麥「餅」這裡沒有漏譯。
回到玉米傳播的問題上。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歷史文獻的解讀一點也不簡單。新證據固然可能導致大發現,但更可能帶人誤入歧途。研究《聖經》的人很多,歷史也很久,《聖經》的誤讀多半可以很快找到錯誤。其他歷史文獻就不見得如此了。我們不知道這些文獻是否為後世偽造的。即使真的出於當時,更不知道作者是否說謊或是誇大。古人對證據力的要求經常不高。由於地圖關係極大的商業利益,更可能造假。因此在得到新發現時,如果沒有其他資料佐證,證據力或許會很弱。好比作者在第九章指出馬雅語言的「雞」與中文發音類似時,不妨先打個問號。譯者不是語言學家,也不懂如何閱讀馬雅文字。但是根據經驗,這種古代語言的解讀經常是見仁見智的。看看前面所舉希伯來文的「玉米」就知道了。
除了單字定義可能有問題外,文獻也可能騙人。當作者提供史料證實西班牙探險家在美洲大陸看到「中國人」出沒,或是美洲某些部落據稱還會說「中國話」時,最好還是先打個問號。用財迷心竅形容當時的西班牙探險家一點也不為過。在西班牙殖民的最高峰,他們不惜殺人放火也要搜刮黃金白銀,然後整船寶物運回祖國。這種「根留西班牙」的「資金回流機制」運作得非常成功。因為全歐洲財貨生產的速度遠遠趕不上金銀運回的速度,讓西班牙人反而變成有錢的窮人,不但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還讓英國坐收漁翁之利。英國皇室索性跟海盜勾結,讓他們在英國保護下公然搶劫西班牙船隻。
本文無意指責西班牙人,而是他們的目擊記錄不能盡信。哥倫布想要發現亞洲,所以把美洲原住民叫成「印度人」。真的認識印度的中國人只好把這個詞改成「印地安人」。在「印度」都發現後,他們怎能不急著發現中國?自古人性皆貪婪。幾年前一堆掛著.com 的網路公司還不是整天嘮叨著馬上發財。如果完全接受他們的本夢比,未來的歷史學家恐怕會不相信二○○○年曾發生股市崩盤。譯者不否認西班牙人確實可能在美洲與亞洲人碰面,但是如何確定記錄的真實性?這些探險家簡直是官方資助的土匪,換成今天恐怕難逃戰犯法庭的審判。他們又如何分辨中國人、泰國人、越南人、日本人或是韓國人?就算當時真有亞洲人的聚落,怎知不是十三世紀出征日本,不小心被「神風」吹走的蒙古人後代?
永樂十九年〈西元一四二一年〉的鄭和第六次航海究竟最遠到了什麼地方,至今仍然是個眾說紛紜的問題。孟席斯的書絕非第一本相關著作,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本。這本書在國際間毀譽參半,除了牽扯到歐洲人與中國人的歷史情感外,書中理論的疏漏也是關鍵之一。花了十幾年時間跟大筆金錢親身造訪各地,實際收集並判斷資料是他最大的功勞。歷史當然不會忘記他對中國的熱愛。但是鄭和的問題顯然不是一個人用很有限的資源和時間,就能研究透徹的。任何問題只要研究透徹,都可能成為一篇擲地有聲的學術論文。只可惜一個人要兼顧這麼多問題,疏漏自然無法避免。
因此在這本書裡,我們看不到蓋棺論定。很多地方必須藉助信念以彌補證據之不足。只是由於證據的品質參差不齊,他的論點非但很難說服不信的人,還可能被當成攻擊其歷史觀的武器。鄭和的第六次航海已經很難考證了,十多年的努力不可能完全涵蓋。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把話說滿,有限的證據不但無法防禦批評者的攻擊,還處處顯露破綻。作者的專長是航海與海圖判讀,這點毋庸置疑。能夠寫出這本書,就是因為他擁有傲人的航海知識。只可惜整本書的證據力被其他非專長的領域淡化。例如說作者用了很多語言學、分子生物學、動植物學、民族學之類的證據證明中國人確實遨遊四海,但是這些證據多半缺乏補強,舉證又過於簡略,結果就壞了整個理論的可信度。哥倫布是否為發現美洲的第一個非美洲人,在學術界都有很多人存疑。因為發現新大陸意味極大的商業利益,很多人就算知道,也會選擇保密。哥倫布很可能只是公開發現的第一個人。美洲如此,其他地理區域何嘗不是如此。很可能整個世界早就被貿易商走遍了,只是他們偷偷數錢,沒在歷史上留名。
其實有關鄭和航海的中文資料也不見得全毀。把檔案滅失的責任歸咎給劉大夏一個人,只是種簡化的理論。很多學者認為檔案並未被毀棄,而是失去維護而散失。即使原始資料已經消失,明清兩代的宮廷還保留了很多宮中檔案至今無人研究。中國人建檔鉅細靡遺。皇上從早到晚的活動都有起居注,其他單位的公文也多半留存。這些檔案堆積如山,根本分析不完。明清檔案不但蘊藏中國歷史的祕密,有些地方也頗有商業價值,例如御膳房的食譜就是炙手可熱的項目之一。等到有人開始考察檔案後,再談鄭和到過什麼地方,或許比較合適。
這本書最早發行的英國版裡光是打字錯誤和其他很容易避免的小瑕疵,信手拈來就是一大堆。雖然錯誤多半不太嚴重,積少成多後還是會造成讀者困擾。好比說作者引用的相關著作中,就包括了多年來學界早就知道的事實錯誤。例如淡江大學邱仲麟教授翻譯李露曄(Louise Levathes)之作《當中國稱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時所找到的許多錯誤,由於原書美國版尚未訂正,又被孟席斯引用到這本書裡。同時因為西方流傳的中國文獻既有威妥瑪拼音,又有漢語拼音,還有字面直譯,華語更有各種方言的不同拼法,作者有時也會搞混。絕大部分沒有爭議性的事實錯誤與錯字很容易在翻譯時更正,也有些是在跟作者溝通時,藉由孟席斯本人的熱心幫助才得以釐清。雖然實際發行的版本已經比之前的初稿少了很多錯誤,英文版仍舊留著很多瑕疵沒找到。不管這份中文版改正了多少內容,英文版的截稿壓力確實給這本書引來很多可以完全避免的批評。
另外在這個譯本裡,很多歐洲人名跟英國版和美國版的原書有出入,簡稱也經常不同。例如Niccolo dei Conti,原書拼為Niccolo da Conti。之所以會改動拼法是根據《大英百科全書》與微軟《Encarta 百科全書》,以及其他資料所決定的。其實作者也在美國版印行時,改掉了一些英國版的錯誤。雖然很多中世紀人名不見得有統一的拼法,百科全書的拼法通常最容易找到相關資料。
部分人名的簡稱也遭到更動。例如Niccolo dei Conti,原書簡稱da Conti,在這個譯本裡直接叫做「孔地」,這是根據歐洲稱呼這個人的一般常規決定的。孔地的生平譯者所知不多,在這裡以另一個每個人耳熟能詳的名字為例做解釋:
在英語世界裡,Leonardo da Vinci 通常簡稱為da Vinci,就是中文習稱的「達文西」。他是佛羅倫斯的文西地方,一個有錢的祕書Ser Piero 和村婦的私生子。「達文西」其實是指他來自於文西。因此學者在稱呼他的時候,一律不是用全名,就是單用他的名「李奧納多」,沒有人叫他「達文西」。從這點細節就可以看出任何一本談到他的書是否寫作嚴謹。同樣的,在百科全書裡,沒有人稱呼dei Conti,而是用Conti 簡稱。所以這個譯本便叫他「孔地」。
中世紀歐洲是個非常多元的社會,命名規則很不統一。所以很多名字稱呼的方法也不一樣,通常是照著百科全書或是其他參考書籍的用法而定。雖然有些人已經採用名字加姓氏的格式,還有人繼續用古希臘流傳而來之名字加地名的命名法;也有很多人用的是中東閃族父子連名制的變體。而冰島也還在使用他們自己的父子連名制。直到一五六三年,教廷才召開特倫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制訂姓名規則,規定每個教區都要紀錄戶籍資料。雖然以前已有地方私下登記戶口,但只有在教廷硬性規定,新教教會跟隨辦理之後,歐洲人的命名規則才比較統一。
對於書中出現的人名,譯者只能盡量找尋適當的稱呼法。對於很多資料不多的名字,也只能按照常識猜測。如有錯誤,請各位讀者不吝指正。
鄭和的艦隊到過什麼地方,有證據可考的答案可能會讓人很失望。在讀完這本書後,即使鄭和後來證實「只」發現了南美洲或是北美洲,大概都會讓某些人扼腕嘆息。即使鄭和真的到過澳洲和美洲,最多也只是到過而已。後來創造歷史的都不是中國人,中國人扮演的是死傷慘重的無名華工。歷史是勝利者寫下的。問到是誰最先「發現」美洲和澳洲,很少人會想到當地的原住民。為什麼?因為具有影響力的,給兩塊大陸帶來繁榮與破壞的,都是歐洲人的後代。因為他們統治美洲和澳洲,他們的後代才會關心這兩塊陸地是誰發現的。誰發現了什麼地方,純粹是佔領者的子孫會問的問題。過去南非的白人政府受到孤立,日本則是個自治的國家,很少白種人會在乎這兩個地方是誰「發現」的。西方歷史上對好望角的第一印象,就是把這裡當成通往東方的關卡,非洲對他們沒那麼重要。直到十九世紀,英國的探險家才深入這塊「黑暗大陸」,進行他們所說的「發現」。
英國的《自然》(Nature)是個報導科學進展的期刊,至今仍是科學界不可或缺的每週資訊來源。十九世紀時,這份刊物經常登載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與史丹利(Sir Henry Stanley)在非洲探險的報告,有時也會刊登日本西化的消息。一八七○年代相當重要的話題之一,便是英國如果不派探險隊到世界各地觀測一八七一年的日全蝕,科技實力就會被當時快速興起的普魯士等國迎頭趕上。從孟席斯的理論裡多少可以看到這段歐洲爭霸的痕跡。在這本書中,鄭和的艦隊航行四海,在每個地方設置天文臺,彷彿是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只不是明帝國是個柔遠人的政權,不像歐洲殖民帝國強取豪奪。放棄海上霸權之後,只留下世界帝國未完成的空殼。不管怎麼說,這本書仍然是西方人眼中的歷史,不是中國人的歷史。
海洋再大,也裝不完人們的過度想像。孟席斯先生出身於有光榮傳統的英國海軍,尚不免於用自己的預設觀點解讀大海。一般沒經歷過海洋的人,就更難不受偏見指引了。現在常見的偏見之一,就是臺灣位在大海之中,應當勇敢走向海洋。抱持這種主張的人懂多少航海,我們就不必計較了。臺灣的先民實際穿越過海峽。如果他們管這麼窄的一段區域叫做「黑水溝」,我們就該知道海洋給他們留下什麼烙印。臺灣東邊是太平洋。這個海洋的名字是空前絕後的產品標示不實。這也證明了大部分好聽的話,都只是說來容易。
歷史上的海權國家,全都是大陸國家。從北非的腓尼基開始,一直到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美國,每個都是大陸國家。英國表面上雖是個島國,卻由很大的三個海島組成,而且英國最偉大的時代,也是為了稱霸歐陸才壟斷海洋。英國文化可以上溯到法國、羅馬跟希臘,英國的知識分子從不到冰島或是格陵蘭取經。他們征服海島,是把海島當成稱霸陸地的籌碼。例如在海島上殖民取得資源,或是把海島當成航海與科學的基地。
海權國家只有少數人在海上活動,換取大部分人在陸地上吃得開。他們並不認同征服的土地,也不在乎他們的文化。海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有些人把歐洲人在臺灣活動當成臺灣與世界接軌的開始,這是很奇怪的。歐洲當時要的是中國。十七世紀歐洲上流社會流行過中國熱,沒流行過臺灣熱。歐洲人發現臺灣,臺灣人沒發現歐洲。如果這叫做接軌,顯然只接了一根。會有人主張走向海洋,其實是在逃避陸地。這是失敗者的邏輯。臺灣位在海洋之中,海洋已經是肉體的監獄。如果又成為心靈的監獄,真不知道下一步該退到什麼地方。
海洋不是藉口,過去的光榮也不該是藉口。除了〈赤壁賦〉般的懷古心態,鄭和的航海給中國人帶來什麼?恐怕很少。不管鄭和的艦隊發現多少地方,都跟今天的中國人無關。歷史不能改變,美洲和澳洲當然也不是中國人的地盤。在鄭和之後的四百年,當中國人在舊金山碼頭上岸時,身分是苦力而不是發現者。中國人犧牲生命修築美國的太平洋鐵路,建設加州的一號海岸公路,卻不是故事的主角。從李約瑟博士開始,中國人回頭留意自己過去的科學與文明,原因自然和近代所受的屈辱有關。很多人想從過去的輝煌找回自信。等到中國走回文明國家之列,有關昔日榮耀的探討倘使離開了學術範疇,多少就有點時空錯置的意味。與其計較鄭和的旅程,還不如問問自己,今天的中國人能帶給世界什麼發現?
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早就過了。如今太空似乎還是個可以探索的地方,海底也蘊藏無盡的祕密,地球的氣候照樣讓人捉摸不定。生物的基因和物理的基本粒子有回答不完的問題等著解決,國際間卻總是找不到和平。中國人在上次的大發現缺席了幾百年,不知道接下來還願意缺席多久。希望我們不會又把自己的責任搞成有趣的歷史問題。
註釋
1.可從Project Gutenburg的網站取得免費電子版文件。
2.可從http://1911encyclopedia.org/查詢目前尚有很多錯字跟疏漏的電子版。
導論
十多年前我意外得到一個難以置信的大發現,那是個藏在一張古地圖裡的線索。雖然這個線索不會帶領人找到埋藏的寶藏,卻暗示我們流傳幾百年來,人們想當然爾的世界歷史可能需要大幅改寫。
當時我對中世紀歷史的愛好,正走上了欲罷不能的道路。特別讓我著迷的,是早期探險家的地圖與海圖。我迷上了查閱這些古老的海圖,追蹤他們畫下的輪廓線與海岸線、形狀多變的淺海和沙洲,還有險惡的岩岸與珊瑚礁。我跟隨著潮汐起伏,順著暗潮牽引與季風的推送前進,一層一層揭露這些海圖隱藏的意義。
激發我進行研究的地方,是在美國...
目錄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誌謝
□導論
第一篇 中華帝國
1 鴻圖霸業/二九
2 大地驚雷/五九
3 艦隊啟航/七三
第二篇 牽星過洋
4 繞過好望角/九七
5 新的世界/一三五
第三篇 洪保的航行
6 南極與澳洲的航行/一六一
第四篇 周滿的航行
7 來到澳洲/一九一
8 大堡礁與香料群島/二一三
9 美洲定居之始/二三五
10 定居中美洲/二五七
第五篇 周聞的航行
11 惡魔島/二八一
12 擱淺的寶船艦隊/三○九
13 定居北美洲/三二七
14 北極探險/三四七
第六篇 楊慶的航行
15 解謎/三六七
第七篇 葡萄牙坐享其成
16 天涯海角/三八七
17 殖民新天地/四一一
18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四三一
□結語:中國的遺產
□譯後記 鮑家慶
□附錄:1中國人在一四二一~二三年之間環繞世界航行的證據索引
2目擊者記事
3描繪第一次環繞世界航行的重要海圖
4十五世紀初期中國人決定經度的方法
5網站上的更多資料
□圖版一覽表
□選錄書目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誌謝
□導論
第一篇 中華帝國
1 鴻圖霸業/二九
2 大地驚雷/五九
3 艦隊啟航/七三
第二篇 牽星過洋
4 繞過好望角/九七
5 新的世界/一三五
第三篇 洪保的航行
6 南極與澳洲的航行/一六一
第四篇 周滿的航行
7 來到澳洲/一九一
8 大堡礁與香料群島/二一三
9 美洲定居之始/二三五
10 定居中美洲/二五七
第五篇 周聞的航行
11 惡魔島/二八一
12 擱淺的寶船艦隊/三○九
13 定居北美洲/三二七
14 北極探險/三四七
第六篇 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