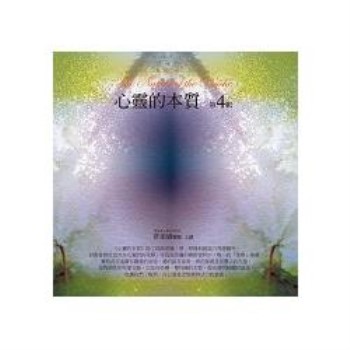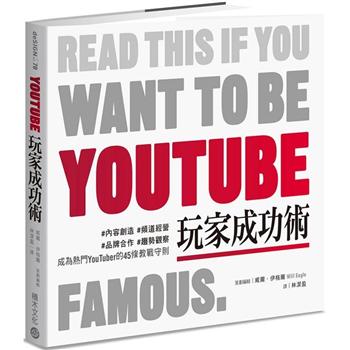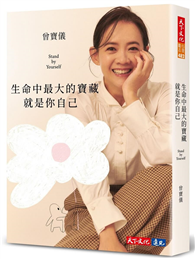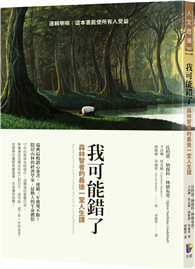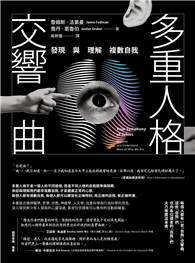詩能醫療憂鬱症
這個年頭,「憂鬱症」成了流行病,從抗憂鬱藥、鎮靜劑的銷行統計看來,不難發現這種病患在迅速增加。
社會競爭愈激烈,人際關係愈複雜,「憂鬱症」患者也愈多,這是必然的現象。
什麼是「憂鬱症」?一般來說,是過於焦慮,無端煩躁,情緒低落,惴惴不安,對任何事缺乏興趣,厭食、失眠,甚至覺得身體是累贅,不知該怎麼安置。
「憂鬱症」是心理病,病原有近因,有遠因,近因大都是遭受感情挫折、工作困擾、事業失敗等等,意志不夠堅強的人,很容易患上「憂鬱症」,病根不深,事過境遷,病情也會隨時間消退。遠因是經年累月的憂患、恐懼,層層疊疊積壓心底,病發時,心境灰暗,了無生趣,這種「憂鬱症」比較嚴重,很難根治,服藥、找精神分析醫生,都少有顯著的功效。
醫治「憂鬱症」的藥物相當貴,心理醫生收費也很高,經濟能力較低的患者,常依靠親人、摯友的慰藉治療。
不久前,英國卜里斯特大學教授羅賓•菲利浦,發表對「憂鬱症」的研究;說詩可以治療「憂鬱症」,他給患者開的處方,是濟慈、布朗寧等詩人的作品。由於他是權威學者,此說引起極大的反響,醫藥界十分緊張,唯恐這一療方有效的普遍採用,就會斷掉他們的一條財路。
詩可以治療「憂鬱症」,應該是可信的,煩惱時讀讀詩,往往能使心胸舒暢,我有此經驗。
讀新詩、舊詩或外文詩都可以,最好選擇喜歡的讀。我少讀外文詩,有些新詩又讀不懂,愛讀舊詩,但也讀得不多。據我個人有限的了解:李白的詩奔放,能給人解除束縛的感覺;白居易和蘇東坡的詩超脫、飄逸,令人渾忘物我;辛棄疾的詩瀟灑,讀來心曠神怡;王維的詩禪意濃,能帶來與大自然合一的寧靜、平和境界。家國觀念太深的人,莫讀陸遊的詩,會造成心靈虐待;杜甫的詩多傷感。
還有,唐詩多悲苦,宋詩較超脫,宋朝詩人中,陳去非的詩最豁達、樂觀,情緒低落時,不妨讀宋詩。這些只是我個人淺陋的看法。
如果肯寫詩,那就更好了,寫詩比讀詩更能宣洩情緒,將內心喜、怒、哀、樂盡情向詩中傾訴,不必計較寫得好不好,儘管寫就是了。我相信用寫詩醫治「憂鬱症」也許更有功效。
不是我
朋友和他的朋友老山東來訪,問我:「你家有幾口子?」
「八口,女兒不在美國。」
朋友插嘴:「你家只有七口,怎會多出一個?」
「確實是八口。」我誠懇的回答。
朋友扳起手指:「你真老糊塗了,讓我數給你聽,你、你的老公、閨女、兒子、媳婦和兩個小孫子,總共七口。」
「還有一個納米(Not me)。」
老山東問:「誰是納米?」
「這是他的洋名,中文名叫『不是我』。」
「好怪的名字,他姓什麼?」
「不知道,我們管叫他納米。」
他以為我的神經有毛病,也就不再追問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家便有了「納米」,且舉例證明他的存在,先從老伴說起吧;他每早要去後園打太極拳,進屋不換鞋,常在淺色地毯上留下濕泥、碎草;出街不鎖門,輕輕一推,大門應手而開;幫我清潔廚房,總有一兩個羹匙或碗蓋失蹤(連同瓜皮、菜根、雞骨、螃蟹殼,一併扔進了垃圾桶),我若責問,他必回答:「納米!」
今年春,由香港回來,收到交通部罰款通知,說我的車在大學校園泊錯了車位。我剛到家,何曾去過校園?問媳婦,她連聲說:「納米、納米!」嚴查之下,才知道「癩痢頭兒子」曾碰壞車,送去修理,無疑的,這期間他用了我的車,我問他:「是誰開過我的車?」他衝著我喊:「納米!」
至於兩個小傢伙,更時常提到「納米」,「誰把玩具撒滿地下室?」「納米!」「誰在地毯上潑了牛奶?」「納米!」「誰忘記關電腦?」「納米!」總之,所有壞事全是「納米」幹的。
月前,我的Beta錄放影機壞了,這種老式機早已遭淘汰,絕跡市場,老伴的兩百多卷京戲小影帶,豈不成了廢物?「癩痢頭兒子」把他的小帶機搬了來。不料,畫面模糊不清。拆開一看,裡面竟塞了顆蠟紙包裹的咳嗽糖。據媳婦記憶,曾經買過這種糖,於是審問兩個小兄弟,弟弟小傑眨眨眼說:「納米!」再問哥哥小騰:「是你嗎?」小騰想了想,說:「梅比(Maybe)。」
當時,小傑只有兩三歲,手多多,我們肯定咳嗽糖是他塞的,但是,為什麼小騰會招供呢?小騰解釋道:「因為你們希望有人承認,那麼,我承認好了。」
小騰帶來令人驚喜的「梅比」,但願他長留我家。
中國的母花
小白屋旁開遍了金銀花,微風起處,濃香撲鼻,花香似白蘭,似茉莉,又似珠蘭,由於藤枝太密,花太多,我怕它擠壞,每早剪一捆插在瓶裡,滿室清香。
有人說,這就是「萱花」。
金銀花竟是「萱花」?真是太好了,金銀花是如此的清幽,黃白兩色又是如此的素潔,多麼適合好母親的形象!
每逢母親節,孩子總會買一束「康乃馨」送母親,我喜歡樹,不太喜歡花,對花卉缺乏研究,以為「康乃馨」既是洋名,必然是洋花,十幾年前,子楚兄給我看一冊古畫,原來我們中國也有「康乃馨」,名「石竹」,我不知道人們為什麽不稱「石竹」而稱「康乃馨」,大概母親節是洋人搞的節日,名稱也該從洋吧?
我很贊成母親節,至少一年中有一天會讓人想到自己的母親,送幾朵花也能給母親溫暖,又何必計較花的名稱?
最近,讀一篇談「萱草」的專題報告,而且附有照片,才知道中國的母花,不是「康乃馨」,也不是「金銀花」,而是「金針花」!
金針花莖粗,葉似菖蒲,只是較柔、較狹窄,花金黃或深紅,類似百合花。幼年最愛喝金針花煮肉片湯,怎的也想不到這就是咱們中國的母花!
查《詞源》,找花譜,才知道金針花就是「萱花」,原名「萱草」,古人指母親的居室為「萱堂」,詩有「白髮萱堂上」句。萱花是代表母親,古代文學中,常引用的「萱」古作「諼」,「諼草可以忘憂」,因此又名「忘憂草」。
金針可作菜肴,也是一種藥草,能鎮定情緒,也能忘憂,萱花比康乃馨更具意義,當孩子遭遇困難時,最能給予撫慰的,就是母親。
小白屋後園一角,有一圍植物,是前屋主栽種的,大堆長葉,從未見開花。我以為是野生雜草,今年二月,寒冬未過,清理花坑,趁它還未重展枝葉的時候,大肆拔除,準備種辣椒,不料,這一輪摧毀,反而使它生機旺盛,春天一到,莖葉成長得奇快,而且更肥更綠,三四月,花葩密集,相繼開放,湯碗大的金黃色花朵,層層疊疊,十分耀眼。
原來是萱花!咱們的母花!
果真象徵了母性的偉大!愈受摧殘,愈能顯示堅強的生命力,世界上的母親,在維護孩子時,都是如此。
面對一片金黃燦爛的萱花,我感到慚愧和深深的敬意。
酒話
我的母親愛酒,也很有酒量,有人說,她的書畫每一筆都有酒味。上海的「聖約翰」和「光華」等大學的學生常來請她分析國事問題,她邊飲邊談,從黃昏到午夜,了無醉意。
我能喝酒,是母親的遺傳,現在,老了,聞酒多過喝酒,嗅嗅酒香,也會有醺醺然的感覺。
年前訪西德,朋友帶我參觀天主教苦修院。院內神父不講話,只是默誦經文,閒時也會種葡萄、釀酒。
歐洲人認為苦修院出產的紅酒,是酒中極品,往往不惜奔波幾百里,去苦修院祈禱,目的在買酒。楞小子說:「意不在祈禱,只為了貪好酒。」
當時,我也曾購買兩小瓶(由於出產不多,都是小瓶裝)。我不太喜歡喝紅酒,就像豬八戒吞人參果,糊里糊塗的喝了。
少時,在軍旅中,老百姓以自釀的米酒勞軍。三湘原是魚米之鄉,農家米酒香醇,但酒精度很高,我只適當的喝兩小杯來驅除巡夜時的疲憊。
抗戰勝利後,退伍,回南京工作。在國際宴上,也曾經嘗過各國名酒。最難忘的是蘇俄特製的軍中伏爾加,此後就再也沒有喝過那麼好的伏爾加了。
而今老了,人家送我的茅臺、五糧液、陳年金門高粱,寫讀時擺一杯在桌旁,微微的酒香,也能提精神。
日前到臺灣埔里鄉間,在出家學生圓誠的「東林淨苑」住了幾天。該庭院前排列著一籮籮新摘的青橄欖,我從未見過那麼大的橄欖。有的大如雞蛋,是用來釀蜜橄欖用的。據說頭年入醰密封,次年開啓,清香滿屋。她給我喝半杯去年的原汁,那濃香的果汁含在嘴裡,竟然捨不得吞呢!其中也有酒味,當然,任何柑果封存久了,都會發酵變酒的,她們的橄欖汁開醰後,滲入泉水,酒味就消失了。
豐子愷先生,一生淡泊,他那「一壺酒,半碟花生米」的超脫,不是世俗人能了解的。他常將喝酒的情趣收入畫中,那深透紙筆的和平、溫暖,今日已難找尋了。
古人多愛酒,尤其是詩人,更離不了酒,隨便翻翻《唐詩》,就有很多與酒有關的詩句,大都是飲酒消愁、助興、抒發感情和捕捉靈感。
白居易的:「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和王翰的「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是我最愛的詩句。前者,充滿飲酒人的安逸;後者,是喝酒人的壯烈豪情。
孟浩然的「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韋應物的「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和老友重聚一起,摸摸酒杯底,是飲者的享受。還有「把酒話桑麻」,個中境界豈只是酒醉人?
李白詩中多飲酒,「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管他什麼青史留名,管他什麼皇帝老子,喝酒緊要哪!唯獨「酒仙」才有這份狂傲。
他那「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以及「舉杯消愁愁更愁」,是詩人的情懷,也說明了酒可以消愁,也不能消愁。只是,酒能帶來寫作的靈感,倒是真有這麼一回事,「李白鬥酒詩百篇」,即一例。
想起來,真可笑,有一回,我頭腦閉塞,無法寫稿,「癩痢頭兒子」買來一瓶洋酒「J&B」,說:「海明威每天要喝一瓶『J&B』,才動筆寫文章,所以這種酒又叫做『作家的威士忌』(Writer’s Scotch),不妨試試。」我大喜,滿以為一杯下肚,下筆千言,豈知,半杯還沒喝完,便伏在稿紙上見周公去了。
多丟人!肚子裡沒有墨水,浸在酒缸裡也是枉然,何況,當年的酒量已隨歲月消失了。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農婦在江湖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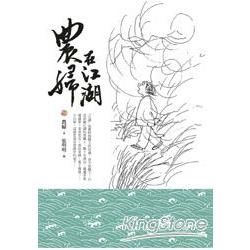 |
農婦在江湖 作者:農婦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5-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9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現代散文 |
$ 237 |
中文現代文學 |
$ 270 |
現代散文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340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農婦在江湖
農婦,海外知名的國際問題專家和散文家,文字簡樸、直接、爽朗,見解獨到,筆鋒幽默富情感,個人魅力十足,作品深受喜愛,被稱之為「在歐美各地,有中文的地方,就有農婦的書。」本書記錄其移居美國馬利蘭州之後窩居小白屋的生活軼事,對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看法,闖盪世界各地所見所聞的感觸,以及緬懷抗戰年代的從軍歲月。雖年紀老大,筆下盡是年輕人、新鮮事,她的那種有趣,那份灑脫,字裡行間展露無遺。
作者簡介:
農婦
原名孫淡寧。祖籍湖南長沙。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八年抗戰末期,曾從軍投入火線。戰後到香港,執教「浸會大學」,任職「明報」。 著作有《狂濤》、《鋤頭集》、《水車集》、《犁耙集》等近二十種。
插畫者簡介
張明明,知名藝術家,以壁畫著稱。為美國中華文化藝術同盟主席。
章節試閱
詩能醫療憂鬱症這個年頭,「憂鬱症」成了流行病,從抗憂鬱藥、鎮靜劑的銷行統計看來,不難發現這種病患在迅速增加。社會競爭愈激烈,人際關係愈複雜,「憂鬱症」患者也愈多,這是必然的現象。什麼是「憂鬱症」?一般來說,是過於焦慮,無端煩躁,情緒低落,惴惴不安,對任何事缺乏興趣,厭食、失眠,甚至覺得身體是累贅,不知該怎麼安置。「憂鬱症」是心理病,病原有近因,有遠因,近因大都是遭受感情挫折、工作困擾、事業失敗等等,意志不夠堅強的人,很容易患上「憂鬱症」,病根不深,事過境遷,病情也會隨時間消退。遠因是經年累月的憂...
»看全部
作者序
老農婦的話
《農婦在江湖》的「江湖」兩字,我想稍作解釋。
「江湖」是舊時指隱士的居處,我不是隱士,只是浪跡江湖的異鄉人。
數十年漂泊,處處非家處處家,老來思定,落居美國,築了個窩——小白屋,這就是我安度餘年的家了。
人問:「小白屋在別人的國土上,你能排除流徙的感覺嗎?」
我的答覆是:「我在大學山區擁有七千多尺的土地,是向美國政府買來的,一如美國買阿拉斯加,踏上小白屋前院的石階,便踏進了中國。」(見〈布拉格小子〉一文)這種意識或多或少能鬆解一些家國的情結。
再說,孫兒小傑六歲時,在作業上畫了幾幅連...
《農婦在江湖》的「江湖」兩字,我想稍作解釋。
「江湖」是舊時指隱士的居處,我不是隱士,只是浪跡江湖的異鄉人。
數十年漂泊,處處非家處處家,老來思定,落居美國,築了個窩——小白屋,這就是我安度餘年的家了。
人問:「小白屋在別人的國土上,你能排除流徙的感覺嗎?」
我的答覆是:「我在大學山區擁有七千多尺的土地,是向美國政府買來的,一如美國買阿拉斯加,踏上小白屋前院的石階,便踏進了中國。」(見〈布拉格小子〉一文)這種意識或多或少能鬆解一些家國的情結。
再說,孫兒小傑六歲時,在作業上畫了幾幅連...
»看全部
目錄
老農婦的話 8
窩居銘 13
杜鵑莫再催歸去 14
滿足 16
北極熊與老公 20
河馬先生 24
管訓老媽 28
領帶媽 31
不是我 34
我的煩惱絲 38
車牌惹麻煩 44
好珍貴的幾根菜 49
母鶴、母雞、母鴨 52
祖居 58
我是齊天大聖的後代 60
一九八一年的故事 63
布拉格小子 66
酒話 70
發瘋 75
詩人鄰居 78
詩能醫治憂鬱症 83
龜行操 87
野獸進屋 92
兩隻腳的浣熊 101
恭迎土撥鼠起床 104
與鬼同樂的萬聖節 109
中國的母花 115
好難下鋤 ...
窩居銘 13
杜鵑莫再催歸去 14
滿足 16
北極熊與老公 20
河馬先生 24
管訓老媽 28
領帶媽 31
不是我 34
我的煩惱絲 38
車牌惹麻煩 44
好珍貴的幾根菜 49
母鶴、母雞、母鴨 52
祖居 58
我是齊天大聖的後代 60
一九八一年的故事 63
布拉格小子 66
酒話 70
發瘋 75
詩人鄰居 78
詩能醫治憂鬱症 83
龜行操 87
野獸進屋 92
兩隻腳的浣熊 101
恭迎土撥鼠起床 104
與鬼同樂的萬聖節 109
中國的母花 115
好難下鋤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農婦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5-01 ISBN/ISSN:978957326777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