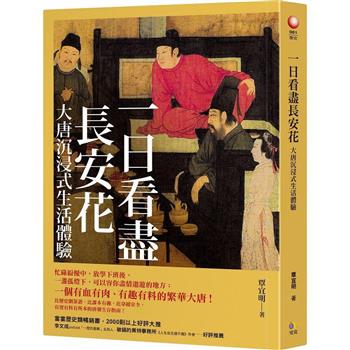自序
書中的文字大部分完成於二○○四年之前,而最早的已經超過十年。真是愧對讀者。原來為我出書的出版社結束營業了,這本書一擱就是七八年。面對生命中大段的空白,尤其虛擲的,竟是上天特別寬容於我的寶貴時光,真覺得怵目驚心,罪無可逭。
出版困難只是怠惰的托詞。舊作不得出版,與繼續寫作何干?二○○二年《馬勒的歌》獨唱會後,雖沒有計劃或決定不再站上舞台,但由於莫名的原因,動力不再,慢慢就停了下來。本來我已經拖得夠久,像個到了時間還遲遲賴著不肯上床的孩子,終究睡著了。
不再唱又與不再寫何干?不是該更有時間了嗎?忙碌了一輩子,如今可說是閑了,卻悟出一個道理:時間是越用越多的。不用它,也要溜走,而且更快。只有在覺得不夠用時才是有用的。我畢竟自認是個歌者而非作者。歌唱是主動的追求,寫作只是被動的因應,只是為音樂服務。寫作的誘因都來自周遭的音樂活動。○三年,因為時間的充裕,也因為國家交響樂團節目冊篇幅的充裕,的確寫了一篇比較長的《崔斯坦與伊索德》,回報冗長的華格納。那時未嘗不幻想著,不再受報紙刊物的局限,暢所欲言地寫幾篇稍有分量的東西吧。但○四年的那篇《唐璜的道德光譜》之後,就幾乎停止了。
在這期間,我的音樂生活(作為一個欣賞者)其實仍然是非常豐富的。常住在維也納,接連幾個歌劇季,和其間的音樂會,我幾乎成了專職聽眾。但竟然沒有留下一篇文字。除了日記上簡短的紀錄,興奮時發出的手機短信,只有記憶,滿滿的記憶,和更多從記憶中溜走的,還要繼續溜走的。我好像在另一個世界,這裡每天發生的音樂事件,要費很大力氣才能對國內的讀者說清楚。 而音樂刊物越來越少了。不知寫在那裡,不知寫給誰看,有誰要看。於是就懶了。然後這幾年,我新添的小孫子又把我常拉到上海。日子過得興興轟轟。難免顧此失彼了。其實我虛擲的,倒未必是時光,而是記憶。記憶只有分享了才能保存。
追根究底還是老了吧。雖然不怎麼自覺。一書之中,好幾篇悼亡之作,證明自己真是很老了。許常惠幾乎就是我們那一代音樂人的縮影。眼看著這一頁翻過去了,茫然四顧,除了自己,竟沒有幾個人能再為他見證。謝安曾對王羲之說:「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羲之說:「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需賴絲竹陶寫。」我不那麼多愁善感。但早過了「中年以來」,面對的是更大的感傷。一位學生卻說:「老師,能被你的文章紀念,也是一種幸福。」用文字紀念我們共有的時代,而期望著後人看到我所看到的他們,竟成了我的責任。
而我記錄的這些現場音樂會,現在也過去十年八年了。我不知道自己努力描摹的,對沒聽過這些音樂會的人有沒有意義,而聽過的還有沒有印象。即便有,這些文字從一開始就只是我個人的印象。縱然努力想真實地記述音樂,其實連表達自己的感想都不準確。文字游離於這些音樂會以外,能不能存在,得看它自己。當有人走過來說:「那一場我也聽了,就是你寫的那樣……」我還是會覺得很快慰。即使知道,我們的感受不會一樣。我分享的,不是這些音樂,是我的記憶。更嚴格的說,是對我的記憶的不準確的紀錄。
唯一例外是卡拉絲。她是我最遺憾沒有現場聽過的歌唱家。但卡拉絲是繞不過去的。因為聯合文學策劃她的專輯而來邀稿,讓我好好地梳理了一下那些矛盾而讓人惶惑的印象,重新深深地被震動。為她的藝術,也為她的命運。兩者都取決於她的性格。就在那前後,迪里拜爾和朱苔麗接連在台北演出,曲目甚至還有重疊。兩位聲音和風格差異如此之大的歌手,彷彿就在考驗我們的美學理論,看看你如何自圓其說。但什麼都不必說,藝術本身是最雄辯的,遠超過我的文字。美的神奇,就在於容許這麼大的差異。甚至因差異而顯現。道理只有一個,美有很多很多種。
然而美自有其難以言宣不可捉摸的標準。〈芭托現象〉是我少有的對明星歌手貶多於褒的評論。我相信名無倖至,尤其在古典音樂這些嚴格的聽眾面前。然而這堅固的堡壘似乎開始崩解了。這不令人擔憂,天才常常挾帶著巨大的破壞力,美的標準向來都會隨著時間被顛覆。令人擔憂的是,越來越多藝術以外的因素伸進手來。通俗化常通往庸俗化。
所以作曲家比演唱家更恆久。歌聲飄散在風裡,而曲譜寫在紙上,可以被詮釋,不易被篡改。詮釋的空間無限,我的紙上談兵不過是詮釋之詮釋。威爾第逝世百年紀念,我一一清點了他歌劇中的人物,每一個都這樣沉重。一個多麼嚴肅認真努力的作曲家,每一筆都用上全力,寫到八十歲。歌劇之重我們這裡至今承擔不起。《托斯卡》,《崔斯坦與伊索德》,《唐喬萬尼》都是國家交響樂團的大製作。即使只是音樂會形式的歌劇演出,在自己的土地上聽到它們還是忍不住興奮得掉眼淚,像來了一個別人不太認得的老朋友,忍不住就要插嘴介紹:那可是個大人物呢!其實我也只是人群中的仰慕者,老朋友是自封的。但想想有許多年輕的心靈被第一次撼動,如我當年……。
當年已經很久遠了,我卻常不自覺。現在的我雖然不務正業,還過得熱熱鬧鬧。或許因為我有「絲竹」,有網路,有精力無窮的小孫子,有書讀(雖然吃力),有電影看。這本談音樂的書裡竟然有三篇和電影有關。(〈合演的那一場電影〉不過是個比喻,但是不是透漏了自己潛意識裡對電影的嚮往?)就在最近,黃斑症又一次侵向我的瞳孔,扭曲了我眼中的圖像。貪看電影至於一日兩三場,就像《新橋戀人》裡那個在失明前潛入美術館看畫的女孩,比她幸運的是我已經看過很多很多年了。而且我的好醫生幾次挽救回我的視力,或許我會一直這樣幸運。《時時刻刻》逾越了自己的戒律:不評論聲樂以外的音樂。但在這文學、電影、音樂的三江併流處,非陷溺不可。我恨不得不自量力地撇開音樂,痛痛快快寫一篇書評影評。對書中電影中(妮可.基嫚怎麼能把伍爾芙演得這麼真!) 陷溺於生命意義這個大問題裡的男男女女,我卻像是免疫了。活到如今,我仍答不出,但也不再問。每一天都是恩賜。八十歲的威爾第寫出一齣胡鬧的《法斯塔夫》。我也好像沒有無聊過。除了生命以外,你沒有更好的東西,唯一真正屬於你的東西。
列子中的故事:「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我和薛譚一樣,終身不敢言歸,卻也沒學到那響遏行雲的境界。對於歌唱, 我是「行到水窮處」了。如今或該「坐看雲起時」。
我不知從流水到行雲是如何幻變的。但我可以換個姿勢,看雲。或許,她也願停下腳步。
二○一一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