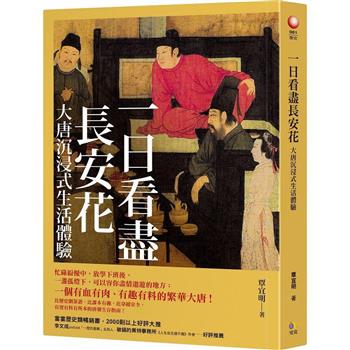一本不可多得的奇書
蘇叔陽
上世紀80年代,新近剛剛去往天國的電影藝術家謝添約我寫一本關於燕子李三的電影劇本。為了了解舊中國江湖的內幕和行話,忘了從誰那裡找來一本《江湖叢談》。我一口氣讀完,痛快地過了一回讀書癮,那感覺很像讀《兒女英雄傳》。我很想知道作者「雲遊客」是何許人也。可惜,問了許多人,都語焉不詳。一直到紀念評書大王連闊如百年誕辰時,我才知道:「雲遊客」乃連闊如也!這大大增加了我對連闊如先生的敬意。
《燕子李三》沒有拍成,連劇本都不知流浪何方,我的那本《江湖叢談》也不知是被同好借走還是遺失在搬家的中途,至今懊喪不止。但我卻記住了《江湖叢談》裡的許多內容,及至看到一些新起的文豪賣弄並不準確的「春點」,甚至用錯字音譯被舊時的藝人蔑視的「臭春」,就想「狗拿耗子」告訴他們,找一本《江湖叢談》看看,省得「謬種流傳」。後來知道,這是瞎耽誤工夫,便死滅了向他們推薦這本奇書的念頭。
這確乎是本奇書,而且我敢斷言,從今往後沒有人能再寫出這樣的書。要寫這樣的書,必須具備以下的條件:
第一,身為江湖中人,而又內心純正,所謂「出污泥而不染」,熟悉江湖內幕和行話以及一切行規。
第二,會寫一手漂亮文章。所謂漂亮不是今日滿篇舶來語、通篇新式名詞,外加倒裝句。而是通順、通俗、生動有趣,且極具韻味,讓人一看便明白這「江湖」所處時代的特色,了然當時北平報紙連載文章的風格。
第三,有拯人濟世之心,無嘩眾取寵之意。鞭撻假惡醜,有勇氣、有肝膽、有俠義之風。
這三點,除第三條之外,一、二兩項今人都無法達到。自然的偉力將這本書推到上世紀30年代北平、天津江湖行當及報紙文風活化石的地位上。能寫這書的人,沒了,沒啦!或許有今日的文人經過仔細地調查,深入地揣摩,寫出頗有當時風格的文章來,這就不錯。只是不會有那種身處其間的真實感,怎麼著都會有今人對舊人的評斷,不再是當時人的感受。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書是空前絕後的。至於第三點,今人絕大多數是真善美的歌頌者,不缺肝膽、俠義,不怕江湖人報復,因為,舊日的江湖已經掩埋在歲月的灰塵裡。可是,擋不住有幾位就願意歌頌假惡醜,愛顯擺自己明白江湖裡的道行,也寫一些這類的文章。但是,這和《江湖叢談》就有了本質的區別。《江湖叢談》為人指點迷津,揭露詭計,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險。這勇氣不是在溫柔鄉裡長大的才子可以比擬的。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風氣和代表人物。對於過往的俊傑我們只能仰視,因為我們無法估計我們倘在那時代生活,會有怎樣的表現,我們還能不能寫出或者做出像樣的東西,留給後人和歷史,成為認識這時代的參照。連闊如先生以一位評書藝人的身份,寫出這樣一本可以讓後人有興味地知道往事的奇書,本身就是奇蹟。奇人奇書,值得我們好好地讀一讀。是為序。
2005年6月8日於寤齋
回憶父親連闊如
連麗如
父親離開人世近40個春秋了,可是沒有一天不想念他老人家,他是我的慈父,也是我的嚴師。
父親是個苦命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閏五月,父親落生在北京安定門外一個窮旗人的家中。我家是滿族鑲黃旗人,祖姓畢魯氏。滿族人指名為姓,我爺爺叫凌保,是個門甲,父親出世前一個月,爺爺就故去了。父親只上了半年私學、兩年小學,12歲就當學徒,進過北京的首飾樓、照相館,天津的雜貨鋪、中藥店;到煙臺、大連做過小買賣;擺過卦攤,飽嘗了人世間的酸、甜、苦、辣。
父親原名畢連壽,拜師李傑恩,學說評書《西漢演義》,藝名連闊如。後又向張誠斌學說《東漢演義》。北京有一位田嵐雲老先生,說《東漢演義》名揚京城,聽眾孫昆波把田老先生書中的精華指點給我的父親,再加上父親的天資、勤奮,20世紀30年代末期在東交民巷伯力威電臺播講《東漢》,名聲鵲起。他刻苦向前輩演員學習,博採眾長,融會貫通,達到書情結構嚴謹,人物性格鮮明。說書時嗓音寬厚,語重聲宏,口齒清晰,娓娓動聽。為摹擬好文生、武將,他借鑑京劇表演藝術,融化於評書中。馬跑、馬嘶等口技輔助表演,被聽眾公認為一絕。父親曾說,「說書時要嚴肅地進行表演,要做到五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貴賓,忘身在今日,忘己之姓名」,全身投入藝術創造中。他重視說功、做功、打功,說到誰,就摹擬那個人物的神情、語言、聲態,有時也使用方言、韻白,加上必要的動作,表情狀物,繪聲繪色,形成了神完氣足、層次分明、起伏跌宕、耐人尋味的獨特風格,藝術精湛已自成一家。
父親說《東漢》的技藝,顯示了他少有的藝術才華。但他並不滿足,仍然精益求精。他虛心請教老師和聽眾,集先輩評書諸家之所長。父親說的是「袍帶」書,為了提高藝術,父親向知名的武術家學習,又結識了許多京劇界的朋友,如蕭長華、徐蘭沅、郝壽臣、譚富英、李萬春、馬富祿,以京劇唱、念、做、打的功夫豐富自己的表演。20世紀30年代末,京劇表演藝術家尚小雲先生曾邀請父親為他的科班──榮春社排演全部《東漢》。榮春社在前門外中和戲院演出,轟動了京城。那時,父親白天在電臺說書,晚上到劇場看戲、指導。尚小雲先生的長子尚長春扮演的武狀元岑彭栩栩如生,是父親說的《東漢》中的一個人物在舞臺上活靈活現的再創造。解放後,他協助王永昌先生排練了全部《水滸》,在大柵欄慶樂戲院演出,盛況空前。幾十年來,父親結交了各行各業的專家,成為朋友,如養馬專家載濤,語言學家吳曉鈴,劇作家翁偶虹、景孤血,針灸名醫胡蔭培,作家趙樹理,史學家吳?等。父親就是這樣廣交博學,不斷地使自己的藝術造詣達到更高的境地。
父親一生勤儉度日,不吸煙,不喝酒,不講穿戴,所掙的錢除去養家外,全都買了書刊。我家原住在和平門外琉璃廠,這是一條有名的古書街。父親則是「邃遠齋」、「來薰閣」等古書店的常客,難怪我去琉璃廠中國書店買書,好多書店的同志一眼就認出了我,津津有味地談起我父親當年買書的情景。我記得父親為了考證漢獻帝的「衣帶詔」一事,購買和翻閱了七八種《漢書》及《三國志》的版本。他鑽研天文知識,把《借東風》、《草船借箭》說得入情入理;他學習、了解山川地理、風俗人情,以備古今對照;為了評價歷史人物曹操,他詳細閱讀了多位學者的有關著作,登門請教。聽眾們反映:「聽連先生的書,不但聽了歷史故事,還學到了不少知識。」
父親為人正直,光明磊落,不奴顏婢膝。抗日戰爭時期,日軍責令我父親在電臺宣傳「大東亞共榮」,父親竟說了一段《廉頗?藺相如》,意蘊人民團結抗戰,結果被日偽電臺斥退。
父親離開了電臺,開始了寫作生涯,以雲遊客的筆名發表了《江湖叢談》。書中的內容是父親身臨其境掌握的第一手感性材料,對許多社會現象作了生動的寫照,正如父親所說:「以我的江湖知識說呀,所知道的不過百分之一,不知道的還多著哪。等我慢慢地探討,得一事,向閱者報告一事,總以愛護多數人,揭穿少數人的黑幕,為大眾謀利除害,以表示我老雲忠於社會啊!」這部書揭露了某些危害社會的江湖行當的黑幕和手段,在當時社會上影響極大。從這部書裡也看出父親的勤奮和洞察社會的能力,我也更加了解了父親青少年時代浪跡江湖的酸楚。
北京解放後,父親響應黨的號召,作為曲藝界的帶頭人,積極主動參加各項工作。1949年7月,被選為代表,參加了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在全國文聯的領導下,父親籌備成立了「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備會」,擔任副主任,協助王尊三、趙樹理同志工作。周恩來總理看過父親的演出後,鼓勵他搞好曲藝革新改進工作。父親立即按照北京市文藝處的指示,組織北京的京劇、評劇、曲藝演員成立「戲曲界藝人講習班」。為加強新曲藝的演出實踐,他帶領曲藝演員在前門「箭樓曲藝廳」每天演唱《新五聖朝天》、《考神婆》等新曲藝。又和新華廣播電臺合作,每天中午用固定時間播唱新曲目,前後堅持了三年,擴大了新曲藝的影響。在父親的帶動下,評書演員趙英頗等開始播講《一架彈花機》、《羅漢錢》等新評書,很受歡迎。
1951年初,父親積極響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受彭真同志委託,組織了「中國人民第一屆赴朝慰問團曲藝服務大隊」並擔任大隊長,率領京、津兩地許多著名曲藝演員,赴朝鮮前線,冒著槍林彈雨在前沿坑道、陣地,進行慰問演出。他經常表演評書《武松打虎》,古事今說,表達了祖國人民不懼強敵的心願,鼓舞了指戰員的鬥志,使曲藝獲得了「文藝尖兵」的稱號。歸國後,父親又帶隊深入大西南去演出,宣傳、推廣普通話,邊演出邊整理,創作了《飛奪瀘定橋》等新書。1953年10月,第二次全國文代會決定成立「中國曲藝研究會」,父親被任命為副主席,和趙樹理、王亞平、韓起祥一起,協助王尊三主席工作。當時是百花盛開的季節,父親除了編演新書《強渡大渡河》、《智取婁山關》等外,還整理了《三國演義》、《東漢演義》、《水滸》等傳統評書,在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整年連續廣播。這時,父親的說書藝術更加精湛,每到播講時間,家家收音機旁擠滿了聽眾,北京市內流傳著「千家萬戶聽評書,淨街淨巷連闊如」的讚譽。父親忙於社會工作,他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還經常到大學去講課。
1957年,父親遭到了無情的打擊,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他的身影從社會上消失了,他的聲音從廣播裡消失了。但他沒有灰心喪氣,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繼續編寫《紅軍長征演義》,研究《三國演義》。父親一直惦記著怎樣實現周總理向自己提出的「要帶好徒弟」、「自己的孩子有沒有學評書」的囑咐。他原來認為女孩子是不能說評書的,可是在上海卻親眼看到了王少堂的孫女王麗堂,受到了王老的言傳身教,16歲就登臺說《武松打虎》。父親想到麗堂,很受啟發,決定選擇難度較大的《三國演義》口授給我。那時我正在北京師大附中讀高中,為了表達「北連學南王」的心情,父親把我的名字改為連麗如,意思是:南麗繼承南王評話,北麗繼承北連評書,祝願我與麗堂同志在書壇上茁壯成長。
粉碎了「四人幫」,1979年11月,有關單位為父親在八寶山舉行了徹底平反的隆重追悼會,《北京日報》予以報導。我也從工廠重返書壇。為了繼承連派評書藝術,我頑強地拼搏,終於恢復了《東漢演義》、《隋唐演義》、《三國演義》、《明英烈》幾部長篇大書的演出,受到廣大聽眾的熱烈歡迎。接著我為電視臺錄製了評書《三國演義》、《東漢演義》、《康熙私訪》等,在北京和各省電視臺播出,聽眾們給予很高的評價。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愛人賈建國的幫助下,我改編整理了200多萬字的評書手稿,並全部出版,包括《評書三國演義》、《東漢演義》、《康熙私訪》、《左良傳》、《程咬金大鬧瓦崗寨》、《斬莽劍》、《逍遙王》等。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父親在1936年出版的名著《江湖叢談》也多次再版,最新的一版就是在出版界享有盛譽的中華書局即將推出的精裝典藏本,著名漫畫家李濱聲老師還特地繪製了精美的彩色插圖──這對於喜歡我父親,喜歡《江湖叢談》的朋友來說,無疑是特大的好消息!
2003年9月4日,在我的努力下,紀念父親連闊如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在湖廣會館舉行,關學曾、譚元壽、常寶華、蘇叔陽、劉蘭芳、李金斗、孫毓敏、李燕、杜澎等藝術界老中青三代齊聚一堂,緬懷父親的高超書藝與崇高品格。劉乃崇老師回憶了與父親在建國初期為新中國曲藝事業共同奮鬥的光輝歲月;郝壽臣先生的公子、年近九旬的郝德元老師滿懷深情地講述了父親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捨身救人的事蹟,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雖然他們每個人的發言都很簡短,回憶父親的事蹟也只是點點滴滴,但一代評書大師的形象卻在人們的講述中逐漸鮮活起來。我想,父親的評書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人,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懷念他,惦記他,這充分證明了他的人格魅力與藝術成就。正如歐陽中石老師為父親題寫的那首詩所說:「敷演春秋稗史,公平月旦無私,口碑評書自相宜,不負微言大義。」
在懷念父親的同時,我也時刻不忘己任──傳承和發展連派評書藝術。其一,在相關部門的幫助下,北京評書順利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我也成為傳承人;其二,2007年6月,我收下了四個徒弟和兩個義子,北京評書後繼有人;其三,將觀眾重新請回書館,讓他們領略和欣賞真正的書館評書藝術。從朝陽小梨園到月明樓,再到如今每週末宣南、崇文、東城三個書館的紅紅火火,從一開始只有我一個人說書,到如今吳荻、賈林、王玥波、李菁、祝兆良、梁彥,這六個孩子每人都能上臺說演長篇大書……父親,如果您在天有靈,看到這一切,一定會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