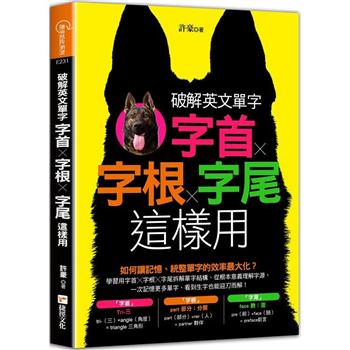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試管蜘蛛的圖書 |
 |
試管蜘蛛 作者:小野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3-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82 |
小說 |
電子書 |
$ 182 |
小說 |
$ 205 |
中文書 |
$ 205 |
中文現代文學 |
$ 234 |
現代小說 |
$ 234 |
小說 |
$ 234 |
文學作品 |
$ 238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試管蜘蛛
我在〈試管蜘蛛〉裡描述一個在中學教物理的魏老師,在他的實驗室裡想要創造一種不必靠蜘蛛網就可以捕抓獵物的蜘蛛,因為當蜘蛛編織好了那個八陣圖般的網之後,牠自己也被困在自己創造的枷鎖裡無所遁逃。我想寫的不止是求生存,還有屬於哲學上的思考。一個讀完生物系的二十多歲文藝青年總是愛胡思亂想,我沒有想到的是,蜘蛛也會在「適者生存」的環境中演化出新的品種……
作者簡介
小野
本名李遠,原本學的是分子生物,曾任國立陽明大學及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助教。就讀師大生物系時開始創作,出版《蛹之生》、《試管蜘蛛》等書,成為七十年代的暢銷作家。後來工作橫跨不同的傳播媒體,如電影、電視、廣告、文學和教育。擔任過中央電影公司製片企劃部副理兼企劃組長、台視節目部經理、華視公共化後第一任總經理、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台北電影節創始第一、二屆主席。
文學作品及電影劇本創作超過一百部,對於青少年及兒童的成長及教育特別感興趣。得過聯合報小說比賽首獎、英國國家編劇獎、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獎、電影金馬獎最佳編劇獎。小野童話得過金鼎獎最佳著作獎、中國時報年度最佳童書獎,並被德國國際青年圖書館列入向全世界推薦優良兒童讀物(White Ravens 1993- 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