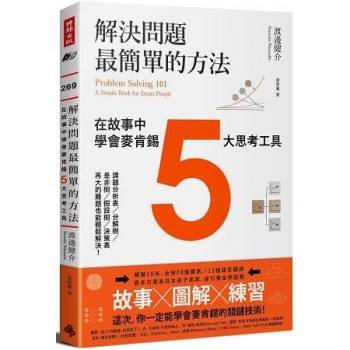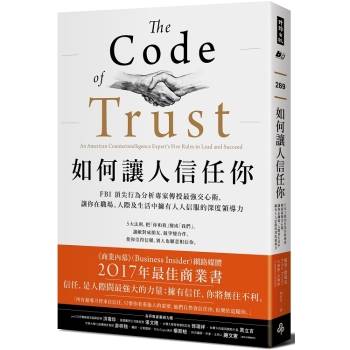一介浪人龍馬,竟從幕府手中獲得軍艦觀光丸,
置紛攘世局於不顧,朝貿易水兵的藍圖,更進一步!
不過一年,局勢翻轉,只見京都腥風血雨,人心生亂;至於地方,薩摩藩趨於保守,土佐藩老藩主山內容堂歸國,整肅勤王派,之前掀起暗殺政變的武市半平太受命切腹。佐幕的會津藩指揮新選組巡邏京都,取締勤王志士,路見即斬;朝中則是倒幕旗手長州藩失勢,倉皇撤退,結果變得益發激進,不斷炮擊歐美船艦,終於引來反擊,幕府也開始準備征伐長州藩。
只有龍馬,超然於尊攘之爭,依舊堅持自己的路線,靜待時機來臨。他同幕府要臣、諸國大名交往,爭取奧援;與恩師勝海舟攜手打造神戶的海軍塾,聚集志士、培訓水手,並終於獲得幕府給予軍艦觀光丸,由江戶駛往神戶與大?。至於千葉佐那子、田鶴小姐、阿龍的縷縷情絲,百般糾結,龍馬如何做出選擇?
龍馬的活躍舞台轉向海洋,幕末風雲將更掀狂濤!
作者簡介:
司馬遼太郎
一九二三年生於大阪,大阪外語學院蒙古語系畢業,原名福田定一,筆名乃「遠不及司馬遷之太郎」之意。
一九六○年以忍者小說《梟之城》獲直木賞後,幾乎年年受各大獎肯定。六一年辭去記者工作,成為專職作家,慣以冷靜、理性的史觀處理故事,鳥瞰式的寫作手法營造出恢宏氣勢。一九九六年病逝後,其「徹底考證」與「百科全書」式的敘述方法仍風靡無數讀者,堪稱日本最受歡迎的大眾文學巨匠。
中譯作品有《新選組血風錄》《幕末──十二則暗殺風雲錄》《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宛如飛翔》《宮本武藏》《項羽對劉邦:楚漢雙雄爭霸史》《鎌倉戰神源義經》《豐臣一族》《關原之戰》等。
《幕末──十二則暗殺風雲錄》
《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
《新選組血風錄》
《豐臣一族》
《關原之戰》
《宮本武藏》
《項羽對劉邦:楚漢雙雄爭霸史》
《鎌倉戰神源義經》
譯者簡介:
李美惠
輔大英文系、輔大日文所畢,研究平安朝古典文學。曾至橫濱菲利斯大學日本文學研究所交換留學。喜歡旅行,正好以翻譯為業,享受生活於動靜之間。譯作包括《影武者德川家康》《傾奇者前田慶次郎》《德川一族:創造時代的華麗血族》《信玄戰旗》《秀吉之枷》《龍馬行》(皆遠流)等。
章節試閱
〈人心騷動〉
總之,下令彈壓的元凶就是老藩主容堂。
龍馬對這位老藩主從未有過好感。
「身為藩主,他太主觀。」
龍馬如此認為。
像長州藩主那般,凡事聽從握有政權主導權的人而搖擺不定,固然讓人不以為然,但太有定見且冥頑不靈的頑固支配者也教人不敢苟同。
動盪不安的時期,時勢將如何發展完全無法預料。
如此時期,藩的指導者究竟是要如織田信長般不顧自己滿身瘡痍仍使勁揮刀、毫不猶豫地領頭開闢新時勢,或是索性把心一橫隨波逐流,只能二選一。
市井隱士就算了,若身為藩的指導者卻對時勢視若無睹甚至不知順應,還死命抓緊自己無用的「定見」,終究只有敗北一途。
「這人最難搞的是他對自己的才能及膽識過於自負。」
龍馬如此認為。
也因此才會對冥頑不靈的「定見」極端自滿。在他眼裡,部下個個笨得要命,其他大名也愚蠢至極。
「僅略勝於他人的智慧和知識,在如此時勢中哪能派上什麼用場?若只知對這些完全沒法指望的東西感到自負,那是注定要成為敗者了。」
龍馬如此預料。
「何況……」
他心裡是這麼想的:
儘管擁有蓋世才智,一旦受到局限就與蠢物無異。他如此認為。
智者容堂是位風度翩翩的英雄。
不幸的是,他卻受自己的聰明才智所局限。
受家世局限。
先祖山內一豐因關原之戰有功,從六萬石的掛川守一躍為二十四萬石的土佐守,得以躋身大大名之列,故對德川家懷著有恩未報的心理負擔。
「若純屬個人情況,這是一種美德。」
龍馬認為。
「但身為大藩之主,必須考量藩之命運及日本之歸趨,此時那些哪算得上麼呢!」
容堂一向受如此「美德」局限。他為擁有如此美德的自己深受感動,總是透過如此美德來審視一切時勢。
因此容堂所見的時事全是扭曲變形的,並非真實影像。
容堂自己明明也主張勤王主義,卻討厭藩內的勤王主義者。「我自己的勤王思想是源自聰明的智慧,他們不過是出自無知的瘋狂信仰罷了,故絕不能容忍。因為勤王無疑是種劇藥,斟酌得宜則成為良藥,但若錯估藥量,目前的社會秩序將整個崩壞。」
真是個不幸的智者。
容堂很厭惡浪人。
他們群聚京都,進出公卿宅邸,煽動大藩藩士。這些人看來雖不似幕府般具有危害性,但也是無用之徒。他如此認為。
「一群浪人豈能成就天下大事?」
他是貴族,當然會這麼想。
何況他愛極藩的統治制度。因為藩的首腦就是自己。
藩士只要像手腳般聽命於己即可,他可不希望手腳擅自做主、任意妄為。
不過最近最受矚目的是,各大藩駐京都的周旋方(譯註:藩派駐於京都的外交官)及其異常的活動情況。他們任意決定藩的方針,硬將整個藩拉往料想不到的方向。容堂是這麼想的。
以往在幕府強盛期,諸藩都設有「京都留守居役」的官職。
插句題外話。赤穗浪人中有位名叫小野寺十內的老人。這人是播州淺野家的上士,祿高一百五十石,職位就是京都留守居役。
當時是承平的元祿時期,據說他們的工作就是向藩報告京都時下最流行的衣服花樣及裝飾品等,以免主君後宮的婦女沒趕上流行。其他就只要與學者、歌人或畫家交流,聊些風流韻事即可。
因此十內夫妻都擅長作詩。他在四十七名赤穗浪人中是最富教養者。
但在幕末,此職位的工作卻完全變了質。
諸藩的京都周旋方、公用方(譯註:負責藩與朝廷、公卿及諸藩間公務交涉之職)及應接方(譯註:負責接待訪客之職)等外交官員乃是京都論壇的中心勢力,諸藩的這些職位者常在三本木一帶的妓院應酬,花錢如流水。
長州藩的桂小五郎、薩摩藩的大久保一藏(利通)、會津藩的外島機兵衛、一橋藩的涉澤榮一等都算代表人物吧。
土佐藩的京都周旋方則是因吉田東洋遭暗殺後的政變,全由勤王黨獨占。
武市半平太(瑞山)
平井收二郎(隈山)
間崎哲馬(滄浪)
這些人都是。
他們以藩的公費與他藩、尤其是激進派的長州藩應酬,也經常出入公卿宅邸,把極端的攘夷主義帶進宮廷之中。
容堂一進京便宣稱:
「無需與他藩應酬。」
而將他們悉數遣返土佐。
平井收二郎的文章中曾出現如下記載:
老藩主從江戶一到京即怒罵並禁止我等出入公卿宅邸。即使如此仍怒氣未消,最後竟撤銷我等官職。
同僚皆愕然而大失所望。
不僅如此。
東洋死後,為將領國內部人事安排改為勤王色彩,平井、間崎及弘瀨健太三人特請青蓮院宮(中川宮)下旨,以此令旨威脅藩之上層才成功推動政變。據說事實如此嚴重。
老藩主重新審查其罪狀,五月令此三人下獄,六月八日即命其切腹。
龍馬在神戶也聽到此消息。
龍馬聽到間崎、平井、弘瀨三人切腹消息,當下即直覺想到:
——啊……武市的勤王黨恐怕要瓦解了。
他立刻趕往京都藩邸。
龍馬這人雖是武市至交,但與武市之黨總是走不在一起。
意見有相左之處。
個性也不相同。
——下巴(武市的渾名)老說正經事。
龍馬總是這樣笑他。「正經事」有兩件,其一是死硬的攘夷主義,另一件則是一藩勤王的理想。
——這哪可能啊!
龍馬的個性是絕對不忘現實。武市半平太則是偏執的理想主義者。
龍馬完全不看好藩內的勤王活動,脫藩後更不將土佐藩放在眼裡。
「再和那個頑固的老藩主角力下去,就跟不上時勢了。」
這就是龍馬的想法。
但他仍十分關心參與藩內活動的成員現況。
「藩內的勤王活動根本是小孩玩火,遲早要搞砸的。」
一衝進河原町的藩邸,突然下起雨來。
邸內鴉雀無聲。自從老藩主大發雷霆,藩邸的火苗就完全熄滅了。他藩人士及浪人也不再出入,更無高聲談論時務者。
龍馬覺得這氣氛實在荒謬,他走在長長的走廊上時故意大喊:
「有誰知道這事嗎?聽說間崎等人在家鄉切腹啦?快告訴我實情吧!」
他邊走邊像個賣貨郎般吆喝。
走廊兩側的房間依然一片死寂。
龍馬往長屋走去。他邊走邊拍著格子門喊道:「告訴我啊!告訴我啊!」不知走到第幾戶時,終於有一扇門拉開了。是個名叫中島作太郎的年輕人。他的臉型就如橡樹子似的。
「?本爺。」
他小聲喚道:
「請進來吧。」
龍馬不識得這年輕人。大概剛從土佐上來沒多久吧。他身穿粗棉服,腰佩紅鞘的打太刀。以這身打扮及粗製的佩刀看來,應是鄉士出身。
「我叫中島作太郎信行。間崎爺在家鄉出事的來龍去脈我很清楚。」
他雙眼炯炯有神道。
龍馬於是走進屋內。
中島以托盤端送大茶碗給龍馬。龍馬一喝,竟是水。
龍馬一臉怪表情。
「您剛剛叫成那樣,我想喉嚨一定很乾吧。」
中島噗嗤地笑了。
這臭小子應該是個可用之才,龍馬心想。他喜歡中島,有幽默感。
作太郎即後來的中島信行(與板垣退助共同提倡自由民權主義,曾任自由黨主席。獲封男爵。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過世)。
根據中島作太郎的說法,間崎等人切腹時態度十分從容。
間崎哲馬因人在獄中身邊無筆,只得拿搓成條狀的紙排成文字而留下辭世之作。
大丈夫今日雖將死亦不悲。
略見聖朝恢復舊儀。
尚有一事空留千古遺恨,
京畿尚未豎起柏章旗。
京都朝廷之威已大致恢復,此乃我生平之志。既已見此成果,今日將死亦不覺悲傷。然而正當薩長已成擁護京都朝廷主要勢力之際,卻唯有我土佐藩的柏章旗尚未能在京都揚起,實在遺憾。大意如此。
柏章旗之所以沒能飄揚京都,全因老藩主容堂的因循苟且。間崎臨切腹之際也忍不住痛罵主君後才動手。得年三十。為他介錯的是其堂弟間崎卓一郎。
間崎之妻已故,只有一個才兩歲的女兒。他死前似乎極不放心,故留下此詩:「是否有人守護呢?白露時節棄而不顧之撫子花(譯註:石竹花,此處是指間崎兩歲的女兒)。」
弘瀨健太平常就說:「男人的名譽取決於能否完美無缺地切腹。」他甚至仔細研究了切腹的方法。根據弘瀨的研究,首先應從左腹刺入,向右橫拉後再將刀鋒斜斜上轉,利用餘勢刺入左乳下之致命處,如此定能絕命。
弘瀨從容不迫地就位準備切腹時,對介錯人道:
「我還沒完成所有步驟之前,千萬別砍掉我的頭啊。」
他根據自己的「研究」一步步進行,最後竟不需介錯。
平井收二郎年二十九,與龍馬同年。
他在獄中以指甲刻下絕命之詩,然後一身白服,從容就位準備切腹。
介錯人是從小和他一起上道場習刀的好友平田亮吉。亮吉面無血色十分緊張,故平井還轉頭鼓勵他:
「鎮定一點。」
他鬆開腹部並撫摸一陣子。
「該上路了吧。」
說著握住短刀,運氣刺入腹中。介錯的亮吉驚慌之餘連忙揮刀砍下。但手一抖,「喀」一聲砍中後面的頭骨,刀刃也彈了回來。
「喂,不是叫你鎮定一點嗎?」
平井道。他的臉已因痛苦而扭曲。
第二刀終於順利砍下頭來。
「我聽到的就是這樣。」
中島作太郎道。
「這樣嗎?」
雨勢愈來愈大。
房間不但更顯昏暗,甚至還聽得見遠處的雷聲。
雷聲迅速逼近,彷彿天空在頭上爆裂般響亮。
「老天爺在要求血祭。」
難得龍馬也會說出這種充滿詩意的話來。
「不上不下的方法是無法改變人世的。間崎等人雖死,但我遲早要用雙手翻轉整個天下,以慰他們在天之靈。」
中島說,武市雖尚未下獄,但依情勢看來一切實在很難預料。
龍馬暗覺中島容貌好笑,是個「橡樹子小鬼」。
這個年僅十八歲的年輕人敘述完後,雙手支地道:
「在下有事相求。請讓我中島作太郎信行入神戶塾學習。」
在這種情況下,龍馬自然而然就答應了。
「你那麼喜歡船嗎?」
「不喜歡。光是在堤防上遠望淀川上的三十石船(譯註:可載三十石米的船,特指江戶時代沿淀川往來伏見、大?之間的客船)左搖右晃,我就暈船了。」
「這麼說來你在京都、大?經常在堤防散步囉。」
「是的。」
「想順便到海上走走嗎?」
「若您要我去,我當然會去。只是得請您先教我怎麼走。」
「你這傢伙還真有意思啊。」
看來,相較於學習航海相關技術,作太郎似乎更想私下跟龍馬學習。
龍馬立刻去見藩的重臣,請他代向藩方申請中島修習航海術的手續。
對方十分乾脆地答應了。
龍馬就此走出藩邸。
他心血來潮,轉到梨木町的三條屋敷找田鶴小姐。
「啊,是?本大爺。」
門衛已認得他。
不過門衛不解的是,這位頗有名氣的土佐藩士並不是來找當主三條實美,每次都只找當主之母信受院夫人身邊的田鶴小姐。
在當時若提到三條卿,可是以長州藩為靠山的激進派尊攘公卿,在天下志士之間頗孚人望呀。
諸藩之士競相親近三條家,武市半平太等人也經常在此出入。
擁戴政治方面毫無智慧的公卿,藉著宮廷的權威來對付幕府。這就是當時志士慣用的手段。
「這也是種手段。」
龍馬也認同。
「但我偏不喜歡公卿。」
公卿對金錢完全不具抵抗力。從前大老井伊直弼締結開港條約時,曾為取得天皇敕許而以金錢賄賂有力公卿,結果眾公卿之意見無不因此而大幅軟化。
此事乃天下周知。
「公卿中惟獨三條大人(對金錢)有潔癖,甚至已達不知變通之地步。」
龍馬如此聽說。
但他卻對三條卿毫無興趣。
信受院夫人係出自土佐山內家,故三條宅邸後院的信受院夫人房間總是瀰漫著一股若有似無的武家風情。
「龍馬大爺又來訪嗎?」
信受院夫人覺得好笑。
「是。」
田鶴小姐點頭,又道:
「聽說他最近在神戶研究黑船,不知現在來京都有什麼事?」
她當著信受院夫人的眼前像個姊姊似地蹙起眉頭。
龍馬和以往一樣被帶到正門邊那間微暗的房間。
田鶴小姐來了。
依然美麗動人。
「好久不見。」
田鶴小姐道。其聲音特徵是溫柔而略顯嬌媚。
「是。」
龍馬搔著背。
「您背癢嗎?」
「啊,我在做什麼?」
他趕緊把手放回膝上。他只是無意識地搔抓,被田鶴小姐一說才驚覺的。
「龍馬大爺身上老覺得癢嗎?」
田鶴小姐覺得好笑。老是這身髒兮兮的打扮,身上當然常覺得癢囉。
「您那件貼身襯衣恐怕都長蟲了吧?」
她收起笑容微偏著頭道。
「沒有的事。那怎麼可能。」
「我看沒錯喔。在背上養蟲的話,女人是不會看上您的呀。啊,對了,說到女人……」
田鶴小姐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表情。
「您後來跟那位楢崎將作之女阿龍小姐有什麼進一步的發展嗎?」
「妳說她呀。我拜託伏見的船宿寺田屋老闆娘收她當養女了。」
「然後呢?」
田鶴小姐似乎對後來發展很感興趣。
「什麼然後?」
「就只有這樣嗎?」
「是啊。」
龍馬又開始搔起背來。
「請您別再抓啦,不是提醒過您了嗎?」
「啊,是喔。」
龍馬用力朝癢處多抓幾下,這才一本正經把手放回膝上。
「您果然需要女人為您打點生活起居啊。難道您沒有意中人嗎?」
「……」
其實我是喜歡田鶴小姐。可在這以身分階級建構而成的人世間畢竟是不可能的事。
在江戶是有千葉佐那子啦。她似乎對自己頗心儀,雖然身分也相稱,但畢竟是師傅的千金,是好人家的女兒。我今後將成為一介窮浪人,恐將如影子般四處漂泊,如此生活怎能帶給千葉家千金應有的結婚生活呢?
還是選擇阿龍吧。
在這茫茫人海中,阿龍是唯一失去我龍馬的庇護就活不下去的女子吧。正因如此,我對阿龍懷有不同於田鶴小姐或佐那子的感情。
「嗯,龍馬大爺,我可是把話說在前頭。我覺得那位名為阿龍的小姐不會帶給您幸福的。」
「我不需要幸福吧。」
龍馬道。
〈人心騷動〉
總之,下令彈壓的元凶就是老藩主容堂。
龍馬對這位老藩主從未有過好感。
「身為藩主,他太主觀。」
龍馬如此認為。
像長州藩主那般,凡事聽從握有政權主導權的人而搖擺不定,固然讓人不以為然,但太有定見且冥頑不靈的頑固支配者也教人不敢苟同。
動盪不安的時期,時勢將如何發展完全無法預料。
如此時期,藩的指導者究竟是要如織田信長般不顧自己滿身瘡痍仍使勁揮刀、毫不猶豫地領頭開闢新時勢,或是索性把心一橫隨波逐流,只能二選一。
市井隱士就算了,若身為藩的指導者卻對時勢視若無睹甚至不知順應,還死命抓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