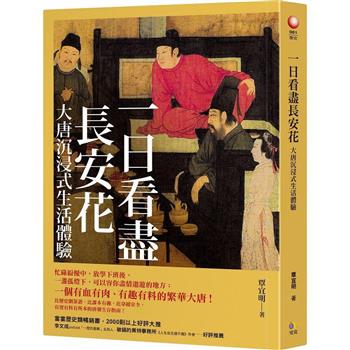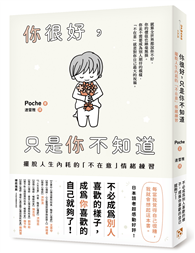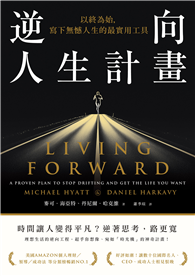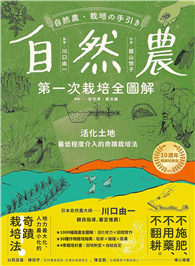遠流╳師大譯研所「經典文學新譯計畫」NO.3
中文版獨家收錄史蒂文生〈關於夢的篇章〉
與《包法利夫人》、《死魂靈》相媲美,
近乎詩一般的小說--納博可夫
納博可夫、波赫士、海明威、吉卜林、喬伊斯.卡洛.奧茲(Joyce Carol Oates)等文壇重量級作家一致推薦
《化身博士》的緣起是作者史蒂文生不斷重複做的一個惡夢,在夢中,他變身為另一個可怕的男人在暗巷為非作歹。史蒂文生在三天內把這個夢中的經歷寫下來,卻被妻子評為「低級小說」,於是便把整份稿子燒毀,花了三至六天的時間重寫,之後又花了四到六週的時間潤飾修改。
由於故事懸疑曲折,深入刻畫人類潛藏的欲望與陰暗面,出版後讓許多從來不讀小說的民眾都爭相閱讀,從維多利亞女王,到講道與教會刊物都引述故事內容,可見其受歡迎之程度。
書中描寫主角傑奇博士是位地方上公認慷慨助人、樂善好施的人士,而某天在倫敦街頭發生了一樁社會案件後,傑奇博士的好友厄特森律師無意間發現,犯案嫌疑者海德先生就住在傑奇博士的家,而且傑奇博士竟然在自己的遺囑中,指定海德先生擔任繼承人。厄特森律師於是和藍楊醫生聯手,想要查明真相到底如何。
不過情況出人意料轉趨惡化,傑奇醫生的行為越來越奇怪,最後變得離群索居,鬱鬱寡歡;海德先生則犯案累累,惡名昭彰。厄特森律師和藍楊醫生想要保護摯友,於是不斷抽絲剝繭,最後赫然查出,海德先生的身份不但啟人疑竇,而且與傑奇博士的關係非比尋常……
《化身博士》是史蒂文生創作生涯的成名代表作,曾多次被改編成舞台劇、電影、音樂劇,近年更被改編為電玩遊戲。本書亦為現代心理小說的先驅,而由於情節扣人心弦,緊張懸疑,納博可夫盛讚為現代偵探小說的鼻祖。
本書特色
★遠流與師大翻譯研究所合作,推出全新譯本
★獨家收錄史蒂文生〈關於夢的篇章〉
★《溢出》作者葉佳怡推薦專文
★附錄史蒂文生年表
★譯者分析文章
★李家同最愛的40本書之一,學子一定不能錯過的好書
★納博可夫、波赫士、海明威、吉卜林、喬伊斯.卡洛.奧茲(Joyce Carol Oates)等文壇重量級作家一致推薦
★開創現代心理小說先河名作;現代偵探小說的鼻祖之一
★關於人格分裂主題有史以來最暢銷的作品
★探討主題深入:雙重人格、人性善惡、文明與野蠻
★多次改編舞台劇、電影、電玩遊戲,主角也成為科幻經典角色原型
作者簡介:
羅勃‧路易斯‧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
出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英國著名的小說家、詩人與旅遊文學作家。自小大量閱讀文學書籍,特別喜愛莎翁的作品與《一千零一夜》,雖於25歲取得律師資格,但因身體狀況不佳,未曾從事過律師一職。之後前往法國,在巴黎結識許多作家、評論家與經紀人後,開始創作,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與評論。
1883年,他在養病的期間,出版首部長篇小說作品《金銀島》,大受歡迎;1886年問世的《化身博士》則讓他聲名大噪,半年內銷售四萬本,旋即超過25萬本,連維多利亞女王都讀過,泰晤士報、各種評論及教會講道都引述這本小說。
史蒂文生1894年因腦溢血過世,死前仍一直創作不綴。雖然他的作品總被歸類為青少年文學與恐怖小說,但到了20世紀晚期,他開始被文學界重新評價為擁有過人洞察力的文學家,與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地位等同,在學術界受好評的排名更超過狄更斯、王爾德與愛倫坡。
譯者簡介:
范明瑛
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畢業,曾任報社兼職編譯、電視台新聞編譯,現專職口筆譯工作。出版譯作包括《非暴力溝通:打造優質校園》(光啟出版社,2012)、Teaching Children Compassionately (尚未出版)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這個悲劇故事是敘述傑奇博士這位對人類智識極限充滿好奇的科學家,如何被另一個充滿罪惡念頭的自我所控制,現今讀來仍是令人毛骨悚然。--觀察家日報
與《包法利夫人》、《死魂靈》相媲美,近乎詩一般的小說。--納博可夫
《化身博士》一開頭就令人欲罷不能,至今仍是關於人格分裂小說的最佳之作。--亞馬遜網路書店
傑奇博士與海德先生是「詩性智慧」(mythopoetic)般的人物,就如同科學怪人、愛麗斯夢遊仙境、德古拉伯爵,而作者筆下描寫的雙重人格可與柏拉圖、王爾德、狄更斯德與愛倫坡的作品相比擬。--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喬伊斯.卡洛.奧茲(Joyce Carol Oates)
名人推薦:這個悲劇故事是敘述傑奇博士這位對人類智識極限充滿好奇的科學家,如何被另一個充滿罪惡念頭的自我所控制,現今讀來仍是令人毛骨悚然。--觀察家日報
與《包法利夫人》、《死魂靈》相媲美,近乎詩一般的小說。--納博可夫
《化身博士》一開頭就令人欲罷不能,至今仍是關於人格分裂小說的最佳之作。--亞馬遜網路書店
傑奇博士與海德先生是「詩性智慧」(mythopoetic)般的人物,就如同科學怪人、愛麗斯夢遊仙境、德古拉伯爵,而作者筆下描寫的雙重人格可與柏拉圖、王爾德、狄更斯德與愛倫坡的作品相比擬。--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喬...
作者序
導讀
化身博士:雙重人格、理性至上,亦或瘋癲失語?
蘇格蘭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一八六六年出版了《化身博士》(Doctor Jekyll and Mister Hyde),這部作品篇幅不長,角色不多,原本被視為簡易的通俗作品。然而通俗作品之所以能成功,便勢必有擊中當時人民心中普遍埋藏的情感或慾望,於是後來也引發了眾多論者分析,抽絲剝繭出許多有趣的時代光影與象徵母題。
這個帶有歌德風的故事發生在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 Era,1837-1901)的倫敦,其中的傑奇博士(Doctor Jekyll)為備受稱譽的科學家,喝下藥水後卻成為邪惡的海德先生(Mister Hyde),所以人們往往將其視為描寫「雙重人格」的作品,並以此脈絡進行一個人「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善惡辯證,然而如果從歷史背景細細推敲到當代,會發現其中仍有許多可疑或值得探討之處。
以當代醫學而言,「雙重人格」或「多重人格」通常為童年創傷後的結果,是為了面對極大衝擊後的應變措施,然而,無論出現的人格數量為何,人格與人格間的關係又是如何錯綜複雜,基本上都仍保持可辨識的人格邊界。以著名的《二十四個比利》(The Minds of Billy Millian)為例,主角的每一個人格幾乎都有不同的性別、個性、職業、喜好甚至身體缺陷,每個人格與人格間或許彼此知曉並表現出好惡,又或許對彼此一無所知。然而,如果我們以此來檢視故事中的「傑奇博士」與「海德先生」,會發現此兩者並非截然不同的人格,或者我們至少可以說: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海德先生」的自白!我們聽到的始終是「傑奇博士」的掙扎與吶喊,然而,如果我們不用「雙重人格」的脈絡來檢視,人性的壓抑與掙扎為何需要以如此奇詭的方式來表現?
為了理解故事背景,讓我們先回到維多利亞時代。首先,英國於一八三二年通過了議會改革法案,確保了資產階級的地位,一八三七年,年僅十八歲的維多利亞女王繼位,在她保守的統治下,英國進行了極為成功的工業革命,於是國家經濟繁榮、科學發展昌盛,對外的殖民地面積也到達高峰,在這樣的情勢下,理性、正向與樂觀的心態主導了社會氛圍,卻也將許多原本流通在社會中的「不潔淨」概念壓抑到了各種必須受限的所在。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便談過維多利亞時期對於「性」的控管,「性被小心謹慎地封藏起來,它遷入新居,被夫妻家庭所獨占,全力以赴承擔起嚴肅的、繁殖後代的職責。於是,提及性,人人緘口。」
此外,精神疾病的醫療化也是源自此時期,心理學家湯瑪斯.沙茨(Thomas Szasz,1920-2012)便提到,十九世紀的前半還是用「道德感化」作為治療手段,但後來也逐漸進入「醫療化」的領域;精神病學開始蓬勃發展,精神病院也成為獨立於理性大眾的隔絕場所。此外,經濟急速起飛後出現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但在社會樂觀的氛圍下,窮人也被掃進角落,沒有人願意去正視劇烈發展造成的弊害。著名文豪查爾斯.約翰.赫芬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的許多作品便是在批判此時的階級與貧窮問題。
因此,如果我們以此歷史背景回頭觀照「雙重人格」的論述,會發現與其探討人類是否於心智內在存有「善惡衝突」,不如拉遠視角,仔細檢視身為律師的主述者厄特森先生、身為科學家的傑奇博士/海德先生,以及另一位同為科學家的藍楊醫生。以社經脈絡來看,此三人都位處菁英階級,其他僕人或妓女等低下階層的角色則是配角,沒有獨特的個性與聲音,於是唯一接近低下階層且形象鮮明的只有「海德先生」;以理性脈絡來看,「海德先生」又是一個科學成就下產生的慾望怪物,而在面對這樣一位「海德先生」時,律師厄特森、傑奇博士與藍楊醫生都有各自的觀點,似乎也都代表了當代各種維多利亞人的心思--面對盛世之下的陰影,法律、科學與醫學各自表態,然而在這些觀點中,「善」真的存在嗎?「慈善」與「善」是同義詞嗎?至於應該在英國社會扮演要角的宗教,也僅在傑奇博士最後的自白中出現這麼一段關鍵句:「它(人類的善惡雙重性)是宗教的起源,也是人類諸多苦難的源頭之一。」似乎只側面映照出那個時代中信仰對於撫慰人心之無力。
如果再往深處探詢,「海德先生」不具羞恥心的作惡心態與其說是邪惡,不如說是被當時視為「瘋癲」的「疾病」。人們對此感到不安、亟於將其消滅,希望這抹幽靈「消失」在眾人生活中。或許為了映照出這股強大的壓力,那所謂「瘋癲」的化身始終處於幾乎失語的狀態。然而到了故事的最後,「消失」的究竟是誰?「死亡」的又是誰?理性等於善良嗎?善良是純粹的概念嗎?或者我們進一步問:邪惡與善良可以截然二分嗎?而瘋癲又等於邪惡嗎?所謂「不顧後果的邪惡」難道不是社會建構下製造出的「邪惡」嗎?即便看似簡潔的文本,當我們仔細檢視每個角色的個性與觀點時,似乎都還能發現這些提問不停在其間游移閃爍。
又或許更重要的是,在不停「化身」的情節中,我們真的看到一個人的意識被切割開了嗎?傑奇博士本來便是善惡綜合體,為何需要另一具身體盛裝「更純粹」的惡?比起「多重人格」的「一身多靈」,《化身博士》其實更像個「一靈多身」的故事,是一種身體被賦予比靈魂更多想像力的「物質性神話」。所以或許,與其說這是一個「善與惡」的故事,不如說是一個「善與惡」在科學物質世界失語的故事--在某些極致的時刻,善與惡都不夠理性、不夠樂觀,不過都是失去了話語權的瘋癲。
如果和一八一八年同樣於英國出版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作對照,故事中的主角同樣以科學手法製造出了另一具「身體」,然而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y)受到強烈的浪漫主義思潮影響,雖然採取狀似當代科學實驗的情節,但想召喚的卻是類似古代煉金術士般的情懷,比如故事主角就曾表示,「我的空想不只是這樣而已。由於我所喜歡的作者一再保證他們能夠喚出幽靈或魔鬼,所以我熱心地要讓那保證實現,但我的咒語總是以沒有成功告終。」於是這個彷彿從遠古時代被召喚回來的怪物,其實也是一個主角身為浪漫主義者的理想實體,只是在當代的科學理性中,即便他自行學會了語言,但永遠註定是具殘缺的身體--半是來自當代科學的無能、半是來自浪漫主義者在當代的命運。
其後的《化身博士》彷彿更進一步,直接把這個不合時宜的身體創造在自己身上,雖然史蒂文森並不像雪萊一樣受到浪漫思潮的洗禮,但這個?多餘的身體」卻都像是來自遠古的控訴。在希臘神話中,預言家常是狀似瘋癲之人,瘋癲本來可以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符號,但現在除了科學理性規範之外,所有剩餘的部分成為必須被隔絕的元素。雖然《化身博士》中對於此元素的描述仍為「善惡二元對立」,但當傑奇提到「我自己從這新生命吸進第一口氣時,就知道這個自我更為邪惡,比原本的我邪惡十倍,將原本的我出賣給我原始的罪惡。」那「原始的罪惡」似乎便已保留了往上追索的通道,只是當時的預言家只需要將瘋癲豢養在自己身體內,科學時代卻需要另一個身體,來證明瘋癲確實存在,甚至我們必須將其稱為「不害怕後果而感受到的邪惡」,才能讓現在的人們稍微接近、嗅聞到瘋癲氣息。
或許就像那讓傑奇博士化身的鹽狀晶體一般,一直要到最後,人們才會發現真正作用的不是科學,而是那偶然存在又消失的雜質,仍穿越古今呼喚我們心底的另一個世界;而那世界無關善惡,純粹是在意識底層,一道毋須被施以價值判斷的湧動伏流。
譯者序
只看過改編作品,別自以為你看過《化身博士》
《化身博士》是恐怖小說文類的經典名著,也讓作者史蒂文生奠定知名作家的地位。此書在一八八六年出版後大受歡迎,歷經無數的改編、重製,搬上舞台,翻拍成電影或電視劇,故事的象徵意義因此廣為人知,影響力超越原來的文本。許多人、包括我,都「自以為」以為了解故事的概念,從來沒想到要把原著找來看看。我看過音樂劇版本的《化身博士》(Jekyll and Hyde)後,大為激賞,從此將之奉為圭臬。後來終於把原著從頭到尾讀完後,我才愕然驚呼:「原來是這樣!」這一回,請忘記所有的「自以為」,看看這個故事「原來到底是怎樣」。
原著的章節架構如同偵探小說,讀者以主要角色厄特森律師的眼光,觀察傑克博士身上發生的變化,以及周遭的環境與事件。透過厄特森律師自己的觀察、友人的轉述、警探的偵查、目擊者的證詞與事件關係人的紀錄與自白,讀者可以一路慢慢拼湊出事件的原貌,並在最後一章做完整的前後對照。因此按照章節順序閱讀至最後,讀者可以享受一路抽絲剝繭、最後真相大白的樂趣。
小說的前八章為敘事穿插對話,著重情節的推展;最後兩章則偏重敘述者的自我剖析。文字風格較為繁瑣,有許多結構複雜的長句,或是一句中使用三至四個分號,部分章節的段落篇幅很長且沒有分段。這種文字風格容易在閱讀時造成心理負擔,拖慢閱讀節奏。尤其段落較長的章節,雖然敘事條理清晰,但是一句接一句連綿不斷,仿佛敘事者害怕一被打斷就無法繼續。讀起來也如同身陷無法醒來的惡夢中。
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羅傑‧拉克赫斯特教授(Roger Luckhurst)在二○○六年編輯一部史帝文生作品選集,他在序言中指出,史蒂文生長年臥病在床,一邊服用鴉片止痛,一邊狂熱地創作。在撰寫某個雙面人故事的期間,他晚上睡覺時,夢到了傑奇博士這號人物:「這個人吞下藥劑、變成另一種生物……我醒來就知道,這是故事的關鍵。在我再度入睡之前,故事所有的細節已經清楚浮現在我腦中。」接下來的日子裡,他瘋狂地把夢境寫成白紙黑字,僅用六週的時間就完成整個故事。以此要證明如同夢囈般的敘述,反映的正是作者的夢境,似乎太過牽強。但這種敘述方式,與書中主角力求從惡夢中解脫的心境,卻不謀而合。
根據我粗略蒐集的資料,台灣《化身博士》的版本將近二十種,書名的翻譯大概都翻成《化身博士》或《變身怪醫》。其中約三分之一為全譯本,另外三分之二是以圖畫書形式呈現的兒童讀物,或是經過縮寫、改寫的簡略版青少年小說,又或是英語學習教材。縮略版本的共同特色,就是刪除與主要情節無關的敘述,切割長句,將長段分為數個短段。雖然減輕閱讀時的負擔,卻也削弱偵探故事不可或缺的懸疑感。全譯本則大多亦步亦趨地緊跟原文,標點、句型少有更動,延續原文長句連綿不絕的特徵。我在翻譯時,一方面想忠實呈現原文,另一方面又想減輕讀者的負擔,因此綜合了兩種譯本處理的方法。我以閱讀的舒適流暢為準則,避免長句,換掉不符合中文習慣的標點。太長的句子就適時斷句,太長的段落也會切成多幾段。新的短句常需要增加字詞,整個句子才完整。為怕增譯扭曲原文,我盡量保留原文每個字意義,以免自己詮釋過度導致譯文偏離原意。
長句分成短句的例子(例一)如下:
(Chapter 2) His past was fairly blameless; few men could read the rolls of their life with less apprehension; yet he was humbled to the dust by the many ill things he had done, and raised up again into a sober and fearful gratitude by the many that he had come so near to doing, yet avoided.
我的翻譯:
他的過去幾乎無可指責,沒幾個人在檢視自己的過去時可以這麼放心。但是他幹過的壞事仍然讓他感到無地自容,而其他許多在最後關頭得以避免的錯事,又讓他恢復冷靜,感到既慶幸又恐懼。
這一段的原文本身是一句完整的句子。我大致在原文打分號、逗號的地方斷句,並且把 raised up again…yet avoided拆成三小句,讀起來較輕鬆,又不致破壞原意。
其他版本的翻譯參考:
他的過去可稱無瑕可擊,不過很少人在細讀過去生涯時會不心存憂慮,為了他做過的一些不軌感到恥辱,但是又因為一些懸崖勒馬的行為而抬頭感謝。──張時譯本
他的過去幾乎是無可責備的,其實每個人都清楚自己過去的是非對錯,但他對於自己所犯的一點小錯卻感到非常卑賤,但另一方面,他也對於自己差點就犯下錯誤但又及時收手的過往經歷而心懷感激。──向日葵工作室譯本
他的過往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地方;很少有人可以跟他一樣如此細審自己的一生,卻能像他一樣坦蕩蕩、鮮有惶惶不安之色。然而,在想到自己過去所犯的罪衍時,卻也不免滿臉羞愧地把頭垂得低低的,繼而再想起許多差點去做,所幸及時避開的事情時,又神情肅穆地抬起頭來,流露出滿心戒慎恐懼的感激。──鄭鳳英譯本
結構上,張時和向日葵的譯本較貼近原文,保留長句。鄭鳳英譯本將長句拆成短句,另加不少字詞解釋語意,例如less apprehension不只是「鮮有惶惶不安之色」,還加了「坦蕩蕩」。
增譯但同時保留原文字意的例子(例二)如下:
(Chapter 10) Strange as my circumstances were, the terms of this debate are as old and commonplace as man; much the same inducements and alarms cast the die for any tempted and trembling sinner; and it fell out with me, as it falls with so vast a majority of my fellows, that I chose the better part and was found wanting in the strength to keep to it.
我的翻譯:
雖然我現在的處境十分奇異,但這場天人交戰的條件,也跟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而常見。一樣的誘惑、一樣的警告,替每一個心癢難搔、顫抖不已的罪人拋出命運的骰子。骰子向我揭示的命運,如同大部分人一樣,就是選擇較為高尚的自我,然後發現自己缺乏堅持正道的力量。
我選擇將human翻譯成「人類的歷史」,是為對應「古老」的形容;而die不只是「骰子」,還是「命運的骰子」,除了增加戲劇性,接下去翻譯 it fell out with me也可以有比較多的詮釋空間。
其他版本翻譯參考:
我的境遇十分奇特,這種辯論的條件已和人類一樣古老。任何受誘的顫抖罪犯會懷著同樣動機與緊張擲下骰子;它落在我頭上一如落在我許多同胞身上;我選擇了最好的部分並且希望能找到維持它的力量。──張時譯本
這有點像賭徒下注的例子,都是滿懷著期待和恐懼擲出那決定命運的骰子。結果我之於海德,就如同那渴望得知輸贏的賭徒般。最後,我還是決定繼續當吉柯。──向日葵工作室譯本
儘管我當時的處境是那麼地詭異,但這番思量所考慮到的條件卻與一般人無異──陳舊且平淡無奇。每一個令人聞風喪膽的罪犯,他們所受的誘惑與所聽到的死亡警訊,和我現在所遭受的情況差不多。就如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最後我還是選擇了那個本性較好的角色,不過事後卻發現缺乏足夠的力量來維持這個決定。──鄭鳳英譯本
張時譯本在結構、用字和標點上都非常貼近原文,反而有點不自然,像是「辯論的條件」和「最好的部分」都語焉不詳。向日葵譯本省略the terms...as man這段,強化「賭徒」這個比喻,骰子也一樣解釋成「命運的骰子」,並且簡化I chose…keep to it的意思。鄭鳳英譯本則捨棄原文中與「骰子」相關的寓意。
比較這三個參考譯本,張時的譯本最貼近原文,不過有時譯文因此顯得古怪或不合邏輯。向日葵工作室有時會略過某些字句不翻,雖不影響文意理解,但也因此略失原文完整的風味。鄭鳳英亦常使用截長句化短句的策略,增譯的部分為三個版本中最多。在長句時,鄭的譯文閱讀起來較舒適;但在比較簡單、平鋪直敘的部分,譯文又顯得繁瑣、累贅,甚至過於咬文嚼字。
除了推敲字句之外,我也一直在「翻譯」和「(重新)寫出一個精彩的中文偵探故事」的尺度之間掙扎。如上文例二所示,我增加的字句中,除了要讓文意通順完整,有時也確實是為了增加效果。這種加油添醋要到什麼程度才不算過分、沒有扭曲原文之嫌,讓我頗費思量。最後的完稿,是在對照原文、反覆推敲增刪之後的成果。至於我的詮釋是否「適當」、有沒有「過份」,只能期待自己自由心證的尺度能合乎讀者的口味了。與其他大部頭經典相比,此書著實輕薄短小。抽出個把小時的空檔,讓新譯本告訴你,流傳超過百年的「傑奇博士與海德先生的奇異個案」,究竟有多奇異。
導讀
化身博士:雙重人格、理性至上,亦或瘋癲失語?
蘇格蘭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一八六六年出版了《化身博士》(Doctor Jekyll and Mister Hyde),這部作品篇幅不長,角色不多,原本被視為簡易的通俗作品。然而通俗作品之所以能成功,便勢必有擊中當時人民心中普遍埋藏的情感或慾望,於是後來也引發了眾多論者分析,抽絲剝繭出許多有趣的時代光影與象徵母題。
這個帶有歌德風的故事發生在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 Era,1837-1901)的倫敦,其中的傑奇博士(Doctor Jekyll)為備受稱譽的科學家,...
目錄
總序
聽見譯者的聲音──賴慈芸
推薦序
化身博士:雙重人格、理性至上亦或瘋癲失語?──葉佳怡
譯序
只看過改編作品,別自以為你看過《化身博士》
化身博士
特別收錄
關於夢的篇章──徐立妍/譯
史蒂文生大事年表
總序
聽見譯者的聲音──賴慈芸
推薦序
化身博士:雙重人格、理性至上亦或瘋癲失語?──葉佳怡
譯序
只看過改編作品,別自以為你看過《化身博士》
化身博士
特別收錄
關於夢的篇章──徐立妍/譯
史蒂文生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