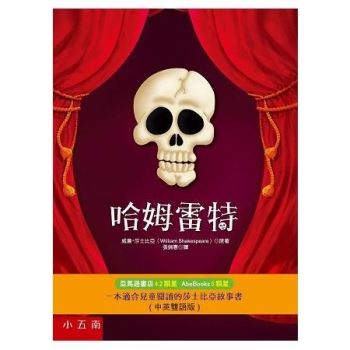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45 |
台灣史地 |
二手書 |
$ 248 |
二手中文書 |
$ 277 |
Others |
$ 315 |
中文書 |
$ 315 |
台灣研究 |
$ 315 |
社會人文 |
$ 357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近年來第一本由賽德克族人撰寫的霧社事件中文專書!
郭明正老師出版《真相‧巴萊》一書後,引發非常大的迴響,很多看過電影《賽德克‧巴萊》的觀眾與讀者都希望更深入了解賽德克族和霧社事件。
事實上,郭老師剛開始向族老們請教時,他的初衷並非研究「霧社事件」,而是先意識到賽德克族沒有文字,所有的經驗與智慧僅憑口傳,眼看著族老們快速凋零,記錄族群的歷史文化才是當務之急。然而,霧社事件終究是遺族耆老們刻骨銘心的記憶,他們講述歷史文化之時,每每會論及霧社事件的人、事、物,讓郭老師深刻體認到這個事件對賽德克族影響之深遠。
多年來,郭老師經常憶起族老們與他對談時的諄諄教誨與期許,於是他決定模仿當時的情景,以一問一答的方式,為賽德克族文化留下珍貴的文字紀錄,並記述先輩族人發動霧社事件的悲壯歷史,以及族人們浴火重生的「餘生」心情。
要確立霧社事件的記述觀點時,郭老師認為這段歷史不是只有過去所熟知的莫那‧魯道,而是六個部落一千多名族人的總體抗暴行動,今日清流部落的每個家庭都傳述著各自的悲歡故事。因此,他勉力彙整不同部落、不同家族的記憶與經歷,希望呈現出霧社事件的多樣面貌。
作者簡介
郭明正
屬於賽德克族德固達雅群,族名叫 Dakis Pawan,1954年出生於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川中島)部落,為參與「霧社事件」的馬赫坡社後裔。師大工業教育系畢業,國立埔里高工機械科專任教師退休。
曾參與多項賽德克族德固達雅語的翻譯、出版品編纂與顧問工作,包括臺大語言所德固達雅語發音人、臺北市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課務專員與講師、中研院民族所《蕃族調查報告書:紗績族前編》德固達雅語復原工作、臺灣歷史博物館「霧社事件口述歷史影像紀錄」翻譯工作、青年高中舞蹈科大型原創舞劇「賽德克之歌」翻譯及顧問、《賽德克‧巴萊》電影歷史文化總顧問、教育部國中小學德固達雅語教材與賽德克族文化基本教材編輯委員、南投縣政府《賽德克族族語圖解辭典》執行編委、行政院原民會《賽德克語字典》編纂協同主持人。 2011年把多年來進行「霧社事件」研究的調查結果,加上參與電影《賽德克‧巴萊》的隨拍札記,出版《真相‧巴萊》一書,極獲好評。亦曾與輔大宗教系簡鴻模教授及東華大學助教依婉o貝林合編《清流部落生命史》,並兩度獲得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散文組優選。目前繼續從事賽德克族歷史文化與「霧社事件」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