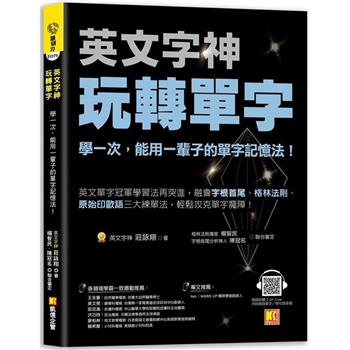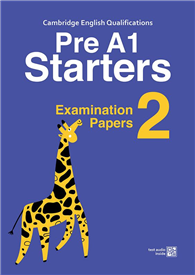推薦序
殘灰中,有人看見新的火∕吳鈞堯(作家、《幼獅藝文》主編)
讀赫曼.赫塞,是在高中與大學時代,特別是高中歲月與戒嚴時刻重疊、徬徨青春和懵懂情苗呼應,壓抑生活的蛛絲馬跡,都能在赫塞的作品中,找到宣洩與合理的看待。
高中至今,書籍累積漸多,每逢書冊出清,我檢視赫塞的小說,總不忍棄之,彷彿丟棄的不只是書,而是一段眷戀。從擁有赫塞的作品至今,已歷幾十個寒暑,他的著作如《鄉愁》、《荒野之狼》等,經過多次遷徙,定居書房門後的書櫃。雖位置隱晦,卻不受干擾,免除被拋售的命運。
重讀赫塞,滋味複雜,依稀老赫塞隔著百年光陰偷偷瞄我,更是自己的舊青春,透過他的故事還魂。
不能說年輕時不認真讀書,而是蒙著一個「愁」字閱讀,任何事都灰陰了。以前的我看《生命之歌》,或將之看作失戀之作,與主角庫恩,互以傷口安慰。《生命之歌》其實寫了許多個深刻主題,而以「殘缺」最能吸引年輕的我。
庫恩的「殘缺」首先表現在性格。庫恩是一個「不受喜愛、沒什麼天分、卻安靜的學生」。他不善交際,常搞得面紅耳赤且不知所云,於愛情部分,常是暗隱的羅盤,悶放在心,難以明現。這樣一個想愛卻無人可愛的年輕人,對愛情是潔癖的,他曾暗戀一個漂亮女孩,心思繞著她轉,知道女孩將在聚會唱歌,庫恩期待滿懷。女孩惡劣的歌喉消解了庫恩的愛戀,愛慕之情消逝無影。
庫恩害羞內向,不能說是「殘缺」,但青春萌發,對於不能說或者說不出的「愛」,不僅是「殘缺」,更是「宿疾」了,且連結沉默但廣大的族群。我不僅年輕時屬於這廣大族群,到現在也都還是。
庫恩在一次滑雪之旅,為贏得莉蒂青睞,一親芳澤,決意挑戰陡峻的崖坡。庫恩摔斷腿,成了瘸子,真的有了他的「殘缺」。瘸子如何走上舞台,成為知名作曲人,戰勝「殘缺」、迎擊心頭病,成為本書激勵人心的主題。
庫恩目睹女孩的爛歌喉,愛慕消散之際,點出本書的音樂主題。儘管庫恩常被漂亮女孩吸引,內在美卻更重要。莉蒂探視摔傷的庫恩,被他發現她的虛榮跟輕浮,庫恩的迷戀成為一場玩笑。庫恩沒怪責莉蒂,養傷時沉潛音樂,譜下他的第一首奏鳴曲。這首熱情奔放的曲子,使庫恩有機會認識演唱家莫德,以及他鍾愛一生的歌特蘿德。庫恩從譜寫不成熟曲子,到寫作歌劇、出版歌本、巡迴演出,一個音樂才華不被認同的人,在音樂領域發光。一條找到了、也勇敢踏上的路,讓庫恩從畏縮而無懼。
在進入本書的大主題「愛情」之前,可先看赫塞於創作的論點。「我的內在命運就是我自己的作品」、「痛苦與快樂是來自同一個源頭,是同一種力與樂的悸動與節奏」,「一投入創作……只剩下我獨自一人,全心投入且怡然自得」。關於作品論,「在她眼中我和我的作品沒有差別,她愛我,也愛我的作品」、「我感受到它的熱度,它不再屬於我,不再是我的作品」、「我的作品拔地而起……它不再需要我了,它已有了自己的生命」。約莫一九九○年代,藝文界開始有了作者與文本分隔的說法,我認同,並也經常闡述,至今重讀,訝然發現我所述說的,很可能正是赫塞的腔調。
雖說「愛情」是重要主題,但依據庫恩的歷程,可表現為占有、祝福以及癲狂。無論是莉蒂、歌特蘿德,庫恩與她們的初逢、動心,欲念都屬於占有。
請看庫恩對歌特蘿德的強烈情感,「如果不能讓她完全並且永遠只屬於我一人,那我的人生便白活了,所有我的善良、溫柔、特出之處,都將沒有意義」。歌特蘿德下嫁莫德,庫恩且計畫以自殺了結自己。後來,父親病危,回鄉探視與料理喪葬、房產,並安排母親,適時拯救了庫恩。與老師羅爾的重逢,為庫恩提供心病的藥方,「學習多為別人想一點,少為自己想一點」、「為他人而活,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庫恩「占有」式的愛情,屬人之常情,但莫德的暴力、不安,說出了愛情的另一種魔力。這種魔力在初期甜蜜瘋狂,卻很快轉為破壞癲狂。莫德與歌特蘿德,很快地走完愛情歷程,進入威脅、猜疑與算計中,莫德的死,是一個音樂家的死,更是瘋狂式愛情的死。庫恩走了出來,看見愛情的分享、祝福以及他者的存在。
《生命之歌》的心理描寫層次豐富。「為了我的朋友莫德……為了生活在眾人之間,卻彷彿身處另一個星球的自己,我流下無聲無息的眼淚」。目睹莫德的死,「我無法憐憫他,因為他死了會比活著輕鬆」。庫恩的兩段心聲,都細膩深刻。
年輕時看《生命之歌》,常疑惑中譯本書名為什麼這樣定?因為主題是音樂、因為這是浪漫的愛情?
或者,「生命之歌」為生死的交替,鬱鬱發聲。比如庫恩摔斷腿,卻讓他深思音樂。肉體的死,導致靈魂的生?父親病危,打亂庫恩的求死,並讓音樂事業更上層樓。庫恩母親與她表姊的關係惡化,成為母子關係的活水。莫德死後,歌特蘿德找回活力,且又開始唱歌……
死與衰疲,不是絕對的灰槁,總有新的覺醒,在看似沉寂的人生真實中,找到另一種價值,且更具意義。我認為這是《生命之歌》所要告訴我的。而且,我常覺得,這是赫塞只跟我分享的小祕密。這樣的竊悅,我一放就是三十年了。而且我也知道,我的憂鬱與微笑,還在延續它們的保存期。
推薦序
不斷成長的小說∕周易正(行人文化實驗室總編輯)
在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裡,主角「渡邊」在女友「綠」家開的小林書店(已歇業)尋找想要閱讀的東西,最後找到的是書背已經變黃,赫曼.赫塞的《車輪下》。這個場景對我來說再合理不過,一方面,赫曼.赫塞確實是早年流行的作家,如今就算走進某間台灣已經歇業多年的「文具型」書店中,發現了赫塞的書也毫不讓人驚訝。另一方面,或許走進這樣的書店,我們仍能感受到吸引力、仍然會想要拿起來逐字閱讀的書,也的確很有可能就是赫曼.赫塞。
從赫曼.赫塞的作品早在一九七○年代就已經大量引進翻譯這件事情看來,他很可能一度是台灣最廣被閱讀的德國作家。他在每本書中大量討論孤獨的段落、生命的價值,都算是五六年級生成長過程的「教科書」。那段時間,每個曾經有過苦澀青春的台灣小孩,或多或少都向他尋求過幫助;都曾經向他「借過」語言,用以描繪自己的「症狀」。雖然他的背景與文學訓練,讓他書中的故事,跟台灣讀者的生活經驗差距很遠(例如德國貴族的生活方式,或者對於情感與生命的激烈措詞),但正是這些反差,證明了赫塞的「成長小說」具有某種穿透時空的力道,架構出每個時代年輕人不變的苦澀心境;而且也是這些反差,讓台灣年輕人學會一種不熟悉的語言、以有距離的方式,了解自己。
《生命之歌》是赫塞早年作品,就文學上來看似乎沒能感覺到他的野心,也未能如他其他作品有較高的評價與知名度,但或許正是早期作品,才最能讓我們看出赫塞在文學及生命探索中,最急迫想要分享的內容。或許如此,這本書也因此成為最容易親近赫塞的作品。愛情、死亡、成就、友情與自我,這些成長過程中隨時出現的「困擾」遍佈全書。
我還清楚記得二十多年前閱讀這本書後,長長地呼出一口氣,彷彿釋放出了某些正在破壞自己的不明物體;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再次閱讀,才驚覺自己竟然還在「成長」歷程中,沒能逃出赫塞構想的世界裡,這個「發現」雖然令人恐慌,但也帶有令人欣慰的意涵:赫曼.赫塞這位被我閒置多年的作家,應該重回床頭、桌邊,最少還能陪伴我們直到下一個二十年到來。
推薦序
赫塞之歌∕焦元溥(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
我對赫塞的最初認識,其實不是來自小說,而是來自音樂。
那是理查.史特勞斯的《最後四首歌》。作曲家先讀到艾森朵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的〈薄暮時分〉,激發創作靈感而完成譜曲,後來再加上三首赫塞詩作,集成所謂的《最後四首歌》。
這是最美最感人的藝術歌曲,是史特勞斯,或說所有音樂作品中,最偉大的創作之一。在〈薄暮時分〉尾聲,當歌手唱出最後一字「死亡」,作曲家引了自己年輕時的交響詩《死與變容》之「變容昇華」主題,溫柔象徵靈魂離開。史特勞斯寫作《死與變容》時才二十五歲,這部作品也常被人批評為浮誇。但在近六十年後,八十四歲的老人再度引用自己的青年少作,感覺竟妙不可言,也巧妙為自己一生做結──或許,這是音樂作品裡最美的引用。
但我常常想,為何史特勞斯不找艾森朵夫其他詩作,而要選赫塞作品來完成《最後四首歌》?
一是赫塞文字節奏跌宕生姿,音韻起伏優美;二來赫塞因反戰而被納粹列入黑名單,最後索性歸化瑞士。戰後的史特勞斯用赫塞詩作譜曲,或許也是呼應自己內心的聲音。
第三,如果《最後四首歌》結尾要引用自己少作,那麼還有誰的作品更適合用以搭配〈薄暮時分〉,如果不是赫塞筆下的青春與追尋?
《生命之歌》正是這樣的作品。「不是詩人,便什麼都不是。」即使寫的是小說,赫塞在《生命之歌》裡還是不折不扣的詩人。不只有詩意文句,更有詩意表達。酒神的不羈不安和日神的理性平和,透過主角在自苦中觀察,見證黑暗躁動撞上光明正向,最後可能是什麼結果。書寫人生,赫塞筆調始終優雅,還不忘幽默詼諧。越到最後,越是深沉的沉澱,筆調卻越是平淡坦然。即使作者自己覺得《生命之歌》應該要寫得更好,這仍然是清朗可讀的作品。
但更精彩的,是在《生命之歌》中,赫塞不只是詩人與小說家,更是音樂家。赫塞的小說,多少都有點自傳色彩──或許也只有如此,他能真實寫出一個平庸音樂家的心路歷程,以及何以在凡俗之中淬煉出深刻藝術的奇妙轉變。那些模糊不明、朦朧難測的感受,在赫塞筆下竟如此真實清晰,讓人為之共鳴、為之嘆息。
而讀了《生命之歌》,再回過來聽《最後四首歌》中以赫塞詩作寫成的三首,竟覺鬼使神差地貼切。「你再次理解我,你溫柔地吸引我,而我因你而幸福快樂,全身顫抖」,難道〈春天〉不是主角庫恩與歌特蘿德的相識?〈九月〉「夏天在戰慄,悄悄奔向自己的末日」,又多麼真實地描繪庫恩的失落心碎。至於〈入睡〉「乘上自由的翅膀翱翔,在黑夜魔圈裡,千百倍深刻地去生活」,不正是小說結尾的清澈餘韻?
或許,這是作曲家沒有說出的祕密,《最後四首歌》在引用之外的美麗暗喻。
推薦序
融合哲學與詩意的魅力經典∕王聰威(小說家)
我初讀赫曼.赫塞,是在高中升大學的暑假,接下來的一整年讀完了所有中譯本,也就註定了他的作品會以「心靈導師」的角色參與我最求知若渴的成長時期。
對我而言,《生命之歌》便是經典的青年養成小說,不僅僅是鼓勵智識上的追求,也一併附送了未來一定會遭遇的戀愛折磨。年輕時並沒辦法感受到那苦痛,只覺得一切只是浪漫的開端,而躍躍欲試,如今重讀則像是印證人生。雖然理解的方式不同了,但是那種沉甸甸的傷懷卻重新回來,我想這是赫塞早期的魅力所在,哲學與詩意靜悄稍地融合,讓何時何地的人間都顯得可愛與無常。
推薦序
內在的命運── 閱讀《生命之歌》∕吳旻潔(誠品副董事長∕誠品生活總經理)
赫曼.赫塞是我最喜歡的作家,從少年時候第一次讀到他的《流浪者之歌》就這麼覺得了,這樣的感受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過。
已經記不清楚這是第幾回閱讀《生命之歌》。每一回,都從詩人沉澱的、如詩一般的語言中,叩問、反芻、回味、沉浸、聆聽、放鬆並得以休憩。很喜歡這部作品的原因,在於音樂家自述生命回憶的第一段自白,就真誠安靜地收服了我的心:
「從外界角度看來,我的一生並不怎麼幸福。不過即使曾經迷惘,也不至於稱之不幸……如果人生的意義在於有意識地接受外在命定的一切,全心品味其中的順境與逆境,同時為自己贏得一個更深層、更原始、不受偶然左右的內在命運,那麼我的一生並不匱乏,也不悲慘。如果我的外在命運就像其他所有人的一樣,是眾神的安排,是不可規避的,那麼我的內在命運就是我自己的作品,甜蜜或苦澀都屬於我自己,所有的責任都該由自己承擔。」
這個探究外在際遇與內在心靈對話的故事,需要讀者靜靜地閱讀與開啟。然而,我想,就是如許描述,總結了我對於赫曼.赫塞的尊敬與喜愛。我感到他正是一位經歷過種種煎熬、痛苦與困頓,並在其間發現了自己深層、原始與不受偶然左右的內在命運的詩人,並將所有的美好與不美好,都吟唱成了一首慈悲的詩歌,讓每位接觸他的語言的人,都有機會感受到清淨的力量,並得以思索、鍛鍊與轉化自己內在的命運。
導讀
赫曼.赫塞、羅曼.羅蘭、卡夫卡 ◎南方朔(文化評論家)
儘管赫曼.赫塞這個名字在近當代文學研究裡,已很少再被提到,但對台灣讀者而言,卻對他始終情有獨鍾,幾乎他所有的小說創作,都早在一九七○年代即有了譯本。他一直是青年讀者探索生命意義和心靈境界的重要指標。
最後的浪漫主義英雄
在文學譜系上,赫塞和法國文豪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乃是經常並論的人物。赫塞比羅曼.羅蘭小十一歲,但他們兩人心性相通,從一九一五年到羅曼.羅蘭逝世的一九四四年都通信不斷,羅曼.羅蘭甚至在一九三九年的信中說:「你是我藝術和思想上的兄弟。」羅曼.羅蘭出道及成名較早,他於一九一五年即獲諾貝爾文學獎,赫塞則遲至一九四六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而他們兩人的關係之所以特別值得重視,乃是他們分別是法德這兩個文學系統「最後的浪漫主義英雄」。這兩個從十九世紀過渡到二十世紀的文學宗師級人物,他們面對著人類思想業已巨變,由「信」往「不信」的方向移動,但他們並未因此而懷疑、犬儒,或走向嘲諷,而是更加確定那浪漫狂飆時代的核心價值,如自然及自由的哲學,以及心靈空間的開創。他們傳承了浪漫主義的香火。
因此,要瞭解赫塞,首要之務即是必須回溯浪漫主義整個人文運動的內在精神。浪漫主義繼承了理性啟蒙的遺緒,將自由與解放的樂觀價值首度推到了高峰,除了自由、平等、博愛、人道,這些現世面的解放外,在美學與哲學上,則出現了真善美合一、歌頌自然、肯定宇宙有情的新意義範疇,並將人類的心靈自由和意義探索,拉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浪漫主義的諸巨人裡,雨果的偉大人道胸懷、華滋華斯的自然和宇宙胸襟、歌德對靈魂自由的探索、貝多芬的自由奔放和熱情、拜倫對公義世界的追求,都將人文關懷的向度做了無限寬廣的擴延。
而羅曼.羅蘭和赫塞就是那個偉大人文傳統的繼承者。本質上,羅曼.羅蘭接近雨果的浪漫人道與浪漫自由精神。他的名著《約翰克里斯多夫》即是最好的例證;至於赫塞,在早期則接近華滋華斯,對大自然的盎然生機有著神祕的崇拜,對萬物一體,交互融合,成為一切生命的律動也有著契合的思維。儘管羅曼.羅蘭和赫塞對浪漫主義的切入點並不相同,但他們在浪漫人道關懷上卻都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羅曼.羅蘭首揭反戰旗幟,不能見容於法國而飽受抨擊,緊接著,赫塞也在瑞士《新蘇黎世報》發表反戰文章,被德國人指為叛徒,但赫塞卻受到羅曼.羅蘭的聲援與支持,並開始了法德兩個最後的浪漫主義英雄長達三十年的忘年友誼。
在此特別將法德這兩個最後的浪漫英雄那段友誼故事加以強調,其實是要指出文學史的一個重要轉折。整個近代文學,在走完十九世紀而進入巨變的二十世紀後,由於世界動盪,災難的頻仍,那種以「信」為核心的浪漫主義已愈來愈感挫辱無力,人類開始進入以「不信」為核心的現代主義這個新的階級。在文學史上,比羅曼.羅蘭、赫塞略晚一點的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可以說即是替現代主義走出新路的先驅之一,他的《審判》、《城堡》等著作,已看不到對世界可以變得更好的熱情,剩下的只有森然冷酷的生存情境,以及人對生命意志的懷疑。文學做為熱情、浪漫、生命探索媒介,因而顯露出淋漓生機的那個階段,已開始要漸漸淡出了。
在文學隨著時代而巨變的時候,像赫塞及羅曼.羅蘭這樣的人物,他們儘管見證了十九世紀末歐洲的動盪,甚至兩次世界大戰的黑暗,以及不同國族間的仇恨對立,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對樂觀浪漫主義的信念,放在二十世紀文學史上來看,那就成了難得的空谷跫音。這也是儘管他們那種高度感性、自我,並直接的文體,現在已很少有人還會那樣寫了,但他們那些熱情含量很高的作品,在幾經變易的當代,對讀者仍極具魔力。特別是赫塞的作品,在一九六○年代不滿青年昂然而興的時代,他那種追求心靈境界的訴求,仍能打動許多年輕的心靈。浪漫主義文字可能會不合時宜,但只要人有心追求,它就有了再起的空間。
《生命之歌》──浪漫主義心靈成長小說
有關赫塞的生平及作品的探索,前人已做了許多。而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赫塞雖作品豐富,但他由始而終,無論思想和風格都有清晰的一致性和連貫性。由於浪漫主義深信個人與社會存在之目的性,它都是透過懷疑、徬徨、挫敗,而後在人的不屈意志下,從無路中找出那美好的出路。因此浪漫主義之學幾無例外的都是成長之學,而這本《生命之歌》,就是謳歌生命,謳歌友情和愛情的不朽之作。
《生命之歌》的結構與情節並不複雜,一個家境不錯的少年,從小就享有極大的自由,由於他對音樂有感,十二歲就開始學小提琴,而後到首都音樂學院就讀。但在這裡,他卻遇到了生命的第一個瓶頸,他追著學校的功課跑,上得很吃力,上鋼琴課更是折磨,他低估了藝術道路的艱辛。於是他開始自我懷疑。由於他年輕,長得也帥氣,而且家境也不錯,於是他便放縱自己,享受當下片刻的快樂,與女孩們打情罵俏,飲酒作樂,到各地遊蕩玩耍。在一個沒課的冬天午後,他們一群少男少女結伴出城嬉遊,飯飽酒醉要回家時,大家又起鬨,於是他坐在平底雪橇上,載著一個女孩由山坡上往下滑。這是個年少輕狂的愚行,他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雪橇瘋狂的向下衝,撞上了樹幹,兩人都摔倒在地。女孩只是皮肉輕傷,他卻左腿多重骨折,變成了一個瘸子,臥床四個月。他的人生已到了一個關鍵的轉捩點。
但他畢竟是個能自思自問、知道生命堅持的人,他很快就從殘缺的痛苦中站了起來,他已無法成為演奏家,但作曲卻是他的夢想,他要努力成為一個作曲家。尤其是他在受傷後去瑞士邊界的一個小村莊住了幾個星期。大自然的蓬勃壯麗及深邃動人,也發揮了療癒作用,且激勵出了他的生命力道,在旅遊途中,他終於寫下了他的第一首雙小提琴奏鳴曲,並開始以一種豁達愉悅的心情重返學校,繼續他的音樂事業。
而後,他的人生又在友情和愛情中再度遭受到極大折磨。他認識了歌唱家莫德,成了好友,莫德也很欣賞他的作曲才華,對他的事業也幫助極大;後來他和莫德又同時喜歡上美麗而有才華的富家小姐歌特蘿德,他因自慚形穢而退出這場感情的角逐,他明知莫德和歌特蘿德的婚姻可能是場不幸,但他為了友情也不能去干預破壞,最後果然是莫德自殺告終,他自己也失去了美麗快樂的布莉姬特的戀情機會。這本書作寫人生各種艱難的友情、愛情與事業的考驗,主角終以他自己的「端正心性」(Decent),修成了生命的正果。浪漫主義視真善美為生命之目的,因此詩人與音樂家常成為文學的中介角色。《生命之歌》的作曲家和《約翰克里斯多夫》裡的作曲家,真的可以拿來對比參照。這也是赫曼.赫塞與羅曼.羅蘭心性相通的原因。
閱讀《生命之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赫塞那個時候德國興起了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心理分析學派,它著重深層的心理分析,每個角色的心理轉折都異常深刻。一個人遇到挫折時的直接反應,以及克服挫折的心理昇華,每一步都軌跡清晰,對讀者的自省能力有極大的啟發,也更瞭解生命的歷程。人生不易,有太多愚昧、不幸,雖然外在的原因不能改變,但那內在的生命始終操持在自己手上,只要自己堅持做個端正的人,當時間過去,一切都被淡化,他留存下來的,就是純淨清澈的生命之歌,它是帶淚的微笑,是殘缺的美好。我讀這本著作,就對其中心理的跌宕起伏和自我超越的部分愛不釋手。赫曼.赫塞已替每一個人寫下了大家共同的生命之歌。
重讀赫塞,重溫理想的光輝
赫塞巨著不斷,他中期最重要的《荒野之狼》(Der Steppenwolf),以心理分析雙重人格的角度,剖析人的「狼心與良心」的自我爭戰的勝利,來標誌人性的必勝。他晚期最重要的《玻璃珠遊戲》(Des Glasperlenspiel),則要為不分東西方的世界,打造一個超脫政治、經濟和道德動亂的精神王國。赫塞橫跨西方基督教、東方佛教及印度教,兼對中國儒道兩家皆有涉獵,而且程度並不泛泛,這遂使得他最後這部《玻璃珠遊戲》,有了更大的走向未知的宇宙胸懷。他會在一九四六年這個二戰剛結束的時間點上被頒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是在推崇他那跨越藩籬、眾生平等、天人合一的世界襟懷。他曾經說過,世界是個表象,看起來各自殊異,但在那根部,則是所有的皆相濡相生。他那浪漫情懷所看的,就是這個根本,這也是今日重讀赫塞,要對那根本格外看重的原因。
浪漫主義的時代早已成了過去,昔日人們的熱情已被冷漠所取代,而由於熱情始可能產生的盼望則被苦澀的犬儒心情所掩蓋。當文學不再以「光照」為目標,文學存在的意義也就讓人懷疑起來。重讀赫塞,緬懷前賢,去體會那些浪漫的理想光輝,讓人們變得更加恢弘,或許才是可以有的覺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