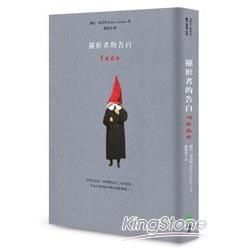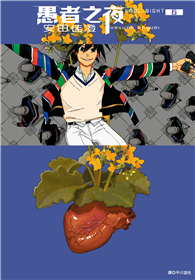專文推薦一
*人生的褪形旅程∕鍾文音(作家)
《褪形者的告白》的英文書名《Fade》,這讓我想起寫劇本時常用的Fade out,螢幕漸漸褪失至黑,也就是逐漸消失。
《褪形者的告白》就是一個擁有消失能力的褪形者保羅,他並非家族的第一個擁有這個能力的人,他繼承這些能力,而這些能力可以用在善,也可以用在惡。
小說一開始藉著敘事者「我」的眼光看著自己的家族,由於是童年的目光,因而小說一開始即有著童真的語氣與表達,寫到少男愛上自己那離經叛道的姑姑羅珊娜時,更挑動了小說的曖昧性。小說逐漸進入核心:一個擁有褪形能力的人,如何運用他的隱形自由與消失的樂趣?他可以逃避眼前的危險,也可以躲在暗處觀看許多人的祕密,但小說顯然是複雜的,有助人的褪形者,勢必也有自私的褪形者(足以危害社會)。
這使得小說的層次逐漸進入了人性的思考介面。脫離了想像的科幻,反而更落實於人間的生存與生活難題:保羅想像的帥氣父親,卻一生都在小鎮的梳子工廠度過一生。那麼保羅自己呢?擁有褪形能力卻使他陷入冥思,他想著為何這個家族同有此能力的亞德拉叔叔常感憂傷?
原來知道太多人的祕密,知曉人間太多之不可得的慾望,這可讓「褪形者」不好受。
這小說非科幻文學,但又帶點科幻的味道(奇幻元素是褪形能力者的隱形時空),這小說是家族文學又不是家族文學(小說提到幾代人,但卻又沒有我們認為的家族文本之國族想像與身份認同等意義追尋)。但這一本小說卻又涵蓋了許多命題:保羅的愛情幻滅,蘿珊娜的無歸屬感,漂泊者亞德拉,探索者蘇珊。可視為成長小說,也是存在小說。
「從你身上的光,……具有褪形能力的就會對我發光。」亞德拉叔叔告訴保羅,從會發光到會褪形,需要經過很多年的時間,亞德拉到保羅,保羅到亞力,保羅是全書最關鍵的敘事者,他串起前一代褪形者的憂傷,與下一代褪形者亞力的徬徨。
全書最有意思的觀點是到了最後,保羅在某個靜夜中,思緒飛到了蘿珊娜。蘿珊娜也是這本小說裡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人物,那種普遍存在生活周遭的女生,為愛情迷惘與個體的追尋失落。保羅透過回憶蘿珊娜,慢慢地感覺到回憶也逐漸地褪形,那麼世間的一切存在也會逐漸消失吧,他忽然體會到:「褪形,不只讓我的形體消失,也讓我退出了別人的生活,包括我的家人。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褪形。」
整個人生確實都在褪形(褪色),「愛會減弱,記憶會模糊,慾望也會消退。」保羅想著蘿珊娜,卻遍尋不著過去的熱情與鮮明的回憶色彩,他明白了過去亞德拉叔叔的憂傷了,原來褪形能力把他和「正常人」區隔了。而這個褪形者的社會身分卻是「作家」,作者也試圖在表達「作家」的行業說來也是某種社會的「褪形者」,因為作家並不以本人面世,而是以「作品」面對世人,作者隱藏在作品之後,故作家也是某種高明的褪形者(隱形者)。
「跟人群保持距離,盡情投入寫作。我躺在旅館上,試著擺脫所有的思緒和罪惡感,因為我已經領悟到人生只有無限的問題,並沒有提供答案。」
人生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必須經由自己去發現去覺知。
這本書的結尾看到會褪形的亞力(保羅的外甥),面對內心另一兇惡人格產生的內心交戰。同時,也看到保羅自己拒絕成為褪形者,因此產生了掙扎。我以為,「對抗內在的瘋子」是這本小說的隱形「核心」。
褪形其實什麼也褪不了,因為人心的魔,會緊抓著我們。
「我的淚水則是顯影液。」
當我們試圖也要發出讀者的同理心時,小說卻又話鋒一轉:「當然是虛構。」原來這是保羅遺下的手稿,但被另一個敘事者蘇珊讀來卻產生不相信的結論,蘇珊不相信有褪形者的存在。小說到了蘇珊這個章節,就帶著懸疑性,一個作家追訪另一個作家(保羅),小說陷入了推理,閱讀似乎切割,但卻又相連,蘇珊藉由追尋保羅留下的遺稿,一步步地踏入褪形者的內心謎底。同時也隱隱寫出一個作家的告白:「一個作家必須勇於冒險,挑戰自己的機運,有一點執迷,有一點瘋狂。」
小說的最後是保羅徹底地從人間褪形,連留下的手稿都被質疑虛構。
虛構也是一種褪形?
活的本身,就是通過一場場的追尋與失落,然後擺脫記憶的黑暗深淵。
我最喜歡作者在書末段寫著關於作家保羅的隱士生活,這在當代幾乎是不可得。而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連結,往往是個謎,這也讓我想到馬奎斯說的:「每個好的小說都是一個謎」。
我在閱讀時不僅擁有閱讀樂趣,也有了更多複雜的思索在心裡隱隱流動著。
專文推薦二
*每個翻轉,都帶來新的思索∕臥斧(文字工作者)
那個陌生人在一個二月的寒冷清晨到來。
陌生人走進小鎮旅店,老闆娘發現他全身都纏著繃帶;過了一陣子,老闆娘催討房錢時,陌生人生氣地從臉上摘下一個東西遞過去,老闆娘定眼一看,放聲尖叫,因為那居然是……。這是H. G.威爾斯(H. G. Welles)的經典作品《看不見的人》(The Invisible Man),出版於1897年。
「隱身」能力在神話傳說裡其實不算少見。
威爾斯作品與神話傳說不同之處,一是主角經由研究實驗之後,以「科學」的方法達成目的,另一則是我們可以清楚地察覺,在逐漸變得透明的過程當中,主角的性格也開始轉變。「隱身」不再只是一種拿到某個法寶之後讓人隨心所欲的能力,而是得去爭取、因此受苦,而且還可能反倒被它影響的麻煩事情。
經過九十幾年,羅柏.寇米耶(Robert Cormier)寫了《褪形者的告白》(Fade)。
故事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可能會以為寇米耶講的仍然是「如果有人能夠隱形,那麼他會怎麼運用能力?」的老套主題,而故事裡提到的「褪形」(fade)能力,也有幾個設定明顯地在向威爾斯的《看不見的人》致敬;但我們也會很快地發覺:《褪形者的告白》並不是《看不見的人》的仿作──不是偏執的科學家自願選擇隱身,而是家族遺傳的某種特殊體質;主角家族中獲得「褪形」能力的成員,可能會成為漂泊四海的探險家,也可能成為窺探人心的文學創作者。
但這個能力並非只帶來好事。
探險者被家族認為沒責任感、創作者在窺探人心時也會看到許多不堪的真相;倘若對世界有許多不滿、眼中充滿各種歪斜,那麼「褪形」能力便可能被用在犯罪行為上。故事發展到一個段落之後,寇米耶從另外一個角度讓我們思考:這個自稱可以「褪形」的人,真的可以隱身嗎?隱身之後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相嗎?
為什麼在看不到自己的時候,反倒認為看得見別人的真實?
事實上,無論在觀察世界的時候有沒有「褪形」,我們永遠都被自己的主觀所限,看出去的視界自然也就會有盲點與不確定的闇影;而假使我們依靠別人的說法來認識一切,那麼無論講述的是慣於虛構故事的小說家還是似乎保持客觀的老警探,都不能完全信賴──自己的眼見無法為憑,他人的轉述又不能盡信,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這是寇米耶藉著故事情節,向我們提出的問題。
每個章節都有意外的翻轉,每個翻轉都會帶來新的思索。《褪形者的告白》先讓我們藉「褪形」能力快速成長,再用文學技法要我們正視「虛構∕現實」之間可能有多大的不同。閱讀的當下,我們會意識到寇米耶要我們思考的題目,雖然不會馬上獲得解答。
但只要翻開這個故事,開始思考--或許,就是最好的答案。
導讀
移民者的史詩:流亡與褪形∕周惠玲(作家、文學研究者)
有許多人認為《褪形者的告白》(Fade, 1988)是羅柏.寇米耶(Robert Cormier, 1925-2000)最優秀的一部小說,包括史蒂芬.金。
在一封寫給編輯的信函裡,史蒂芬.金說:「這是一部緊張刺激,讓人讀得很爽的小說……我看得目不轉睛,完全被迷住了,而且情緒跟著跌宕起伏……寇米耶早已是公認的優秀小說家,無疑的,這本《褪形者的告白》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他還為這本小說寫下一句無比華麗的註腳:「宛如《麥田捕手》的主角潛入了《看不見的人》裡……」真不愧是全世界最會說故事的鬼才兼文學點評名家,短短一句話,以兩大文學經典來比喻,不僅定位了《褪形者的告白》的文學成就,還點出了這部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特質。
是否是最好作品,見仁見智,但肯定是寇米耶用情最深的一部小說。在當時,羅柏.寇米耶已經以《巧克力戰爭》(The Chocolate War, 1974)震撼文壇,並以隨後四部傑作《我是乳酪》(I Am the Cheese, 1977)、《第一次死亡之後》(After the First Death , 1979)、《大黃蜂總算飛了》(The Bumblebee Flies Anyway, 1979),以及《超越巧克力戰爭》(Beyond The Chocolate War, 1985),奠立大師地位,並成功開闢出一塊成人與青少年跨界閱讀的沃土。然而,在寫這部《褪形者的告白》時,寇米耶似乎改變了關注的視野,從他最擅長的當代社會問題探討,轉向大河小說的書寫(順道一提,原稿有六百多頁,成書時剪裁成三百多頁)。
因此,史蒂芬.金的點評雖然華麗精準,卻只著重故事劇情,沒點出這本小說之於寇米耶個人的意義,以及他企圖在其中吟唱的移民史詩。
寇米耶曾說,《褪形者的告白》是他最接近自傳的一部小說,但他強調這不是指人物故事而是指背景。小說敘述少年保羅在十三歲那年發現他繼承了一種能讓自己隱身的能力,這個天賦是家族遺傳,由叔叔傳給姪子。保羅原本以為這是上天賜予的恩典,藉由這能力,他逃過了幾次死亡,隨心所欲潛入他想去的地方,看盡一切祕密,做任何他想做的。但也因此,他逐漸領悟到:這或許並不是上帝的恩典,而是一種詛咒……。
全書分成五部,第一部是少年保羅.莫侯和他的家族故事,時間是一九三八年;第二部是蘇珊.羅傑的故事,時間設定在一九八八年(本書出版年),蘇珊有一位叔公是全國知名的大作家,這位叔公(保羅.羅傑)生前十分神祕低調,從不接受任何報章雜誌採訪或拍攝,卻安排律師在他死後將一份神祕手稿寄給經紀人,手稿內容是講述一位褪形者保羅.莫侯的故事(小說第一部的主角);第三部回溯到一九六三年的保羅.莫侯,這時保羅已成為大作家,並發現有下一代隱身者流落在外;第四部則是下一代隱身者亞力的故事,敘述他自小被雙親遺棄,為了存活下去,而逐步變成恐怖的暴力分子。第五部則再跳到一九八八年,蘇珊從一份新聞報導中發現,似乎有新一代隱身者出現了。
這本書的敘事和結構相當複雜精巧,寇米耶設計了許多相似的角色(蘿珊娜與蘿絲、雙胞胎、猝死的兄弟)反覆出現在不同世代,暗示讀者歷史的重複性,同時他安排了三種不同的敘事聲音,來述說前後幾代隱身者的故事,而且隨著敘事聲音的變換,敘事節奏和文字風格也截然不同,第一個聲音(保羅)的敘事風格就像一曲懷舊的田園史詩,第二個(蘇珊)就像理性刻板的紀實報導,而第三個聲音(全知觀點)卻帶來史蒂芬.金式的驚悚奇幻小說。
不過這本書最引人注目的並不是它的敘事美學,而是故事成功地引爆了寇米耶身世的八卦。很多讀者紛紛臆測:「羅柏.寇米耶該不會就是那位褪形者保羅吧?」就連寇米耶很多朋友,也在小說出版之後不斷私下問他:「你是不是真的會隱身?」
也難怪大家會產生這種困惑,因為寇米耶在這本小說中使用了多重「自我指涉」的手法。「自我指涉」這種後設寫作會產生一種美學效果:顛覆或模糊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線。更何況,寇米耶還刻意用真實發生的人事物來混淆讀者。
首先,羅柏.寇米耶和小說裡的作家保羅.羅傑,以及羅傑遺稿裡的隱身者保羅.莫侯,他們三人擁有相似的家世背景,這使得寇米耶∕羅傑∕莫侯三人成為相互指涉的對象。他們三人都是一九二五年出生,祖先都是來自魁北克的法裔移民(小說裡稱為「加拿客」),他們都生長在麻州一個小鎮的法國城(法裔移民的聚集社區),親朋鄰居都是小鎮上梳子工廠裡的勞工;小說裡所描述的保羅父親的工作狀況,以及隨後發生的罷工事件,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事。而羅柏.寇米耶也幾乎像保羅.羅傑一樣,後來成為舉國聞名大作家,並始終低調地隱居在故鄉(差別在於寇米耶有結婚生子)。在他小說中的那個小鎮馬紐曼(Monument)是一個虛構地名,卻幾乎可以用寇米耶生長的小鎮萊姆斯塔(Leominister)來對號入座,特別是小說中的法國城內景物,也和寇米耶童年居住的法國丘(French Hill)一模一樣。亦即,寇米耶是套用了自己的故鄉和自己的身世來寫這部小說。
其次,寇米耶在這自我指涉的敘事裡,一方面進行自我解構,另一方面又引導讀者反解構。在小說裡,寇米耶透過蘇珊和她的警察爺爺以理性思惟、各種紀實性報導與證據,一再否認保羅是隱身者。但同時,作者又暗示蘇珊和她爺爺其實都保留了某些不願公開的證據。甚至,小說最後以一則新聞報導顯示,隱身者可能正存在於世界的某一角落,以其不受控制的超能力形成這社會的潛藏危機。可見,寇米耶其實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暗示讀者,保羅.莫侯就是書寫他的作家保羅.羅傑自己,而因此,讓讀者產生了一種錯覺:保羅.莫侯=保羅.羅傑=寇米耶。
寇米耶的手法顯然十分成功,以至於後來他的好友坎貝拉(Patty Campbell)在撰寫他的傳記與書評時,還得花去頗長篇幅,列舉各種證據,來澄清這個故事裡的兩個保羅,絕對不是寇米耶自己。只是這種解釋難免更讓人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聯想。
問題是,寇米耶將自己獻上「祭台」的目的為何?只為了一種美學效果嗎?
最簡單合理的解釋,就是寇米耶自己的解釋:這是一部自傳小說,但不是個人,而是背景──也就是說,關於他的故鄉、他的父祖同鄉們,是那一群住在「法國城」的移民傳記。他們從加拿大流亡,來到新英格蘭落腳,群居在狹小簡陋的法國城,在高溫的梳子工廠中揮汗工作,賺取微薄的薪資養活一家人,他們被資本家剝削,也被同為加拿客的高利貸買辦剝削,以致最後起而對抗……。小說第一部中所記錄的加拿客是極令人動容的,華人讀者也許會聯想起當年華僑在美國中西岸建築鐵路的血淚史。
家族移民歷史雖是寇米耶關注的故事主軸,但他並沒有因此寫成歷史小說,相反的,他將之淡化成為一部奇幻懸疑小說的背景,去突顯前景的「褪形者」。弔詭的是,「褪形者」其實是一種缺席的存在。全書以一幀褪色的家族照片作為小說開場,當莫侯一家要從魁北克移民到美國前夕,他們在老家門前拍了一張照片,快門按下瞬間,其中一個人消失不見了。那人就是保羅上一代的「褪形者」(fader),後來浪跡天涯的亞德拉叔叔。
寇米耶的小說一向以豐富的隱喻象徵見長,這本《褪形者的告白》雖不像《巧克力戰爭》裡有繁多的隱喻意象,但那幀老照片以及缺席的褪形者,即是全書最核心的意象(寇米耶說他曾考慮用Fader而非Fade作為書名),兩者互為表裡,譜成一曲悠長不止息的移民者之歌。當寇米耶藉著亞德拉的口說「褪形者」「搞不好可以追溯到基督誕生的時候」(令人想起摩西帶著族人渡過紅海),即暗示人類流亡與移民的歷史源遠流長。有些移民會像老照片裡的人們,努力在某個地方紮根,也有一些人像亞德拉和保羅那樣,成為完全透明的存在,因而只能自我流放。亞德拉的自我流放是浪跡天涯,保羅的方式是自我閉鎖在某個無名小鎮裡,而無家可歸的亞力則存活在黑暗中,對社會進行破壞,或許他下意識裡希望因而被看見。
寇米耶所希望的,就是喚起我們對於這些流亡者的關注,不再將存在於社會底層的移民視為透明。就像小說中作家保羅.羅傑刻意揭露自己身為「褪形者」的祕密,寇米耶也用「自我指涉」的手法,讓我們相信「褪形者」的存在。
「褪形者」確實存在著,不是嗎?即使在台灣,過去的移民、新移民的故事也不斷發生,而那些「褪形者」渴望被我們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