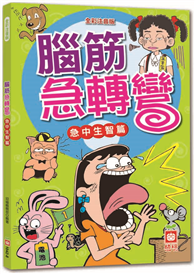自序
野地的啟示∕劉伯樂
學美術的我,天生喜愛自然美景。曾經爬山涉水尋找一幢神祕的瀑布,不遠千里捕捉森林裡的一片紅葉。上到玉山頂峰拍攝岩鷚,下至曾文溪口等待黑面琵鷺。一度以為只有壯麗的山光水色和稀有的飛禽走獸,才是自然生態藝術唯一的題材。偶爾創作出精采的作品感動了日益疏離自然的人們,卻又不自覺地展示出身為藝術家對唯美的狹隘看法,以及生為人類高高在上的優越意識。一頭栽進了追求極致的行列,處處想要能人所不能,就好像登上了最高山一樣,除了寒冷就是枯寂,縱有成就在外,內心反而益形空乏。
直到那一次奇妙的「邂逅」……
在山區林道的轉彎處,我看見一群竹雞正在沙坑上享受日光浴。一般人都認為竹雞既不是雞又不是鳥,不具有食用和觀賞價值。竹雞成群大約七隻,這七隻竹雞蹲踞在沙坑上窩成一團,時而瞇起眼睛怡然自得;時而啁啁細語相互磨蹭。和煦陽光透過扶疏枝葉,斑斑駁駁的光影灑在地上,粗俗野鳥在自然環境裡看起來竟是這麼雍容華貴。我不忍心因為攝影的動作或聲響,干擾這一群竹雞,於是緩緩蹲下然後趴在地上,儘可能讓自己看起來不像是一個「人」。
慢慢從身體裡感覺到來自土地裡的溫暖,同時接收到一些微妙訊息:金龜子幼蟲在土裡蠕動,地鼠在不遠處翻土。枯葉堆裡有一個奇怪的蛾蛹,地衣岩石上有藍色石龍子和冒充枯葉的蝴蝶。地面上禾草子實蠢蠢欲動,草葉上滴滴露水在陽光下顯得晶瑩剔透。空氣中聞到了花香味、椿象的臭味和腐熟水果的味道。紫蛇目蝶也聞香而來,細細品嚐一粒爛熟的榕果。聽到了青楓翅果翩然落下和酢漿草彈射果實的聲音。還有新芽冒出來了、空氣流動著、葉子簌簌飄落、茶蠶蛾大啃大嚼的聲音……。
看似安靜祥和的世界也隱含著令人不安的氣氛。樹林裡枝葉婆娑搖曳,其實是一場爭奪生存權的殊死戰;攀木蜥蜴正虎視眈眈凝視著一隻蜚蠊;人面蜘蛛滿腹心機,勤奮地葺補牠的羅網;白痣珈蟌著急地捍衛地盤;岩石後面草叢裡,更不時傳來窸窸窣窣,讓人忐忑的聲響……。
竹雞似乎也察覺到了危險的氣息,帶頭的緩緩站了起來,依照長幼次序,一隻接著一隻鑽進路旁箭竹林裡。
「一,二,三,四,五,六……」我數了一數,「咦?怎麼少了一隻?」
第六隻竹雞臨走前在竹林邊緣停了下來,回頭疑惑的望著我,好像聽到牠不耐煩嘀咕著說:「你怎麼還不跟上來?」原來我已經成為牠們的第七隻竹雞。
短暫天人交會讓我脫胎換骨,彷彿經歷了百萬年進化淬鍊一樣。原來只要拿掉人類的優越感,用自然的身心去體會自然,就算是一隻粗暴恐龍也可以演化成溫馴的鳥類。林道邂逅並沒有留下任何彌足珍貴的生態照片。不過,在我心中烙印著一段至真、至善、至美的生態生命藝術,卻是永遠無法用影像的切片或畫筆描繪來取代的。
所謂:「為學日益;為道日遠」,我們加諸於自然的討論和干涉,常常困惑在專家們艱澀的理論裡,執著於偏執的保護、保育熱潮中,迷失了人之於自然的本性;忘記了人在自然界中所以為人的角色。
生物生態保育學者安卓.杜布森從日常居家生活中一再提醒自己:「……人的多元化和動、植物的多樣性一樣重要」。亨利.梭羅也認為:「……遠在加州的巨木對我而言,還不如家門前的小草來得有意義」。
在這本書裡,我用尋常百姓的眼光,從我們生活的週遭多看一眼;用野人獻曝的想法,在多元的自然社會裡多想一下,畫畫寫寫只是想告訴喜好自然的人們,毋需遠卦法布爾家鄉取經;也不用去大峽谷驚嘆;更不用哆嗦著去南北極探索,只要稍加用心顧盼,在我們身旁、腳下,自然而然也就有無限驚奇可以追尋。
推薦序一
大地是萬物的家∕林良(作家)
本書作者劉伯樂先生,在大學時代學的是繪畫,為了寫生,不知不覺的走進了大自然,成為一位大自然的觀察家。多少年來,他寫寫畫畫,畫畫寫寫,都離不開他所關心大自然。這幾年,因為關心飛禽,又開始寫飛禽,畫飛禽,成為一位畫鳥寫鳥的「奧杜本」(Audubon)。
像他這樣一位幾乎整年在野地、林中、高山、谿谷間遨遊的「徐霞客」,熱愛大自然是必然的。他到處尋訪鳥獸蟲魚的身影,觀察牠們的營生,卻是出自一種仁慈的關懷,因為大地是萬物的家,鳥獸蟲魚是這個大家庭的成員。
對讀者來說,這是一本散文集和一本風景畫集的結合。沒有那些畫,你就等於漏讀了一篇散文的美妙註辭;沒有一篇篇的散文,你就讀不到圖畫裡隱藏的作者的心聲。散文集和畫集,在這本書裡合而為一。
劉伯樂在這本書裡的所作所畫,具有動人的臨場感。他畫的雖然也是風景,卻是一種「生態畫」。風景裡,畫的是美妙的風景。生態畫,是把生態環境畫得很美妙。生態畫不是畫美景,「淺水平沙」固然可以畫,「殘垣斷壁」也得畫,但是要畫得既生動又具有美感。讀者在這本書裡,可以欣賞到劉伯樂繪畫的手上功夫以及呈現真實情況的功力,獲得一種看畫的喜悅。
在這本書裡,劉伯樂的散文,因為是要寫在明信片上的緣故,所以都精短像小品文。「寫在明信片上」是這本書的一項「文學的設計」。其實,他本來就很擅長書寫精短而又具有濃濃趣味的小品文。他的散文,內容充實,言之有物。不喜歡讀「無病呻吟」或「有病呻吟」那一類文章的讀者,一定會發現他的散文裡十分可愛。
讀這本書以前,我只知道「大地是萬物的家」,但是並沒有什麼真切的感受。讀了這本書,才知道大自然是熱熱鬧鬧的,充滿活力的。我很感謝本書的作者:
他為我揭開一個平日視而不見的世界。
他讓我聽到平日聽而不聞的一片生命的喧嘩。
推薦序二
重新看見野地的一扇窗∕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我們在國外旅行的時候,看到美麗的風景,心有所感之餘,總會在販賣紀念品的地方,挑幾張紀錄當地景致的明信片,然後找個路邊咖啡座,寫下自己的心情寄給遠方的親友,甚至是寄給將來返家之後的自己。
可是,當我們在自己的家鄉遊逛,或者到自然野地散心,產生同樣的感動時,除了拍下相片之外,是否會想到用文字或繪圖留下自己的心得呢?
其實,因為外在景象引起內心感動進而抒發情意,自古以來就是我們文化的大傳統,從詩經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孔子看到流水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捨畫夜」,或者「碧雲天、紅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乃至於「枯藤老樹昏鴉,古道西風瘦馬」,短短幾句對風景的簡單描繪似乎也把書寫者的心情呈現了出來。的確,外在的世界,往往是人情感的投射,也是人情意的象徵,甚至可以反映出人類社會及當下環境的種種對話關係。
而伯樂兄在這本可愛的小書裡,將他多年來在台灣各處野地漫遊的觀察與感動,以動人的水彩與素描圖繪,配上質樸清新的短文,帶領我們回到自然場域,讓每個人感受到他當下所體驗的土地脈動、呼吸與震撼,正是為前述這樣的美好傳統提供了一個最好的示範。
伯樂兄在他<野地的啟示>這篇自序裡,提到他與竹雞的一場邂逅,雖然是短暫的天人交會,卻使他脫胎換骨,改變了對自然的態度,這段敘述讓人非常感動,也使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曾經一群荒野的夥伴與幾個二十多歲在國外出生的ABC,一起在初春的思源啞口露營。晚上大伙在營火邊聊天,有人感慨小時候住在忠孝東路四段,附近都還是稻田池塘,國父紀念館附近的停車場當年還是潺潺小溪。當我們為自然的失去而感慨時,那群ABC很不以為然地說:「停車場有什麼不好?很方便實用嘛,再說鋼筋水泥還不是來自大自然,也算是自然的一部分啊!」
戰火挑起,經過一陣紛亂的討論後,並沒有產生什麼正式的結論,卻讓我進一步去思索:自然與非自然最大的差別何在?我認為在於自然裡富含生命力,人在其中會被感動。而自然與「來自自然的人造物」其間的差別,就像是自然野域中突然遍地盛開的野百合與花圃中整整齊齊的花卉,一種會讓你感動落淚,另一種則只是得到「很漂亮」的評語罷了。也如同我們在動物園裡觀察一隻台灣黑熊的樣貌,的確很方便,但是一旦半夜你在思源啞口的原始林中聽到熊的吼聲甚至與熊相遇,那種心中的震撼與悸動,就是生命力!就是我們重歸自然,重獲與萬物合為一體的喜悅感!
當晚那群ABC雖然對我們所說的不以為然,但是隨後幾天跟著大家一起在森林中探索時,看到他們的目光逐漸柔和起來,身軀也逐漸柔軟下來,到最後甚至可以和我們一起跪在大地上看一株小小的野花,也可以抱著大樹感受森林的傾訴!我不禁為他們感到高興!
的確,因為人們群居於都市,遠離自然之後,逐漸變成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遲鈍又麻木的人,很多人失去了親近大自然的能力,以至於一時之間無法從大自然那裡得到啟示與喜悅。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樂觀的,因為我覺得人類內心深處有一股來自遠祖的呼喚,那種能量會驅動著我們去尋找基因所熟悉的感覺,也就是回到大自然裡。
不過,這種自然的鄉愁是必須被適當引導與陪伴的,甚至對於久居都市的人們而言,是必須重新學習的,而且這種學習對忙碌的現代人而言,機會並不是很多,這本書或許就是能引領我們重新看到大自然的那一扇窗。
推薦序三
存在的與消失的∕凌拂(自然文學作家)
我已多年不搭乘火車,總嫌它太慢。讀《寄自野地的明信片》之際,我又沿著西部幹線一路迤邐,自北而南走的是海線。啊!這一趟離我第一次搭乘火車的記憶,無論從哪一方看,十個指頭來回盤算,都是不堪計量的了。
這個世界追求速度,從最早的西部幹線、到高速公路、到高鐵……許多鐵路支線已經消失。
新舊交替,我看著車窗外一路改變的地貌,格外珍惜《寄自野地的明信片》裡所踏察漫遊的自然記憶。不僅是台灣,整個世界都在改變,淡水線已被捷運取代,我搭乘的這一條西部幹線,難說還有幾回迤邐風光。
沿海朔風野大,濱海人家耕植,以芒草為籬,叢聚的芒草成排狀羅列,形成了一方一方的旱地耕作景觀。火車向南行駛,右邊是海、左邊是山,我翻著一頁一頁明信片般的手繪文稿,景入眼來,村鎮、郊山、溪流……我先看圖再看郵戳,試試看自己根據圖稿可猜中幾許地貌所在。離離原上草,我的車窗望出去是海,近處淤積的汙泥,相形之下,在失去與存在之間,《寄自野地的明信片》對我有著種種糾結的起伏。
一張一張的圖搭配文字,恰似明信片一般,其中有人文、有風景、有季節、有物種,還有種種讀著的心情。作者在明信片裡展現的心情,和我從車窗裡觀景的心情,多麼熟悉,每一處都含納了許多既動人又有趣的故事。每一頁明信片都彷彿一片窗景,我從車窗裡望出去,恰如書從我手中一頁一頁翻過,既親近又遙遠,景物與時間的流動,作者告訴我們許多存在但被忽略的細節。
劉伯樂的畫很好。小品、安靜,淡淡的水墨煙雲,細草間見微風,遠雲中見地貌,處處有他行走間的深情。喜歡自然、走過野地的人,應當都會受他的畫波動,因為熟悉,所以很容易走進《寄自野地的明信片》裡去。
他的文字疏淡,一如日子,但恬靜中亦有突起。他寫燈蛾的麇集、鳥獸蟲魚的爾虞我詐、生物間的狐假虎威,淡靜中一如飛鳥拍翅、斑蝶搧風,仍然輕巧,但一動一靜間譜出自然的律動與訊息。
在書中作者走了很多地方,許多是人們熟悉、常見的處所,透過明信片的形式、郵戳的印記,尋常景觀,文圖配合,更為親和的拉進了生活與野地的距離。隨機的美,極其家常,卻見出作者的取景與用心,信手摭取情意自在,自然就在我們的身邊。
作者側寫
安安靜靜的鳥世界—我所認識的劉伯樂∕吳明益(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作家)
其實我並不十分準確記得,和劉伯樂老師認識的時間。大約是幾年前,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在士林官邸營造了一個生態園,由我和劉老師(我向來稱閱歷足以教導我的人老師)各寫一本書來做為生態園的導覽手冊。我們設定的閱讀對象並不相同,我所寫的那本針對所謂「大人」,試著以歷史、人文和自然交錯的資料,結合感性引導去寫,希望能擺脫導覽手冊千篇一律的困境。
劉老師的寫作對象卻是孩子,我一向認為,那比寫給大人閱讀還要困難得多(或許這對畫過許多繪本的劉老師而言不是問題)。記得在書完成後的一個座談會裡,劉老師提到說如果是他不能解釋得很清楚的東西,不妨讓孩子留下疑問也沒有關係。
確實如此,在自然裡行走,存在疑問的時候,往往比馬上有解答的時候多,而且總會因此留下一種牽掛的情緒,那種情緒總讓我們重新回到現場,回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時空裡。
從此我就常向劉老師請教一些攝影上的問題,或者交換一些野地的訊息。我記得那幾年我們正面臨從傳統幻燈片是否轉換為數位攝影的掙扎,總覺得使用數位影像拍照可能意謂著「少了些什麼」—也許是少了以前那種拍完照後的等待過程:出外旅行、等待、按下快門,將膠卷收到胸口的口袋裡,回來沖洗,一張張放在燈箱上用放大鏡審視,記憶在腦中閃現而過,然後用簽字筆在幻燈片匣上寫下拍照的時間、地點,以及鳥或昆蟲的名字。
那裡頭彷彿有一種孩子氣的執著,我們像個什麼都不知道的孩子,慢慢將龐大的自然在各自小小的暗室裡歸檔。
有一年春天劉老師問我是否有興趣到占山看灰面鵟鷹,另一個原因是,他在那地方曾經拍過升天鳳蝶。我還記得那天我們是搭另一位小學退休校長柯明雄老師的車上山,找到一處制高點,頂著北台灣已經十分強烈的日頭等待灰面鵟鷹的出現。不久風起,劉老師和柯老師舉起鏡頭,然後那不可見的氣流,便帶著準備北返的鷹群出現。不算密集的鷹群像是從我們眼前的等高線飛過,底下是淡水河的線條.. 我注意到那個剎那,確實有一隻升天鳳蝶在難以接近的花叢間吸蜜,旋即飛離。我們各自在自己的觀景窗裡想著屬於自己的心事,直到鷹群暫時隱沒在我們的可見視野之外。一些鳥友的手機響起,原來是另一邊山頭的鳥友,打電話來報告我們所不得見的,另一片天空的鷹訊了。
劉老師跟我說過,他拍鳥有很大一個原因是為了畫鳥。為了把鳥從各個角度畫得清楚沒有差錯,因此需要各種角度的照片。我偶爾會收到劉老師傳來他的畫作,攝影,或者是他從網上發現的一些國外優異的生態攝影作品,署名也變成「劉鳥」(而他的網站則叫「什麼鳥世界」)。我特別喜歡收到劉老師自己出外觀察時的速寫畫作,線條因為時間受限的關係,不像在室內畫鳥那般謹嚴,卻能以最簡單、直接的筆觸勾畫出一種「訊息」:即使我們現在只坐在電腦前,但「自然」仍在地球上的每一處生氣勃勃的運作著。
對劉老師來說,他那輛看起來有點破舊的箱型車就是一個活動基地吧。有一回他從台北來到花蓮,我留他在校內住一夜,他說已經決定先去黃昏市場買些野菜要帶回南投,今晚準備睡在神祕谷裡,看看明天早上會拍到什麼鳥。
帶著某種等待(或者說期待)的情緒睡去(多半時間是睡不著的),然後在天未光之前起身,尋找地點,架起腳架,或帶著速寫本,尋思一個構圖的角落(面對廣袤的野地,我們永遠只能留下一個角落在畫本上)。我常常想像這樣的劉伯樂的身影,想像或許有某一天會在某個不知名的溪谷和他偶然相遇。一向話少的劉老師,或許仍是安安靜靜的微笑跟我打聲招呼,就再回到屬於自己的「時空」裡。那是一種喜歡自然的人都會擁有的,屬於自身的「抽離時空」,只能等待有朝一日,從他們的畫作、攝影或文字才得以窺見。原來那一刻,他心裡是這麼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