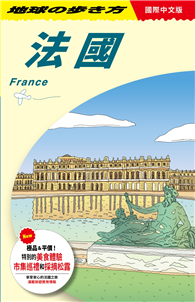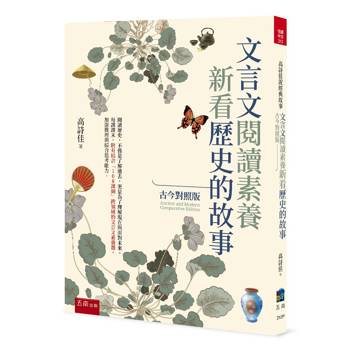專文推薦
萬教並生蓮花──心道法師傳∕柏楊
當一個舊星球破碎時,另一個新星球會再昇起;當一個舊人生破碎時,另一個新人生會再創造。祇要你有足夠的虔敬,總有一天你會感謝你苦難的來源,同時也是你營養的來源。人,不可能瀟灑走一回,他的負擔跟他的使命,同時沈重。
心道大師奇離的喪父,又詭異的失母,我讀到那一段,滿紙眼淚,他母親抱著襁褓中的妹妹,夜深人靜,悄悄走到年紀還不到四歲的心道床前,掖了掖被子,向半睡半醒的孩子凝視著,沒有吻他,沒有抱他,沒有一句叮嚀他的話,只留下來永遠無法解開的謎,回頭走去,從此沒有任何消息,孩子的心滴血,我們讀者的心也隨著滴血。
這個無法彌補的遺憾,永遠掛在心道大師的心頭,對他的影響是入骨的,所以,他終身從不離棄一個人,尤其是那些心靈上倚靠他的人。
在另一片世界裡,我和心道大師有一個共同奇特的緣分,一九五○年代,我在報上寫「異域」,十年監牢之後,我又繼續寫「金三角.荒城」,曾引起廣泛的「送炭到泰北運動」,而心道大師就是第一次撤退的第一代孤軍(《異域》一書中對這第一次的撤退有過介紹)。心道大師那時候才十幾歲!寫到這裡,回想五十年前,當還是孩子的心道在清泉崗赤膊操練的時候,柏楊在汗流浹背的伏案報導孤軍故事,而今心道安坐在他的宗教博物館,柏楊繼續汗流浹背的伏案為心道的傳記寫序,這就是緣分吧!
每個人生來都有宗教情感,心道大師生在緬甸這個佛教國家裡,他來台灣後,又不斷的接觸到佛教大師,所以他的悟道很早,而且有更廣的開拓。真正為心道大師剃度,把他領進佛門的是星雲大師。邊區孤軍第一次撤退到台灣後,心道年紀實在太小,那年才十四歲,身子還沒有鎗的三分之二高,他既扛不動鎗,鎗也扛不動他,軍事訓練單位對這一批孩子們,實在無從著手,於是由教育部分別把他們轉入各小學──白天到學校讀書,晚上回營房睡覺。心道大師讀過員樹林國小,而就在這個時候,他迷上了武俠小說,他和一般小朋友一樣,決定當大俠,打盡世界不公平的事,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一本武俠秘笈,幾個小毛頭自己練起神功,尤其又練起輕功,方法很簡單,祇要在腳上綁個砂袋即可,在上學的路上走得怪模怪樣,堅信有一天,可以練成飛簷走壁,他們有一個信條,當大俠不是夢,而是正義與力量的延伸。
大俠當然沒有當成,心道大師最後被星雲大師接入佛門,剃度出家。我想起一個比喻,星雲大師好像唐僧,莊嚴肅穆,嚴守戒律,慷慨高貴,捨身佈施。而心道大師則像孫悟空,雲遊各界。二十年後,心道大師成立宗教博物館,組成新的淨土。使萬教並生蓮花,星雲為他祝福。星雲東天送經,使當年玄奘西天所取的經,更加豐滿後,再東傳萬邦。
出家千千萬萬,高僧是國家之寶,面對高僧,我們合十頂禮。
序
釋心道
三十年前,我到荖蘭山閉關斷食,很辛苦,幾乎連命都沒有了。
剛開始借住在普陀巖山洞,那時看管仙公廟的詹廟祝和福隆當地的耆老,還有後來把聖山寺捐給我的吳春泉老先生,都說這山很奇,是聖山。
這裡一片荒山漫漫,沒有水,沒有電,什麼都沒有,只有前山腰的仙公廟、普陀巖。
有一天,我坐在斷巖上望著海,一望無際,海潮一波波推送過來,日日夜夜的潮音,我感到這裡未來會度很多的人,很多海外的緣。當時徒弟法性還笑我說:師父啊,你會不會餓到「起了肖」?明天怎麼過還是問題,這裡什麼也沒有啊!師父你是怎麼看到未來的呢?
出關後,每天有很多人來找我,我天天等著人上門來「踢館」;都是問些人生問題,什麼都問,還有很多宗教問題,也是緣起。
這樣一路過到今天。回頭看看這裡,就是一個菩薩居的地方,這裡處處是緣起,處處是菩提。它不屬於羅漢,也不只是道廟,這裡是觀音訂走的地方,觀音在這裡產生能量,祂要做的事就是對應這時代的疑難雜症,祂有一套呈現教化因緣的方法與工具,我覺得我只是祂的手腳,這裡是菩薩居地。
一切從零開始。靈鷲山團隊是從籌設世界宗教博物館開始的,沒有建宗博這個大願力,就沒有這個團體。一開始,我們在國際佛學研究中心找一些專家顧問互動,慢慢激盪出五大志業,其中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因緣先成熟。有了計畫,接下來就是怎麼啟動?當時宜蘭有一家證券公司,他們主管來結緣,整個公司的人都來皈依,讓我們去說明世界宗教博物館的理念。
從宜蘭開始,再往台北,到全台走透透,我們開始做人的連結,有了人就成立護法會;為了募款,後來水陸法會的因緣也開始了。又因為建宗教博物館要得到各宗教的見解與支持,我們四處參訪各宗教,主動去敲門,謙卑地向他們請教,就這樣,一路把願力擴散開來,把很多資源串聯起來,可以說大家有什麼就出什麼、會什麼就幫忙什麼,一遇到問題就是突破,突破到底。
我是一個窮和尚,什麼也沒有,什麼專業也不懂,就是一直拜會、一直做關懷、一直在緣上去貫串我的體會,只是把這些有緣的人都啟動起來,這樣日以繼夜地做。可以說,我這一生到現在最大的供佛,就是宗博。然後,接著就是要把這個和平的基因延伸出去,複製這個和平基因,延伸到一個人人可以成佛的學園。
不修行,我不可能有這個願力。這個願,就是〈大悲咒〉的力量,也是觀音菩薩的力量,一一化為我的實踐。
導讀
春深猶有子規啼─訪道與勘驗∕林谷芳
禪問答中有個大家熟悉得不得了的故事:
白居易向鳥窠禪師問佛法大意,鳥窠給予最「傳統」的答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以為這答案三歲小兒都曉得,鳥窠則回以「三歲小兒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的回答。
這回答在佛門是老生常談,鳥窠的對應從機鋒高峻的禪者來說,更係聞之須掩耳疾走之論,不過,如此卑之無甚高論的言語,後來卻仍不斷出現在披雲狂笑的禪門,究其故,則因它扣準了修行的原點。
修行是什麼?對禪或其他法門而言,核心都在「了生死」。而「了生死」並非語言文字的遊戲,它只能親身體踐,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因此,看個修行人,重點不在他談的理論有多系統,多玄妙,而在他是否有能力「化抽象的哲理為具體的證悟」。
的確,修行是化抽象哲理為具體證悟之事,因此,求道雖強調解行並重,但所有的解如果未有化成行的能量,就只能是一種戲論。也所以,讀遍經論,常不如直接閱讀行者所體踐出來的生命大書有用,所謂「聽其言」,不如「觀其行」,正是許多人所以須親近大德的原因。而在特別標舉言語道斷的宗門,祖師行儀更是一個離乎言語相的公案,師徒能否承續,關鍵往往就在徒弟能否從師門行儀中得到自己聞思的印證。
不過,能親炙固然最好,但還得具備一定的時節因緣,因此,祖師傳記乃常成為有心者的重要資糧,歷史中從較簡的高僧傳、傳燈錄,到詳細的祖師年譜及傳記之所以能不絕於書,也正緣於此。它是我們在談修行、談傳承、談法門所不能忽略的一環,而其中的內容、體例,以及讀者切入角度的不同,則使它們在修行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
從體例而言,年譜較如實,傳記則常有主觀的想像,而小說式的寫法,主人公更往往只是寫者觀點的代言。當然,公案、語錄的記載,精簡且直扣核心,最能予人啟發,但行儀既略,有心者乃很難由之窺知行者那點滴在心頭的轉折歷程,於是也只能停留在心嚮往之的階段。
至於內容,老實深刻的行者本以整個生命面對生死,不著一處,全體即是,下筆就難,以此行儀中應以何者為核心,乃成為寫者落筆取捨的關鍵。而在此,因不同人的不同詮釋,彼此自可差異極大,例如弘一法師,要以俗情的文化藝術,還是似根柢的宗教情懷寫他出家的因緣,結果就可判若兩人。
而即使體例及寫法問題不大,誰來讀這本書也可以導出不同的判準,有些人看祖師行儀像在求靈異紀錄,有些人則永遠以人的世界為最終關懷,有的人看度眾事業,有的人卻窺內心幽微,有人想理出修行步驟,有人則強調悟後風光。
就這樣,雖說高僧傳略、祖師行儀是重要資糧,但就如佛法講因緣般,不同對應乃可以使它是藥,也可以使它是毒,而就中,讀者既是攝受者,自己能否獨具隻眼就成為個中關鍵,過去講「師訪徒三年,徒訪師三年」即因於此。
師訪徒是尋人才,伯樂找千里馬,機率小,但不容易看走眼,因為是以先進印後學;可徒訪師就不然,以外行看「內行」,未證之地談已證之人,看走眼的機率基本就大,而這也正是怪力亂神始終可大張旗鼓的原因,多少人或為印象所惑,或因理事不夠圓融強作最勝義解,結果不要說魔軍可以惑眾,連江湖小卒也常沐猴而冠,可憐的是訪道之人,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莫此為甚。
***
不過,勘驗雖不易,卻也非完全無法可想。首先,修行的系統固提供了一個基底座標,不同行儀的比較也讓勘驗有了相對基準。這些基準,有些是所有行者必須共同體現的,例如,向道之心、如實行儀。有些則是不同法門所欲達致的,例如禪者根柢上有其自性天真或截斷眾流的要求,密宗行者則要求理事相即,在不同因緣內呈現不同對應,其間的不同,在禪是一絲不掛,直取本心,只破不立;在密則為即事而真,我手即為佛手,從妙有體証。
當然,宗派之外,還有個人生命情性與修持法門顯現的不同生命風光。
如此,若能從上述三個面相切入,對行者的勘驗固不能說能立即相契,但雖不中亦不遠矣!而這也正是修行的原點儘管在體證,深入經論卻永遠有其重要性的原因。因為,當應世的人格不在時,故應「以法為師」,而即使在世,習者若要免於識而不見,仍需系統修行理論的指引。
以這樣的角度來看行者的行儀,下面的一些重點恐怕是大家必須注意到的。
首先:行者的向道因緣何在?是生具夙慧,天生具有宗教心?還是因某種因緣使然?這種因緣是家事、國事、天下事的世間情?還是對死生天塹的諦觀?也或者只是對未知世界的嚮往?
其次:行者是以如何的心情,如何的實踐來對應這向道的因緣?是捨離萬緣,孤獨求道?還是寄身叢林,直領宗風?甚或是慈悲應緣,度人自度?在此,行者對世間變動事務依戀的俗情總要能不在,也所以老實、堅忍、綿密就是許多行者人格的基本特質,常常讓人為其一生的投入而動容。
此外,更關鍵的是他修習什麼法門,又如何相應?坦白說,這才真是考驗習者的地方,而就此,哪個法門是以信為本?哪個法門強調智為能入?哪種法門直取慈悲?哪種法門強調能量轉換?又有哪個法門當下即是?習者不僅基點的認知要準,對行者相應的勘驗尤其要在訪道中不斷反思觀照,終至具備識人的法眼才行。
最後,行者成就整體生命的風光何在?或他面臨生死所映現的成就為何?更是觀照的焦點。前者就整體觀之,可免去「但見秋毫,不見輿薪」之病,例如有些乩童雖有靈通,但除此之外,一無可取,不僅缺乏生命境界,法門其實也不足恃;而後者則是最核心,最無可重來的應現,也是最嚴厲的考驗,因此禪者示寂乃成為禪門最大量也最值得參究的公案,就如天童宏智臨終偈有「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淹沒,秋水連天」之句,以此,他一生標舉的默照風光才有堅實的支撐,而弘一雖不在宗門,但去掉了「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去掉了「悲欣交集」,則一生行儀所能照亮人者,恐怕也將減半。
坦白說,一個人掌握了這些基點要來勘驗行者,則除非對方真乃潛修密行之輩,應該都能窺見一些真實;甚且,經由理論與實證的磨練,對「內修菩薩密,外顯羅漢形」的微細行儀,也能體得事情並非只是外表所見到的那般;至於那些妖言惑眾,未證言證者更就難逃法眼了。
有了勘驗,求道者就會回到「更如實」的立場,來看修行者應現的一切,不會活在一種假相的追求中。這就如同釋尊有背痛,行者觀照的不應是他有沒有背痛,而是悟者究係如何面對苦痛。猶記得年輕時,有一好友一次提及他在寺院中聽經,看到座主面對炎炎夏日,汗如雨下,邊拭汗邊講經時的震撼般,一個求道者在了解了「和尚也是人,也要流汗」時,其在「如實」上就又過了一層。當然,話說回頭,行者真的在炎夏中都必會揮汗嗎?有沒有不畏寒暑的情形?有沒有以心轉物的生命?「安禪不須入山水,滅卻切心頭火自涼」真只是一句唯心的標舉,還是有其如實的印證可能?習者這樣一層層地轉進,與道相應自然不遠。
***
誠然,這些年來台灣宗教大興,應世的宗教人格以傳記型態呈現自己者所在多有,這些或自述,或由他人書寫,儼然已成為弘法的重要資糧,不過,有心者還是要問:這其中究竟反應了哪些訊息?而就此,傳略的本身,其實並不只是書中主人的分身,它更是一面直接映現主人翁當今生命風光的鏡子,對訪道者而言則更提供了直探幽微的大好機緣。可惜的是,這弘法的資糧目前果真也只是弘法的資糧,它映照的功能並沒被大家注意,許多書的寫法更常只是將外界固定的印象加以圓滿化而已。
那麼,《靈鷲山外山》中所說,從兒時受戰爭之苦,親睹行者天足神通,與觀世音的夙世因緣,樂於禪坐,入於塚間修行,長期斷食閉關,短短十年道務興隆,由頭陀行而轉菩薩道,建立世界宗教博物館,以及對宗教大學的願力,乃至三乘合一的穿著,接續不同密法的認證,這些心道法師事蹟之異於常人者,其所彰顯的意義究竟為何?有心者自應由此探入。而更甚地,還需深入這些事蹟異於許多修行人之處又在哪裡?他的意義又該如何看待?當然,更如實地,還可以問:在基本的事蹟外,書中的一切哪些是作者的貫連?哪些是弟子的理解?哪些又是當事者主體的記憶與詮釋?
而若如此來問,我們或者就可以發現文字陳述故無法描摹行者全貌,也很難直探心境幽微,但這本書所寫相較於時下許多道場行者的傳記則的確仍顯現了一些關鍵的不同,而這不同對修行還非常重要。
不同在哪裡呢?最根柢也最明顯,讓人領受深刻的,也許就在那「行」的徹底。塚間修、斷食、閉關,這看來自了、無益世間的一切,不就該是行者的本份嗎?就是有了這本份,應世的風光才不會因入於世間而與世間法無盡糾纏,甚至喪失了主體,而這也正是靈鷲山一直強調實修,且以閉關等修行為常務的原因。從大環境講,這是台灣在極端強調人間佛教後必要有的返觀;從個人言,守住這個原點,行者才所以是個行者,而在家眾之所以該禮敬三寶,不正也因這行者修行的本務!
當然,修行本須理事圓融,行者更得面對如實的末後一關,因此將任何的傳略作最勝義解,也就有它虛妄的本質,而當事者若離開了「應緣」的基點,有關的一切也將成為魔事。
也就因如此,即使與道場有較深因緣,我還是得即事就理,直扣那對行者勘驗的本質,而好在,靈鷲山的法師邀稿時,竟也在其中表示了以文為鏡的意思,這點可說極不容易,畢竟人的信仰常為道場的核心。即此,這本書的幽微內在乃就有其「依於法」的本質。而這,也將是道場能否宏揚正法,乃久乃大的關鍵。
但雖言勘驗,可坦白說,拋開書中某些作者或弟子立場的解釋,就行者看行者,主人翁心道法師的一些歷程之於我心,正可謂多所戚戚焉。
戚戚焉首先來自「超人」的嚮往。本來,宗教談超凡入聖,原該以聖者為目標,但既言「了生死」,則前提即在敏感地覺受到生死之所限,於是超越生死,或可以預示能超越生死的神仙、靈界、超人之能力,如各種神通的出現,對於行者就有絕對的意義,而初期以有形有相「神通」顯現的超人為嚮往,也就是許多行者的「自然」,坦白說,不經一番的反思、印證而侈言神通不足恃,或排斥神通,其實往往與基本的了生死有違,而在此,心道法師睹羅漢飛行而習道,與個人年少時之歷程實有同工之妙。
戚戚焉之二來自實踐上的頭陀行。本來,禪者「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也所以四祖道信攝心無寐,脥不至席,祖師幽棲林居,入山唯恐不深,其目的當然不在苦行避世,而是未經這一番寒徹,就難照見無明幽微,而也只有如此,接引度眾才能有堅實基礎,否則即使不以盲導盲,也容易止於人天福報,終與死生大事有隔。
人常謂末法是「言道者多,證道者少」之時,而證之所以少,即因必須嚴厲面對生命之貪、嗔、癡,可這種修行何如口頭禪爽快。不過,雖說這是習者通病,但死生之苦既無時不相逼,則一個真正的行者生涯,即必是許多人內心的渴望,而從這,也才可以說明不善言辭的苦行者為何常能迅速集聚信眾的原因。
禪講滌蕩,只有一絲不掛,方有全體即是的風光,就此,心道法師前期的行持雖非禪門直接之透脫,卻深扣行者基點,正足以使人動容。
戚戚焉之三來自立場的消磨。坦白說,這在書中並沒特別拈提,但從不拘一乘的教法,從援引各宗高僧大德的入山,乃至靈鷲道場在興建時,不見一般常有之宗教本位,而力圖與山林、自然相溶,這些都說明了法師這一特質,而下面的一個小故事正可以看到行者柔軟心之所在:
有一次在年度法會的開示上,不善長篇辭令的心道,在必須「填滿」時間與信徒之期待下,在台上乃一路說去,可卻愈說愈遠,最後他摸摸自己的頭,靦腆的一笑,說:「你看,又在這裡胡說八道了!」
***
本來,既非明明白白的示現,則即使位臻菩薩之位,也仍有隔陰之迷,但道場、師父既為眾生心念之所繫,人間層次故作的「勝義解」乃常不能免,但在這完整行儀與完美人格自描寫與詮釋下,修行本質卻因此常隱沒不彰,而行者若能不諱言自己尚在修習,尚有「罩門」,即正是不離本心的體現。禪講「自性天真」,但能對應於此的又有幾人?
誠然,儘管「了生死」是行者共同的觀照,但不同生命情性,不同法門修習,自然就呈現出不同的生命風光。以此,《靈鷲山外山》的描寫,也就不盡然能在不同行者身上起相應。而對我而言,那守住行者基點的部分正是我想提醒大家的,至於就當事者來說,禪門「劍刃上行、冰稜上走」的提醒,則已說明了「立傳」會帶來「稍一不慎,即喪失性命」的危險,而要免此危險,只有守住因緣之理,體得事物無實性,因緣而生,因緣而滅的道理,如此,身為局中人,心道法師自須一哂即可,而讀者更當從體會此傳生成的因緣切入,至於獲邀為文的我,書與此文自然該是照見自己修行的一面鏡子。
在言語機巧充斥的當代,「如實」對行者甚至也已成為遙遠的詞語,以是,師徒相訪、行者印證,竟已模糊不清,這不禁讓我想起「萬壽辯」的一首禪詩:
人傳師死已多時,我獨躊躇未決疑;
既是巢空雲又散,春深猶有子規啼。
子規何在?這的確是習者入道最需面對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