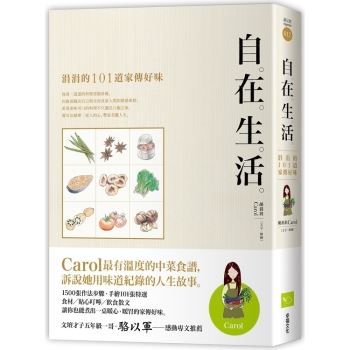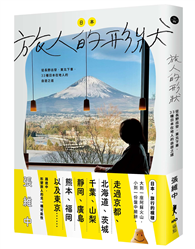譯後記
完成《流浪者之歌》翻譯工作的第一個感受不是成就感,不是閱讀的喜悅,而是盤旋不去的疑問:即使是個主角求道有成的故事,這般圓熟的、充滿慈悲的赫塞依然讓我感到意外,雖然不必充滿激昂的情緒,和五年後(一九二七)出版的《荒野之狼》散發的憤世嫉俗、書空咄咄,甚至可說是滿紙的怨言相較之下,《流浪者之歌》更像多年歷練而生命智慧增長之後寫出來的作品──從赫塞的書信中可以得知,有些讀者,那些從《流浪者之歌》得到啟發、以為找到人生方向的讀者,甚至因此對《荒野之狼》感到失望。而和三年前(一九一九)初版的《徬徨少年時》相比,《流浪者之歌》卻又少了那份為了追求個體性,渴望擺脫整體束縛的那種掙扎。
赫塞如何能平心靜氣地寫下這樣一個故事?文學作品雖然未必便是作者個人的生活故事,但是作者當時的心境和經歷必然反映在作品上。赫塞當時可說是命運多舛:他的妻子因為精神宿疾多次出入療養院,三個兒子託付友人代為撫養,幼子重病幾乎早夭,他自己的精神狀態也不穩定,曾經多次向榮格尋求心理方面的協助。而整個大環境又如何呢?從一次世界大戰前就開始醞釀的、敵視和平主義者的氣氛壓抑著他,直到戰後都未稍歇;而他大戰時為德籍戰俘奉獻心力,即使他在瑞士生活,他還是和德國人民的命運相連,感受戰爭的殘酷、平民的無奈和痛苦,而大戰後的經濟蕭條、貨幣貶值也直接衝擊他的生活,他在德國的收入只剩下原來的十分之一,如果不是友人贊助,他必然陷入絕境──這種種內外交迫之下,《流浪者之歌》的第一、二部之間整整隔了十八個月。他可以抱怨的,他可以控訴的!
然而在猶豫了年餘之後,赫塞決定讓他筆下的王子走入世間,經歷所謂「童稚之人」的悲歡離合,而非避世出家,尋求解脫。轉念一想,這樣的安排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許就是當時大環境的種種讓赫塞的自身體驗昇華,面對普遍的人間苦難,他讓悉達塔走上超越個人─群體對立的道路,在充分經驗世間甘苦之後,體認個體的救贖不在尋求絕對的個體化,而是在於完全融入群體,認識到群體對個體性的必要。至少在一九二○年代之初赫塞的看法大致如此。
而從赫塞的書信也可以了解到,和《徬徨少年時》同時開始構思寫作的《流浪者之歌》並非是對立的,而是一體兩面:悉達塔的成道之路不在擺脫群體,而是從群體認知個體生存的意義,而他的方式卻絕對是獨特的──悉達塔沒有走上出生以來幾乎可說是必然的道路,他並未成為婆羅門,也未尋求個人精神的超脫而成為脫離世俗的僧侶,而是跳脫他的階級和原本的生活氛圍,以他自己的、回歸世間的方式「得道」,這是他超越群體的方式。德密安不全然是革命家,悉達塔也不必然是甘於流俗。
無論我們如何詮釋這本書,從《流浪者之歌》直到五年後的《荒野之狼》和晚年的《玻璃珠遊戲》,個體─群體間的關係無疑地都是赫塞作品的最重要主題,而這些作品都是赫塞對這個主題的反覆思惟、試驗。我們可以在《荒野之狼》裡讀到年近五十的主角哈利,在他認為已經變調的世界裡踽踽獨行,渴望找到讓自己能在那個世界裡自在生活的方式,雖然最後仍然學不好幽世界一默這堂課。又在《玻璃珠遊戲》裡讀到遊戲大師如何生於群體之中,個人特質在其中得到最大的發揮,最後仍渴望脫離這個群體,只為了讓這個群體的精神更為發揚,卻在離去之後隨即驟然逝去……不管是哪一本作品都耐人尋味。
在我們這個處處講究個體化,而個體卻不斷迷失而感到疏離,群體不時崩解到讓「個體性」顯得可笑的時代,赫塞很in!
能夠有機會翻譯赫塞中晚年這三部最重要作品,身為譯者是很幸福的,也祈願讀者能從閱讀之中得到樂趣和啟發。
導讀
詩篇.還原
赫塞是個詩人,不僅就廣義而言。只要是稍微熟悉赫塞作品的讀者應該不難發現,在他的著作裡多少都會出現一些短詩,而他的晚年鉅著《玻璃珠遊戲》更收錄了十三首長詩。但是只因為這些詩作,我們就可以稱他為「詩人」嗎?他的作品難道不是以敘述文為主體?
德文的「詩人」(Dichter)和「文學作品」(Dichtung)有相同的字根,而西方文類「敘述文/散文」(Prosa)也是由「史詩」(Epos)直接演化而來,「詩」的形態甚至意味就在文類的發展當中,逐漸從散文當中消失。現代文學作家或單一作品大多擇一而為,詩和散文之間出現清楚的界線。但是偶爾我們會驚喜地在詩當中清楚看到敘事的脈絡,或者在敘述文的字裡行間嗅到詩的意味,感覺到詩的節奏脈動。
《流浪者之歌》就是這樣的作品。第一眼並無法從文本外在形式發現詩的蹤跡,但是如果朗讀德文文本,第一段就能察覺這個文本明顯不同於散文的地方:最初四個短句之間只以逗號分開,刻意省略串連文意的連接詞,以「陰影」為主要意象,第一、三和二、四句隱隱對稱呼應,引出悉達塔眼中、心中的陰影,而我們甚至不必藉助西洋詩韻分析的技巧,詩的韻律和節奏依舊觸動鼓膜,這種詩的意味在第一章尤其濃厚。詩的意象,濃縮的語言,清楚或隱蔽的譬喻在全文之間不時浮現,甚至以短詩般的文句鑲嵌在敘述文句段落裡,呈現悉達塔修行法門時的心境幻化,或是表現出主角初覺醒時的心無罣礙,意識的飛揚跳脫。和其他同時代作品比較,好比托瑪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甚至和赫塞其他的作品比較起來,這樣的手法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樣的文字律動──為赫塞作傳的雨果.巴爾直接表示,《流浪者之歌》的文字裡有音樂--突破了散文的侷限,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
西方詩韻和中文詩律大不相同,近宋詞而遠唐詩,要把德文的詩翻譯成中文有基本的困難之處,然而我們並不因此放棄傳達赫塞文本特出之處,盡力在這個中譯本之中保留赫塞的「文字音樂」,希望讓中文的讀者也能感受到赫塞吟詠般的文字。
或許讀者此時會浮現一個問題:赫塞為何選擇以這樣的文字風格來說這個故事?為何不中規中矩地以散文來表現故事內涵,而是把詩韻瀰漫、暈染在字裡行間?我們也許可以從《流浪者之歌》這本印度詩篇究竟有多「印度」來討論。
從赫塞的生平得知,赫塞和印度的關係可以追溯至他的祖父輩。他的外祖父不僅是長居印度的傳教士,更是研究印度文化的學者,通曉幾十種印度方言,編輯許多印度文獻百科,而赫塞的母親在印度出生,也能說數種印度方言。赫塞從小就在他外祖父塞滿印度文獻的書房裡流連,和他的兄弟姊妹一起唱著印度教的傳統經典──印度教有許多經文正是口頭流傳而非立於文字的。可以說這樣的詩韻從赫塞幼年起就在他的血液裡流動。
而赫塞對印度教的喜愛也許就在那是一種深入庶民生活的宗教──想像赫塞到印度旅行的時候,他一定不只一次聽到這樣的旋律,可能在祭祀慶典之間,可能出自目不識丁的農夫口中,或是被船夫詠唱著,讓他發出由衷的讚嘆,讚美印度教的思想美妙地被轉化成荒誕或神奇的故事,不斷被傳唱--而這正是赫塞對宗教的理想:宗教不必是高深的思想體系──他本身所屬的基督新教正是這種把信仰從生活抽離成抽象的理性系統的代表,而這也是他對新教不滿的地方──宗教應是一首簡單的詩歌,是一種生活態度,可以隨時慰藉任何有所需求的心靈。
然而赫塞對印度/印度教並非毫無批判的,在他的東方之旅之中(一九一一年經印度、中國到東南亞的馬來西亞等地),看到印度當地生活之後,他對印度的看法已經改變,幼時美好印象的現實面是經濟上的落後,平民生活艱苦而缺乏活力,他也許因此不再那般重視印度教,轉而將觸角更深入其他東方哲學系統。他當然熟悉同樣誕生於印度的另一種宗教--佛教,據赫塞自己的說法,曾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佛教是他的信仰所在,是他唯一的心靈慰藉。然而在他書寫《流浪者之歌》的時候,他對佛教的看法已經改變,認為佛教的世界觀之中沒有神的存在,只有純粹理性的觀點,只能從佛法當中得到個人救贖,這一點其實是和新教類似的。不論他對佛教的看法是否正確,他的確認為佛教在某些層面就像改革過的印度教,自有其優點,然而他仍看重在他眼中──姑且如此形容──比較感性、感官的印度教。赫塞完成《流浪者之歌》的第一部之後,歷經了一年半的躊躇才著手寫作第二部,從他的書信可以得知,其中原因在於他當時還不知道要讓覺醒的婆羅門之子走向什麼樣的道路,他無法描述自身尚未經歷的道路。雖然他個人的實際生活多所困頓,對自己的人生道路感到迷惑,這些的確影響他的寫作,但是他對佛教及印度教的取捨必定左右了他對故事的安排:悉達塔走向世間,走進生活,而非鑽進任何宗教系統。
赫塞和東方思想的關係不止於此,佛教和印度教只是浮現在本書文字表面而清楚可見的,其實赫塞當時對道家老莊──尤其是《道德經》──以及儒家思想多所涉獵。在他寫作《流浪者之歌》的這段時期,也就是一九二○年代,已經有許多這方面的書籍被多次翻譯成德文,而赫塞不時在報章發表他對這些譯本的評論,甚至比較同一部經典的不同譯本之優劣,儼然是當時德語地區的東方哲學專家。而他也曾多次表示,他其實已經捨印度教、佛教而就儒、道,對《道德經》非常推崇。當悉達塔對葛溫達說明知識可以用文字傳達,智慧卻是無法言傳的,雖然可以從佛教來理解這個觀點(例如禪宗),但是這個說法也令人不禁想起《道德經》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綜觀而言,赫塞雖然把故事背景安排在印度,借用佛陀的名字(悉達塔),提及許多印度經典,但他並不試圖書寫一個佛教或是印度教的故事,以赫塞本人的話來說,那只是一種「外衣」,並未深入觸及印度教義的核心。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探討「個人」和「一體」的關係:他之所以引進重視一體的東方宗教以及哲學系統,寫成這樣一個故事,為的是讓西方讀者認識到追求個體性是好的,但是不必因此視群體為對立面,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而「一體」這個概念,人與萬物合一,不僅在印度教當中,在儒、釋、道三家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更是道家最中心的思想。赫塞想寫的不是任何一派哲學思想,也不是任何宗教的教義,而是尋求所有思想體系共通的普世價值。
於是印度對本書的獨特印記只剩下印度教經典的散文詩格式:他刻意切斷文字的連結,讓﹁意義﹂可以從文字解放出來,使思想得以輕颺,卻又連綴成一完整故事,揭露本書最終主旨,這完全符合他透過悉達塔想要傳達的「知識可以言傳,智慧只由體驗」--不拘泥於文字邏輯與文類形式,而是體驗文字,感受文字的脈動,讓讀者自行想像、理解,給讀者傾聽自心聲音的空間。這難道不是亞里斯多德《詩學》所主張的「內容與形式統一」?
赫塞是個詩人!
柯晏邾(本書譯者)
推薦
發光的傷口--閱讀《流浪者之歌》
多年後,再次閱讀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這部作為讓我從此認定赫曼.赫塞是我這一生最喜愛的作家的作品--真誠的讚嘆與喜悅如泉湧般,滋潤了日復一日在商業計量生活中打轉的、躁懼的心。
我越來越明白,生命中,若要能超越自尊、自負、自卑、自憐、自厭、自棄等種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習氣,悲傷的重要、傷口的必須。
傷悲,因為感受著終究徒勞無功的原地打轉。
傷口,因為陷入膠著於求而不得的痛苦掙扎。
是這樣的。只有經歷當下認為再也無法承受了的哀傷,只有默默忍耐傷口持續的發燙與燒灼,我們才有機會具足真正謙卑聆聽的同理之心,才有機會開啟自身關照世界的無盡慈悲。
是這樣的。縱然離苦求樂的習氣,總是在第一時間抗拒傷悲之感受、預防受傷的可能。縱然巨大的悲傷可能襲捲不退使人沉溺、初時炙痛的傷口可能變成持續自我哀憐的藉口,我知道,這仍是無法避免、驚險、但只得勇敢迎向的唯一道路。
心融化了、心柔軟地、不再排拒與判斷,超越自憐與自尊,發現了溫柔接納世界的道路。
「他的微笑發出光芒,當他看著朋友,這時悉達塔臉上也亮起同樣的微笑。悉達塔的傷口開花了,他的傷悲發出光芒,他的自我已經融入一體。在這一刻,悉達塔停止對抗命運,停止受苦,他的臉上綻放出領悟後的明朗,再也沒有意志與之對立,認識到圓滿,認同諸事之河,認同生命巨流,充滿悲憫,充滿同喜,同流沉浮,融入一體之中。」
這就是傷悲與傷口的禮物,讓流浪的旅人同樣歌唱著、卻不再流浪。
吳旻潔(誠品副董事長/誠品生活總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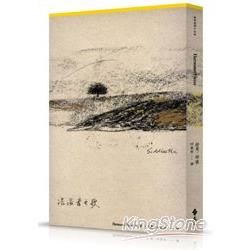
 2024/02/14
2024/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