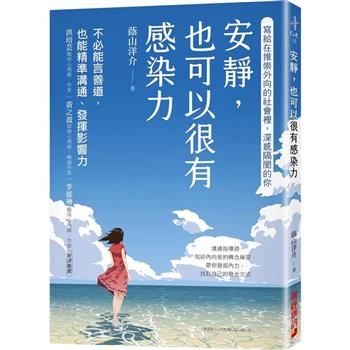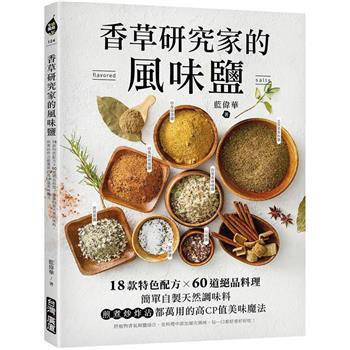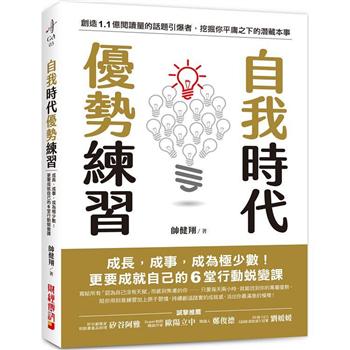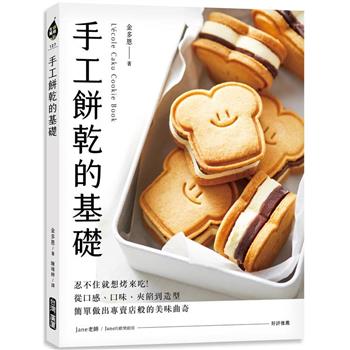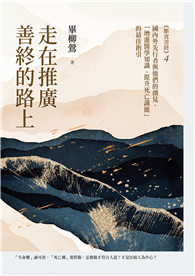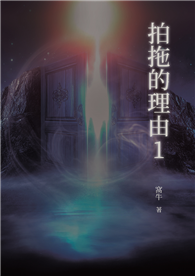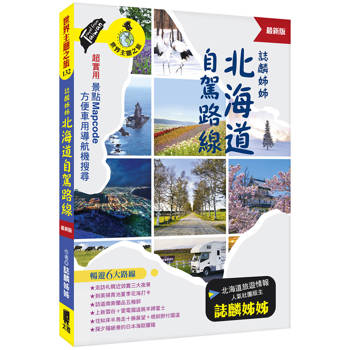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狂人之血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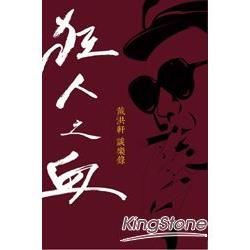 |
狂人之血:戴洪軒談樂錄 作者:戴洪軒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45 |
音樂 |
電子書 |
$ 245 |
音樂總論 |
$ 277 |
音樂總論 |
$ 277 |
音樂 |
$ 315 |
音樂總論 |
$ 315 |
中文書 |
$ 315 |
音樂總論 |
$ 315 |
音樂 |
$ 315 |
藝術設計 |
$ 360 |
藝術設計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圖書名稱:狂人之血
戴洪軒(一九四二~一九九四)
是那個年代最勇敢的藝術家。
他對學生是毫不掩飾、毫無保留的。一個人既然敢赤裸裸地站在學生面前,那麼,他也是赤裸裸地面對自己。
在社會的價值觀與體制的面前,他是不低頭的。然而,這個衝擊力道反彈回來,受傷最大的是他自己。就像希臘神話的伊迪帕斯,面對弒父娶母的真實時,只能刺瞎自己的雙眼。真正有勇氣直面面對真相的人,就只能做瞎子,因為真相太過凶猛,凶猛到沒有一雙人類的眼睛能夠直視。從此之後,伊迪帕斯就成為先知。
戴洪軒是個先知,而先知的代價就是瞎掉,以及毀掉他自身,而周遭的世界也隨之塌陷,變成一個黑洞。──侯德健
思想敏銳,見解獨到,文風別具一格。──馬水龍
至情至性,靈光閃耀。──孫瑋芒
誠摯推薦
李欣芸(音樂製作人)、馬水龍(作曲家)、孫瑋芒(作家)、莊裕安(醫師/作家)、葉綠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鴻鴻(詩人)
作者簡介
陳家帶/編選
寫現代詩,迷古典樂,愛創意電影,更喜歡與人分享生命中的美好。現任文山、新中和社大講師,台大新聞研究所兼任講師。著有《人工夜鶯》(書林)、《城市的靈魂》(書林)、《雨落在全世界的屋頂》(東林)等現代詩集。戴洪軒之於他,亦師亦友,如詩如樂。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