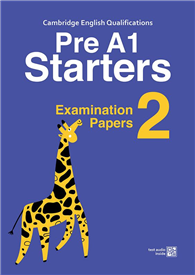彼得.史塔姆
2013年曼布克獎提名‧當代德語小說家第一人
每一個完美家庭的背後,至少都有一顆受傷的心?
《紐約時報》2011年100本最值得關注的好書
田馥甄(歌手)
陳雪(作家)
駱以軍 (作家)
鄧惠文(精神科醫師、廣播節目主持人、作家)
激賞推薦
婚姻生活充滿了各種潛藏與明顯的危險與誘惑,這裡頭真正的危機是:不知道危險會從哪個方向襲來,而誘惑也會以難以想像的面貌出現,人──特別是男人──終究逃不出性格的宿命。
這是一個已婚男人和兩個女人的故事,引爆的時間點在結婚七年之後。但是作者完全出乎刻板認知,刻劃了一段動機、樣態皆不同於一般的婚外情,而「七年」也不只有一個,而是環環相扣了三個「七年」,使得小說的時間跨度上接柏林圍牆倒塌的年代,這二十一年間角色境遇和德國社會的變化。
彼得‧史塔姆不愧是當今德語世界最優秀的小說家,一方面在作品中勾連社會脈動,反映德國統一之後的大興土木、東歐外勞湧入所造成的問題,同時還安排一個超乎常情的佈局,卻能透過精準的心理鋪陳,讓角色的行為顯得合理,又近乎無情地驅動情節推展,讓讀者不忍讀但又停不下來。
彼得‧史塔姆是歐洲最令人興奮的小說家,即便離開會計業多年,筆下的人物仍像會計師一般,計算自己的利率與成本、得與失。──《紐約時報》
本書是關於慾望與欺騙的寓言,製造了存在主義的經典。──《每日電訊報》
對情感的獨到描述,使本書超越同類作品,成為當代最精采的小說。──《衛報》
這部令人不安的作品,呈現了殘酷的現實。──《獨立報》
對婚姻的描繪如此真實,使我落淚。──Amazon讀者
作者簡介:
彼得‧史塔姆Peter Stamm
1963年生於瑞士,早年唸商業,當過五年的會計師,後來入大學,修習英語文學、心理學和精神病理學,在紐約、巴黎、柏林、倫敦等地居留多年。1990年起,成為專職自由作家與記者,創作長篇與短篇小說、廣播劇及劇本,多次獲獎肯定,被譽為德語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2013年獲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提名。著有童書《為什麼要住在城外》(Warum wir vor der Stadt wohnen)、小說《阿格尼絲 如此一天》(Agnes/An Einem Tag Wie Diesem)、《七年》(Sieben Jahre)等作品。
譯者簡介:
姬健梅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德國科隆大學德語文學碩士,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中英文組。從事翻譯多年,文學類譯作包括:杜倫馬特《拋錨》、卡夫卡《變形記》、施奇皮奧斯基《美麗的賽登曼太太》、馬丁.瓦瑟《一個戀愛中的男人》、托瑪斯.曼《魂斷威尼斯》等。
章節試閱
室內燈火通明,索妮雅站在中央,位於中心,向來如此。她微微低下頭,手臂貼近身體,嘴巴在微笑,眼睛卻瞇了起來,彷彿光線太刺眼,又彷彿她覺得痛。她顯得心不在焉,像件展示品,一如牆上那些畫作,沒有人去注意那些畫,雖然大家正是為了這些畫而齊聚一堂。
我抽著一根小雪茄,透過畫廊的大片櫥窗,看著一個相貌堂堂的男子走向索妮雅,跟她攀談。她彷彿回過神來,微微一笑,跟他碰杯。他嘴在動,她臉上流露出一種近乎天真的詫異,接著再度微笑,然而就算從我這兒望過去,我也看得出來她沒在聽那個男子說話,看得出來她在想別的事。
蘇菲還留在我身旁,似乎也在思索。然後她說:「媽媽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是的,」我說,用手摸摸她的頭。「沒錯,妳媽媽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
從早上就開始下雪,但雪一碰到地面就融化了。「我好冷。」蘇菲說,正好有人把門打開,她就鑽進了畫廊。一個高大的禿頭男子走出來,嘴裡叼著一根香菸。他在我面前停下腳步,近得讓人覺得不自在,彷彿我們彼此認識,然後他把香菸點燃。「刺眼的畫,」他說。我沒有答腔,他便轉過身,走開了幾步,頓時顯得沒有自信,有點失落。
我仍然透過櫥窗向裡面望。蘇菲朝著索妮雅跑過去,索妮雅露出喜色。那個相貌堂堂的男子仍然站在她身邊,看到這個小孩,有點尷尬,幾乎像是被得罪了。索妮雅朝蘇菲彎下身子,兩人說了幾句話,蘇菲指著外面。索妮雅把手遮在眼睛上方,皺起額頭,帶著一抹煩躁的微笑,朝我這邊望過來。我相當確定她看不見在黑暗中的我。她對蘇菲說了句什麼,伸手把她往門的方向推。在那一刻,我有股逃跑的衝動,想隨著下班的人潮而去。他們踏進從畫廊流洩而出的燈光裡,只有短短片刻,朝那群衣冠楚楚的高雅人士匆匆一瞥,就急忙繼續踏上歸途,沒入人群之中。
我將近二十年沒見到安蒂了,卻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她。她想必有六十歲了,但一張臉還是顯得很年輕。嗨,她說,親了我的臉頰。我還沒來得及回話,一個年輕人就走到她身旁,在她耳邊輕聲說了些什麼,拉著她的手臂,把她從我身旁帶開。他留著一撇可笑的小鬍子。我看著他帶她到一名身穿黑西裝的男子那兒去,那人的臉我曾經見過,不然就是在報上見過。蘇菲逮住了剛才跟索妮雅搭訕的男子,對他撒嬌,顯然令他很窘。索妮雅笑著聆聽,但我又有了那種感覺,覺得她在想別的事。我朝她走過去,摟住她的腰,享受另外那名男子羨慕的眼神。他問蘇菲她幾歲。「你猜呢?」她說。他裝出思索的樣子。「十二歲?」「她十歲。」索妮雅說,蘇菲說:「妳很討厭。」「妳跟妳媽媽長得很像。」那男子說。蘇菲向他道謝,行了個屈膝禮。「她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她似乎很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我先開車帶蘇菲回去,你介意嗎?」索妮雅問,「安蒂想必得一直待到結束。」我提議由我帶蘇菲回家,這樣她就能留下,但她搖搖頭,說她累壞了,說反正她和安蒂有整個週末可以在一起。
蘇菲請她的仰慕者去替她拿杯柳橙汁。他問其他人是否也想喝點什麼。「妳別再使喚別人了,好嗎?」我說。「她這是遺傳到誰?」索妮雅說。她咬住嘴唇,向地板望了一眼,然後看進我的眼睛,但我假裝沒有聽見。「我們走了,」她說,在我嘴上匆匆一吻。「你們回來的時候,不要弄出太大的聲音。」
畫廊裡漸漸空了,但過了很久,最後幾個來賓才離去。到最後,除了安蒂和我,只剩下一位老先生,她沒有向我介紹。他們兩個並肩站在一幅畫前面,小聲說話,聲音那麼輕,讓我本能地遠遠站開。我翻著目錄,一再望向他們倆。終於安蒂擁抱了那男子,在他額頭上一吻,領他走到門邊。然後她朝我走過來。「那是葛歐格,」她說:「我曾經為他瘋狂。」她笑了。「很難理解,不是嗎?那是幾百年前的事了。」她朝櫃臺走去,拿了兩杯紅酒過來,遞了一杯給我,但我搖搖頭。「我戒酒了。」她露出不相信的微笑,把酒一口喝乾,說我們可以走了。
畫廊主人把鑰匙留給安蒂。她在電燈開關上按了又按,所有的燈光終於熄滅。到了外面,她挽起我的手,問車子停得遠不遠。雪始終還微微飄著。「天氣真糟,」她說:「下回我們還是在馬賽見。」她問我喜不喜歡那些畫。「妳變得比較文明了。」我說。「但願是更內斂了。」安蒂說。「我不懂藝術,」我說:「但是相對於從前,現在我能想像把妳的一幅畫掛在家裡。」安蒂說她不確定這是否算是恭維。
我問她是否沒有邀請索妮雅的爸媽來參加預展,說我以為他們會來。安蒂沒有回答。「如果妳想去拜訪他們,我可以把車借給妳,」我說:「去史塔貝格就只有一小段路。」安蒂還是不說話。直到我們走到車子旁邊,她才說她幾乎沒有空,說她太累了,沒有精神開車到處跑,籌備這場展覽的壓力很大。我問她是否有什麼事不對勁。安蒂猶豫著,「沒有,」她說:「又或許有。他們年紀大了,變得氣量狹小。」「可是他們一向如此。」我說。安蒂搖搖頭。當然,索妮雅的父母一向都很保守,她說,但她父親從前對藝術是真感興趣,她常跟他聊起藝術。最近這幾年他卻越來越封閉,也許是因為年紀的關係。他無法再接受新的東西,變得尖酸刻薄。「他不必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同意我的看法,」她說:「但他至少應該聽聽我想說些什麼。上次見面的時候,我們為了古爾斯基 大吵一架,在那之後,我就懶得再去見他了。」
我暗忖安蒂避開索妮雅的父親是否還有其他理由。我常懷疑她跟他曾經有過一段情。有一次我問起索妮雅這件事,她很生氣,說她爸媽婚姻和諧。就跟我們一樣,我心想,沒有再說什麼。
雖然路上車輛已經不多,我們還是開了很久才離開市區。安蒂沒有說話。我朝她望過去,看見她已經閉上眼睛。我還以為她睡著了,此時她說,她有時會自問,當年她是否幫了我一個忙。「妳指的是什麼呢?在哪件事情上?」「索妮雅當時不確定。」安蒂說。我們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安蒂說,索妮雅當時不確定我們是否適合彼此。「不確定我是否配得上她?」「你有潛力,」安蒂說:「我想這是當年她所用的字眼。另外一個男生……」「魯迪格。」我說。「對,魯迪格,他很有趣,但是太過懶散。然後另外還有一個男生,」她在回想,「他後來娶了那個學音樂的女生。」「費爾迪?」我問,「有可能。」安蒂說。
我無法想像索妮雅對費爾迪曾經感興趣過。「那沒有維持多久。」安蒂說,「她跟他有過什麼嗎?」我們停在一個紅燈前面,我望向安蒂。她微微一笑,帶著歉意。「我不認為她跟他上過床,如果你問的是這個。她從來沒跟你提起過嗎?」
索妮雅一向很少提起什麼。我常覺得彷彿在我們交往之前她根本沒有別的生活,不然就是她從前的生活沒有留下痕跡,除了在她書架上那些相簿裡之外--而她從不曾把那些相簿拿下來。當我去看那些相片,我覺得它們彷彿來自一個遙遠的年代,來自另一個人生。我偶爾問起索妮雅她跟魯迪格在一起的時光,她的回答就只有三言兩語。她會說她也沒問我,在我們交往之前我都做了些什麼。「我不介意,」我說:「畢竟妳現在屬於我。」但索妮雅還是堅決保持沉默。有時我自問,她是否根本無話可說。
安蒂的微笑變得嘲諷。「你們男人總是想當征服者,」她說:「你不妨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她考量了幾種選項,最後選擇了你。」
後面那輛車按起喇叭,我猛然開動,輪胎發出刺耳的聲音。「妳在這整件事裡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呢?」我問。「你還記得你們在我那兒度過的頭一夜嗎?」安蒂說:「索妮雅早早上床睡覺了,我跟你一起看我的畫。那時候我真想引誘你,你很討人喜歡,一個俊帥的大學生。但我卻哄著你,說索妮雅愛上了你。而第二天我也好好向她勸說。」「妳為什麼這麼做?」安蒂聳聳肩膀。「你怪我嗎?」這句問話聽起來很認真。「出於好玩,」她接著說:「我替你說好話,那時還牽扯到另一個女生,我想她是個外國人。這事兒你應該自己最清楚。」「伊芙娜,」我說,嘆了一口氣,「這事說來話長。」
室內燈火通明,索妮雅站在中央,位於中心,向來如此。她微微低下頭,手臂貼近身體,嘴巴在微笑,眼睛卻瞇了起來,彷彿光線太刺眼,又彷彿她覺得痛。她顯得心不在焉,像件展示品,一如牆上那些畫作,沒有人去注意那些畫,雖然大家正是為了這些畫而齊聚一堂。
我抽著一根小雪茄,透過畫廊的大片櫥窗,看著一個相貌堂堂的男子走向索妮雅,跟她攀談。她彷彿回過神來,微微一笑,跟他碰杯。他嘴在動,她臉上流露出一種近乎天真的詫異,接著再度微笑,然而就算從我這兒望過去,我也看得出來她沒在聽那個男子說話,看得出來她在想別的事。
蘇菲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