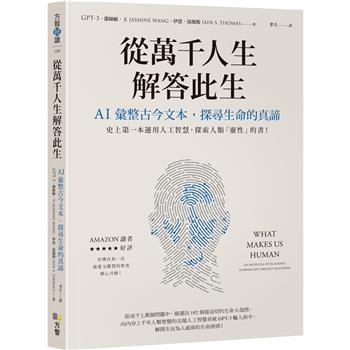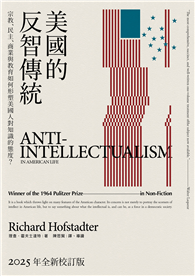推薦導讀
另一個觀看時代的角度──談《穿黃外套的下等人》/劉韋廷(文字工作者)
史蒂芬.金的這本《穿黃外套的下等人》,由五則中短篇組成,除去在角色方面互有連結外,這五篇小說同時也有著一致的主題──越戰。
關於我們對越戰的印象,其實是件相當奇妙的事。對於出生於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後的人而言,由於不曾實際生活在那個時期,因此對於當時的社會、國際氛圍縱然有所聽聞,卻也始終難以真正的感同身受。然而,要說我們對越戰全然陌生,似乎也並非如此。
一直以來,我們透過了眾多大師級導演的電影,看見他們對於越戰的詮釋及見解,其中更不乏許多今日被譽為經典的作品。例如《越戰獵鹿人》、《現代啟示錄》、《金甲部隊》等等。像是上述的這些電影,均透過戰場上的殘酷光景,讓我們看見了戰爭如何改變人性。而在《七月四日誕生》、《第一滴血》這樣的電影中,則將焦點放在越戰歸來的退伍軍人身上,藉由電影主角的遭遇,道出了這場戰爭對美國社會所帶來的諸多後遺症。
於是,越戰對我們來說,在眾多電影的推波助瀾下,似乎也並未顯得如此遙遠,甚至還影響了全球的流行文化。包括我們所熟悉的香港導演吳宇森,也在《喋血街頭》一片中,利用越戰時的越南作為主要背景,再度講了一次時間點設立於六○年代的《刺馬》故事(對於年輕一點的觀眾來說,也就是六○年代版本的《投名狀》)。
只是,一場戰爭的觀看角度,真的只能從曾經參與戰役的角色觀點來切入嗎?
對我而言,這本《穿黃外套的下等人》真正最為吸引人之處,正在於金的確提供了另一個不同角度,透過故事時間軸橫跨將近四十年的五篇小說,一口氣展現出數種關於越戰這件事的不同切入點。
全書首篇的〈穿黃外套的下等人〉,堪稱是本書金氏色彩最為濃厚的作品。本篇的故事時間點是美國正式派兵參與越戰前夕的一九六○年,故事的主角巴比,是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十一歲男孩。正如金的知名作品〈總要找到你〉(收錄於《四季奇譚》中)一樣,這篇小說生動地描繪出孩童眼中的世界,並同時反映了家庭、校園等社會問題,充滿懷舊氛圍,以及回首往事不時會有的惆悵情緒。此外,這篇小說也讓我們藉由巴比的角度,窺見金自身在成長過程中的閱讀及觀影回憶,更能透過另外一名年長角色泰德的角度,看見寫作這篇小說時的金又是如何看待那些作品。關於這點,對於金的書迷而言,自然也是本篇的另一個重點所在。
除此之外,本篇所具有的奇幻及驚悚元素,雖說與金的奇幻小說「黑塔」系列有著密切關連,但對沒看過「黑塔」系列的讀者而言,卻一點也不妨礙我們能從這篇作品裡得到的閱讀樂趣。事實上,要是我們從全書主題觀來,那些緩步進逼,帶來未知恐懼的「下等人」,其實更像是美國於五○年代抵達高峰、接著又在當時捲土重來的恐共意識,以及越戰的即將到來等等,有著明顯的相互呼應之處,亦使這篇小說無論是外在故事或內在主題,均具有濃厚的「告別純真」意味。
至於發生於一九六六年,作為全書第二篇的〈我把心遺留在亞特蘭提斯〉,則是讓金真正有了創作這整本小說念頭的中篇小說。金曾表示,這篇小說就像鑰匙一樣,打開了他三十年來一直想要描寫六○年代及越戰的創作欲望,促使他於寫完本篇後,繼續創作了本書中的其餘三篇作品,並回頭將一九九四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盲眼威利〉大幅改寫,一同收錄在這本作品之中。
相較於〈穿黃外套的下等人〉的山雨欲來,本篇故事的時間點,正是美國大幅增加前往越南參戰的美軍人數的時刻(美軍駐守越南的人數,足足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超過二十萬人)。然而,像是這樣一個絕大多數創作者都會選擇把重心放在戰場上的時間點,在金的筆下,卻出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敘事角度。
這回,我們看見的並非身陷槍林彈雨,面對道德難題的軍人主角,而是身處於大學之中,對於未來感到茫然恐懼的學生角色。
在獨特的歷史背景下,由於成績不好而被退學,並非我們如今這種大可重新考過,抑或轉身就業的情況。相反地,被退學與否這件事,成為了你是否會被派上戰場的關鍵(對於老師而言,當不當掉學生,也真真切切地成為了一個道德上的難題)。而金在本篇之中,則漂亮運用如此特殊的背景,講出一則與迷失及彌補有關的故事,甚至還讓人不禁與金自身曾深陷酒癮與毒癮的遭遇互作聯想,成功打造出極為豐厚的閱讀層面,一舉直入人心。
而在接下來篇幅短上許多的〈盲眼威利〉、〈我們為什麼會在越南〉、〈夜幕低垂〉三則短篇裡,故事的時間點則是八○與九○年代。故事的主題,也轉向了對於越戰戰場上的回憶,以及這場戰爭在參戰軍人心中所留下的巨大陰影。
對於〈我把心遺留在亞特蘭提斯〉的主角來說,他把心留在了那個曾經使他一度迷失,卻又始終眷戀不已的校園生活中。然而對實際踏上過戰場的人而言,卻是把自身的靈魂給留在了越南,就此抱著各式各樣的心中罪愆,過著或許努力麻痺自己,又或許努力贖罪的人生。
在那樣獨特的時代裡,無論你身在何處,似乎總難免得要失去什麼。而金藉由本書所辦到的,正是為我們指出了我們未必熟悉的觀看時代角度,以及或許能被時間撫平的救贖之光。
這是本抱持著溫柔之心,講述傷痛的小說。既關於時代,也不受限於時代;說的既是那個時代的人,然而,也何嘗不是我們呢?
推薦序
史蒂芬‧金,這個時代的傳奇/傅月庵(茉莉二手書店書物總監)
一切都是不停寫出來的。
自從一九七三年,塔比莎(Tabitha King)從字紙簍裡將他已經揉棄了的《魔女嘉麗》(Carrie)原稿撿了回來,同時鼓勵他繼續寫下去那一刻起,「史蒂芬.金」(Stephen King)這個名字便註定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則傳奇了。三十多年來,他的作品被翻譯成至少三十三種文字,在三十五個國家裡印行了三億本以上,同時還改編成了七十部以上的影視作品--這一列名《金氏世界紀錄》的事實,恰恰呼應了「有史以來最暢銷、最會賺錢的作家」的說法。
傳奇不僅止於此。史蒂芬.金一天一千五百字,一年三百六十二天(生日、國慶日、聖誕節三天停筆)的瘋魔式寫法,不但寫出了「社會恐怖小說」(Social Horror Fiction)這一類型閱讀;寫出了「小說還在寫,電影就說要拍」的這一「影視出版綜合體」的文化產業,甚至,在歷經整整三十年的筆耕奮鬥之後,他還寫翻了長久以來人們對於「文學」的定義。
二○○三年,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National Book Foundation)將年度「傑出貢獻獎」(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 Award)頒發給史蒂芬.金,原因是他的作品「根植於美國文學注重敘事和氣氛的偉大傳統,體現吾人內心深處種種美麗和悲慘的道德真相」。這一宣布,引發了軒然大波,卻也迫使人們不得不去面對、思考種種問題:史蒂芬.金真的可以與菲力普.羅斯(Philip Roth)、約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亞瑟.米勒(Author Miller)、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這些文學大家們同起並坐,相提並論嗎?暢銷小說是否就沒有文學價值呢?或者說,「僅僅給人以閱讀的歡樂」能不能算是一種「文學價值」?將小說劃分成「通俗」與「嚴肅」,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這一「驚世駭俗」的舉動,在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資訊時代「模糊」(Blur)的趨勢。事實上,由於電腦網路的出現,許多的「價值定義」正在崩潰重組當中,前此由上而下,由學院一錘定音的「訓話」、「指導」,正轉變成為眾聲喧嘩、雙向交流的「對話」、「引導」。這類對話並非為了追求「一個」絕對的答案而起,討論本身經常就是「一種」答案,討論不會終止,答案繼續層出不窮,文學的定義與價值,則因此而更加多元與豐饒了。
史蒂芬.金作品的出版,也就是要把「詮釋」的權力,交還到讀者手中,讓讀者以一種不具成見的、新時代的眼光,重新閱讀、討論這一則傳奇。也許你會從《四季奇譚》中看到馬克.吐溫的足跡,也許你會從《一袋白骨》發現莫里哀(Daphne duMaurier)的筆路,也許你會從這本、那本小說中看到了瑪莉.雪萊(Mary Shelley)、愛倫坡,甚至狄更斯的身影(當然,你也可能什麼都看不到,只看到了「好看」),請都不要客氣,大聲無畏地說出來!因為,如今,再沒有什麼「純」與「不純」的界線,我們有的只是「好」與「不好」而已。
一切都是不停寫出來的。我們也正在書寫一種文學的定義與價值。
編者序
《穿黃外套的下等人》編輯室報告/吳程遠 亞特蘭提斯、《蒼蠅王》和史蒂芬‧金
從前從前,有座大陸叫做亞特蘭提斯,因驕傲、自大和貪婪而沒入海中。有個水手在船觸礁之後,發現自己身在其中。他發覺在這沉沒之城中,還有許多居民,每到星期天,鐘聲響起,大家都到奢華的教堂做禮拜,為的就是希望一星期其他六天都可以把上帝拋在腦後,互相欺詐……那個從陽世來的水手,目睹了一切,頓時目瞪口呆,他知道自己要小心不被發現,要不然,永遠見不到陸地與陽光,享受愛情、生命與死亡。--彼得‧杜拉克 (《旁觀者》,麥格羅‧希爾及聯經出版,廖月娟譯)
第一次聽到史蒂芬‧金這一號人物時,我還在美國念大學二年級。物理系有個美國同學身高一九五公分,是學校橄欖球隊隊員。有一天他跟我說,他正在讀史蒂芬‧金的《The Shinning》(一般譯為《鬼店》或《幽光》),「晚上獨自待在房間裡讀,還真的覺得背後涼涼的,害怕起來呢!」他那龐大粗壯的身軀配上害怕的表情,既滑稽又詭異,讓我對這個以寫恐怖小說名滿全球的史蒂芬‧金印象深刻。
多年以後,《穿黃外套的下等人》這本書讓人見識到史蒂芬‧金溫軟輕柔的另一面。當然,《四季奇譚》是另一次的展示。在《四季奇譚》的後記中,史蒂芬‧金有點不服氣地說「……於是我被定了型,但我並不是很在意--畢竟大半時候,我寫的確實是恐怖小說,不過我寫的只是恐怖小說嗎?」
而史蒂芬‧金在寫這本《穿黃外套的下等人》時,除了說故事之外,似乎懷著更大的企圖心,要證明他寫的不「只是恐怖小說」而已,書中包含了許多的文化意涵和譬喻,比方說,用很多的電影、歌曲和書本將美國的六○年代重新編織在我們眼前。這本書的結構滿有趣的,基本上是一個長篇,可是卻分為五部,五部之間好像各自獨立,卻又互有關聯(情形有點像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吧),其中分量最重的是第一和第二部,分別約十七萬字和十萬字,加起來差不多等於全書的五分之四了。
故事的第一部,〈穿黃外套的下等人〉,主角是正值青少年叛逆期的十一歲小男孩巴比,主線是巴比和他的單親媽媽之間的親情和誤會,以及巴比和他的三個好朋友--小女友凱若、好朋友薩利以及住在樓上的房客布羅廷根先生--之間的友情。我們沒有跟史蒂芬‧金查證過,不過他的小說中許多的描述很可能和他從小由單親媽媽帶大有關。而如果你有看過《四季奇譚》或者《捕夢網》,你也會知道史蒂芬‧金很喜歡描述三、四個小孩子之間的友情,以及他們的成長故事(通常周遭出現一群壞小孩,備受欺凌,最後不得不反擊)。在這一方面,史蒂芬‧金可能受到英國作家、一九八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 1911-1993)所寫的《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的影響。在《蒼蠅王》這個故事裡,一群流落荒島的小孩,為了爭奪領導權和食物,最後互相攻擊,質樸天真的本性逐漸逝去,人類心靈中的黑暗面卻被引發出來。
事實上,透過《蒼蠅王》,史蒂芬‧金也得以抒發「長久不被主流文學重視」所累積下來的悶氣。布羅廷根送給巴比的生日禮物,正是一冊《蒼蠅王》。當時,巴比對這本書到底好不好看沒啥信心:「但是,萬一我不喜歡這本書呢?」
布羅廷根聳聳肩回答:「那就不要把它看完。書就像幫浦一樣,除非你先付出,否則它也不會給你任何東西。幫浦的價值在於打水,而你得用自己的力氣來壓幫浦的把手。你會這麼做,是因為你期待最後得到的會比原先付出的多……明白嗎?」
接著他說:「這本書有兩百頁厚,你可以先讀前面十分之一,也就是二十頁左右吧,我知道你的算術沒有閱讀來得好──如果你不喜歡這本書,如果到那時候,你的收穫還是沒有大於付出,那麼就把書放下別讀了吧!」
滿明顯的,史蒂芬‧金說的也是他寫的書,特別是讀者手上拿著的《穿黃外套的下等人》(我可以想像史蒂芬‧金會對你說:「你可以先讀前面十分之一,試試看吧!不好看免錢!」)。
隨著故事的發展,巴比、凱若等人渡過了驚心動魄的一九六○年,他們也從純真少年轉進到需要各自面對世間善惡的階段(從Innocence 到Experience)。「成年的過程是點點滴滴累積而來的,是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史蒂芬‧金這樣寫道。
《穿黃外套的下等人》這本書的英文原名是「Hearts in Atlantis」。二零零一年拍成電影時,電影的英文名稱沿用「Hearts in Atlantis」(中文叫《勿忘我》),可事實上,電影只採用了第一部的內容,然後加上一個絕大部分觀眾大概看不懂的結尾。其實「Hearts in Atlantis」是《穿黃外套的下等人》第二部的部名。這一部分的故事--〈我把心留在亞特蘭提斯〉--由緬因大學的學生彼特以第一人稱來敘述。
六年過去,青少年已經到了念大學的年齡,而在一九六六年的美國,男生設若不念大學就得去越南當兵,面對提早到來的死亡和恐懼。結果,大學校園變成了逃避現實的荒島,也變成了亞特蘭提斯。蒼蠅王的故事,以變奏曲的形式在不同的時空中再次上演著……
一年多前,當我們還在考慮是否出版《穿黃外套的下等人》的中文版時(畢竟這本書十分厚,市場反應實在難料),連續好幾個星期,我每天在上下班坐捷運時都在讀這本書的英文版。後來,捷運時間成為我最期待的快樂時光。記得讀到最後的第五部〈夜幕低垂〉時,除了替書中人物感嘆時光飛逝(故事從一九六零橫跨到一九九九年)以及人事滄桑之外,更感受到史蒂芬‧金的血與汗。要知道在這本書出版之前的大約十年,儘管史蒂芬‧金的小說仍然本本大賣,但許多讀者覺得他水準參差不齊,不若早期的《魔女嘉莉》、《鬼店》、《四季奇譚》、《戰慄遊戲》等等,網路上批評聲浪不少,有些讀者更開始掉頭而去(包括我在內)。
可是,《穿黃外套的下等人》讓人看到史蒂芬‧金在很努力、很用力地要再寫一本好書,一個好故事。似乎,他也在掙脫他的亞特蘭提斯。
布羅廷根老先生還跟巴比說了一段十分有意思的話:「很多書雖然也寫得很棒,但是故事卻不夠好。巴比,有時候要為了好故事而讀一本書,不要像那些挑剔的勢利讀者那樣,有時候則要為了文字----為了作者的語言,而讀一本書,不要像那些保守的讀者那樣。但當你找到一本故事又棒、文字也很精采的書時,千萬要好好珍惜那本書。」
希望讀者會喜歡、甚至珍惜《穿黃外套的下等人》這本書。
吳程遠,編輯人,也曾經譯過《別鬧了,費曼先生》、《這個不科學的年代!》、《神經外科的黑色喜劇》、《創意工廠MIT》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