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抗敵自衛的戰爭。全民族犧牲之大,所受痛苦和屈辱之深,也是史無前例的。在民國史中,唐德剛教授最重視的即為他成長年代所經歷的血淚抗戰史。他想寫的抗戰史,不僅僅是政治和軍事史,而是中國軍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以血肉之軀抵抗日寇,從亡國滅種的邊緣,終於轉敗為勝、浴火重生的宏觀歷史。可惜天不假年,因病中輟,未能得償夙願。
本書收錄了唐先生生前所撰有關對日抗戰的二十篇史論,以及五篇雜文和祭文。作者不但親聞親見抗戰,閱讀過大量史料,更可貴的是,他與民國史上有影響的許多人物長期來往,還因為岳父吳開先的關係,認識不少國民政府內外的人物,獲得了不見於書簡的種種細節和感受,使他對民國史,尤其抗戰史,有非比一般的認識和體會。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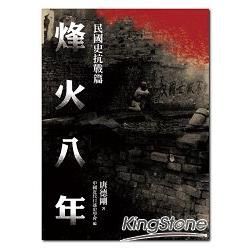 |
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 作者:唐德剛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14-07-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32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27 |
科學科普 |
二手書 |
$ 209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94 |
中國史地 |
$ 332 |
史地 |
$ 378 |
中文書 |
$ 378 |
中國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唐德剛(一九二○~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張學良口述歷史》、《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中國之惑新編》、《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
唐德剛(一九二○~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張學良口述歷史》、《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中國之惑新編》、《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
目錄
□序 譚汝謙
□編者的話 吳章銓
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的回思與警惕/003
八年抗戰的歷史意義/009
──《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序言
中國抗戰在世界史中的意義/「善敗者不亡」才是關鍵/為抗敵英烈立血淚碑/海外治中華史學的持平之論
中國抗戰決策論/019
──盧溝橋事變
「滿洲國」成立後的華北/七七盧溝橋事變前中國內政中的抗日問題/汪黃聯盟的全盛時期/雙重外交/盧溝橋事變與抗戰/蔣中正決定不阻止戰爭
南京大屠殺不是從南京開始的/053
維護抗戰史實的文藝復興/大屠殺發端於上海/從撤退到潰退/殺人競賽,不在南京/天堂變成地獄/戰略為政略所誤/真正的兵敗如山倒/強敵處心積慮,守將臨渴掘井/不留俘虜,隨地殘殺/殺盡工農百姓和婦女兒童/以最殘酷的方式殺人為娛樂/地毯式的劫財劫色/且看上海的慰安所/強姦後還要殺人滅口
華裔「慰安婦」的「口述歷史」/079
把歷史當作小說寫下來/阿寶的慘死/蘇州姑娘李香蓮的故事/從寡婦到姨太太到反革命家屬到餓死/千萬「華裔慰安婦」哪裡去了?
日本的「三光政策」/091
台兒莊大捷的歷史意義/093
──一九九三年四月八日「紀念台兒莊大捷五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兒莊現場開幕式中發言稿
【高宗武和汪精衛】
[1]從高宗武之死談到抗戰初期幾件重要史料/097
一、陶德曼「絕密史料」/二、日本「南京大屠殺」/三、高宗武「口述歷史」
[2]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109
十個「邊緣政客」的叛國陰謀/周佛海、高宗武推汪下海/「不下桌子不算輸」/「低調」才是高調/日方看我如水晶球
[3]走火入魔的日本現代文明/127
──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二
中國兩公,日本五相/為日本帝國主義定位/害人害己的愛國狂/「其言甚辯」的侵華哲學/大小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日本侵華的底線和極限/侵華是日本民族行為/半封建的日本軍部/其立國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4]使中國全土「滿洲化」的和戰經緯/153
──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三
不能「入主中原」,企圖支解上國/慘烈的「上海之戰」/「陶德曼調停」中的近衛七條/是「忽略」還是「謀略」?/日本要把中國全土「滿洲化」/日本對華外交中的小手腳/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早期的日製偽組織/偽組織終不敵正組織/閻錫山通敵而不當漢奸
[5]從通敵到出走的曲曲折折/179
──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四
日本人不敢打延安/周佛海吃定日汪兩造/董道寧是誰派到日本去的?/五人核心的通敵小組/所謂「藝文研究會」/騙蔣和誘汪/台兒莊血戰後的新形勢/張群建議汪精衛與日談和/除蔣是日本各派一致要求/日人暗設陷阱,汪氏主動投敵/為高宗武訪日定案/影佐禎昭的供詞/汪派梅思平為「正式代表」/日孔密談破裂,日汪密談開始/可怕的戰爭,可議的陳委員/周佛海「指導」通敵/近衛屈從軍部的「二次聲明」/重光堂《汪日密約》兩件/日方「出爾反爾」/汪偽買空賣空,龍雲虛與尾蛇/張發奎、龍雲不會附汪/汪周投敵的真正企圖/汪偽要求日方「徹底轟炸重慶」/沙坪壩傳奇/潛離重慶,兩頭落空/恩怨斷時論汪精衛/反侵略也是我們的民族行為
抗戰期中「高陶事件」的一家之言/247
──陶恆生著《「高陶事件」始末》讀後感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口述歷史是當代顯學/有關陶學的見聞/苦撐待變,和比戰難/自覺清醒,實是愚昧/鼎足三分,危而不亡/俄日瓜分中國,製造波蘭第二/國史謎案的一「家」之言
李士群為「通共」被殺的種種瓜葛/265
──兼答上海胡實聲先生問
歐亞兩戰場之勝負關鍵/難忘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只是個「笨蔣幹」/潘漢年是汪精衛的貴賓/期待美軍登陸,兩黨爭吃汪偽/潘李搭配的前因與後果/歸隊的本錢和貢獻/李士群之死/順便談談張愛玲
〈滬上往事細說從頭〉遲來的導論/293
──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
被捕後的生死抉擇/何以能越獄脫險?/生還後的是非
◎附錄:岳丈吳開先先生嵩壽獻辭
從美國檔案中看史迪威事件/309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五次學術討論會紀錄(紀錄:呂芳上先生)
什麼是史迪威事件?/史迪威事件的背景/史迪威其人及其來華之職權/羅斯福、馬歇爾、史迪威、陳納德間之錯縱複雜關係/史迪威撤職的經過/結論──史迪威撤職後,對中國、世界政局之影響
◎附錄:羅斯福總統致蔣主席電
挖出良心‧紀念「七七」/323
改變了歷史發展方向/日人毒辣殘忍甚於納粹/「以德報怨」一筆勾銷?/國仇不報反而同族相殘
紀念抗戰‧對日索賠/327
──「日本侵華百年:華人對日索賠國際研討會」講辭
東方的民族國家,西式的封建社會/模仿西方帝國主義,青出於藍/蠶食邊疆,強佔屬國(一八七四~一九一四)/控制中央,割裂地方(一九一五~一九三七)/上海抗戰與南京大屠殺/侵華日軍暴行之人證物證與抵賴/把全民對日索賠運動進行到底
八年抗戰史新解雜錄/345
──「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閒話偶拾
日本種族主義與殖民地/憲法與國旗/寧願他「老奸巨猾」一點/從「決不能戰」到「決不能不戰」/五十位歷史家的盛會
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359
外編:其他雜文和祭文
「蘆溝橋」還是「盧溝橋」?/363
──答黃文範先生問
紀念抗戰‧對日索賠/369
──海外華人團體推動索賠經過及目前相關組織簡介
一、索賠始自學術運動/二、「對日索賠同胞會」之成立與活動/三、「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之繼起/四、《日本侵華研究》與《對日索賠專刊》/五、香港、台灣、西歐、南美之友會
對保釣運動的微觀探索/377
──「萬船齊發,三岸同心」、「不惜一戰才能避免一戰」
回顧第一次保釣運動/為什麼要保釣?/日本堅持「主權」,中國只保「漁權」/美國違約移交琉球/美日對釣魚台的黑箱作業/還有個「台灣主權未定論」/兩岸政權「一面不抵抗,一面交涉」/余氏方案不可行/萬船齊發,三岸同心/中央嫡系部隊也不聽指揮
南京大屠殺五十年祭文/389
祭中國抗戰烈士文/397
□編者的話 吳章銓
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的回思與警惕/003
八年抗戰的歷史意義/009
──《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序言
中國抗戰在世界史中的意義/「善敗者不亡」才是關鍵/為抗敵英烈立血淚碑/海外治中華史學的持平之論
中國抗戰決策論/019
──盧溝橋事變
「滿洲國」成立後的華北/七七盧溝橋事變前中國內政中的抗日問題/汪黃聯盟的全盛時期/雙重外交/盧溝橋事變與抗戰/蔣中正決定不阻止戰爭
南京大屠殺不是從南京開始的/053
維護抗戰史實的文藝復興/大屠殺發端於上海/從撤退到潰退/殺人競賽,不在南京/天堂變成地獄/戰略為政略所誤/真正的兵敗如山倒/強敵處心積慮,守將臨渴掘井/不留俘虜,隨地殘殺/殺盡工農百姓和婦女兒童/以最殘酷的方式殺人為娛樂/地毯式的劫財劫色/且看上海的慰安所/強姦後還要殺人滅口
華裔「慰安婦」的「口述歷史」/079
把歷史當作小說寫下來/阿寶的慘死/蘇州姑娘李香蓮的故事/從寡婦到姨太太到反革命家屬到餓死/千萬「華裔慰安婦」哪裡去了?
日本的「三光政策」/091
台兒莊大捷的歷史意義/093
──一九九三年四月八日「紀念台兒莊大捷五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兒莊現場開幕式中發言稿
【高宗武和汪精衛】
[1]從高宗武之死談到抗戰初期幾件重要史料/097
一、陶德曼「絕密史料」/二、日本「南京大屠殺」/三、高宗武「口述歷史」
[2]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109
十個「邊緣政客」的叛國陰謀/周佛海、高宗武推汪下海/「不下桌子不算輸」/「低調」才是高調/日方看我如水晶球
[3]走火入魔的日本現代文明/127
──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二
中國兩公,日本五相/為日本帝國主義定位/害人害己的愛國狂/「其言甚辯」的侵華哲學/大小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日本侵華的底線和極限/侵華是日本民族行為/半封建的日本軍部/其立國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4]使中國全土「滿洲化」的和戰經緯/153
──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三
不能「入主中原」,企圖支解上國/慘烈的「上海之戰」/「陶德曼調停」中的近衛七條/是「忽略」還是「謀略」?/日本要把中國全土「滿洲化」/日本對華外交中的小手腳/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早期的日製偽組織/偽組織終不敵正組織/閻錫山通敵而不當漢奸
[5]從通敵到出走的曲曲折折/179
──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四
日本人不敢打延安/周佛海吃定日汪兩造/董道寧是誰派到日本去的?/五人核心的通敵小組/所謂「藝文研究會」/騙蔣和誘汪/台兒莊血戰後的新形勢/張群建議汪精衛與日談和/除蔣是日本各派一致要求/日人暗設陷阱,汪氏主動投敵/為高宗武訪日定案/影佐禎昭的供詞/汪派梅思平為「正式代表」/日孔密談破裂,日汪密談開始/可怕的戰爭,可議的陳委員/周佛海「指導」通敵/近衛屈從軍部的「二次聲明」/重光堂《汪日密約》兩件/日方「出爾反爾」/汪偽買空賣空,龍雲虛與尾蛇/張發奎、龍雲不會附汪/汪周投敵的真正企圖/汪偽要求日方「徹底轟炸重慶」/沙坪壩傳奇/潛離重慶,兩頭落空/恩怨斷時論汪精衛/反侵略也是我們的民族行為
抗戰期中「高陶事件」的一家之言/247
──陶恆生著《「高陶事件」始末》讀後感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口述歷史是當代顯學/有關陶學的見聞/苦撐待變,和比戰難/自覺清醒,實是愚昧/鼎足三分,危而不亡/俄日瓜分中國,製造波蘭第二/國史謎案的一「家」之言
李士群為「通共」被殺的種種瓜葛/265
──兼答上海胡實聲先生問
歐亞兩戰場之勝負關鍵/難忘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只是個「笨蔣幹」/潘漢年是汪精衛的貴賓/期待美軍登陸,兩黨爭吃汪偽/潘李搭配的前因與後果/歸隊的本錢和貢獻/李士群之死/順便談談張愛玲
〈滬上往事細說從頭〉遲來的導論/293
──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
被捕後的生死抉擇/何以能越獄脫險?/生還後的是非
◎附錄:岳丈吳開先先生嵩壽獻辭
從美國檔案中看史迪威事件/309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五次學術討論會紀錄(紀錄:呂芳上先生)
什麼是史迪威事件?/史迪威事件的背景/史迪威其人及其來華之職權/羅斯福、馬歇爾、史迪威、陳納德間之錯縱複雜關係/史迪威撤職的經過/結論──史迪威撤職後,對中國、世界政局之影響
◎附錄:羅斯福總統致蔣主席電
挖出良心‧紀念「七七」/323
改變了歷史發展方向/日人毒辣殘忍甚於納粹/「以德報怨」一筆勾銷?/國仇不報反而同族相殘
紀念抗戰‧對日索賠/327
──「日本侵華百年:華人對日索賠國際研討會」講辭
東方的民族國家,西式的封建社會/模仿西方帝國主義,青出於藍/蠶食邊疆,強佔屬國(一八七四~一九一四)/控制中央,割裂地方(一九一五~一九三七)/上海抗戰與南京大屠殺/侵華日軍暴行之人證物證與抵賴/把全民對日索賠運動進行到底
八年抗戰史新解雜錄/345
──「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閒話偶拾
日本種族主義與殖民地/憲法與國旗/寧願他「老奸巨猾」一點/從「決不能戰」到「決不能不戰」/五十位歷史家的盛會
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359
外編:其他雜文和祭文
「蘆溝橋」還是「盧溝橋」?/363
──答黃文範先生問
紀念抗戰‧對日索賠/369
──海外華人團體推動索賠經過及目前相關組織簡介
一、索賠始自學術運動/二、「對日索賠同胞會」之成立與活動/三、「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之繼起/四、《日本侵華研究》與《對日索賠專刊》/五、香港、台灣、西歐、南美之友會
對保釣運動的微觀探索/377
──「萬船齊發,三岸同心」、「不惜一戰才能避免一戰」
回顧第一次保釣運動/為什麼要保釣?/日本堅持「主權」,中國只保「漁權」/美國違約移交琉球/美日對釣魚台的黑箱作業/還有個「台灣主權未定論」/兩岸政權「一面不抵抗,一面交涉」/余氏方案不可行/萬船齊發,三岸同心/中央嫡系部隊也不聽指揮
南京大屠殺五十年祭文/389
祭中國抗戰烈士文/397
序
序
在濟濟旅美華裔歷史學者中,唐德剛先生和吳天威先生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輩。我特別佩服他倆宣導對日本侵華史的重視,並帶頭推動對日索賠運動。請容許我述說認識兩位先生的緣由。
一九八九年初夏,我還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有幸在吳先生的邀請和指導下,參與在美國伊利諾州吳先生任教的南伊州大學創辦《日本侵華研究》季刊 (一九九○年二月發刊),越洋協助吳先生約稿、組稿、為長篇論文用中英日文撰寫提要,並協助香港教育家杜學魁先生在香港和大陸發行和推廣這本季刊。一九九○年仲夏,由吳先生和杜先生任共同主席、我任祕書長,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第一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邀約近百名老中青學者共同探討近現代中日關係問題,並且檢討日本的戰爭責任,引發國際學術界研究中日關係和重視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應負的責任。此後,此一國際研討會隔年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和東京慶應大學續辦,其論文集亦先後面世,嘉惠後學。可惜一九九七年之後,這個國際研討會便停辦。
追溯起來,唐先生是我認識吳先生的介紹人。早在冷戰結束之前,唐吳兩位先生便在美國發起對日索賠,並且大力推動保釣運動。兩位先生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進出象牙塔與社會之間、坐言起行的學者,早就成為我崇敬的偶像。一九七○年秋季起,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日本史專業),一九七一年夏季經師友介紹,課餘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助理,協助一些研究生和教授研讀日文資料和史料翻譯。我又加入由哥大博士生黃養志學兄主持的「紐約國是研究社」,從事留美學生保釣運動的對日連絡、日文資料收集和編譯工作。那時唐先生雖然已經離開哥大到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我還是有機會向他請益問難。一九九○年我從香港移居美國明州,由於出任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執行副會長(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及會長(一九九八~二○○○),在組織學術和社會活動時遇到疑難,總是懇請唐先生指點迷津,唐先生總是有求必應,出手相助,不遺餘力,使我和聯合會的朋友一直感激不已。
唐先生令人欽佩的地方很多。首先,唐先生治史雖然以嚴謹著稱,誠如胡菊人先生所言,唐氏為文「暢曉易讀」,「都以幽默的筆調,亦莊亦諧來著墨,使人讀來猶如可愛的散文,一點都不感到枯燥,而覺興味盎然。」我認同胡先生的評論,唐氏確實「不同於一般寫歷史的人的習慣……這是很難得的修養。」(胡菊人〈悼唐德剛先生:可讀可賞的文章〉,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編輯委員會編《唐德剛與口述歷史──唐德剛教授逝世周年紀念文集》,頁五八。)唐先生又是筆耕甚勤的學者,他的學術成果不但以專著形式面世,也見於學術機構的叢刊(例如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更奇特的是,唐氏不少著作首見於台灣《傳記文學》月刊、香港《明報月刊》,乃至台北《中央日報》、台北《中國時報》、紐約《中報》等新聞媒體及其副刊。職是之故,久而久之,唐先生對於普及史學教育和中國近現代史知識,貢獻良多,可惜這一貢獻往往被人忽視。
不過,正是由於唐先生行事不拘一格,喜歡放下高端學者身段,通過大眾傳媒與讀者見面交流,今天要系統地閱讀唐先生著作,並非易事。可幸承吳章銓先生和禤福煇先生努力不懈,搜集唐先生關於抗戰史實的論著,悉心校訂,託請奉行「出版界的蔡元培主義」的遠流出版公司,編輯出版《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我舉手加額感恩慶幸之餘,有幸先讀本書文稿。喜見所收各篇,不論長短,都可反映唐文特殊風格, 而且可以驗證唐先生的史學特色。
讀者不難發現,唐先生重視發掘新史料,不斷從中外檔案和口述資料尋找新線索、新證據,充分讓史料說話。因此他往往能夠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本書所錄〈從美國檔案中看史迪威事件〉、「高宗武和汪精衛」系列、〈南京大屠殺不是從南京開始的〉等幾篇論文,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別是 〈使中國全土「滿洲化」的和戰經緯──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三〉一文,證實汪精衛明知日本企圖使全中國都「滿洲化」,但是為了一己之私,拒絕有所作為,加深我們對汪氏罪惡的了解。唐先生關於高宗武的論述,有效地填補了幾個中國近現代史的空白。
唐先生對人對事都善於觀察入微,洞悉個中奧祕,因此可以理順〈李士群為「通共」被殺的種種瓜葛〉,寫成情文並茂的〈「滬上往事細?從頭」遲來的導論──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考證〈「蘆溝橋」還是「盧溝橋」?〉等見微知著的「小問題」。唐先生的〈華裔「慰安婦」的「口述歷史」〉、〈日本的「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殺五十年祭文〉、〈祭中國抗戰烈士文〉等短文,頗有梁任公筆端常帶感情的遺風,讀來特別真摯感人。
唐先生更善於反思、綜合、總結,顯示其史識,呈現大家風範。例如,〈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的回思與警惕〉、〈八年抗戰的歷史意義〉、〈台兒莊大捷的歷史意義〉、〈八年抗戰史新解雜錄〉這幾篇,都是辯證的結論,揚棄浮誇大話,擲地有聲,創意洋溢,讀者不難體味。
最後,我要指出的是唐先生不但善於治史,也非常關注今天海外華人的對日索賠和保釣運動,同時為破解今天國際紛爭和促進和平友好,唐先生多方出謀獻策。本書所收的幾篇雜文,就是最好的明證:〈紀念抗戰‧對日索賠──「日本侵華百年:華人對日索賠國際研討會」講辭〉、〈紀念抗戰‧對日索賠──海外華人團體推動索賠經過及目前相關組織簡介〉、〈對保釣運動的微觀探索〉等,都是難得一見的點評。當今之世,學術界都有相同的潛規則:因為時局變化莫測,一般歷史學者都避談當前爭議,讓給政論家或新聞評論員發聲。唐先生卻從來不避嫌;他深信研究日本侵華歷史可以幫助我們透視今天的中日關係,為破解今天中日之間的難題提供有建設性的參考。唐先生能夠在學術與現實之間游刃有餘,可以比美英國牛津學者米特(Rana Mitter)教授在其近著《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Lond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所顯示的修為。我覺得唐先生的建言比米特教授來得更加直接了當,因而更加管用。例如,在〈對保釣運動的微觀探索〉一文,唐先生為解決今天中日釣魚台主權之爭,毫不猶豫開了兩劑藥方:「萬船齊發,三岸(陸、台、港)同心」及「不惜一戰才能避免一戰」。前者用民間力量去解決問題,較為溫和;後者訴諸武裝實力,顯示不惜一戰的勢態,毫不閃閃縮縮,讓對方知難而退,這樣才能真正避免一戰。我們保釣已經四十多年,進展殊慢。唐氏所開兩劑藥方,都值得我們深思、試用。
今天,中日東海釣魚台爭議未平,中越、中菲南海主權爭議又起,美國決心重返太平洋,西方鼓吹「中國威脅論」,國際危機日益加劇。《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面世,實在是適應時代的需求。我們有機會閱讀唐先生的舊文,也許憑添幾分信心和智慧,使我們能夠化解當前危機,增進睦鄰友好,維護世界和平。我們的鄰人,孰敵孰友,也應細讀唐先生的著述,體味他的建言,以史為鑒,然後和平可期。
譚汝謙敬識
二○一四年六月十二日於美國明州
【序者簡介】
譚汝謙,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英語文學系畢業;日本京都大學日本文化研修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專攻日本史學、中日關係史、東西文化交流史。現職美國明州默士達學院(Macalester College)史學教授。曾長期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師、高級講師、碩士及博士生導師;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所客座教授、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特邀顧問等。歷任美國明州雙城五所大學聯合(ACTC)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文化研究學報編委會顧問;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北京)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天津)常務理事、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三藩市)會長及榮譽會長。主要中文著作有《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中日關係全書》二卷(與關捷等合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與蔣永敬等合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實藤惠秀原著,與林啟彥合譯)。
編者的話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在唐德剛先生逝世後,整理出版他的文稿,已出了《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中國之惑新編》、《中國革命簡史》,現繼續推出這本關於抗戰史的文集。
唐德剛先生早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就有意要寫一部民國史,並且想好第一篇定名為“Trial of Parliamentary System in China”。一九六四年,唐先生向他在中央大學讀書時的老師郭廷以先生請教。郭師對民國史同樣最感興趣,非常熟悉民國的史實掌故,中外朋友們都期待他寫一部民國史。當時郭師正在中央研究院籌辦近代史研究所,曾回信詢問唐先生的撰寫計畫(郭日記十月四日)。
一九七九年,唐先生覺得他所設想的民國史計畫太大,不是一個人可以獨立完成,擬邀請幾位名家共同撰寫,並初步擬定了兩個大綱,大同小異,除按照時間先後分期(通史)外,還按照內容(專史)和人物(紀傳),共三個系統,涵蓋一九一二到一九七六年大時代的方方面面。其中政治和軍事部分由他自己執筆。
由於教書和教育行政的事務繁忙,唐先生始終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推動他的大計畫。到了一九八四年,有一天,他沉痛地跟唐師母說:「天如不喪斯文,兩千萬抗日烈士在天有靈,千餘萬中共大躍進所造成的餓鬼地下有知,則余畢生計畫之民國史(一九一二~一九七六),必會完成!」(唐日記)在其後二十幾年,他這心願一推再推,可惜天不假年,終於齎志以歿。
一九八七年,唐先生曾經寫了《民國通史》的序文四千字,但這篇序似乎遺失了。
到一九八九年,唐先生即將退休前,訂出一個以十年工夫寫一部共二十冊的《民國全史》的計畫,大綱和十年前擬定的框架類同。他在《傳記文學》上宣布(一九九○年六月),計畫每兩個月寫一章。但他不能婉拒各方的邀稿或會議稿,不能摒除一切雜務,按照完整的總體規畫順序,專心一志地、按部就班地寫下去。到二○○一年十二月發病前,只寫到北方段祺瑞皖系政權的一小部分。
在民國史中,唐先生最重視的是他成長年代所經歷的血淚抗戰史。一九七八年他與吳天威、楊覺勇兩位教授合組「三人小組」,於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參加在康州大學舉行的亞洲歷史學會英倫分會年會,分別提出「西安事變」、「七七事變」、「中日關係」論文。三位教授談起日本以各種殘酷手段屠殺同胞的歷史,相約共同致力於日寇在華暴行的研究和寫作。唐先生想寫的抗戰史,不僅僅是政治和軍事史,而是全民血肉抗戰、在慘痛犧牲和恥辱中浴火重生的宏觀歷史。
在一九九○年代紀念抗戰和向日本索賠運動最活躍的那些年,唐先生念茲在茲地就是要寫一部抗戰史,還想寫一本《抗戰八年回憶錄》,以個人的回憶為綱,寫下他在抗戰歲月中的見聞。
不幸,二○○一年以後,由於生病,唐先生自己不可能寫任何巨著了,他的老朋友們這時候都已在八十高齡上下,於是唐先生將目光轉向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下一代。他曾經幾次邀集口述史學會的朋友,力勸大家合作,共同編寫民國史。可惜年輕人各自有工作,沒有唐先生那樣的熟悉民國史實,沒有經歷過抗戰歲月,同時缺乏研究環境,沒有方便的圖書檔案可資利用,都是力不從心,雖然唐先生再三催促,大家卻一直行動不起來。
唐先生不但親身經歷抗戰,目睹全民族的慘痛奮鬥,閱讀過大量史料,更可貴的是,他與民國史上有影響的許多人物如胡適、李宗仁、陳立夫和宋子文、張學良等各有十幾年的個人來往,還因為岳父吳開先的關係,認識不少國民政府內外的人物。唐先生從他們身上體認到的民族精神,和他在交往中所獲得的不見於書簡的種種細節和感受,使他對民國史,尤其抗戰史,有非比一般的認識和體會。加之唐先生自幼喜讀古今巨著,學貫中西,足跡遍及東西兩半球,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雄心壯志。那些非文字的史料,對照著大量的文字史料,在他心中融會成為對宏觀歷史的卓越史識。唐先生想寫民國史、抗戰史的那種欲望,那種感情和責任感,我們都深深感覺得到。他最後沒能寫出那部巨作,令人惋惜。
唐先生生前所完成的民國史篇章,有關抗戰部分,只有在高宗武去世後,唐先生感於他與高氏的多年友誼,談話多次,對高氏當初參與的錯綜複雜對日交涉的內幕和高氏心情,頗有獨特了解,因此連續寫了幾篇關於高宗武與日本交涉的一小段歷史事件。除此之外,那驚天動地十四年(一九三一~一九四五)抗戰的各方面可歌可泣血淚史都沒有來得及寫。
本書的最前兩篇是唐先生紀念抗戰的短文,簡明地提出了中國抗戰的歷史性意義,可視為開宗明義。中國的抗戰是「二次大戰中唯一的黑白分明,義正辭嚴的『反侵略、反殖民主義』的戰爭」。日本自「九一八」開始攻略東三省,是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早的戰役;日本的投降,是二戰最後的結束。中華民族自主奮鬥獲得勝利,掀起了戰後亞非拉殖民地風起雲湧的獨立運動。中國的抗戰不是新老帝國主義之間爭霸混戰的一部分。(編者按:新帝國主義指左派的蘇聯和右派的德義日,他們各有一套自認為優越的一黨[皇]專政新理論;舊帝國主義指英法美。在西方是蘇聯結合舊帝國集團,打敗德國;在太平洋是日美相鬥。)
早在一九六○年代,唐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現代中國研討會」中提出過兩篇英文的關於抗戰的學術性論文,其中“China’s Decision for War: A Study of the Chinese Wartime Foreign Policy, part 1”(University Seminar on Modern East Asia: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1963),現在根據一九八七年唐先生自譯的大意殘稿(作為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紐約市立大學舉辦的「紀念七七事變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背景史述」),全文翻譯出來。原文有註釋百餘個。因本書大多數讀者對一般性的史實都已經知道,不必注解,所以在譯稿中刪減了大半,只保留有破疑、存真、解釋、發揮的部分。讀者如果要尋源,不難查閱英文原文。另一篇“Japan’s Seduction for Peace with China During Wartime: The First Phrase–the story of Gao Zongwu–”(見《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年)是關於日本誘騙汪精衛的部分經過,大體就是後來寫的中文「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內容,本書就不必重譯了。
從關於「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幾篇文章,可以看出唐先生如果有機會從容寫一部抗戰史,將是多麼精采。
唐先生所寫的其他關於抗戰的文章,都是散篇,不能構成單元,只能窺見唐先生豐富學識的一鱗半爪。因為稀有,也彌足珍貴。有的雖已編入唐先生的其他集子,為便利本書的讀者不必他求,也予列入。如〈「滬上往事細說從頭」遲來的導論〉曾經編入《書緣與人緣》。吳開先先生在敵後的驚險經歷,是抗戰謀略戰史的一部分。日本很早就一再想以誘和方式,結束那場它打不贏的侵略戰爭,中國政府虛與委蛇。蔣中正日記開放後,其中記載他曾經召見吳一次,吃飯,沒有談任何事情。顯然蔣就是對吳表示知道了。
關於史迪威的一篇,是唐先生在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五次學術討論會上的演講記錄。他的演講稿不存;這是「唐言」。
唐先生不是象牙塔裡的學者。他關心平民百姓的苦難與幸福,特別對日本在戰時加諸中國人民的凌辱、殘殺、迫害,認為應當在道德上、歷史上和法律上加以審判。
前面提到的吳、唐、楊三位教授,在研究抗戰史的同時,發起了美國各地紀念抗戰的宏偉運動。二十多年間,唐先生積極參加人道主義團體掀起的運動,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賠償。他親自參加許多集會、演講、遊行,並寫文章,為伸張人類正義而採取實際行動。我們把他主要的幾篇紀念抗戰文章納入本集,以期比較完整地顯示唐先生有歷史正義感、有濃厚同胞愛的史家人格。
唐先生發起或積極參與推動的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日本侵華研究學會、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對日索賠同胞會、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等等,建立後雖經不少人奔走呼號,頗有若干成績,但由於大環境的關係,都遠遠沒有接近唐先生的目標。這和他未能寫出抗戰史著作一樣,令人扼腕歎息。口述史學會出版本書,表示對他的尊敬與懷念。
吳章銓
二○一三年十月
在濟濟旅美華裔歷史學者中,唐德剛先生和吳天威先生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輩。我特別佩服他倆宣導對日本侵華史的重視,並帶頭推動對日索賠運動。請容許我述說認識兩位先生的緣由。
一九八九年初夏,我還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有幸在吳先生的邀請和指導下,參與在美國伊利諾州吳先生任教的南伊州大學創辦《日本侵華研究》季刊 (一九九○年二月發刊),越洋協助吳先生約稿、組稿、為長篇論文用中英日文撰寫提要,並協助香港教育家杜學魁先生在香港和大陸發行和推廣這本季刊。一九九○年仲夏,由吳先生和杜先生任共同主席、我任祕書長,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第一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邀約近百名老中青學者共同探討近現代中日關係問題,並且檢討日本的戰爭責任,引發國際學術界研究中日關係和重視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應負的責任。此後,此一國際研討會隔年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和東京慶應大學續辦,其論文集亦先後面世,嘉惠後學。可惜一九九七年之後,這個國際研討會便停辦。
追溯起來,唐先生是我認識吳先生的介紹人。早在冷戰結束之前,唐吳兩位先生便在美國發起對日索賠,並且大力推動保釣運動。兩位先生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進出象牙塔與社會之間、坐言起行的學者,早就成為我崇敬的偶像。一九七○年秋季起,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日本史專業),一九七一年夏季經師友介紹,課餘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助理,協助一些研究生和教授研讀日文資料和史料翻譯。我又加入由哥大博士生黃養志學兄主持的「紐約國是研究社」,從事留美學生保釣運動的對日連絡、日文資料收集和編譯工作。那時唐先生雖然已經離開哥大到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我還是有機會向他請益問難。一九九○年我從香港移居美國明州,由於出任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執行副會長(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及會長(一九九八~二○○○),在組織學術和社會活動時遇到疑難,總是懇請唐先生指點迷津,唐先生總是有求必應,出手相助,不遺餘力,使我和聯合會的朋友一直感激不已。
唐先生令人欽佩的地方很多。首先,唐先生治史雖然以嚴謹著稱,誠如胡菊人先生所言,唐氏為文「暢曉易讀」,「都以幽默的筆調,亦莊亦諧來著墨,使人讀來猶如可愛的散文,一點都不感到枯燥,而覺興味盎然。」我認同胡先生的評論,唐氏確實「不同於一般寫歷史的人的習慣……這是很難得的修養。」(胡菊人〈悼唐德剛先生:可讀可賞的文章〉,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編輯委員會編《唐德剛與口述歷史──唐德剛教授逝世周年紀念文集》,頁五八。)唐先生又是筆耕甚勤的學者,他的學術成果不但以專著形式面世,也見於學術機構的叢刊(例如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更奇特的是,唐氏不少著作首見於台灣《傳記文學》月刊、香港《明報月刊》,乃至台北《中央日報》、台北《中國時報》、紐約《中報》等新聞媒體及其副刊。職是之故,久而久之,唐先生對於普及史學教育和中國近現代史知識,貢獻良多,可惜這一貢獻往往被人忽視。
不過,正是由於唐先生行事不拘一格,喜歡放下高端學者身段,通過大眾傳媒與讀者見面交流,今天要系統地閱讀唐先生著作,並非易事。可幸承吳章銓先生和禤福煇先生努力不懈,搜集唐先生關於抗戰史實的論著,悉心校訂,託請奉行「出版界的蔡元培主義」的遠流出版公司,編輯出版《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我舉手加額感恩慶幸之餘,有幸先讀本書文稿。喜見所收各篇,不論長短,都可反映唐文特殊風格, 而且可以驗證唐先生的史學特色。
讀者不難發現,唐先生重視發掘新史料,不斷從中外檔案和口述資料尋找新線索、新證據,充分讓史料說話。因此他往往能夠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本書所錄〈從美國檔案中看史迪威事件〉、「高宗武和汪精衛」系列、〈南京大屠殺不是從南京開始的〉等幾篇論文,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別是 〈使中國全土「滿洲化」的和戰經緯──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之三〉一文,證實汪精衛明知日本企圖使全中國都「滿洲化」,但是為了一己之私,拒絕有所作為,加深我們對汪氏罪惡的了解。唐先生關於高宗武的論述,有效地填補了幾個中國近現代史的空白。
唐先生對人對事都善於觀察入微,洞悉個中奧祕,因此可以理順〈李士群為「通共」被殺的種種瓜葛〉,寫成情文並茂的〈「滬上往事細?從頭」遲來的導論──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考證〈「蘆溝橋」還是「盧溝橋」?〉等見微知著的「小問題」。唐先生的〈華裔「慰安婦」的「口述歷史」〉、〈日本的「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殺五十年祭文〉、〈祭中國抗戰烈士文〉等短文,頗有梁任公筆端常帶感情的遺風,讀來特別真摯感人。
唐先生更善於反思、綜合、總結,顯示其史識,呈現大家風範。例如,〈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的回思與警惕〉、〈八年抗戰的歷史意義〉、〈台兒莊大捷的歷史意義〉、〈八年抗戰史新解雜錄〉這幾篇,都是辯證的結論,揚棄浮誇大話,擲地有聲,創意洋溢,讀者不難體味。
最後,我要指出的是唐先生不但善於治史,也非常關注今天海外華人的對日索賠和保釣運動,同時為破解今天國際紛爭和促進和平友好,唐先生多方出謀獻策。本書所收的幾篇雜文,就是最好的明證:〈紀念抗戰‧對日索賠──「日本侵華百年:華人對日索賠國際研討會」講辭〉、〈紀念抗戰‧對日索賠──海外華人團體推動索賠經過及目前相關組織簡介〉、〈對保釣運動的微觀探索〉等,都是難得一見的點評。當今之世,學術界都有相同的潛規則:因為時局變化莫測,一般歷史學者都避談當前爭議,讓給政論家或新聞評論員發聲。唐先生卻從來不避嫌;他深信研究日本侵華歷史可以幫助我們透視今天的中日關係,為破解今天中日之間的難題提供有建設性的參考。唐先生能夠在學術與現實之間游刃有餘,可以比美英國牛津學者米特(Rana Mitter)教授在其近著《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Lond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所顯示的修為。我覺得唐先生的建言比米特教授來得更加直接了當,因而更加管用。例如,在〈對保釣運動的微觀探索〉一文,唐先生為解決今天中日釣魚台主權之爭,毫不猶豫開了兩劑藥方:「萬船齊發,三岸(陸、台、港)同心」及「不惜一戰才能避免一戰」。前者用民間力量去解決問題,較為溫和;後者訴諸武裝實力,顯示不惜一戰的勢態,毫不閃閃縮縮,讓對方知難而退,這樣才能真正避免一戰。我們保釣已經四十多年,進展殊慢。唐氏所開兩劑藥方,都值得我們深思、試用。
今天,中日東海釣魚台爭議未平,中越、中菲南海主權爭議又起,美國決心重返太平洋,西方鼓吹「中國威脅論」,國際危機日益加劇。《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面世,實在是適應時代的需求。我們有機會閱讀唐先生的舊文,也許憑添幾分信心和智慧,使我們能夠化解當前危機,增進睦鄰友好,維護世界和平。我們的鄰人,孰敵孰友,也應細讀唐先生的著述,體味他的建言,以史為鑒,然後和平可期。
譚汝謙敬識
二○一四年六月十二日於美國明州
【序者簡介】
譚汝謙,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英語文學系畢業;日本京都大學日本文化研修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專攻日本史學、中日關係史、東西文化交流史。現職美國明州默士達學院(Macalester College)史學教授。曾長期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師、高級講師、碩士及博士生導師;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所客座教授、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特邀顧問等。歷任美國明州雙城五所大學聯合(ACTC)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文化研究學報編委會顧問;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北京)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天津)常務理事、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三藩市)會長及榮譽會長。主要中文著作有《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中日關係全書》二卷(與關捷等合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與蔣永敬等合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實藤惠秀原著,與林啟彥合譯)。
編者的話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在唐德剛先生逝世後,整理出版他的文稿,已出了《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中國之惑新編》、《中國革命簡史》,現繼續推出這本關於抗戰史的文集。
唐德剛先生早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就有意要寫一部民國史,並且想好第一篇定名為“Trial of Parliamentary System in China”。一九六四年,唐先生向他在中央大學讀書時的老師郭廷以先生請教。郭師對民國史同樣最感興趣,非常熟悉民國的史實掌故,中外朋友們都期待他寫一部民國史。當時郭師正在中央研究院籌辦近代史研究所,曾回信詢問唐先生的撰寫計畫(郭日記十月四日)。
一九七九年,唐先生覺得他所設想的民國史計畫太大,不是一個人可以獨立完成,擬邀請幾位名家共同撰寫,並初步擬定了兩個大綱,大同小異,除按照時間先後分期(通史)外,還按照內容(專史)和人物(紀傳),共三個系統,涵蓋一九一二到一九七六年大時代的方方面面。其中政治和軍事部分由他自己執筆。
由於教書和教育行政的事務繁忙,唐先生始終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推動他的大計畫。到了一九八四年,有一天,他沉痛地跟唐師母說:「天如不喪斯文,兩千萬抗日烈士在天有靈,千餘萬中共大躍進所造成的餓鬼地下有知,則余畢生計畫之民國史(一九一二~一九七六),必會完成!」(唐日記)在其後二十幾年,他這心願一推再推,可惜天不假年,終於齎志以歿。
一九八七年,唐先生曾經寫了《民國通史》的序文四千字,但這篇序似乎遺失了。
到一九八九年,唐先生即將退休前,訂出一個以十年工夫寫一部共二十冊的《民國全史》的計畫,大綱和十年前擬定的框架類同。他在《傳記文學》上宣布(一九九○年六月),計畫每兩個月寫一章。但他不能婉拒各方的邀稿或會議稿,不能摒除一切雜務,按照完整的總體規畫順序,專心一志地、按部就班地寫下去。到二○○一年十二月發病前,只寫到北方段祺瑞皖系政權的一小部分。
在民國史中,唐先生最重視的是他成長年代所經歷的血淚抗戰史。一九七八年他與吳天威、楊覺勇兩位教授合組「三人小組」,於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參加在康州大學舉行的亞洲歷史學會英倫分會年會,分別提出「西安事變」、「七七事變」、「中日關係」論文。三位教授談起日本以各種殘酷手段屠殺同胞的歷史,相約共同致力於日寇在華暴行的研究和寫作。唐先生想寫的抗戰史,不僅僅是政治和軍事史,而是全民血肉抗戰、在慘痛犧牲和恥辱中浴火重生的宏觀歷史。
在一九九○年代紀念抗戰和向日本索賠運動最活躍的那些年,唐先生念茲在茲地就是要寫一部抗戰史,還想寫一本《抗戰八年回憶錄》,以個人的回憶為綱,寫下他在抗戰歲月中的見聞。
不幸,二○○一年以後,由於生病,唐先生自己不可能寫任何巨著了,他的老朋友們這時候都已在八十高齡上下,於是唐先生將目光轉向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下一代。他曾經幾次邀集口述史學會的朋友,力勸大家合作,共同編寫民國史。可惜年輕人各自有工作,沒有唐先生那樣的熟悉民國史實,沒有經歷過抗戰歲月,同時缺乏研究環境,沒有方便的圖書檔案可資利用,都是力不從心,雖然唐先生再三催促,大家卻一直行動不起來。
唐先生不但親身經歷抗戰,目睹全民族的慘痛奮鬥,閱讀過大量史料,更可貴的是,他與民國史上有影響的許多人物如胡適、李宗仁、陳立夫和宋子文、張學良等各有十幾年的個人來往,還因為岳父吳開先的關係,認識不少國民政府內外的人物。唐先生從他們身上體認到的民族精神,和他在交往中所獲得的不見於書簡的種種細節和感受,使他對民國史,尤其抗戰史,有非比一般的認識和體會。加之唐先生自幼喜讀古今巨著,學貫中西,足跡遍及東西兩半球,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雄心壯志。那些非文字的史料,對照著大量的文字史料,在他心中融會成為對宏觀歷史的卓越史識。唐先生想寫民國史、抗戰史的那種欲望,那種感情和責任感,我們都深深感覺得到。他最後沒能寫出那部巨作,令人惋惜。
唐先生生前所完成的民國史篇章,有關抗戰部分,只有在高宗武去世後,唐先生感於他與高氏的多年友誼,談話多次,對高氏當初參與的錯綜複雜對日交涉的內幕和高氏心情,頗有獨特了解,因此連續寫了幾篇關於高宗武與日本交涉的一小段歷史事件。除此之外,那驚天動地十四年(一九三一~一九四五)抗戰的各方面可歌可泣血淚史都沒有來得及寫。
本書的最前兩篇是唐先生紀念抗戰的短文,簡明地提出了中國抗戰的歷史性意義,可視為開宗明義。中國的抗戰是「二次大戰中唯一的黑白分明,義正辭嚴的『反侵略、反殖民主義』的戰爭」。日本自「九一八」開始攻略東三省,是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早的戰役;日本的投降,是二戰最後的結束。中華民族自主奮鬥獲得勝利,掀起了戰後亞非拉殖民地風起雲湧的獨立運動。中國的抗戰不是新老帝國主義之間爭霸混戰的一部分。(編者按:新帝國主義指左派的蘇聯和右派的德義日,他們各有一套自認為優越的一黨[皇]專政新理論;舊帝國主義指英法美。在西方是蘇聯結合舊帝國集團,打敗德國;在太平洋是日美相鬥。)
早在一九六○年代,唐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現代中國研討會」中提出過兩篇英文的關於抗戰的學術性論文,其中“China’s Decision for War: A Study of the Chinese Wartime Foreign Policy, part 1”(University Seminar on Modern East Asia: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1963),現在根據一九八七年唐先生自譯的大意殘稿(作為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紐約市立大學舉辦的「紀念七七事變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背景史述」),全文翻譯出來。原文有註釋百餘個。因本書大多數讀者對一般性的史實都已經知道,不必注解,所以在譯稿中刪減了大半,只保留有破疑、存真、解釋、發揮的部分。讀者如果要尋源,不難查閱英文原文。另一篇“Japan’s Seduction for Peace with China During Wartime: The First Phrase–the story of Gao Zongwu–”(見《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年)是關於日本誘騙汪精衛的部分經過,大體就是後來寫的中文「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內容,本書就不必重譯了。
從關於「高宗武探路、汪精衛投敵始末」幾篇文章,可以看出唐先生如果有機會從容寫一部抗戰史,將是多麼精采。
唐先生所寫的其他關於抗戰的文章,都是散篇,不能構成單元,只能窺見唐先生豐富學識的一鱗半爪。因為稀有,也彌足珍貴。有的雖已編入唐先生的其他集子,為便利本書的讀者不必他求,也予列入。如〈「滬上往事細說從頭」遲來的導論〉曾經編入《書緣與人緣》。吳開先先生在敵後的驚險經歷,是抗戰謀略戰史的一部分。日本很早就一再想以誘和方式,結束那場它打不贏的侵略戰爭,中國政府虛與委蛇。蔣中正日記開放後,其中記載他曾經召見吳一次,吃飯,沒有談任何事情。顯然蔣就是對吳表示知道了。
關於史迪威的一篇,是唐先生在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五次學術討論會上的演講記錄。他的演講稿不存;這是「唐言」。
唐先生不是象牙塔裡的學者。他關心平民百姓的苦難與幸福,特別對日本在戰時加諸中國人民的凌辱、殘殺、迫害,認為應當在道德上、歷史上和法律上加以審判。
前面提到的吳、唐、楊三位教授,在研究抗戰史的同時,發起了美國各地紀念抗戰的宏偉運動。二十多年間,唐先生積極參加人道主義團體掀起的運動,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賠償。他親自參加許多集會、演講、遊行,並寫文章,為伸張人類正義而採取實際行動。我們把他主要的幾篇紀念抗戰文章納入本集,以期比較完整地顯示唐先生有歷史正義感、有濃厚同胞愛的史家人格。
唐先生發起或積極參與推動的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日本侵華研究學會、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對日索賠同胞會、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等等,建立後雖經不少人奔走呼號,頗有若干成績,但由於大環境的關係,都遠遠沒有接近唐先生的目標。這和他未能寫出抗戰史著作一樣,令人扼腕歎息。口述史學會出版本書,表示對他的尊敬與懷念。
吳章銓
二○一三年十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