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競爭/上海
通敵合作絕不是單純的關係,前面幾章已經顯示。從遠處看,通敵合作像是直截了當的協議,順從的地方行政官員同意與武裝的占領當局合作。仔細觀察,它透露出一個非常堅韌的共謀網,牽涉到許多不同方向的各路人馬。錯綜複雜的這些路線交織出共謀的反面,即敵對競爭。有這麼多扈從擠在軍事當局籌劃占領機關時狹隘的走廊,這些扈從勢必互相爭寵。若是沒有敵對競爭,反倒代表菁英不肯與占領者發生關係;這將是占領者幾乎完全失敗、不能招徠他們進行國家建造、建立政權正當性的證明。但是中國完全不乏敵對競爭。占領政治使得敵對競爭存在;它也預料到會有敵對競爭。
由於占領突如其來,擾亂了政壇及涉及政治活動的人員,它招致各式各樣的投機者冒出來,從急欲維持特權的既有掌權者、到現在企求更高地位的非菁英,不一而足。那些我們或許會認為漢奸的人、以及當時被視為通敵漢奸的人,不是唯一進入占領政治的一批人。急欲保護本身利益、或打算藉常態停擺而占便宜的非漢奸,也爭先恐後搶進占領所製造的政治園地,與原先已經掌握權力的人士競爭。他們或許甚至尋求擠掉已在位置上的漢奸,爆料他們是投機派、自己才是正直的公民,為百姓福祉服務。日本人占領下的上海是探討這些敵對競爭的理想場域,一部分是因為上海幅員廣大、情勢複雜,一部分也因為它文件檔案豐富,留下最基層地方機關各派人馬較勁的紀錄。這些敵對競爭不僅使得合作的過程更加複雜,它也傷害到產生穩定的占領體制的可能性。
日本人處理上海宣撫工作的方法,與在長江三角洲其他地方不同。我們已經看到,宣撫部派一小組滿鐵職員分赴各縣,盡力重建行政管理。上海則不同。在這個政治、社會都更複雜的都會中心建立合作政府,不歸滿鐵人員執行。它直接接受軍方特務部指導。低階的滿鐵人員被認為已足以處理縣級事務,但是上海宣撫工作要交給在中國促進日本政治、軍事利益有更長久紀錄的特務部人員。如此重要的任務,不能輕易交付給匆匆召募的業餘人員負責。
雖然日本占領下的上海比其他占領地區受到更多的研究,但它仍是個難以理解的題目。困難,有部分原因是它市區遼闊:上海面積太大、情勢太複雜、人口太密集,又分成好幾塊華人區和洋租界,非常不容易綜合歸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這個貿易城市的核心,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都沒受到日本控制。日本在公共租界中有一小塊日租界,位於蘇州河北邊,由它自行管理,日本特務部即設在這裡。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時,租界以外的上海各地全被日本控制。法租界南邊是明朝即已建城的舊上海,稱為南市,它是本地人的商業中心。公共租界的西邊是越界築路(Extra Settlement Roads Area),中國官員稱之為滬西,西方人則稱之為「惡劣地區」(Badlands)。北邊是新劃定的江灣區(英文為 Central District)。另外,公共租界北邊還有閘北區和真如區;洋人租界之東,隔著黃浦江是浦東區。即使它們都歸同一個政府管轄,甲區所發生的事,乙區未必照單全收。即使住在當地的居民也沒把這個分治的城市當做單一一塊地區,「上海」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
就我所知,特務部或滿鐵都沒有留下日本治理上海的報告。接近建立上海市政府過程的日本特務人員或觀察家,也沒有人留下回憶錄。這表示上海本地通敵合作的故事,幾乎必須完全借助中方保留得並不均衡的文件予以重建。(註1) 中方的文件視角沒有告訴我們太多有關占領者的資訊,但是對於漢奸的狀況倒是頗多鋪陳。通敵合作者小心穿梭於來自上面及底下的種種不同主張之間,與日本人及許多競爭者周旋,前者仍是一切爭端最終裁決者,後者則隨時隨地會出現,要從占領的亂局中伺機圖謀私利。讓情況變得更複雜的是大家都玩推拖手法。宣撫工作在其他縣份還可大致保持一致,在上海就不行。呈現出來的就是各路人馬各顯神通,治理上海占領區成為人人頭痛的問題--中國人、日本人都力有未逮。
上海的宣撫史始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所謂「大道政府」這個令人難以想像的實體宣誓就職。儀式於南市舉行。當著一小群形形色色人等,這個新實體的首腦蘇錫文行禮如儀,朗誦宣言。一群人旋即坐上渡輪過黃浦江,從設在浦東的臨時總部負起治理上海的任務。新政權當天第一項動作就是分發一套文件,向上海廣大群眾宣示政權的正當性和權威:正式宣告蘇錫文接任市長、公布臨時組織大綱、通電其他政府機關宣告政府更迭,並向實力強勁的銀行公會和市商會做類似的通告。大道政府亦貼出告示,通知前市府員工可在七天之內決定是否打算回到工作崗位上。宣言、電報和歸隊通知送到上海所有報紙,並附一封信要求報館立刻發表。那些反應遲緩的人又收到第二封信,重申這道命令。(註2)
在這些文件中,大道政府的身份只是市政府,背後還有個幽靈國家,由它代表發言。宣言揭明,國民政府製造「人間地獄」,「無法選賢與能」,戕害真正民主的活力。它的「一黨專制」也製造負面氣氛,「國際上無法信任、親善」--這是唯一一處間接提到日本。大道政府將診治國民政府加諸中國之弊病,以華治華。宣言將和平這個目標--日本在東亞稱霸的潛台詞--和傳統的大同世界概念的訴求結合在一起,透過大道的形象表達出來。它說:「唯有人與國彼此互動時履行大道,才能達成真正的和平。否則,無論法律如何限制,如果它們不遵循大道,肯定談不上真正的和平。」「大道」一詞出自《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英文本係由理雅各(James Legge)所翻譯(註3)上海新政府希望恢復大道的傳統理想,超越家族本位、促進公共服務和公共福祉的意識型態。大道政府選擇陰陽太極為標誌,以它和其他標誌自我標榜為道地的中國政府,致力恢復傳統價值,拯救華東中國人不再受近年習染的外國風氣汙染。
日本在創造這個地方政府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在這些文件中只有模糊的影子。發給各政府機關的電報承認日本扮演了角色發起改組,它說:「幸好日本皇軍來到華中,替我們剷除奸邪頑癖。」大道政府十二月五日發出去的文件就完全不提日本在促成政府成立做了什麼。隻字不提宣撫班,也不提日本顧問。日本方面對大道政府的紀錄同樣滴水不漏。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日方一份內部報告有一段簡短評論提到,大道政府「在皇軍協助」下成立。次月東京發行一本有關大道政府的宣傳小冊,提到西村展藏是大道政府首席顧問,但是堅稱「這個政府裡只有兩個日本人」。鑒於內部報告顯示不下於三十四個宣撫人員擔任這個政府全職顧問,我們很難分辨這個說法究竟有何依據。很顯然雙方的共識是大道政府必須維持完全獨立不受日本控制的表象。就職典禮演出的政治自主、具有全民正當性的啞劇,其實是進入民國之後每個政治演員必須表演的一幕戲,免得沾上軍閥罵名。對於合作者而言,想要表現得具有正當性的壓力更大,尤其是背後替它撐腰的是日本人,這是再明白也不過的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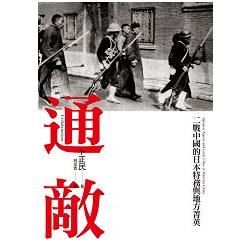 |
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出版日期:2015-08-0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0 |
Others |
二手書 |
$ 200 |
Others |
二手書 |
$ 255 |
二手中文書 |
$ 277 |
史地 |
$ 315 |
中文書 |
$ 315 |
政治 |
$ 408 |
科學科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
卜正民在《維梅爾的帽子》中,展現了藝術修養以及對史料的嫻熟,剪裁出一幅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迷人圖像;在《通敵》中,則是處理卜正民另一個專精領域──二十世紀日本侵華史。
兩岸政權為了「抗戰是誰打的」,爭奪話語權、詮釋權不休;政治立場不同者,動輒饗以「民族大義」、「漢奸」的大帽子,把道德/政治標準驟然拉到無可轉圜的高度,無視於抗日的神話,有許多是事後製造出來的,也不顧錯貼亂貼的漢奸的標籤不在少數。
卜正民的《通敵》並非為某些特定的「漢奸」平反,而是集中在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這五個地方的史料與數據,試圖從人性與生活的層面、實際發生的事情,讓讀者了解,「通敵合作」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為模稜、廣泛而普遍。
當外敵入侵,烽煙四起,戰火燎原。無辜生靈,危在旦夕,無一能倖免於暴力威脅。你若是地方上的頭臉人物,或是有志做出一番事業,或有心服務鄉里,值此危難,選擇挑起領導的責任。武裝抵抗,只聞其聲,游擊隊伏於鄉間,且與盜匪強梁無異。日寇的文職人員出現在你家門前,請你提供合作。那麼,你會怎麼辦?
作者簡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中國史教授,曾擔任史丹福大學歷史系教授。卜氏研究視野廣闊,成果出眾,主張從全球比較的角度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中國歷史,研究重點主要是中國歷史明史、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大日本帝國侵華戰爭史、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大日本帝國亞洲侵略史。著有《維梅爾的帽子》。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近百本,包括《台灣的未來》、《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等。
TOP
章節試閱
第六章 競爭/上海
通敵合作絕不是單純的關係,前面幾章已經顯示。從遠處看,通敵合作像是直截了當的協議,順從的地方行政官員同意與武裝的占領當局合作。仔細觀察,它透露出一個非常堅韌的共謀網,牽涉到許多不同方向的各路人馬。錯綜複雜的這些路線交織出共謀的反面,即敵對競爭。有這麼多扈從擠在軍事當局籌劃占領機關時狹隘的走廊,這些扈從勢必互相爭寵。若是沒有敵對競爭,反倒代表菁英不肯與占領者發生關係;這將是占領者幾乎完全失敗、不能招徠他們進行國家建造、建立政權正當性的證明。但是中國完全不乏敵對競爭。占領政...
通敵合作絕不是單純的關係,前面幾章已經顯示。從遠處看,通敵合作像是直截了當的協議,順從的地方行政官員同意與武裝的占領當局合作。仔細觀察,它透露出一個非常堅韌的共謀網,牽涉到許多不同方向的各路人馬。錯綜複雜的這些路線交織出共謀的反面,即敵對競爭。有這麼多扈從擠在軍事當局籌劃占領機關時狹隘的走廊,這些扈從勢必互相爭寵。若是沒有敵對競爭,反倒代表菁英不肯與占領者發生關係;這將是占領者幾乎完全失敗、不能招徠他們進行國家建造、建立政權正當性的證明。但是中國完全不乏敵對競爭。占領政...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主編的話:
前一陣,網路上流傳中國大陸拍抗戰戲,拍到走火入魔,渾然全無歷史常識,以致出現「抗戰已經7年了,還有一年同志們加油啊!」這種台詞。
我們在嘲笑之餘,有時不小心,也很容易犯同樣的毛病,成了沒比鱉高明多少的龜。如果說以「後見之明」知道抗戰還有一年就打完是錯誤的,那麼以為蘆溝橋的那聲槍響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打仗又不是賽跑。賽跑大家都聽槍響動作,拿槍的裁判也知道自己扣扳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打仗並不是如此,在蘆溝橋開槍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將會引發一場大戰,正如在塞拉耶佛刺殺奧...
前一陣,網路上流傳中國大陸拍抗戰戲,拍到走火入魔,渾然全無歷史常識,以致出現「抗戰已經7年了,還有一年同志們加油啊!」這種台詞。
我們在嘲笑之餘,有時不小心,也很容易犯同樣的毛病,成了沒比鱉高明多少的龜。如果說以「後見之明」知道抗戰還有一年就打完是錯誤的,那麼以為蘆溝橋的那聲槍響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打仗又不是賽跑。賽跑大家都聽槍響動作,拿槍的裁判也知道自己扣扳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打仗並不是如此,在蘆溝橋開槍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將會引發一場大戰,正如在塞拉耶佛刺殺奧...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章 何謂通敵合作
第二章 計劃
第三章 表象∕嘉定
第四章 成本∕鎮江
第五章 串謀∕南京
第六章 競爭∕上海
第七章 抵抗∕崇明
第八章 整合各占領區
第二章 計劃
第三章 表象∕嘉定
第四章 成本∕鎮江
第五章 串謀∕南京
第六章 競爭∕上海
第七章 抵抗∕崇明
第八章 整合各占領區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卜正民 譯者: 林添貴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8-01 ISBN/ISSN:978957327653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正25開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政治
圖書評論 - 評分:
|













二十世紀以來,華人史學界或許是受到西化風潮的影響,原本重人事的紀傳傳統受到極大的挑戰,不論海峽兩岸皆然。新文化運動以來,先有梁啟超、何炳松等文人提出「通史」的概念,鼓勵大家多寫事,「打破將相王侯的歷史觀」,而在遷台後又受年鑑、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大歷史」、「史料當家」、「事件解構」成為學者研究的顯學;對岸的中國更不用說,馬克斯史學強調的是「歷史階段」,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積極、充分條件」,人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這斯乎有些不妙,兩岸史學界對於「人」的研究似乎正逐漸淡化,這樣子作為表現人類行為的歷史學又算什麼呢?至少,在這本書的主題「通敵」上面,以上作法將會出現巨大的盲點。 相較於西方學界對於「戰後」、「敵後」這個領域的研究,亞太地區的相關研究顯然是不足的,特別是中國。或許正是前述史觀的影響,加上稍後的國共分裂,兩岸之間對於「抗戰」歷史詮釋的角力,讓這數十年來兩岸對於「抗戰」的研究許多都集中在戰場上。如果說對於「敵後」還有什麼論述,大多集中在「南京大屠殺」這個議題上,而且研究的重點也不是集中在活下來的人,而是那些不幸的戰爭冤魂。事實上「南京大屠殺」(甚至有「南京大姦殺」的說法)對於形塑中國抗戰的影響力實在太大,幾乎佔滿了一般人對於整個抗戰的認知;而至於1938年之後的故事,恐怕正如書中所擔憂的,「真相埋沒於歷史之中」。 這種擔憂也與史料不足有關。少了史料,年鑑學派最擅長的壯闊篇章將難以重現,也讓事實似乎落入只能用馬克斯史觀的那種簡單二分法來檢視,即大多數中國人民堅苦卓絕,而少部分頭殼壞去的才會去當漢奸。以研究歷史的角度來說,這種做法恐怕根本就犯了研究法的大忌,因為培根研究法代表成見的「四偶像」在此全員到齊:先是欠缺史料而自由心證的解釋,讓「洞窟偶像」一竿子打翻所有佔領區人民;再來是為了要強愛國與國共政權的正當性,這種英雄式的「種族偶像」從而否定了佔領區人民生活上遭受的精神壓力;而對於佔領區的缺乏瞭解,又只能從敵後特務工作的角度來看這段時間的歷史,形塑抗日版的「劇場偶像」;最後也因研究成果不足,於是只能利用前面的研究資訊,就形成勝利者式,人云亦云的「市場偶像」,最終讓歷史真相繼續遠離。 針對上面提到當前兩岸地區對於抗戰史研究的困境,卜正民老師的《通敵》提出了相當不錯的新研究方向。受限於中國的幅員以及資料搜集困難,書中不打算處理整個八年抗戰這麼長的時間以及場域,而是把時間地點濃縮在戰爭剛發生的1937年底,那些發生在長江下游重點城市的故事,並且藉由年鑑學派所謂的「歷史的泡沫」,也就是通敵者的紀錄來重新檢視這段歷史。 到底什麼是通敵?如同前面所討論的,只用單純的二分法、與敵人接觸與否這些簡易的根據恐怕都不是好方法,而作者採用的是西方學界目前研究納粹佔領區內的模式,即「在出現佔領當局所產生的壓力之下繼續運用權力者」,簡言之,就是「那些與敵人合作的人必須是使用權力的人,才能說是通敵」。這種分法雖然可能仍然會有些道德議題上的爭議,不過至少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在史料之中那些充滿道德批判的描述中藏著怎樣的實情。 比起1895年處理台灣接收問題的青澀,1937年的日本在處理佔領區的問題其實已經步入熟年,稍早的滿洲國雖然手法拙劣,但又提供了日本人一種更適宜宣傳的新佔領手段。於是1937年,在戰爭確定將擴大化之後即將進攻南京城的前夕,日本人開始自滿鐵、台灣等具備通譯中文人才的公司、地區找尋適合的宣撫人員。不同於滿州國建立時關東軍的角色,這時招募的宣撫人員刻意的以民間人員的身份登場,藉以形塑日本「親善仁慈」的形象,並且為「日支提攜」的口號背書。 但弔詭的是,宣撫工作雖然號稱是民間推動,但工作一開始推行,就相當(或說是不得不)依賴軍方特務機關的協助,宣撫人員才能基本掌握他們要「宣撫」地方的資訊,偏偏這時候日本軍在上海戰役之後軍紀事件頻傳,早已臭名遠播,讓許多宣撫人員到了宣撫地之後意外的落入根本「無人可宣」的窘境,居民能躲得早就躲光了,剩下的是跑不了的老弱人士。 可是即使「無人可宣」,資料還是要做。於是宣撫人員們藉由發行良民證以及成立地方自治會等方式,希望藉由讓中國人快速回歸「正常生活」的方式來達成他們的宣撫工作,但偏偏戰爭中的許多直接交戰地點也正是這些城市,即使宣撫人員有心,但是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殘破的;而且更麻煩的是居民的心態,如果說日本軍的姦淫擄掠是為了瓦解中國的作戰意志,在某些地區是有了初步成效:男人們被集中起來,被迫眼見日本軍姦淫他們的妻女,然後日本軍回頭在這些可憐女人面前槍殺這些男人。這種侮辱中國男人的做法讓日本宣撫班在這些地方要找自治會成員時根本找不到人,不是死了就是跑了。發現這點真相,讓有的日本自己的宣撫人員甚至乾脆放棄工作,另謀高就。 於是宣撫的工作更加複雜了。城市需要重建,商業需要重開,這些都需要錢糧,但這根本不是日本政府與軍方計劃中的事情。對於宣撫人員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盡其可能的尋找可以合作的中國人,而且最好是有辦法能協助解決重建與災民安置問題的人;而至於自治會成員當然是以這種人優先,即使他不是當地人也無妨。 當限制放寬後,可以看到各地的自治會如百花齊放的快速誕生,可是無可避免的,裡面的人員多不是宣撫人員的第一首選,自治會會長們的出現是一種宣撫人員與實際狀況妥協的成果,能提供錢糧的才是王道。可是就這些會長們的角度而言,當然他們也知道與日本人合作的負面影響何在,除非必要,這些會長,或者更好的說法,也就是地方的士紳菁英們根本不願意就這樣喪失自己在地方的影響力,於是雙方相互利用,倒也暫時成了一種平衡。這也讓日本人要找「漢奸」時省去了很多心力。 可是新的挑戰旋即到來。日本畢竟只是控制點狀的城市,廣大的農村、山區實在難以掌握,而這也是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繼續存在控制力的溫床。在他們的制衡下,前述的「漢奸」往往只能找到失意於國民政府的角色,而這種角色往往很難達成日本人希望的樣板作用,這也讓日本宣撫人員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很像」中國人或是有日本留學經驗的角色,如上海大道政府的負責人蘇錫文,可是這又回到前面宣撫剛開始的老問題,這些人跟宣撫人員一樣是空降而來,必須依靠日本的援助才能有所作為,偏偏這些援助資源不是在日本政府算計內的事。 外國勢力對於日本來說也是麻煩的象徵。這點在南京最明顯,外國人希望自己是個第三勢力,能中立於日本以及日本的「親善組織」之外,可是他們忘記了,光他們本身的長相,就已經是對日本「大東亞共榮」此一口號的挑戰。華人信任他們的程度遠超過日本培植的自治組織。宣撫工作至此又多了一個強力競爭對手。 受夠了的日本政府於1938年開始收網,專心致力打造一個可以跟國民政府競爭的新政府,同時開始廢止前述的自治會,並且基本上切斷那些成員的參政道路。這是一種相當冒險的嘗試,中國政府依賴地方菁英勢力協助辦事是已經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深厚傳統,日本的作為則是徹底切斷了地方菁英與上層政治勢力的關係。既然在上位的「漢奸」們無須對地方負責,自然更不可能把地方利益置於優先,例如崇明島的例子,最後的新縣政府根本就是以貪污己任。 之後類似的模式逐步往日本軍的新佔領區推進。各地基本上比照長江下游的模式—自治、找人、新政府成立,逐漸公式化。或許,如果持續下去,真的會出現一個日本滿意的中國政府,但是這種幻想隨著1941年底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而破滅,日本軍的急速擴張讓有系統的建設變成不可能,如同日本在台灣的軍事化建築一般,日本在中國的政治建設因為軍情的緊急紛紛成了「斷尾樓」,即使有再多的理想也只是一種假像罷了;如果硬是要說有啥貢獻,恐怕就是日本徹底切斷了舊地方菁英與上層政治勢力的關係,並且讓潛伏在地方的中國政府,特別是共產黨的政府掌握了不用菁英而能自成一格的權力基礎,成為稍後的國共內戰共產黨勝利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