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將軍一騎
1
傳騎(傳訊兵)快奔進入鎌倉府。
首先到達的傳騎是義經派出的,緊接著前來傳達這項事變者,是範賴的手下。
「什麼事啊?」鎌倉騷動著。
傳騎報告,法皇的法住寺御所被義仲燒毀了,數位皇族公卿被殺,法皇則被義仲囚禁。京都傳言義仲很得意,還笑著說:
「我也可以當王了。」
不論如何,闖進御所這種事,可說是古今從未有過的粗暴行為。
「廣元,海潮到了吧?」賴朝對京都的落魄文官大江廣元說道。
廣元因為家世低微,在京都很不得志,於是來到東國,在賴朝的關東政權下工作。賴朝大力借助他的政治能力,他自己也盡情發揮才能。
─海潮嗎?
賴朝之意是:是追討義仲的好時機了嗎?該不該發動軍隊,必須配合潮起潮落,在漲潮時乘勢而起,才能夠獲得人力以外的聲勢,如此一來,不管面對什麼敵人,都能一舉擊潰。這是大江廣元的論調,賴朝也很贊成。
「果然已經潮起了!」
廣原也用力點著頭。全天下正以迎接救世主般的心情,期待著鎌倉軍出兵。
「這是百年才出現一次的大滿潮。」
「說得好!」
賴朝聽到廣元愉快的祝賀之詞,高興得想拍腿叫好。他終於等到這個時機了。為了把京都的義仲逼到絕地,他不知忍耐了多久,運用了多少謀略與外交手段!
「立刻布陣!」
賴朝命令侍所別當,分別派兵增援範賴與義經,準備進攻京都。
義仲在京都忙碌著。
附帶一提,義仲在壽永二年十一月下旬逮捕法皇,武裝政變成功,一直到翌年正月二十日在瀨多湖岸兵敗而死為止,他只享受了六十多天的繁華歲月。這是多麼快樂﹑難過又繁忙的一段日子!
「我也可以成為王。」
在法住寺之戰結束後,他高興的這麼說。他說的是事實,神情也像孩童般天真無邪。他把木曾家的孩子及北陸道來的鄉下武士全都叫到身邊來,大肆喧鬧。
「你們有什麼要求,都可以告訴我。想當大納言的,就讓你當大納言;想當中納言的,你現在就是中納言。」
可是,他立刻受到軍師大夫房覺明的責備:
─公卿是由藤原氏擔任的,清和源氏不可以當公卿。
他這麼告誡義仲,義仲搔著頭說:
「是這樣嗎?」
於是他放棄亂封公卿的行為,卻要脅法皇將自己升到從四位下的官品。就鎌倉的賴朝也不過是從五位下兵衛佐這一點來看,義仲超越賴朝,在源氏家族中可就取得最高位了。
公卿雖然只能由藤原氏擔任,義仲當不了王或公卿,然而,對喜歡的人,他就不斷提拔到高位,討厭的人則不讓對方擔任任何官職。義仲表示:
「我是事實上的王。」
他白天闖入公卿家,進入女孩的房間說:
「陪我睡覺!」
然後形同強姦似的,硬當了女孩的夫婿。在這方面,義仲控制著整個京都,他要哪家的女兒陪宿,都是他的自由。他藉此來品味權力的樂趣,這個在大夫房覺明口中「無法成為公卿的清和源氏」,以這種行為展示自己的喜悅。
這天,義仲從白天就一直窩在前關白松殿基房之女的房間裡,並從部下處得知,叔父新宮十郎行家在播磨(兵庫縣)的室津大敗。
「畜牲!」
義仲穿著睡衣跑到屋外迴廊大叫。這是義仲的口頭禪,是句不僅在木曾,在京都也通用的俗語。
行家叔父在義仲要進攻法住寺御所之前,就知道了這項計畫,為了逃避,不想跟義仲一起政變,也不徵求義仲的同意就遠征西海,向平家大軍挑戰。
─叔父難道以為,人數那麼少的軍隊可以打敗平家?
義仲後來聽到這件事,嘲笑著行家低能的軍事能力。但是,新宮十郎行家本人也預料到會戰敗。行家具有複雜的明哲保身直覺,他看出義仲勢力將逐漸衰退的命運。
(不能跟他在一起。)
他這麼想。鎌倉軍就快來了,到那時候,他絕對會跟義仲一起被放在鍋中煮殺的。
而且賴朝那麼痛恨他,所以也不能向賴朝投降,賴朝不會饒了他的。賴朝跟義仲不和的導火線,就是行家。
「把行家送來我這裡。」賴朝這麼說。
義仲卻反駁道:
「有血緣關係的叔父來投靠我,身為男人,怎麼可以把他交出去呢?」
總之,行家無法像近畿的其他源氏一樣,拋棄義仲去投靠賴朝。
行家已無容身之處,在京都待不下去,只好去攻打敵人平家,結果大敗。
平家勢力龐大,幾乎可稱之為西海王國。行家只帶著一小隊兵馬去挑戰,就像對著大石頭丟雞蛋一般。
行家慘敗,一個人逃走,他雇了艘漁船,由北而南渡過大阪灣,於和泉國深日(大阪府泉南郡)的港口登陸,在原野上奔走,最後投靠河內國長野的石川源氏。
「他會死!」
義仲站在屋邊迴廊,眺望著遙遠的河內天空,這麼說道。那名像狐狸般的策士,只會在暗地裡耍謀略,可是戰鬥力之弱,簡直無人可出其右。
「去死!去死!」
他叫著,並回到原來的屏風後面。女子驚訝著。
「你在叫誰死?」
「我的叔父。」
義仲再度抱緊女子纖細的身軀。這位前關白松殿的千金,名叫小子。人如其名,她的眼鼻手腳都很小,然而,京都沒有一個人比得上她的美。她是松殿的掌上明珠,本來想讓她成為皇后,可是義仲闖了進來,使她成為一名小小的情婦。
義仲離開松殿府邸,回到自己家中。更詳細的情報在等著他。
聽說行家召集了河內及大和的士兵約七十人,揭起了叛變之旗。
─討伐義仲。
「為什麼叔父要討伐我呢?」
到了這個時候,義仲仍搞不懂其中微妙之處。他大概天生就欠缺政治感吧!
「我對他施恩不少,不是嗎?我和賴朝會演變成今天的局面,講起來不都是因為我袒護行家叔父的緣故嗎?」
「一切都是為了明哲保身。」大夫房覺明說:「人都是為自己著想的,除此之外,不會為其他人著想。」
「我被出賣了!」
「別嘆氣,你信任這種人,是你的錯。」
根據覺明的解釋,行家是為了博得賴朝的好感,才會以僅有的七十名士兵,舉起反義仲的旗幟。行家的旗幟不是要給義仲看的,而是向遙遠的鎌倉全力拋媚眼。
「那隻狐狸!我絕對不讓他活下去。」
只要新宮十郎行家繼續活著,就會不斷計算這種蠅頭小利,陰謀陷害別人。覺明對這一點也沒有異議。
「派刺客去吧!」
「什麼?」
義仲一剎那間停止呼吸。聽懂了覺明的意思後,他大聲怒罵:
「我是源家的首領,怎麼可以派出鼠輩去殺人呢?」
必須堂堂正正一決勝負才行!我可是威名遠播的武家首領,不比以往的首領差─義仲這麼認為。他不顧大家的反對,派了?口次郎兼光麾下的主力部隊前去討伐行家,京都的木曾軍隊因而越來越少。
2
這段期間,義仲並不是什麼事都沒做,他甚至沒有在任何女人房中超過一刻鐘以上。他總是匆忙從女人房間出來,來到法皇的住所,順便參見幼帝、拜會攝政,並派間諜去近國。而在自己府邸時,則大多在開軍事會議,甚至有一天連開七次會的記錄。
最後,他終於決定要跟平家結盟。
「只有這條路了!」覺明建議。
對義仲來講,在感情上,實在無法聯想到要跟宿敵平家結盟,可是,想跟鎌倉的賴朝作戰,只有這個辦法最好。把他逼到這步田地的是賴朝。由於義仲手上握有法皇,所以賴朝將義仲視為比平家更大的敵人。
「那個男人根本不顧骨肉親情。」
這一點,使天真的義仲也下定決心,必須與平家聯手,打敗共同的敵人賴朝。
他立刻派使者去西部。
這時,平家以室津為最前線的本營。他們立刻召開全族會議,可是,好議論的平知盛(清盛的四男)反對。
「即使已經到了末世,也不能因木曾這種人一句話就回去京都。」
知盛認為,平家應該回答:
「你們快脫下盔甲,放下弓箭,向我們投降!」
大家一致贊成知盛的說法,便這麼回答木曾的使者。平家的實力已經重生,強大到可以傲語示人。而且,義仲和行家在西國對平家之戰都大敗。
使者回到京都後,義仲以最嚴厲的咒罵高聲責備自己。一想到幾個月前自己還是全勝將軍,現在卻這麼落魄,真是情何以堪!
「覺明,你去!」
他派唯一的謀臣為使者,再度前去,條件讓步到令人感到屈辱的程度。
我們會歡喜迎接平家前來京都,也會將法皇獻給平家。
義仲連手上最重要的王牌「法皇」都讓給平家了。而且,為了怕對方毀約,還寫了文契。
依照慣例,文契寫在熊野誓紙上就可以了。可是,已經走到絕境的義仲,竟把約定刻在鐵片上,鑄成鐵鏡,鏡面刻著熊野權現的神像,背面用平假名寫著內容。
覺明西下,將這面鏡子獻給平家總大將宗盛,作為講和的象徵。平家終於說道:
「好吧!」
這時是壽永三年正月初。覺明鬆了口氣。
「那麼,你們什麼時候來京都?」
「早一點的話,義仲也會比較高興吧?」
「當然!你們來了之後,憑義仲的勇猛,也可以成為你們手下的一員大將。」
要是義仲聽到覺明這麼說,恐怕會生氣吧!可是,面對這麼困難的和議,也只好低聲下氣。
「那義仲算是投降嗎?」
宗盛訝異於覺明的低姿態,不禁脫口而出。覺明的小臉微微搖動。
「這一切都只能藏在心裡!」
他只這麼說。其中微妙之處在於為了尊重義仲的自尊心,所以不能公開明示。
覺明慌忙回到京都,向義仲報告和議成功。義仲非常高興。
「賴朝已經不足懼了。」他說。
可是,才過十天,就發生了意料之外的事。
事情發生在丹波(京都府下)。和議的條件中,有一條是「開放丹波給平家」。所謂開放,不是徵收租稅,而是募兵,把丹波視為木曾與平家的共同募兵地。
對平家來講,這就是和議的妙處。他們立刻從西海派募兵官進入丹波,不料卻被當地的木曾兵趕了出去,甚至有十三個人被殺。當他們的人頭被當成戰利品送回京都時,義仲卻遲鈍得出人意料之外,而負責外交的大夫房覺明,則臉色蒼白地想:
(這下子木曾窮途末路了。)
平家會以此為題發怒吧?他們會懷疑義仲的誠意,一定不會派兵來京都。
「去向平家道歉吧!」
他問義仲。可是義仲有自己的道理。
「不必!」
他認為不就是打架而已嗎?打輸的人是可恥的,打贏的人贏得名聲,勝者不必向敗者道歉,這是木曾谷憨直的道理。可是,用這種道理是無法統治天下的。
(該是逃亡的時候了。)
覺明這麼想。平家如果不來,木曾義仲的沒落是顯而易見的。覺明並非他的族人,若跟他到最後還丟了性命,可就太無趣了。
那一晚,覺明逃亡了。
「那個和尚逃了嗎?」
義仲吃早餐時點著頭問道,筷子還是繼續攪動碗中的飯。對義仲來講,這個男子並不算什麼。覺明以為自己是參謀,義仲可不覺得他有那麼重要。因為,不管有多少個會講道理的和尚,都無法在晚上偷襲或早上進攻時派上用場。
可是,義仲對平家不來這件事也閉口不言。平家大軍團如果不來,不僅無法防衛京都,連進攻追討鎌倉軍都沒辦法。
「為什麼?怎麼回事呢?」
他不斷派人去調查。平家似乎因為丹波事件而僵持不動。
「是嗎?」義仲直率的說。他本來就是個不太會執著的男子。
「平家多年待在京都,也感染到公家的性格,氣量真小。我不應該去求他們這種人。」
他爽快的決定放棄,已經毫無辦法了,他得拋棄京都,逃往北陸。
可是……好可惜!
即使他對事物不太執著,然而,要放棄如寶石般的京都,還是十分捨不得。想到法皇和天子都在自己手上,日本的朝廷就像家中的雞籠,是自己的所有物;而就私人情感來講,每晚枕邊不斷更換的情人,不全都在京都的大小路上嗎?
(怎麼能拋棄他們,回到雜草叢生的鄉下呢?)
義仲一時想不開,仍每天遊樂度日。
「乾脆把法皇帶走吧?」他一天會有好幾次這麼說。
他並沒有什麼惡意,他不像賴朝有讀書或知性冥想的習慣,所以無法將言語放在腦中,他必須把想法講出來才能思考,這實在是很不好的習慣。
義仲身邊有好幾個人跟法皇秘密保持聯繫,他們將義仲的思考過程,毫不保留的向法皇報告。
─義仲要帶我去北陸嗎?有可能!
法皇在被拘禁的五條東洞院裡大聲鼓噪著。這次的談話內容馬上就傳了出去,京都市井小民也跟法皇一樣感到驚訝。
(要怎麼安撫那個男人?)
後白河法皇拚命想著。法皇已經可以不顧死活了,義仲想必也是如此吧!
(讓義仲產生甜蜜的幻覺。)
對法皇而言,再過沒幾天,鎌倉軍就會把自己拯救出來,這段期間如走在白刃上一般,絕不可以讓義仲產生絕望感。義仲若絕望了,就會自暴自棄,到時候會帶自己去北陸吧?搞不好還會殺了自己!
「必須給那隻木曾猴子一點希望。」
法皇低聲與近臣籌畫。太大聲的話,會讓院子前的木曾兵聽到。
「這裡有三個計策……」
法皇是個能力很強的企畫家,近臣不過是將他的計畫付諸實行而已。
他馬上召來義仲。當義仲跪行到法皇御簾前時,近臣說:
「院宣。」
義仲恭敬接旨。
近臣表示,為了鞏固與平家的同盟關係,法皇已派使者會見平家,這一切都是為了義仲,把義仲視為最重要的人物。
「順便……」近臣在旁邊搧風點火,繼續說道:「還對奧州平原的藤原秀衡也下了院宣,要求奧州十七萬騎來京都援助。」
─原來如此。
義仲歪著頭。他這十幾天正需要兵力援助,現在派院使去奧州的話,最快也要三月或四月才會到達京都吧?在這段期間,義仲的命運一定早就改變了。
「還有……」院的近臣說。
任命他為征夷大將軍─最後一項院宣對義仲而言─更是無上的喜悅。
「啊!」義仲俯伏於地。
義仲曾經聽過這個制度,也期望能被任命,可是,院以從未給源氏這個頭銜為由,一直拒絕。所謂征夷大將軍,第一個接受任命的是平安初期的?上田村?,接著在天慶三年,藤原忠文也受封此頭銜。之後的兩百四十五年,就再也沒有人獲任擔當這個職位了。
這次院宣下旨,封義仲為征夷大將軍,使他成為源氏第一位征夷大將軍。後來,這職位一直被源氏霸佔,源賴朝﹑足利尊氏﹑德川家康都承繼這個職位。
「過去源氏沒有擔任這職位的前例,你開創了新例。」奏者轉達法皇的話。
「我很高興!」義仲高喊出聲。
有了這個官職,在名義上具有動員全國武士的權力,雖然在現實上,根本沒有人會接受動員而來。
義仲也知道這只是形式。若沒有實力,還是不會有人來依附自己。義仲的京都軍已剩下不到兩﹑三百名了。
可是,義仲成了征夷大將軍,這將會成為他一生的回憶,名垂後世吧?義仲已經覺悟到自己即將滅亡,因此想趁活著的時候,為自己的武士名聲造勢。
「你就改名叫旭將軍吧!」
御簾後傳出後白河法皇的聲音,向義仲宣示著。法皇是當代最熟悉今樣(庶民的流行歌謠)的權威,也是位文字學家。他取的這個名字多好!具有旭日東升的命運象徵,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名字了。
「太感激了!」義仲喉嚨深處抖動著。
任何人都看得出,義仲的命運只有沒落一途,法皇卻反而幫他想了個好名字。
義仲感激退出。
法皇從御簾後出來,命人拿來火盆,準備玩陞官圖。
「這樣行了吧!」
「是的。看他那麼高興,應該不會亂來了。」
「還流淚了呢!」
法皇也很滿足。
這是他的絕招。朝廷若要讓在時勢下造就出來的權勢人物失去骨氣,就盡量讓他們的地位越來越高。在官吏之間,暗稱這種絕招叫「位打」,義仲就是遇到了法皇的位打。
義仲退出後,在臨時御所門前召集自己的家丁子弟,告訴他們這個消息,並命令道:
「去將這消息傳遍京都。」
馬上回家太可惜了!他坐著牛車在大街小巷繞,並一家家到女人們家中通知。按照道路的順序,最後一個被通知的是松殿的女兒。
「我聽說了。」女子點頭。
雖然這個人硬當上她的丈夫,可是對她來講,這男子已是她正式的男人了,她自然會很注意他的事情。她的侍女每天都會來報告宮廷或大街小巷的流言。
一切都對義仲不利,他的沒落已經指日可待,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可別太過分了。」
侍女一天到晚這麼說。要是不小心,搞不好撤退離開京都的木曾軍會把她們帶走。
「說不定我們都會有危險。」侍女們說。
可是,在這個時期很難判斷情況,因此她每天派侍女出去打聽。
「妳已經知道了?」義仲天真的開心笑著,用粗大的聲音說:「小姐……」
「什麼事?」
「到我家來吧!」
「咦?」
松殿的千金慌了。義仲可能想帶她到北陸吧?她立刻用衵扇(編註:宮中女子使用的木摺扇)遮住自己的臉,不讓義仲看到蒼白慌張的表情。京都人的智慧就是將一切都放在心裡。
「怎麼樣?」
義仲解開女子的領口,把手伸進去。
「我真的很高興。」
「真的?」
「我沒騙你!」
女子將身體偎在義仲的膝蓋上。
「可是……」女子說:「我有外病。」
「什麼外病?」
「這……」
她向義仲表示,自己只要在外面睡覺就一定會生病,曾經有一次在伯母家得了失心症,甚至還暫停呼吸一段時間,而住在二條內親王鄉下御所時,也發生過相同的事情。
「如果沒有這種病,我是很高興去你家的。」她含淚說著。
義仲慌了。
「這可糟糕!」
他似乎覺得,自己提出如此無理的要求,實在太差勁了!他用袖子擦掉額上的汗水,當場就收回剛才的要求。
義仲回到府邸,又有新的情報在等著他。
在尾張、美濃附近屯集的鎌倉軍,開始往近江前進,人數也比以前增加許多。
而伊賀附近的義經軍隊,似乎也增加了數倍,可能已獲得鎌倉的增援吧!
「目標是哪裡?」
「我知道,」緊急來報的人說:「是京都。」
3
鎌倉軍的戰略是視京都為一個廣大的城域,以北方的入口近江瀨多為正門,以宇治為後門。進攻正門的,是從美濃往近江急行軍的賴範部隊,也就是本隊。
義經負責後門,轉往伊勢﹑伊賀,走捷徑到宇治。
進攻的總兵力不多,範賴軍不過八千名,義經也只有一千名士兵。
義經部隊走過的區域,當時幾乎都尚未開發出道路,也就是後人所謂的:
─伊賀路。
爬上伊賀頂,馬蹄踏在樵夫的林木道上,眾人來到木津川的斷崖,此地稱為笠置。
坂東武者雖然是天生的騎兵,可是他們的故鄉是日本最大的原野,所以很不會走山路。有人在岩石間滑了馬蹄,馬兒疲倦不已,很多人不得不換馬。
「御曹司,休息一下吧!」賴朝派來的軍監(參謀兼監視)梶原景時說。
可是義經不說話。
「速度」正是他的戰術要件之一,是他領先世界戰史的騎兵作戰關鍵。
「快點!」
他在馬上揚著鞭,毫不容情的催促坂東武者。
行軍速度若快的話,沿路遇到的平民百姓,就無法一個接一個將他們的位置往京都傳,自然就不會讓敵人得到情報,可以攻敵於不意。
─速度就是勝利。
這是義經的原則,對他來講甚至類似信仰,是他在奧州山野縱馬奔馳時自然學會的。
這也是義經第一次作戰。
「九郎對戰事不會很熟悉吧?」
鎌倉的賴朝理所當然這樣想,因此派老奸巨猾的梶原景時跟著他,並叮嚀著:
「你要聽他的話。」
可是,義經根本不聽這名軍監的意見,反而自己揚鞭通令全軍。
而且,他雖然身為大將,卻不留在軍隊中,竟然跑去當先鋒。
「各位,請像我這樣做!」
他如一陣風般說著。
─他連作戰方法都不知道。
景時大聲說他的壞話,不少將士也有同感。
不過,他的騎術如何呢?
「聽說他是在京都長大的,真意外。」
對義經有好感的?山重忠說。
義經駕馭馬匹,不只是操縱韁繩的熟悉度,還有一種彷彿讓馬奔馳在雲端,盡量不讓馬疲倦的妙法。他會這種技巧,是因為在馬匹產地奧州長大成人的關係吧!
他的馬是一匹命名為「大夫黑」的駿馬,而可供他換乘的馬有四匹。順便一提,賴朝的馬共有十四匹,而義經麾下那些?山﹑河越﹑兒玉﹑豬?﹑丹﹑平山﹑熊谷附近的知名人士,都從自己的牧場選了五﹑六匹馬來,所以四匹馬絕對不算多。
不久,樹梢間已經看得到平等院的屋瓦,宇治到了。
宇治川的水向前流著,這湍急流可說是保護京都盆地的天然壕溝吧!義經一秒鐘也不鬆懈地策馬立在南岸。
架在河流上的宇治大橋,已經被木曾的手下拆掉了,只剩下橋的骨架立在兩岸之間,與對岸的敵人相對。
「你看,這條河水流湍急。」擠在岸邊的坂東武士高聲說。
在坂東的概念裡,所謂河川,就是緩慢流動的水。
像宇治川這樣水流相衝、濺起白色浪花的河流,只有在很高的山上才看得到,而且還是雪融後形成的,冰冷得可以割裂皮膚。
對岸架設著木曾軍的弓箭,建有圍牆掩護體,飄揚著白旗;河中有阻擋馬匹行走的木樁或木頭,上面釘著大小釘子。看來無法直接渡河。
「岸邊的敵人是誰?」
義經問身邊的平山武者季重。平山略往遠處張望。
「那是住在常陸志田的三郎義廣。」平山說。
「叔父嗎?」
「現在卻是我們的敵人。」
(可是確實是叔父!)
義經這麼想。
志田義廣是義經亡父義朝最大的弟弟,當然是賴朝﹑義經的叔父。
賴朝在關東舉旗出兵成功時,義廣以為賴朝會給予自己應有的待遇,然而,當他前來祝賀賴朝時,賴朝的態度卻意外的冷淡。
「別開玩笑了!我雖然是你的姪子,可是,別忘了我是源家的首領。」
他受到如家臣般的待遇。
志田﹑新宮因此都與賴朝對立,成為賴朝追討的敵人,紛紛跑去投靠義仲。重骨肉親情的義仲非常歡迎他們,以對待叔父的態度禮遇之。
志田義廣此時正擔負守備宇治川的任務,白旗飄揚。這裡將是義仲殉身之處。
(人手那麼少!)
義經覺得他很可憐。他們的兵力大約只有一百五十人。
這期間,義經派幾個熟悉水性的人去查探河底的深淺。
不久,士兵間爆發一陣歡呼聲。
只見佐佐木高綱和梶原源太景季(景時的兒子),正從宇治南岸的小島崎(平等院境內)聲勢壯大地策馬下水。
「繼續!」
義經揚起鞭,自己也下到河邊平原。那裡比橋面略低,在當地稱為「橘小島」,附近水流也很急。可是,根據探查者回來報告,此處河底比較淺。
「勇敢的人啊!爬到橋上,開始射箭作戰。」
義經下達掩護射擊的命令。善於弓箭的平山季重以及麾下士兵,俐落的爬上橋墩,走到一半便開始不斷射箭。這可說是對木曾戰的第一箭。
其他人則組成馬筏過河。凡事謹慎的?山重忠一邊過河,一邊對左右士兵大聲吆喝,提醒他們要小心─
健康的馬要拉到上游,虛弱的馬則安排在下游。在馬腳踩下以前,要拉著韁繩讓馬游泳。馬腳如果踩空了,就放鬆左手的韁繩,縮短右手的韁繩,使馬保持平衡游過去。不可拉緊韁繩讓馬牽著走,犯下錯誤。若水淹到嘴巴與尾巴,就靠近鞍頭,不要讓馬撞到石頭。要配合內側馬鐙。渡河時,敵人一定會射箭攻擊,千萬別反擊,只要小心別讓箭射到護頸和頭部。朝敵人的那隻手要護住身體,不要在盔甲上露出破綻……。
他雖然這樣叫喊著,可是在現實上,穿載著著沉重盔甲的武士馬匹,是無法游過深河的。沒穿盔甲的騎馬者,才有可能讓馬游過河。結果,眾人只好盡量選擇河底可供馬腳落足的地方,小心前進,水流也因為馬筏而變得較為緩慢。最後,眾人終於士氣高昂地上岸了。
從水裡一上來,他們的氣勢立即壓倒了志田的軍隊,一擊便擊潰對方。義經還是跑在最前面。
「停!」
武者本來要快速追趕,然而,義經突然命令全軍停下來。
─怎麼回事?
對坂東武者來講,這真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不快。在這個時代,作戰就是要以氣勢進攻,沒有所謂的戰術,一切都看個人的武勇,戰事不過是靠大家殺死的人數總和來看結果罷了。可是,義經這位年輕的指揮官卻使用戰術。
「時間會浪費掉的!」
武者焦躁的讓馬刨著地。義經毫不通融地依照自己的方式,把軍隊分成四隊。
他打算從四面衝入京都市街,擾亂敵人,使敵人難以防衛,疲於奔命。
「這又怎麼樣呢?」
以梶原為首的重要小名,用分成四隊會使各隊兵力稀薄的理由反對,可是義經面無表情的堅持:
「照我說的去做!」
義經腦中似乎以為,不必信任大家的智慧,只要相信自己的直覺,要統率軍隊,只有靠將領的獨斷與強力意志。若對照他在奧州讀過的中國兵書,他的態度是正確的。
可是,從關東武士團的習慣來看,這是很怪異的。
關東武士團本來就是有血緣關係的團體,由各族族長率領部下來參戰,因為他們的聚集,才組成了一支軍隊。因此,軍團要採取統一行動時,都必須取得族長的認可。連賴朝都要這樣做,可是義經卻毫不理會。
可以說從一開始,便是由一個具有完全不同思想的異質人類,擔任這一軍的指揮官。
眾人一表現出不同意的臉色,義經就以權威壓制大家:
「我是鎌倉的御代官。」
眾人對這一點也很不滿。
─那個御曹司以為自己跟鎌倉大人同級。
梶原等人都暗地偷笑。他們是賴朝的近臣,十分清楚賴朝並沒有將義經擺在特殊的位置上,只把他當家臣看待。
可是,面對敵人,眾人卻不得不順從他。
總之,到達宇治川北岸的義經軍,分成四個方向,飛塵四起開始奔馳。第一隊走小野經勸修寺到七條。第二隊從小幡經過深草。第三隊走伏見、尾山、月見岡、法性寺去京都。第四隊走小幡、大道、醍醐,越過阿彌陀峰東麓,前往一路市街。義經直接指揮走最短路線的第四隊,擔任先鋒部隊。
義經的部下武藏房弁慶﹑佐藤繼信﹑忠信兄弟﹑伊勢三郎義盛﹑江田源三﹑熊井太郎﹑大內太郎等人,跑到義經的馬旁邊。
「不要輸喔!不要輸喔!」伊勢義盛不斷喊著。
言下之意是:我們這些以前的浪人,可不想輸給坂東的正規武士。爬著醍醐的坡道,每個人都沒有時間愛護自己的馬,只是不斷揚鞭抽打。
「就算一戰而死也無所謂。」江田源三說。
趕走京都的敵人,佔領京都!
能參與這麼輝煌的戰鬥,是多麼幸運啊!
4
義仲落敗了!
鎌倉軍的出現實在太快了。實際上,義仲想著:
─會戰可能在明天或後天吧!
因為在京都的北門﹑近江瀨多川對岸,這一、兩天才開始看到範賴軍隊的蹤影。範賴軍紀鬆弛,與眾族長雜亂的由近江路南下,似乎要前往瀨多川的預定路線上。
(沒什麼大不了的!)
義仲會這麼想,是因為範賴軍毫無管制,使身為軍人的義仲感到很安心。
而且,範賴軍的先發部隊大概是在等後面的主力,似乎不打算先渡過瀨多川。
這一天早上,是義仲命中注定的一個早晨─元曆元年(壽永三年)正月二十日。天尚未明,他增強瀨多的守備,任木曾軍的第一將領今井四郎兼平為指揮官,給他三百名士兵,並派大約相同人數的士兵給叔父志田義廣防守宇治川。
(要是?口在就好了!)
義仲後悔著。他派?口次郎兼光去河內攻打新宮行家。如果他那三百名士兵在的話,現在將會是防衛京都多強的強心劑啊!
─畜牲!畜牲!
義仲從早上就一直罵著。由於將士兵分散給部屬,因此他手邊只剩下三十名士兵。
(三十名嗎?)
連他自己都對這種狼狽狀感到驚訝。可是,義仲將現有的士兵從郊外撤回,聚集在自己身邊,並不是要他們保護自己。這是他的優點,他看重的不是勝敗,而是會戰的轟轟烈烈。
男人必須轟轟烈烈才行,義仲這麼相信著。這也是這時代男人的精神。
可是,義仲聽到宇治川的防守已經被義經一舉擊破時,他也無可奈何。
「九郎已經出現了嗎?」
報告者染滿血跡的束腹布就是證明。一問之下,才知道宇治川的守將,亦即叔父志田義廣也逃往伊勢了。
「沒志氣!」
對義仲而言,這是第二次的戰敗。
這時,與義仲從小一起長大,住在信濃國的根井小彌太,穿著卯花護胸大盔甲以及星白頭盔,靠近義仲說:
「快點覺悟,帶院(法皇)去北陸吧!」
他不斷催促義仲逃離京都。北陸有很多義仲的擁護者,帶法皇去的話,可以到處下院宣,召募士兵。
可是義仲猶豫了。
「我要死在京都。」
他認為,既然時勢已經離自己遠去,剩下的一條路,就是死得轟轟烈烈。
「我們不會一直這麼倒楣。北陸現在正在下雪,藏在下雪的山野中,各街道都被截斷,等待時機,好運很快就會輪到我們的。」
「是嗎?」
義仲也開始想逃了。
既然如此,最重要的就是逮捕法皇。
「去院!」
義仲騎上馬奔馳而去。他背後有三十名士兵,馬蹄聲大作。
院的臨時御所大門沉重的關著。
「快開門!」
他們喊叫著。可是裡面沒有回答,一片靜寂。
門內,院的近臣廚房長官(大膳大夫)藤原成忠,正躡手躡腳到處奔跑,指揮傭人。
「別開門!別開門!」
傭人也害怕得臉上失去血色,各自把門閂得緊緊的。
「我是旭將軍義仲!」
門前的義仲焦躁的騎馬繞圈子,對門內報上姓名,卻沒有人回答。
「旭將軍」是五天前門內的法皇下旨賜給他的官名。法皇應該有聽到義仲的叫聲,卻完全沒有回應,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是義仲!」
義仲掄起拳頭,重重拍打著門。門還是不開。
義仲絕望了。每次拍打著門,他內心似乎就有什麼東西脫落了,最後,他的膝蓋開始無力,盔甲突然變得很重。
(運勢已終。)
義仲停止拍打。
這時,東方的加茂河原傳來馬蹄聲。
「什麼事?」
他一回頭,看到六﹑七名騎兵雜亂的奔來。是沒見過的武者,不是木曾兵。
「難道……」
義仲十分驚訝,是擊潰宇治川防衛部隊的義經軍先鋒部隊吧?竟然只有六﹑七名士兵就敢闖進來,如此勇猛,應該不是京都或近畿附近的武者。
「射箭!」
義仲回到馬上,從背後抽出箭,邊跑邊射。可是,他立刻後退了。六﹑七騎的另一邊,有十騎﹑二十騎衝下河原而來。
「去瀨多!」
義仲採取了跟早上的方針完全不同的行動。他要去瀨多與守備隊長今井兼平會合,若要死,就跟兼平死在一起。兼平是義仲乳母的兒子,與他從小像兄弟般長大。
可是,義仲跑著跑著,卻有點膽怯。他還有個牽掛:松殿的女兒。他跑過高倉,進了萬里小路,到達三條。
「你們在這裡等我!」
義仲下了馬,進入屋裡。部下啞然失聲。其中,從義仲少年時代就跟著他的鬼頭次,甚至拉住他的盔甲下襬。
「大人,你為什麼來這裡?」
鬼頭次跑到院子裡連聲喊叫:
「大人,大人!」
可是義仲視若無睹,一直沒有出來。
他戴著護腕的手突然把女子抱緊,女子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
(他會把我帶去北陸。)
這樣的恐懼使她全身無法動彈。她手腳關節不聽使喚,在義仲的懷裡全身軟綿綿的。
可是,從義仲斷斷續續的木曾腔中,她才知道義仲不是要來帶自己走,也不會逃去北陸。
義仲對她說要死在瀨多,作為他一生的結束。他從盔甲裡拿出一個小指大小的念持佛,放在女子小小的手掌上,要她緊握著。
「這是什麼?」
「是我的靈魂。」義仲說。
事實上,那應該是比靈魂還重要的東西。身為源氏一派之長的義仲,將源氏的氏神八幡大菩薩的神像放在盔甲的八幡座,作為自己的武運守護神。他將這神像當成遺物留給她,代表著將血統的榮耀留給她之意。
「是神降罰嗎?」
好可怕!女子表示,把神像送給外族人,就等於放棄了自己的武運。
義仲沉默著,然後用非常開朗的聲音說:
「我早就放棄了!」
接著,他把手伸進女子的裙襬,碰觸她的私處。義仲的手指上套著皮革,因此女子痛得幾乎想跳起來,可是她拚命忍耐著。對她來講,若忍過去的話,這場風暴似的命運,就會像完全沒發生過一般。
(就是這個……)
義仲這麼想。他這個舉動不是為了女子,也不是因為好色,而是想確定這份實際的感受。義仲覺得這位公卿小姐的私處,正是他在木曾時對京都的憧憬象徵。
(這就是京都。)
他想著自己短暫的繁華。從北陸進入京都後,算來也不過只有一年半。
鬼頭次在院子裡叫喊著。義仲受不了他的吵鬧,便走出屋邊迴廊。
鬼頭次死了!他卸下鎧甲,露出肚子刺了三次,最後一刀刺進喉嚨而死。
(他在鼓勵我嗎?)
義仲在他的屍體旁蹲下,割下他的頭髮放入懷裡,沒有回頭看女子就出了門。
後來,他來到三條河原,要前往栗田口,卻遇到義經軍,被打得潰不成軍。他過了神樂岡,離開京都,經過四宮﹑神無之森﹑關之清水﹑關之明神,來到關寺之前,琵琶湖畔的栗津濱,在那裡的松林裡遇到今井兼平,與追擊而來的義經軍奮戰,最後兩人決定自殺。在尋找地點的時候,太陽西斜,於暮色深沉的松林間奔馳時,馬腳在深田受傷,無法行動。剎那間,他又被相模的三浦黨石田次郎為久的部下射了一箭,他用劍擋開不成,被深深的射進頭盔內,氣絕而亡。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鎌倉戰神源義經(下)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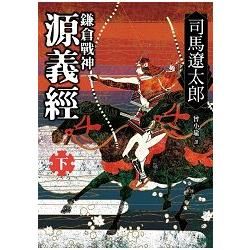 |
鎌倉戰神源義經(下) 作者:司馬遼太郎 / 譯者:曾小瑜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11-2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武俠/歷史小說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日本文學 |
$ 270 |
歷史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27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98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鎌倉戰神源義經(下)
日本近代文學史上,備受推崇也廣受歡迎的歷史大河小說巨匠司馬遼太郎,描寫平安時代與鎌倉時代交替之際,戰神源義經(一一五九─一一八九年)獨特而短暫一生的傑作。
義經是源氏首領之子,但他的名字被提及時總是伴隨著悲劇性的音調。雖然出身武家,卻被寄養於鞍馬山,之後則輾轉於關東、奧州度過黑暗的少年歲月。但矮小清秀的義經一鳴驚人,以轟轟烈烈之姿登上歷史的舞台,將木曾義仲趕出京都,接著轉戰平家,先後在一之谷、屋島、壇浦戰役中奇兵制勝……義經建立了輝煌的戰功,登上英雄的寶座,滿心只想為父報仇和贏得哥哥賴朝的垂青,就在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候,毀滅之神卻悄然到來。
縱然有軍事天才,可是義經對政治卻遲鈍到令人悲哀的地步,因此,對苦心經營鎌倉幕府的哥哥賴朝而言,弟弟義經便如毒藥一般……
作者簡介:
司馬遼太郎(1923-1996)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大阪,大阪外語學院蒙古語系畢業,本名福田定一,筆名乃「遠不及司馬遷之太郎」之意。
一九六○年以忍者小說《梟之城》獲直木賞後,幾乎年年受各大獎肯定。六一年辭去記者工作,成為專職作家,慣以冷靜、理性的史觀處理故事,鳥瞰式的寫作手法營造出恢宏氣勢。一九九六年病逝後,其「徹底考證」與「百科全書」式的敘述方法仍風靡無數讀者,堪稱日本最受歡迎的大眾文學巨匠。
中譯作品有《龍馬行》《新選組血風錄》《幕末:十二則暗殺風雲錄》《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宛如飛翔》《關原之戰》《豐臣一族》《宮本武藏》《項羽對劉邦:楚漢雙雄爭霸史》等。
TOP
章節試閱
旭將軍一騎
1
傳騎(傳訊兵)快奔進入鎌倉府。
首先到達的傳騎是義經派出的,緊接著前來傳達這項事變者,是範賴的手下。
「什麼事啊?」鎌倉騷動著。
傳騎報告,法皇的法住寺御所被義仲燒毀了,數位皇族公卿被殺,法皇則被義仲囚禁。京都傳言義仲很得意,還笑著說:
「我也可以當王了。」
不論如何,闖進御所這種事,可說是古今從未有過的粗暴行為。
「廣元,海潮到了吧?」賴朝對京都的落魄文官大江廣元說道。
廣元因為家世低微,在京都很不得志,於是來到東國,在賴朝的關東政權下工作。賴朝大力借助他的政治能力,他自己也盡情...
1
傳騎(傳訊兵)快奔進入鎌倉府。
首先到達的傳騎是義經派出的,緊接著前來傳達這項事變者,是範賴的手下。
「什麼事啊?」鎌倉騷動著。
傳騎報告,法皇的法住寺御所被義仲燒毀了,數位皇族公卿被殺,法皇則被義仲囚禁。京都傳言義仲很得意,還笑著說:
「我也可以當王了。」
不論如何,闖進御所這種事,可說是古今從未有過的粗暴行為。
「廣元,海潮到了吧?」賴朝對京都的落魄文官大江廣元說道。
廣元因為家世低微,在京都很不得志,於是來到東國,在賴朝的關東政權下工作。賴朝大力借助他的政治能力,他自己也盡情...
»看全部
TOP
目錄
總目錄
〈上卷〉
睡著等死的官差 4
四條聖人 28
稚兒懺法 51
鏡之宿 73
蛭小島 96
白河關 117
弁慶法師 139
京都源氏 161
富士川的水鳥 184
鎌倉新府 207
木曾殿 228
窮途末路的木曾 251
火燒法住寺 275
〈下卷〉
旭將軍一騎 4
堀川館 27
鵯越 50
八葉之車 72
前進屋島 93
讚岐之海 114
源氏八百艘 135
壇浦 157
波濤之上 177
都大路 198
磯禪師 218
腰越狀 237
堀川夜討 257
浦之逆浪 277
〈上卷〉
睡著等死的官差 4
四條聖人 28
稚兒懺法 51
鏡之宿 73
蛭小島 96
白河關 117
弁慶法師 139
京都源氏 161
富士川的水鳥 184
鎌倉新府 207
木曾殿 228
窮途末路的木曾 251
火燒法住寺 275
〈下卷〉
旭將軍一騎 4
堀川館 27
鵯越 50
八葉之車 72
前進屋島 93
讚岐之海 114
源氏八百艘 135
壇浦 157
波濤之上 177
都大路 198
磯禪師 218
腰越狀 237
堀川夜討 257
浦之逆浪 277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司馬遼太郎 譯者: 曾小瑜
- 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11-27 ISBN/ISSN:978957327741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96頁 開數:正25開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歷史小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