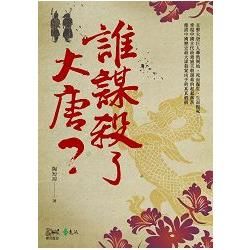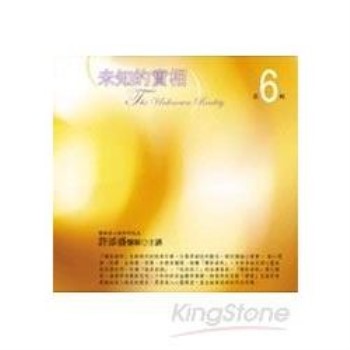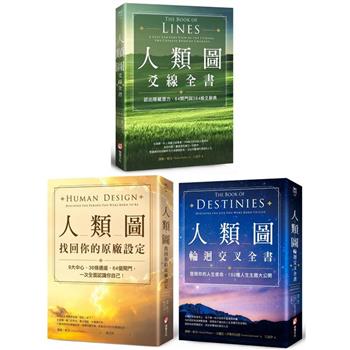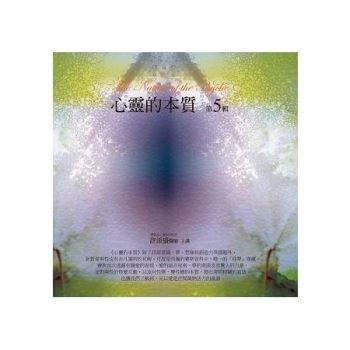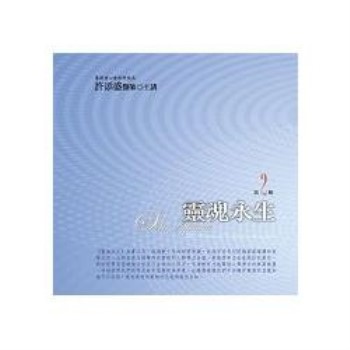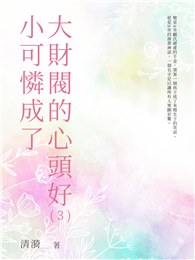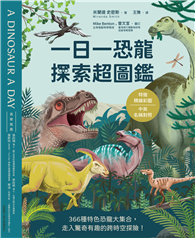他序
誰能調侃歷史?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中 國歷史雖然以統一為總的趨勢,卻也多次出現過混亂分裂的局面,較著名的比如漢末三國、東晉南北朝、殘唐五代,等等。其中要說最亂的,大概非五代莫屬了,從 唐末黃巢起義算起,直到北宋建立,雖然還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卻亂得夠徹底、夠血腥,後人看來是既扼腕歎息,又一頭霧水。
誰能把這一頭霧水驅除乾淨,把無數團亂麻梳理清楚呢?陶短房先生的《誰謀殺了大唐?》,算是基本做到了這一點。
《誰謀殺了大唐?》雖然沒有完整地解構五代史,只寫了唐末和其後的後梁、後唐兩朝,但整個殘唐五代的混亂局面卻可以一目了然了,再往後也不外乎軍閥混戰、皇帝輪流做而已,天子換了一朝又一朝,骨子裡的殘暴和血腥基本不變。
本 書書名裡所謂的「大唐」其實有兩個含義,一是指李淵建立的隋唐之唐,二是李存勗建立的後唐之唐。前一個唐亡於官僚黨爭、宦官弄權和藩鎮割據,後一個唐其實 也差不太多,病根不除,哪怕再有多少個中原王朝建立,有多少個野心家頂著「大唐」的名號「復興」,短命的結果恐怕也都相同。
對於歷史 來說,陶先生有知識、有見識,更有一枝鞭辟入裡的犀利文筆,讀他的書實在是一種享受。所謂「嘻笑怒罵,皆成文章」,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現今流 行著一種風潮,那就是用調侃的筆調去解構歷史,使得原本沉重的歷史變得輕鬆,原本艱澀的史學變得大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能不說是一件好事情。然而只有 對一件事情了解足夠之深,足夠之廣,才能去調侃,才能用看似輕鬆的筆調抒寫沉痛之事,坊間流傳的很多書籍卻根本達不到基本要求,在史識不足、史觀不正的前 提下還膽敢調侃歷史,說句不客氣的話,那根本就是缺乏史德。
要知道,你從史書上看到的,你打算用今文解構以傳達給讀者的,並不是憑空 虛擬出來的故事,而是一大群留下名字或被歷史大潮湮滅的實實在在的人,有五官、有四肢,有血有肉、會動會走、或喜或悲的,與你並無不同的活生生的人,對於 他們在歷史大潮中主動或被迫所做的、被史家所記錄下來的事情,站在今人的高度固然有資格去評論成敗、臧否得失,但因何以成、因何而敗,為何能得、為何而 失,若無深入的研究和縝密的分析,還是不宜妄加品評的,更遑論調侃了。調侃古人、往事本是很簡單的事情,但易地而處,你又能做得比他們更好嗎?
懂 得皮毛,就敢調侃,只把歷史當成自己手裡可以隨心任意揉搓的玩具,這種治史態度,給個「缺乏史德」的評價,一點也不過分。歷史要怎樣才能輕鬆描述,從而順 利傳達給讀者,調侃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方法,但要怎樣的作者才有調侃的資格,要怎樣調侃才不失公允、不乏史德,那些二把刀作者其實都應該來讀讀陶先生所寫的 書。
對於歷史人物來說,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卻不能隨意地嘲其不悟、笑其不敏,因為把你自己放到那個時代,你恐怕比他更不悟且更不敏。看人挑擔不吃力,但在根本就不了解挑擔之苦的前提下,看過以後還要嘲笑對方,那實在是太輕率,太不負責任了。
從柏楊開始,有很多作者用調侃的筆法來寫歷史,其中又有幾個人真有深厚的史識、正確的史觀,從而真有調侃的資格呢?鳳毛麟角之中,陶先生無疑算是一個吧,讀 他所寫的歷史,治世也好,亂世也罷,看看笑笑之餘,掩卷卻不由得人長歎和長思,只有這樣寫史,才真正能夠達到傳播知識、警戒後人的作用。若不能作為鏡鑒來 警戒後人,若不能讓後人比較準確地窺知歷史大潮的一星一斑,只不過看時一笑,看完拋諸腦後,那麼這種書還出它幹嘛?讀它幹嘛?
好在還有陶先生這般寫史的作者存在,還有這種表面調侃、內在深刻的文章存在,才讓我覺得中國歷史不至於學界神祕化、坊間庸俗化,這兩條枝杈越分越遠,最後一腦袋撞進死胡同裡去吧。
歷史,可以高深,但決不能神祕,可以通俗,但決不能庸俗。讀陶先生的《誰謀殺了大唐?》,我才終於從近年來滿坑滿谷卻大都不堪卒讀的歷史散文中找到了一本好書。
── 知名歷史小說作家 赤軍
自序
中國人津津樂道而又很少會引起不同傾向者對掐的朝代並不多,除了漢朝,大約也只有唐朝能享此殊榮。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無不亡之國,即使強盛如漢唐,也無法例外。然而這兩個朝代又不約而同地出現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奇妙局面:東漢之亡,先有劉備的蜀漢續命,迨三家歸晉,天下一統;又有八竿子打不著的匈奴左賢王劉淵,打著「漢朝外孫」的旗號重建了一個「漢朝」。唐朝之亡,則有個後唐替這個大帝國收屍、復仇、還魂,這個後唐的主人非但本來不姓李、不是漢族,而且總共四位帝王,居然有三個姓氏。好不容易後唐也折騰完了,東南又冒出個南唐,將這個光輝的國號,一直延續到宋朝開國後很久。
可同樣是盛世末葉,同樣是死而不僵,殘漢以《三國志》、《三國演義》而不朽,殘唐卻顯得寂寂無聞。
要說沒人寫那是冤枉:論正史,《三國志》只有一本,《五代史》卻有新舊兩套;論小說,《三國演義》和《殘唐五代史演義傳》都是羅貫中所寫。可《三國志》備受重視,裴松之的注校竟比原文多出數倍,而《新五代史》則被譏為「主觀史」,《舊五代史》乾脆失傳,要逼得後人從字紙堆裡去扒拉;《三國演義》流傳千古,中外馳名,而《殘唐五代史演義傳》非但籍籍無名,甚至現在流行的這本是否當年羅貫中的原著都說不清楚。同是大國,殘唐未免死得太冤了吧?
其實關鍵出在謀殺者身上。
漢朝的謀殺者證據確鑿,罪證清楚,案情簡單──不就是老曹家麼,所爭的,無非是這樁謀殺是有罪或無罪,是替天行道、正當防衛、防衛過當還是謀財害命;而唐朝的謀殺者則撲朔迷離,一拎能拎出一串兒來,這一串疑凶中,有的是有賊心沒賊膽,有的是有賊膽沒賊心;有的動了刀,卻沒砍著要害,有的本來是去殺人的,卻不留神把別的凶手給砍跑了……如此亂糟糟的案情,偏攤上中國傳統紀傳體按人頭記事的習慣,專業人士倒沒什麼,普通人翻開書本,除了人名還是人名,沒翻幾篇傳記便一腦袋糨糊,自然是提不起興致來。
其實越是複雜的案情,就越有故事性、趣味性和研究價值。關鍵在於,第一,要把脈絡理順;第二,要用大多數人看得懂、願意看的語言寫出來。
《誰謀殺了大唐?》便是筆者試圖按照上述兩個要素,所做的一次小心翼翼的嘗試,力圖用淺顯的語言,明白的脈絡,有趣的表達,展示從盛唐到殘唐,從真唐到假唐的一段歷史,以及歷史背後的鏡鑒和感悟。
當然,最重要的不僅是勾勒出唐帝國這個受害者的遇難過程,更是揭示那一大串真真假假、大大小小的謀殺者,揭示他們的作案動機、背景和手法。
殘漢之所以精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謀殺者──曹操父子──形象豐滿,有很強的故事性;筆者不揣冒昧,希望通過這樣一本小書,將原本精采不遜色於殘漢的「殘唐謀殺案」,用更多人能讀、樂讀的語言勾勒出來。
「殘唐」習慣上總和「五代」連在一起說,這部書只說殘唐,不全及五代,並非殘唐之後的五代十國不精采,而是為了集中筆墨,把這樁「謀殺案」的來龍去脈交代得更清楚。
前言
大國的伏地挺身
中國是地球上盛產帝國和皇帝的國度,從西元前二二一年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到西元一九四五年最後一個「皇帝」偽滿洲國溥儀,能被稱作「朝代」的「正版」帝國有十七個,雖不被列入朝代但也獨霸一方的「帝國」差不多上百,正版的盜版的、公認的自稱的皇帝更多到難以統計的地步。
帝國數量多自然也意味著被消滅的帝國多,中國人講究「天無二日,國無二君」,除非實力相當,誰也吃不掉誰,否則皇帝甲的登基坐殿必然意味著皇帝乙的人頭落地。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山東泰山一帶有個國境大約只有幾座山頭大小的「帝國」,其皇帝王始在被別的皇帝捉住,押赴刑場就地正法之前,大義凜然地喊出了一句流傳千古的真理:「自古豈有不亡之國!」
的確,自古無不亡之國,別說王始的小小帝國,即使號稱強盛的漢、唐、元、清,也一樣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
古人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意思是大國的崛起不易,大國的趴下卻又快又容易,元朝從斡難河源一個小小部落到橫跨亞歐的空前帝國,歷經百年征戰,但他們被趕回蒙古高原卻只經歷了短短十餘年;清朝從西元一五八三年努爾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到一六四四年滿清入關,建立最後一個全國性帝國,經營了六十一年之久,而武昌起義一聲槍響,不過幾個月工夫就土崩瓦解。
但號稱中國歷史上最強大富足的漢族人帝國--大唐王朝的衰亡軌跡卻與眾不同,它在被消滅十六年後又重新出現,彷彿做了一個伏地挺身(俯握撐),又奇跡般支撐起身軀。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在哪兒趴下、就在哪兒爬起來的伏地挺身現象非常罕見,只有另一個漢族強大王朝──大漢帝國,在被王莽的「新朝」取代後又復國成功,形成著名的西漢、東漢;如果連不叫皇帝的也算,那還可以勉強加上史前的夏代,那個連一件確切文物都沒有流傳下來的王朝,曾經在喪失王權兩代人之後成功復國。
然而夏代復國的少康是已故國王太康的嫡親孫子,東漢復國的光武帝劉秀也是錯了管換的正宗皇族子孫,他們的復國是真正的復國,把原先顛倒過來的再挪回原位。唐朝並非如此,以大唐的名義從血泊中重新站起來的真龍天子,其實是個跟姓李的唐朝皇帝毫無血緣關係的少數民族沙陀族人,更有意思的是,這個「復」出來的大唐一共產生過四位皇帝,卻分屬三個姓氏、兩個民族,而且他們沒有一個是原本姓李的皇族。
看到這裡我們應該有點明白了:所謂的大唐復興,其實不過是一個虛幻的影子,倒下去的是大唐帝國的軀殼,重新站起來的卻是個借屍還魂的新生命。
黑格爾曾說,歷史往往會重複兩次;馬克思補充說,這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但對於趴下又立起、立起又趴下的大唐帝國和「殘唐」而言,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同樣是悲劇。
喜劇是屬於小丑的,悲劇卻永遠屬於英雄。不論是推翻大唐帝國的朱全忠,還是讓這被顛倒的乾坤至少在表面上重新顛倒回來的李存勗,都是憑藉過人的膽略和能力,決定和影響了歷史進程的人物。儘管他們的結局都是悲劇,但前者赤手空拳打倒巨人,後者更打倒了打倒巨人的人,誰敢說他們不是英雄?
下面就讓我們步入大唐帝國的餘暉,看一看這段奇特的「謀殺─詐屍」,和上演這齣歷史妙劇的兩位聯合主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