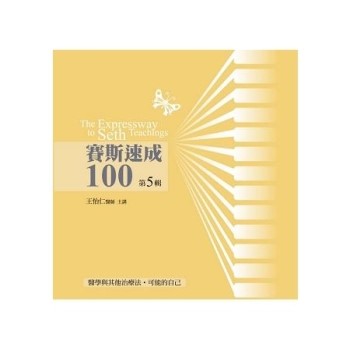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唐代的鄉愁》是一部風格獨特又充滿趣味的歷史、文化讀本。作者富於想像力,從日常細節和民俗時尚著眼,努力爬梳史料,透過衣食住行、宴飲娛樂、城市發展、民族交流、莊園生活、婦女形象、少年豪情、佛道寺廟、長安興衰等主題,串起唐朝生活史的方方面面,內容繽紛多彩,讓人看了有如置身萬花筒之中。
全書以散文的筆調,娓娓道出那個魅力無限的時代──唐,喚起了我們沉睡千年的鄉愁。
作者簡介:
師永濤,一九八三年生於陝西鳳縣,廣西師範大學畢業。目前客居杭州。曾經在桂林、西安、杭州等城市工作生活,關注「日常生活史」課題,業餘寫作。著有文化散文集《回望的目光》。
章節試閱
以下摘自【第二章‧夜宴】
「只有弱者才睡覺」,《時代周刊》(TIME)稱。AC尼爾森(ACNielsen)進行的一項全球睡眠習慣調查,結果顯示,四分之一的中國大陸受訪者午夜之後才就寢,調查還表明,越來越多的人正成為夜生活的主力軍。中國已經進入夜生活的黃金時代,中國人的口味和消費方式正在成熟。
林語堂曾經在《生活的藝術》中指出,中國人對於快樂和幸福的概念是「溫暖、飽滿、黑暗、甜蜜」──實際上,中國人對於黑暗的夜晚有莫名的恐懼感和安全感。這種矛盾的情緒來源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因為眾多的宮廷政變和流血事件都發生在晚上,而在小說和民間傳奇中,夜晚更是陰謀的孵化器;而在另一方面,夜晚成就了人們對隱私的渴望,躲在小小的明亮的家裡,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作家曹乃謙有部小說集,名字叫《到黑夜想你沒辦法》──恐懼感和安全感交錯的情緒往往帶來欲望。於是,就有了夜宴。
一千三百年前的農曆三月初三晚上,長安城南的曲江燈火通明,飛埃結霧,游蓋飄雲。
三月初三在唐朝是國家的公眾假期,此時陽光明媚,百花盛開,和風微拂,水波蕩漾,草木青翠,足以賞心悅目。在這一天,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會來到曲江,所謂「舉國盛遊」。唐朝的皇帝會在這一天晚上大擺宴席招待百官,《全唐文》卷六六八載有〈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一文,白居易在其中寫道:「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獲侍宴於內庭,又賜歡於曲水。蹈舞跼地,歡呼動天。况妓樂選於內坊,茶果出於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間。」這一年是唐文宗大和九年(八三五年),六十四歲的白居易老淚縱橫,看的是皇家教坊的伎樂,吃的是供皇帝享用的茶果,有一種「戰慄的幸福感」。
而帝王與妃嬪的內廷夜宴則更為常見,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唐人筆記《松窗雜錄》中留有詳細的記載:「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唐玄宗)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李隆基最喜愛的坐騎之一),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子弟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據說,李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於是留下了千古傳唱的三首詩,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裝。」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雲想衣裳花想容一句更是成為了後世形容女子百樣美麗的用語。
宮廷夜宴對於出席的官員、貴族服飾也有著嚴格的要求:「其諸親朝賀宴會服飾,各依所准品,諸司一品、二品許服玉及通犀,三品許服花犀及班犀及玉,又服青碧者,許通服綠。」在歐洲的宮廷,儘管服裝的區分沒有這麼嚴格,但是宮廷宴會時的禮服確是貴族們約定俗成的定律。十八世紀時,法國宮廷禮服,主要以絲緣、花邊、絲綢、天鵝絨和淡色的花緞等製成。同時,用黑色天鵝絨的貼片代替以前的化妝面具和撲有香粉的頭髮或假髮。男人戴黑皮和獺皮的三角帽,帽緣鍍金或鑲花邊,並飾以鴕鳥毛。他們把頭髮或假髮編成辮子,以黑色絲帶繫住,置於背後。帶扣的鞋子上配有紅色鞋跟。盛裝時須穿灰白色的絲襪,平時則穿白色毛襪。不難看出,無論是在唐代的宮廷還是歐洲的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比帝王更有權威的主宰便是「禮法」,或稱「禮儀」,就像歌劇院的芭蕾舞一樣,一舉手一投足都有明確的規定。
宮廷夜宴上必不可少的是極盡華彩絢麗的宮廷燕樂,這些樂舞名目繁多,唐初主要的「十部伎」以民族樂區分為:燕樂、清商樂、西涼樂、扶南樂(或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前二者為中原傳統音樂,其他皆由外國傳入。唐玄宗時,因各民族文化逐漸融合,改從樂隊演出形式來分類,有堂上坐奏型的「坐部伎」和堂下立奏型的「立部伎」。坐部伎的表演規模較小,舞者約三到十二人,舞姿典雅,服飾清麗,技藝精湛,用絲竹管弦伴奏。立部伎一般在坐部伎演奏後再演,其陣容更大,舞者最少六十四人,多則一百八十人,加以舞姿威武,服飾華麗,又用鉦鼓伴奏,顯得氣勢雄壯,場面宏偉。坐部伎主要樂曲有六首:燕樂(又分為景雲樂、慶善樂、破陣樂、承天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歲樂、龍池樂、小破陣樂;立部伎主要樂曲有八首:安樂、太平樂、破陣樂、慶善樂、大定樂、上元樂、聖壽樂、光聖樂。
其中舞姿最柔美者,乃是屬於「軟舞」的《春鶯囀》,一名女舞者頭上簪花,身穿短衣長裙,帛帶飄揚,舒展雙臂而舞。舞者站在一花毯上起舞,娉婷月下步,羅袖舞風輕。據《教坊記》記載,這支舞蹈來自「曉聲律」的唐高宗李治:一天清晨,高宗在閒坐時,聽到黃鶯鳴唱,十分動聽,於是命宮廷音樂家、龜茲人白明達作了一首曲子,名為《春鶯囀》,依曲編舞,由女子表演。此舞舞姿柔婉,唐人張祜〈春鶯囀〉有「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的詩句。唐代的夜宴生活一般持續時間長,不到夜半不會散席,通宵達旦而徹夜喧飲的現象也極為常見。唐人夜宴,多邀女性參加,其中更多的是挑選年少貌美者陪坐,這些女子穿著輕盈的帔和飄揚的披帛,配上由傳統裙襦裝改造形成的袒露裝,在燈火之下變化多端。宴席之間,男女往往並肩而坐,看起來成對成雙。當然,女賓有時也會被男客設圈套灌酒,弄得玉容半酣,《全唐詩》中施肩吾〈夜宴曲〉為此有云:「碧窗弄嬌梳洗晚,戶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罰琉璃盞,酒入四肢紅玉軟。
」在唐代,稱呼相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排行)或最後再加以「郎」呼之,例如,白居易呼元稹為「元九」,唐德宗曾呼陸贄為「陸九」;而稱呼女子則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呼之,例如:「公孫大娘」、「李十二娘」等等叫法。很明顯,這是唐人一夜情的生動寫照,其間的聲色靡麗溢於言表。
這一晚的曲江有彩舟巡遊,有百囀流鶯的歌聲,有長袖飄逸的舞者,有頂竿鑽火的藝人,有吆喝叫買的商販,整個曲江沉浸在歡樂之中。
以下摘自【第七章‧少年遊】
在唐代,二十七歲是一個具有神祕色彩的年齡,李世民在二十七歲這一年登上了大唐帝國的寶座,開創了貞觀盛世;永徽六年(六五五年),二十七歲的李治立武則天為皇后,為後來的武周埋下了濃厚的伏筆;而永徽元年(六五○年),李治到感業寺行香再次重逢武則天的時候,武氏亦是二十七歲。
但對於那些才華洋溢的年輕詩人來說,二十七歲卻是一個致命的年齡,李賀在二十七歲病卒,另外一個知名的天才王勃亦是歿於二十七歲。
王勃,字子安,被稱為「詩傑」,生於李治和武則天重逢的永徽元年。王勃出身望族,為隋末大儒王通(號文中子)的孫子,未成年即被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讚為神童,向朝廷表薦,對策高第,授朝散郎。
乾封元年(六六六年),十六歲的王勃被沛王李賢召為王府修撰,兩年後,因在諸王寒食節鬥雞時,「戲為〈檄周王雞〉文」,遭唐高宗怒斥後逐出府,隨即出遊巴蜀。彼時,唐人癡迷鬥雞,舉國以鬥雞為樂,時人有云:「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李白在〈古風〉一詩中也感歎:「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據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八〈支動〉云:「威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鬥雞,高於常雞數寸,無敢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匹強買之,因寒食乃進,十宅諸王皆好鬥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氣。穆宗大悅,因賜威遠監軍帛百匹。主雞者想其跖距,奏曰:『此雞實有弟,長趾善鳴,前歲賣之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一隻雞價格高達二百萬錢,以故連諸王子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也會因此而「傾帑」。
各位王侯鬥雞,互有勝負。一次,適逢沛王李賢與周王李顯(後改封英王)鬥雞,年輕的王勃開玩笑地作了〈檄周王雞〉,討伐周王雞,以此為沛王雞助興,文中寫道:「兩雄不堪並立,一啄何敢自妄?」。唐高宗李治看了文章後,勃然大怒:「此乃交構之漸。」這是一個在唐代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意味著王勃在挑動皇子的關係。高宗的父親李世民就是在玄武門之變中殺了其兄建成、弟元吉而獲得政權的,而李治在登上權力之巔的過程中,他的兄弟們包括太子李承乾、吳王李恪、魏王李泰等先後被殺。高宗當天立即下詔罷除王勃官職,斥出沛王府。
咸亨三年(六七二年),二十二歲的王勃補虢州參軍,因擅殺官奴當誅,遇赦除名。其父王福畤亦受累貶為交趾縣令。上元二年(六七五年)或三年,王勃南下探親,這是他人生最輝煌的頂點和終點交織的年分。路過南昌時,正趕上都督閻伯嶼新修滕王閣成,重陽日在滕王閣大宴賓客。王勃前往拜見,閻都督早聞他的名氣,便請他也參加宴會。閻都督此次宴客,是為了向大家誇耀女婿吳子章的才學。讓女婿事先準備好一篇序文,在席間當成即興所作書寫給大家看。宴會上,閻都督讓人拿出紙筆,假意請諸人為這次盛會作序。大家知道他的用意,所以都推辭不寫,而王勃以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晚輩,竟不推辭,接過紙筆,當眾揮筆而書。閻都督很是不高興,拂衣而起,轉入帳後,叫人去看王勃寫些什麼。聽說王勃開首寫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閻都督便說:不過是老生常談。又聞「星分翼軫,地接衡廬」,沉吟不語。等聽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閻都督不得不歎服道:「此真天才,當垂不朽!」《唐才子傳》則記載:「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
當年,辭別南昌的王勃經嶺南渡海前往交趾,途中溺水,驚悸而死,時年二十七歲。
在唐代所有的二十七歲男子中,最吸引人的是玄宗李隆基。他少有大志,在宮裡自詡為「阿瞞」,被認為是性格、才華及氣質最接近曾祖父李世民的皇子。雖然不被掌權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見。七歲那年,一次在朝堂舉行祭祀儀式,當時的金吾大將軍(掌管京城守衛的將領)武懿宗大聲訓斥侍從護衛,李隆基馬上怒目而視,喝道:「這裡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竟敢如此呵叱我家車騎隨從!」弄得武懿宗看著這個小孩兒目瞪口呆。武則天得知後,不但沒有責怪李隆基,反而對這個年幼志高的小孫子加倍喜歡。到了第二年,李隆基就被封為臨淄郡王。
李隆基是唐代轉折期的帝王,他在位期間開創了唐朝乃至中國歷史上的最為鼎盛的時期,史稱「開元盛世」,但是他在位後期(天寶十四年)爆發安史之亂,使得唐朝國勢逐漸走向衰落。中國人常說「盛極必衰」便是李隆基時代的唐朝留給後世太多強烈對比的緣故。
先天元年(七一二年),二十七歲的李隆基登上了皇位,威脅他的只剩下那位著名的鎮國太平公主了。次年七月初三,李隆基果斷地先下了手,親自率領兵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幹幾十人,將傾向太平公主的官員全部罷黜,終於掌握了皇帝應有的權力,史稱「先天之變」。當年,他把年號改為開元,表明了自己勵精圖治,再創唐朝偉業的決心。
天寶四年(七四五年),唐玄宗李隆基將時年二十七歲的楊太真接入後宮並冊封為貴妃,其地位僅次於皇后,他視這位女性為自己的生命,讚其為「解語之花」。
以下摘自【第二章‧夜宴】
「只有弱者才睡覺」,《時代周刊》(TIME)稱。AC尼爾森(ACNielsen)進行的一項全球睡眠習慣調查,結果顯示,四分之一的中國大陸受訪者午夜之後才就寢,調查還表明,越來越多的人正成為夜生活的主力軍。中國已經進入夜生活的黃金時代,中國人的口味和消費方式正在成熟。
林語堂曾經在《生活的藝術》中指出,中國人對於快樂和幸福的概念是「溫暖、飽滿、黑暗、甜蜜」──實際上,中國人對於黑暗的夜晚有莫名的恐懼感和安全感。這種矛盾的情緒來源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因為眾多的宮廷政變和流血事件都發生在晚上,...
作者序
【前言】
唐代的鄉愁
西元六二七年,關中大旱,災民賣兒鬻女以求生。去年在玄武門宮鬥中斬殺兩位競爭對手的唐太宗面對旱災憂心忡忡,剛即位的他下令開倉救濟,解決災民的燃眉之急,並拿出御府金帛,供災民贖回賣掉之子女,以免骨肉分離。這一年李世民二十八歲。
就在同一年,一位叫玄奘的僧人「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他乘著夜色混在流民中溜出長安城,踏上了西行取經求法的漫漫征途。這一年玄奘二十五歲。
西元六二七年,唐朝的貞觀元年,是「貞觀之治」的起始,歲次丁亥。
根據中國傳統五行學說,中國古人利用干支紀年法,以六十為周期(一甲子)把歷史重複編排,他們認為每六十年一個輪回中,事物發展就像草木隨四季更替一樣生長、繁茂、凋落與衰敗。而其中的丁亥年則是由衰而盛的關鍵性轉折年,它意味著從丁亥年開始,各種事物都將步入一個長期的發展和繁盛階段。
一
歷時十七載,西去取經的玄奘在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正月回到了長安。四年之後的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年)三月,比玄奘年長三歲的李世民感到身體不適,很快便輾轉病榻,不能下地走路了。
四月二十五日,實在撐不住的李世民終於決定,離開他日理萬機的太極宮,攜家眷和近臣到翠華山下的離宮翠微宮避暑養病。時值孟夏,這裡林木清幽,涼風習習。
在〈秋日翠微宮〉一詩中,李世民寫道:「秋日凝翠嶺,涼吹肅離宮。荷疏一蓋缺,樹冷半帷空。側陣移鴻影,圓花釘菊叢。攄懷俗塵外,高眺白雲中。」對於翠華山,李世民有著特殊的感情,此前的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年)四月,他命人重建太和宮,改名翠微宮,籠山為苑,列臺觀其中。他似乎和這翠華山之間有一種宿緣。最終,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在寢殿含風殿辭世,此時,他的繼承人太子李治心中除了悲傷,還在惦記著感業寺中一個姓武的女子。
即位的高宗李治把玄奘安置在了大慈恩寺中譯經。在李治心中,大慈恩寺和大雁塔是他的母親長孫皇后靈魂寄寓的場所,而他居住的大明宮,「北據高崗,南望爽塏,視終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窺。」(韋述《兩京新記》)如果再登臨高出平地十五公尺的含元殿,透過宮殿的門楣,穿越丹鳳門的鴟尾,一直往南,李治可以清晰地看見「壯麗輪奐,今古莫儔」的大慈恩寺,以及寺中「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的大慈恩寺浮屠。
龍朔三年(六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高宗李治偕皇后武則天入住尚未完工的大明宮(時稱蓬萊宮),自此取代太極宮而成為大唐帝國二百四十餘年內政和外交的中樞。
此後數百年間,無數道大唐帝國的政令自燈火通明的大明宮發出,影響著一個帝國的脈搏。當唐朝皇帝威望最高的時候,大量的突厥人內附,突厥王族成為了大唐最勇猛的將軍;波斯薩珊王朝(Sassanid Empire)末代的兩位波斯王都希望借助唐朝的力量復國,最終終老在長安;大量的遣唐使來自新羅和日本;而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與安南人亦來帝國定居,散落在從敦煌到廣州的帝國城市。國子監亦即國立大學中,有這些國家的留學生,其中最具熱忱的是日本人,他們有的像今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在中國曾居留達幾十年,有的終身為唐官,深埋大唐。而更多的人回國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有了具體的貢獻,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都城設計建造完全模仿長安,從銅幣的設計到婦女的髮髻,從室內的布置到圍棋、茶道、詩詞都參照大唐的時尚,從此之後,後世出土的日本文物深具中國色彩。
那個時候,初次來長安的人都充滿了陌生感,踏進這座大城市的每個訪客無不感到驚詫,大開眼界,長安的瑰麗和宮殿的雄壯,已經超越了想像極限。這些外來的人們為長安城的狂放情趣、繁華市井而目炫神迷,嚮往,畏縮,好奇,慌張……,各種反應,百態畢現。
二
在唐朝統治的三個世紀中,東方各地的財富也經由陸路被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車裝,或駝載,或馬運,或驢馱。偉大的絲綢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亞的重要商道,它沿著戈壁、荒漠的邊緣,穿越唐朝西北邊疆地區,最後一直可以抵達撒馬爾罕(Samarkand)、波斯和敘利亞。從玉門關向西,有兩條道路可供行人選擇,這是兩條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要經過流沙、戈壁和荒漠,還要面臨極度的寒冷或酷熱。
唐貞觀九年(六三五年)十一月,來自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國(Sogdians)的使臣由撒馬爾罕再次來到長安,粟特人的足跡遍布於絲綢之路所經過的一切地方,從東海之畔的揚州,到沐浴在地中海陽光下的拜占庭(Byzantium)。
他們中最著名的卻並不是商人,而是一位「柘羯」(武士)。他是一個胖子,擅長跳胡旋舞。這個叫安祿山的粟特胖子和唐朝最著名的美人楊玉環有著一種曖昧的關係,而且後來他還把楊玉環的丈夫李隆基從長安趕到了成都。歷史上,把這段往事稱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起因卻來源於一個皇帝藝術家的「黃昏戀」。
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年)十二月,武惠妃病重,玄宗李隆基決定去驪山過冬,第一次遇見楊玉環。只是皇家一次例行的謁見,卻讓一個五十多歲的皇帝和自己二十出頭的兒媳訂下了山盟海誓的約定。
至德二年(七五七年),在數千精騎的簇擁下,從成都準備返回長安的「太上皇」李隆基取道鳳翔東行。約莫走了三天,來到了馬嵬驛,他銘心刻骨、晝思夜想的地方。驛站猶在,佛舍猶在,梨樹猶在,可「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玄宗之後近半個世紀的元和元年(八○六年),三十五歲的周至縣尉白居易作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敘事詩〈長恨歌〉,詩人以極富想像力的筆調,描寫唐明皇(後人給玄宗的稱呼)終夜不眠,看著宮前螢火蟲飛來飛去,階下落葉也無心找人打掃。這樣的憂恨纏綿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間任何因素能稍一舒慰。這首〈長恨歌〉也隨之流傳千古,直到一九二○年代,仍舊為小學生所習誦。但奇怪的是,當時在位的唐憲宗李純竟然默許了白居易寫皇家愛情的行為。甚至當時長安歌女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自誇,並因此身價倍增。(白居易〈與元九書〉)
這個皇帝和中國古代最優秀的宮廷舞蹈家之間的愛情,終止在了馬嵬坡,一個很小的地方,在陝西省咸陽市代管的縣級市興平市西北十公里的土原上。而他們愛情開始於長安東邊驪山一處叫「華清池」的皇家園林。驪山是歷代皇家的行宮,一個很教人不安分的地方,周幽王曾經在那裡烽火戲諸侯。李隆基最愛的華清池,位於今天西安市臨潼區驪山北側,東距西安三十公里。當旅遊者乘火車或汽車前往臨潼參觀驪山及華清池時,應先注意四周黃褐色的泥土,黃仁宇先生曾經說,這種泥土與美國田納西州一帶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國歷史展開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三
著有《宋:現代的拂曉時辰》一書的「宋粉」吳鉤曾經說:唐代是中世紀的黃昏,而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作為一個舶來品,「中世紀」一詞是十五世紀後期的歐洲人文主義者開始使用的。這個時期的歐洲從「文藝復興」中衰落下來,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權來統治,傳統上認為這是歐洲文明史上發展比較緩慢的時期。
而當「中世紀」這個詞出現在中國史及其相關敘述中的時候,被默許指稱七到十世紀的隋唐時代,儘管學界對這一學術名詞的「拿來主義」持質疑態度。日本文史家內藤湖南就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見《歷史と地理》第九卷第五號)中說:「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
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唐文學文化論集也取名為《中國「中世紀」的終結》(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估計他也料到此種提法會有誤會,故用了引號。
或許,「中世紀」這個名稱是宇文所安的策略,是一個國外漢學家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視野。在我看來,「中世紀」的「中」字用到唐朝,卻是恰如其分,中者,中興也。唐,這個中國歷史中最能引人遐想的歷史片段之一,無論我們從哪個角度進入,都會有陌生的新鮮感。既然這個詞來到了中國,不妨給予它一個中國的身分。
更遑論歐洲從中世紀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和中國從唐到宋的轉型,其中的轉化有著可以比較的研究。英國學者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比較歐洲中世紀與初唐、盛唐的差異時說:「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於蒙昧黑暗之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並蓄而好探求的。」
我喜愛的作家紅柯說過:「我們從遠古開始建造莊園、城堡和城市,卻不相信地球是宇宙裡的飛行物,是長翅膀的神鳥。」
沒有想像的歷史,並不能算是真的歷史。
四
天復四年(九○四年)正月,黃巢降將出身的宣武節度使、梁王朱溫,挾天子以令諸侯,劫唐昭宗李曄遷都洛陽。朱溫「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木,自渭浮河而下」,使長安淪為廢墟。(《舊唐書‧昭帝本紀》)
唐長安城留於後世者,僅剩殘垣斷壁和若干城牆遺跡。
唐帝國最後一個皇帝哀帝(或稱昭宣帝)李柷先被降為濟陰王,遷於開封以北的曹州(今山東菏澤),安置在朱溫親信氏叔琮的宅第,後又被廢除帝位。由於太原李克用、鳳翔李茂貞、西川王建等仍然奉「天祐」正朔,不承認梁朝,朱溫擔心各地軍閥的擁立會使廢帝成為身邊的定時炸彈,就一不做,二不休,於後梁開平二年(九○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將十七歲的哀帝鴆殺。
至此,建國二百八十九年(六一八~九○七)的大唐帝國一去不返。
天祐三年(九○六年)之後,長安再未曾成為中國的國都。帝國的重心已逐漸移至東邊,中國開始了藍色的大洋夢,東南區域以其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更有吸引力。所以唐朝之後的歷史中,幾乎所有的王朝都採取一種南北為軸心的戰線,與長安漸漸遠隔。
今天,當我們穿過長安的軀殼西安,伸手撫摸一下眼前這粗糙、沉睡的四方城城磚,心裡就莫名地溫暖而踏實了──儘管唐朝的長安城牆是夯土築造的,僅在城門部分有城磚包裹。我們的內心中只要泛起愁思,我們仍會以《春江花月夜》的豔麗或《霓裳羽衣曲》的飄灑不斷穿越歷史,相望那個繞梁千年的江湖絕唱。
曾經,一個王朝的風花雪月主宰了那個叫長安的城市轉瞬即逝的春秋,詩歌的漂泊帶來了哀愁、天才、江山和美人,還有揮之不去的思念。那些焰火、野草、王孫和驛站,以及大氅,最終成了鄉愁。今天,這種鄉愁仍在。
------------------------------------------------
【後記】
一份唐代生活史的私家書單
寫這份書單的時候,我一邊聽袁惟仁的專輯,一邊翻閱法國漢學家馬伯樂(Henri Maspéro)的《唐代長安方言考》(Le dialect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聶鴻音譯,中華書局,二○○五年)、《唐詩紀事》,以及《全唐文》、《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這些大部頭的龐雜的唐代史料。很多時候被一種情緒包揉,為浩瀚史料所呈現的唐代感動,心生嚮往,就如同多年前的夏日,在老家土房背後的梧桐林下,被漏下的陽光感動得渾身戰慄。
這個不築長城的朝代和中國歷史上其他朝代一樣,也有著皇家的荒淫、門閥士族的黑暗和戰爭的殺戮。有人據此來評價唐代,但時至今日,我們的世界仍然沒有遠離這些黑暗。
這個朝代是文學的時代。一在於唐詩,另一在於唐傳奇。我曾經寫過「古紙硬黃臨宋怨,短箋勻碧錄唐幽」的句子,唐人的詩文,總是有一種塵土般的質感,如同蒼茫的曠野。
我還曾經數次想像自己穿行在唐代通往撒馬爾罕的絲綢之路,抑或是在途經長安東市的時候聽那個幽怨的安邑坊女唱「巴陵一夜雨,斷腸木蘭歌」,抑或是在杜甫的五城做一個戍卒。
在這裡寫一份私人的書單,不局限於正史,而是羅列傳奇、小說、研究甚至奇幻,在這些或嚴謹、或瑰麗、或不忍卒讀的文字裡,唐代閃爍著精細的光芒,而我們的視界則或許可以延伸得更遠,這不是歷史的可能性,而是歷史的想像力。
一
謝弗(Edward Hetzel Schafer,漢名薛愛華)著的《撒馬爾罕的金桃──唐朝的舶來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中譯本改名為《唐代的外來文明》。據說這本書是西方漢學的一部名著,被視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古代文化的必讀之作。其實在中國,這本書的影響力更大,因為此前從來沒有一本書從「物」出發來深入研讀一個時代的歷史,而這些物質碎片,比如「一隻西里伯斯島(Celebes,即蘇拉威西島)的白鸚,一條撒馬爾罕的小狗,一本摩揭陀的奇書,一劑占城(Champa,位於今越南中部的古國)的烈性藥等等──每一樣東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發唐人的想像力,從而改變唐朝的生活模式,而這些東西歸根結柢則是通過詩歌、法令,或者短篇傳奇,或者是某一次即位儀式表現出來的。」
在這本書裡,謝弗引用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話來闡釋這種寫作的必要性:「歷史隱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範圍以外的地方,隱藏在我們無法猜度的物質客體之中。」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本影響了很多中國歷史學者及歷史愛好者的書,對其作者我們卻知之甚少,我們僅能從簡介中知曉謝弗是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精通漢語和日語,並通晚近法語、古拉丁語等十數種古今語言文字。而謝弗著述頗豐,除《唐代的外來文明》外,還有《朱雀──唐朝南方的意象》(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ines of the South)、《珠崖──古代的海南島》(Shore of Pearls: Hainan Island in Early Times)和《時光之海蜃──曹唐的遊仙詩》(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神女──唐代文學中的龍女和雨女》(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點評杜綰〈雲林石譜〉(Tu Wan's Stone Catalogue of Cloudy Forest: A Commentary and Synopsis)、《閩國──十世紀時的華南王國》(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步虛──唐代對星空的探求》(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和《唐代的茅山》(Mao Shan in Táng Times)。其中《唐代的外來文明》是公認的謝弗的代表作,並與《朱雀》共同被視為其研究唐朝外來文化的雙璧。但除了《唐代的外來文明》、《朱雀》、《神女》,其餘各種並未見在中國出版。
二
已逝的曾經執教於香港大學的莊申先生,以美術史學家的身分寫有一本《長安時代──唐人生活史》,亦是不常見的大師所著唐代生活史,可惜此書大陸未見引進,不能使更多人一睹真容。在莊申看來,唐人的詩書樂弈、繪畫陶瓷、雕刻工藝、舞蹈服飾,凡此種種,無不令人耳目一新。當中的巧思慧心,全在唐人的生活中表露無遺。今人與唐人雖緣慳一面,但愈來愈多的考古文物,使今人也能一窺唐人社會的全貌。
莊申家學淵源,尊翁為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尚嚴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他幼承家學,勤於研究。早在他就讀於臺灣師大史地系,及稍後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期間,便常有專文論述中國美術史,刊登在《大陸雜誌》,是當時引人注目的青年學者。他的《根源之美》、《扇子與中國文化》、《從白紙到白銀》等都是非常精采的著作。
作為一名唐史學者,賴瑞和先生被人知曉卻是他的旅行散文集《杜甫的五城》,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三年,他先後九次暢遊中國大地,一路風塵,走過城市和鄉村,尋求歷史與現實的交會。當他第一次乘坐火車前往西安的時候,竟然隨口問列車員:「到長安的嗎?」結果列車員狠狠地愣了一愣:「長安?哦,對!您是指西安吧?」
這是一本關於唐代「另類」的書,賴瑞和並沒有直接討論他所了解的唐朝,而是興致勃勃地記錄了一系列的「流水帳」:九次旅行的路線與詳細費用、國營旅社、衣服、美食等等,賴瑞和作為一個局外人,一路用新鮮的眼光角度來體驗大陸的種種出人意料的不同。他脫掉洋氣的教授行頭,穿上在內蒙古買的保暖羊絨衣,坐在擠滿鄉民的巴士裡,就像一個普普通通的大陸中年男人。在西安,他騎著自行車去北郊尋找大明宮的遺址,彼時三清殿的廢墟,前面並沒有任何標誌,也沒有任何圍牆,只是孤零零地立在玉米田中。「我也隨著那些好玩的小孩,爬到土堆上頭去。那裡長著一些雜草。在夕陽下,登高望遠,所看到的景物都染上一層溫馨的金黃色調。」賴瑞和的壯遊,歷史與現實交融,那個叫唐的國度如影隨形在日常的瑣碎中,讓人有了恍如隔世的憂愁,夾雜著淡淡的悲傷。
賴瑞和一九八一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師從《劍橋中國隋唐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AD)的主編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教授習唐史,並在這位西方公認的唐史和中國通史學界的大師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唐代的軍事與防禦制度》。賴瑞和目前在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專任教授,曾經主講唐代長安與士人的生活(碩、博士班)、唐代日常生活史(大學部人社系),我讀過他對第一門課的一個講演提綱,是用PPT做的演示,極其生動。
三
除了中國人之外,對於唐代關注最多的便是日本學界,儘管沒有唐代生活史的專門論著引人注目,但日本作家在其大量的關於唐代的小說中,徐徐展開了一個王朝的面目。井上靖或許是此類小說的開創者,其《天平之甍》(天平の甍)講的是鑒真東渡的故事。井上靖寫道,準備第一次東渡時,「鑒真已五十五歲,相貌卻仍骨骼嚴整,巍然如山,有偉人氣質,額寬,眼、鼻、口皆大而穩定,頂骨秀氣,顎部卻頗有意志地展開。留學僧覺得這位高名高德的僧侶,很像故國的武將。」後來,一九七九年這部小說在被拍成電影時,曾經在揚州取景拍攝,彼時揚州數萬人圍觀拍攝。
而井上靖《楊貴妃傳》(楊貴妃伝)一書則開啟了中日之間對於楊貴妃生死的大討論,這部小說影響之深遠,以至於國內有些歷史學者拿其作為史料使用。
近年來,聞名的日本作家乃是陳舜臣,其兩百餘本和中國歷史有關的著作已經被引進了數十本,他和井上靖一樣,對於唐代西域有著莫名的夢想。一九七九年,中央電視臺和日本NHK電視臺聯合組成大型紀錄片《絲綢之路》攝製組,沿著古代絲綢之路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採訪攝製。陳舜臣參加了此次攝製活動,並用文字記錄下重走絲綢之路的奇妙見聞與瑰麗隨想,成書的名字就叫《西域余聞》。儘管也寫了一點漢代的西域,但此書更多是在唐代西域的物品、詩人和生活方式對於帝國的影響。
相對而言,日本作家辻原登的代表作、歷史小說《飛翔的麒麟》(翔べ麒麟)知道的人就比較少了,究其原因,是簡體字版中譯本有一個莫名其妙的書名為《唐朝那些事兒》,這種爛到大街的譯名完全毀了這本書。實際上,這本小說寫作功底和歷史考證極其精細,而且更勝在歷史想像力與史詩的契合度。
四
中國人關於唐代生活史的論著多為專著,例如衣飾、飲食、官制等等,以「唐代生活史」為題的專門著作則鳳毛麟角,即使有也是大量常見史料以及傳統的論文研究,黃新亞《消逝的太陽:唐代城市生活長卷》一書為其中可以讀一下的書籍。究其原因,是此書儘管亦屬學術著作,但其形式上卻引入大量和生活、習俗、用具有關的史料及傳奇故事,使得以「生活」為名的專著有了點煙火氣。
建築設計師唐克揚有一篇關於長安的文章〈長安的煙火〉曾經在《生活月刊》刊發,但至今仍未成書,而他本意是通過實驗文本來梳理中國古代的城市,因此其中關於城市的敍述及想像力頗為動人,是難得一見的創作。
還有一位筆名叫「騎桶人」的作家,因為寫的是奇幻文學而不被歷史研究者知道,他大量的短篇小說如《終南》、《雙髻》、《歸墟》等有著深深的唐傳奇影響的影子在裡面,其文字入微,纖細空靈,甚至算得上晶瑩剔透,能通過微妙的詞語表達心靈。想像力極奇詭綺麗,於最幽靜處,發前人之所未想,有一種罕見的神祕特質。他的文字具有相當高的純文學水準,把唐人傳奇中的生活場景演繹得十分淋漓盡致。
近幾年,得益於網路的出現以及歷史熱,大量的關於唐代的書籍出現,但是仔細看起來這些唐代的書籍無一例外是:那些人那些事、光榮與夢想、趣聞與軼事,而關於唐代生活史方面卻無人關注,以至於大量的寫唐代宮廷的小說中,僅僅人名是唐代的,而各種生活歷史細節卻是瓊瑤小說或者清朝電視劇的翻版。
五
曾在央視「百家講壇」節目講過《敦煌資料與唐五代衣食住行》的隋唐五代史學者黃正建,對此亦是有所發現,在〈關於唐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現狀的思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二○○四年九月十四日第三版)中,他寫道:「但是在中國,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並沒有形成規模或形成學派,甚至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雖然我們也有關於衣食住行的研究,但它們都是孤立的、個別的、零散的。學者們分別從政治、經濟、民族、宗教、文化、風俗、文物、科技、歷史地理等各種角度來研究它們,卻恰恰很少將它們作為『日常生活』來研究。」
實際上,西方學界對「日常生活史」的關注已久,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英國漢學家魯惟一(Michael Loewe)的《中華帝國早期的日常生活:兩漢時期》(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During the Han Period, 202 BC-AD 220)一書,都是極其精采的關於生活史的論著。
具體到唐代,彬仕禮(Charles D. Benn)有《傳統中國的日常生活:唐朝》(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Tang Dynasty)一書,作為「格林伍德出版社日常生活史叢書」(The Greenwood Press Daily Life Through History Series)的一種出版,可惜無人引進翻譯。另有《中國的黃金時代:唐代日常生活》(China's Golden Age: Everyday Life in the Tang Dynasty),已出版中譯本。
另一方面,大量的記錄唐人生活場景的唐代筆記和傳奇實際上並沒有被人們足夠關注,中華書局曾經出版唐宋史料筆記三十九種,亦是唐宋雜錄。實際上中華書局還有一套《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其中「唐」卷,共有筆記七十種,不可謂不煌煌。
在前言中我寫道:曾經,一個王朝的風花雪月主宰了那個叫長安的城市轉瞬即逝的春秋,詩歌的漂泊帶來了哀愁、天才、江山和美人,還有揮之不去的思念。那些焰火、野草、王孫和驛站,以及大氅,最終成了鄉愁。今天,這種鄉愁仍在。
可惜的是,這種鄉愁只存在於史籍和唐詩中,大量面目模糊的細節無從考證、查找,比如朱溫如何拆毀長安使得這座偉大城市消失的過程,《舊唐書》及《資治通鑒》僅有寥寥數語,《新唐書》則完全不記載。歷來國人修史,重史識而輕細節,重人而輕物,重考據而輕整合,這也使得唐代的生活史散落於史書的各個角落,沒有完整地呈現,這是一種深深的遺憾。
作為一本小眾的生活史圖書,《唐代的鄉愁》在二○一四年一月出版後,如意料中一樣,並未引起什麼關注,很快便被淹沒在海量的出版物中。對於我這個業餘寫作者來說,自己的作品能夠出版便是獲得了滿足與喜悅,並無其他的「野望」。
好在還有一些網友讀到了這本書,在豆瓣網、新浪微博上表達了喜愛之情,這不啻是一種意料之外的「嘉獎」,讓我暗自欣喜。
此番臺灣遠流出版公司決定出版《唐代的鄉愁》繁體字版,令我感到的不僅是個人的喜悅,還有「日常生活史」這個小眾門類被更多人了解的快樂。
我在這裡必須感謝遠流編輯陳穗錚女士,她在編校過程中的嚴謹和專業,不但讓我在修訂此書時因為一些錯誤而汗流浹背,而且讓我對於臺灣的出版人有了別樣的敬意。也感謝我的前同事劉斌先生、網友谷大建先生和攝影師魏華先生、王海東先生,為這修訂本提供了部分照片。
我還要感謝本書大陸版的編輯,安徽文藝出版社的岑杰先生,此書完稿兩年後,歷經波折,終於在他手裡付梓,得以問世。也感謝我的好友吳窮先生為此書出版之事奔波努力。
二○一六年四月 於杭州和美弄
【前言】
唐代的鄉愁
西元六二七年,關中大旱,災民賣兒鬻女以求生。去年在玄武門宮鬥中斬殺兩位競爭對手的唐太宗面對旱災憂心忡忡,剛即位的他下令開倉救濟,解決災民的燃眉之急,並拿出御府金帛,供災民贖回賣掉之子女,以免骨肉分離。這一年李世民二十八歲。
就在同一年,一位叫玄奘的僧人「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他乘著夜色混在流民中溜出長安城,踏上了西行取經求法的漫漫征途。這一年玄奘二十五歲。
西元六二七年,唐朝的貞觀元年,是「貞觀之治」的起始,歲次丁亥。
根據中國傳統五行學說,中國...
目錄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前言:唐代的鄉愁
第一章 唐人的世界
第二章 夜宴
第三章 從揚州到長安
第四章 胡人們的唐
第五章 帝國時代的莊園
第六章 女人在她們的時代
第七章 少年遊
第八章 未能皈依的寺廟
第九章 最後的長安
□後記:一份唐代生活史的私家書單
□附錄一:西元七~九世紀的唐代和世界
□附錄二:七十種唐人筆記書目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前言:唐代的鄉愁
第一章 唐人的世界
第二章 夜宴
第三章 從揚州到長安
第四章 胡人們的唐
第五章 帝國時代的莊園
第六章 女人在她們的時代
第七章 少年遊
第八章 未能皈依的寺廟
第九章 最後的長安
□後記:一份唐代生活史的私家書單
□附錄一:西元七~九世紀的唐代和世界
□附錄二:七十種唐人筆記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