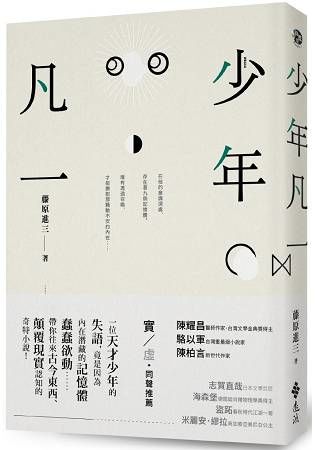後記
從厚繭中長出的生命
之所以會有這部文字的書寫,是為著因應兒子的請求,要我寫一個故事送給他,唬弄他內心不安定的靈魂,作為伴他度過十八歲生日的禮物。一開始,根本沒有什麼整體架構情節大綱,連故事會講多長多久都沒有預期。從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那個週六開始,逢週六就寫一章節,連寫了十八個週六。每個週六,總是趴靠在墊於大腿的紙板上,利用室內還有光線的時間,一口氣,寫上八到十二個小時。寫完,總是腰痠背痛、既虛脫又滿足。這樣子長期固定在單一姿勢執筆的衍生紀念物,就是紙板依靠支點的膝蓋和身體重心著力處的臀部,在摩擦中長出了一層粗糙硬實的厚繭。凡一的故事,也就這樣,在兒子播下種子之後,自己長出來了。
身處這樣的境遇下寫作,有兩大特點有別於一般作者。其一是,無法自由查閱資料。別說上網google、維基百科,抑或是到隨時到外面的圖書館或誠品書店蒐集資料了,在這裡,我連一本國語辭典都沒有呢!常常頂多就是在工作的資源回收場垃圾堆中撿到的書籍,從裡頭掇拾一些可以再生利用的素材。但說也奇怪,似乎許多訊息都會自動跑來找我,主動讓我發現,好被寫進故事裡。其二是,無法修改作品。不僅整個故事事先沒有規劃,每一個章節,在每個週六開始著手動筆的當下,往往都還沒構思好內容會如何發展。經過恍若夢中的一氣呵成之後,隨即封緘郵寄回家去。故事文字,從此脫離了我獨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一週一封信,一次書寫一個章節。直至原稿交付出版、進行正式校對前,之前寫成的部份,我再也沒能瞧上一眼,更別說修改校正了。沒有底稿可以回顧參照,我只能憑著記憶,琢磨著情節如何鋪陳發展。所以,只能採取一種最為簡約的格式架構,讓故事的脈絡維持在得以僅止於透過印象予以駕馭而不至於失控的程度範圍內。如今回頭一看,好像是巴哈的賦格似的,迴旋再迴旋,在簡單之中追求對於繁複的包容。
故事到進行到一半時,自以為是用一種「在傳奇中發現事實,在事實中創造傳奇」的方式在書寫。現在寫完了,卻沒了那種感受,反而覺得:「據實說出看似不可能的真相」,說不定比「虛構一些看似合理的情節」更有趣得多。
這個故事,是送給兒子的,他是催生者,也是共同創作者。能夠完成,要感謝我的妻子,沒有她,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誠摯地感謝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長、黃靜宜總編輯,以及這本書的責任編輯蔡昀臻小姐,因為有他們的幫忙,這一個故事才有機會讓世人知道。也衷心感謝陳耀昌教授,應允為本書作序。
妻兒一致支持,將本書的版稅收入,全數捐贈給從事難民援助的非營利組織「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簡稱IRC)。目睹苦難不斷,總令我想起一位印度詩人的話語:「擁抱光明,但永不忘記曾在黑暗中為我們點燈的人。」
推薦序
無邊際作家的無邊際作品
遠流王榮文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有一本新書請我寫序。知道作者是誰後,我迫不及待馬上去取書稿,毫不思索地答應。
拜讀約五分之一後,我就開始請教谷哥大神了,也震驚於我這老友的作品,涵蓋範圍竟如此寬廣。書中有精神醫學(但不是最近風靡台灣的阿德勒「勇氣學」)、有宗教(竟是奇特的摩爾門教與冷僻的古佛教,我Google之後仍然分不出哪些是史實,哪些是作者虛構)、有藝術史(這一點我倒知道淵源所在,作者夫人是藝術史家),更驚訝的是,也談物理(作者文組出身,如何能將物理學大師的理論,談得如此深入又有趣,不可思議)。他寫亞美尼亞大屠殺,竟然好像身歷其境,而且融合西方詩集,又有戲劇張力。日本神話裡的「輝耀姬」(月光姬),在小說中化身成了主角凡一的準女友。春秋時代的盜跖在他筆下,則完全被顛覆,變成一流哲學家,先把孔仲尼修理一番,又與日本文人志賀直哉暢談日本文學、文化,再與世界各方大哲縱論上下古今。最後古今東西哲人齊聚一堂,天人合一,令人拍案叫絕!
本書的表現手法也很特殊。作者像文字魔術師,在他筆下,古代與現代之間,異想與現實之間,西方與東方之間,如穿越劇,來去自如。而全書以日本為背景,無一字提到台灣,卻又時而針對台灣現況,作一針見血的評論。他評析日本總理「鞍馬天九」、反對黨黨魁「有文英菜」,談領導風格,又提福島災變,縱論核電政策。其實一字一句,莫不針對台灣,讓我不禁掩卷狂笑。還藉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之口論科學與政治間的糾葛,這是永遠存在的兩難,但作者舉重若輕,令人擊節讚嘆。更談AKB48,談蘿莉控,嚴肅中有輕鬆調皮,頗多創見。再加上作者選擇以小說人物「藤原進三」作為筆名,而「進三」又與日本首相名字(晉三,Shinzo)發音相同,妻子則成了三菱財閥「岩崎」家族一員。凡此種種,道出他雖然一時受挫,而不改鴻鵠之志。我感覺他正以這本「無邊際作品」來展示他未來可能的「無邊際人生」。
難怪王老闆說他讀了之後「驚豔」,而我則是「拜服」。
我不知道讀者的反應會如何?但我會用主持醫學會議時稱讚演講者的最高級形容詞「very inspiring」來表達。是的,用「inspiring」(啟發性)這個字來形容這本書應該最合適吧!
王老闆說,為什麼邀我寫序,除了我與進三兄是朋友外,還認為我們都是「跨領域的新銳作家」。進三先生的這本《少年凡一》,融宗教、玄學、哲學、藝術、廚藝於一爐,又創作出兼合自修、家書、神話的文學新風格,無所不包,無邊無涯。是的,一言以蔽之,無邊際,borderlessness,正是這本書的最大特色。
許多朋友告訴我,他們喜歡我的《島嶼DNA》,因為我從人類學到台灣史,都能提出新觀點。在《福爾摩沙三族記》與《傀儡花》中,又展示考證及說故事的功力(抱歉自吹自擂)。然而,我只能算是多元multidisciplinary,而Dr. Shinzo(作者是法學博士)則真正是無邊際borderless。
我只是運氣好。二○○九年開始寫《福爾摩沙三族記》時,正好《熱蘭遮城日誌》問世;二○一二年寫《傀儡花》時,又逢台史博出版了《李仙得台灣紀行》的英文版,讓我在真實史料的蒐集方面,得來全不費工夫。此外,我大大受益於Apple、Google,還有Facebook。
因為有了智慧型手機,我可以二十四小時隨時上網,可以斜躺在床上寫作,在火車上、計程車上、捷運上、等電梯、等人、等上菜時,都是上網時刻。可以隨時照相留存,資料巨細靡遺,又可以分類歸檔。網路提供了我無窮的資訊,包括去何處踏查。然後我以過去寫醫學論文的訓練,去蕪存菁、去偽存實。就這樣,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朋友或讀者眼中的「專家」。數位化讓貿易無邊際,造就了全球化;地域無邊際,成了地球村;也讓知識傳播無邊際,人的學習遂可以無疆界。總之,如果早生二十年,我只是一個愛好閱讀的醫師或教授,無法跨界有成。
然而,我的朋友Dr. Shinzo更厲害,他處於一個無法使用網路的環境,無Apple、 Google及Facebook,甚至無書店、無電腦、無綜合圖書館。他竟然能寫出無所不包,無所不精,又似論述,又似神話的小說。我真的不知他是怎麼做到的,只能說天縱英明吧!
更可怕的,他僅利用十八個週末就寫成了《少年凡一》的家書原稿,真是速度驚人。他的夫人麗子告訴我,家書原稿大多整整齊齊,只有極少數幾個字經立可白塗改。而我自己的小說,不但原稿分散各類紙張,而且經助理打字後,我都還要修改五遍、十遍以上。甚至章節重新來過,布局重新來過,結局重新來過,主角命運重新來過。總之,Dr. Shinzo才是無邊際作家,我只是多元書寫。
在這樣無邊際時代,資訊與知識的取得相對容易得多,教育的目的不再只是傳遞知識,還要引領下一代有效吸收消化並靈活運用知識。我的朋友Dr. Shinzo博聞強記,知識豐富,並且受過專業法學訓練,《少年凡一》原是不自由的他為了「唬弄」孩子所寫的家書,他以特出的記憶與統整能力,天馬行空地編織出一則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故事,結果意外成就了這樣一部帶有神話意味的穿越小說,也成為了一份送給讀者的新奇禮物。
Dr. Shinzo寫給兒子的家書成了這本小說《少年凡一》,寫給太太的情書成了另一本小說《彩虹麗子》。這家庭的三位成員,感情甜蜜交流,又各有獨特專長,真是令人稱羨。Dr. Shinzo在四面高牆裡已能夠寫出無邊際作品,將來重歸自由之後,會有怎麼樣的爆發力,展示其無邊際人生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陳耀昌
■陳耀昌,醫師作家,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著名血液疾病專家,為台灣骨髓移植先驅與幹細胞研究開拓者。著有歷史小說《福爾摩沙三族記》、《傀儡花》,文化論述《島嶼DNA》等,並獲巫永福文化評論獎、台灣文學金典獎等。
附錄
書寫自成悟境──讀藤原進三的《少年凡一》
「藤原進三」不只在《少年凡一》中登場,也是文壇的新名字。然而,這個陌生的異國姓名,並不只是空白的符號;相反地,由於小說之外的「個人歷史」,使其意義豐沛。作者後記說,《少年凡一》是送給兒子的十八歲禮物,然小說裡凡一的失語病徵,很難不讓人聯想起作者的獄中困境:身體的禁制,話語的封鎖──少年凡一折射的,畢竟是作者自我。不能說,總可以寫:作者完成這部十餘萬字的長篇,化身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人」,在無光囚房弔詭地滔滔不絕。
凡一是一,也是多;是內在的自我,也是宇宙萬物的起點。《道德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主角凡一的身體,是降靈的祭台,是乩身,通過父親藤原進三的「催眠」,喚出橫跨古今的人們。凡一擁有一副老靈魂,而那些紛紛現身的人們,「並非『人格分裂』,而是『潛意識』──『在集體潛意識中,存在著最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和文明』。」
《少年凡一》並非情節取向的作品,更接近一部百科全書。作者任意揮手,就召來日本小說家志賀直哉,德國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海森堡(在凡一的宇宙,他並未獲獎),甚至春秋時代的盜跖……,展開哲學,數學,美學,乃至於神學的辯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身陷囹圄,文獻資料查詢不易;除了記憶,只能仰賴監獄裡偶然出現的傳單、報紙與書籍。編者指出,作者就像《過於喧囂的孤獨》中的老人,在廢紙堆中撿拾文明的碎片;然我認為《少年凡一》更是一部《懺悔錄》,其反覆叩問的,還是罪罰與救贖的問題。作者通過書寫求索的,與其說是文明的輝煌或幽深,毋寧看作在恍若廢墟的現世,找尋與自我,與親人,甚至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或許正如小說裡,透過皮拉姆斯談論其師拉斐爾所道出的:「透過信仰、透過藝術創作,一直試圖探索『自己是誰』、『想變成誰』,以及自己如何和別人連結的方法。」
小說發生在京都,小說人物也是日本人,「閉著眼睛,我都知道如何從四條大橋轉下河堤沿著鴨川走道出町柳……」小說中對於京都的描述,並不是川端康成《古都》那樣體察風土肌理,而更像一幅遠方的幻片風景。記憶裡的都城愈是豐盛華美,愈對照出「此時此地」的崩毀與寒愴。作者決絕地說:「台灣不能再作為我的故鄉」,因此他必須通過「另一個故鄉」來演繹故事。那麼,為什麼是日本?日本對於寫作者來說,又代表什麼?這讓我想起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日本將作者推入寫作情境,這情境甚至震動了作者的心靈,推翻以往所閱所讀,意義動搖、撕裂,直到衍生出無可取代的虛無,而物件卻充滿意義……,總而言之,書寫自成悟境。」
是的,書寫自成悟境。就此看來,古今人物的召喚,京都地景的幻設,都是為了療癒「凡一」,使其開悟。小說最後,凡一臨行贈予的詞彙「有難」,是日文的「感謝」之意;他說:「(是你們)讓我的靈魂變得更加輕盈而自在,可以去追尋自由。」緣此,《少年凡一》不只是一部長篇小說,更是一張診斷表,一紙家書/家訓,一卷無聲而無限的辯詞。
陳柏言
(本文轉載自《聯合文學》雜誌第三八九期)
■陳柏言,一九九一年生,高雄鳳山人,台大中文所碩士班就讀。曾獲聯合報文學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夕瀑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