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到底能夠為學生「做」什麼?我們所活著的世界已經發生過種種革命性的劇變,那麼,學校是否應該花更多心思來因應這險峻世局,或把學生推向唐吉訶德式的尋夢之途,以便讓他們在這多變的世界中仍能優游生活?
在這部探討教育可能性的精闢評論中,知名心理學家傑羅姆·布魯納指出教育如何企圖引領下一代融入文化,卻經常以失敗收場。他把新興的「文化心理學」運用到教育上,提出若要讓人類心智的潛能充分發揮,只有透過融入參與文化一途。但他並非指較為正式的文化活動,如藝術與科學,而是該文化如何理解、思考、感覺以及進行論述的方式。藉由檢視教育的實踐與理論,布魯納以新穎又豐富的觀點探討了過去令教育學家困惑的經典難題。
不同於以往累積的教育評論著作,布魯納在本書中不再將教育視為促進自我實現的手段,而是教育如何讓個人變得有能力可參與融入生活和謀生所仰賴的文化。不論是教育學家、心理學家與心智及文化的研究者,都能在這劃時代的評論中讀到如何挑戰現今一成不變的教育實踐,以及為未來指向的智慧願景。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教育的文化:從文化心理學的觀點談教育的本質(2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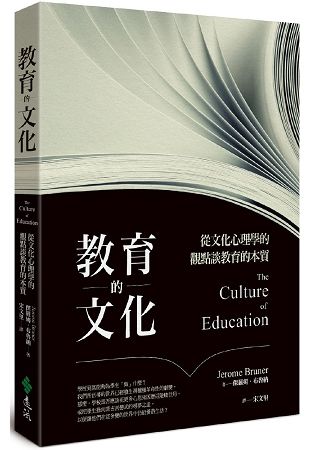 |
教育的文化:從文化心理學的觀點談教育的本質 作者:傑羅姆.布魯納 / 譯者:宋文里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5-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0 |
二手中文書 |
$ 238 |
社會人文 |
$ 300 |
教育總論 |
$ 342 |
教育總論 |
$ 342 |
教育概論 |
$ 342 |
中文書 |
$ 34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教育的文化:從文化心理學的觀點談教育的本質(2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 1915-2016)
美國心理學家、教育家。1941年於哈佛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曾任教哈佛大學、劍橋大學與紐約大學。1987年以「理解人類心靈的畢生貢獻」獲得學界至高榮譽的巴仁獎(International Balzan Prize)。著作豐富,除了本書外,尚有《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1960)、《論認知》(On Knowing, 1962)、《教學論》(Toward a Theory of Instruction, 1966)、《實作的心靈,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1986)、《意義的行動》(Acts of Meaning, 1990)等。在2002年出版的《普通心理學評論》(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調查中,布魯納在二十世紀中最常被引用的心理學家排行中排名第28。2016年過世,享壽一百歲。
譯者簡介
宋文里
1952年生於台灣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榮退教授,輔仁大學心理系兼任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娥百娜–香檳校區)諮商心理學博士。研究與教學興趣為:文化心理學、文化的精神分析、藝術心理學、宗教心理學、批判教育學等。他是個跨領域的人文學者,著作散見於各種人文、社會科學專業期刊以及文化/藝術評論雜誌。目前專騖於學術翻譯,已出版的學術譯作包括《成為一個人》(左岸,2014新版)、《教育的文化》(遠流,2001初版)、《宗教的動力心理學》(聯經,2014)、《正常人被鎮壓的瘋狂》(聯經,2016)、《關係的存有》(心靈工坊,2016)、《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心靈工坊,2017)等。
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 1915-2016)
美國心理學家、教育家。1941年於哈佛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曾任教哈佛大學、劍橋大學與紐約大學。1987年以「理解人類心靈的畢生貢獻」獲得學界至高榮譽的巴仁獎(International Balzan Prize)。著作豐富,除了本書外,尚有《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1960)、《論認知》(On Knowing, 1962)、《教學論》(Toward a Theory of Instruction, 1966)、《實作的心靈,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1986)、《意義的行動》(Acts of Meaning, 1990)等。在2002年出版的《普通心理學評論》(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調查中,布魯納在二十世紀中最常被引用的心理學家排行中排名第28。2016年過世,享壽一百歲。
譯者簡介
宋文里
1952年生於台灣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榮退教授,輔仁大學心理系兼任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娥百娜–香檳校區)諮商心理學博士。研究與教學興趣為:文化心理學、文化的精神分析、藝術心理學、宗教心理學、批判教育學等。他是個跨領域的人文學者,著作散見於各種人文、社會科學專業期刊以及文化/藝術評論雜誌。目前專騖於學術翻譯,已出版的學術譯作包括《成為一個人》(左岸,2014新版)、《教育的文化》(遠流,2001初版)、《宗教的動力心理學》(聯經,2014)、《正常人被鎮壓的瘋狂》(聯經,2016)、《關係的存有》(心靈工坊,2016)、《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心靈工坊,2017)等。
目錄
新版譯者序
譯者導言
序言
第1章 文化、心靈與教育
第2章 庶民教育學
第3章 教育目的之複雜
第4章 現在、過去與可能之教學
第5章 對他者心靈的理解與解釋
第6章 科學的敘事法
第7章 敘事理解之中的現實
第8章 以知為行
第9章 心理學的下一章
索引
譯者導言
序言
第1章 文化、心靈與教育
第2章 庶民教育學
第3章 教育目的之複雜
第4章 現在、過去與可能之教學
第5章 對他者心靈的理解與解釋
第6章 科學的敘事法
第7章 敘事理解之中的現實
第8章 以知為行
第9章 心理學的下一章
索引
序
新版譯者序
文化心理學對於教育本質的學術承諾
本書初版時,我在介紹中說「學術長青樹布魯納教授今年已屆八十五高齡」,但到了再版的此時,布魯納教授已經以一○一高齡,在二○一六年辭世。他所倡議發展的文化心理學,對於教育本質的探討,該從哪裡談起?
我認為可以從原本就以實踐為本質的教育那裡展開——我們似乎不應籠統地說我們要「以教育學來探討教育」,而是要「以文化心理學來探討教育的文化」。我們已談過:文化心理學必然是以本土心理學為基礎而產生的心理學下一頁,亦即它必須發展為超文化心理學(transcultural psychology)。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布魯納討論「庶民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的方式重新攤開來檢視一遍,應該不難理解此中道理。
布魯納對於庶民心理學比較集中的討論,是出現在他的《意義的行動》(Acts of Meaning)一書。他的說法是:任何文化在不經過學院式討論之前都會出現某種對於「內心」「外界」兩分的「心理學」概念,而這些概念會變成某種常識,或某種預設(presupposition),用來決定其他種種概念。但在這二分法的結構之外,還會產生某種「中介」的領域(布魯納稱此為「第二界」,所以,相對的,內心就是「第一界」,而外界就是「第三界」),各個文化對此一領域的認知深淺和多寡都會有很多差異,因此,當我們對原有的二分法的結構有所知悉之後,我們要設法瞭解其「第二界」的實際內容,甚至要為原先所缺乏的瞭解而大力補充其內容,譬如從第一界到第三界之間的交通究竟是透過超自然巫術的方式、人文溝通和想像的方式,或科學假設和考驗的方式等等,而這樣的補充可以包括釐清,也可以包括改寫。於是經過這道手續之後,原先的「庶民心理學」就必然會轉化為「文化心理學」。至於這種轉化為何會發生,我們很難用民族文化的「本土性」來解釋,而必須將它放進社會-歷史演化的過程——特別是異文化間的接觸過程——才足以理解。
這種庶民心理學的討論最有助於我們判斷「本土心理學」究竟是不是「文化心理學」的地方,不在於區分所謂的「本位/客位」,而在於揭示那個中間「第二界」之必然存在——無論你對它是有意識或無意識。
***
二○○九年我去開封參加過一次「中國心理學會:全國心理學學術會議」。在會中極有意思的發現是:當時我參加的「理論心理學組」裡也還沒人提過「文化心理學」,但很多學者、學生都知道台灣有「本土心理學」。不過,大多數的與會者已經不談「本土心理學」,而換上不用任何主張就能朗朗上口的「中國心理學」,並且這種話語也已經是屬於「元理論」(後設理論)的層次,也就是說:在談文化是什麼之前,大家對於文化早已有個共識,那就是「中國文化 vs. 西方文化」的提法,也認為那是個不證自明的「理論架構」。所有的人(除了極少數例外)都認定了文化差異的命題,並且也認定西方理論的缺陷可以用中國理論予以補足。像這樣的共識,在台灣竟然動用過一個「大型研究計畫」(也就是「本土心理學研究計畫」)才能為此做出勉強的肯定。我之所以要這樣提,是因為隔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的《民族教育研究》期刊編輯輾轉來信向我邀稿,他就特別聲稱:大陸學界至當年還很少人知道有「文化心理學」的存在,而我在九年之前已經翻譯介紹了布魯納的作品,實在很令人驚奇。但我也要提出我在「中國心理學」中的驚奇發現:在台灣,我從來沒聽過任何學術人使用過「心理學的學科承諾」這樣的說法,而在那次的會場上卻三番兩次聽到一些有心於學術發展或改革的人會用「學科承諾」來標示他們針對此承諾應該提出什麼改革方案。所以,我現在要以兩岸學術觀察的角度,來談談文化心理學可能的「學科承諾」會是什麼。
嚴格來說,「文化心理學」在現有的心理學學術建制中還算不上是一門「學科」,而比較像是一種「學說」。具體的證據是:即令在美國學界,至今也還沒出現一本適合作為大學本科教科書的「文化心理學概論」之類作品,所以,就學科而言,它頂多是個「發展中」的學科。但我們要談的重點是在於知識本身的「承諾」問題。對此,布魯納有一種討論的方式,是出現在《實作的心靈,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一書中的第九章「教育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文中敘述了一名女生在聽到他所主張的「任何題材都可以教給任何年齡的兒童,假若我們能採取某種誠實的知識形式」之後,她採取相當積極的態度逼問道:如何才能保證那種知識形式是「誠實的」?布魯納承認他用了自己以前說過的一些教學程序和方法來回答問題,但事後,他自己覺得非常心虛,因為他知道那不是那位女生想要的答案。而他的想法是:我們必須回到「語言」本身來回答這問題。我們使用的語言其實都具有「兩面人」的性格(也就是說:不容易用「誠實」與否來形容它)。語言一直同時具有雙重功能:它一方面是一種溝通的模式,另方面也就是它所代表的世界觀之如實呈現。
為了要具體說明這個意思,他引用了法國作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thes)寫的一篇短文〈法國玩具〉來呈現,大意是說:法國小孩所玩的玩具,除了極少數例外(譬如積木),大多數都是在呈現大人的慾望、大人的需求、大人對世界的理解,並且還一概是採取「消費者」角度來獲取以及使用那些玩具:戰爭、官僚、美醜、外星人等等。孩子們不只是在玩玩具,他們得同時「消費」這種「溝通工具」中所承載的整套世界觀。所以,所有的法國小孩將來長大後就自然會成為一個個加味調理的法國世界觀和法國自我。布魯納對於羅蘭.巴特這位「精雕細琢的自嘲大師」除了讚揚有加之外,當然也立刻知道了美國人和美國教育缺乏批判自省的問題——大家都只看到教育語言似乎積極的一面,而忽視了以批判態度來如實呈現其另一面。
法國也好,美國也好,對我們而言,重要的理解一定也會在反身自省中以批判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所說的華人、中國人或什麼本土,以及我們所使用的漢語本身,到底攜帶了多少不能被我們自己用「自嘲」來發現的世界觀?我們恐怕都只是汲汲於利用「本土心理學」、「華人心理學」、「中國心理學」這些名義來「發揚」自己的文化,卻不太會同時反省這些文化內容裡可能隱含的偏見和盲點——特別是那些被革命者所詛咒,但同時也完全繼承下來的「封建社會關係」、「官僚主義思維」,以及不知是褒是貶的所謂「集體主義文化」——這就是我所謂的兩岸同步觀察。一旦我們真的也都同時發現這些問題,那麼,我們不得不把以上所有的「發揚式學科」提升成為「批判的下一頁」:文化心理學為了要超越傳統思維的限制,必須邁向更為「誠實」的教育。換句話說,我們要讓學問發達到這樣的程度,才能說它是在完成它自己的承諾。
關於「學科承諾」,我們還需要一個更為基本的說法——能「承」擔起知識發展,能給出思考的「諾」言者,並不總是已經完成建制的學科,而是在思考中、也能不斷思考的學者。譬如布魯納這位老教授,他在《教育的文化》一書六、七兩章所談的「敘事法」,總有些讀者和評論者認為他的表達意猶未盡。於是,布魯納在六年之後,集結他在紐約市立大學法學院的授課心得,對敘事法的問題再作了一次更徹底的發揮,讓敘事法成為解決文化衝突的一種基本手段:
任何一個人類文化,在其本性中,既是對於社群生活(之難題)的一種解決之道,而隱 含在此之下的,則是對於生活在此(文化)界限之內者所提出的威脅與挑戰。如果一個文化要存活下去,它就需要一些手段來處理這些埋在社群生活之下的利益衝突……。
這種敘事法的學說,對於想瞭解自身所處的文化者而言,實具有普世性的意義,而不管這是美國教授或法國作家所提的理論,一旦我們有所理解,我們也就同時知道了他們是在承擔什麼知識,以及給出什麼諾言。這樣的承諾,讓我們更能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我們只要能讀到這樣的書,我們就是文化遺產的受益者——為什麼我們不能拋棄本位主義,來迎接所有的知識遺產呢?而在這種受益狀態中,你能不感謝像布魯納這位「非本土的」知識開發者嗎?
***
最後還特別要感謝楊茂秀教授,他不但在最初推薦我翻譯此書,也促成了本書的再版。我把全書重讀了一遍,儘量作了目前知識狀態最可能的修訂。雖還不可能完備,但就是盡了最大的可能。
宋文里
2018年
譯者導言
布魯納的轉變是心理學及教育學界中很引人注意的話題。論述學派的大將哈瑞(Rom Harré)曾說:這是個「很令人欣喜的諷刺」——「布魯納是曾參與第一次認知革命的建築師,但卻也是第二次認知革命中最活躍的份子和最具原創性的發言人之一。」學術長青樹布魯納教授今年已屆八十五高齡,而正用他自己的生命史來見證某種意義的心理學術發展史。
一九五六年,布魯納和兩位合作者出版了《思維的研究》(A Study of Thinking)一書,用結構發展論向當時的主流,也就是行為主義和刺激-反應的學習理論,提出直接的挑戰。自茲而後,對於認知、思維和心智的心理學研究逐漸取代非心靈論,並且使心智的形式結構和計算機科學的人工智慧理論合流而逐漸形成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這就是「第一次認知革命」的意思。是的,布魯納在一九六○年出版了《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一書,更使之成為代表皮亞傑結構理論而成為發展心理學的經典之作。但是,他在享譽三十年之後,竟從根柢上轉向另一個知識典範,也就是維高茨基(Lev Vygotsky)的社會歷史心理學(socio-historical psychology),或就叫文化論(culturalism)。所謂的「第二次認知革命」事實上就是指文化論在人的科學(human science)之中的發展,它到目前都還在默默地進行中——十幾年來,有一支逐漸成形的心理學,叫做「文化心理學」,正反映了這場無聲的革命。我們可以說:「第一次認知革命」把認知研究帶進來,然而 「第二次認知革命」卻正要把認知帶出去。
出去哪裡呢?用我們對於成長的一句俗話來說罷——出社會!首先要把心理學裡的個體主義予以徹底社會化,要揉合置身在地(situated)的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理論,然後要從二十世紀語言哲學的人文研究裡取出最為核心的方法論——敘事法(narrative)和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來安置這種社會化過程。這「社會化」對心理學來說,至少有兩個意思,一是說:長期以來心理學被視為「非社會的社會科學」(nonsocial social science),因此,它終究難免會產生內在的反省動力來改變它的體質;其次,它毋寧更像是說:心理學需要「社會學化」,因為布魯納在提出這個轉向的新名稱(也就是「文化-心理取向」,或「文化心理學」)之時,他一方面建議讀者參看一些屬於這種努力的新作,另方面則說,這些作品的古典源流應是維高茨基、涂爾幹(Emile Durkheim)、舒茲(Alfred Schutz)以及韋伯(Max Weber)。
個體性和社會化之間為什麼不能各安其所?譬如說,心理學是研究個體性和心靈本質的心理學,而社會學是研究社會體制和社會化的社會學,為什麼要讓它們之間形成像知識演化一樣的過渡關係?為了解釋這種關係,布魯納有句箴言似的說法:「心靈之獨特奧祕,就在於它本具有隱私性且稟賦著主觀性,但儘管它有那麼多隱私,心靈還是不斷創生了公共的產物」——這「公共的產物」就是指在世界之中透過符號系統(譬如語言)而保存和傳達的公用知識。事實上,心理學仍是心理學,但對於「心靈」這個概念,以及承載心靈的那個本體,我們不能再簡單地說:那不就是個人嗎!不是的。教育學長久以來仰賴心理學來界定教育的主體。當心理學不能理解「社會主體」或「文化主體」的存在樣態時,我們的整套知識體系通過各級學校教育而把我們歪曲地模塑成「個體主義」的樣子。然後我們會發現個體主義和社會/文化的運作之間,有極不諧和的關係,更嚴重一點說,竟會造成像「右派/左派」那樣的意識型態衝突。處在這種思想衝突中而茫然無解,於是教育變成了相當虛無主義的飄渺幻境。咱們這樣說吧:社會運作的根本機制是合作,為什麼我們的學生竟要被切割成離子化的個體,永遠只能一個一個分開來考核?
***
我從進入九○年代之後才開始斷斷續續聞到這股新心理學的味道,但是在世界邊陲的台灣,我還得一直懷疑是不是我的嗅覺器官患了過敏的疾病。一九九三~九四年之間,我有機會到哈佛大學進修一年,雖然在計畫中我要作的研究不是這種心理學,但無論如何,我買到兩本布魯納的新作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1986),以及Acts of Meaning(1990),從而真正注意到這樣的發展。經過這十年的探索,我發現「文化心理學」和我原來所知的心理學實在差距太遠,也自認為無法以自己的說明來把這種帶有革命性內涵的轉變交代清楚,因此我就一直轉著一個念頭,要用譯書的方式來向中文世界作引介的工作。雖然我知道「文化心理學」是許許多多數不清路數的人文知識和心理學的重新結合,而布魯納也不完全代表這種發展,但是,因緣和合,一九九九年,我的一位好友楊茂秀教授竟然說,他正在替出版社物色一個譯書人,就是要譯布魯納這本更近期的作品。
***
我就從布魯納講起也罷。根據我對本書論證脈絡的理解,用這篇短短的導言,也許可以為布魯納這種「文化心理學」做個起碼的說明。
本書的第一章,開宗明義地用計算論(computationalism)和文化論(culturalism)的對比來說明個體主義和人工智慧理論在教育上根本行不通之處。計算機,就是俗話說的電腦,已經輕易取得了當代知識的主導地位——不論就知識處理的技術來說,或就它所形成的隱喻來說皆然。我這樣想:如果我們去買電腦,我們知道每一部電腦是用許多零件組裝而成,然後我們給它「灌進」需用的軟體,測試它的各種功能,沒出問題,這就成交了。但你怎麼知道它沒問題?因為測試有個標準程序,既然能通過,就是沒問題。那麼你怎麼知道那個程序是標準的?因為各零件硬體和各使用軟體之間連接得是否正常,在螢幕上可以完全表現。這整套關係形成一種「完整形式」,所以我們把它定義為「標準」和「沒問題」。在一定的程序和有限的表現上,就可以看出來——這是「每一部」電腦測試的基本邏輯,不可能有例外。但是心靈的硬體零件是什麼?它被灌進了什麼軟體?你又從哪裡看出它的表現?這每一題的答案都是不確定。而最糟的是,在企圖測試之時,連品管師都不得不承認,他要測試的對象總是會不斷反映著測試者的自己——在測試者和被測試的對象之間,通常沒有確定的標準,也沒有所謂「完整形式」的字典或測試手冊可以翻閱。即使勉強編出這樣的手冊,那編者還是得承認,這只是「不完整」或永無完整性的參考文件而已。在心靈的品管師和對象之間不可能有測試(testing)的關係,而只能有關聯(relating)和摸索(exploring)的「不完整」關係——人必須用意欲(intention)來超過他自己,然後和他人的意欲形成交互關聯的關係,而在意欲和意欲之間,也就是在心靈和他者心靈(other minds)之間,只有摸索而不會有確定的關係。
關聯和摸索的關係方式,在人類之間就叫做「生活在一起」,或叫做「社會/文化」。有一種特別的「社會/文化」生活,是專指發生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那就是養育(rearing)。而經過特殊的分工之後,我們把其中的符號性成分區分出來,用特殊的社會體制來加以經營處理,就約莫是「教學」(teaching/learning)的樣子,但通常會有個更抽象的系統名稱,叫做「教育」。而即使是這樣說,也是要強調這過程一點也不簡單,至少不是像生產線(裝配線)那麼簡單——用一條線就可以直指向目標。教育是社會體制,是文化的自我摸索和自我生產,所以它會經歷一些生活者對自身的定義,這是在「庶民理論」(folk theory)裡頭可以看出來的。而我們的種種教育理論模型就是建立在庶民理論所種植的前提之上。要隨著庶民理論-教育模型來做個綜述時,也會發現它們的「目標」各自相異,很難確定,甚至是充滿著相互悖謬的關係,譬如特殊主義/普同主義,個體智能/文化工具學習,開發創造/複製傳統等等這幾套悖論,以及永遠的爭議,這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的邏輯。
回到文化心理學的重新反省,教育的起點確實包含著個人的行事自主(agency)、反身自省(reflection)以及人類的公有文化、協同合作這些理念之間的關係。所以第四章要把這些關係重新整合成一張理解教育的全圖,並且用時間的延續來作為整合的基礎。最重要的時間是現在,而不是過去——因為參與過去就是進入已經形成的固定意義,而參與現在則當下面臨了意義的不確定。對「現在」的重新發現,也就是理解人如何和他的文化有「置身在地」的關係,會因而發現文化之不斷處於形塑之中的樣貌。對於「置身在地」的當事人而言,他是和「未來」形影不離的,但布魯納不說那是「未來」,而寧稱之為「可能」(the possible)。在教育中,以當前問題為教材,用文化所能提供的一切裝備和社會一切的組織合作方式去對付問題,那才是時間延續和文化整合的教育。
重省之後的教育所重者不在於個體心靈的表現,而在於發現人類心靈具有「從我至他」的一貫脈絡。心靈和「理論」是一體兩面。理論就是建構的理解,而理解有兩種不同的形式,那就是因果解釋(explanation)和意義詮釋(interpretation)。教育之中的學習不只是學習客觀的事物,學會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還要學習「學習本身」,也就是用理論的理解來學習心靈的理論,用詮釋來學習事物如何被賦予意義,簡單地說,這就是「以心學心、知己知彼」。一旦有此可能,於是自我之心和他者之心就會具有同形同構的關係。這是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問題,也是第五章的核心。
「計算論/文化論」以及「解釋/詮釋」這樣的對比,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量之為物(quanta)/質之為物(qualia)」的基本問題。當然在通俗的理解(也一定是一種庶民理論吧?)之中,甚至還會以為這是「科技/人文」對比的問題。這種談法已是每況愈下、不知所終。布魯納認為:如果科技是心靈的問題,是教師和學生心靈之間交會的問題,那麼科技無論如何是得在某種非科技的理解方式中存在。科技本身的解釋語言是特殊的人工語言(譬如數學),但敘述科技的語言則是日常語言,而它的方法是敘事法,也就是講故事的方法。以故事結構為襯托,才會有科學內容的存在。那麼故事是怎麼講的?敘事法可是人類文化的一大成就——早在科學誕生之前,人類就一直在講故事,也靠著講故事來傳遞文化生活的種種理解,包括神話、歷史、法律和哲學,無不如此。於是在當代文學和史學理論的捉摸下,敘事法的真髓益發為人知曉。第六章到第七章的脈絡告訴我們,怎樣讓敘事法成為教育者真正的看家本事。
置身在地的經驗還孕生一種比理論更為細膩的知識——實踐的知識,或說是行動中的知識。這種知識並非特別有別於理論知識,而應該說,在心理發展的過程中,最先發展的應是行動中的知識,後來逐漸生出替代行動的知識模式,最後生出符號性的替代,而完全可供作理論之用。這是第八章所要談的意思。
最後一章,布魯納回頭看心理學本身的發展。他以「生物性的限制-文化建構-置身在地的實踐」這樣的三角模型來總結自己的理論,也說這就是他所倡議的「文化心理學」。對生物性限制的重視呼應了文化心理學之前的心理學,但是加上文化建構的理解,使心理學開始走向社會化的下一頁,而實踐知識則又更進一步把知識主體和主體所在的文化/社會脈絡聯貫成一氣。布魯納的預言是:下一世紀的心理學必當如是。從某一角度來說,這樣的話又必定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學者在晚年的化境之中才能說得出來。
***
布魯納在本書中曾經提到,有些心理學家還轉變到更為基進的文化論,譬如葛根(Kenneth Gergen)和哈瑞,而根據我的了解,後面這兩位所代表的是後結構主義哲學潮流下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和論述心理學(discursive psychology)。在當今的文化心理學發展中,他們和布魯納一樣受人矚目,甚至更代表下一代文化心理學的發展。一九九六年在英國創立的期刊《文化與心理學》(Culture and Psychology),事實上幾乎可說是建構主義和論述心理學的天下,而美國的「文化心理學」反而成為其中的一個支流。
我從一九九五年決定開始開授「文化心理學」課程時,確實是以較為基進的葛根和哈瑞來開頭的,因為我記得培根(Francis Bacon)說過︰你想把已經偏斜的桿子校正,那就一定得用矯枉過正的辦法,才能使它彈回原位。在那段時間,很多新心理學冒出來,哈瑞等人主編的《反思心理學》(Rethinking Psychology)一書正反映了那時候百家爭鳴的情景。但這些心理學都帶有一種意味,我用另一位維高茨基的信徒柯爾(Michael Cole)來說明——他把文化心理學稱為「第二心理學」(second psychology),我相當同意,因為它表明了從原來的「第一心理學」中脫胎換骨,而不再屬於同樣知識體系的意思。席尉德(Richard Shweder)說得更清楚:文化心理學不是普通心理學(general psychology)、不是跨文化心理學(cross-cultural psychology)、不是心理人類學(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也不是民族心理學(ethnopsychology)。那麼,在席尉德心目中,文化心理學是什麼?那就是通過以上四種「不是」而形成的某種叛教(heretical)轉向,它形成一種「重新萌生的學科」(reemerging discipline),它反對普同主義的心靈論,反對心靈統一體(psychic unity)的想法,而主張邁入個別生活脈絡中尋求心靈的種種特殊表現。這意思是:只有文化實踐中的心靈,而沒有特別可以從文化脈絡中抽繹而出的心靈抽象物;只有在意欲之中的心靈,而沒有不動的心靈。這樣的脫胎換骨確實是徹底的,所謂「基進」也者,正是這個意思。
相對而言,在我看來,布魯納所發展的就不是那麼基進的論述。他強調解釋和理解是兩種各自成立的思維模式,而皮亞傑和維高茨基是兩種互補的典範。除此之外,對於生物天性的因素,他認為必須保留。不過,這並不是折衷主義。在這樣溫和的表面之下,布魯納其實都表示了兩種堅持︰第一是,後者不能化約為前者,理解不是解釋的暖身操,維高茨基不是皮亞傑的衍生物;其二,我們之所以能看出第二種、第二階的性質,是以第一種、第一階的知識作返身自省的結果。就拿「生物性」的議題來說吧,文化論者不把生物天性視為人類發展的上限,而是下限。人類生來是未完成的動物,只有靠文化才能把自己製作完成。這樣的論述方式,雖然並不基進,但可稱是諄諄善誘;雖然語不驚人,但卻一直堅定地導向那場無聲的革命。
所以,有此理解之後,我也開始把徹底文化論的論述基調轉換成較為溫和的演奏。譬如說,我決定要在我的課程裡增加一些關於靈長類研究的單元,讓學生一邊觀看黑猩猩行為,一邊想想文化從哪裡開始。
***
「文化心理學」原是個標準的美國心理學現象,因為在歐洲早已有文化科學、哲學人類學、辯證科學、詮釋學、現象學、精神分析等等傳統的溫床,所以「文化心理學」這個字眼對他們而言是畫蛇添足的。但我們還必須知道,「心理學」從某個意義來說,就代表美國心理學,當它在第三世界流通時,確已造成嚴重的文化殖民現象。目前我們知道台灣和鄰近的中文社會已經發動「本土心理學」運動,企圖對抗文化殖民的勢力,而這是和「文化心理學」發展最為相近的學術運動,值得拿來討論。
這裡我要提出一個有趣的關係:文化心理學在美國的「脫胎」「叛教」,和本土心理學在華人學術圈的「去殖民」,兩者都一樣是以美國的「第一心理學」為對象的。那麼,它們之間究竟是對抗性的關係?還是會有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我們還沒看到足夠的證據來回答,但這關係的發展肯定是值得拭目以待的。馬屈(Nancy Much)曾說,每一種心理學在開始發展時都是該文化裡的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psychology),但當今的這波「文化心理學」,其實是「超文化心理學」(transcultural psychology)的意思。但我們必須注意︰和強勢的異文化站在對面而力圖抵抗,或是站在本文化中對文化提出置身在地的反省,其結果常不會相同。我們的本土心理學裡,似乎在強調前者之時,鮮少對後者加以深思。因此「超文化」的字眼可能會讓「本土派」人士覺得相當不解,或至少是不舒服。
布魯納這本書,當作是美國的本土心理學來看,應是很合適的,但我們卻必須同時瞭解:那也是他們的超文化心理學。看完之後,我們也許會對於自我批判增加一點了解——至少可以從強調實踐的「教育」那種文化裡展開。
***
這本書在翻譯進行之時,曾經用原文本在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作為「文化心理學」課程的討論材料。選課的學生很用心閱讀,我感謝他們的投入;而從他們提出的許多問題,我也感受到這本書的價值何在。我還感謝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及人文社會學院提供寬廣優游但頗有挑戰性的心智環境,使我能夠在教學研究之餘完成迻譯本書的工作。
序言
本書包括了幾篇關於教育的論文。但所談的卻不限於通常那種關於教室和學校的教育。因為,就一個文化之能引導其年輕成員進入其典律的方式來說,學校教育當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確實的,從學校教育和文化之引導其年輕人進入社群生活的必需條件來說,兩者甚至可能會背道而馳。我們這個變遷的世代有個顯著的特色,就在於一直要猜測:我們到底要期待學校為那些志願以及強迫入學的學生「做」什麼?或說,在某些給定的環境條件下,對於此事,學校到底能夠做什麼?學校的目的究竟應該是複製原有的文化,讓其中的年輕人都被「收編」(這是當今人人嫌惡的字眼)為小美國人或小日本人就好嗎?然而像收編、吸納這類概念一直到本世紀之初還是各文化之毋庸置辯的信念。或則我們可以轉口說,我們所活著的世界已經發生過種種革命性的劇變,那麼,學校是否就應該花更多心思來因應這險峻世局,或把學生推向唐吉訶德式的尋夢之途,以便讓他們在這多變的世界中仍能優游生活?但是我們怎麼決定將來的變化會產生什麼結果?這世界對他們的要求又會是什麼樣子?這些都已經不是抽象的問題了:我們已經天天都面對著這些無端的變化,而教育的論辯也就環繞著這些境況而在世間反覆迴響著。
在這些論辯之中,愈來愈清楚的是:教育並不只是傳統學校裡的那些玩意而已了,譬如課程、標準、或測驗之屬。我們在學校裡所應該作的究竟是什麼,只當放在更廣大的脈絡中,來思考社會對於年輕人所挹注的教育投資到底是為了什麼目的,然後我們才能據以理解。我們最後終會認清,對於教育之理解,乃是對於文化及其目的之理解的一個函數——當然,文化的目的是包含著文化所宣稱的部分,也包含未加言宣的部分在內。這種情形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自從像《險境中的國家》(A Nation at Risk)這樣的教育「現狀」報告以來,已經有川流不息的報告源源而出。
構成本書的各篇論文所涵蓋的題旨,無疑是超過一般談論「教育」的範圍了,但所有的討論都還是來自於同一個發源地。其中有些所反映的,確是我在過去數年中參與教育論辯時所表明的立場。不過,我寫出來的確實不只是些「論戰」之文。拿第一章來說罷,竟是論戰中的反論。寫成該章的時間晚於其他各章,而我之所以把它擺在開頭,是要用來顯現:這十年的爭辯之中,到底有哪些隱含的基本預設。
把全部論文加在一起所形成的這本書,給個總題叫做教育的文化,我覺得很合適。因為其中的核心論點乃是說:文化形塑了心靈,而文化也提供了一套工具箱,讓我們得而藉此來建構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對於自己和對於我們的力量何在之種種觀念。也許在理想上,這本書應該包含對於許多不同文化之教育的廣泛檢視,不過,對教育採取文化的觀點則並不一定要不斷從事文化間的比較。比較需要的倒是把教育和學校裡的學習看成置身在文化脈絡之中的事業。這才是我嘗試要做的工作。
安吉拉.馮.德.利珀(Angela von der Lippe)是我的朋友,也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她向我提議出書,我聽了有點猶豫。當時我的想法還在形變狀態中,因為我也和其他幾位有心人一樣,正在一心一意想建立一套嶄新的「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到了後來,把我說服的是,我終於體認:教育的問題和需要創立這種文化心理學的背景問題其實是緊密相連的——問題就是:關於意義的生成與協議,關於自我和行事感(sense of agency)的建構,關於符號技能(symbolic skills)的習得,以及尤其是關於所有心理活動之文化 「置身性」(situatedness)等等。因為除非你把文化情境以及其中的各種資源(也就是能使心靈獲得其形式和視野的東西)都放入考慮,否則你不可能理解心理活動。學習、記憶、言談、想像:所有這些都只在參與於文化之中始有可能。
一旦開始這樣想,對我而言日漸明顯的事實乃是:教育正是使文化心理學之中的觀念得以淬鍊轉生的試金石。讓我來解釋解釋吧。我們選來作為觀念試金石的東西,可以把觀念底下的預設之量塊顯現出來。譬如說,拉.梅特希(La Mettrie)那套聲名狼藉的「機械人」(L’Homme Machine)觀念使用了路易十四設置在凡爾賽宮的水力引動塑像作為他的試金石:你可有辦法以這個機械人為起點,為它裝設各種官能,使它到最終能成為有智能的生物?史金納(B. F. Skinner)的試金石則是裝在與世界隔離的史金納箱(Skinner box)中啄食的鴿子。巴列特爵士(Sir Frederic Bartlett)似乎是以聰明的板球投手來設想人類的思維活動。魏特海默(Max Wertheimer)則是以神似於小愛因斯坦的方式來試驗他的假設。但是教育實踐的試金石卻與上述各例迥然不同,因此會特別需要一種文化心理學來進行試驗。
我的預設是:人類的心理活動既不是一場獨腳戲,也不是完全孤立無助的行為,即便是發生在「腦袋裡」亦復如此。我們是能夠用顯著有效的方法來教學的唯一物種。心靈生活乃是和他人一起過的生活,是依能溝通的形式而形塑,並且是仰賴著文化的符碼、傳統等等而得以展開的。但這些事情的發生會延伸到學校之外。教育不只發生在教室裡——在晚餐的餐桌上,當全家人一起想把當天發生的事情一起弄明白時,或當兒童聚在一起想搞懂大人的世界時,或當一個徒弟和他的師傅一起參詳他們的工作時,教育就此發生。所以,要考驗某種文化心理學的話,再合適不過的方式就是教育實踐。
從我積極從事教育之後幾年開始,我把我當時認為最合理的結論寫成《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一書。三十年後的現在回顧起來,覺得當時的我所專注的研究領域乃是內在心靈歷程之中的一門獨腳戲,也就是認知歷程,而我要解決的問題則是:認知歷程如何能以合適的教育來襄助其發展。現在我可以把那些早年研究所發現的要點在此摘述一下:首先,教育中的人與人相會,應是以理解為基礎而不是以表現。理解包括掌握一個觀念或事實在一套更為一般性的知識結構之中所在的位置。當我們理解某一事物,那就是把它理解為一套更廣泛的概念原則或理論的一個實例。更且,知識本身的組織乃是:當觀念的結構被掌握時,就會使其中的特例變得更為不證自明,或乃至變為多餘。對於一個學習者來說,能學會的知識是最有用的,而當該知識是透過學習者自己的認知努力而「發現」到的,那就更是如此,因為那就會使該知識和過去習得的東西串連起來,也會在該關連狀態中使用。像這樣的發現動作會大受知識結構本身的促發,因為不管一個知識領域有多複雜,它總是可以被一套比較不那麼繁複的方式所再現,使它對人而言變得可以企及。就是這樣的結論才使我倡議道:任何題材的知識都可以某種誠實的方式教給任何年齡的任何一名兒童——雖然「誠實的」這個字眼就以沒有定義的狀態留在那裡,並且自茲而後一直縈繞在我心頭。
話說回來,這一條思考路線所隱涵的意義乃是:教學目標的訂定,其真旨不在於範圍的廣度,而在於題材的深度:需要儘可能教人學會或加以例示的,乃是一些可使各種特例都得以不證自明的普遍原則。到了此一地步,距離形塑課程整體的概念就不遠了。這裡的意思「課程整體」是指:一套螺旋形的一貫結構,其起點是對於知識領域的直觀顯示,透過反覆來回的過程而使該領域不斷依實際需要而增強,或不斷獲得更完整的表達形式。在此一版本的教育之中的教師,乃是一位通往理解的嚮導,他會幫助你,以你自己的方式而發現知識。
當然,這是因為心理學中有一段持續進展的認知革命,因而激發了我對於教育歷程所採取的研究取向——這段革命是在一九五○年代末期到一九六○年代初期開始漸趨興盛——乃至有點志得意滿的樣子。至少當時對於參與其中的我們來說,看來就是這樣。況且,當時確實也有些「外在」的紛擾會變成內在關切的前提,那就是國際的冷戰。冷戰不只是意識型態和武裝的競賽,它同時也是「科技」的戰爭。在當時,有所謂的「知識鴻溝」,而我們的學校就被指控為製造該鴻溝的罪魁禍首——我們的學校在無休無止的冷戰中,能不能夠使美國在科技上保持領先於蘇聯的地位?所以,教育改革運動的首要焦點會落在自然科學和數學上頭,那就一點也不令人驚訝了。而新興的認知心理學就是從那些學科裡採獲其原則。於是反過來說,受到這些新原則的指引,自然科學和數學類的課程果然花開滿園。所有相關的其他事情也同時被認為理所當然。譬如說,改革者假定:學校裡的學童們和製作新課程的人一樣有興趣於學會改良的課程;另一個理所當然的是:學童們生活在某種教育的真空狀態裡,絲毫不受大文化脈絡中的問題所苦。
直到「發現貧窮」以及美國民權運動的時代,我們才從自滿而又不自覺的教育改革之夢中醒來——特別是發現貧窮、異化和種族歧視對於心靈生活的衝擊有多強烈,以及這些社會疾病對於兒童成長的侵害有多深多遠。因此,一個可以用來為所有人服務的教育理論就不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定有個良性或甚至中性的文化在它的背後為其奧援。當時的我們一直認為由「文化剝奪」所造成的「赤字」,需要一些補償。而為克服這些剝奪所提議的救濟之道,最後就變成了一個叫做「起頭」(Head Start)的方案,以及另外一些類似的方案。
在那之後幾年,我發現自己對於文化在學校教育中影響學童的方式愈加投注心力。我自己的研究把我捲入問題的程度愈來愈深——我是指實驗室的嬰幼兒研究,以及在非洲學校對於心智發展的田野研究。而我其實是得道不孤。我的學生、博士後研究員、和我的研究同仁等都捲入同樣的問題;甚至在此期間的幾趟旅行都好像替我密謀出這樣的遭遇。我特別記得一次和亞力山德.陸理亞(Alexander Luria)一起作的訪問,他就是列夫.維高茨基(Lev Vygotsky)有關發展的「文化歷史」理論最投入的代言人。他對於語言和文化在心智功能上的角色作了熱切的解說,使得我對那仰之彌高的皮亞傑理論竟發生了信心動搖。皮亞傑的主張一向是更為自足、更為形式主義的理論,在其中的心智發展幾乎沒留下什麼空間可讓文化來揮灑。雖然當時的我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算不上是個維高茨基主義者,但我發現這樣的新研究對於思考教育的問題來說,卻產生了極大的幫助。不過,關於「心靈中的文化」這個議題的關切和當時的任何一個心理學「學派」都搭不上關係。確實的,它完全超過心理學,而是以當今的靈長類研究、人類學、語言學、涂爾幹式的社會學、甚至是和專研心態(mentalités)史的年鑑學派歷史學等為基礎。確實的,在過去十年以來,對於教育中的文化問題已經有些興趣開始發生了真正的復甦——不只是在理論,還包括對於教室實踐的引導論述在內。由於我在後面幾章會討論這樣的工作,所以我就不在此多談。
本書寫作期間,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我妻子的卡露.弗萊舍.費爾德曼(Carol Fleisher Feldman)正在進行一項協同研究,該研究計畫的主要題旨乃是以敘事法(narrative)來作為思考的模式和一個文化之世界觀的表達模式。我們是透過我們自己的敘事法,才能建構出我們存在於世界的一個版本,而文化就是透過它自己的敘事法才能為它的成員提供身分認同(identity)和行事權(agency)的種種模型。對於敘事法之具有核心性質的認識並不是來自於哪一個學科,而是來自於許多學科之匯流,也就是實際上的文學研究、社會-人類學研究、語言學、歷史學、心理學,乃至計算機科學。而我把這樣的匯流當作是人生的事實,也不只是在我們自己所作的敘事研究,而更要包含整個教育研究在內。
然而,就算執行了這些新方案,就算從認知革命以來有滾滾不絕的努力,但對於那些深受貧窮、歧視與異化之病所困的兒童,我們是不是真的能夠改善他們的教育呢?而為了幫助兒童走向真正能夠更新的起頭,我們是否已經發展出任何頭緒可用於重組學校的文化?要創造出一個真正能有滋養的學校文化,使所有的幼者都能有效地得利於廣大文化的資源和機會,且能由茲而增能(empowered),那麼,它需要的條件是什麼?
顯然的,對於這樣的問題不會有打包票的答案。但一定會有讓人敢確信的線索,使人能夠鼓足勇氣投注嚴肅的努力。其中最具有保證的研究之一,乃是某些用學校來進行的實驗,並在此而發展出「相互學習的文化」(mutual learning cultures)。這些教室文化的形成,最終就是為大文化脈絡如何能聚焦於教育實境之中,並以最佳、最鮮活的方式運作,而提供了模型。知識和想法是能夠相輔相成的,能夠相互支援而達成學習材料的精熟,能夠作分工和交換,也能在團隊合作的活動中反映出新的機會。而那就是關於「文化之最佳狀態」的一種可能的版本。學校,以這樣的方式重新配製之下,就必須被理解為:一方面是在整個社群心智活動之可能性的狀態下,所進行的一種意識提升操作,另方面則是獲得知識技能的手段。而教師呢,就是個(在同類人物中居於先位的)促成者。這裡所說的,只是其中一個成功的實驗,而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他的例子。
但這樣作下去,到底實際不實際?撇開學校常要背負的壓力不說,我們所謂互助社群的理想,實際上可以成功嗎?難道這只是另一個教育的烏托邦嗎?烏托邦其實不是這裡真正的議題。學校本身的功能有其強大的限制,這根本就毋庸置疑。雖然從來沒有人能自由自在地把有助有用的事情都做出來,但我們也不必把那些教育實驗者看成只會用現狀來作反射動作的呆子。我們實際上是一直在系統性地低估教育革新所帶來的衝擊。即令是那相當脆弱也飽受批評的「起頭方案」也曾經產生過驚人的結果,我們就會在本書的下文裡看到。除此之外,我們真正拿來應用的,其實還比我們所知者少得多——包括孩子們會在教室裡形成他們自己的互助社群,並且讓他們的知識表現變好,也讓他們的眼界提高。當我們把文化心理學帶入教育領域之後,我們還會學到很多其他的東西。我希望我有足夠的說服力,讓大家相信教育並沒有走入窮途末路。確實的,我們反而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我們正走在一條新路的起點上。
對於本書的整個寫作構想,我這就來說幾句話。雖然每一章都可以拿來獨立閱讀,但全部合攏起來則可以形成一種更為寬廣的觀點。該觀點乃是關於個體人(individual human)的心靈在文化所提供的能量之中如何活動的看法,這在首章中是用幾種「主張」的形式來鋪陳。接下來的一章則是對於各個主張作進一步的陳述。其中涵蓋了許多「教育的」論題——從庶民教育觀對教育的影響,到教育政策本身之內在的相悖性;從敘事法的使用,到靈長類的教育法;從「閱讀」他者的心靈,到追問我們如何將世界再現於人與人之間。涵蓋的範圍(用寫書人的老話來說),不是我的問題。我也不打算對現下教育政策的熱門話題提出很多當頭的質疑。在我們能夠對教育的文化獲致更深的理解之前,我相信對這些問題是不可能有解答的。這才是本書真正要談的東西。
我必須對於使這本書得以完成的人和機構表達我的謝意:史本賽基金會(Spencer Foundation)慨助我的研究,紐約大學心理系提供我工作的空間以及各種設備,還要特別感謝紐約大學法學院,我有機會參與其中的知識生活而獲益良多,並且我還持續以特殊身分在其中教授一門關於法律、文學、人文科學之詮釋理論的研討課,我的授課同伴是湯尼.阿姆斯特丹(Tony Amsterdam)、珮姬.戴維斯(Peggy Davis)和大維.李察茲(David Richards)——這門課裡的種種聲音在本書的每一章中都有迴響。
我把這本《教育的文化》題獻給大衛.歐爾森(David Olson),我從前的博士後研究員、長期的朋友,他是振奮我心的共謀者,也是始終不渝地來與我對談或辯論的夥伴。我想感謝的還有多位,無法在本序言裡一一舉出,但在本書的文脈之中,還會有機會再提到他們。
文化心理學對於教育本質的學術承諾
本書初版時,我在介紹中說「學術長青樹布魯納教授今年已屆八十五高齡」,但到了再版的此時,布魯納教授已經以一○一高齡,在二○一六年辭世。他所倡議發展的文化心理學,對於教育本質的探討,該從哪裡談起?
我認為可以從原本就以實踐為本質的教育那裡展開——我們似乎不應籠統地說我們要「以教育學來探討教育」,而是要「以文化心理學來探討教育的文化」。我們已談過:文化心理學必然是以本土心理學為基礎而產生的心理學下一頁,亦即它必須發展為超文化心理學(transcultural psychology)。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布魯納討論「庶民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的方式重新攤開來檢視一遍,應該不難理解此中道理。
布魯納對於庶民心理學比較集中的討論,是出現在他的《意義的行動》(Acts of Meaning)一書。他的說法是:任何文化在不經過學院式討論之前都會出現某種對於「內心」「外界」兩分的「心理學」概念,而這些概念會變成某種常識,或某種預設(presupposition),用來決定其他種種概念。但在這二分法的結構之外,還會產生某種「中介」的領域(布魯納稱此為「第二界」,所以,相對的,內心就是「第一界」,而外界就是「第三界」),各個文化對此一領域的認知深淺和多寡都會有很多差異,因此,當我們對原有的二分法的結構有所知悉之後,我們要設法瞭解其「第二界」的實際內容,甚至要為原先所缺乏的瞭解而大力補充其內容,譬如從第一界到第三界之間的交通究竟是透過超自然巫術的方式、人文溝通和想像的方式,或科學假設和考驗的方式等等,而這樣的補充可以包括釐清,也可以包括改寫。於是經過這道手續之後,原先的「庶民心理學」就必然會轉化為「文化心理學」。至於這種轉化為何會發生,我們很難用民族文化的「本土性」來解釋,而必須將它放進社會-歷史演化的過程——特別是異文化間的接觸過程——才足以理解。
這種庶民心理學的討論最有助於我們判斷「本土心理學」究竟是不是「文化心理學」的地方,不在於區分所謂的「本位/客位」,而在於揭示那個中間「第二界」之必然存在——無論你對它是有意識或無意識。
***
二○○九年我去開封參加過一次「中國心理學會:全國心理學學術會議」。在會中極有意思的發現是:當時我參加的「理論心理學組」裡也還沒人提過「文化心理學」,但很多學者、學生都知道台灣有「本土心理學」。不過,大多數的與會者已經不談「本土心理學」,而換上不用任何主張就能朗朗上口的「中國心理學」,並且這種話語也已經是屬於「元理論」(後設理論)的層次,也就是說:在談文化是什麼之前,大家對於文化早已有個共識,那就是「中國文化 vs. 西方文化」的提法,也認為那是個不證自明的「理論架構」。所有的人(除了極少數例外)都認定了文化差異的命題,並且也認定西方理論的缺陷可以用中國理論予以補足。像這樣的共識,在台灣竟然動用過一個「大型研究計畫」(也就是「本土心理學研究計畫」)才能為此做出勉強的肯定。我之所以要這樣提,是因為隔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的《民族教育研究》期刊編輯輾轉來信向我邀稿,他就特別聲稱:大陸學界至當年還很少人知道有「文化心理學」的存在,而我在九年之前已經翻譯介紹了布魯納的作品,實在很令人驚奇。但我也要提出我在「中國心理學」中的驚奇發現:在台灣,我從來沒聽過任何學術人使用過「心理學的學科承諾」這樣的說法,而在那次的會場上卻三番兩次聽到一些有心於學術發展或改革的人會用「學科承諾」來標示他們針對此承諾應該提出什麼改革方案。所以,我現在要以兩岸學術觀察的角度,來談談文化心理學可能的「學科承諾」會是什麼。
嚴格來說,「文化心理學」在現有的心理學學術建制中還算不上是一門「學科」,而比較像是一種「學說」。具體的證據是:即令在美國學界,至今也還沒出現一本適合作為大學本科教科書的「文化心理學概論」之類作品,所以,就學科而言,它頂多是個「發展中」的學科。但我們要談的重點是在於知識本身的「承諾」問題。對此,布魯納有一種討論的方式,是出現在《實作的心靈,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一書中的第九章「教育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文中敘述了一名女生在聽到他所主張的「任何題材都可以教給任何年齡的兒童,假若我們能採取某種誠實的知識形式」之後,她採取相當積極的態度逼問道:如何才能保證那種知識形式是「誠實的」?布魯納承認他用了自己以前說過的一些教學程序和方法來回答問題,但事後,他自己覺得非常心虛,因為他知道那不是那位女生想要的答案。而他的想法是:我們必須回到「語言」本身來回答這問題。我們使用的語言其實都具有「兩面人」的性格(也就是說:不容易用「誠實」與否來形容它)。語言一直同時具有雙重功能:它一方面是一種溝通的模式,另方面也就是它所代表的世界觀之如實呈現。
為了要具體說明這個意思,他引用了法國作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thes)寫的一篇短文〈法國玩具〉來呈現,大意是說:法國小孩所玩的玩具,除了極少數例外(譬如積木),大多數都是在呈現大人的慾望、大人的需求、大人對世界的理解,並且還一概是採取「消費者」角度來獲取以及使用那些玩具:戰爭、官僚、美醜、外星人等等。孩子們不只是在玩玩具,他們得同時「消費」這種「溝通工具」中所承載的整套世界觀。所以,所有的法國小孩將來長大後就自然會成為一個個加味調理的法國世界觀和法國自我。布魯納對於羅蘭.巴特這位「精雕細琢的自嘲大師」除了讚揚有加之外,當然也立刻知道了美國人和美國教育缺乏批判自省的問題——大家都只看到教育語言似乎積極的一面,而忽視了以批判態度來如實呈現其另一面。
法國也好,美國也好,對我們而言,重要的理解一定也會在反身自省中以批判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所說的華人、中國人或什麼本土,以及我們所使用的漢語本身,到底攜帶了多少不能被我們自己用「自嘲」來發現的世界觀?我們恐怕都只是汲汲於利用「本土心理學」、「華人心理學」、「中國心理學」這些名義來「發揚」自己的文化,卻不太會同時反省這些文化內容裡可能隱含的偏見和盲點——特別是那些被革命者所詛咒,但同時也完全繼承下來的「封建社會關係」、「官僚主義思維」,以及不知是褒是貶的所謂「集體主義文化」——這就是我所謂的兩岸同步觀察。一旦我們真的也都同時發現這些問題,那麼,我們不得不把以上所有的「發揚式學科」提升成為「批判的下一頁」:文化心理學為了要超越傳統思維的限制,必須邁向更為「誠實」的教育。換句話說,我們要讓學問發達到這樣的程度,才能說它是在完成它自己的承諾。
關於「學科承諾」,我們還需要一個更為基本的說法——能「承」擔起知識發展,能給出思考的「諾」言者,並不總是已經完成建制的學科,而是在思考中、也能不斷思考的學者。譬如布魯納這位老教授,他在《教育的文化》一書六、七兩章所談的「敘事法」,總有些讀者和評論者認為他的表達意猶未盡。於是,布魯納在六年之後,集結他在紐約市立大學法學院的授課心得,對敘事法的問題再作了一次更徹底的發揮,讓敘事法成為解決文化衝突的一種基本手段:
任何一個人類文化,在其本性中,既是對於社群生活(之難題)的一種解決之道,而隱 含在此之下的,則是對於生活在此(文化)界限之內者所提出的威脅與挑戰。如果一個文化要存活下去,它就需要一些手段來處理這些埋在社群生活之下的利益衝突……。
這種敘事法的學說,對於想瞭解自身所處的文化者而言,實具有普世性的意義,而不管這是美國教授或法國作家所提的理論,一旦我們有所理解,我們也就同時知道了他們是在承擔什麼知識,以及給出什麼諾言。這樣的承諾,讓我們更能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我們只要能讀到這樣的書,我們就是文化遺產的受益者——為什麼我們不能拋棄本位主義,來迎接所有的知識遺產呢?而在這種受益狀態中,你能不感謝像布魯納這位「非本土的」知識開發者嗎?
***
最後還特別要感謝楊茂秀教授,他不但在最初推薦我翻譯此書,也促成了本書的再版。我把全書重讀了一遍,儘量作了目前知識狀態最可能的修訂。雖還不可能完備,但就是盡了最大的可能。
宋文里
2018年
譯者導言
布魯納的轉變是心理學及教育學界中很引人注意的話題。論述學派的大將哈瑞(Rom Harré)曾說:這是個「很令人欣喜的諷刺」——「布魯納是曾參與第一次認知革命的建築師,但卻也是第二次認知革命中最活躍的份子和最具原創性的發言人之一。」學術長青樹布魯納教授今年已屆八十五高齡,而正用他自己的生命史來見證某種意義的心理學術發展史。
一九五六年,布魯納和兩位合作者出版了《思維的研究》(A Study of Thinking)一書,用結構發展論向當時的主流,也就是行為主義和刺激-反應的學習理論,提出直接的挑戰。自茲而後,對於認知、思維和心智的心理學研究逐漸取代非心靈論,並且使心智的形式結構和計算機科學的人工智慧理論合流而逐漸形成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這就是「第一次認知革命」的意思。是的,布魯納在一九六○年出版了《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一書,更使之成為代表皮亞傑結構理論而成為發展心理學的經典之作。但是,他在享譽三十年之後,竟從根柢上轉向另一個知識典範,也就是維高茨基(Lev Vygotsky)的社會歷史心理學(socio-historical psychology),或就叫文化論(culturalism)。所謂的「第二次認知革命」事實上就是指文化論在人的科學(human science)之中的發展,它到目前都還在默默地進行中——十幾年來,有一支逐漸成形的心理學,叫做「文化心理學」,正反映了這場無聲的革命。我們可以說:「第一次認知革命」把認知研究帶進來,然而 「第二次認知革命」卻正要把認知帶出去。
出去哪裡呢?用我們對於成長的一句俗話來說罷——出社會!首先要把心理學裡的個體主義予以徹底社會化,要揉合置身在地(situated)的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理論,然後要從二十世紀語言哲學的人文研究裡取出最為核心的方法論——敘事法(narrative)和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來安置這種社會化過程。這「社會化」對心理學來說,至少有兩個意思,一是說:長期以來心理學被視為「非社會的社會科學」(nonsocial social science),因此,它終究難免會產生內在的反省動力來改變它的體質;其次,它毋寧更像是說:心理學需要「社會學化」,因為布魯納在提出這個轉向的新名稱(也就是「文化-心理取向」,或「文化心理學」)之時,他一方面建議讀者參看一些屬於這種努力的新作,另方面則說,這些作品的古典源流應是維高茨基、涂爾幹(Emile Durkheim)、舒茲(Alfred Schutz)以及韋伯(Max Weber)。
個體性和社會化之間為什麼不能各安其所?譬如說,心理學是研究個體性和心靈本質的心理學,而社會學是研究社會體制和社會化的社會學,為什麼要讓它們之間形成像知識演化一樣的過渡關係?為了解釋這種關係,布魯納有句箴言似的說法:「心靈之獨特奧祕,就在於它本具有隱私性且稟賦著主觀性,但儘管它有那麼多隱私,心靈還是不斷創生了公共的產物」——這「公共的產物」就是指在世界之中透過符號系統(譬如語言)而保存和傳達的公用知識。事實上,心理學仍是心理學,但對於「心靈」這個概念,以及承載心靈的那個本體,我們不能再簡單地說:那不就是個人嗎!不是的。教育學長久以來仰賴心理學來界定教育的主體。當心理學不能理解「社會主體」或「文化主體」的存在樣態時,我們的整套知識體系通過各級學校教育而把我們歪曲地模塑成「個體主義」的樣子。然後我們會發現個體主義和社會/文化的運作之間,有極不諧和的關係,更嚴重一點說,竟會造成像「右派/左派」那樣的意識型態衝突。處在這種思想衝突中而茫然無解,於是教育變成了相當虛無主義的飄渺幻境。咱們這樣說吧:社會運作的根本機制是合作,為什麼我們的學生竟要被切割成離子化的個體,永遠只能一個一個分開來考核?
***
我從進入九○年代之後才開始斷斷續續聞到這股新心理學的味道,但是在世界邊陲的台灣,我還得一直懷疑是不是我的嗅覺器官患了過敏的疾病。一九九三~九四年之間,我有機會到哈佛大學進修一年,雖然在計畫中我要作的研究不是這種心理學,但無論如何,我買到兩本布魯納的新作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1986),以及Acts of Meaning(1990),從而真正注意到這樣的發展。經過這十年的探索,我發現「文化心理學」和我原來所知的心理學實在差距太遠,也自認為無法以自己的說明來把這種帶有革命性內涵的轉變交代清楚,因此我就一直轉著一個念頭,要用譯書的方式來向中文世界作引介的工作。雖然我知道「文化心理學」是許許多多數不清路數的人文知識和心理學的重新結合,而布魯納也不完全代表這種發展,但是,因緣和合,一九九九年,我的一位好友楊茂秀教授竟然說,他正在替出版社物色一個譯書人,就是要譯布魯納這本更近期的作品。
***
我就從布魯納講起也罷。根據我對本書論證脈絡的理解,用這篇短短的導言,也許可以為布魯納這種「文化心理學」做個起碼的說明。
本書的第一章,開宗明義地用計算論(computationalism)和文化論(culturalism)的對比來說明個體主義和人工智慧理論在教育上根本行不通之處。計算機,就是俗話說的電腦,已經輕易取得了當代知識的主導地位——不論就知識處理的技術來說,或就它所形成的隱喻來說皆然。我這樣想:如果我們去買電腦,我們知道每一部電腦是用許多零件組裝而成,然後我們給它「灌進」需用的軟體,測試它的各種功能,沒出問題,這就成交了。但你怎麼知道它沒問題?因為測試有個標準程序,既然能通過,就是沒問題。那麼你怎麼知道那個程序是標準的?因為各零件硬體和各使用軟體之間連接得是否正常,在螢幕上可以完全表現。這整套關係形成一種「完整形式」,所以我們把它定義為「標準」和「沒問題」。在一定的程序和有限的表現上,就可以看出來——這是「每一部」電腦測試的基本邏輯,不可能有例外。但是心靈的硬體零件是什麼?它被灌進了什麼軟體?你又從哪裡看出它的表現?這每一題的答案都是不確定。而最糟的是,在企圖測試之時,連品管師都不得不承認,他要測試的對象總是會不斷反映著測試者的自己——在測試者和被測試的對象之間,通常沒有確定的標準,也沒有所謂「完整形式」的字典或測試手冊可以翻閱。即使勉強編出這樣的手冊,那編者還是得承認,這只是「不完整」或永無完整性的參考文件而已。在心靈的品管師和對象之間不可能有測試(testing)的關係,而只能有關聯(relating)和摸索(exploring)的「不完整」關係——人必須用意欲(intention)來超過他自己,然後和他人的意欲形成交互關聯的關係,而在意欲和意欲之間,也就是在心靈和他者心靈(other minds)之間,只有摸索而不會有確定的關係。
關聯和摸索的關係方式,在人類之間就叫做「生活在一起」,或叫做「社會/文化」。有一種特別的「社會/文化」生活,是專指發生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那就是養育(rearing)。而經過特殊的分工之後,我們把其中的符號性成分區分出來,用特殊的社會體制來加以經營處理,就約莫是「教學」(teaching/learning)的樣子,但通常會有個更抽象的系統名稱,叫做「教育」。而即使是這樣說,也是要強調這過程一點也不簡單,至少不是像生產線(裝配線)那麼簡單——用一條線就可以直指向目標。教育是社會體制,是文化的自我摸索和自我生產,所以它會經歷一些生活者對自身的定義,這是在「庶民理論」(folk theory)裡頭可以看出來的。而我們的種種教育理論模型就是建立在庶民理論所種植的前提之上。要隨著庶民理論-教育模型來做個綜述時,也會發現它們的「目標」各自相異,很難確定,甚至是充滿著相互悖謬的關係,譬如特殊主義/普同主義,個體智能/文化工具學習,開發創造/複製傳統等等這幾套悖論,以及永遠的爭議,這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的邏輯。
回到文化心理學的重新反省,教育的起點確實包含著個人的行事自主(agency)、反身自省(reflection)以及人類的公有文化、協同合作這些理念之間的關係。所以第四章要把這些關係重新整合成一張理解教育的全圖,並且用時間的延續來作為整合的基礎。最重要的時間是現在,而不是過去——因為參與過去就是進入已經形成的固定意義,而參與現在則當下面臨了意義的不確定。對「現在」的重新發現,也就是理解人如何和他的文化有「置身在地」的關係,會因而發現文化之不斷處於形塑之中的樣貌。對於「置身在地」的當事人而言,他是和「未來」形影不離的,但布魯納不說那是「未來」,而寧稱之為「可能」(the possible)。在教育中,以當前問題為教材,用文化所能提供的一切裝備和社會一切的組織合作方式去對付問題,那才是時間延續和文化整合的教育。
重省之後的教育所重者不在於個體心靈的表現,而在於發現人類心靈具有「從我至他」的一貫脈絡。心靈和「理論」是一體兩面。理論就是建構的理解,而理解有兩種不同的形式,那就是因果解釋(explanation)和意義詮釋(interpretation)。教育之中的學習不只是學習客觀的事物,學會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還要學習「學習本身」,也就是用理論的理解來學習心靈的理論,用詮釋來學習事物如何被賦予意義,簡單地說,這就是「以心學心、知己知彼」。一旦有此可能,於是自我之心和他者之心就會具有同形同構的關係。這是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問題,也是第五章的核心。
「計算論/文化論」以及「解釋/詮釋」這樣的對比,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量之為物(quanta)/質之為物(qualia)」的基本問題。當然在通俗的理解(也一定是一種庶民理論吧?)之中,甚至還會以為這是「科技/人文」對比的問題。這種談法已是每況愈下、不知所終。布魯納認為:如果科技是心靈的問題,是教師和學生心靈之間交會的問題,那麼科技無論如何是得在某種非科技的理解方式中存在。科技本身的解釋語言是特殊的人工語言(譬如數學),但敘述科技的語言則是日常語言,而它的方法是敘事法,也就是講故事的方法。以故事結構為襯托,才會有科學內容的存在。那麼故事是怎麼講的?敘事法可是人類文化的一大成就——早在科學誕生之前,人類就一直在講故事,也靠著講故事來傳遞文化生活的種種理解,包括神話、歷史、法律和哲學,無不如此。於是在當代文學和史學理論的捉摸下,敘事法的真髓益發為人知曉。第六章到第七章的脈絡告訴我們,怎樣讓敘事法成為教育者真正的看家本事。
置身在地的經驗還孕生一種比理論更為細膩的知識——實踐的知識,或說是行動中的知識。這種知識並非特別有別於理論知識,而應該說,在心理發展的過程中,最先發展的應是行動中的知識,後來逐漸生出替代行動的知識模式,最後生出符號性的替代,而完全可供作理論之用。這是第八章所要談的意思。
最後一章,布魯納回頭看心理學本身的發展。他以「生物性的限制-文化建構-置身在地的實踐」這樣的三角模型來總結自己的理論,也說這就是他所倡議的「文化心理學」。對生物性限制的重視呼應了文化心理學之前的心理學,但是加上文化建構的理解,使心理學開始走向社會化的下一頁,而實踐知識則又更進一步把知識主體和主體所在的文化/社會脈絡聯貫成一氣。布魯納的預言是:下一世紀的心理學必當如是。從某一角度來說,這樣的話又必定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學者在晚年的化境之中才能說得出來。
***
布魯納在本書中曾經提到,有些心理學家還轉變到更為基進的文化論,譬如葛根(Kenneth Gergen)和哈瑞,而根據我的了解,後面這兩位所代表的是後結構主義哲學潮流下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和論述心理學(discursive psychology)。在當今的文化心理學發展中,他們和布魯納一樣受人矚目,甚至更代表下一代文化心理學的發展。一九九六年在英國創立的期刊《文化與心理學》(Culture and Psychology),事實上幾乎可說是建構主義和論述心理學的天下,而美國的「文化心理學」反而成為其中的一個支流。
我從一九九五年決定開始開授「文化心理學」課程時,確實是以較為基進的葛根和哈瑞來開頭的,因為我記得培根(Francis Bacon)說過︰你想把已經偏斜的桿子校正,那就一定得用矯枉過正的辦法,才能使它彈回原位。在那段時間,很多新心理學冒出來,哈瑞等人主編的《反思心理學》(Rethinking Psychology)一書正反映了那時候百家爭鳴的情景。但這些心理學都帶有一種意味,我用另一位維高茨基的信徒柯爾(Michael Cole)來說明——他把文化心理學稱為「第二心理學」(second psychology),我相當同意,因為它表明了從原來的「第一心理學」中脫胎換骨,而不再屬於同樣知識體系的意思。席尉德(Richard Shweder)說得更清楚:文化心理學不是普通心理學(general psychology)、不是跨文化心理學(cross-cultural psychology)、不是心理人類學(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也不是民族心理學(ethnopsychology)。那麼,在席尉德心目中,文化心理學是什麼?那就是通過以上四種「不是」而形成的某種叛教(heretical)轉向,它形成一種「重新萌生的學科」(reemerging discipline),它反對普同主義的心靈論,反對心靈統一體(psychic unity)的想法,而主張邁入個別生活脈絡中尋求心靈的種種特殊表現。這意思是:只有文化實踐中的心靈,而沒有特別可以從文化脈絡中抽繹而出的心靈抽象物;只有在意欲之中的心靈,而沒有不動的心靈。這樣的脫胎換骨確實是徹底的,所謂「基進」也者,正是這個意思。
相對而言,在我看來,布魯納所發展的就不是那麼基進的論述。他強調解釋和理解是兩種各自成立的思維模式,而皮亞傑和維高茨基是兩種互補的典範。除此之外,對於生物天性的因素,他認為必須保留。不過,這並不是折衷主義。在這樣溫和的表面之下,布魯納其實都表示了兩種堅持︰第一是,後者不能化約為前者,理解不是解釋的暖身操,維高茨基不是皮亞傑的衍生物;其二,我們之所以能看出第二種、第二階的性質,是以第一種、第一階的知識作返身自省的結果。就拿「生物性」的議題來說吧,文化論者不把生物天性視為人類發展的上限,而是下限。人類生來是未完成的動物,只有靠文化才能把自己製作完成。這樣的論述方式,雖然並不基進,但可稱是諄諄善誘;雖然語不驚人,但卻一直堅定地導向那場無聲的革命。
所以,有此理解之後,我也開始把徹底文化論的論述基調轉換成較為溫和的演奏。譬如說,我決定要在我的課程裡增加一些關於靈長類研究的單元,讓學生一邊觀看黑猩猩行為,一邊想想文化從哪裡開始。
***
「文化心理學」原是個標準的美國心理學現象,因為在歐洲早已有文化科學、哲學人類學、辯證科學、詮釋學、現象學、精神分析等等傳統的溫床,所以「文化心理學」這個字眼對他們而言是畫蛇添足的。但我們還必須知道,「心理學」從某個意義來說,就代表美國心理學,當它在第三世界流通時,確已造成嚴重的文化殖民現象。目前我們知道台灣和鄰近的中文社會已經發動「本土心理學」運動,企圖對抗文化殖民的勢力,而這是和「文化心理學」發展最為相近的學術運動,值得拿來討論。
這裡我要提出一個有趣的關係:文化心理學在美國的「脫胎」「叛教」,和本土心理學在華人學術圈的「去殖民」,兩者都一樣是以美國的「第一心理學」為對象的。那麼,它們之間究竟是對抗性的關係?還是會有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我們還沒看到足夠的證據來回答,但這關係的發展肯定是值得拭目以待的。馬屈(Nancy Much)曾說,每一種心理學在開始發展時都是該文化裡的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psychology),但當今的這波「文化心理學」,其實是「超文化心理學」(transcultural psychology)的意思。但我們必須注意︰和強勢的異文化站在對面而力圖抵抗,或是站在本文化中對文化提出置身在地的反省,其結果常不會相同。我們的本土心理學裡,似乎在強調前者之時,鮮少對後者加以深思。因此「超文化」的字眼可能會讓「本土派」人士覺得相當不解,或至少是不舒服。
布魯納這本書,當作是美國的本土心理學來看,應是很合適的,但我們卻必須同時瞭解:那也是他們的超文化心理學。看完之後,我們也許會對於自我批判增加一點了解——至少可以從強調實踐的「教育」那種文化裡展開。
***
這本書在翻譯進行之時,曾經用原文本在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作為「文化心理學」課程的討論材料。選課的學生很用心閱讀,我感謝他們的投入;而從他們提出的許多問題,我也感受到這本書的價值何在。我還感謝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及人文社會學院提供寬廣優游但頗有挑戰性的心智環境,使我能夠在教學研究之餘完成迻譯本書的工作。
宋文里
2000年11月
寫於新竹,清華大學
2000年11月
寫於新竹,清華大學
序言
本書包括了幾篇關於教育的論文。但所談的卻不限於通常那種關於教室和學校的教育。因為,就一個文化之能引導其年輕成員進入其典律的方式來說,學校教育當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確實的,從學校教育和文化之引導其年輕人進入社群生活的必需條件來說,兩者甚至可能會背道而馳。我們這個變遷的世代有個顯著的特色,就在於一直要猜測:我們到底要期待學校為那些志願以及強迫入學的學生「做」什麼?或說,在某些給定的環境條件下,對於此事,學校到底能夠做什麼?學校的目的究竟應該是複製原有的文化,讓其中的年輕人都被「收編」(這是當今人人嫌惡的字眼)為小美國人或小日本人就好嗎?然而像收編、吸納這類概念一直到本世紀之初還是各文化之毋庸置辯的信念。或則我們可以轉口說,我們所活著的世界已經發生過種種革命性的劇變,那麼,學校是否就應該花更多心思來因應這險峻世局,或把學生推向唐吉訶德式的尋夢之途,以便讓他們在這多變的世界中仍能優游生活?但是我們怎麼決定將來的變化會產生什麼結果?這世界對他們的要求又會是什麼樣子?這些都已經不是抽象的問題了:我們已經天天都面對著這些無端的變化,而教育的論辯也就環繞著這些境況而在世間反覆迴響著。
在這些論辯之中,愈來愈清楚的是:教育並不只是傳統學校裡的那些玩意而已了,譬如課程、標準、或測驗之屬。我們在學校裡所應該作的究竟是什麼,只當放在更廣大的脈絡中,來思考社會對於年輕人所挹注的教育投資到底是為了什麼目的,然後我們才能據以理解。我們最後終會認清,對於教育之理解,乃是對於文化及其目的之理解的一個函數——當然,文化的目的是包含著文化所宣稱的部分,也包含未加言宣的部分在內。這種情形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自從像《險境中的國家》(A Nation at Risk)這樣的教育「現狀」報告以來,已經有川流不息的報告源源而出。
構成本書的各篇論文所涵蓋的題旨,無疑是超過一般談論「教育」的範圍了,但所有的討論都還是來自於同一個發源地。其中有些所反映的,確是我在過去數年中參與教育論辯時所表明的立場。不過,我寫出來的確實不只是些「論戰」之文。拿第一章來說罷,竟是論戰中的反論。寫成該章的時間晚於其他各章,而我之所以把它擺在開頭,是要用來顯現:這十年的爭辯之中,到底有哪些隱含的基本預設。
把全部論文加在一起所形成的這本書,給個總題叫做教育的文化,我覺得很合適。因為其中的核心論點乃是說:文化形塑了心靈,而文化也提供了一套工具箱,讓我們得而藉此來建構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對於自己和對於我們的力量何在之種種觀念。也許在理想上,這本書應該包含對於許多不同文化之教育的廣泛檢視,不過,對教育採取文化的觀點則並不一定要不斷從事文化間的比較。比較需要的倒是把教育和學校裡的學習看成置身在文化脈絡之中的事業。這才是我嘗試要做的工作。
安吉拉.馮.德.利珀(Angela von der Lippe)是我的朋友,也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她向我提議出書,我聽了有點猶豫。當時我的想法還在形變狀態中,因為我也和其他幾位有心人一樣,正在一心一意想建立一套嶄新的「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到了後來,把我說服的是,我終於體認:教育的問題和需要創立這種文化心理學的背景問題其實是緊密相連的——問題就是:關於意義的生成與協議,關於自我和行事感(sense of agency)的建構,關於符號技能(symbolic skills)的習得,以及尤其是關於所有心理活動之文化 「置身性」(situatedness)等等。因為除非你把文化情境以及其中的各種資源(也就是能使心靈獲得其形式和視野的東西)都放入考慮,否則你不可能理解心理活動。學習、記憶、言談、想像:所有這些都只在參與於文化之中始有可能。
一旦開始這樣想,對我而言日漸明顯的事實乃是:教育正是使文化心理學之中的觀念得以淬鍊轉生的試金石。讓我來解釋解釋吧。我們選來作為觀念試金石的東西,可以把觀念底下的預設之量塊顯現出來。譬如說,拉.梅特希(La Mettrie)那套聲名狼藉的「機械人」(L’Homme Machine)觀念使用了路易十四設置在凡爾賽宮的水力引動塑像作為他的試金石:你可有辦法以這個機械人為起點,為它裝設各種官能,使它到最終能成為有智能的生物?史金納(B. F. Skinner)的試金石則是裝在與世界隔離的史金納箱(Skinner box)中啄食的鴿子。巴列特爵士(Sir Frederic Bartlett)似乎是以聰明的板球投手來設想人類的思維活動。魏特海默(Max Wertheimer)則是以神似於小愛因斯坦的方式來試驗他的假設。但是教育實踐的試金石卻與上述各例迥然不同,因此會特別需要一種文化心理學來進行試驗。
我的預設是:人類的心理活動既不是一場獨腳戲,也不是完全孤立無助的行為,即便是發生在「腦袋裡」亦復如此。我們是能夠用顯著有效的方法來教學的唯一物種。心靈生活乃是和他人一起過的生活,是依能溝通的形式而形塑,並且是仰賴著文化的符碼、傳統等等而得以展開的。但這些事情的發生會延伸到學校之外。教育不只發生在教室裡——在晚餐的餐桌上,當全家人一起想把當天發生的事情一起弄明白時,或當兒童聚在一起想搞懂大人的世界時,或當一個徒弟和他的師傅一起參詳他們的工作時,教育就此發生。所以,要考驗某種文化心理學的話,再合適不過的方式就是教育實踐。
從我積極從事教育之後幾年開始,我把我當時認為最合理的結論寫成《教育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一書。三十年後的現在回顧起來,覺得當時的我所專注的研究領域乃是內在心靈歷程之中的一門獨腳戲,也就是認知歷程,而我要解決的問題則是:認知歷程如何能以合適的教育來襄助其發展。現在我可以把那些早年研究所發現的要點在此摘述一下:首先,教育中的人與人相會,應是以理解為基礎而不是以表現。理解包括掌握一個觀念或事實在一套更為一般性的知識結構之中所在的位置。當我們理解某一事物,那就是把它理解為一套更廣泛的概念原則或理論的一個實例。更且,知識本身的組織乃是:當觀念的結構被掌握時,就會使其中的特例變得更為不證自明,或乃至變為多餘。對於一個學習者來說,能學會的知識是最有用的,而當該知識是透過學習者自己的認知努力而「發現」到的,那就更是如此,因為那就會使該知識和過去習得的東西串連起來,也會在該關連狀態中使用。像這樣的發現動作會大受知識結構本身的促發,因為不管一個知識領域有多複雜,它總是可以被一套比較不那麼繁複的方式所再現,使它對人而言變得可以企及。就是這樣的結論才使我倡議道:任何題材的知識都可以某種誠實的方式教給任何年齡的任何一名兒童——雖然「誠實的」這個字眼就以沒有定義的狀態留在那裡,並且自茲而後一直縈繞在我心頭。
話說回來,這一條思考路線所隱涵的意義乃是:教學目標的訂定,其真旨不在於範圍的廣度,而在於題材的深度:需要儘可能教人學會或加以例示的,乃是一些可使各種特例都得以不證自明的普遍原則。到了此一地步,距離形塑課程整體的概念就不遠了。這裡的意思「課程整體」是指:一套螺旋形的一貫結構,其起點是對於知識領域的直觀顯示,透過反覆來回的過程而使該領域不斷依實際需要而增強,或不斷獲得更完整的表達形式。在此一版本的教育之中的教師,乃是一位通往理解的嚮導,他會幫助你,以你自己的方式而發現知識。
當然,這是因為心理學中有一段持續進展的認知革命,因而激發了我對於教育歷程所採取的研究取向——這段革命是在一九五○年代末期到一九六○年代初期開始漸趨興盛——乃至有點志得意滿的樣子。至少當時對於參與其中的我們來說,看來就是這樣。況且,當時確實也有些「外在」的紛擾會變成內在關切的前提,那就是國際的冷戰。冷戰不只是意識型態和武裝的競賽,它同時也是「科技」的戰爭。在當時,有所謂的「知識鴻溝」,而我們的學校就被指控為製造該鴻溝的罪魁禍首——我們的學校在無休無止的冷戰中,能不能夠使美國在科技上保持領先於蘇聯的地位?所以,教育改革運動的首要焦點會落在自然科學和數學上頭,那就一點也不令人驚訝了。而新興的認知心理學就是從那些學科裡採獲其原則。於是反過來說,受到這些新原則的指引,自然科學和數學類的課程果然花開滿園。所有相關的其他事情也同時被認為理所當然。譬如說,改革者假定:學校裡的學童們和製作新課程的人一樣有興趣於學會改良的課程;另一個理所當然的是:學童們生活在某種教育的真空狀態裡,絲毫不受大文化脈絡中的問題所苦。
直到「發現貧窮」以及美國民權運動的時代,我們才從自滿而又不自覺的教育改革之夢中醒來——特別是發現貧窮、異化和種族歧視對於心靈生活的衝擊有多強烈,以及這些社會疾病對於兒童成長的侵害有多深多遠。因此,一個可以用來為所有人服務的教育理論就不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定有個良性或甚至中性的文化在它的背後為其奧援。當時的我們一直認為由「文化剝奪」所造成的「赤字」,需要一些補償。而為克服這些剝奪所提議的救濟之道,最後就變成了一個叫做「起頭」(Head Start)的方案,以及另外一些類似的方案。
在那之後幾年,我發現自己對於文化在學校教育中影響學童的方式愈加投注心力。我自己的研究把我捲入問題的程度愈來愈深——我是指實驗室的嬰幼兒研究,以及在非洲學校對於心智發展的田野研究。而我其實是得道不孤。我的學生、博士後研究員、和我的研究同仁等都捲入同樣的問題;甚至在此期間的幾趟旅行都好像替我密謀出這樣的遭遇。我特別記得一次和亞力山德.陸理亞(Alexander Luria)一起作的訪問,他就是列夫.維高茨基(Lev Vygotsky)有關發展的「文化歷史」理論最投入的代言人。他對於語言和文化在心智功能上的角色作了熱切的解說,使得我對那仰之彌高的皮亞傑理論竟發生了信心動搖。皮亞傑的主張一向是更為自足、更為形式主義的理論,在其中的心智發展幾乎沒留下什麼空間可讓文化來揮灑。雖然當時的我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算不上是個維高茨基主義者,但我發現這樣的新研究對於思考教育的問題來說,卻產生了極大的幫助。不過,關於「心靈中的文化」這個議題的關切和當時的任何一個心理學「學派」都搭不上關係。確實的,它完全超過心理學,而是以當今的靈長類研究、人類學、語言學、涂爾幹式的社會學、甚至是和專研心態(mentalités)史的年鑑學派歷史學等為基礎。確實的,在過去十年以來,對於教育中的文化問題已經有些興趣開始發生了真正的復甦——不只是在理論,還包括對於教室實踐的引導論述在內。由於我在後面幾章會討論這樣的工作,所以我就不在此多談。
本書寫作期間,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我妻子的卡露.弗萊舍.費爾德曼(Carol Fleisher Feldman)正在進行一項協同研究,該研究計畫的主要題旨乃是以敘事法(narrative)來作為思考的模式和一個文化之世界觀的表達模式。我們是透過我們自己的敘事法,才能建構出我們存在於世界的一個版本,而文化就是透過它自己的敘事法才能為它的成員提供身分認同(identity)和行事權(agency)的種種模型。對於敘事法之具有核心性質的認識並不是來自於哪一個學科,而是來自於許多學科之匯流,也就是實際上的文學研究、社會-人類學研究、語言學、歷史學、心理學,乃至計算機科學。而我把這樣的匯流當作是人生的事實,也不只是在我們自己所作的敘事研究,而更要包含整個教育研究在內。
然而,就算執行了這些新方案,就算從認知革命以來有滾滾不絕的努力,但對於那些深受貧窮、歧視與異化之病所困的兒童,我們是不是真的能夠改善他們的教育呢?而為了幫助兒童走向真正能夠更新的起頭,我們是否已經發展出任何頭緒可用於重組學校的文化?要創造出一個真正能有滋養的學校文化,使所有的幼者都能有效地得利於廣大文化的資源和機會,且能由茲而增能(empowered),那麼,它需要的條件是什麼?
顯然的,對於這樣的問題不會有打包票的答案。但一定會有讓人敢確信的線索,使人能夠鼓足勇氣投注嚴肅的努力。其中最具有保證的研究之一,乃是某些用學校來進行的實驗,並在此而發展出「相互學習的文化」(mutual learning cultures)。這些教室文化的形成,最終就是為大文化脈絡如何能聚焦於教育實境之中,並以最佳、最鮮活的方式運作,而提供了模型。知識和想法是能夠相輔相成的,能夠相互支援而達成學習材料的精熟,能夠作分工和交換,也能在團隊合作的活動中反映出新的機會。而那就是關於「文化之最佳狀態」的一種可能的版本。學校,以這樣的方式重新配製之下,就必須被理解為:一方面是在整個社群心智活動之可能性的狀態下,所進行的一種意識提升操作,另方面則是獲得知識技能的手段。而教師呢,就是個(在同類人物中居於先位的)促成者。這裡所說的,只是其中一個成功的實驗,而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他的例子。
但這樣作下去,到底實際不實際?撇開學校常要背負的壓力不說,我們所謂互助社群的理想,實際上可以成功嗎?難道這只是另一個教育的烏托邦嗎?烏托邦其實不是這裡真正的議題。學校本身的功能有其強大的限制,這根本就毋庸置疑。雖然從來沒有人能自由自在地把有助有用的事情都做出來,但我們也不必把那些教育實驗者看成只會用現狀來作反射動作的呆子。我們實際上是一直在系統性地低估教育革新所帶來的衝擊。即令是那相當脆弱也飽受批評的「起頭方案」也曾經產生過驚人的結果,我們就會在本書的下文裡看到。除此之外,我們真正拿來應用的,其實還比我們所知者少得多——包括孩子們會在教室裡形成他們自己的互助社群,並且讓他們的知識表現變好,也讓他們的眼界提高。當我們把文化心理學帶入教育領域之後,我們還會學到很多其他的東西。我希望我有足夠的說服力,讓大家相信教育並沒有走入窮途末路。確實的,我們反而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我們正走在一條新路的起點上。
對於本書的整個寫作構想,我這就來說幾句話。雖然每一章都可以拿來獨立閱讀,但全部合攏起來則可以形成一種更為寬廣的觀點。該觀點乃是關於個體人(individual human)的心靈在文化所提供的能量之中如何活動的看法,這在首章中是用幾種「主張」的形式來鋪陳。接下來的一章則是對於各個主張作進一步的陳述。其中涵蓋了許多「教育的」論題——從庶民教育觀對教育的影響,到教育政策本身之內在的相悖性;從敘事法的使用,到靈長類的教育法;從「閱讀」他者的心靈,到追問我們如何將世界再現於人與人之間。涵蓋的範圍(用寫書人的老話來說),不是我的問題。我也不打算對現下教育政策的熱門話題提出很多當頭的質疑。在我們能夠對教育的文化獲致更深的理解之前,我相信對這些問題是不可能有解答的。這才是本書真正要談的東西。
我必須對於使這本書得以完成的人和機構表達我的謝意:史本賽基金會(Spencer Foundation)慨助我的研究,紐約大學心理系提供我工作的空間以及各種設備,還要特別感謝紐約大學法學院,我有機會參與其中的知識生活而獲益良多,並且我還持續以特殊身分在其中教授一門關於法律、文學、人文科學之詮釋理論的研討課,我的授課同伴是湯尼.阿姆斯特丹(Tony Amsterdam)、珮姬.戴維斯(Peggy Davis)和大維.李察茲(David Richards)——這門課裡的種種聲音在本書的每一章中都有迴響。
我把這本《教育的文化》題獻給大衛.歐爾森(David Olson),我從前的博士後研究員、長期的朋友,他是振奮我心的共謀者,也是始終不渝地來與我對談或辯論的夥伴。我想感謝的還有多位,無法在本序言裡一一舉出,但在本書的文脈之中,還會有機會再提到他們。
一九九五年九月寫於愛爾蘭共和國
科克郡的格藍多爾城
科克郡的格藍多爾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