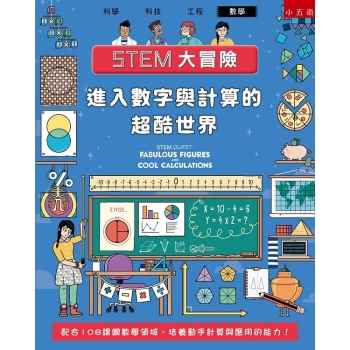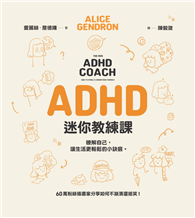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後言】
《一千零一夜》正文前,有這樣一段歷來為譯家們所刪掉的導言:
萬讚歸於教育眾世界的安拉。……
前人的故事、傳記成為後人的訓誡和殷鑑,以供人們吸取先人的經驗,並以此為鑑,瞭解先前諸民族史實及經歷,藉以檢點、規範自己的行為。
讚美那些把前人的故事、傳說化為後人殷鑑的人們。
在那些訓誡中,有一部名為《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集,其中蘊藏著豐富奇珍異寶、鑑戒嘉言……
筆者以為,這便是編纂這部宏大故事集的立意和初衷。
《一千零一夜》以阿拉伯文為母本的故事共有一百六十三個。故事的時空範圍極廣,許多故事中穿插著動人的愛情故事,妙趣橫生,惹人喜愛。此外,還有冒險故事、神怪故事、幻想故事、諧趣故事、寓言故事、歷史故事、教誨故事等。
故事中出現的角色,除了神翁天仙、天兵天將、妖魔鬼怪、猴王蛇女、鳥王獸王、海王陸王等之外,人類社會各個階層的各種人物應有盡有。透過蒙在故事之外的那層神秘紗衣,讀者可以看到中古時代阿拉伯社會及東方許多國度的社會生活畫面,堪稱五彩斑斕、動人心魄。這些故事就整體而言,字裡行間充滿著勸人進取,宣揚真善美,抨擊假惡醜的積極向上的精神;熱情謳歌青年男女之間的純真愛情,責斥不正當的男女關系;讚美女性的聰明才智,駁斥蔑視婦女的謬論;揭露帝王的殘暴及宮闕生活的淫亂,反映勞苦大眾的悲苦處境;揚善抑惡,抒發平民百姓的美好理想和嚮往。此外,還可以看到反映商賈階層生活的篇章。
愛情是永恆的主題。愛情是社會、家庭大廈的支柱。愛情故事在《一千零一夜》中占有很大篇幅。這些故事,不論寫王子戀公主,還是商人戀王妃,或者寫人仙戀、自由人與女奴戀,無不深刻反映了青年男女追求自主婚戀的熱切嚮往,具有強烈的反封建色彩,間接或直接揭露了宮闕生活的混亂與荒唐。
〈哈西普‧克里姆丁遇蛇仙的故事〉(第482~536夜),是寫人仙戀的愛情故事,給人留下的印象最深,酷似中國的〈天仙配〉。〈巴士拉銀匠哈桑的故事〉(第778~831夜)與這個故事略有雷同之處,但更富神話色彩,情節更為曲折,趣味性更勝一籌,是又一個人仙相戀的美妙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仙塵、神蛇、飛馬、飛魔、神象、神馬、隱身帽和魔杖,還有日行千里的羅馬紅瓦罐,相繼顯示神功,合力成全哈桑與西娜的愛情,奇異的想像力得以充分展示,讀來頗引人入勝。
衝破傳統阻力,男女喜結良緣,是《一千零一夜》中另一個類型的愛情故事。〈努爾丁與瑪麗亞的故事〉(第863~894夜)中,對愛情忠貞不二的瑪麗亞歷經險阻,最後殺退追兵,將親弟弟斬於馬下,終於與努爾丁團圓。相較之下,瑪麗亞比《梁祝》中的祝英台就勇敢得多了。此類事未必真有,但可能有,合乎魯迅老先生為小說規定的標準,讀來也很令人開心。
〈文尼斯與沃爾黛的故事〉(第371~381夜)也屬於此類型。在這個故事中,雄獅也通人性,為文尼斯指引方向並帶路,現實中夾帶著童話,讀來又是另一種新鮮感。
〈蓋麥爾與布杜爾的故事〉(第170~237夜)是《一千零一夜》中篇幅最長的愛情故事,內有一百零八首詩歌,是詩文並茂的典型篇章。公主最後女扮男裝繼承某王國王位。蓋麥爾輾轉來到此地的消息傳到布杜爾的耳際,布杜爾立即宣之進宮。布杜爾公主見到丈夫,不禁喜在心中,只是未溢於言表,但蓋麥爾卻完全沒有認出眼前這位國王就是自己的妻子。布杜爾有意給丈夫驚喜,百般調情挑逗,反被蓋麥爾誤會。直到寬衣解帶上床,蓋麥爾也未曾悟出眼前這位國王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妻子。此處的圓房雲雨之情雖寫得稍見粗俗,但不失拙樸之美,保留了當年說書藝人口頭傳述的風貌,並不像有些學者所說的「不堪入目」。
〈阿里‧沙爾與祖姆魯黛的故事〉(第308~327夜)與以上兩個故事稍有相仿之處。此外,〈烏木馬的故事〉(第357~371夜)、〈國王與公主的故事〉(第738~756夜)、〈設拉子王子與伊拉克公主的故事〉(第719~738夜)、〈賽伊夫‧穆魯克與白迪阿‧賈瑪麗的故事〉(第756~778夜)等,都是跌宕起伏、生動感人的愛情故事。最值得一談的愛情故事要算是〈富商與靚女的故事〉(第845~863夜)和〈蓋麥爾‧澤曼與寶石匠妻子的故事〉(第963~978夜),前者展示了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婚姻的道理,後者闡明的是這樣一個趨向:新舊道德觀相互抗爭中,封建禮教必將讓位於生活中更高層次的東西──愛情。商人與王妃相愛,是《一千零一夜》中又一個類型的愛情故事。〈商人與王妃的故事〉(第959~963夜)講的是商人艾普‧哈桑與哈里發的愛妃舍吉萊‧杜爾相愛的故事。哈里發宮中有嬪妃四千,與我國古代的秦王宮、漢王宮情況一模一樣。成群嬪妃當中,有幸蒙召侍寢機會者甚少,正如〈貴妃醉酒〉裡高力士所說:「我們這個宮裡,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宮女、彩人三千餘眾,都是伺候皇上一個人的。有的人,從小姑娘時就進了宮,頭髮都白了,還沒有見過皇上的面呢!」她們的性愛權利被封建帝王無情地剝奪了。她們畢竟是骨肉之軀,有著七情六慾,一心嚮往真正的愛情生活,不肯忍受寒宮之苦,不願當金籠中的鳥兒,甘願嫁給商人為妻。〈阿里‧本‧畢卡爾與莎姆絲‧奈哈爾的故事〉(第153~169夜)講的是哈里發哈倫‧拉希德的愛妃莎姆絲與商人阿里相愛的悲劇。
《一千零一夜》中有關哈里發哈倫‧拉希德的故事占有顯著篇幅。哈倫‧拉希德一向被當作開明君主歌頌,而實際上卻是個奢侈君王。據史料記載:哈倫‧拉希德有一個妹妹,名叫阿芭賽。哈倫‧拉希德很喜歡她,不讓她嫁人,他允許賈法爾(即許多故事中的賈法爾宰相)以清客身分跟她做名義上的夫妻,以便於同座喝酒。有一次,哈倫‧拉希德朝覲天房,發現妹妹已經跟賈法爾偷偷生了一個男孩兒,暗地裡送到麥加城去,隱藏起來。賈法爾因此於803年被處死,首級懸掛在巴格達的一座橋上,屍體被割成兩半,掛在另外的兩座橋上。當時,賈法爾年僅三十七歲。一個堂堂的哈里發,自己放蕩無羈,嬪妃成群,卻對妹妹和宰相實行禁慾主義,天理何在!宮闕生活的黑暗由此可見一斑。
談到《一千零一夜》中的婦女形象,首先浮現在筆者腦海中的,是宰相的女兒莎赫札德:她聰明美麗,智勇雙全,博學多才,善良純潔,總歸一句話,她就是真善美的化身。然而阿拉伯學者們另有議論。美籍黎巴嫩學者希提說:「到了這個王朝(指阿巴斯王朝)衰落時代,由於過多的蓄妾,兩性道德的鬆弛,過分的奢侈,婦女的地位一落千丈,正如《天方夜譚》所描述的那樣。婦女被描繪成為陰險狡猾、卑鄙下流的東西。」〔《阿拉伯通史》第389頁,〔美〕希提著,馬堅譯,商務印書館。〕埃及批評家艾‧哈‧扎亞特說:「《一千零一夜》中對人的最壞描寫,是對女性的極端嚴酷。在其中,女性的命運是不幸的,其形象是醜惡的。」敘利亞的女作家烏勒法‧伊德莉比甚至認為,《一千零一夜》對女性「充滿不公和詆毀」,再加上此書「流傳極廣」,對阿拉伯社會中婦女地位的長期低落狀態產生了一定影響。誠然,《一千零一夜》中有幾個壞女人的形象,如:將哈里發愛妃姑蒂‧格魯普活埋或賣掉的王后祖貝黛(見〈商人阿尤布及其子女的故事〉,第36~44夜;〈漁夫海里法的故事〉第831~845夜);〈努阿曼國王及其兒子的故事〉(第44~145夜)中老太婆扎特‧達瓦希;〈國王、太子與妃子的故事〉(第578~606夜)中勾引太子卻反誣告太子調戲自己的那個妃子;〈戴麗萊母女的故事〉(第698~708夜)中的「騙子」母女;〈富商與靚女的故事〉(第845~863夜)中背棄丈夫的澤妮‧穆娃綏芙;〈蓋麥爾‧澤曼與寶石匠妻子的故事〉(第963~978夜)中跟人私奔的福拉娜;還有最後一個故事中的鞋匠馬魯夫的元配刁妻……其實,社會中確實有這樣的女人,描述也難說過分,與慈禧太后及「還有精生白骨,自比武則天后」(郭沫若辭)的那個女人相比,她們根本算不上什麼壞女人。關於「婦女地位的長期低落狀態」,首先與生產力發展有關,其次有待於思想解放,與《一千零一夜》恐怕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一本書有這麼大力量,還要革命何用?不能忽視,《一千零一夜》中也寫了許多壞男人,為何沒有影響男人的地位呢?
譯完《一千零一夜》所有以阿拉伯文為母本的故事,留給筆者印象最深的則是故事中一位位天姿皎潔、滿腹經綸的東方女子,而且故事裡的社會中,愛多於恨,和多於鬥,融合多於分裂。
宰相的女兒莎赫札德面對暴君枉殺無辜女子的嚴竣形勢,她沒有膽怯,沒有逃離,而是胸有成竹,自願進宮,這是何等的勇氣,單用「不怕犧牲」、「品格高尚」之類的詞語能夠道出莎赫札德的外美內秀嗎?老宰相天明時帶著殮衣準備為女兒收屍,誰不為她的生命擔憂?每當天亮,誰敢保證她能再多活上一天?她講了一個又一個故事,把舍赫亞爾國王講得捨不得殺她,誰講的故事能有這麼大的力量!一千零一個夜晚,將近三年時間過去,莎赫札德為國王生下三個可愛的小王子,國王納之為后──漫長的夜過去了,光明終於來臨,天下的少女得救了,誰又能不衷心感謝莎赫札德?這不是一曲偉大女性的頌歌嗎?這不正是真善美征服假惡醜過程的偉大藝術再現嗎?
人分男女,有好有壞,有善有惡,本是平常之理。《一千零一夜》中塑造的高尚女性遠遠不只這一位,還有多位忠於愛情的公主、民女、村姑、貴婦人。〈施捨麵餅的女人〉(第347夜)、〈善女與歹徒的故事〉(第394夜)中的善女;〈一個聰明女人的故事〉(第404夜)中的用小計令國王悟過的女人;〈法官妻子的故事〉(第465~466夜)、〈信守誓言的婦人〉(第466~467夜)、〈鐵匠與善女的故事〉(第471~473夜)中,寧願餓死而不肯失身的善女;神話故事中的一位位仙女,哈里發笑納的那位「才女」(第685~686夜),賽詩三姊妹(第686~687夜),從容應付好色國王的「相國夫人」,巧戲眾達官的那位智謀雙全的女子,還有多位在青年男女戀人之間往返穿梭、傳遞情書的老紅娘,她們一個個吃苦耐勞,無怨無悔,形象栩栩如生,親切可信……善女良婦,真是多不勝數。
最令人驚羨的還是故事中的那幾位公主和婢女。在此僅舉一二例。《一千零一夜》中最長的故事〈努阿曼國王及其兒子的故事〉(第44~145夜)裡,努茲蔓本是一位公主,因與弟相伴去麥加朝覲,途中遇上麻煩,姊弟失散。姊姊努茲蔓被輾轉賣作女奴,最後竟與異母長兄結為夫妻;這在蓄妾盛行的阿拉伯帝國裡,出現此等荒唐事,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故事以極大篇幅描繪這位公主「姿色無與倫比,博學多才,精通多門學問」,在向四位法官和商人講王政、禮法等重要問題時,引經據典,深入淺出,又借用大量故事作佐證,加強自己的論點,以非凡才學和見地使法官和商人五體投地,自嘆弗如。
〈男女貴賤爭論的故事〉(第419~423夜)中的那位女子「聰明伶俐,知識淵博,才高八斗,性情賢淑,精於講道。」她以充足論據,引用多首詩歌,駁斥了「經典」和「聖人」關於女不如男的謬論,把伊瑪目們蔑視婦女的言論批駁得體無完膚,他們一個個瞠目結舌,啞口無言。〈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附錄)中的婢女麥爾加娜機警出眾,屢屢識破盜賊們的伎倆,用沸油澆死藏在油甕中的數十名盜匪,又藉跳舞助興之機,用匕首結束了盜匪頭領的性命,成功地保衛了主人,被主人納為兒媳。
令人分外羨慕和讚嘆的恐怕是〈婢女泰沃杜德的故事〉(第436~461夜)中的女奴泰沃杜德姑娘。她豈止貌美,且「博學多才,通曉多門技藝,故以才貌雙全著稱於世,堪稱絕代佳麗。」她「懂語法、詩歌、法學、注釋語言」和「音樂、遺產繼承學、算術、測定法」,「熟知先人軼事,通曉《古蘭經》讀法……」,「研究過數學、幾何學、哲學、醫學、邏輯學、辭義學、修辭學」,「能彈會唱,能歌善舞」,「各方面均有極深造詣。」哈里發哈倫‧拉希德得知姑娘如此才貌出眾,即召集《古蘭經》朗誦家、學者、醫生、占卜師、哲學家、工程師等,一一提問題,要姑娘回答。泰沃杜德儀態大方,從容不迫,就宗教禮儀、宗教信仰、《古蘭經》、生理衛生、天文、哲學等多門知識一一作答,果然對答如流,有根有據,大家們無不拜倒在姑娘面前,一個個被扒掉衣服,狼狽離去。細讀這五萬餘言的故事,不僅自感學識大長,更由衷讚美說書人為婦女叫好、大長女子志氣的浪漫主義立意,怎麼會得出《一千零一夜》侮蔑婦女結論呢?
不妨回過頭來談談〈努阿曼國王及其兒子的故事〉中的老太婆扎特‧達瓦希。故事描繪的是基督徒大軍與穆斯林大軍之間的一場戰爭。「扎特‧達瓦希」這個名字的意思就像文中所譯,即「智多星」,也可譯作「女謀士」、「有謀略的女子」等,可見說書人對老太婆懷有幾分敬意。她是基督徒,運用苦肉計,女扮男裝,冒充修道士打入穆斯林營中,用計謀毒死了努阿曼國王,並置努阿曼國王的長子舒爾康於死地。從兩國交戰,各為其主的法則出發,扎特‧達瓦希不愧為英雄。自然,站在穆斯林大軍的立場上,簡單地將老太婆打入壞女人之列,筆者想那是有違作者初衷的。
婢女泰沃杜德在回答學者們的提問中,談到性愛與健康,且頗有醫學根據,這不僅是大膽的,而且也是難能可貴的。筆者由此想到《一千零一夜》中的性描寫,不妨順便簡略一談。以筆者拙見,性是社會的原動力。沒有性,人類社會也就不存在了,焉談進步與發展。恩格斯指出:「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產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從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這就是著名的兩種生產的理論。從這個理論看來,人類自身的生產問題、種的蕃衍問題、性問題對於歷史和社會的發展,具有多麼重要的決定性作用。」〔《中國古代性文化》第5頁,劉達臨著,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從原始初民到現代人,都能從性生活中獲得極大的歡樂。這似乎是造物主的偉大恩賜。但是,性實在是一個怪物,它能給予人們極大的快樂,又給人們帶來巨大的痛苦。進行性教育,是文明社會發展的標誌,是遠見卓識的象徵。簡單地把性愛與淫亂混在一起談是極不適當的。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一千零一夜》的種種節、選譯本多以青少年讀者為對象,刪除性描寫,是得體舉動。但是,以研究者和成年人為對象,則應該保留文化遺產的原貌。人類經過漫長歲月探索,最後確定以婚姻作為對性實行控制的制度,即把人類的性行為限制在婚姻關係範圍之內,並據此判斷性行為是正常性愛還是淫亂,是正確還是錯誤,是有罪還是無罪。《一千零一夜》中為數不多的幾處性描寫,多在婚姻關係的範圍之內,並無淫亂之嫌。讀者會發現,《一千零一夜》中有不正當性行為的黑奴埃杜班、剃頭匠的二哥、布赫特等,不是被殺,就是被閹,都得到了應有的懲處。當然,裡面有關於平民情趣、挑逗戲弄的性描寫,此外還有戀獸癖,即與熊、猴子性交的描繪,亦有狎孌的同性戀等性變態描寫,那是不能以一般情理來衡量的,正所謂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然而,眾所周知,因為性描寫,發生過轟動世界文壇的訴訟案。英國著名作家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1928年問世之後,即在國際上引起爭論,不少國家還將它列為禁書。1960年,英國企鵝出版社為紀念勞倫斯逝世三十周年,決定出版此書的全文本,此舉即遭英國檢查部門的竭力反對,並向法庭提出控告,認為它是「腐化讀者心靈」的淫書。出版社不服,於是聘請律師出庭辯護,律師邀請三十五名專家、教授、評論家、神學家、心理學家等出庭作證,並由法院挑選了九男三女的陪審團,經過長達六天的辯論,法庭終於判企鵝出版社無罪,並駁回檢查官的控告,而使該書得以公開面世。這部小說的男主人公查泰萊是擁有礦場和森林的爵爺,從前線回來,下肢癱瘓,要妻子康妮「與別的男人生個孩子」,繼承家業,康妮無法忍受死氣沉沉的生活,與雇工梅勒斯相戀,相約出走,查泰萊拒絕離婚。其實全書立意嚴肅,愛憎分明,爵爺所維護的婚姻道德是十足的虛偽與自私。該書中的性愛描寫達到了藝術的高度,但官司也就產生在這裡。
時隔二十五年,即1985年5月17日,埃及傳出一則驚人的消息:埃及道德法庭宣佈《一千零一夜》為淫書,勒令對其禁售、查封、銷毀,並對出版此書的出版社課以罰款。這消息不僅使埃及文化界和社會大譁,也使世界文壇為之一驚。道德法庭的公訴書中稱:「在檢查了該書後,發現其含有有損公共品質、庸俗下流、違背埃及社會公德、違背《古蘭經》教義和伊斯蘭道德的故事、詞句和繪畫。」該書由埃及政府訂正的善本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平安無事,突然被起訴為「淫書」,不失為八○年代地道的「天方夜譚」。判決宣佈後,立即遭到埃及文化界人士譴責。作家、評論家紛紛發表聲明、評論。著名作家馬富滋說:
不管是文學著作還是法律著作,縱使目的有別,卻都包含我們所說的「性公開」。像其它文化遺產一樣,這是不能更動的。文化遺產是供研究人員使用的,而且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所有特徵正是集中在這裡。目前市場上出售的價格昂貴的四卷本《一千零一夜》不是以學生為方向,沒有必要擔心普通讀者的污染問題,他們沒有機會接觸這些東西。如果決定在學生或社會青年中普及文化遺產,倒不妨盡力做些精選工作,刪去那些可能被誤解為淫穢色情的地方。至於遺產本身,則必須予以肯定,原封不動地發行,以便成為歷史上我們民族精粹的真實記錄。
在埃及廣大知識界人士的譴責聲中,時隔半年,一批埃及律師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抗議書。抗議書中說:「如果出於科學和藝術的需要,書中的性描寫並不是罪過。如果出於窺探欲和性挑逗,則被認為是有損於公德和品行的。」抗訴書還說:「本查禁的《一千零一夜》,數世紀以來吸引著東西方讀者。東西方都把它看作是一種娛樂、消遣和享樂。此外,它還是研究的良好課題。……《一千零一夜》曾是許多精美藝術品的泉源。世界許多著名作家,特別是阿拉伯作家曾從中吸取營養,創作出自己的優秀作品。由此否定了關於《一千零一夜》能在讀者中引起窺探欲和性挑逗的猜測,除非這讀者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病態者,而這在評價這部文學作品中是無需考慮的因素。」最後法庭宣判取消原判,宣佈「被告」《一千零一夜》無罪。
英國的現代性學先驅靄理士說過:「性是任何事物也無法熄滅的長明之火。我們應該像摩西那樣,扔掉鞋,赤著雙足,去探索這不可思議的火焰。」但是,幾百年來,許多世界文學名著因為有性描寫而被查禁或閹割。莎士比亞的某些作品被刪節得支離破碎,薄伽丘的《十日談》被沒完沒了地又禁又毀。《一千零一夜》的命運就更糟了,被介紹到中國滿一個世紀,讀者尚未見其原貌。劉達臨先生在他的新作《世界古代性文化》中指出:
《天方夜譚》中,比較膾炙人口、眾所熟知的〈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阿拉丁神燈〉、〈航海家辛巴達的故事〉等,雖然趣味盎然,但不一定是此書最傳神、最精采的故事,其中有些比較浪漫、涉及性愛的故事大都不為人知,這是有原因的。
這是因為有些比較保守的阿拉伯文學史書都排斥《天方夜譚》,不願承認它是阿拉伯文學,主要是他們認為書中有些故事過於浪漫、過於色情、過於諷刺和刺激了。在《天方夜譚》成書後至今五、六百年中,書中的故事不斷被人增刪,不但故事的數目和篇名在各種版本中都有所不同,而且有時同一故事內的文字情節也有更改,有些較為浪漫、有性內容的故事已被刪去,所以《天方夜譚》可以說是人人都聽過,但很少有人完整地看過的一部書。
通過鳥獸之口,講人間經驗教訓的寓言故事,在《一千零一夜》中也占了一定篇幅,頗各盡其妙,恰到好處。善惡報應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朱德爾三兄弟的故事〉(第606~624夜)、〈巴士拉總督三兄弟的故事〉(第978~989夜)、〈洗染匠與剃頭匠的故事〉(第930~940夜)等許多故事中的善良人與惡人,都毫不例外地得到了應有的獎勵與懲罰,真正體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善惡俱報」的眾望所歸的真理與規律。不能否認《一千零一夜》這部民間文學巨著中有宣揚拜金主義、宿命論的篇章,宗教色彩亦過分濃重,后妃爭風吃醋等是為糟粕。但就總體而言,瑕不掩瑜,不愧民間文學「最壯麗的紀念碑」的佳譽,正如葉聖陶先生所說:「雖然全集是一個大故事,但是,我們若截頭其尾,單單取中間包蘊著的最小的一個故事來看,也覺得完整美妙,足以滿意;這譬如一池澄淨的水,酌取一勺,一樣會嘗到美甘的清味。」
筆者在翻譯中最大的困難是多達萬餘行的詩。我很喜歡詩,也寫過詩,填過詞,但不是以發表為目的,有的簡直就是為自己寫的,目的在於平定心中的某種激情;心中有情思,提筆在小本子上寫幾句,也就感到平靜、舒暢了。譯詩,也是我的愛好。我曾於八○年代初譯過若干首阿拉伯詩,但譯得很不滿意,只發表過一首長詩,其餘的譯作都還留在本子上,或許有機會在課堂上向弟子們朗讀一下,也就是它們的歸宿了。我也曾決心在詩海裡游泳一陣兒,但終因自感才疏學淺,尤嘆文采不足,只得激流勇退,心中委實留下了一絲遺憾。我讀過譯界前輩關於譯詩的高論,令我更生怯意。許多老前輩都說詩是不可譯的。郁達夫先生說:「翻譯比創作難,而翻譯有聲有色的抒情詩,比翻譯科學書及其他的文學作品更難。」〔見《翻譯論集》第390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我很相信這是翻譯巨匠的肺腑之言。詩,不要說從一種文字譯成另一種文字,就是用同一種文字,把詩意解釋清楚,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英國大詩人雪萊在《詩辯》中有過這樣一段名言:「譯詩是徒勞無益的,把一個詩人的創作從一種語言譯成另一種語言,猶如把一朵紫羅蘭投入坩堝,企圖由此探索它的色澤和香味的構造原理,其為不智一也。」〔同上,第675頁。〕然而說來也怪,正是這位認為詩不可譯的「天才預言家」(恩格斯語)卻從希臘文選譯過荷馬和柏拉圖的詩作,從拉丁文選譯過味吉爾的《牧歌》,從義大利文選譯過但丁的《神曲》,從西班牙文選譯過卡爾德隆的《神奇的魔術師》,從德文選譯過歌德的《浮士德》。明知不可譯,卻偏偏譯了那麼多,究竟為什麼呢?這大約因為看到了譯詩的好處,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說:「詩的翻譯對於任何民族文學、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莫大好處。不僅僅是打開了若干朝外的門窗;它能給民族文學生命力,由於它能深入語言的中心,用新的方法震撼它、磨練它,使它重新靈敏、活躍起來。如果去掉翻譯,每個民族的文化都將大為貧乏。」既然譯詩這麼重要,不懂原文的讀者們又要瞭解詩的意思和意境,那就不得不譯,於是譯詩的途徑就產生了種種選擇,無論是形似、神似、意美、形美或音美,也都引起過譯界的關注。但正如行家指出的那樣:詩歌翻譯是一種「遺憾的藝術」,「因為譯者不可能同時『忠於』詩歌的內容。一首詩的全部詩意(格式、韻律、節奏)和內容(主題、意境、詩質)的有機結合,缺少哪一種因素,都會造成詩意的喪失。」〔見李蘭生:〈論跨文化誤讀的難譯超越性──關於翻譯的思考〉,原載於《比較文學報》1996年總第13期。〕我想,在譯詩過程中,不管怎樣努力,譯作都只能是原作的臨摹品,要求譯詩「形神兼備」,真是太難太難了,簡直就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化」境。《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千三百餘首詩,都是格律詩。其中情詩占的比例最大。應該說,有些詩句的含義是隱晦難懂的。站在這詩海面前,我始終是小心翼翼,冥思苦索,走路時想,吃飯時想,推敲再三,未厭其煩,然而直到譯完最後一行詩,也沒有「容易譯」的感覺。我深深體會到,譯詩比作詩要難多了,況且譯詩的功夫更在詩外呢!拙譯付梓,數月躊躇,若蒙同仁賜教,是為求之不得矣。
《一千零一夜》中究竟有多少故事,幾乎都說有二百六十四個,查其根據,當是來自一個英譯本的「序」中。但就目前所見到的十二種阿拉伯文版本,哪一種版本裡也沒有這麼多故事,哪一個版本裡也沒有〈阿拉丁與神燈〉和〈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那兩個有名的膾炙人口的故事。「布拉克本」裡故事最多,確切地說,有一百六十個故事(故事中套的故事不計算在內,無論長短如何)。其餘十一個版本,故事就少得多了。由此可知,英譯本裡的許多故事是沒有阿拉伯文母本的,而是首先用英文寫成,並將之編入《一千零一夜》的,編者對《一千零一夜》的崇敬心情由此可見一斑。
但是,筆者看到〈阿拉丁與神燈〉、〈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阿拉伯文單行本的序言這樣寫道:「〈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或〈阿拉丁與神燈〉)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個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這些故事本是世代口傳的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的故事。這些故事第一次以阿拉伯文形式出現是在公元1450年,之後由阿拉伯文譯成世界上的各種文字。」(黎巴嫩書店版本)這段文字的含義有些含糊不清,也許會造成某種誤解,因為它沒有特別強調〈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就是「第一次以阿拉伯文形式出現的」。按照《一千零一夜》中多數故事的習慣,人物總借用詩歌抒情,而那兩個知名度極高、最膾炙人口的兩個故事裡卻沒有一首詩,似乎與整個《一千零一夜》的體例不大協調,筆者曾由此猜想原文是非阿拉伯文寫成的,然後由阿拉伯人將之譯成阿拉伯語。〈阿拉丁與神燈〉講的故事發生在中國,阿拉丁的故鄉是中國,但作為一個故事的主人公,阿拉丁是唯一的一位中國人,無疑是東方故事。若〈阿拉丁與神燈〉的母本是阿拉伯文,「布拉克本」卻不將這個精彩的故事收進去,那是沒有理由的。〈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這一故事發生在埃及。埃及雜誌《埃及》1995年第四期上有這樣一段文字:「也許很多人不知道《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故事發生在哈萊依布地區。那裡現在還有一個山洞,名叫『奧里巴巴』,本係比伽語,寫成阿拉伯語則是『阿里巴巴』。羅馬時期,奧里巴巴統治著比伽。奧里巴巴消滅了所有被羅馬人派到這裡掠奪黃金和貴重礦藏的強盜,並將他們搶劫的寶物藏在那個山洞裡。直到今天,還有一些遊人進入那個山洞尋找奧里巴巴藏起來的黃金。」這說明〈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故事確實發生在埃及。如果此故事首先用阿拉伯文寫成,而埃及政府訂正的「善本」不予收入,那就更沒有理由了。由此看來,西方人也參加了《一千零一夜》的創作、編纂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千零一夜》是東方人和西方人的合作產物,也是東西方智慧的結晶,難怪西方人也那樣喜歡這部民間文學巨著,竟把《一千零一夜》增編至二百六十四個故事,真可堪稱世界第一「合作」的民間文學大作了。
十八世紀初(1704年),法國人安托尼‧加蘭德(亦譯作「迦蘭」、「葛蘭」)在君士坦丁堡任大使期間,根據從敘利亞寄給他的一個手抄本,「首先將《一千零一夜》的部分故事譯成法文,編成十二卷,這就是《一千零一夜》傳入歐洲的開始。」〔《天方夜譚‧總序》,新潮出版社,1948年。〕但是,「加蘭德的譯文,不但不是全譯,甚至還把故事大加刪改,使它適合於歐洲人的口味,並且還加入了不少別國的傳說,因而只能說它是一種改譯。」〔《〈一千零一夜〉研究‧前言》,〔埃及〕蘇‧蓋勒瑪薇著,埃及知識出版社。〕儘管如此,「自從這一迷人的東方傳奇集錦於二百七十年前傳入西方後,在西方讀者的印象中,很少有書能與之媲美。事實上,我們西方人對於神秘而浪漫的東方所具有根深蒂固的概念主要來源於這本可愛的傳奇。」(豪澤語)《一千零一夜》風靡西方,至1888年巴登十七卷譯本的出現達到了高潮。巴登不僅將以阿拉伯語為母本的全部故事譯成英文,而且還搜集、整理了一百多個東方故事,將之續在《一千零一夜》之後,並有研究文集出版,彩色、黑白插圖精美而傳神,令人嘆為觀止。《一千零一夜》曾直接或間接影響了為數可觀的西方世界級知名大家,如俄國的托爾斯泰(1828-1910)、英國的喬叟(約1343-1400)、莎士比亞(1564-1616)、斯威夫特(1667-1745)、笛福(1660?-1731)、狄更斯(1812-1872)、斯蒂文森(1850-1894)、凡爾納(1828-1915),法國的拉伯雷(1493-1553)、拉封丹(1621-1695)、大仲馬(1802-1870),德國的萊辛(1729-1781)、歌德(1749-1832)、格林兄弟(1785-1863,1786-1859)、豪夫(1802-1827),西班牙的塞萬提斯(1547-1616),丹麥的安徒生(1805-1875)等等。《一千零一夜》也影響到音樂、電影和美術。英國推出了根據《一千零一夜》拍攝的「巴格達竊賊」,美國拍出了「月宮金盒」,法國拍出了「阿里巴巴」,義大利拍出了「美女神燈」,無不引人入勝。「美女神燈」以荒誕的手法塑造一位新「神女」,取代了宰相之女,情節更動人。有資料表明,《一千零一夜》在西方的讀者及其銷售量,皆僅次於《聖經》。
阿拉伯國家曾試圖拍一千零一集電視連續劇「一千零一夜」,想法獨到,膽識可佳,不知何因至今未見結果。《一千零一夜》給許多阿拉伯藝術家帶來靈感,埃及的「阿拉伯文學之柱」塔哈‧侯賽因(1889-1973)、阿拉伯最偉大的劇作家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者馬富滋(1911-)等,都曾從《一千零一夜》中擷取過故事加以改編,賦予新的生命和哲理。阿拉伯國家也曾拍過取材自《一千零一夜》的電影、電視劇,巴格達街頭有《一千零一夜》的雕塑,但總不像在西方那樣風風火火,難怪塔哈‧侯賽因在為埃及女作家蘇阿黛‧蓋勒瑪薇所著《一千零一夜研究》的〈序言〉中說道:「本書(指《一千零一夜》)數世紀以來,扣動著東方和西方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弦。東方把它看作享受、娛樂和消遣;西方也把它看作享受、娛樂和消遣。不過與此同時,西方還認為它是卓有成效可供研究的豐富課題。」
一語道破了阿拉伯人對《一千零一夜》研究的不夠重視。黎巴嫩文學家哈納‧法胡里所著《阿拉伯文學史》洋洋四十八萬餘言(中譯本),而談及《一千零一夜》時只寫了七百字。莫非阿拉伯名諺「聖賢在當地沒有尊嚴」(或譯作「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當用在此處囉?有學者說:「《天方夜譚》在中國的傳播絕非近百年之事,而至少大可追溯到十四世紀吧。」〔《天方夜譚‧續篇‧譯者的話》,丁岐江譯,雲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但見諸文字的確是本世紀初年的事。「楊世驥曾著文談及此事,據他所知,略早就林氏(林紓)翻譯了此書的,尚有上海周桂笙。周氏別號新庵,早年肄業於上海中法學堂,治英、法文,最初向梁啟超所編《新小說》雜誌投稿,後在汪慶祺創辦的《月月小說》社任職。」「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上海清華書局出有他的譯著《新庵諧譯》一種,凡二卷,上卷係節譯《一千零一夜》。」
這是最早的譯本。1903年有大陸書局出版的《一千零一夜》,另有「繡像小說」本《天方夜譚》,但這兩個譯本均未署譯者姓名。錢楷的《海上述奇》(即〈航海家辛巴達的故事〉)由日文本轉譯而來,也問世於這一年。1904年,「女子世界」連載周作人譯的〈俠女奴〉(即〈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署名為「萍雲女士譯」,1905年由「女子世界出版社」印成單行本。周作人回憶譯〈俠女奴〉的情景時說:「我是偶然得到了一冊英文本的《天方夜譚》,引起了對於外國文學的興趣,做了我無言的教師……我看到了不禁覺得『技癢』,便拿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來做試驗。這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覺得很有趣味,陸續把它譯了出來,將譯文寄到那裡去,題上一個『萍雲』的女子名,不久居然分期登出,而且後來又印成單行本,書名是《俠女奴》……。」
看到一冊英文本的《天方夜譚》,引起了對於外國文學的興趣,且覺得「技癢」,進而激發出了翻譯創作的衝動,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青年讀者如何喜歡《天方夜譚》。周作人又說:「《天方夜譚》是我在學堂裡看到的唯一的新書,如讀本所說,我想我該喜歡它的。在中文書方面,當時看了很喜歡的也有好些,如《飲冰室自由書》等,真可以說是讀了不忍釋卷,但是後來也就不怎麼珍重了。《天方夜譚》的時間卻是很長,正如普通常說的,從八歲到八十歲的老小孩子大概都不會忘記它,只要讀過它的幾篇。……《天方夜譚》原是這一類質料,但從市場上經過了來,由多年說話人的安排與聽眾的取捨,使它更是豐富純熟……要拿以前茶館裡的《聊齋演義》相比,多少近似,不過它並無蒲留仙那樣的原本,所以可說是真正的民間文學了。」
《一千零一夜》確乎是一部雅俗共賞、老幼皆宜的民間文學讀物。
190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元和奚若的四卷文言文譯本《天方夜譚》。奚若的譯本規模較大,內有四十八個故事,影響亦大,頗受讀者歡迎,1911年被收入「說部叢書」,1924年被收入「萬有文庫」,卷首有葉紹鈞先生寫的長序。近日從上海圖書館查知,該譯本還在1914、1930、1939年多次印刷。1987年在岳麓書社重印。
1928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洪都屺瞻生、吳門天笑生合譯的《天方夜談》,內收十三個故事。僅在同一年就印刷了七版。據學者說,還有會稽金石先生的四冊漢譯本、彭兆良的譯本、林俊千的譯述本等。
1930年,亞東圖書館出版了汪原放由英文本譯出的《一千零一夜》,這是首次使用原來本名的中譯本。該譯本據美國金因公司林痕的英譯本譯出,內有原譯者寫的〈序〉,正文中有二十一個故事。至1941年,該譯本已印行九版之多。此外,還有樊仲云、范泉等的譯本。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回族學者納訓先生在《一千零一夜》翻譯上的歷史性貢獻。三○年代末,納訓留學埃及時開始首次直接從阿拉伯文翻譯《一千零一夜》,「譯出了《天方夜譚》五冊,每冊十萬至十二萬字,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後四十余年間,納訓先生筆耕不輟,將畢生獻給了《一千零一夜》的翻譯大業,成就卓著。1957至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納訓的三卷譯本;此書曾有三種開本不同的版本先後問世,成為相當長一個時期最流行的譯本。1980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納訓的《天方夜譚》。1982至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納訓的六卷本《一千零一夜》,意在這種「全譯本」是當時最全的譯本,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重要資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但由於種種條件限制,這個譯本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全譯本,不僅缺少了十四個故事,而且原文中的詩歌多被刪去,還刪去了多段關於兩性間的描寫,那個漂亮的「結尾」也不見了,留下無法彌補的缺憾。
1948年,永祥印書館出版了范泉譯的《天方夜譚》,內收〈神燈〉、〈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航海的故事〉等三個故事。該譯本一年之內發行了四版。
1948年,新潮出版社計畫分十輯出版《天方夜譚》,每輯五冊,且「另有翻譯全譯本的計畫」,但從季諾譯的第一輯第一冊《腳夫艷行記》(即〈腳伕與姑娘的故事〉)的版權頁公告上,只看到出版了《腳夫艷行記》和《神燈》(即〈阿拉丁與神燈〉),其餘各冊有的注著「排校中」,有的注著「翻譯中」,第二輯各冊注著「出版預定」,其後情況如何,因手頭沒有材料,就不得而知了。
1982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丁岐江的《天方夜譚‧續篇》,其中收有從俄文本譯來的五個故事。
八○年代以來,中國各地出版社爭相出版《一千零一夜》或《天方夜譚》,包括兒童繪畫本在內,據收藏家估計,眼下總數已在百種以上。除了納訓先生的六卷本之外,都是以青少年為對象的,很受歡迎,有的印刷竟達二百餘萬冊。
九○年代中期,各家出版社開始物色通曉阿拉伯語的譯者,由阿拉伯文直譯《一千零一夜》,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等先後推出各種由阿拉伯文直接譯出的版本。1998年6月,花山文藝出版社推出了中國第一部故事體的《一千零一夜》「善本全譯」版本。尤為可喜的是,1997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郅溥浩先生的中國的第一部《一千零一夜》的研究專著《神話與現實──〈一千零一夜〉論》,把中國的《一千零一夜》譯介和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將近一個世紀以來,《一千零一夜》在中國的譯介高潮迭起,起初由英、俄文轉譯,逐漸過渡到從原文直譯,幾代翻譯家付出了巨大辛苦,也贏得了數代讀者的熱情支持。在這千年之禧,適逢《一千零一夜》中譯本百歲華誕之際,本人有緣將《一千零一夜》善本「分夜全譯」典藏本奉獻給讀者,不勝榮幸之至。如若讀者能從拙譯中領略到《一千零一夜》迷人的稍許瑰麗與風采,亦感到莫大安慰。切望讀者批評指正,更盼方家教誨。譯本無定本,譯作是譯者對於原作理解的表達;理解總是隨著譯者各方面修養的提高而漸次入深的。筆者將努力加強修養,期盼日後有緣重譯這部巨著。
1999年11月26日 於西安凱悅飯店/李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