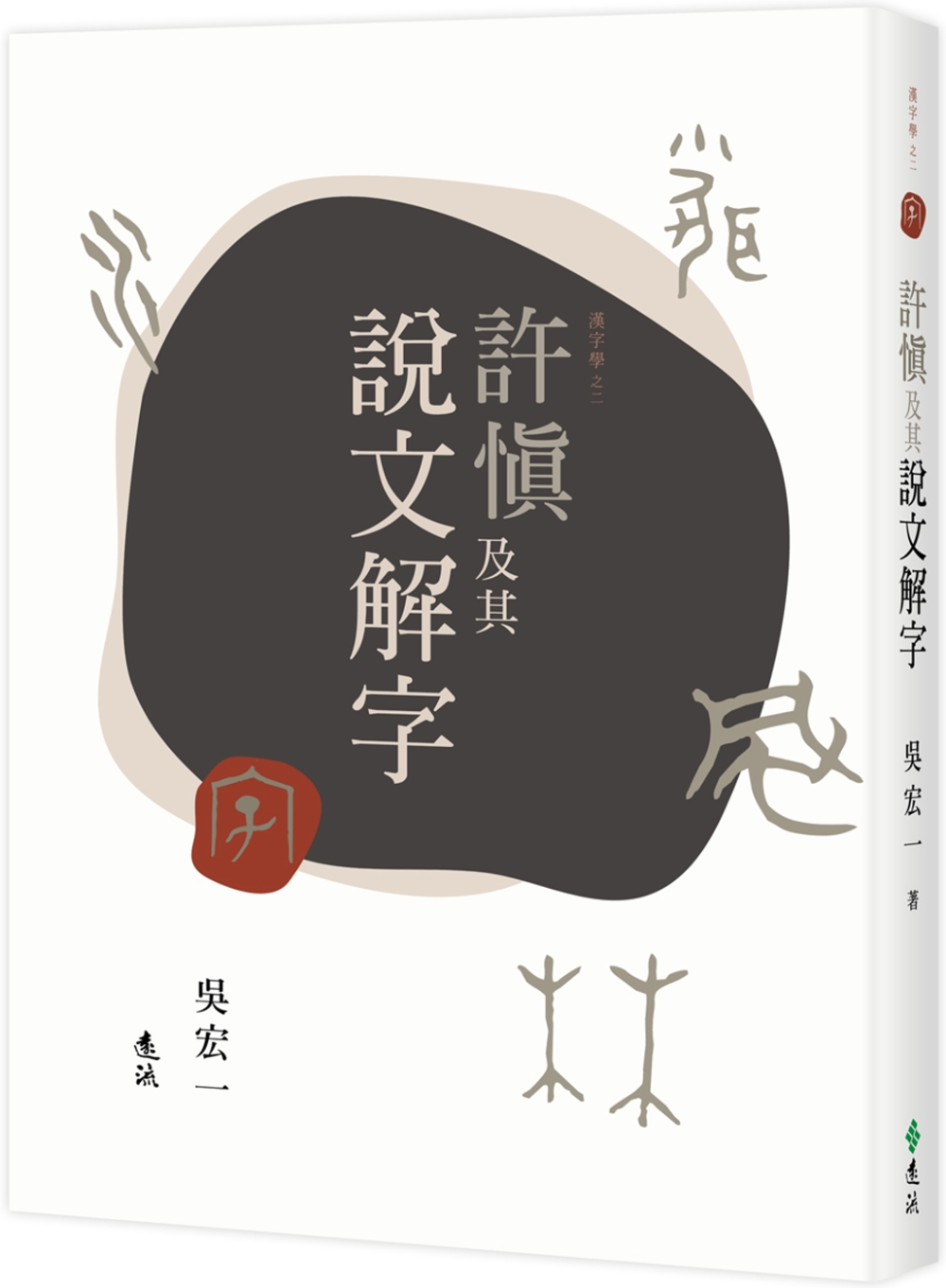了解六書之說 明白造字之法
許慎為漢代知名經學、文字學、語言學學者,是漢字學的開山鼻祖。他以傳世經籍和出土文獻為依據,彙集秦、漢之間通行的九千多個文字,歸類分為五百四十部,釋其音義,考其源流,纂成《說文解字》一書,成為後世讀書人必讀的經典之一。
《說文解字》可說是第一部按部首編排的字典,以六書理論解釋字形、字義、字音及其互相關係,對文字學影響深遠,是中國語言文字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不朽鉅著。
本書旨在評述許慎的生平事跡,及其《說文解字》一書的內容概要。特別注重許慎的仕宦經歷與經學思想的考證,漢代的六書說,以及《說文解字》一書的敍文、部首的詮釋與分析,這些都是了解《說文解字》必先解決的問題。此外,亦論及六書次第、若干部首的取捨,論述分明,解說詳盡,有助於進一步認識許慎的著書動機和宗旨,並了解其編撰體例及其詮釋方式。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許慎及其說文解字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許慎及其說文解字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吳宏一
臺灣高雄人,一九四三年生。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國家文學博士。曾任臺大中文系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主任、中正大學籌備處顧問、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講座教授、北京大學人文基金高級訪問學者;曾主編教育部國立編譯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並擔任臺、港、大陸等地多種學術期刊之編審顧問;曾獲美國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赴美訪問一年,並曾擔任新加坡教育部海外華文顧問;曾獲臺灣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教育部詩教獎、國家文藝獎(文學理論類),香港研究資助局多次研究資助等。
已出版《清代詩學初探》、《清代詞學四論》、《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詩經與楚辭》、《白話詩經》、《先秦文學導讀》、《儀禮鄉飲酒禮儀節簡釋》、《中國文學鑑賞(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品)》、《溫庭筠菩薩蠻詞研究》、《作文課十五講》、《從閱讀到寫作》,以及人生三書之《論語新繹》、《老子新繹》、《六祖壇經新繹》、《詩經新繹全集》等專書三、四十種,學術論文約百篇。除研究中國文學及古代文獻外,也從事新文藝創作,出版過《回首》、《微波集》、《波外》、《合唱》、《留些好的給別人》等詩文集,作品曾被選入臺灣、韓國、馬來西亞等地語文教科書。
吳宏一
臺灣高雄人,一九四三年生。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國家文學博士。曾任臺大中文系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主任、中正大學籌備處顧問、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講座教授、北京大學人文基金高級訪問學者;曾主編教育部國立編譯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並擔任臺、港、大陸等地多種學術期刊之編審顧問;曾獲美國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赴美訪問一年,並曾擔任新加坡教育部海外華文顧問;曾獲臺灣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教育部詩教獎、國家文藝獎(文學理論類),香港研究資助局多次研究資助等。
已出版《清代詩學初探》、《清代詞學四論》、《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詩經與楚辭》、《白話詩經》、《先秦文學導讀》、《儀禮鄉飲酒禮儀節簡釋》、《中國文學鑑賞(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品)》、《溫庭筠菩薩蠻詞研究》、《作文課十五講》、《從閱讀到寫作》,以及人生三書之《論語新繹》、《老子新繹》、《六祖壇經新繹》、《詩經新繹全集》等專書三、四十種,學術論文約百篇。除研究中國文學及古代文獻外,也從事新文藝創作,出版過《回首》、《微波集》、《波外》、《合唱》、《留些好的給別人》等詩文集,作品曾被選入臺灣、韓國、馬來西亞等地語文教科書。
目錄
序
寫在我的漢字學書前
第一章 許慎的時代背景
第一節 序論許慎《說文解字》
第二節 漢代經學的今古文之爭
第二章 許慎生平與著作考述
第一節 許慎的家世里籍生卒年
第二節 許慎的仕宦經歷
第三節 許慎的著作及其流傳
第三章 《說文解字.敘》析論
第一節 《說文解字.敘》原文
第二節 敘文題解與白話譯注
第三節 內容分析及段落大意
第四章 《說文解字》的部首
第一節 部首的意義與價值
第二節 對後世字書的影響
第三節 在文字學上的地位
第五章 《說文解字》的編撰體例及詮釋方法
第一節 編排原則
第二節 著述體例
第三節 詮釋方式
第四節 引證條例
第五節 常用術語
第六章 六書說
第一節 六書的名目與次第
第二節 漢三家舊說的檢討
第三節 分論之一:象形與指事
第四節 分論之二:會意與形聲
第五節 分論之三:轉注與假借
第六節 餘論:三書說
寫在我的漢字學書前
第一章 許慎的時代背景
第一節 序論許慎《說文解字》
第二節 漢代經學的今古文之爭
第二章 許慎生平與著作考述
第一節 許慎的家世里籍生卒年
第二節 許慎的仕宦經歷
第三節 許慎的著作及其流傳
第三章 《說文解字.敘》析論
第一節 《說文解字.敘》原文
第二節 敘文題解與白話譯注
第三節 內容分析及段落大意
第四章 《說文解字》的部首
第一節 部首的意義與價值
第二節 對後世字書的影響
第三節 在文字學上的地位
第五章 《說文解字》的編撰體例及詮釋方法
第一節 編排原則
第二節 著述體例
第三節 詮釋方式
第四節 引證條例
第五節 常用術語
第六章 六書說
第一節 六書的名目與次第
第二節 漢三家舊說的檢討
第三節 分論之一:象形與指事
第四節 分論之二:會意與形聲
第五節 分論之三:轉注與假借
第六節 餘論:三書說
序
序
寫在我的漢字學書前
寫漢字學,是我十幾年來的一個藏之於心卻遲未動筆的願望。
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九月,我考取臺大中文系,註冊入學。本來我在中學時代喜歡的是現代文學及文藝寫作,所以會以臺大中文系為大專聯考的第一志願,也就是為了想成為詩人或新文藝作家。想不到進入臺大中文系以後,受了大一國文葉嘉瑩老師的影響,閱讀與寫作的興趣,竟然由現代文學而逐漸轉向中國古典文學。到了大二,除了葉老師所講授的「詩選及習作」之外,對李孝定老師所講授的必修課「文字學」,也同樣發生濃厚的興趣。
那時候,臺灣各大學中文系的課程,沿襲教育部民國初年所訂的標準,重視傳統經典與人才培育,都規定了一些基本必修課。例如配合「大一國文」及選修的專書課程,詩歌方面,大二必修「詩選及習作」,大三必修「詞曲選及習作」;古文方面,大二必修「歷代(唐宋)文選及習作」,大三必修「歷代(漢魏六朝)文選及習作」。至於傳統小學方面,大二必修「文字學」,大三必修「聲韻學」,大四必修「訓詁學」,分別研讀中國文字的形、音、義。
那時候,李孝定老師由臺大與中研院史語所合聘,原先擔任校長室秘書,後來轉任中文系教授,講授「文字學」。教我們這一班,是他教「文字學」的第二屆。據他自己說,他不會講課,請大家多多包涵。那時候,坊間買不到什麼參考書,他請人刻印鋼板,印發馬宗霍的《文字學發凡》與唐蘭的《古文字學導論》上半部給我們當講義,要求我們自己課外研讀;他上課時則只提示書中的一些要點,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由他舉一些例字,講漢字的起源與演變,並沒有預定的進度。
記得開學不久,有一次上課,他先用粉筆在黑板上畫個像「田」字的鬼頭,下畫似乎人體四肢、雙手高舉的線條,說這是古文字,要同學猜是什麼字。有同學說像「異」,他那寬大而略嫌蒼白的臉上,竟難得露出笑容。接著他又寫了「鬼」字和「思」字,問同學二字的上半像什麼。「鬼」頭不難解,但「思」的上半為何是「田」,則無人回答。這時候,李老師才告訴我們,上半的「田」不是「田」,而是頭腦「囟」部的形狀,是隸變時訛變了形體。像「異」字原來就是「象人首戴甾之形」,確實有人解釋為鬼頭。
也就從那一堂課起,他開始連續幾週講解《說文解字》人部、手部、共部等等若干例字,從甲骨文、金文以迄隸書形體的演變以及相關的一些問題。然後說,希望同學自動去翻閱《說文解字詁林》的哪些部首及屬字。一切看似隨興而發,沒有事先準備,但我仍然覺得他講得很精彩,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特別是他講「保」字、「沫(頮)」字時的神采,一直深印在我的腦海裡。很多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在教我們「文字學」時,正在撰寫《甲骨文字集釋》,也才知道漢字的起源與演變,一直是他主要的研究課題。
記得那時候,常在晚飯後,到總圖書館(今已改為校史館)西翼二樓的「參考股圖書室」,去翻閱丁福保的《說文解字詁林》,隨興之所至,挑有興趣或容易了解的部首及屬字看,看不懂的地方就闕其疑而略過。但久而久之,經過前後對照,互相印證,原先不懂的部分,竟然有的也可以領會出一些道理,因此使我對「文字學」這門課,逐漸產生興趣。
記得那時候,系裡開設的專書課程中,還有一門由董作賓教授主講的「甲骨學」,供高年級及研究所的同學選修。我沒有見過董老師,只因對「文字學」有了興趣,又因按照慣例,系所開設的課程,只要主講的老師不反對,誰都可以去旁聽。所以在大二上學期中途,我曾經不自量力,跑去文學院特二教室旁聽「甲骨學」的課。教室小,人不多,只見一位中年瘦小的老師在臺上講課,我以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董作賓教授。哪裡知道他講課時,好幾次被臺下另一位瘦小的老先生打斷,加以糾正、補充,而他竟敬謹苦笑著唯唯稱是。後來我才知道:在臺上講課的是金祥恆先生,在臺下發言的才是董作賓教授。金先生是義務幫董老師「講」課。這嚇得我只旁聽了一次,就不敢再去了。從此乖乖的在「參考股」看《說文解字詁林》。
那時候,我常常想起去世多年的祖父。記得剛進小學時,讀過私墊的祖父教我認字。他曾經指著家裡廳堂的大門問我:「門」這個字像不像那兩扇大木版門的形狀;曾經告訴我「問」與「聞」二字,就是人與人在門內門外互相問答,加上嘴巴、耳朵的形狀組合而成的。最有趣的是,他還教我認識「愛」這個字,說它是一個人用手捧著心交給另一個人。這些童年往事,原先以為是祖父開玩笑,但在我大二學「文字學」看參考書的時候,卻常常浮上心頭來,給我增添很多溫馨的回憶。
大二下學期,有一次上課時,李老師提起了清代段玉裁、王筠、朱駿聲、桂馥《說文》四大家的著作,說我們系裡都有完備的藏書,又說甲骨文四大學者羅雪堂、王觀堂、郭鼎堂、董彥堂「四堂」之一的董彥堂(董作賓教授)就在我們系裡,有如此理想的學習環境,應當有同學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下課後,李老師特別找我去談話。他說看了我上學期的期末考卷,知道我看了很多課外參考書,所以給了我高分,希望我能再接再勵,將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當時我受寵若驚,當然一口答應了。
雖然一口答應,但我也對李老師實話實說。說我雖已立志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我最感興趣的仍然是純文學和文藝寫作。記得當時李老師寬大的臉上怔了一怔,似有不悅之色,只這樣說:「你知道陳夢家吧?他寫新詩,但也研究古文字。」我不敢多說一句話。
從此,除了上「文字學」課之外,我總是有意無意間避開李老師。其實我對李老師說的是真心話,雖然我也愛「文字」,但我真的更愛「文學」。
過了兩年左右,大約在我大學畢業前後,李老師離開了臺大。據說和王叔岷老師一樣,即將出國講學。從此失去了聯絡。後來我在臺大中文研究所讀碩士班、博士班的時候,仍然一本初衷,在詩詞純文學的天地裡討生活。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清代常州派詞學,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清代詩學,這些都是我的興趣所在。
上博士班時,經由屈萬里老師推薦,我參加了「儀禮復原小組」,並承孔德成老師不棄,主動要我旁聽他講授的「金文選讀」,使得我又有機會接觸殷周古文字。那時候,大多數的老師、同學都以為我醉心於古典詩詞,很少人知道我同時也愛好文字學。大概很少人知道我在博士班念書時,學弟之中,張光裕、邱信義、黃沛榮他們由屈老師指導有關古文字的碩士論文,都曾由我先幫忙修飾文字,使得我有機會對他們的大著先睹為快;大概也很少人知道我從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校外兼課教書開始,在講課時就常引用古文字來輔助教學。例如教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且以汝之有身」的「身」,先把它金文、小篆的字體畫出來,原來就是女人懷孕的形狀;教《左傳》的〈曹劌論戰〉,先說《史記.刺客列傳》中,「曹劌」作「曹沫」,並進一步說明「劌」和「沫」、「湏」、「頮」、「靧」等字形音義之間的關係,等等。這種教法,似乎頗能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所以我臺大博士班畢業以後,留校任教,無論教什麼課,只要與古文字有關的詞語,我都會「依樣畫葫蘆」、「老王賣瓜」一番。尋思起來,這和當初上「文字學」的課,受到李老師的啟蒙大有關係。因此,我常常想起李老師當年對我的期許。我覺得辜負了他當年的好意,如果有機會,應該對李老師說聲「對不起」。
我從大學部畢業以後,就沒有和李老師見過面,一直到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李老師來校參加古文字學研討會。我才又有機會接觸到他。事實上,流水三十年間,曾經斷斷續續聽到李老師的一些動態,包括他在新加坡講學時和王叔岷老師失和,以及他和王老師又先後回到南港中研院史語所的一些消息。但那時候,因為他和王叔岷老師已經失和,有了誤會,而王老師不但也教過我,並且在我籌備中研院文哲所時,擔任諮詢委員多年,時常連繫,因而我去大學賓館見李老師時,不知為什麼,氣氛真的有點尷尬,也不知從何談起才好。記得當時只是向李老師報告,大二時聽了他的課,受益良多,一直感念在心。這些年來雖然荒廢了,但將來如有機會,我仍然願意從頭學起。
二○○九年夏天,我從香港退休返臺,決定不再教書,要專心讀書寫作。不但要讀以前未讀之書,而且要重溫以前讀過的好書。好書當然值得一讀再讀,愈讀一定愈有滋味。如果重溫之餘,能有新的體會,上焉者推陳出新有創見,當然最理想;否則,即使只是檢討舊說,提出質疑,也都值得寫出來,提供給有相同興趣的讀者參考。我覺得這樣做,無論對自己或對別人,都有好處。中國文字學,就是我退休後讀書寫作的計劃之一。它對我而言,是自我修煉;對已經去世多年的李老師而言,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紀念。
幾年來,我一直在持續不斷的閱讀與寫作之中。考慮時間空間的歷史因素,我把中國文字學改稱為漢字學。預定寫三部書。第一部書名《漢字從頭說起》,旨在探討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成書以前的古代漢字,有關它的起源、特質以及演變的種種問題。其中甲骨文、金文部分,出版專書之前,曾在香港《國學新視野》連載,有事先藉此向各方專家請教之意。事實上,我也確實得到一些專家學者的教益,已分別補記在各章節之中。
第二部書名《許慎及其說文解字》,旨在評述許慎的生平事跡,及其《說文解字》一書的內容概要。特別注重許慎的仕宦經歷與經學思想的考證,漢代的六書說,以及《說文解字》一書的敍文、部首的詮釋與分析。因為這些都是了解該書必先解決的問題。其中像談六書次第,許慎為何置「指事」於「象形」之前,像談若干部首的取捨,是否與其經學思想背景有關,等等,筆者在書中都曾論及。書名所以定為《許慎及其說文解字》而不取《許慎與說文解字》,也是有意表示:人人皆可說「文」解「字」,但用「與」字,則許慎是一回事,「說文解字」可以是另一回事。許慎可以說文解字,別人也可以各自有其說文解字。如用「及其」,則書中所論,僅限於許氏該書。這是強調筆者所探討的,是許慎所編撰的《說文解字》一書,而不是一般泛稱的說文解字。
以上這兩部書,兩三年前都已完稿了。第三部書名《說文部首及關鍵字》,到目前為止,都還在分部陸續撰寫中。因為能力有限,涉及的問題又多,不易解決,何時可以完成,實在不敢說。因此徵得出版社同意,先出版這前兩部。
我非常感謝遠流出版公司曾淑正女士的費心編輯,包括配圖、描字,也很高興能陪有興趣的讀者,一起來認識漢字,一起來學習。我覺得我彷彿還在祖父和李老師溫馨的回憶裡。
寫在我的漢字學書前
寫漢字學,是我十幾年來的一個藏之於心卻遲未動筆的願望。
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九月,我考取臺大中文系,註冊入學。本來我在中學時代喜歡的是現代文學及文藝寫作,所以會以臺大中文系為大專聯考的第一志願,也就是為了想成為詩人或新文藝作家。想不到進入臺大中文系以後,受了大一國文葉嘉瑩老師的影響,閱讀與寫作的興趣,竟然由現代文學而逐漸轉向中國古典文學。到了大二,除了葉老師所講授的「詩選及習作」之外,對李孝定老師所講授的必修課「文字學」,也同樣發生濃厚的興趣。
那時候,臺灣各大學中文系的課程,沿襲教育部民國初年所訂的標準,重視傳統經典與人才培育,都規定了一些基本必修課。例如配合「大一國文」及選修的專書課程,詩歌方面,大二必修「詩選及習作」,大三必修「詞曲選及習作」;古文方面,大二必修「歷代(唐宋)文選及習作」,大三必修「歷代(漢魏六朝)文選及習作」。至於傳統小學方面,大二必修「文字學」,大三必修「聲韻學」,大四必修「訓詁學」,分別研讀中國文字的形、音、義。
那時候,李孝定老師由臺大與中研院史語所合聘,原先擔任校長室秘書,後來轉任中文系教授,講授「文字學」。教我們這一班,是他教「文字學」的第二屆。據他自己說,他不會講課,請大家多多包涵。那時候,坊間買不到什麼參考書,他請人刻印鋼板,印發馬宗霍的《文字學發凡》與唐蘭的《古文字學導論》上半部給我們當講義,要求我們自己課外研讀;他上課時則只提示書中的一些要點,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由他舉一些例字,講漢字的起源與演變,並沒有預定的進度。
記得開學不久,有一次上課,他先用粉筆在黑板上畫個像「田」字的鬼頭,下畫似乎人體四肢、雙手高舉的線條,說這是古文字,要同學猜是什麼字。有同學說像「異」,他那寬大而略嫌蒼白的臉上,竟難得露出笑容。接著他又寫了「鬼」字和「思」字,問同學二字的上半像什麼。「鬼」頭不難解,但「思」的上半為何是「田」,則無人回答。這時候,李老師才告訴我們,上半的「田」不是「田」,而是頭腦「囟」部的形狀,是隸變時訛變了形體。像「異」字原來就是「象人首戴甾之形」,確實有人解釋為鬼頭。
也就從那一堂課起,他開始連續幾週講解《說文解字》人部、手部、共部等等若干例字,從甲骨文、金文以迄隸書形體的演變以及相關的一些問題。然後說,希望同學自動去翻閱《說文解字詁林》的哪些部首及屬字。一切看似隨興而發,沒有事先準備,但我仍然覺得他講得很精彩,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特別是他講「保」字、「沫(頮)」字時的神采,一直深印在我的腦海裡。很多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在教我們「文字學」時,正在撰寫《甲骨文字集釋》,也才知道漢字的起源與演變,一直是他主要的研究課題。
記得那時候,常在晚飯後,到總圖書館(今已改為校史館)西翼二樓的「參考股圖書室」,去翻閱丁福保的《說文解字詁林》,隨興之所至,挑有興趣或容易了解的部首及屬字看,看不懂的地方就闕其疑而略過。但久而久之,經過前後對照,互相印證,原先不懂的部分,竟然有的也可以領會出一些道理,因此使我對「文字學」這門課,逐漸產生興趣。
記得那時候,系裡開設的專書課程中,還有一門由董作賓教授主講的「甲骨學」,供高年級及研究所的同學選修。我沒有見過董老師,只因對「文字學」有了興趣,又因按照慣例,系所開設的課程,只要主講的老師不反對,誰都可以去旁聽。所以在大二上學期中途,我曾經不自量力,跑去文學院特二教室旁聽「甲骨學」的課。教室小,人不多,只見一位中年瘦小的老師在臺上講課,我以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董作賓教授。哪裡知道他講課時,好幾次被臺下另一位瘦小的老先生打斷,加以糾正、補充,而他竟敬謹苦笑著唯唯稱是。後來我才知道:在臺上講課的是金祥恆先生,在臺下發言的才是董作賓教授。金先生是義務幫董老師「講」課。這嚇得我只旁聽了一次,就不敢再去了。從此乖乖的在「參考股」看《說文解字詁林》。
那時候,我常常想起去世多年的祖父。記得剛進小學時,讀過私墊的祖父教我認字。他曾經指著家裡廳堂的大門問我:「門」這個字像不像那兩扇大木版門的形狀;曾經告訴我「問」與「聞」二字,就是人與人在門內門外互相問答,加上嘴巴、耳朵的形狀組合而成的。最有趣的是,他還教我認識「愛」這個字,說它是一個人用手捧著心交給另一個人。這些童年往事,原先以為是祖父開玩笑,但在我大二學「文字學」看參考書的時候,卻常常浮上心頭來,給我增添很多溫馨的回憶。
大二下學期,有一次上課時,李老師提起了清代段玉裁、王筠、朱駿聲、桂馥《說文》四大家的著作,說我們系裡都有完備的藏書,又說甲骨文四大學者羅雪堂、王觀堂、郭鼎堂、董彥堂「四堂」之一的董彥堂(董作賓教授)就在我們系裡,有如此理想的學習環境,應當有同學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下課後,李老師特別找我去談話。他說看了我上學期的期末考卷,知道我看了很多課外參考書,所以給了我高分,希望我能再接再勵,將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當時我受寵若驚,當然一口答應了。
雖然一口答應,但我也對李老師實話實說。說我雖已立志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我最感興趣的仍然是純文學和文藝寫作。記得當時李老師寬大的臉上怔了一怔,似有不悅之色,只這樣說:「你知道陳夢家吧?他寫新詩,但也研究古文字。」我不敢多說一句話。
從此,除了上「文字學」課之外,我總是有意無意間避開李老師。其實我對李老師說的是真心話,雖然我也愛「文字」,但我真的更愛「文學」。
過了兩年左右,大約在我大學畢業前後,李老師離開了臺大。據說和王叔岷老師一樣,即將出國講學。從此失去了聯絡。後來我在臺大中文研究所讀碩士班、博士班的時候,仍然一本初衷,在詩詞純文學的天地裡討生活。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清代常州派詞學,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清代詩學,這些都是我的興趣所在。
上博士班時,經由屈萬里老師推薦,我參加了「儀禮復原小組」,並承孔德成老師不棄,主動要我旁聽他講授的「金文選讀」,使得我又有機會接觸殷周古文字。那時候,大多數的老師、同學都以為我醉心於古典詩詞,很少人知道我同時也愛好文字學。大概很少人知道我在博士班念書時,學弟之中,張光裕、邱信義、黃沛榮他們由屈老師指導有關古文字的碩士論文,都曾由我先幫忙修飾文字,使得我有機會對他們的大著先睹為快;大概也很少人知道我從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校外兼課教書開始,在講課時就常引用古文字來輔助教學。例如教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且以汝之有身」的「身」,先把它金文、小篆的字體畫出來,原來就是女人懷孕的形狀;教《左傳》的〈曹劌論戰〉,先說《史記.刺客列傳》中,「曹劌」作「曹沫」,並進一步說明「劌」和「沫」、「湏」、「頮」、「靧」等字形音義之間的關係,等等。這種教法,似乎頗能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所以我臺大博士班畢業以後,留校任教,無論教什麼課,只要與古文字有關的詞語,我都會「依樣畫葫蘆」、「老王賣瓜」一番。尋思起來,這和當初上「文字學」的課,受到李老師的啟蒙大有關係。因此,我常常想起李老師當年對我的期許。我覺得辜負了他當年的好意,如果有機會,應該對李老師說聲「對不起」。
我從大學部畢業以後,就沒有和李老師見過面,一直到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李老師來校參加古文字學研討會。我才又有機會接觸到他。事實上,流水三十年間,曾經斷斷續續聽到李老師的一些動態,包括他在新加坡講學時和王叔岷老師失和,以及他和王老師又先後回到南港中研院史語所的一些消息。但那時候,因為他和王叔岷老師已經失和,有了誤會,而王老師不但也教過我,並且在我籌備中研院文哲所時,擔任諮詢委員多年,時常連繫,因而我去大學賓館見李老師時,不知為什麼,氣氛真的有點尷尬,也不知從何談起才好。記得當時只是向李老師報告,大二時聽了他的課,受益良多,一直感念在心。這些年來雖然荒廢了,但將來如有機會,我仍然願意從頭學起。
二○○九年夏天,我從香港退休返臺,決定不再教書,要專心讀書寫作。不但要讀以前未讀之書,而且要重溫以前讀過的好書。好書當然值得一讀再讀,愈讀一定愈有滋味。如果重溫之餘,能有新的體會,上焉者推陳出新有創見,當然最理想;否則,即使只是檢討舊說,提出質疑,也都值得寫出來,提供給有相同興趣的讀者參考。我覺得這樣做,無論對自己或對別人,都有好處。中國文字學,就是我退休後讀書寫作的計劃之一。它對我而言,是自我修煉;對已經去世多年的李老師而言,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紀念。
幾年來,我一直在持續不斷的閱讀與寫作之中。考慮時間空間的歷史因素,我把中國文字學改稱為漢字學。預定寫三部書。第一部書名《漢字從頭說起》,旨在探討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成書以前的古代漢字,有關它的起源、特質以及演變的種種問題。其中甲骨文、金文部分,出版專書之前,曾在香港《國學新視野》連載,有事先藉此向各方專家請教之意。事實上,我也確實得到一些專家學者的教益,已分別補記在各章節之中。
第二部書名《許慎及其說文解字》,旨在評述許慎的生平事跡,及其《說文解字》一書的內容概要。特別注重許慎的仕宦經歷與經學思想的考證,漢代的六書說,以及《說文解字》一書的敍文、部首的詮釋與分析。因為這些都是了解該書必先解決的問題。其中像談六書次第,許慎為何置「指事」於「象形」之前,像談若干部首的取捨,是否與其經學思想背景有關,等等,筆者在書中都曾論及。書名所以定為《許慎及其說文解字》而不取《許慎與說文解字》,也是有意表示:人人皆可說「文」解「字」,但用「與」字,則許慎是一回事,「說文解字」可以是另一回事。許慎可以說文解字,別人也可以各自有其說文解字。如用「及其」,則書中所論,僅限於許氏該書。這是強調筆者所探討的,是許慎所編撰的《說文解字》一書,而不是一般泛稱的說文解字。
以上這兩部書,兩三年前都已完稿了。第三部書名《說文部首及關鍵字》,到目前為止,都還在分部陸續撰寫中。因為能力有限,涉及的問題又多,不易解決,何時可以完成,實在不敢說。因此徵得出版社同意,先出版這前兩部。
我非常感謝遠流出版公司曾淑正女士的費心編輯,包括配圖、描字,也很高興能陪有興趣的讀者,一起來認識漢字,一起來學習。我覺得我彷彿還在祖父和李老師溫馨的回憶裡。
二○一九年五月初稿,二○二○年四月初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