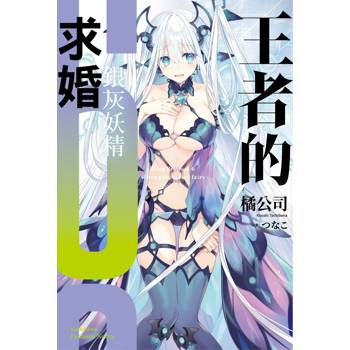認識台灣原住民族,不可不讀的人文經典
台灣人類學先驅巨作 ╳ 台灣古道研究權威譯註
森丑之助──
台灣原住民調查第一人
循著足跡,可以見識到以往文章中從未出現的高山祕境
「森丑之助的著作與論述,是百年前異文化互相衝擊的現場,也是深藏於台灣高山的原住民真實的見證。」──楊南郡 森丑之助自日治初期走遍台灣山地部落,踏查規模遠超過同期到台灣研究原住民的伊能嘉矩和鳥居龍藏,是在台山地部落最久的學者。有關台灣原住民部落的調查報告,不僅記錄了百年前「文明」與「異文化」衝突的現場,並見證了台灣高山原住民的真貌,處處充滿人道關懷。本書譯註者楊南郡花費多年蒐集森丑之助散佚各處的資料、史籍,甚至親身循著他當年足跡踏勘曾造訪的部落,完成此一台灣探險紀錄,同時對森丑之助的傳奇一生做了動人描述。
【典藏推薦】
徐如林(自然文學作家、知名古道探勘及登山學者)
陳耀昌(醫師、台灣史小說作家)
陳偉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孫大川(前監察院副院長、台大及政大台文所兼任副教授)
夏曼.藍波安(海洋文學家)
雪羊(知名登山部落客)
蕭宇辰(「臺灣吧」、「故事 StoryStudio」共同創辦人)
宋文薰(台灣考古學家)
笠原政治(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授)
劉克襄(作家、自然觀察者)
森雅文(森丑之助曾孫)
「我寫的書就是我的紀念物。」在楊南郡老師故世五週年時,遠流出版公司用「典藏紀念版」的方式再度出版這套書,讓楊南郡老師能夠繼續活在讀者的心中。
──徐如林(自然文學作家、知名古道探勘及登山學者)
楊老師的書代表了「台灣學」,不會因時間而褪色;就好像「楊南郡」三字,代表了「台灣魂」,將永遠長存在台灣人的心中。
──陳耀昌(醫師、台灣史小說作家)
楊南郡老師豐富的譯註……我認為這是原來文本以外的重要參考資料,也像是楊南郡老師與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的對話。
──陳偉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感謝楊南郡先生,他用手、用腳翻譯、訂正、註釋、消化了調查時代所留下來的資產。……他用再踏查的堅實證據,告訴我們中央山脈並不是沉默不語的,台灣的文化和歷史也不是漢人的獨白!
──孫大川(前監察院副院長、台大及政大台文所兼任副教授)
楊南郡先生就像一位孤寂的航海家,在廣袤無邊際的太平洋海上牽著他的夫人徐如林女士,尋覓北極星照明的那座港澳登岸。沒有楊南郡先生用生命譜曲,【台灣調查時代】系列鉅著就不可能像宇宙上天空的眼睛,襯托出夜空深深的奧妙。
──夏曼.藍波安(海洋文學家)
楊南郡老師不僅賦予登山深邃的文化意涵,讓珍貴史料跨越語言藩籬重見天日,更讓後世得以跟著偉大學者們的踏查足跡,依循故道找回台灣的根與山岳的魂,開啟台灣文化的耀眼新章。
──雪羊(知名登山部落客)
楊南郡先生在《生蕃行腳》書中所投注的精神,絲毫不遜於森丑之助本人。我敢說這一本書,不僅是台、日兩地最完整的森氏研究紀錄,保證也是全世界最完整的森氏研究。
──宋文薰(台灣考古學家)
森氏畢生獻身於台灣原住民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已成為百年前台灣原住民的珍貴證言。……由於楊南郡先生的努力,森丑之助一生被埋沒的作品始能重見天日。
──笠原政治(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授)
不論就譯註者生平精采的野外追探,或者是二十世紀初台灣自然科學的踏查,如果鳥居是最漂亮的分號,伊能是華麗的句號,那麼森就是最神祕的驚歎號了。
──劉克襄(作家、自然觀察者)
在楊南郡先生超乎常人的努力下,家祖森丑之助一生的業績得以彰顯,並介紹給現代的台灣各界讀者。對於這件事,本人內心充滿感激,並深感榮幸。
──森雅文(森丑之助曾孫)
【系列特色】
●台灣南島文化探源與田野調查的珍貴文獻史料
日治時期的人類學家與博物學者──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數度來到台灣,調查研究台灣原住民族,開啟台灣田野調查的先路,留下珍貴且浩繁的報告、資料與圖像紀錄,保存著各族群豐富多樣的文化原型。不僅是認識台灣原住民族不可不讀的文化寶庫,也是早期台灣高山聚落的地理學、植物學、人類學、社會學的重要文獻史料。
●台灣高山遺址與文史調查先行者──楊南郡先生最權威、完整譯註
楊南郡先生是台灣登山界的傳奇人物,是攀登台灣百岳風潮的開拓者之一,在諸多登山行旅者和古道探險家之中,他也是看見原住民部落與古道遺跡文化價值的第一人。他從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的報告及著作當中,精選出跟台灣相關的部分譯為中文,並且透過綿密的田野踏查,將史料一一印證後詳盡譯註,補充大量的註解與圖片,完成【台灣調查時代】系列,讓珍貴史料得以出土重現。
對於楊南郡先生的譯註,日本學者於笠原政治給予高度肯定:「每一本譯註卷首都刊載經過嚴謹考證的人物誌、勘查足跡以及學術業績等,並於譯文中詳盡標示注解、探險調查路線圖、年譜及著作目錄等,是楊南郡以其深厚的日文底子,再加上其多年登山、古道調査以及採訪原住民等所培養的廣博知識,作為譯作整體極厚實的基礎,才有這獨樹一格的譯作出版。」
●深入理解台灣豐富多元的異質文化,促進族群之間的了解及尊重
已故人類學家及民族學者劉斌雄先生在【台灣調查時代】總序〈台灣的田野是無盡的寶藏〉文中指出,台灣能保存許多異質性極高的文化或族群,是拜其高山林立、地理複雜所賜,就像海洋需要有洋流的匯集才有豐富的魚群,台灣在異文化的錯綜交織下,正是難得的大漁場。【台灣調查時代】不僅保存了台灣原住民的社會文化、地理生態和價值觀,透過「他者」(日本學者)的眼光和書寫,也呈現出不同文化視角的碰撞,可增進族群之間的了解及尊重。
●認識台灣原住民文化,同時認識三位「影響台灣的日本人」
【台灣調查時代】系列每本書的卷首,都有楊南郡先生撰文的〈學術探險家〉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的小傳,深入描述「台灣調查三傑」的生平事蹟、學術貢獻、研究精神和勘查路線等,可作為年輕學者和文史工作者的學習典範。而從歷史角度來看,鳥居龍藏等人類學三傑,也足為台灣歷史重要的一部分。
作者簡介:
森丑之助(1877-1926)
日本京都市五條室町人。年少就讀於長崎市長崎商業學校,並學習中國南方官話。十六歲棄家、輟學,決心過流浪的生活。一八九五年,以陸軍通譯身分抵台,隨軍隊移防台灣各地,開始巡察台灣原住民各社,所見所聞激發他調查研究台灣「蕃地」的雄心壯志。
一八九六年,結識正在台灣東部進行調查旅行的鳥居龍藏,日後成為鳥居氏幾度在台的助手兼嚮導、翻譯。一九○○年,與鳥居氏展開大規模的人類學調查,一度捲入「社蕃」的復仇戰,險遭馘首之禍。此行兩人登上玉山主峰頂。此後森氏即潛心台灣人類學、地理學、植物學……之調查,足跡遍及台灣全島。一九一三年,森氏短暫告別台灣。一九一四年,復應台灣總督府之邀,重返台灣擔任蕃族科「囑託」,並整理資料。一九二六年,由於台灣原住民前途問題暨種種不如意,由航行台、日間的輪船上投海自殺。得年四十九歲。
著作除了業已成書的《台灣蕃族志》一卷及《台灣蕃族圖譜》二卷之外,其他散見於當時的台灣與日本各報紙、雜誌。本書為台日兩地首次對森氏著作、論文目錄較完整的整理。
譯者簡介:
楊南郡(1931-2016)
台灣省台南縣人,一九五五年畢業於台大外文系。曾擔任英文教師、外國駐台機構職員。在工作之餘,從事登山、台灣南島諸語族文化、古道、遺址探勘研究,長達五十年之久,為國內最富盛名的登山前輩暨古道、原住民調查專家。一九七六年即完成台灣百岳的攀登目標,並開拓許多新的登山路線,是台灣登山運動的先驅。
其文筆流暢自然,博聞強記,考證精微,無論調查報告或創作譯述,均獲各界高度評價,曾榮獲吳三連獎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金鼎獎、順益基金會個人成就獎、省文獻會傑出文獻工作獎、教育部原住民譯著甲等獎等,並於二○一○年獲國立東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二○一一年獲選為國立台灣大學傑出校友。二○一六年過世,獲頒總統褒揚令,原住民族委員會追頒「一等原住民族專業獎章」。
著作包括:《台灣百年前的足跡》、《尋找月亮的腳印》、《浸水營古道》、《與子偕行》、《合歡越嶺道》、《能高越嶺道穿越時空之旅》(以上三書與徐如林合著)等。
譯註有:《探險台灣》、《平埔族調查旅行》、《台灣踏查日記(上、下冊)》、《生蕃行腳》、《鳥居龍藏》、《鹿野忠雄》、《台灣百年花火》、《台灣百年曙光》、《台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究》、《山、雲與蕃人》、《東南亞細亞先史學民族學研究(上、下册)》等。
章節試閱
《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內文試閱
生蕃行腳
從基隆到高雄
(前文略)這裡是細雨綿綿的台灣基隆港,大沙灣近前雨霧迷濛中的一棟洋樓,原來是屬於台灣總督府的基隆海關。這一棟建築物外表不怎麼起眼,是清國政府時代所遺留的海關大樓舊址,日軍攻略基隆後,首任台灣總督最早在這裡設置總督府。附近海岸密生著巨大的膠木和林投樹,以及屬於海岸植物的馬鞍藤、黃槿等。淺灘中點綴著疏疏落落的水筆仔,長長的果莢垂掛於水面,看起來生動有趣。[註9]
這時候,不知名的海鳥上下斜飛。放眼一望,遠處的小基隆到大基隆那邊,景物全在一片雨霧和煤煙中,浮現出沈悶的鉛灰色。中國戎克船上鮮艷的旗子迎風飄揚,從那裡傳來一陣一陣震耳的鑼鼓聲,接著迸出猛烈的鞭炮聲,大概是船上正在舉行出航前的祭典罷。
對面的陸軍運輸部軍營大門前,不斷的有兵士三三五五經過。基隆大街小巷到處有叫賣聲,挑擔賣布的小販搖動著小鼓,發出咯咚、咯咚聲,招引行人注意;也有人吹著海螺,原來是賣肉小販的叫賣聲。在岸上等候船客的舢舨船主,正在拉胡琴打發時間,琴聲穿過沈鬱的雨聲,幽幽地傳過來。
鳥居先生的船進基隆港後,他的老同鄉,同時是海關稅務員的高木隆二,駕小艇把他接到海關官舍。這是鳥居先生第四次渡台,從現在起他和我將作全島蕃地調查旅行。[註10]
次日,我和鳥居先生一起到台北,向台灣總督府交涉到蕃地旅行事宜。文書課長木村匡先生給我們一封向各地蕃務單位照會的「添書」,在學務部官員幫忙之下,雇用曾經受過日語教育的台北士林人張君楚。[註11]
我曾經在內地學過清國官話,但是不太會講台灣話,調查旅行中要用到本地苦力,所以需要張君幫忙連絡。我們在台北和基隆分別辦好「入蕃許可」和其他應該準備的事項,然後在基隆海關官舍住三天,等候開往高雄的船隻。[註12]
回想二十五年前,我們三人於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一月四日〔一月十五日〕,在眾多朋友歡送下走到陸軍運輸部臨時搭建的棧橋,搭乘海關小艇駛向開往高雄的汽船。在碼頭歡送的朋友中,有以前服務於台灣守備隊時的同事──加藤、河內、鈴木及青木諸兄、市內的朋友,以及高木夫婦。我記得高木太太背上的小兒子揮動著紅葉般紅潤的小手,也記得朋友們在雨中給我們送行的情誼。[註13]
我們所搭乘的船是排水量一千五百噸級的公務船,船名已忘記了。當時的印象是船很髒而且設備不好,但是在當年算是新式的汽船。從基隆出航後,途中暫時停靠於淡水,然後直駛澎湖群島的媽宮城〔馬公港〕,城內建築很像畫冊上的海龍王王宮。當時駐紮著很多陸軍和海軍守備兵。因為距離啟航還有一些時間,我們去訪問澎湖廳及軍營裡的舊識,和老朋友圍爐吃海鮮火鍋,暢談台灣總督府施行軍政年代的軼事。 這是我第三次的澎湖行,鳥居先生以前曾經來過一次,這是他第二次趁汽船停靠馬公的片刻,上岸來和老朋友敘舊一番。[註14]
一般的汽船只沿著海岸航行,途中要停靠於「大安港」、「梧棲」、「塗葛窟」等港口,然後才到安平,但是我們搭的是特派公務船,所以經由媽宮城後直接航向安平港。[註15]
船駛入安平港後,我們先到台南縣官署拜訪知事和內務部長,請官員照料我們在轄區內蕃地旅行。擔任殖產課長的舊識藤根吉春技師特別給了我們各種協助。聽說海關稅務員角儀太郎現在服務於設在安平熱蘭遮城內的海關,我們也做了禮貌上的拜訪,最後又回到安平港搭船。[註16]
台南是典雅的史蹟古都,當時還沒受到人為的破壞。如果詳述台南的印象記,我可能會把它描繪成一幅富有情調的繪畫,不過閒雅的文字留待來日有空暇時再寫,現在敘述安平港和航行於安平、高雄間在船上所見的景物罷。
明治年代的安平熱蘭遮城舊址雖然已傾頹,但還保留著三百年前荷治年代詩一般優美的容貌。當年荷蘭人手植的馬尼拉麻和鳳凰樹老木,依然伸出茂盛的枝葉……,此情此景,足夠勾起懷古的情緒。現在還有很多外國商賈居留於安平,難怪五、六個國家在這裡設置各自的領事館,而且濃密的椰子林中可以看到低矮的洋樓、洋館,以及椰影搖曳中升起的各種外國國旗,正在綻放異彩!
海濱停放著很多竹筏和小型戎克船,還有四、五艘外國汽船。旭日直射下的海面,冒出數不清的水蒸氣冉冉上升。啊!我看到熱帶的雲彩了。時序還是正月,但是映照著南國熾熱陽光的大自然現象,充滿著詩情畫意和多樣性的色彩變化,這是我們在日本內地所看不到的光景!
我和鳥居先生斜靠在甲板上的藤椅,悠然看風景,也暢談文學和地學的看法,談累了就各自沈入冥想中。陸陸續續地許多漁夫用竹篙撐動竹筏要出海捕烏魚,晨光中看見無數的竹筏勇敢地駛向海洋的情景,真是難得的入畫題材。
暮色蒼茫中我們的汽船緩緩駛進打狗港,停泊於離麥耶斯氏洋樓不遠的地點。[註17]
築港以前的打狗港,比現在有更濃厚的熱帶性氣氛。就海岸植物而言,這裡的紅樹林及其他海岸性植物,呈現典型而完整的植物景觀。物質文明逐漸破壞大自然的妙趣,這是很不得已的事態,但是我堅持說,人的生活不完全靠物質。天然紀念物及史蹟物的保存、保護都很重要。日本人習慣於先破壞天然美景,然後好像要哄小孩似地建設小規模的人工公園。如果能夠早些警覺,應該是要善加利用天然的景物,只要稍加一點人工修飾,相信能夠完成非常好的公園設計。哎,好可惜喲!
地名叫打狗,不久以前政府把台語的「打狗」(Takao)譯音為「高雄」,行政上當時屬於台南縣,但是二、三年前由於行政區域的改制,高雄已獨立成為一個州,叫「高雄州」了。[註18]
從高雄到枋寮
上面敘述了沿途所看到的景物。我們在平地方面的學術工作,是探查石器時代的遺跡與遺留物,也要調查平原平埔蕃的今昔狀態。蕃地的學術調查要從高雄方面開始。
我們在高雄港下船,下船的地點是旗後〔旗津〕。當時高雄還沒開始築港,因此沒有造就港邊新生地,港內處處有林投樹成林,只有旗後一地才有繁華的街市,其他地方都是小漁村。雖然人數不多,西洋人都住在旗後,市街有濃厚的漢人色彩。
上岸後,我們採陸路前往鳳山,過了下淡水溪〔高屏溪〕就到阿猴〔屏東〕。離開陰鬱的雨港基隆,來到萬里晴空的南部,感覺這裡的景物顯得明亮活潑。
陸軍已架設軍用輕便鐵路,連接台南、高雄和鳳山,主要是供軍事輸送,也准許平民搭乘。
鳳山是清代鳳山縣官署所在地,周圍仍有當時所建造的城牆。城內有街市,有日本守備隊駐紮,也有不少日本人僑居於此。我們來的時候,鳳山縣已撤廢,只設一個辨務署,署長是東京帝國大學筧法學博士的父親。
當時的鳳山比現在更熱鬧,熱鬧的程度可謂現今鳳山的數倍。因為景氣好,光是「料理屋」〔酒家〕就有五、六家,數十名「阿嬌」好比是路旁的花朵,供過路的客人摘取,暫時紓解旅情。當時的鳳山是台灣南部除了台南以外的唯一街市,而二十五年後,現在的鳳山則像一盞燈火被吹熄了一般,沒有活力了。
從鳳山起開始步行。我們坐竹筏過下淡水溪,溪的對岸是阿猴的範圍了。當時的阿猴街沒有城牆,到處有雜木林,有一條馬路,兩旁只有幾間簡陋的茅屋毗鄰而立,不像是一個真正的街市,只有濃厚的鄉村風味。像辨務署也設於一座廟裡,把廟當做辦公廳。這裡有不少廣東人,風俗和其他地方大不相同。一般而言,鳳山以南的風俗比較純樸,本地的漢人似乎有剛毅的民性。
從阿猴出發,前往東港。在東港的辨務署接洽我們進入力里社蕃地事宜。原來,阿猴方面蕃地屬於東港辨務署管轄區內。[註19]
我和鳥居先生從打狗出發,經由鳳山、阿猴到東港,全程由數名憲兵或武裝警察荷槍隨行保護;從東港起入山,只有武裝警察隨行。因為當年土匪出沒無常,行旅常常遭到殺害,一般而言,每天有一次或二次,官署派警衛保護遞送郵件的隊伍,行人趁這個機會跟隨官方隊伍旅行,以便受到保護。我們受到特別待遇,當局為我們兩人指派四、五名武裝警察隨行。
東港是高雄以南唯一的貿易港,港內停泊著多艘來自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戎克船。岸邊有等待船隻運出的麻竹(竹筏的材料)、黃麻、樹豆、胡麻、蕃薯籤(曬乾的地瓜細條),堆積如山。出口的農產品中,本地特產黃麻占大宗。往日的東港腹地是胡麻及黃麻的主要產地,但是今日這些農作物已經被甘蔗取代了,到處是蔗田。
東港也是我舊遊之地。回想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歲末,我從東海岸回到西海岸來,立即南下到東港,從東港進入大武山的周邊,巡訪各蕃社。次年一月,在東港客棧和到南部來視察的小藤博士及山崎直方先生邂逅,在異鄉共渡新春佳節以來,又過了三年,我陪鳥居先生再度來東港。[註20]
我現在執筆撰寫本文時,不由得憶起在台灣見面後,又過了二十多年,我在東京帝國大學地理學教室,和主任教授山崎博士一起,圍爐看窗外雪景的情景。當時,我一邊翻看山崎博士在東港過台灣新年時所作的素描,一邊和他縱談古今。這是我常常懷念、常常憶起的往事之一。
在東港的第一夜,我和鳥居先生相偕到街上的一家戲院站著看戲。這是有關陳三五娘的故事,劇情已由幾年前來台灣旅遊的作家佐藤春夫譯成一篇文章,作為「台灣土產」帶回日本。戲中的對話是清國官話,不是台灣話,所以甚至本地的漢人也只能看戲中人物的動作和手勢,來判斷劇情。鳥居先生對漢語一竅不通,看得莫名其妙,我和張君雖然也不太懂,卻忙著給他解釋故事的梗概。[註21]
東港是位於台灣西南海岸的一個港口,船隻進出頻繁。台灣島南端有面向台灣海峽的車城射寮港和面向巴士海峽的南灣大板埒港,都是小得微不足道的港口。從華南啟航的戎克船大都由東港出入。東港街市狹窄,但卻是熱鬧異常,到處瀰漫著海港特有的浪漫情調。
從東港啟程,通過石光見的原野到水底寮,在這裡做入山準備。水底寮是這一帶的大村落,村裡有名字叫黃漢生的漢人擔任「生蕃通事」。我們決定雇請這位老人陪伴我們進入蕃地。村子裡也住著一個有名望的人,人家稱他為周望三大人,他對地方史瞭若指掌,簡直是一部活的歷史,因而向他請教種種問題。[註22]
台灣割讓後,為增援台灣征討軍而調來台灣的乃木希典將軍第二師團,就在水底寮西側的枋寮登陸,所以枋寮是有歷史淵源的地方。市街北端有一座廟,守備隊駐紮於廟內。上次來的時候,看到我服務於陸軍守備隊時認識的軍官,但是這次重遊舊地,人已被調走,只看到陌生的面孔。[註23]
我們在水底寮看到下山的排灣族。他們是來自力里社和萃芝社一帶的蕃人,男女都頭戴用美麗鮮花編成的頭環;頭目及勢力者都披著雲豹皮衣,腰跨用老鷹翎羽裝飾的長刀,悠然闊步於街頭,光是看到這情景,就十足興起歡愉色彩的旅情![註24]
到街上來買東西的漢人,都揹著蕃人編製的藤籠。不管是漢人或蕃人,每一個人都在嚼檳榔,他們的嘴唇紅紅的,牙齒已被檳榔汁染成黑色。不管到那一家,住民習慣先端出一個檳榔盆,上面堆滿用荖葉包好的檳榔子。鳥居先生和張君楚不會嚼檳榔,連看都不看。我曾經在東海岸和南部「南蕃」〔排灣族、卑南族或南部阿美族〕居住的地方吃過檳榔,所以入鄉隨俗,高高興興地從主人手裡接下一顆,放進嘴裡。
我看到街上一個小店,主人是已漢化的蕃人,娶漢女為妻。他幼小的時候,被本地的漢人收養,長大後繼承家業。山地蕃人在漢人村落開店,是一個罕見的例子。
我也記得在高雄看到一個出身於恆春龜仔角社的蕃女。她曾經和被派駐鵝鑾鼻燈塔的外國人相愛,後來乾脆和這個外國人同居於燈塔宿舍。台灣割讓後,清國官吏全部撤出台灣,在鵝鑾鼻為清國服務的這個外國人也離開了台灣。依照蕃地習俗,已嫁給平地人或已經與外國人同居過的蕃女,因為蕃社禁忌(Parisi),不可以重返部落居住。很不得已地,她和燈塔內一個漢人換油工同宿同飛,最後二人搬到高雄定居下來。我想,異族之間的愛慕、交遊、同居,最後變成一個棄婦的故事,只要稍加潤色,就可以舖展成一篇現代版的「陳三五娘」故事,可能會比戲中所唱的故事還要精彩啊。[註25](文未完,全文請見《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
【譯註|楊南郡】
9. 大沙灣位於基隆外港與內港交接處東南側,在港灣整建以前是一個小小的淺沙灣,清法戰爭中法國艦隊從這裡登陸激戰之地。今已有碼頭及長榮海運的貨櫃場等。 10. 鳥居龍藏的船於一九○○年一月七日抵達基隆港,隨即換乘海關小艇到有小碼頭的海關宿舍。當時的基隆港還沒建設完整的碼頭供大船停靠,所以船客在港內換乘小船。森氏從台北趕來迎接鳥居。 11. 添書,指隨同信件或文書寄出的另篇文字,目的是照會對方,或向對方介紹、引薦持信者。 12. 雇用講台灣話的張君楚擔任譯員,因為在平地和山麓地帶所用的苦力,以及所要接觸的人都講台灣話,森氏的中國官話派不上用場。按「苦力」,是清代及日治時代初期通用的名詞,原來是歐洲殖民官僚對印度及中國苦工的稱呼,英文寫成Coolie。鳥居和森氏搭船出發前的行動,依照鳥居本人於同年寄自台灣的五封信,日期分別是一月七日、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及十八日,他於一月九日起到台北辦理手續,其間住進殖產局技師田代安定的官舍,同時幾乎每天都見到伊能嘉矩,得到田代和伊能的幫忙。幾天後回到基隆候船,大概是三天左右在基隆到處跑,於獅球嶺一帶撿到石器,十五日搭乘汽船「明石丸」從基隆出發,前往台南。 13. 事隔二十四年,森氏記得在碼頭被歡送的情形,卻不記得船出航的日子,以為是一月四日。森氏於一九二四年寫本文,距離一九○○年調查,已經過了二十四年,文中森氏都寫二十五年。 14. 當時航行的船都是定期班論,船採反時針方向環繞台灣一周,沿途停靠於每一個港口。但是本文中森氏說他們搭公務船,航次和停靠港口,與一般的客、貨兩用班輪不同。 15. 梧棲指台中縣梧棲港,今已擴建為台中港。大安港是地名,也是港口名稱,位於大安溪出海口南側。塗葛窟,正式寫法是塗葛堀,位於大肚溪出海口北岸,今水裡港位置。據安倍明義的《台灣地名研究》,清道光初年以後,梧棲港被流砂所淤塞,船舶改從大肚溪口塗葛堀進出,因而後者也被叫做梧棲港。以上各港口是清代以來有中國戎克船進出貿易的舊港,日治初期梧棲港(含塗葛堀港)被指定為特別輸入港。 16. 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來調查時,台南縣包括今日分別屬於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及屏東縣全境。他們拜會台南縣最高首長「知事」,請求協助台灣南部蕃地旅行。 17. 原文寫船停泊於「マイヤスの邸宅」前面,不知指那一棟洋樓,詳情待查。 18. 大正九年(一九二○年)的大規模行政改制,結果,舊台南縣分成台南州和高雄州,高雄州的行政轄區包括今高雄市、高雄縣及屏東縣。另外,日語漢字「高雄」,唸Takao,亦即打狗。 19. 日人領台之始,採取懷柔主義,因而於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三月頒布撫墾署官制,在平地與蕃地接壤的重要據點,設置撫墾署多處,掌管蕃地綏撫與拓墾事務。明治三十一年六月,由於地方官制的改革,廢除撫墾署制度,其主要職掌改由新設的辨務署負責。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地方官制再度改制,各縣及各地辨務署全面廢止,全島改為二十廳,轄區內有蕃地的廳署,由總務課協同警務課處理有關蕃人事務。在山地直接負責治安的機構,有隘線監督所、警戒所、分遣所及隘寮等,從明治三十三年森氏等人入山的年度起,山地設有駐在所多處,統轄區內的治安網。辨務署是早期在地方辦理蕃務的行政機構。 20. 小藤和山崎分別是東京帝大地質科教授及助手,他們奉命來台調查台灣地質。 21. 佐藤春夫(1892-1964)是著名的詩人兼小說家。他於大正九年(一九二○年)夏天旅遊於台灣,當時在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擔任囑託的森氏陪他觀光二週,兩人成為好友。佐藤氏的紀行作品,如〈霧社〉、〈殖民地之旅〉等描寫台灣旅行的印象。當時佐藤氏二十八歲,森氏四十三歲。 22. 生蕃通事,指通曉蕃語,辦理番餉的繳納、差役的派遣及傳達政令於蕃社的人,本身是漢人,但工作對象是舊稱生蕃的山地原住民。另有熟蕃通事,則本身是熟蕃(平埔族),但擔任與漢人通事一樣的工作。清代通事,部分是由蕃社自雇,部分由官署指派,視蕃社開化程度而定。清光緒十四年蕃社改制後裁撤通事額缺,社務及社租事務歸屬頭目及由熟蕃通事改稱的董事辦理。日治初期仍有像黃漢生的通事,但職權大不如前,只是被蕃社所雇用,或依照習慣幫助頭目對外連絡而已。另外,石光見是平埔族部落名,石光見與南邊的水底寮的情形,依照明治四十三年實測地形圖,兩村以東盡是原野,舊稱大響營。森氏一行人從東港南行,經石光見到水底寮,準備入山。當時的水底寮比鄰村枋寮還要大,枋寮之北有番仔崙,都是漁港。山區排灣族下山交易,都來枋寮,後來水底寮形成新聚落後,便改到水底寮,水底寮變成入山門戶,同時是通往後山的三條崙古道起點。 23. 森氏於明治二十八年九月來台,當時是以「陸軍通譯」身分配屬於台灣守備軍花蓮港守備隊本部,所以他說「服務於陸軍守備隊時」。 24. 萃芝社的社名很怪,可能是I芒社及加芝萊社的縮寫。 25. 上面所提蕃人、蕃女均指排灣族。舊時候,山麓地帶的原住民從小被漢人收養的例子不少;反過來講,漢人小孩被原住民收養者也有,最著名的例子是瑯E十八蕃社總頭目潘文杰。鵝鑾鼻燈塔是清國海關監督之下,由英商承建,花費二十萬兩,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竣工。台灣割讓前後時期,雇請三名英國海關技術人員,住在那裡負責燈塔運轉與維修工作,另外雇用十七名漢人雜工。明治二十九年,亦即台灣割讓次年,日人派軍艦接管,繼續雇用漢人,但是不再雇用英國人,特派船隻把他們遣送到廈門。森氏講到排灣族棄婦的故事,對象顯然是這三名英國技術人員之一。按龜仔角社位於今社頂一帶,是最接近燈塔的排灣族部落。這一個英國人可能是指George Taylor, Taylor很活躍,任內經常出入於龜仔角社及豬D束社,與住在豬朥束社的十八蕃社總頭目潘文杰交遊,也曾經由潘文杰陪同,前往台東知本社訪問。
《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內文試閱
生蕃行腳
從基隆到高雄
(前文略)這裡是細雨綿綿的台灣基隆港,大沙灣近前雨霧迷濛中的一棟洋樓,原來是屬於台灣總督府的基隆海關。這一棟建築物外表不怎麼起眼,是清國政府時代所遺留的海關大樓舊址,日軍攻略基隆後,首任台灣總督最早在這裡設置總督府。附近海岸密生著巨大的膠木和林投樹,以及屬於海岸植物的馬鞍藤、黃槿等。淺灘中點綴著疏疏落落的水筆仔,長長的果莢垂掛於水面,看起來生動有趣。[註9]
這時候,不知名的海鳥上下斜飛。放眼一望,遠處的小基隆到大基隆那邊,景物...
推薦序
〈總序〉
台灣的田野是無盡的寶藏
劉斌雄(人類學暨民族學家)
我從小就存疑;人為什麼活?人為什麼打仗?後來走上人類學的道路,與期望解開這些疑問,相信是有一些關係的。一九五七年,我首次參加蘭嶼的民族學調查,從事雅美族的系譜採錄工作。我對所目睹、所接觸的現象,有強烈的想知所以然的欲望。譬如說,對系譜一面記錄一面問,「系譜空間」是什麼?其中所蘊藏的豐富資訊,如何開採而取用?雅美人居住的房屋,其大小有顯著的差異,但居住者所組織的都是核心家庭,為什麼其他類型都不見?有什麼定律可以證明大家庭之不可或無法存在?東南亞諸島因有獵首風俗的民族居住而著名,雅美族能擺脫此風俗,為什麼?加上淳樸和睦的民風,待人彬彬有禮,遇落成禮,賀客依序唱著古雅的禮歌,通宵達旦不停,祝福禮主鴻運亨通。他們建構以禮節規範的和平民主社會,我們不得不問,我們不能的,為什麼雅美族能?雅美族不喝酒、不抽煙,把人類的欲望壓低,這是維持和平必付的代價?後來有機會訪查其他族群的親屬結構,但知道得越多疑惑越深。譬如,為什麼母系社會只見於平原,而父系社會只見於山地?這是否偶然?若是非偶然,用什麼定律來證明其必然性?又,母系大家族和年齡組織為主軸的社會盛行於台灣平原地區,但這種組合卻不見於島外的任何族群,為什麼?這很可能是台灣平原族群的獨創,那麼原來的面貌又是如何?有無數個「為什麼?」始終在腦際盤旋,所目所睹無一不使我深思,深感台灣田野資源的豐富,實是取之無盡的寶藏。
人類學者雖然認為「系譜方法」是在田野採集親屬資料最佳的工具,但不認為「系譜空間」是在研究室裡值得作進一步探討的範疇,無人相信其中充滿 DNA 般的訊息,足以成為親屬研究的重心。在沒有多少資料可引為奧援的情形下,我只好自己來尋覓自己所提問題的答案。親屬的 DNA 將呈顯何種面貌?親屬理論應該如何重建?那把解謎的密鑰,到底在那裡?這些都成為近四十年來我日以繼夜,夢裡也不忘追求的中心課題。在多年的暗中摸索,偶遇志同者交換心得,深入討論,嘗試突破。在多項試行錯誤後,我們終於發現「數學」是一把能打開其門的鑰匙,一點一滴抽出來的訊息淬礪成「親屬數學」這一門新科學。至於其他問題,如在腦中埋著一些火種,時而冒煙,但始終尋找不到解決的鑰匙。
解決這些問題的線索來自古生物學的「島嶼律」。該律認為動物體型如象般的巨大化,或如老鼠般的小型化,都與生態環境,如敵獸的存在等孜孜相關。同時維持巨大化或小型化的體型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故在無敵獸的島嶼上,象的體型自然會恢復到原來的山豬般大小,老鼠則如兔子般大小。若容許我們把巨大化的觀念引進於社會科學,來看家族、親屬團體、部落的規模大小問題,而從「島嶼律」的觀點來解釋,則雅美族的維護小家庭莫非是社會祥和的象徵?一千乃至二千的人口是否維持一個民族文化的最低界線?因此島嶼不容許居民玩戰爭遊戲,分成敵我陣營而互相攻殺?雅美族認為死亡是兇惡的象徵,是最忌諱的。整個文化朝避兇招祥的方向設計,上面所提的種種疑難,從這個觀點是否可以化解?
回顧這一段追索、探討的過程中,對於人類學、對於台灣這一片土地,我也逐漸有了一些更深入的認識:
第一、人類學雖然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也有一些資料的累積,但其理論的建構,只能說才就緒,無法回答一切的質疑或解惑。換個角度來看,人類學,事實上,是一門才剛起步的「新科學」。現階段,田野工作仍是最重要的,極需更多的參與、收集與記錄,來促進理論的建構。同時,學者與異文化接觸的過程中,可觸發出無數個「為什麼?」,進而探索這些疑難,追求其所以然,深思如何來建構知識體系。如此,田野與研究工作,一如「身與影」,是不可分離的。因此對於年青一輩的研究者,我想提出的忠告是「深入田野,體驗異文化」,這實是人類學的原點,切不可遺忘的。同時,打開疑難的鑰匙,如上面諸例所示,先進科學常提供線索,是故,學者具備幾門學科的素養,或者,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人來參加調查研究,這是對人類學的生長,尤其理論建構,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假如把文化當作海流來看,台灣是海流匯集的地方,所以食物豐富,有眾多的魚類群聚,是一個難得的大漁場。在這麼一個小島上,若連平埔族也算在內,加上近四百年前來台的漢族,及已遁跡的荷蘭、西班牙和日本諸族群,已經有超過二十個以上持有不同文化的族群居住或居住過。台灣不是一個平坦的島嶼,拜高山林立,地理複雜之賜,因此能保存這許多異質性極高的文化或族群。再從世界地理的角度來看,台灣正處於東西方交會的十字路口上,文化的發展與變遷過程也格外具有特色,引人注目───總之,真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寶島!
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見得到人類學者的蹤影,在默默從事田野工作,但所收集的資料無論如何豐富,卻都有時間上的限制,這使得人類學者深深感覺,美中有所不足。這就是說,所獲得的資料都是同時性的,然而,文化有流動性或變易性,但相關的異時性資料卻極難或無法獲得。台灣的田野資料,我們擁有一百年前,鳥居龍藏和伊能嘉矩兩人所做的田野調查記錄,其難得與重要性,也就不言可喻了。
萬物在流轉,社會、文化也沒有例外,瞭解變遷的軌跡也就是瞭解文化時所不可或缺的。百年前的台灣到底是什麼模樣?漢人和原住民的關係又是如何?平地和山地有什麼樣的差異?前人所留下來的文獻資料雖然有一些,但說到寬廣與正確性,恐怕還是不能不先想到,這二位受過人類學訓練的年輕學人所留下的田野調查記錄。百年來,台灣社會變得太多、太快速。許多事物、制度,到今天都已消逝不見了。但在鳥居龍藏與伊能嘉矩的時代,卻是活生生的存在著,他們兩人親自去接觸,正確地記錄下來。透過這些文獻,我們可以和百年前的台灣見面,但想要與當時的人們同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百年前的聚落,該當今天的何地?當年所走的路,今何在?今天這些文獻終於由勘查舊聚落、古道有深厚造詣的學人譯成中文,能與讀者見面,實是一件喜訊!
楊南郡先生是台大登山社的指導老師,熱愛登山活動,其熱情至今不變。楊先生不止於登高峰而滿足,他注意到通往山地的道路已有很大的變遷,早期地圖所記載的山路何在?許多聚落已遷移,其舊址如何訪查?楊先生旺盛的知識欲,使他走上孤獨的知識探索之旅。新知識的累積,自然形成一門學問。進入山地的先民,如何利用台灣特有的地勢,建構交通網或交易網?部落的遷移或民族的移動,是否恣意的?或者有定律可循?交通的難易對族群的形成無不影響,真正要了解台灣複雜的族群配置與其互動,交通是不可或缺的知識之一。譬如,鹽是不可缺乏的,山區的住民在異族環繞下,如何建立交易的關道?誰來扮演仲介人?占據交通的要津是福是禍?是四方八達或是四面受敵?跋涉峻嶮偶有新發現,在今天被認為人類不能居住的高嶺發現部落舊址,又做何種解釋?脆弱的人類學理論立刻崩潰改寫,新解釋跟從而來,這是顯而易見的。
台灣在異文化的錯綜交織下,使田野充滿機鋒,處處都是寶藏所在。許多事物都為人帶來驚喜、帶來啟發、帶來震撼。任何的疑難,不要輕易打發掉,疑惑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原動力,是通往真理的羊腸小道,這是現象之後必有理則存在之故。最後,謹以「以知為知,以不知為不知」這一句千古箴言來勉勵讀者。學問不論大小,只問深淺。學問與知識已飽和者無緣,知識的女神只對承認自己知識有限,有疑惑者招手。面對未知的世界,勇敢地踏出一步,自然可以走出一條路來───路是人走出來的。楊南郡先生是開路的先鋒,勇者的典範,台灣充滿寶藏的最好見證人。
〈總序〉
台灣的田野是無盡的寶藏
劉斌雄(人類學暨民族學家)
我從小就存疑;人為什麼活?人為什麼打仗?後來走上人類學的道路,與期望解開這些疑問,相信是有一些關係的。一九五七年,我首次參加蘭嶼的民族學調查,從事雅美族的系譜採錄工作。我對所目睹、所接觸的現象,有強烈的想知所以然的欲望。譬如說,對系譜一面記錄一面問,「系譜空間」是什麼?其中所蘊藏的豐富資訊,如何開採而取用?雅美人居住的房屋,其大小有顯著的差異,但居住者所組織的都是核心家庭,為什麼其他類型都不見?有什麼定律可以證明大家庭之不可或無法存在...